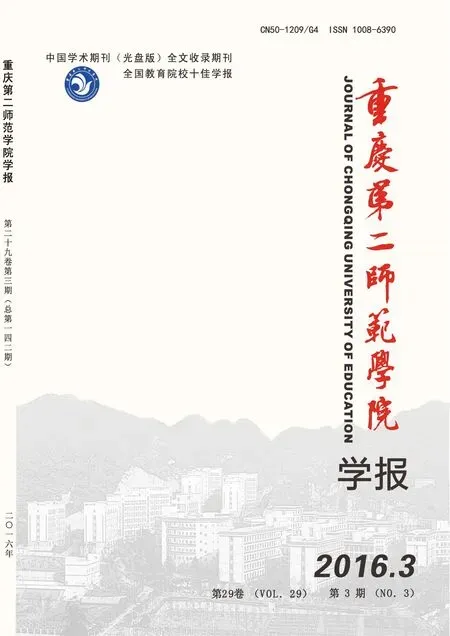基于英汉互译过程的改写特质研究
2016-03-29谢君平
谢君平
(莆田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莆田 351200)
基于英汉互译过程的改写特质研究
谢君平
(莆田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莆田 351200)
摘要:英语和汉语作为全球非常重要的两种语言,其互译是不可避免的交流活动。由于两种语言分属印欧语系与汉藏语系,存在许多差异,因此,在互译时须注意改写的不同特质。本文从英汉语言结构维度的差异性、英汉情态意义的不同建构以及英汉文化的多样性这三个方面分析了英汉互译过程中改写的特质,并关注二者在语言结构、情态意义以及多样性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
关键词:英汉互译;改写;特质
一、引言
英语与汉语存在明显的差异,英语突显的是“形合”,而汉语则偏重于阐述“意合”。在传递信息时,英语与汉语均有各自个性化的应对策略,并充分体现在英汉的互译过程中[1]。同时,“形合”式的英语和“意合”式的汉语在进行互译时,并非是对等的翻译,原因在于英语偏重于形态逻辑的结构,而汉语则更关注的是具体的信息内容,如此便会出现翻译“增生”的情况,也就出现了英汉互译的改写现象,而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直译。显然,要能够顺利而又准确地实现英语和汉语之间的互译,就必须做好“衔接”的工作。要注意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互译,既要考虑到两种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素,又要考虑到接受主体的异化现象,凸显出鲜明的改写特质。本文试从英汉语言结构维度的差异性、英汉情态意义的不同建构以及英汉文化的多样性这三个方面来分析英汉互译过程中改写的特质,并关注二者在语言结构、情态意义以及多样性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
二、英汉语言结构维度的差异性
我国最早提出“翻译即改写”观点的翻译家是思果。在他看来,翻译属于改写范畴,文字好似桎梏,必须打破这个桎梏才能够获得新生[2]。具体翻译时,须以译意为主,寻求中文对等的表达模式,同时确定相匹配的情感指向;在必要的时候还需进行一定的改写甚至是重写,从而让目的语读者明白译者的用意所在。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英汉语言结构维度上的差异。就语言发生学与类型学的层面而言,英语与汉语分别归类为印欧语系与汉藏语系。其中,汉语属于音足型与语义型的语言类型,而英语属于形足型与形态型的语言类型。就语法特点的层面分析,汉语语法显现出柔性与隐匿的特点,英语语法则为刚性与外显化的。就宏观语序的层面来看,汉语更关注音韵律与逻辑律,英语则偏重于贴近律和形态律。就组织话语的法则层面而言,汉语偏向于意合,英语则更倾向于形合。[3]根据语言心理的视角分析,汉语注重悟性,关注总体思维与主体理念;英语突出的是理性,关注个体的价值与客体理念。就篇章修辞而言,汉语在篇首即象征性地为全文的中心做好了铺垫,突出体裁性,即不同的体裁对应着各自的文风;英语则更倾向于在开头彰显全文的主旨或目的,同时界定全文的展演模式,更倾向于通过一定的技巧吸引读者的眼球。就交际所采用的语用方略角度而言,汉语在表现文明礼仪时,体现出的是贬损自我褒扬他人的特点;英语则更偏好于采用愉悦、迎合对方的表达方略[4]。正是上述的种种区别,给互译带来了诸多困难。因此,要想达到顺利交际的目的,必须加以一定的改写。
例1He is thirsty for freedom.
译:他渴望自由。
例2接到来信,大喜过望。
译:I am too thrilled to have received your letter.
在例1原句中“thirsty”表示的中文含义是“口渴的”,若整句直译为“他口渴自由”显然不通。同时英语中“thirsty”在表示“渴望”含义时,须用词组“be thirsty for”来加以表达,尤其是介词“for”是不可省却的,这是英语固定化的语言结构。而翻译成汉语时,若要翻译出介词的含义,必须对原句的语序加以调整,即改写翻译成“他对于自由非常渴望”,如果再精练些,则可改写翻译成“他渴望自由”,而不能对等翻译成“他渴望对于自由”。这是汉语结构上的表达习惯。例2原文为汉语,该句是一种省略性的语言工整化的结构,前后均为4个字,省略了接到来信与大喜过望的主语“我”以及来信的定语“你的”。但在翻译时,必须将上述的省略成分加以补足,同时也将接到来信与大喜过望的意思整合成“too…to”的句式结构。此外,原文汉语更注重逻辑性,更符合事理的自然发展过程,而译文则更偏向于形合,弱化了中文“因为收到对方来信而感到极其喜悦”的先后顺序的语义,而把“大喜过望”的语义放置于“接到来信”语义之前,当然是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改写翻译,目的是使译语更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反之,如果按照字面翻译成“Received letter,big happy has already passed respect”,那么就是Chinglish(中国式英语)意味十足的翻译,显然,这样的翻译是失败的。
三、英汉情态意义的不同建构
(一)英汉情态意义的理论分析
韩礼德提出功能语言学理论,指出语言凸显出概念、人际与语篇等不同的三大纯理功能。其中,人际功能指的是人们通过语言媒介的方式和他人进行交往,建立并维持一定的社会关联性,并对他人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表达出对客观世界的观点。情态是达成人际功能的核心方式,是发言主体对自己所说的命题在成功性与有效性维度所展开的推断,或基于命令中要求对方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与义务,或基于提议的内容来表述个体的意愿。情态意义一般通过情态动词、情态副词与谓语的扩展式等几个主要的部分来共同加以表示。此外,韩礼德还提出了有关情态隐喻概念,将“I think it is so.”视为相同语义的“It is probably so.”的隐喻变体。在功能语言学家看来,情态能够基于主观与客观两个不同的视角来加以表述,把情态取向细化成四类情形,即显性主观、隐性主观、显性客观与隐性客观。其中,显性取向大多数的表达结构主要是短句,如“I think Mary knows.”或者是“It is likely that Mary knows.”等等。至于隐性取向的表述主要包括情态动词、情态副词与谓语扩展式(主要有“be supposed to”、“can”与“probably”等)。此外,基于情态的表述及其界定程度,把情态大体划分成高级、中级与低级共三级量值,也就是把情态的级别区分量化处理,更为细致地对情态进行量化研究。
从类别的范围而言,“情态”属于跨语言的普遍性存在。英汉两类语言均附有相应的语言资源,从而表达出丰富而又多元化的情态意义。在英语中,通常使用的情态动词包括“may,will,need,can,must与should”等。朱德熙界定的对象是汉语言体系内的27个情态助动词,即“可以、能、可能、要、会、应该”等。Palmer把英语情态动词大体上划分成3种,也就是动力情态、认识情态与道义情态等。相类似地,他也把汉语情态划分成相一致的类别。
情态会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重要的意义,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情态是听话者基于言语维度所感受到的态度情况,包括语气的轻重、强弱与缓急等。因而,情态意义的翻译必须为“偏重于感染型的”,而非“偏重于内容型的”,翻译者必须根据情态意义所具有的人际功能对等情况,灵活地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就句式与语义维度上加以相关的调整,从而确保情态的表达与译语的文化语境及其行文习惯相吻合,基于情态意义的原本含义完成翻译任务。
可见,英汉情态方面的意义存在着分歧,由于受到不同国家习惯性语言表述方式的影响,即使在表述相同的情态意义时,无论是具体的语词还是表述方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化现象[5]。因此,在翻译时须对情态变量进行一定的改写,从而使得原文与译文的表述习惯相匹配。
(二)情态值(value)的改写
所谓的情态值(又名情态级别)在体系功能语言学情态体系内属于情态变量,关键表现的是情态意义及其程度。韩礼德把情态值区分成高、中、低不同等级的数值,分别代表三类情态意义。在界定情态定义时,他引入极性(polarity)的概念,指的是肯定与否定性的表达,同时据此认定情态为处于肯定与否定极性内部的意义[6]。因为英汉语言在思维与表达方面的差异性,在挑选情态量的数值时亦存在区别。
例3某日,外国教师出题,检测学生们用洋文写作的水平。
译:Some day,to know how well the students could write in English,he set them all essay.
原文所采用的是肯定极性情态方式,以散句形态为主,没有情态性的表达,然而句子在停顿时却隐藏了有关人际层面的意义[7]。译文则通过对原句的结构加以调整,使其显得紧凑了些,同时也强调了情态意义,把原句中的“检测……水平”翻译成“could”,包含着潜藏性的主观化的情态语义,进而深层次地体现出师生内部的权力式的社交关联性,使得译文与英语的表达相吻合。
(三)情态取向(orientation)的改写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内容,把情态取向细化成四类:显性主观、显性客观、隐性主观、隐性客观[8]。情态取向所强调的是发言人表达情态意义的多元化维度,包括视角的多样性(主观或客观)与方式的多样性(显性或隐性),从而更为恰当地与发言人的职业或观念以及倾听者的态度相匹配,顺利地完成对话社交过程。
例4Lucy is supposed to pay for the bill of party, however, she loses her promise in the end.
译:露西原本是这次聚会的东道主,然而她失信了。
在原句中“is supposed to”表述的意思是一种义务情态,属于隐性客观的情态取向范畴,但汉语翻译之后,将其翻译成“是……的”,即改写成显性客观的情态取向,强调了露西所应该承担“东道主”的责任义务,而这与汉语的表达方式是一致的。
四、英汉文化的多样性
(一)互译过程中的文化不对等现象
由于西方语言更注重语言的对等性,许多西方学者都提出了对等方面的译论,比如,威尔斯的“受者等值”,奈达的“动态对等”、“等效翻译”以及卡特福德的“功能等值”等。然而西方语言和汉语言存在更多的现象是“异”超过了“同”,仅有少部分才可以进行对等,因而对等译论只适用于少数的互译现象,而至少一半以上的情况均得采用异化或归化策略加以处理,才能合理地解决文化不对等的互译问题。无论是郭沫若的“创作论”还是朱光潜的“艺术论”,都是归化策略的变式方法,本质均指的是翻译中的改写论。这种文化的不对等现象也揭示出不同语言环境下文化的缺位情况。郭建中指出,与改写或是重写相关的理念与方法都应该始终贯穿于翻译的过程中,须基于不同语言及其文化层面上进行落实[9]。
具体而言,应显现出异文化所应该具有的功效,突出跨文化的国际理念,摈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积极汲取他国的文化精华部分。事实上,若国外文化和本国文化相差无几,那么也无须翻译了。异化在这里指的是翻译的具体方法与国外文化的语言特征相吻合,有意识地汲取外来语的表达式,基本上改写的成分不算多。比如“时间就是金钱”的短语源自英语中的“Time is money”。归化则指的是翻译时更注重译文读者的文化语言传统,在翻译时尽量地将源语改写为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比如,傅东华在翻译《飘》时,即将书中的人名与地名进行了中国化的处理,体现出中国化的文化格局。这种基于文化层面上的改写是常态化的,也是翻译过程中必需的一种变通的处置方式,能够减轻解读语码过程中所产生的认知负担,从而获得真实有效的交流效果,最大化地完成语用功能的对等以及文化层面上的过渡。
例5It says in the Bible: Thou shalt not steal.
原译:基督教圣经上说:不许偷窃。
改译:《圣经》有云:勿偷窃。
此句关键是原文冒号之前句子的翻译,涉及了文化层面的内涵。译者是否需要将句子中的基督教文化加以增译?一般情况下,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译者应该适当加以拓展,且若处于20世纪初环境下也有诠释的必要性,然而在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众多读者都已经明白《圣经》与基督教的关联,因此无须增译。另外,就文体而言,“thou shalt”属于古英语类型,并非现代英语的规范化表述,这就提醒译者,在翻译成中文时,最好选择与之相吻合的文体。原译“不许偷窃”是现代文体,而改译则将“不许”用了“勿”字,更加凝练,也有古语的色彩,同时为了使得全句的语体色彩相一致,改译也使用了“有云”的表达方式,从而使得改译更具有古文化的特色,与原文的表达方式相吻合。最后,汉英的标点符号也有文化上的细微差异。英文表述著作名称时一般会把首字母改写成大写的方式,而中文则采用的是书名号的方式,因此,改译明显优于原译,更符合中文规范化的表达习惯。原译就内容层面而言,存在着显著错误或是不尽如人意的成分,应对原译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从而使其更符合目的语文化体系的表达习惯。
正是英汉语言文化体系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从而决定了翻译的改写特质。从实际情况来看,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也就是说,二者天生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均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同时也没有和具体的语言文化相背离。也就是说,英汉语言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显现出英汉文化之间的巨大区别。
早在20世纪 80年代,翻译领域便出现了“文化转向”情况,翻译的定义已不再局限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单纯性改变,它既是不同形式之间的转化,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转化”、“诠释”与“再现”。显然,这样的转化、诠释与再现是基于语言媒介完成的。此类转化能够让人们感受到翻译和其他交流渠道内在的有机关联性,同时把翻译看作一种写作实践,贯穿全部文化表现的各类张力都囊括其中。此外,文化翻译学派的先驱勒弗维尔提出改写理论,同时指出不同的翻译文本,诸如传记、电影、读者指南、编选文集、文学批评、文学史、戏剧与编纂历史等相同,是改写文本的一类模式,是构建另一种文本形象的新型载体,均是对文本的一类改写,所谓的改写即“撰纵”(manipulation)。
(二)审美规范性文化的分野
英汉审美文化也突显出差异性。就语言的纯表征而言,英语的行文组织结构要高于汉语,在语句的连接时均呈现出规范化的形式之美;汉语的行文则体现出错落有致的美感,即短句与长句错杂,整句与散句相间,不同语句内部存在着连接的成分。因此,英汉互译时须留意到审美文化上的分野现象,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改写。基于“简单化”的理据,进行一定量化的语言表征拓展,尽可能使用高频率的词汇或表达式来展开有效的信息传递,注重文化审美的多样性特点。
例6As far as scan can arrive, those tourists feast their eyes on a vastness of limitless view that emerges in a abundant of colorful verdant exuberance, euphonious tweet, pervading perfume, undulate wave, cataract sprays, bent gurgitation, plowland crisscross and verily in vitality and variety.
译:极目远眺,游客们能够尽情地饱览风光无限的景色,花团锦簇,生机盎然,啁啾啼啭,兰薰桂馥,微波粼粼,龙翔凤翥,层峦叠嶂,阡陌纵横,一派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美景。
原文句子在描述风景时采用了押头韵(“pervading, perfume, plowland”)与尾韵(“vitality and variety”)的技巧,即具有押韵的行文美感,这样的表达是与描述的风景对象相吻合的,二者相得益彰。译文虽然没有沿袭原文的表达特点,然而也采用了和汉语表达相匹配的特色,即大量地将原文的词组改写成四字成语的模式,从而让译文突显出工整之美,完全能和原作相媲美,同时也非常符合汉语文化的审美接受心理。
例7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译: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 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原文是汉语中的一句俗语,前后皆五个字,对仗工整,同时也包含了典故,体现出汉语的结构美与意蕴美。译文英语则通过复合长句将原文整合在一起,体现出英语的形式之美,同时,为了更好地诠释原文中“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译文还特意添加了短语“the master mind”,这样貌似留尾巴式的表达与西方文化的习惯性表达方式相吻合。
五、结语
英汉互译的改写特质兼有客观与主观的原因,客观的原因在于英汉语言的结构不同,而主观的原因在于两种文化体现完全不同。因而,翻译改写也相应地有潜意识与有意识两类改写。传统的翻译理论更注重对原文的忠实性,不允许出现改写原文的现象,其实,翻译改写情况并不鲜见,而且是必要的处理。在许多环境下,忠实原作难以实现,尤其是跨文化交流无法实现。根据具体情况与翻译目的,适当地改写原文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由于英汉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因而,改写是英汉互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不仅仅是文学翻译,也是非文学文本翻译的本质属性与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郭建中.汉英/英汉翻译:理念与方法(上)[J].上海翻译,2005(1):2-8.
[2]马秉义.英汉篇章修辞比较[M]//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3]韩加明.翻译研究学派的发展[J].中国翻译,1996(5):77-79.
[4]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4.
[5]胡文仲.超越文化的屏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6]黄跃文.翻译教学应重视佳译欣赏[J].教育导刊,2004(10):38-40.
[7]连淑能.汉英对比研究(增订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8]王宁.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J].中国翻译,2005(6):5-9.
[9]吕俊.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2(5):48-54.
[责任编辑亦筱]
收稿日期:2015-11-20
作者简介:谢君平(1965-),女,福建莆田人,高级讲师,研究方向:笔译和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6)03-007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