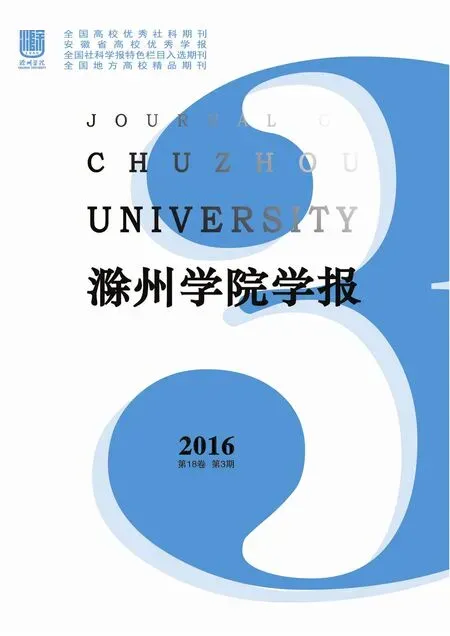朱湘诗歌翻译的文化取向及翻译策略
——以《老舟子行》为例
2016-03-28余秋兰
余秋兰,张 文
朱湘诗歌翻译的文化取向及翻译策略
——以《老舟子行》为例
余秋兰,张文
摘要:朱湘在外国诗歌翻译中通过灵活运用“亦归亦异”的翻译策略,完美兼顾了中西诗歌文化的特质。他的《老舟子行》译本就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这一特色。一方面,为了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他以异化为主,大胆将西诗中丰富的形式特征,如音韵、格律、节奏、诗行等,移植到译文中,使其译诗充满音乐美和形式美。另一方面,在语言表达和文化传递方面,遵循了以中国文化为取向的归化策略,对原诗意象往往进行创作性改写,让译文接近读者,展现了其传承和弘扬我国古典文学精神的立场。
关键词:朱湘译诗;《老舟子行》;异化;归化
朱湘(1904-1933)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他的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但他对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做出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为了“复兴中国诗学”而大量翻译外国诗歌,所付出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朱湘先后发表译诗120余首,出版两部译诗集《路曼尼亚民歌一斑》和《番石榴集》。虽然这个数量在中国翻译史上不算最多,但与其所处时代的同仁相比,他的译诗不仅涉及所译国度和诗人数量众多、年代久远,而且范围广、体裁多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通过研读朱湘译诗的相关研究发现,学界多数从传统翻译学理论视角对他的译作加以审视。笔者认为,在当代国际翻译理论的“文化学转向”的大潮流下,从翻译的“文化取向”考察朱湘诗歌翻译,是一项值得探索的活动,因为译者的文化取向制约着翻译策略的选择:以源语文化为主,主要采用归化策略;以目的语文化为主,则多采用异化策略。
《老舟子行》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传世佳作,也是朱湘所有译诗中最长的一篇。原诗结构简洁,音律优美,寓意深刻,充满瑰丽想象的奇幻色彩。朱湘在充分把握原作精神的前提下,灵活运用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手法,来传达原诗的整体意境,体现了他在翻译中对中西诗歌特质的兼顾并举。本文以此译诗为切入口,探讨朱湘“亦归亦异”的翻译策略与其背后的翻译主张和文化诉求的密切关系,积极拓展其译作研究的领域。
一、以异化为主移植原诗的形式
文化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不单是语言之间的信息转换过程,也是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在翻译中,译者遵循的是源语文化取向还是目的语文化取向,会形成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即异化和归化。异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相当于源语言的表达方式和形式,将原作内容、风格、思想、形象、意境、感情等再现出来,将读者引向源语的文化氛围当中;归化是对源语语言文化进行本土化的处理,用目的语文化表达原作特征,将翻译后的语言文化纳入目的语读者的知识范畴内。[1]这两种翻译策略看似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朱湘在其诗歌翻译中,有效地结合了两者各自的优点,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精炼优美、诗味浓郁、融汇中西的佳译。
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朱湘在《说译诗》一文中明确指出:他译诗的目的是为了把西方的真诗介绍过来,同我国古代诗学昌明时代的佳作进行参考研究,从而悟出并铲除我国诗中芜蔓的部分,培植广大菁华的部分[2]。简言之,他译诗的目的就是通过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为中国“诗歌复兴”开辟一条新路。因此,朱湘通过翻译的途径,吸收西方诗学的新质,将西方诗歌中优美的音韵、整齐的格律和极强的节奏,以“异化”的翻译策略横向移植到他的译诗中,使其译诗“洋味儿”十足。
节奏、音韵、音步、抑扬、诗行是构成西方诗歌的外在形式,也是西方格律诗的基本要素。因此,它们也是诗歌翻译的要点。[3]作为新格律派译诗的大力践行者,朱湘在译诗时多数采用整齐的格律体。原诗是格律诗,一般都照样译为格律诗,并尽可能地注意每行的节拍,尽量保持原诗的押韵方式,同时还往往限制译文中每行的字数。《番石榴集》中的每首译诗几乎都是协韵,有音节,每行的字数也是相对固定。像《老舟子行》这样的长诗,也基本上照原诗节的单行押韵。
《老舟子行》原诗采用古歌谣体,共七章,每章由十几个诗节组成,大多数诗节一般是四行结构,极少数超过四行。单行为八音节,节奏基本为抑扬格四音步;双行为六音节,节奏为抑扬格三音步。韵式一般是双行押脚韵,同时大量使用内韵和头韵,形成圆润铿锵、回环宛曲的音律,极富“建筑美”和“音乐美”。朱湘为了再现原诗的这些艺术特点,就尽可能模仿原诗的节奏和韵式,直接将原诗的形式移植到他的译文。下面以《老舟子行》第一章里其中一个诗节为例分析:
The ice/ was here/, the ice/ was there,
a
The ice/ was all/ a/round; /∂'raund/
b
It cracked/ and growled/, and roared/ and howled,
c
Like nois/es in /a swound/. /swaund/
b
航过/一程/还是/冰岛。
a
更航行/晶岭/当前;/qian/
b
它们/毕剥/,喧豗/,澎湃,
c
如晕时/声震/耳边。[4]25/bian/
b
在韵律上,译诗和原作基本上都用同一种韵式,即abcb式的交韵。译诗的双行分别用“前”和“边”押了脚韵,来对应原诗的脚韵“around” 和“swound”。在音顿上,译诗的节奏遵循原文,节拍感很强,基本实现了以音顿代音步的规范,多以二音顿和三音顿为主。各行字数整齐,译诗的单行用八个汉字来代替对应诗行的四音步,双行为七个汉字代替对应诗行的三音步。从中可以看出朱湘看重译诗的外在形式,注重译诗的格律化和规范化。同时译文还采用双声“毕剥”“澎湃”(相当于英诗的头韵),创造性将船破冰面发出的碎裂声(crack)、隆隆声(growl)、咆哮(roar)、嚎叫(howl)绘声绘色的传达出来。可见,朱湘的译本既着力再现了原诗的韵律节奏,又颇具中国古典诗歌的音律之美,绘声绘色,堪称佳译。这样的例子在其他译作中比比皆是,在此,笔者不再逐一列举。
综上所述,朱湘在译诗过程中,强调了格律对于诗的重要性。虽然译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生涩之处,如上文中使用了生僻词语“喧豗”,但译文充满了音节的音乐感、字句诗行的匀称美和建筑美;既吻合英诗严格的音律和整饬的形式,又保留了旧词韵律节奏的灵魂。[5]从而创造了规整的诗风,纠正了自由诗体过于散漫的弊端。在中国新诗形式的发展上,颇有建树。
二、以归化为主翻译原诗的意象
任何文学翻译,都存在创造性叛逆的现象。诗歌翻译尤其如此。作为文学的最高形式,诗歌是韵律、修辞、意象和意义的结合体,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字里行间往往承载着独特的源语文化因素。因此,在所有文学体裁的翻译中,诗歌翻译最具有挑战性和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译性,也是最让人望而止步的。可见,诗歌的特性使得译者不得不进行创造性甚至叛逆性的翻译,否则,就很难产出让目的语读者接受并欣赏的佳译。
朱湘认为,在译诗者的手中,原诗只能算作原料。译诗者如果认为目的语有比源语更好的材料,能将原诗的意境更好地传达出来,或者原诗虽好,但移植到目的语会出现水土不服,那么,译者可以应用创作者的自由,对原材料进行合理的归化处理,将原诗的意境更深刻地嵌入目的语读者的想象中。[6]为了突出意境,朱湘提出了诗歌翻译的创作论。主张在异化的基础上,合理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让目的语读者不仅可以接受,还可以欣赏原作。
受中国传统诗学中的“立意取象”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朱湘十分重视诗歌翻译的“意象”和“意境”。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中西诗歌存在着大量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象。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具有鲜明的主观情思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诗人往往通过寥寥几行,将思想感情具体化、个性化的同时,还创设出新颖奇特的艺术形象或意境,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7]深受中国传统诗学的影响,朱湘认为,为了将原诗的意境整体传达出来,译者在实践中做些枝节上的变动是可取的。因此,有人认为朱湘的翻译手法有时接近创作。
在意象塑造方面,由于遵循的是目的语文化取向,朱湘在翻译时会通过增添、替代、删除等手法改写原诗意象。他的译文增添了不少丰富生动的形象,切合汉诗中文学情景盛大丰富的传统。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突出事物特征,将客观景象与艺术形象融合在一起。我们以《老舟子行》的其中两节原诗和译文对照来看:
The Sun came up upon the left,
Out of the sea came he!
And he shone bright, and on the right
Went down into the sea.
日头在水左方升上,
过苍苍似是孤帆。
他待长庚出来时候
向右方掷下金丸。[4]13
THE Sun now rose upon the right:
Out of the sea came he,
Still hid in mist, and on the left
Went down into the sea.
日头自水右方升上,
隔水瞧好似银丸,
它落寞的奔驰一日,
在左方落下波澜。[4]35
这两个诗节描写舟子射杀信天翁前后的海上日出日落的景观。用词简单常见,第二、四诗行分别重复。两句简单的诗行“Out of the sea came he”和“Went down into the sea”,朱湘通过添加 “苍苍”“孤帆”“金丸”“银丸”等意象,将原诗中的隐含的形象以逼真的画面呈现出来:一只孤帆行驶在茫无边际的大海上,天气晴朗时海上日出发出耀眼的金光;有雾笼罩时则发出宛如月色的银光。这种将译诗向汉语的辞采之美归化的策略,既避免直译带来的苍白干枯,又赋予译诗以丰腴新颖的艺术想象力和浓郁的诗味。用中国调译外国意,展现了朱湘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对传统文学的倚重及传承古典文学精神的立场。
在遣词造句方面,朱湘常常对原诗的意象进行替代性改写,从而使原诗向汉语文化靠拢。比如,当老舟子拦住一位参加喜宴的宾客,欲向其诉说海上经历时,急于离开的宾客不得不说:“站开!放手,羊须老汉!”(“Hold off! Unhand me, grey-beard loon!”[4]9) Loon 在英语中的意思是“懒人;蠢人”,含有责备、谩骂的语气,属于贬义词。朱湘将其译为“羊须老汉”,弱化了原诗中贬损的语气,迎合了我国传统文化尊敬长者的价值取向。
柯勒律治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最具有宗教气质的诗人。从思想寓意上看,《老舟子行》包含着浓厚的神秘宗教色彩和丰富的宗教内涵。因此,原诗中出现许多基督教文化词汇,如 God(上帝)、 heaven(天堂)、Hell(地狱)、 Christ(基督)、Christian (基督徒;基督教的)、kirk(教堂)、angel (天使)等。但是在译文中,这些基督教文化因素大有被禅化意味。它们或删除,或替代,只有极少数采用直译的方法处理。下面以含有heaven一词的原诗句及其译文对比为例:
(1)Heaven’s mother sends us grace 天哪,那多么骇人![4]61
(2)I looked to heaven and tried to pray 仰对青天我想祷告[4]81
(3)She sent the gentle sleep fromHeaven它带来了我甜的疲倦[4]95
(4)That makethe Heaven be Mute. 九天之内悄然谛听[4]113
根据基督教传统,heaven主要指的是上帝、天使居住的地方和好人死后去的地方,译为“天堂”。显而易见,该词具有西方基督教的文化内涵[8],但在伊斯兰国家和信奉儒道的中国却没有类似的文化内涵。佛教中也没有天堂一说。在以上四句诗行中,除了(3)句中采用删除的翻译策略,朱湘将(1)(2)(4)三句中的heaven分别译为天、青天和九天,舍弃了该词原有的宗教文化色彩,使原诗向中国文化靠拢。因为中华传统信仰是敬天法祖,即敬畏上天,尊崇祖先。因此,中国人的心目中往往只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和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爷。相信天生万物,天行有道。敬天是一种人文信仰而非宗教信仰,体现了朱湘在语言表达和文化传替方面,遵循的是以中国文化为取向的翻译主张。
三、结语
《老舟子行》是朱湘翻译的最长的一首外文叙事诗,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诗歌翻译理念和文化取向。一方面,译诗大胆移植西方诗学中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出诗歌的节奏韵律,突显其形式上的美,留下了源语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运用中国传统美学在意象等内在方面的优势,采用中国古典诗词的辞采美、如诗如画般的形象结构,既增添译诗的意蕴美,又传承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人读起来赏心悦目。这种亦归亦异的的翻译策略使其译诗做到了形似和神似的统一。朱湘也正是通过这种对外国诗歌多方面的“异化”处理,最终以“归化”中国古典诗学为目的的方式,实现他复兴“中国诗学”的主张。
当然,朱湘的译诗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传统翻译批评观的审视下,有人认为朱湘对形式和简练的过分重视,过度违反了目的语的可接性。也有人认为朱湘的译诗肆意发挥,脱离原诗,有的地方词不达意,如朱湘把白朗宁《异域乡思》中 pear-tree(梨花)创造性地翻译成“夭桃”而引发与王宗璠一场笔墨之争。但鉴于朱湘所在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不应求全责备,毕竟他所处的五四时期白话新诗的发展还不成熟。能在格律的制约下传达原作的神韵,向读者贡献了众多精炼而又优美的佳译,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成熟的诗人和翻译家。因此,朱湘在近代诗歌翻译史上和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周志平.基于文化取向的翻译异化与归化探讨[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3):86-88.
[2]朱湘译.朱湘译诗集[M]. 洪振国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337.
[3]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305.
[4](英)柯勒律治.老舟子行[M].朱湘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5]吴赟. 翻译·构建·影响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1-73.
[6]朱湘.说译诗[A].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C].海岸选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50.
[7]曹帅.朱湘译诗中的异化与归化研究现象[D].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1.
[8]贾德江.论文化因素对英汉翻译的影响[J].外语教学,2000(4):56-60.
责任编辑:李应青
Zhu Xiang's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His Translation Strategy——Taking His Version of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as an Example
Yu Qiulan, Zhang Wen
Abstract:As Zhu Xiang flexibly applied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as his majo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his translation of foreign poetry, his Chinese versions represented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he good qualit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ry. His version of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can serve as a typical model for this feature. On one hand, to introduce the merits of foreign poetry, foreignization was widely used to transplant their rich poetic forms, like cadence, stanza, rhythm, line, etc. into his translation to make his versions full of musical and formal charm.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he firmly took Chinese culture as his orientation when dealing with the expression of words and cultures, he mainly domesticated the images in foreign poetry through creative rewriting, making his version closer to the reader and thus showing his inheritance and promoting our classic literature.
Key words:Zhu Xiang's poetic translation;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794(2016)03-0057-04
作者简介:余秋兰,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翻译;张文,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安徽 安庆 246011)。
基金项目:教育部英语国家级特色专业项目(TS12154);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6A0561);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AHSKY2015D122)
收稿日期:2016-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