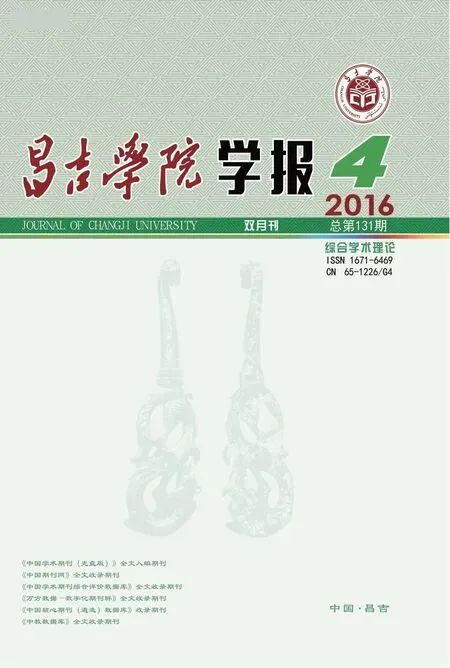《父与子》的美学观相
2016-03-28马晓玖
马晓玖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父与子》的美学观相
马晓玖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父与子》是德国幽默大师埃·奥·卜劳恩创作的一部连环漫画集。以父子间的情感点滴为创作原料,《父与子》为读者讲述了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本文通过对《父与子》的解读,从中分析作者的美学构想及其作品的美学价值。
《父与子》漫画;陌生化;召唤结构;寓教于乐
埃里希-奥赛尔是著名的德国漫画家,埃·奥·卜劳恩是他的艺名。卜劳恩自小家庭贫困,曾中途辍学成为一名钳工。后在莱比锡皇家绘画与出版学院学习期间,因为参加画展而受到人们关注,此后逐渐成名。卜劳恩在1921年至1933年的十余年间,发表了大量的幽默画作。纳粹掌权后,卜劳恩因之前发表的一幅刻画希特勒丑陋面目的政治漫画而被掌权者追究,从此被禁止发表任何政治漫画,只能在《柏林画报》上发表一些无任何政治倾向的漫画,《父与子》便诞生于此时。《父与子》是一部讲述父子间细小的情感趣事的作品,卜劳恩与儿子克里斯蒂安便是父、子主人公的原型。从1934年至1937年三年间,卜劳恩一共创作了两百余幅作品,他把对克里斯蒂安的爱融入到简单的线条中,为非常时期的人们带来了甜蜜和微笑。
一、《父与子》中的陌生化
《父与子》的诞生时期正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对文学作品的读者接受问题进行关注和讨论的初期。在深受现象学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眼中,任何艺术都不是凭空的想象和创造。艺术家们精心选取自然、社会或人类自身的某一部分,经过特殊处理令其改头换面,以让欣赏者抛弃以往的惯性认识而产生新的审美感受。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作品与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片面的感知,人们向来对自己熟悉的事物有自动、惯性的感知。在读者与作品的对接中,常态的角度和方式会让读者以僵化的思维模式接受作品而不会产生审美感受。因此,如果要将自动感知变为审美感知,就要采取陌生化的手段。[1]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关键词,是一种对现实事物的偏离、改动或变形。这种以加工手段将原作品以新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使读者脱离常规的感知重新审美和接纳原本已经熟悉的事物,尽可能的延长审美感知的过程在文艺理论和生活实践中都频繁的被提及和引用。
在《父与子》的创作中,卜劳恩凭借对人物形象的陌生化处理体现了他非凡的艺术创造力。虽然卜劳恩和克里斯蒂安平日的情感点滴令《父与子》拥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但以怎样的人物形象展现这些生活趣味是卜劳恩先要作出的思考,在这部漫画中,卜劳恩将自己和儿子逐一变形,以摒弃传统的陌生的形象出现,演绎了一种另类的父子之情。卜劳恩自身是一位容貌英俊、才华横溢、举止儒雅、谦和且十分有性格的艺术家。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蔓延到德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希特勒当权后,德国更是沦为人间地狱。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卜劳恩仍然坚持留在柏林,将这个城市视为他作品孕育、发芽的唯一土壤。卜劳恩大胆的行为流露出他倔强、不羁、坚韧不屈的性格。但在漫画中,读者却丝毫感觉不到这样一位执拗、坚定的卜劳恩。
为了创造出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主人公,卜劳恩艺术化了自己的一切特质。漫画中的他,锃亮的光头、粗壮的眉毛、夸张的圆眼睛、浓密的胡子、臃肿的身材一点也不具备传统观念中父亲高大、威严、霸气的伟岸感。他不以成人思维角度出发,永远怀有一颗童心,虽然名义上是父亲,但其实更具备小伙伴的特质,是一个极为特别的父亲形象。这样的人物穿梭在近200个故事当中,颠覆了读者对父亲形象的旧有认知,建立起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父亲形象,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新鲜感和好奇心。
对克里斯蒂安的创造也同样体现出了卜劳恩的创新智慧。现实中的克里斯蒂安长相帅气、伶俐可爱,与卜劳恩颇为相似。但在漫画中,卜劳恩抛弃了这种遗传性基因的影响,将克里斯蒂安变成了一个头发凌乱,身体纤瘦,一脸古灵精怪之气并且总是闯祸的小朋友。大腹便便、傻里傻气的父亲和古灵精怪、不爱学习的儿子在画面中一大一小、一胖一瘦、一精致一邋遢,为读者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人物形象的陌生化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因为主人公的平凡和相似而产生的审美疲劳提前收场,也为故事的有序发展做好了铺垫。
二、《父与子》中的“召唤结构”
“短小”与“无字”是《父与子》最大的特点。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如何通过简单的线条和狭小的空间将作品的主题完整地传达给读者,是卜劳恩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而与此同时,如何从简洁的画面中感知到作品的含义,也对读者的阅读提高了难度。
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者认为,作品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个体,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感受将是对作品留下的空白的填充,在这一具体化的过程中,读者的所思所想参与了作品的再塑造。“空白”是文艺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被英伽登提出后受到了许多理论家的赞同。英伽登认为,作品本身是一个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的图示化纲要结构,如果要将作品的骨架充盈起来需要读者阅读的具体化,具体化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未定点确定及对空白填补,如果读者被动的阅读只能获得一些图式化的方面,只有当读者积极的调动自己的想象填补作品中的不定点和空白时,作品不完备的意向性关联物才能变为活生生的审美客体。[2]
“启发”作为“空白”的精髓,连接了作者和读者的创作、阅读感受,作者对读者的审美感受产生期待,读者又对作者的情感意识产生好奇,二者情感的和谐、统一达成了作品接受的共鸣。而这种朦胧的创作模式,无论在保守的东方文化还是开放的西方文化都已存在良久。在中国古代,创作者在艺术创作中极少采用全盘托出、一览无余的创作手法,而是以一种隐藏、遮掩、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表露将作品的意境表达出来。这种从作品的整体塑造中体现出的间隔、空白、断层,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光环更增添其艺术魅力,水墨画和书法中的留白便是对这一概念的最好体现。而在西方的文艺创作中,雕塑的无色、电影中的空镜头、戏剧的静景布置、歌曲的间奏等也验证了省略与含蓄在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普遍性和价值。
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也认为,读者的视野和文本的视野存在着一种相互交融,文本的意义无法由单一的个体承载,它既不存在于文本之中,也不由读者来决定,而是既存于二者视野融合的无限过程当中。
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在研习了英伽登和伽达默尔的理论后,将其加以改造、综合,提出了“文本的召唤结构”概念。伊瑟尔认为,“空白”和“否定”都是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性机制。他十分肯定“空白”的作用,认为文本的隐密性刺激了读者的思维运动,暗示其主动承担起填充文本的任务,这样便对作品的完整建构给与了有力支持,同时也对读者的引导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空白”还是“视野融合”,卜劳恩在《父与子》中都体现出了他深厚的美学修养。中国古代有“此处无声胜有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而《父与子》亦通篇无对话与解说,并且采用“个数格”构图,读者从自身的审美角度出发,在有限的空间中发挥想象,探求趣味和哲理,酿造审美感受。这种不完全表达的创作模式,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满乐趣和挑战,感受作者乐观的处世精神和人生哲学,把握了作品的真谛。
三、《父与子》中的“教”与“乐”
不具备传统漫画强烈的政治隐喻和社会讽刺性是《父与子》的另一大特色,虽然它的诞生伴随着卜劳恩对现实的心酸和无奈,但是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读者却完全感受不到这种悲辛的人生遭遇。卜劳恩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生活中的乐趣,他剔除了自己的不幸,只将一切美好作为作品成长的养分,使作品充满了人情味。
贺拉斯曾在他的《诗艺》中提出著名的“寓教于乐”说。他从诗的角度认知,认为诗作为一种人们生活中的文艺创作方式,不仅应当给人们带来精神愉悦和益处,还应当对他们产生教育和救助作用,贺拉斯主张在乐趣中释放教育。
教的功效在于促使人们接受文明、崇尚美德。在贺拉斯眼中,它应当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呈现,以艺术和美的形式展开,让欣赏者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而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学生的对来源信息的加工能力和学习过程中的情绪愉悦程度是决定寓教于乐成功的关键。寓教于乐思想对18世纪启蒙运动以及古典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教育的认知在已经渐渐脱离了简单的以知识储备为标准的判断模式,更多的是对真、善、美的考量。而作为承担着这一教化任务的载体,艺术作品以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的存在模式积极引导着人们,促使他们加强自身的心灵净化和人格修养,积极参与精神的补充。因此,是否兼具乐趣和教育功能也成为衡量艺术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在《父与子》中,卜劳恩对父亲的塑造发挥了他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心思,以保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父亲的出其不意所保持的冷静。
童心未泯的父亲常常会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事,比如帮儿子写家庭作业、和儿子一起踩栏杆、帮儿子打架、惦记儿子存钱罐等稀奇古怪的事情,但在故事不断丰富的过程中,读者渐渐感受到了父亲独特的教育方式和良苦用心,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被他严苛的家庭教育所触动。
尽管中西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自由意志及人的价值等一些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父与子》是一部充满着深刻的哲理思想的作品,它当中所体现出的一些思想与中国传统处世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勿以善小而不为”、“百行孝为先”等观念不谋而合。因此,《父与子》一进入中国,便受到了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传播与相互认同。
《圣诞节的贵客》讲述的是父子二人去森林里寻找圣诞树时,意外地和小动物们建立了感情,最后一起欢度了圣诞节的故事。《袋鼠的友谊》展现的是克里斯蒂安因为救了差点被秃鹰抓走的小袋鼠,而被袋鼠妈妈邀请和爸爸一起到家中做客的情景;《可疑的螺旋形》里,克里斯蒂安因为贪玩将小象的鼻子绕了起来,令布劳恩十分恼火,以至于当他再见到螺旋角的山羊也怀疑是克里斯蒂安的“杰作”;《放生以后》讲述了父子两在河边捞到一条大鱼,因为不忍心杀戮而将其放生,却不料竟让它成了鳄鱼的午餐的不幸之事。在这些故事当中,卜劳恩用简洁的画面展现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微妙关系,以虚实结合的创作为出发点,表达出自己热爱自然、崇尚和谐的美好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早在庄子时期便已存在。季羡林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解释:“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相互理解,结成友谊。”[3]“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相生相克的循环模式明确的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已经走入了以生态和谐为代价的发展误区,但仍不知觉醒。卜劳恩采用了无声的抵抗的方式,在作品中展现出人类与自然的情感统一,相互交融,让读者在开心之余也被画面中温暖的情景所感动,受到教育和启发。
《不值得帮助的家伙》、《同情马蜂的教训》、《行善的结果》、《恩将仇报》记录的是父子二人在好心帮助别人后却收到令人气愤的回报的经历。在《不值得帮助的家伙》中,父子路遇辛劳的车夫便上前帮忙,没想到车夫却独自坐在车上消遣起来;《行善的结果》中的卖唱者在接受父子慷慨的施舍后,第二天居然搬来了钢琴,企图索取更高的赏金;《同情马蜂的教训》中的马蜂和《恩将仇报》中的花豹,也都不念父子的救命之恩,反而恶意报复,令人愤慨。这些故事与《伊索寓言》中的《农夫与蛇》有异曲同工之妙,劝导人们分清善恶,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善”是具有伦理学、哲学、和佛学内涵的人性道德。最早对“善”的解释和定义是“可欲之谓善”,这时的“善”十分模糊和片面,即认为人的欲望得以满足便是善。随着历史的发展,善的定义逐渐丰富起来,成为具体事物完好、圆满的组成,具有吉祥、幸福、美好等多重意义,也因此成为日常生活中最具荣耀的溢美之词。
善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在人类的生活中存在已久,《论语》中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国语》中有“善,德之建也。”《左传》中有“供养三德为善。”它作为人类不可缺少的精神信仰,对社会的前进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存在。
在《父与子》中,卜劳恩通过细小的情节展现父子二人的纯良性情,将父子一心向善、与人为善的美好品性贯彻始终。
在《不必要的悲哀》中,父亲和儿子对魔术表演中的切割术信以为真,竟专程为女演员买来了花圈。《悲伤的乐曲》中,父亲对卖艺者大加施舍却不厌其烦。《飞来的一只野鸭》中,大风刮走了父亲拴在伞柄上的野鸭,野鸭顺着烟囱掉在了穷人家的炉灶上,看着一家人欢呼雀跃的样子,父与子欢欣的心情如自己吃了一般;而《爱心的奉献》,虚荣的贵妇更是衬托出了父子关爱自然、同情弱者的善良品行。
在善之上,国人常道“百行孝为先”。《诗经》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反映出了中华民族极其注重孝道的观念。
“敬”与“顺”是“孝”的前提和体现,意味着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论语》中有子夏问孝,孔子仅用“色难”二字便点出了孝的精髓。父母遇到事情,由年幼的操劳,有了酒食先让年老的吃就是孝了吗?并非如此,最难的是子女对父母的脸色,任何时候都对父母保持悦色,令父母心情感到舒畅、愉悦才是最大的孝。
《家教》和《虚荣心治好了》无疑是卜劳恩对孝道最好的传达。卜劳恩带着克里斯蒂安和父亲一起去看望祖父,祖孙三代在拍照时不小心打碎了祖父的植物,祖父很生气的打了父亲,父亲又打了卜劳恩,克里斯蒂安自然也未能幸免。原本严肃的《家教》,经卜劳恩有趣的画面诠释,显得十分活泼可爱。而《虚荣心治好了》更是阐明了无论任何社会恶气,在强大的家庭传统下都将一文不值的宿命。
中华民族视“勤俭节约”为传统美德。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曾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训言,而古人也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之说。在中华民族诸多的优良传统中,“勤俭”最被贤哲伟人所推崇,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石,在后世对历朝历代的评判中,勤俭一向被当作检验朝代兴衰的重要标准之一。即使是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不以节俭为羞涩之事,反而极力推崇和大力宣扬。
《习惯的力量》中,意外继承了财产的父子二人虽然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仍然没有丢弃勤俭节约的习惯。当看到遗落煤块的运煤车时,两人都追了出去,最后却因为迷路而不得不打电话向管家求救。虽然故事中豪车拉着小煤车的画面略显夸张,但这却深刻地体现了卜劳恩提倡节俭、不愿浪费的美好品质。《实例警告》中,卜劳恩将不爱惜粮食的克里斯蒂安带到博物馆参观拉奥孔的雕塑,虽然拉奥孔的意义与物质浪费并无关系,但是其贴切的形象却令年幼的克里斯蒂安产生畏惧,从而改正自己的恶习。故事中父亲的教育方式虽然有些笨拙和滑稽,却也正影射出了父母为教育子女而绞尽脑汁、盲目的心情。
“勇”作为一个伦理范畴,在人类诞生起便是实现民族强盛的关键要素。孔子主张仁政,“勇”便是它作为施“仁”的条件之一。从汉字的构成来看,“勇”是力量和精神的象征。狭义的“勇”是剽悍、凶猛的行为,而广义的“勇”却包含着“仁、义、礼、智”等多个方面,所谓“有勇有谋”“智勇双全”都表达了“勇”是思想与行动的和谐、统一。
在《吃力不讨好》中,父亲因接到儿子的呼救不假思索的跳入河中,而被“得救的落水者”拳脚相加。卜劳恩用这一图画简单、明了的向人们展示了鲁莽的后果。但在《击中了要害的题词》、《图钉妙用》、《这才是金子》中,父亲智慧与勇气并存的做事风格却让读者羡慕和崇敬。《击中了要害的题词》中,傲慢的滑冰者因为小朋友们的无意而对其严厉指责,父亲在冰面上划出了“虚荣者”的单词后将小朋友们带走,令滑冰者颜面尽失。《图钉的妙用》中,父子二人遭遇抢劫。父亲却临危不惧,用一颗图钉擒获了歹徒。在孤岛上发现海盗的金库后,父亲却对金子视而不见,只带走了锋利的斧头。《这才是金子》表现出了父亲在困难前的冷静和勇敢,向读者传达出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四、结语
《父与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它既没有现代艺术所广泛包含的悲观主义和抽象化特征,也没有绝大多数艺术作品共有的商业性和功利性。它通过人物形象的陌生化,使一对普通父子的日常生活充满感染力,令读者在持续的审美情绪中体会到父与子之间微妙的情感。作品以无字的形式讲述故事,留给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使读者能够与作者建立起联系,共同完成作品的构建。除此之外,是作品最重要的核心——乐观而豁达的人生态度。作品通过两百余个故事,营造出一种大爱的氛围,深刻地展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与美好,使作者在享受审美愉悦同时,也获得了人格的升华。
《父与子》的问世是对传统艺术作品的一种超越,也是对未来艺术的一种启发。它具有文艺作品的格调,但是却摆脱了“纯粹艺术”的孤傲,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
[1][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9,138.
[3]蔡仲德.也谈“天人合一”——与季羡林先生商榷[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05).
B83
A
1671-6469(2016)-04-0062-05
2016-04-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伊犁师范学院新疆哈萨克文化与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开放课题“形象构建·文化内涵·民族认同——新疆哈萨克族题材电影研究”(XJEDU080115C18)阶段性成果。
马晓玖(1986-),女,回族,新疆昌吉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学与艺术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