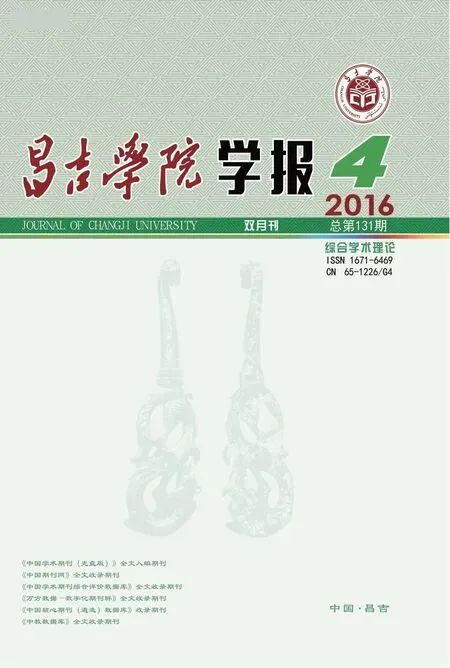和瑛西域著述的基本特征
2016-10-20孙文杰
孙文杰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和瑛西域著述的基本特征
孙文杰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清代边疆重臣和瑛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但其最具价值的不是那些经义之作,而是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较高学术价值的西域著述:《回疆通志》、《三州辑略》、《易简斋诗钞》。和瑛西域著述作为乾嘉年间西北舆地学转变期的典型代表,为乾嘉之后西北史地的兴盛做出了诸多成功的表率,更为清代西北舆地之学的繁荣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在清代西北史地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本文拟对和瑛西域著述的基本特征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和瑛;回疆通志;三州辑略;易简斋诗钞;基本特征
清代中期,随着康雍乾三代对西北地区的持续用兵,至乾隆二十年平定达瓦齐政权,二十二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两定准噶尔政权之后,又于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最终统一西域,开始了对天山南北地区的经营和管理。同时,伴随着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统一和经营活动的展开,清代官府以及文人学士亦更加关注西北地区,对西域边陲的历史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官于私,均出现了大量的西域著述,为清廷中央政府如何经营和管理提供资料与借鉴,其中,私人著述的一个典型代表即是曾经为宦新疆的和瑛西域著述。和瑛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更具学术性、更加系统性的私人著述,他在西域为官期间所著的《回疆通志》、《三州辑略》、《易简斋诗钞》莫不如此,具有鲜明的特征,综合其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内容丰富
嘉庆七年,和瑛因事贬往新疆时,恰逢西北史地学兴起之后的发展期,在这之前,无论是官修史志还是私人著述,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西域图志》、《大清一统志》、《新疆回部志》、《西域闻见录》等。但与之相比,和瑛的西域著述全书旁征博引,史料繁复,显然内容更加丰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即是与《新疆回部志》的对比。
《新疆回部志》,又名《回疆志》,永贵等人初纂,苏尔德增修,于乾隆三十七年成书,全书约四万余字。《新疆回部志》与《回疆通志》类似,均为描述天山南路地区各城之通志,在清代新疆方志中成书较早,保存了重要的史地资料。但二者相比,显然《回疆通志》内容更加丰富,首先从两志之目录即可见端倪,如表1:

表1 《新疆回部志》与《回疆通志》目录比较表
通过上表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回部志》虽然对天山南路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风俗民情、宗教服饰等方面有诸多记载,为后世学者研究清代中期回疆地区地方史与民族史保存了重要资料。但是,《回疆通志》与之相比,在体例、门类上显然就更为丰富,比《新疆回部志》多了哈密、吐鲁番《回部总传》、回部有爵位者列传,以及天山南路地区八大回城之沿革、疆域、古迹、兵防、军械、粮饷、赋税、税则、钱法、杂支、牧厂、卡伦、军台、事宜、硝局、伯克、回务、伯克、布鲁特等诸多方面内容,毫无疑问,《回疆通志》内容更为丰富、更具价值。即使是与《新疆回部志》记载的同一地之同一内容,《回疆通志》亦是更加丰富,如有关喀什噶尔河流之记载,详见表2:

表2 《新疆回部志》、《回疆通志》喀什噶尔河流记载之比较
霍色尔即克色尔,泰里布楚克即大比楚克,雅吗雅尔即依满雅尔。通过上述表格内容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回疆通志》关于喀什噶尔河流情况的记载,伊兰乌瓦斯河、图木舒克塔什河、乌兰乌苏河等三条河流,显然对喀什噶尔民众生产、生活更具重要意义,而这些正是《新疆回部志》所无。即使是二志同载之霍色尔、泰里布楚克、雅吗雅尔三河,《回疆通志》不仅更为详细、丰富,更是纠正了《新疆回部志》的许多相关错误。
二、实地考察
随着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兴起,自顾炎武、梁份等人始,学术界关于西北史地的研究即开始重视实地考察,但因清初的时局所限,学人足迹大多未履疆土,因此并未真正的做到实地考察。自康雍乾开始,伴随着清廷西北战事的逐步推进,尤其是乾隆二十四年最终统一西域并全面设员经理后,大批的文人、官员进入西域,此后大批涌现的西域著述,无论是《大清一统志》、《西域图志》这些官修史志,还是《西域闻见录》、《回部志》这些私人著述,均具有明显的实地质实考证、实地见闻经历等特征,清代西北史地也开始真正地具有了实地考证之因素。这些方志的编纂虽然保存了大量的切实可靠之史料,但作者实地考察的缘由皆因他而起,并非出于己身的主动积极,因此其著作的实地性不免具有某些程度的缺憾。
而和瑛自嘉庆七年因事发往西域效力以来,先后在新疆担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等职,驻疆时间长达七年。在这七年间,和瑛因为职责所在,每年均要巡查驻地各城,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天山南路以及乌鲁木齐都统所辖的每个区域。而和瑛利用每次巡查各城的机会,每到一地便积极访问当地历史古迹、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大量搜集历史资料,在其西域著述《回疆通志》、《三州辑略》中也多次出现“亲至”、“亲证”、“尝询”、“尝至”、“考其地”、“以地考之”、“今考”等字眼,如《回疆通志·库车·沿革》
库车在阿克苏东北六百三十里,喀喇沙尔西南九百四十里,古龟兹国也。汉延光二年夏,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示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还屯田柳中。又《西陲纪略》云:鲁陈,一名柳城,亦名柳陈。柳中,汉车师前王地,唐为西州属邑柳中县。后汉班勇出屯柳中,经大川、沙碛,无水草,大风倐起,人马相失,土人谓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冈,云风沙所积。道北火焰山,山色如火,城方三里,又别开一境云。今以地考之,交河宜在吐鲁番,柳中宜在布古尔、库尔勒一带,故班勇以前部开通还屯柳中也,或以库车城皆柳条夹土而筑,故名柳城。[1]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和瑛在编纂其西域著述时并不迷信于历史典籍所载之内容,而是“以其地考之”,在借鉴历代典籍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了实地考证,这为他编纂其西域著述积累了大量更准确、更客观、更详实的数据与史料,最终保证了和瑛西域著述的质量与准确性。即使是其诗集《易简斋诗钞》也充满实地考察的因素,如《喀什噶尔巡边》、《巡阿克苏城》、《英吉沙尔》、《喀浪圭卡伦》、《纪游行》、《续纪游行》等诗歌,内容均是叙述边疆史地,足可补舆图之阙。所以,和瑛的西域著述不管是方志还是诗集,均充满实地考证的因素,尤其是与前人西域著述相比,显然更具实地考察特征。在这方面,一个明显的对比即是同为私人著述的《西域闻见录》。
《西域闻见录》,七十一著,乾隆四十二年成书。又有《西域琐谈》、《西域记》等名,版本多达十余种。该书凡八卷,约四万字,内容以作者亲历见闻为主,丰富的记载了天山南北各城、新疆境外诸部及绝域之国、清廷平定西域及土尔扈特回归、维吾尔族风俗、物产等方面的历史,由于内容多为耳闻目睹之事,保存了清廷统一西域前后新疆的政治、社会、军事、经济等方面史料,可信度较高,为后世研究边疆史地的重要资料之一。因为曾担任库车粮饷局章京、镇迪道观察、阿克苏主事等职,其对天山南路回疆地区的记载较为详实,颇为可靠。但《西域闻见录》也存有致命缺憾,对天山北路,尤其是对外藩的描述,并未亲身实地考证,严重失实,舛讹颇多,甚至是贻笑大方,正如何秋涛所评:
惟回疆风土系得诸目睹,多资考证。其外藩列传,如哈萨克、布鲁特之类,岁时朝贡,土尔扈特、和硕特之属,已列藩封,耳目较近,纪述亦详。若绝域诸国,则得自传闻,山川道理,半涉茫昧,其舛讹尤甚者,莫若鄂罗斯、控噶尔二篇。[2]
与何秋涛一样,祁韵士亦称其为:“所载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乘,皆无考据。又于开辟新疆之始末,仅就传闻耳食为之演叙,讹舛尤多。”[3]其后,魏源又称《西域闻见录》:“于葱岭以西各国,道听途说,十伪六七,不可依据。”[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沈瑞麟评价《回疆通志》“裁融方册,校核前闻,证必穷原,辞无甚泰,事为后法……视《一统志》而事详,本《闻见录》而时近。”[5]吴丰培先生赞扬《三州辑略》:“此书为著名新疆地方志之一,仅次于《西域图志》和《新疆图志》,与《伊犁总统事略》之作,为研究新疆必备之书。”[6]符葆森曾誉《易简斋诗钞》为:“诗述诸边风土,可补舆图之阙。”[7]由此可见,和瑛的西域著述显然数据更详实、史料更可靠,更具实地考察特征。
事实上,和瑛在编纂其西域著述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又利用职务之便按之以府衙档案,其实地考察的特征不仅比同时期的私人著述更为明显,更是丝毫不逊于清廷组织的官修史书《西域图志》、《大清一统志》,如《大清一统志·乌噜木齐·卡伦》,详见表3:

表3 《大清一统志》与《三州辑略》乌鲁木齐卡伦对比表
通过上表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大清一统志》虽然是清政府主持编纂,卷帙浩繁,但前往西域调查测绘之人员并非自己主动前往,而是受清廷所派,积极性显然并不是很强,实地调查考证的效果并不特别明显,就乌鲁木齐所属卡伦而言,只是罗列卡伦名字而已。而和瑛在担任乌鲁木齐都统期间多次实地调研、考察,在自己亲身考查的基础上,《三州辑略》所载各卡伦情况比《大清一统志》更加完备、准确,进而给后世留下了更为切实可信的史料。和瑛通过亲身实地调研所获得的这些史料,其对西域真实可信的感性认识显然非当时内地兴盛的文献考据可比。
三、纠误补缺
清代之前,由于西域长期隔绝于内地,偏处一隅,只有极少数人能亲历其地,大多数人对西域的了解也仅限于极少数的典籍所载,但各种典籍均属于彼此继承,乃至以讹传讹,更甚者“罔克凿空撰述”[8]。因此,人们对西域的了解也就仅局限于汉唐时期之官修史书,如前后《汉书》、新旧《唐书》,但绝大多数人对西域的印象依然十分陌生、乃至误解。自清政府重新收复西域之后,随着清廷在新疆的全面建置的展开,大批的文人、官员亦有机会亲至域外,如此便有了验证史上典籍之机遇,最终了解西域并对史籍纠误补缺,诚如和瑛在《三州辑略》中所言:
夏书即叙之戎,蔑详疆址;周书西旅之贡,不纪封圻。厥后《佛国记》法显浮夸,《水经注》道元罣漏。张博望初通西域,凿空之道里失真;笃招讨再溯河源,重译之山川多舛。指巴延喀喇为昆仑,并积石山而谬定;取罗卜淖尔为星宿,兼蒲类海而讹传。他如柳陈、鲁陈,火州、和卓,皮禅、辟展,海都、开都,和阗、赫探,轮台、仑头,乌兔、务涂,伊犂、伊列。或一地而名殊,或近音而字异。黑河有六,执泥则相去径庭;疏勒凡三,浑同则更离霄壤。皆由荒酋裂土,代远年湮,一惑于罗什方言,再惑于昂霄译语。此《地志》、《山经》所不载,《类函》、《通考》所未详者也。[9]
如上所揭,由于种种原因,历代典籍有关西域的记载讹误频频,以致后人对西域也误解频发。因为清廷重新收复西域,让和瑛有机会:“游异域十三年,未窥半豹;历训方二万里,敢目全牛。兹乃忝护北庭,旁搜西史,爰成辑略,裒纪三州。盖不志西州,不知庭州之所自始;不志伊州,不知庭州之所由通。”[10]因此,和瑛西域著述编纂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纠误补缺。
和瑛在编纂其西域著述时,首先对人们最为熟悉的历代正史提出质疑,如:“自玉门、阳关出,有二道。从鄯善旁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车,今叶尔羌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氐、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至疏勒,今喀什噶尔为北道;北道北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通鉴》作西踰,误。故皆役属匈奴。车师部有前、后王庭。前王治交河城,今之吐鲁番广安城也。元封间,赵破奴将兵虏楼兰王,遂破姑师。盖姑师、车师,一国两名,《纲目》以姑师为楼兰王名,非是。”[11]“《元史·地理志》以大雪山为昆仑。大雪山者,巴延喀喇山总名库尔坤,非昆仑也。又以河州西小积石,本名唐述山,误为《禹贡》积石,非是。今考积石山在青海境内,名阿木尼玛勒占穆逊山,当罗卜淖尔东南之境,山东麓有水出焉,名阿勒坦河,东北流三百余里,有泉千百泓,名鄂敦塔拉,所谓星宿海也。”[12]和瑛对《资治通鉴》、《元史》等史书不仅提出质疑,而且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再次加以考证,纠正讹误。
清代以前,由于西域与内地隔绝,学人对西域记载有误在所难免。但随着清廷对西域全面经营的展开,人们对西域的认知也逐渐有了亲历的感知认识,但同样也有诸多错误之处,因此和瑛对与其几乎同时代的史志也提出疑问。清代有关西域的方志对新疆地理争议比较大的是罗布淖尔的确切位置,如清以前史书均以蒲类海为蒲昌海,清人史志在有了实地勘探之后,虽未再以讹传讹,但一直没能真正进行切实的亲身考证,仍然争论不休,如《西域闻见录》误以罗卜淖尔为星宿海,又《西陲纪略》误以蒲类海为蒲昌海,而清代官修史志如《大清一统志》、《西域图志》亦未能探定清晰,模棱两可。和瑛自西域为宦之后,便开始了对罗布淖尔的关注,并多次实地考证,最终确定了罗布淖尔的确切位置,这在他的《回疆通志》以及《三州辑略》均有体现:
《西域闻见录》以罗卜淖尔为星宿海,非也。考《汉书》:于阗河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据《地志》:盐泽,一名辅日海,一名穿兰,一名盐海。盖蒲昌海又名黝泽,番名罗卜淖尔也。其淖尔受西域回疆诸大河水及北雪山春夏消融之水,亦渟而不流,潜行地下耳。其所受之水,一自叶尔羌西南徼外温都斯坦西北山后,有大河曲曲东北流径拉虎尔部落、克什米尔部落,又东至叶尔羌西南二百里分为二流,又自米勒台玉山流出一水注之,总名曰玉河,又名得叶尔河,其水最大,夹白沙而行,其色如银,东南流。一自和阗南山中流出,分而为二,亦名玉河。一自叶尔羌正北葱岭外流出一水,在堪达哈尔部落之南;一自哈尔部落山后流出一水;俱南行至什克南城北山后合流,径瓦罕城至大河沿分而为二,至奇兰戈壁又分为三支。一自叶尔羌东北拜哈尔城北流出一水,西南行至阔喇普分而为二,径塔什干城东南流。此叶尔羌西、南、北三路诸水皆归于罗卜淖尔者也。又自喀什噶尔北来,伊兰乌斯河西来,图舒克塔什河、乌兰乌苏河南来,泰里布楚克河、霍色尔河俱东南流归罗卜淖尔。又乌什西来大河一道,源出布鲁特胡什齐地方,东至察哈喇克台出境。又阿克苏城西浑巴什河源出穆苏尔达巴罕,又托什罕河、瑚玛喇克河、汤纳哈克河、楚克达尔河、穆杂喇特河俱东南流归罗卜淖尔。又库车城西之渭干河绕沙雅尔东南流喀喇沙尔城西之开都河,源出北大雪山东南流,俱归罗卜淖尔。又吐鲁番城外交河二道,源出金岭,自北东南流;又辟展北来之河,东南流;又哈密西雪山融化之水,正南流;此南路西北两面之水,皆归于罗卜淖尔者也。其淖尔渟而不流,潜行地中,东至青海境枯尔坤山之巴延喀喇山东麓始复出,为星宿海。又名鄂敦淖尔,蒙古语鄂敦,星也;淖尔,海也;即《元史》所称火敦脑儿者也。史传所谓黄河源出星宿海,不知更有罗卜淖尔受西域诸大水。程子曰:水本异而末同不信然与。[13]
由此可见,和瑛不仅对古代史说进行“质实”、“辨讹”、“证古”等工作,更利用自己亲历域外的机会,有意识的加以实地考证。更重要的是,和瑛在“辨古”与“史地考证”的基础上最终纠正了历代史籍之舛讹,不仅避免了后代史书以讹传讹,更保存了真实可靠的西域地理信息。这与前文所述的“实地考证”乃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之举。
难能可贵的是,和瑛在编纂其西域著述时,“辨疑”与“纠讹”精神始终存在,在《回疆通志》、《三州辑略》中也处处可见和瑛“纠误补缺”之处。同时,和瑛纠误补缺之举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地理等大的学术范围,还把目光投向了诸多小问题,如地名含义:“喀什者,初也;噶尔者,创也;汉语初创之谓。《西域闻见录》译为花砖房子,非也。”[14]再如小到西域之特产,和瑛也同样进行纠讹辨析:“黄瓜,李时珍曰: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陈藏器以为避石勒讳改胡瓜名黄瓜,杜宝以为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二说不同,然俗以月令王瓜生即此,大谬矣,此南人音‘王'、‘黄'不分之故耳。”[15]
如前所揭,和瑛在征引前代史籍并加以实地考证的基础上,对历代史书进行甄别,并纠误补缺,这在他的西域著述中特征比较明显。毫无疑问,和瑛及其西域著述在纠讹补缺方面比同时期的《大清一统志》、《西域闻见录》更具系统性、更有代表性。
四、经世致用
有清一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使西域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研究宝藏,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兴起与发展,也正是在时势和时代学术发展影响之下逐渐茁壮,在这之中,学术影响最大的即是乾嘉学派。乾嘉学派质实求证的考史风气对清代学术发展的贡献毫无疑义,但乾嘉学派由于受到当时文化专制的严重束缚,大多数学人只注重传世文献的考订,却遗忘了以史为鉴、以古治今的学术精神,因此,尽管他们的考据之学在清代学术发展中虽然有着巨大的贡献,但同时因严重脱离社会现实而逐渐不能适应时代的新要求。与之对应的是,自清初开始,即有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根据明末清初社会巨变的现实,明确提出以学术经世,进而匡济天下,也即是明确提出“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经过顾炎武、朱舜水等思想家不断地实践与倡导,到了乾嘉时期,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已经初具规模。伴随着这种社会思潮的变化,学术思潮亦随之巨变。反映在史地学方面,最大的变化即是,部分以经国纬世为己任的文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亦逐步不再拘泥于古籍之考证、局限于内地朴学之考据,而是由追求考据之学转向了以学术求治世,进而使沉寂已久的经世致用之学风再度兴起。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即是和瑛及其西域著述。可以说,和瑛及其西域著述正是经世致用的社会风潮、乾嘉质实求证的考史风气、西北开辟的政治环境和西学知识的引进因缘际会的时代产物,他最大的一个特征即是不再专注于传世文献的考订,而是更多的去留意现实、关注民生、关心边防、思考边疆经营等国计民生的大事。
可以说,为了适应清政府对重新收复之西域有效经营的需要,和瑛在其著述思想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正如其在《回疆通志·序》中所说那样:“稽册籍以成编,毕胪形胜,叨旌麾以治事,恪守规模。惟愿职斯土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矢志公清,俾怀恩信。”[16]这种明显的经世致用思想贯穿于他所有的西域著述编纂之中,无论是《回疆通志》中的“官制”、“兵防”、“粮饷”、“赋税”、“伯克”、“回务”、“钱法”、“卡伦”、“兵屯”,还是《三州辑略》中的“库藏门”、“仓储门”、“户口门”、“屯田门”、“营伍门”、“台站门”、“流寓门”,无不明显渗透着和瑛经世致用的思想。毫无疑问,和瑛正是抱着经世致用的态度去编纂他的《回疆通志》、《三州辑略》乃至《易简斋诗钞》的,志中大量严谨认真、资料详实的内容,不仅增加了史料的可信度,更是为加强清政府对西域的经营和管理提供了众多的有益材料。
所以,和瑛虽然优于文学,一生笔耕不辍,但其最具价值的著述与思想,不是那些经义之作,而是那些体现其执行清政府经营与管理西域边疆理念的著述:《回疆通志》、《三州辑略》以及《易简斋诗钞》。和瑛这些西域著述,是清代西北舆地学的重要组成,更是当时经世致用社会思潮的产物,即使其诗集《易简斋诗钞》,也被誉为:“诗述诸边风土,可补舆图之阙。”可见,和瑛比林则徐、魏源更早的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应用于边疆的经营与管理思想之中,体现于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中,因此,和瑛西域著述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即是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思想。
五、略古详今
众所周知,文字狱对清代学术的影响极大,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即使一批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有识之士,其边疆研究也仅仅局限于考据、训诂之学,如极重经世致用的洪亮吉,虽曾流寓西极,但其著却多述纪闻,如《西海释》、《昆仑山释》,可以看出洪亮吉的西域著述仍然详于“古”而略于“今”。而其他类似洪亮吉亲履西土之士的著述,受文字狱影响,亦回避现实问题,普遍具有详古略今之特征。但是和瑛,作为嘉庆时期宦新的官员/文人代表,自入新伊始,便开始思虑如何加强清政府对西域的经营与管理,与之对应的是,和瑛西域著述无不透露出浓郁的经世致用观念,时刻关注现实,具体表现在其著述上即是具有明显的略古详今的特征,更具价值。
例如《三州辑略》,和瑛在编纂时便体现了其略古详今的撰写原则,无论是该志的沿革、疆域、山川等门,还是官制、仓储、营伍、台站库藏等门,尤其是屯田门及流寓门内容,均以清政府统一新疆前后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三地区的历史、军事、社会、经济为重点,具有明显的详今略古的特征,毫无疑问是清廷收复新疆之后为适应管辖治理、加强对该地区的经营和管理服务之需要,为当时的现实政治而服务。
更明确体现和瑛西域著述略古详今特征的是《回疆通志》,《回疆通志》卷一所收乾隆平定回疆“御制诗”,主要反映在清政府统一新疆过程中的重要军事行动,歌颂清政府的文治武功;卷二至卷六的列传,则详细记载清政府统一新疆期间的诸多历史事实,主要反映维吾尔上层领袖在统一过程中的历史功绩。卷七至卷十一分别详细记载了天山南路所属各回城之沿革、疆域、山川、建置、官制、古迹、营伍、屯田、粮饷、卡伦、军台、回务、事宜、赋税、钱法、牧场、伯克等,这些内容更是严格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进行编纂。可见,《回疆通志》一个突出的特征即是“略古详今”,重点突出收复之后的新疆,无论是传记、沿革、建置,还是官制、营伍、粮饷等内容,都主要以康雍乾时期出兵收复新疆前后的政治、军事、经济为重点,为当时的现实政治服务,为清朝统治阶级如何更好地经营和管理西域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历史资料。
综上所述,作为清代西北史地学由兴起期向发展期转变的主要代表,和瑛及其西域著述具有明显的时代及学术特征,无论是内容之丰富、实地之考察,还是纠误补缺、经世致用、兼具学术与系统、略古详今,均具有鲜明的特征。更难能可贵的是,上述和瑛西域著述的这些特征并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存在,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融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和瑛西域著述的价值之所在,为清代西北史地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可靠的历史资料。
[1][5][14][15][16]和瑛.回疆通志[M].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丛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309,2,185,418,3.
[2]何秋涛.朔方备乘(卷56)[M].畿辅志局光绪七年刻本:341.
[3]祁韵士.西陲要略自序[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8:2.
[4]魏源.圣武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1:179.
[6]吴丰培.吴丰培边事题跋集[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215.
[7]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寄心庵诗话(卷81)[M].咸丰七年刻本:462.
[8]纪昀.乌鲁木齐赋[A].转引自和瑛.三州辑略[M].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册6).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290.
[9][10][11][12]和瑛.三州辑略[M].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册5).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1,2,35,2.
[13]和瑛.回疆通志[M].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丛书(册2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3;和瑛.三州辑略[M].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112—117.
K29
A
1671-6469(2016)-04-0018-08
2016-03-10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11&ZD095)”成果之一,2015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西域文史研究中心项目“和瑛西域著述考论(XJEDU040215C02)”成果之一。
孙文杰(1981-),男,河南沈丘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西北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