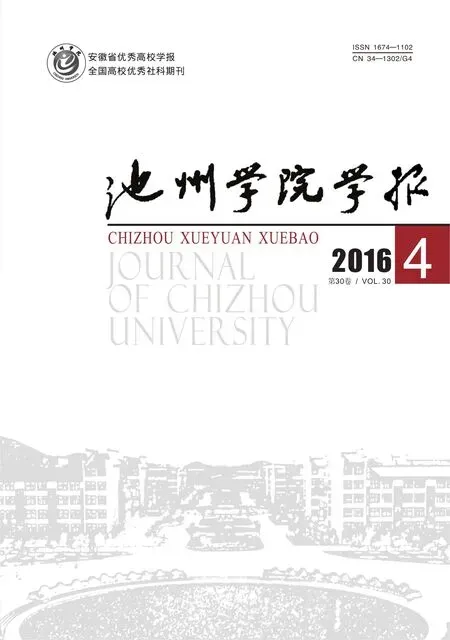咸同兵燹后的徽州社会重建
——以祁门县为中心的考察
2016-03-28余敏辉
孙 唤 ,余敏辉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安徽淮北 235000)
咸同兵燹后的徽州社会重建
——以祁门县为中心的考察
孙 唤 ,余敏辉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安徽淮北 235000)
咸同兵燹后,曾经繁荣富庶的古代徽州遭受毁灭性打击。由于曾国藩曾将湘军大营设在祁门县,先后在此与太平军数次血战,破坏尤为严重。战后祁门艰难开展重建,包括救济邑民、发展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和复兴文教等。重建在地方官主持、邑民广泛参与中开展,突出重点、夯实基础,且能因时变革。不过重建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已难恢复祁门往昔辉煌。
咸同兵燹;祁门;破坏;重建
众所周知,“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的桑梓故里、拥有“东南邹鲁,文化之邦”美誉的千年徽州,在长达十年的咸同兵燹中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元气大伤,无论城乡,户口皆咸衰飒”[1]48,徽州社会从此由盛转衰。而在徽州一府六县中,祁门因其地“处皖赣交界,通闽广,接苏杭,可上达安庆以扼南京,下抵南昌以控西地”[2],且在1860年7月至1861年5月间成为湘军大营所在地,很自然成为清军与太平军双方开展拉锯战之地,当然也就成为咸同兵燹的重灾区之一。那么,就学术界较少关注的咸同兵燹后徽州社会如何重建、有什么特点,以及成效怎样等问题①,本文以祁门县作为个案来探讨,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1 咸同兵燹重创下的祁门
关于咸同兵燹,目前公认最有权威的评说,当推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陈登原。他指出咸同兵燹之“可知者”有四,即:清军纪律之驰、生产大受破坏、杀人几同儿戏、典籍化为灰烬[3]192-194。我们认为,虽说“太平天国时期,徽州曾经是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最为激烈的一个主战场,也是遭受兵燹破坏最为深重的一个地区”[4],不过据《太平军兵争期内皖省府州县经过兵事年月表》[5]统计,仅祁门县城就被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过11次,且还多次侵犯边境,可见这里曾是清军与太平军激战的区域,战祸尤为惨烈,对当地经济社会、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破坏也极大。主要表现在:
1.1 人口锐减,素质下降
祁门沙堤叶氏有言,“自咸丰四年以来,贼(太平军)犯境节次蹂躏,惨不勘言”[6]545。咸同兵燹后的祁门,满目疮痍,村庐为墟,人民流散死亡。据同治《祁门县志》记载,道光五年(1825)祁门县人口为470279,而到兵燹已过七年的同治十年(1871),人口数骤降至100249,锐减几近八成。究其原因:
一是战祸。清军、太平军曾在祁门血战数次,县城反复得而复失,连年的战火,死伤不计其数。且不多说清军借剿太平军之机屠杀掳掠乡民,就以太平军而论,在祁门行军烧杀抢掠,死伤无数,如县志载“(1862)二月贼由赤岭入,踞伦阬等村,焚杀极惨,五日乃去”[7]44。
二是瘟疫。连年战火之后,瘟疫随之而来,以致于有“庚申之乱,徽人之见贼遇害者,才十之二三耳,而辛酉五月贼退之后,以疾疫亡十之六七”[8]657,以及“(皖南)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9]146之说。
三是饥荒。祁门丰收年份粮食只够三个月,更何况在兵灾之年。“贼未退以前,乡村粮食已尽,往往撅野菜和土而食。贼既退,米价每斗至二千钱……于是饥饿而毙者,亦不可胜计”[8]657。
值得一提的还有,“兵燹之后人口的锐减,引发了徽州相关习俗的一系列变化,其中一个重要习俗变化即是严重早婚现象,而这种早婚现象又给当地人口造成了生理素质和文化素质双双下降的深远影响”[4],如祁门县“富厚之家,往往男未及冠,女未及笄,即议婚嫁,筋力未强,疾病丛生”[10]601。
1.2 税负加重,经济凋敝
对于咸同兵燹后的祁门经济而言,除了人所共知的“徽商一撅不振”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纳税负担加重”、“乡村经济凋敝”[4]。
就前者而言,如祁门沙堤叶氏文书表明,“由于饱受战火创伤,民房庄屋烧毁严重,税户死亡和外逃避难者甚众,加上虚粮又多,导致叶氏国课万难催征”[4]。咸丰年间开始对商业征收的厘金税,此时无疑更加重了祁门商人的税负。
就后者来说,“纵有城池克复一两年者,田地荒芜,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殊乏来归之户”[11]244,而祁门“创巨痛深,地方虽有已复之名,而田亩多系不耕之土,其尤甚者,或终日不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11]245。如“(1862年)二月二十九日,贼窜西赤岭入境,盘踞十七、十八、十九三都,烧叶村民房八十余家,伦坑民房二十余家,以及上下汪村、金山栗里、马山、若坑、陈田、曹村、塘下、许村、彭壠、历溪民房百五十余家,大肆杀掠,耕牛掳尽”[7]464,耕牛减少,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恢复。
由以上可见,长达十年的兵祸已使祁门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加之战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以致于乡村经济恢复极为缓慢。
1.3 房舍毁损,社会无序
首先是公署毁坏,如典史署“咸丰四年贼至被毁”[7]66,城守营署“咸丰四年毁于兵”[7]67。
其次是神坛庙宇,如关帝庙“咸丰四年粤寇陷城,庙正殿供奉神像暨两旁侍立四将,神像两柱之金甲盘龙,两廊之绣鞍宝马,尽遭毁损。墙垣亦渐就颓塌”[7]73,崇圣祠“遭兵燹倾颓”[7]73,文昌宫“咸丰间兵燹残毁”[7]73,十王寺“咸丰甲寅兵毁”、青萝庵“咸丰甲寅兵毁”[7]91,其它还有城隍庙、火神庙、忠烈庙等。
再者是居民住宅和宗族祠堂,如1858年,太平军八月至西乡高塘等处,“男女被杀、财物被掠、屋宇被焚遍”[7]462;1861年正月,“贼宵遁,沿途烧民房屋”[7]463;1862年十一月,“烧正街及赤山汪氏宗祠,烧杀甚惨”[7]464,胡笃庆堂“兵燹圮,基存”[7]85。据黄次荪《凤山笔记》所述,“屋庐残毁之痛,犹未暇计及也。比贼退各还其家,惊悸之魄既定,顾视家中百物乃无一存,而日食之计一无所出”[8]657。
且不论公署被毁,值守官员无处办公,无人理事,以及神坛庙宇被破坏,既亵渎了神灵和信仰,也中断了民众日常社交活动,就以徽州“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数姓,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12]41来讲,经过战火洗劫后,祁门县境内祠堂、家谱大都焚毁殆尽,原本作为社会基础和准基层组织的宗族已很难在乡村社会中继续发挥控制作用了。
1.4 罹于战乱,文教颓然
徽州向来文教昌盛,作为徽州一邑的祁门也不例外。然而,咸同兵燹后的祁门,文化备受浩劫。
一是大量珍贵档案、志书、家谱等典籍或被洗劫,或沦于战火,如同治《祁门县志》何家骢所做序言,“将欲考之掌故,而简册剥残书籍,焚毁如省志郡邑志千百什一,几于无存”[7]。
二是学宫、书院破坏严重,如学宫于道光八年(1828)修葺完工,然而到“咸丰甲寅至辛酉递次毁于兵,惟大成殿两庑戟门间架仅存”[7]160;祁门东山书院,兵燹后“风教堂、养浩斋、朱子殿三处,仅留空架,门壁槛扇无存,十堂肄业房舍向共六十九间悉毁于兵”[7]183。
陈登元认为,“咸同兵燹固当由清军纪律之弛负其全责者矣”[3]195。那么,就祁门来说,究竟谁是罪魁祸首呢?虽说近人陈去病《五石脂》有曾国藩“纵兵(指湘军)大掠,而全郡窖藏一空”[13]613的记载,而我们则认为,“徽州咸同之际的兵燹,清军与太平军都有责任。分阶段而言,前期(咸丰四年至六年间,1854—1856年)清军负有主要责任;后期(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间,1857一1864年)太平军破坏更甚,在曾国藩驻徽期间,太平军的破坏作用超过了湘军”[14],这个结论是比较公允可信的。
2 咸同兵燹后祁门重建
正如前文所述,咸同兵燹对祁门经济、社会、文化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为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抚平战争创伤,祁门社会各界人士在“户口逃亡、田地荒废、城垣毁坏、庙宇倾颓,一切人事物产今昔悬殊沧桑改变”[7]的残破与凋敝中,开始了艰难的重建之路。
2.1 及时开展救济
从民本角度出发,咸同兵燹结束后的祁门,百废待兴,不过头等大事是要救荒“活民”,这是不言而喻的。
需要指出的是,其实在战乱之时“活民”就从未停止过,特别是一些民间慈善组织的贡献很大,如勉济局,因1860—1861年间曾国藩行辕设于祁门,周围沦陷地之民,纷纷来此避难,“死亡枕藉,同人议赈恤,乃立铺捐以每日三十钱为一愿,随人乐输,月计得钱七百千文有奇。设局稽查,贫予米,病予药,又于幼童之无依者另设恤孤堂收养。如是者年余嗣,因人多费绌,乃集五乡捐输,得米数千石、银数千两”[7]142;又如同善局,“咸丰庚申粤匪猖獗,四面皆系贼踪,邻邑逃至祁者以数万计。饥疫交厄,死者相枕藉。局中施棺每日多至百数,费用甚巨,当经城乡竭力劝捐以赀接济”[7]142。
而在战乱之后,重建仍旧以“活民”为先,只不过它更多是在官方主导下进行的。一方面是中央给地方予以政策倾斜,如曾国藩于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八日向朝廷上《皖省蠲免各被灾州县钱粮税课折》云:“安徽八府五十九州县,限于粤逆者十居其七,破于捻匪叛练者十居其三,蹂躏情形,较他省为尤甚……旋据查复,皖南徽、宁、广等属兵戈之后,继以凶年,百姓死亡殆尽,白骨遍野,此受害最重者也……兹值残岁将终,阳春布泽,皖省全清已历数月。合无吁恳天恩,准照所请年限分别豁免,以纾民困而广皇仁。”[11]243-245清政府于同治四年(1865)正月出台政策,“蠲免安徽……五十九州县暨安庆、新安、宣州……被扰地方新旧额赋并杂课有差”[15]13。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在贯彻中央政策的同时,积极开展捐赈活动,如对勉济局,“县协同劝捐以赀接济,总办山内粮台知府李兴锐暨各营官皆有资助”[7]142;又如对同善局,“知县林用光及各宪皆有捐助,总办山内粮台知府李兴锐捐置田租一百秤为局内清明、中元两节焚化镪帛之资,本邑教谕谭捐置田租十六秤”[7]142。
还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民间救助力量也不容忽视。如上述兵燹期间民间慈善就组织救济,而在灾后重建中也是贡献很大的,诸多乡绅自发捐粮救饥,如许炳南“例贡生……其族向有义仓以备岁饥,同治癸亥尽被贼掳,炳南独捐谷一千秤以复兴之”[7]346;又如章作肱“附贡生……咸丰中粤寇陷城,居民被难,祁南饥者甚众,肱独出谷周之,颇多全活”[7]346。
还要说明的是,曾国藩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除上文所提他向朝廷上书请求蠲免安徽受灾地钱粮税课外,还下谕褒奖勉济局的创办,同时“拨米四百石助赈”[7]142;又对同善局大力支持,“大臣曾有买存军米千余石储于官仓,后移营安庆,所存之米不便装运,粮台李禀请就地变价,拨银七百二十两归同善局为永远计。大臣曾深悉局用支绌情形,准如所请。局赖此项添置田租若干,至今棺木各费深获其利”[7]142。
2.2 优先发展生产
咸同兵燹后的祁门,满目疮痍、田地荒芜,一片残败的景象,这是不难想象的。因此,在“活民”之后,如何动员全社会力量,优先发展生产,就成为当务之急。
从中央来说,朝廷于“同治四年乙丑,诏免二年以前民欠丁漕正杂各欵钱粮。五年丙寅,诏免民欠丁漕正杂各欵钱粮”[7]146,这是恢复生产的前提条件。而从地方来说,主要是招民垦荒,发展实业,如祁门灾后首任知县蔡钟,当时“寇氛甫靖,百废方举,奉檄丈量。钟因祁税仍旧田鲜荒芜,虑扰民,请免履亩”[7]219。
值得一提的是,茶商、茶农对祁门茶业重焕生机做出了重要贡献。众所周知,茶是徽商传统经营大宗,然而步入近代后,“闻近岁茶行亏折每至数十万元之巨,大半为日本、印度茶所夺。何者滞销、何者畅行,自当急筹抵制之”[10]475。在内外交困的情境以及地方官的大力支持下,祁人胡元龙于光绪八年(1882)创制祁门红茶成功,“英、美、法等国茶商都来采购,销售量逐渐扩大,茶价日高。茶农植茶之风蔚起”[16]111,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祁门红茶产量达到六万余箱,茶商有百十余家……这是祁门历史上的最高产量恐怕不会有错”[17]88,祁红也终成世界名茶。
此外,祁门瓷土也是当地土产之一,其采掘历史可上溯至西周。兵燹后胡元龙生产的“胡培春”瓷土质量最佳,其中太和坑瓷土矿被定为御瓷专用矿,林家坞瓷土矿成为出口瓷、电用瓷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宣统元年(1909)南洋劝业会召开各国土特产展览会,“瓷土、茶叶、祁术、丝线等诸多得奖。胡培春瓷土……给奖最优”[16]118。
2.3 尽快恢复秩序
安定有序、繁荣和谐的社会环境是民心所盼,因为它既是祁门重建的必要外部条件,也是尽快恢复社会秩序的应有之义。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其一,重修官署。官署为一县政治核心,维持着一地秩序正常运行。兵燹期间祁门官署毁坏严重,但因其重要性而及时重建,“咸丰四年粤寇数犯,随毁随修,仍如前式”[7]66。但完全修缮则是在兵燹之后,如官署仪门内的典史署,“咸丰四年贼至被毁,同治八年署知县陈本仁奉拨茶监厘项就地重建,一如前式”[7]66。
其二,重筑神坛、寺院、道观等。这些民间信仰象征和开展日常祭祀、祈福活动场所,如风云雷雨山川坛,“同治十年(1871)知县周溶奉拨茶厘公款重建”[7]72;先农坛,“同治十年(1871)知县周溶奉拨茶厘公款重建”[7]72等。此外还有宗族或个人重修的,如忠烈庙,“同治元年(1862)贼至庙毁,汪姓重建”[7]73;又如岳忠武王庙,“咸丰甲寅兵燹圮”,邑人洪道善于同治十二年(1873)“劝捐重修”[7]75。寺院、道观大都为民间重建或宗教人士募建,如永慧庵,“咸丰五年兵毁,王姓重建”[7]94;天宝庵,同一年被毁,也为王姓重建[7]94;善庆禅院为僧人重建,“咸丰五年(1855)兵毁,同治间僧复建”[7]94。
其三,重建宗族。唐力行认为,“要恢复宗族社会秩序,首先要恢复宗族记忆”[18]85,而追寻宗族记忆的重要依据便是族谱。如祁门红紫金氏宗族,“房屋烧毁一空,男逃女散,惨不胜言。因谱牒散失,幸同治初年,四方平静,查考宗谱,半属遗亡”[20]92,战后就及时开展了宗谱编纂工作。又据光绪二年(1876)《祁门倪氏族谱重修族谱序》载,“粤寇披猖压境,吾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先君子不禄又十余年矣。本逢国家中兴之□奋武揆文、四海肃清、万端毕举、型仁讲让之化,意在斯乎……居数月更宣冬祭□程事毕与九祠,踞父兄谋修斯谱……于是筹财用、选贤体,相语以事无欲速,明年各考世系而兮之又一年,始集宗支而合之”[19]。
此外,兵燹后地方风气整顿也很重要。因练团带来的赌风以及吸食鸦片的陋习均得到整顿,1907年刘汝冀任徽州知府时曾推广戒烟,地方乡绅也立公约禁止赌博和吸食鸦片,如胡元龙“为了禁止赌博、吸鸦片之事,于清同治四年,报准政府,立《严禁烟赌》石碑于村中广场”[21]177。
2.4 重振文教事业
祁门自古重教兴学,虽“偏隅,素瘠苦,蒙童入学随处皆然”[10]602,故而在兵燹后大力重振文教事业,也就成为所有祁门人的共同心愿。
一方面,从文教场所重建开始。如文庙的崇圣祠遭兵燹倾圮,“戊辰知县蔡会邑绅谨移建于明伦堂上”[7]73;文昌宫,“咸丰间兵燹残毁,同治九年(1870)知县周溶奉拨茶监厘项兴修规模如式”[7]73。又如学宫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学校,“同治五年(1866)知县蔡钟率绅重修大成殿、明伦堂”[7]160,原建于学宫外的忠义孝悌祠,“咸丰甲寅(1854)兵毁,同治八年(1869)许马二姓重建”[7]174。
说到文教场所,就不得不提当时最负盛名的学府——东山书院。由于在兵燹中破坏严重,同治二年(1863)“知县刘端率绅士筹赀,修风教堂、朱子殿、养浩斋,建十堂肄业房舍六十九间,基址、门窗、庖厨、楼阁一如前式”[7]183。东山书院在地方官带领、士绅踊跃捐输下得以重建,遇经费不足处则“以所余筑碉之缗而益助之,经始于春三,告成于秋九,先是书院捐合万金,岁收其息以为用”[7]185。
另一方面是补救文献。兵燹中大量书籍被毁,“焚毁如省志郡邑志千百什一,几于无存。倘此时不振起而修辑之,墜绪茫茫以后,更难旁搜……兵燹乱离之后,前千百年之事不可听其涣漫而散佚,近十余年之事尤不可任其湮没而不传”[7]卷首。虽说战后安徽各府县均在补修方志,然而在清末完成的并不多,徽州也只有祁门、黟县和婺源编修成功。祁门能在兵燹后十年内完成县志的重修,既是在地方官带领下,又多有民间捐输,如许尚诚、程师达均“修志捐五百金”[7]343-344。新修县志刊刻时,亦不少民间捐输,如郑英珠“捐洋钱六百枚”,陈有光“捐曹平纹银二百两”[7]465。
政府官员对重振文教事业也是非常重视的。战乱期间,祁门文教停滞,如“曾爵相(曾国藩)驻祁门,时拨五百金为考课费”[7]185;又如蔡钟“同治四年知县事,寇氛甫靖……百姓安之乐于课士,每月亲临考棚,扄课一次分俸给赏公余喜与诸生,剖晰文艺虽病不倦”[7]219。
3 咸同兵燹后祁门重建特点
从上述可见,祁门灾后重建除了具有以官带民、以人为本等特点外,还有如下特点:
3.1 广泛参与
在祁门地方官带领和号召下,商人、士绅、普通民众甚至宗教人士均参与重建,不过主要力量还是是政府、商人和士绅。
重建中地方官的领导作用必不可少。林用光于咸丰七年至十一年(1857-1861)任祁门知县,此间他曾着手关帝庙重建,但因不能继续任职,加之战事未平,直到同治八年(1869)知县周溶任上,才完成关帝庙重建。祁门灾后首任知县为蔡钟,他曾带领士绅主持重建文庙、学宫,对文教、农业生产的恢复做出贡献,但“(同治)七年以劳致疾,卒于官”[7]219。周溶于同治八年(1869)任祁门知县,在他任职期间,重建了大部分官方祭祀坛庙,且招徕民众开垦荒田,复兴文教,并在其主持下完成了同治《祁门县志》纂修和刊刻,是祁门灾后重建史的关键人物。
重建必须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才能顺利进行。据县志载,祁门地方官多奉拨茶厘税重修官署以及官方坛庙。茶厘即对茶叶经销所征的附加税,自同治六年(1867)起“裁去引捐厘三票,改用落地税照以归简便,其税仍完二两四钱八分,于内划出一两二钱准作捐银”[7]149,这些茶商交作捐银的税成为祁门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祁门茶商在灾后救济中也大力捐助,如同善局“施棺以埋道毙者”[17]87,祁邑茶商“每箱取规银三分以助”[17]87。祁商在祁门近代转型中,尤重教育,茶商在创办高等小学中亦有投入,“学务经费惟官立高等小学为最,岁入墨银叁千余元。西乡学堂抽园户茶捐,岁墨银贰千余元,南乡学堂岁墨银一千八百余元,东乡初等小学四所约共墨银六百元,皆取之园户茶捐”[10]607。八国联军侵华后,全国开始建立起警察制度,祁门也不例外,警察经费则“由商家月捐约计四十余元”[10]607。
重建当然也离不开士绅支持。士绅阶层处于经济和文化的上层,有财力和学识支持地方政府重建工作。地方官员也积极号召士绅参与重建,如文庙重建便是知县蔡钟号召邑绅参与完成。《附捐输告成皖南道张凤翥奖谕告示略》嘉奖祁门士绅重修东山书院,“该书院自兵燹后荒废已久,赖各该绅等实力举济或尽心经画或倡首乐输或董理而罔易初终或劝捐而不辞劳瘁”[7]184。
3.2 突出重点
祁门重建能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分阶段有序扎实推进,且每一个阶段都有重点,各方面工作相辅相成。
比如说,在灾中以及灾后之初,以活人为先,有“东南邹鲁”之称的徽州,无处不彰显儒家民本思想,祁门为徽州一县自然不会例外。然而救济只是一时救急,与此同时优先恢复生产才是稳定社会最根本途径,祁门战后地方政府紧锣密鼓地招民开垦、恢复生产。而社会秩序稳定又是恢复生产的前提条件,祁门在抓紧恢复生产之时进行了从官方到民间的秩序恢复。地方政府战后注重办公场所的重建,如官署,以恢复政府的社会控制力。民间社会则表现为重修宗祠和族谱以达收族目的。
再比如说,祁门自古文风昌盛,社会稳定后,恢复文教提上日程。在地方官员带领下,祁邑民众积极参与到文庙、学宫、文昌宫的重建中来。东山书院历来是人才辈出之地,祁门自古进士及第者和中举者大都出自于此,东山书院重建也成为文教复兴的重点。
3.3 因时变革
咸同兵燹后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之时,尤其清末,皖南一隅的徽州当然包括祁门在内也开始了政治、经济、教育的变革之路。
政治方面,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后,1909年9月于各省成立省级民意机构,而咨议局议员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意代表选举。《祁门县赵令元熙申报选举人名册批》的批示便是祁门选民意代表的情况,刘汝冀《陶甓公牍》中详细记载了祁门选举人名册,虽困难、缺陷重重,但开祁门民主风气之先。
经济方面,清末采取了一系列振兴近代农业的措施,如设立官办机构农工商局和民间社团农会,鼓励编印外国先进农书、引进介绍西方近代农学。1900年左右徽人程方壶编写《徽州劝兴农务支会启》分为十条兴农纲要,“一兴修水利,二垦辟荒产,三劝兴蚕桑,四考究茶叶,五稻田改良,六荒山扞树,七肄业农学,八畜牧动物,九稽查保甲,十劝办团练”[22]2-5,虽只有六七千字,但涉及范围却较广泛,是近代徽州发展农业的纲领性指导。其农林牧副渔的农业体系完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保卫,从农业理论到农业实践,从农学研究人才到农业技工培养,层次清晰。但徽州真正开始经济、农业方面的改革,要到刘汝冀任徽州知府。光绪三十三年(1907)刘汝冀任徽州知府,“面对洋货充斥,经济衰退之状,刘汝冀从振兴农工商和实施宪政入手,拉开了徽州近代改革的序幕”[23]92。在发展实业方面以茶叶为代表,正如刘汝冀所言近代徽州“茶木两大宗实阖属人民命脉所寄”[10]563,祁门茶业因祁红创制重新焕发生机。传统工艺已经难以跟上世界潮流,刘汝冀认为徽州发展实业不仅需要资本注入,还需要先进的技术,“急需扩充者如祁门之磁土,岁可供全国陶业之用……倘得大化学家、大矿学家、大资本家赓续而合作之,更足开万世无穷之利”[10]563。
教育方面,清末废科举后全国办新式教育之风盛行,祁门各地新式小学堂也有所发展。祁门红茶创始人胡元龙开祁门办新学之先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平里创办南乡乡立高等小学堂[24]857。东山书院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也开始革新,就地改为高等小学堂。祁门地方政府则创办了县立高等小学,以及西乡乡立高等小学。
3.4 夯实基础
美国著名汉学家芮玛丽认为咸同兵燹后地方重建的成败在于“传统社会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重新整合”[25]154,以及地方行政官员重新运用传统方式管理社会,“利用社会力量,特别是利用地方士绅来作为他本人和他辖下的广大民众的桥梁”[25]154,可见恢复士绅阶层对地方的管理,是重建的重要任务之一。
士绅大都是受过儒学教育的群体,他们广布乡村,得到基层群众的尊敬,并且受到政府信赖。但兵燹后祁门士绅数量缩减,那么恢复士绅在地方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从朝廷层面看必先恢复儒学教育和科考,恢复士绅数量及其管理力度和效度,因此无论中央还是祁门地方都非常注重儒学教育的复兴。
徽州是宗族社会,宗族作为管理地方的自治机构,通过谱牒和宗祠管理宗族成员,而宗族族长和谱牒编纂者大都是士绅阶层。祁门恢复士绅阶层在地方作用,主要体现在士绅带领各氏族完成宗祠重建和族谱编纂,如倪望重在兵燹后重修《倪氏族谱》中提及修谱是为了“达人情、联宗谊也,故修族谱以明之。俾论世而犹知一本居乡关而犹若一家亲亲长长之义,勃然而兴”[19]。祁门通过宗族重建,唤回宗族记忆系统,巩固社会基础,正如唐力行所说:“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因为它与地方社会秩序重建是一致的。传统中国社会特有的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交织而成的完善的记忆系统是中华文明历经劫难而长盛不衰的内在机制之一”[18]82。
4 结语
清代结束时,兵燹已过近半个世纪,祁门重建取得一定成效,如地方秩序稳定,村落依旧聚族而居,战时被破坏的公署得到重建,文化符号的象征如坛庙、寺观等部分得到重建。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后,山陬小邑的祁门也看到民主曙光。祁门实业发展仍然以本地资源为中心,如祁门红茶和瓷土。文教得到恢复,并且创办了一批近代小学堂。然而咸同兵燹后,徽州“窖藏一空”,摧残极大,祁门虽完成部分表面的重建工作,但人口锐减、乡村士绅阶层缩小是不争的事实。祁门聚族而居的现实,使近代风气进入困难,民众思想保守,改革困难重重。加之吏治腐败、徽商衰落,祁门想要恢复明清以来的辉煌,难以实现。
注释:
①学术界就咸同兵焚对徽州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有专论,如郑小春《从繁盛走向衰落:咸同兵焚破坏下的徽州社会》(《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而关于徽州社会重建,却未见较为系统的探讨,仅卞利在《近代徽州社会与文化发展论纲》(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转型安徽与跨越发展安徽省社会科学界第六届(2011)学术年会文集》,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3页)有所论列。
[1]民国.董氏族谱·凤游续修族谱序[M]//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二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2]郭卫东.转折之地:曾国藩在祁门[J].安徽史学,2014(3):14.
[3]陈登原.国史旧闻: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郑小春.从繁盛走向衰落:咸同兵焚破坏下的徽州社会[J].中国农史,2010(4):88-96.
[5]安徽通志馆.安徽通志稿·大事记[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201-202.
[6]刘伯山.徽州文书:第2辑:第2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集55:同治祁门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8]黄崇惺.凤山笔记[M]//许承尧.歙事闲谭[M].合肥:黄山书社,2001.
[9]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0]管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管箴书集成10:陶甓公牍[M].合肥:黄山书社,1997.
[11]温林.曾国藩全集:奏稿(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2]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集51:民国歙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1.
[13]殷安如,刘颍白.陈去病诗文集: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4]冯剑辉.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考辨——兼论徽州成同兵燹[J].安徽大学学报,2007(2):120.
[15]穆宗实录:4[M]//清实录第4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祁门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祁门旅外商业特点初探[M]//祁门文史:第1辑.祁门:祁门县印刷厂,1985:111-118.
[17]祁门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祁门旅外商业特点初探[M]//祁门文史:第2辑.祁门:祁门县印刷厂,1988.
[18]唐力行.“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动乱与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以徽州绩溪县宅坦村为个案的研究[J].史林,2007(2):82-94.
[19]倪望重.倪氏族谱[O].刻本.光绪二年(1867):重修族谱序.
[20]民国.祁西金氏族谱:卷八:谱略[M]//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徽学:第八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21]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一辑6[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2]程方壶.徽州劝兴农务支会启[M].刻本,清末.
[23]卞利.近代徽州社会与文化发展论纲[M]//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徽学:第八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24]安徽省地方志委员会.安徽省志人物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25]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M].房德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钱果长]
K03
A
1674-1102(2016)04-0086-06
10.13420/j.cnki.jczu.2016.04.023
2016-04-13
孙唤(1991-),女,安徽旌德人,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徽学;余敏辉(1966-),男,安徽黟县人,淮北师范大学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徽学,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