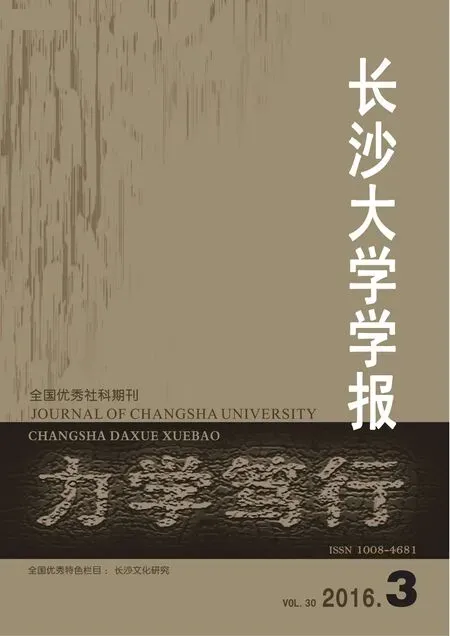唐代儒学权威失坠表现及原因分析
2016-03-26刘亮红
刘亮红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01)
唐代儒学权威失坠表现及原因分析
刘亮红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01)
摘要:在唐代三教努力争夺思想和社会地位的背景下,儒学相比同时的佛道二教,不仅自己原来被统治者所倚重的纲常伦理在佛道的融合吸摄中优势弱化,而且在理论的思辨水平与完备方面因对佛道二者吸纳较少而相对落后,在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终于权威失坠,陷入了自身治国无力治心无门的现实窘境。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其权威失坠主要表现为:明于礼义,暗于知心;形式繁荣,发展不力;士风颓坏,儒家无策。
关键词:唐代儒学;经学;权威;治国乏力;治心无门
唐立国后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在唐代统治阶段思想中,他们既不能放弃儒学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作用,也不愿意对“有助王化”的佛教和道教势力进行实际上的限制,这就形成了唐代三教并存的局面。至中唐时,道教空前兴盛,这时的道教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的社会影响,而是从义理与人生哲学方面整合儒佛之学,倡导“性命双修”与“理身理国”,既融合儒家忠君孝亲的纲常伦理以满足治国理政的需要,又借鉴吸收佛教的思辨哲学及心性修养理论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进而传播日广、影响日深,成为与儒家相抗衡的思想力量。这时的佛教也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化进程,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术。不仅如此,佛教因其“由博而约、由繁而简的发展趋势”[1]吸纳着众多信徒,抚慰着世人普遍不安的心灵,成为又一与儒家争取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劲敌。而此时的儒家,一方面“依持自己占据国家政权的地位,作威作大,不肯低下头来”[2],对外来的佛学、民间的道教均持一种排斥的态度,致使儒学在心性论及宇宙观方面,不及佛道二教;另一方面也因汉代以来经学的固步自封、注释繁琐限制了自身理论的发展而停滞不前。相比佛道二教,此时的儒学不仅原来被统治者所倚重的纲常伦理在佛道的融合吸摄中优势弱化,而且在理论的思辨水平与完备方面因对佛道二者吸纳较少而相对落后,在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权威失坠,陷入了自身治国无力治心无门的现实窘境。
一明于礼义,暗于知心
早在六朝时代,东晋宗少文在《明佛论》中就借《庄子》的“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之说讥评儒学是“明于礼义而暗于知心”[3]。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中唐以前的儒学在为统治阶级与全社会提供意识形态指导的同时,却没能从理论上解决普通民众普遍关心的生死寿夭问题,对于客观世界的解释也显得粗略[4]。这也是唐代佛教和道教得以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
礼是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历代统治者都极重视礼的作用,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不学礼,无以立。唐人亦极重礼,《贞观政要·礼乐篇》记唐太宗曾与诸臣论礼,而且提倡以礼易俗,谓“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高宗显庆年间,郭瑜为太子率更令,尝云“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非礼无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唐德宗《令应选人习三礼诏》云:“王者设教,劝学攸先。生徒肆业,执礼为本……然则礼者盖务学之本,立身之端,居安之大猷,致治之要道。”[5]《新唐书·礼乐志》记载了唐代前期修《贞观礼》、《显庆礼》的概况。
《大唐开元礼》沿《贞观礼》、《显庆礼》发展而来的,是对秦汉王朝以来封建礼仪制度完备化的总结。至此,唐代儒学之明于礼义可见一斑,而儒学暗于知心则为古今学人所共诟,唐君毅总结汉代以后的儒学概况时对比了儒学在探索宇宙、人生与心性方面与佛教的差距与不足:
方中国魏晋六朝至隋唐佛学大盛之日,中国传统之儒者,正从事于经注与经疏。其智慧心思之所注,皆唯及于世间礼乐政教,人生日用之常,而不能外是。此与佛教高僧大德之期佛果之究竟,而穷法相之广大,探心识之精微,极语言之设教与当即立教之妙用者,诚不可以相及[6]。
重性命之道的李翱也将儒学的衰微归结于“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皆入于庄、老、列、释”[7]。刘禹锡也持同样观点,“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寝息”[8]。
华严五祖宗密认为,就惩恶劝善的功用而言,三教的教化作用相似,但以对“本源”的推究为标准,则佛教居上,较委婉地道出儒学在解决人的本质和性命本源问题的理论建构方面的不足,“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9]。
任继愈认为在隋唐时期哲学的中心议题已是心性问题,但这方面儒家发言权不够:中心议题己转向心性论,只有在心性方面取得发言权,才可以在哲学上有地位。这一方面佛教领先,道教次之,儒家比较起来最落后,儒家只是靠其政治理论和统治经验被统治者所重视[10]。儒学与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已经脱节,在中唐道佛二家治国治身治心之道兼具的双层冲击下陷入治国乏力治心却无门的窘境,“官方确立的以正统儒学是非为是非的界限已经模糊……这种本来就很有诱惑力的经典(老庄之学)就使士人对传统的知识与思想(儒学)产生了离心力,至少也使他们原本相当清楚的思想世界的边界变得混乱起来”[11]。
“明于礼义而暗于知心”的批评可谓切中儒学要害,也道出了佛道之所以在唐代能大行其道的缘由。唐代中叶以后的社会动乱为重心性的佛、道二教的进一步蔓延提供了土壤,加之“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因而佛、道教大盛,儒学在佛道的强势冲击面前明显乏力。
二形式繁荣,发展不力
因为儒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故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唐代统治者也不例外,初唐极力倡导经学,把尊儒崇经、推行仁义之道作为治国之本,并采取了许多复兴儒学的措施。唐高祖颇好儒臣,早在建义太原之时,就采取了重视儒学教育的措施,于义宁三年五月,曾令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上中下郡等各级官学令官员子孙入读,武德元年,又下诏令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后又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此举首创唐代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雏形,表明了唐初统治者兴儒重教的努力与决心。
继高祖之后,太宗更加深刻认识到儒道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即位不久即置弘文学馆、选弘文学士、立孔庙、征天下儒士为学官、增筑国学学舍等,尤为后人铭记、影响重大的莫过于刊定《五经正义》并令天下传习了。
唐玄宗重视儒学立天下之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有助王化、教化治世的功能,将儒学作为文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以为《儒学篇》”[13]。
但唐诸帝都一样,他们崇尚儒学主要不是要从学术层面要恢复汉儒传统,而是看重其政治教化功能,正如玄宗所言,“宏我王化在乎儒术,能发挥此道,启迪含灵”[14]。玄宗时提高经学在科举中的地位,加大经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以期通过政治手段保证儒学的权威性地位。但由于统治者过分强调经典注疏在科举取士中的作用,使其成为考试唯一的评判标准,导致考试范畴渐渐僵化,限制了经学的发展,使儒家文化失去了精神动力而走向衰微,陷入重形式轻实质的困局,并导致传统儒学的政治理论,隐而不彰;传统儒学的道德学说,郁而不明。
可见,在统治者的重视下,立孔庙于国学,兴太学,重著述,唐代儒学再现了博大恢宏的局面。但“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则天称制以后,一味佞佛媚道,对待儒学,表面上虽准贞观旧制,但实际上“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15]。
对儒学社会实用功能的过度重视,事实上仅仅实现了儒学表象上的繁荣,却无益于恢复传统儒学的本体信仰。儒学不再是向里由正诚格致来安顿生命、升华生命的路径,其仅仅是“讨论经义,商略政事”的外王之道。“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要发挥其现实功能,除了用政治手段保证其权威性地位之外,更主要的是凭其内在的义理吸引人们,否则只能是沦为一种口号,难以成为维系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16]
中唐儒学即遭遇到这种发展困境。儒家形式繁荣却发展不力的困境在《五经正义》中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五经正义》的制订和颁行,使唐初经学完成了内部的统一,从而改变了东汉以来儒家经说纷纭矛盾的局面,使经书注解义疏得以统一,儒家主要经典有了音训、文字、义疏彼此配套的标准定本,标志着南北经学的统一,这无疑有助于当时学者客观、准确地了解和把握经籍,解决了“文字多讹缪”、“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问题。官方对于儒家经典的统一,使儒学走向自身发展的高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17]。这对于巩固政治上的全国大统一无疑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传统经学远离于社会现实,通经致用的儒学传统荡弃泯灭,儒生们不究旨义,惟事浮艳,逐渐走入死胡同”[18],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经学家对义理之探求:“学术定于一尊,使说经之儒不复发挥新义,眯天下之目,锢天下之聪。欲使天下士民奉为圭臬,非是则黜为异端,不可谓非学术之专制矣。”[19]
尽管孔颖达在编纂《五经正义》时已经感觉到单纯靠重复儒家教条已经不足以对抗佛道二家在思想领域的攻势,想尽力挖掘五经中的“心”“性”“情”“欲”及佛道常有的“动” “静”“理”“道”等概念,尝试将“心”“性”“欲”与儒家礼法规范结合起来,提出:“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醨,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20]
但这种非常粗略的探讨,在佛道二家,尤其是在佛教渊奥的义旨、精微的教义面前仍然显得有心无力,楚楚可怜。整体而言,经学内圣的传统精神、通经致用的儒学传统在《五经正义》为代表的中唐儒学中是缺位的。 在《五经正义》的修撰过程中,“儒学思想家们既没有创造出完整的宇宙生成体系或高明的哲学本体论,也未能建立系统的认识论或心性修养学说……缺乏本体论哲学和严密的思辨能力,注重政治制度化的经学,忽视了对心性、个体、人生的现实关怀,其体系内部己失去了经学继续发展的空间和张力……无力担负以思想统一来保障政治统一的任务”[21]。
从《五经正义》的修撰“注重于儒家特有的社会实践功能的利用,反而忽视了经学内圣的传统精神……经学统一后的儒学,虽然实现了它在形式上的繁荣,而对于传统经学的义理精神来说,却没有得到实质上的发展”[22]。《五经正义》的修撰结果则是,本来作为主流知识与主导思想的儒学在权力的支持下,成为垄断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僵化的思想教条后,就会失去其内在的信仰力量,失去了与之相符的社会秩序与结构,成为悬浮在生活世界之上的文字形式,失去了诊断和批判当时社会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导致儒学权威失坠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士风颓坏,儒家无策
“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袭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23]唐人李栖筠这段话既指出了唐中期后一士风颓坏的现象,又指出了士风颓坏的原因。贞元十九年(803)正月,当时的左承相贾耽针对士风颓坏的现象,曾颁布《劝善经》一道,以期用佛教净土门的方法“劝诸众生,每日念阿弥陀佛一千口”来阻断恶欲,用从道教经典中学到的五种病死的威胁,来劝人行善,以改善当时世风日下的颓势,这里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原来儒家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似乎已经对这个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崩溃束手无策,于是不得不让开一块地方,让佛教一起与道教从旁门进入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主流世界。
台静农曾经指出了那个时代的士风颓坏,如士人以浮辞丽藻为文才,自甘作弄臣依附贵族与王室,结为朋党钩心斗角,普遍的道德沦落等等[24]。葛兆光在其专著《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了儒学对当时人们道德失落的软弱无力与束手无策,认为当时传统的礼法制度以及伦理道德观念,已经无法针对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批评。不要说遵循法度,他们不再以社会事业的成功为最高理想,无力对这种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提出有效的疗救方法,勤俭、克己复礼、亲政爱民等等,只能不断重复老一套的勤俭、克己复礼、亲政爱民等传统的药方。
不仅如此,随着唐代文化的开放与民族的大整合,文明的冲突与较量在悄悄地进行,各个民族文化相交融的结果之一,就是使传统的以汉族文明为中心的伦理准则渐渐失去普遍的约束力,使传统的行为模式渐渐失去普遍的合理性[25]。因此,针对外来民族文化在唐代流行的现象,当时的士人吕无泰曾提出一个表现很简单,实际上却很深刻的文化如何保持其民族性的问题:“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26]这句话也再次映证了儒学“依持自己占据国家政权的地位,作威作大,不肯低下头来”的保守与排外心态,在文化大交融的大背景下,儒学权威的失坠似乎也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参考文献:
[1]赖永海.中国佛性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范文澜.唐代佛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程遂营.卫儒、逆儒与异儒——唐代儒学及其贫困原因刍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5]德宗·令应选人习三礼诏[A].全唐文(卷52)[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李翱.李文公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刘禹锡.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A].刘宾客文集(卷4)[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9]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2·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2)[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2]刘昫.礼仪志4[A].旧唐书(卷42)[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13][15]刘昫.儒学传(上)[A].旧唐书(卷189)[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14]元宗·追溢孔子十圣并升曾子四科诏[A].全唐文(卷31)[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6][21][22]张巍.中晚唐经学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17]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中国经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19]刘师培.国学发微[A].刘师培全集[C].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20]礼记正义·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3]欧阳修,宋祁.选举志上[A].新唐书(卷44)[C].陈焕良,文华,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7.
[24]台静农.论唐代士风与文学[J].文史哲学报,1965,(14).
[25]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A].中华文史论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6]欧阳修,宋祁.宋务光传[A]. 新唐书(卷118)[C].陈焕良,文华,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7.
(责任编校:简小烜)
An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and Its Reasons of the Loss for the Authority of Confucianism in Tang Dynasty
LIU Lianghong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Hu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Changsha Hunan 410001, China)
Abstract:In Tang Dynasty,Buddhism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ll made their great efforts to get the highest status in ideological and social. Compared with the Buddhism and the Taoism in the same time, the principal relationships and constant virtues of the Confucianism relied on heavily by the rulers not only had been weakened,but also fell behind the Buddhism and the Taoism. All of these had led to the loss of the authority in the ideology and the culture, and the Confucianism had fallen into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and been disable to rule the nation and the hearts.
Key Words:Confucianism in Tang Dynasty;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authority;disability to rule the nation and the hearts
收稿日期:2016-02-24
作者简介:刘亮红(1977— ),女,湖南桃江人,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统一战线学。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16)03-007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