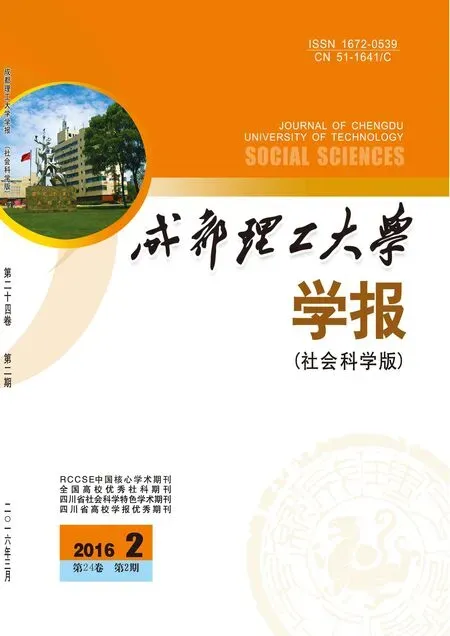论鲁迅文学创作中拜伦式英雄的中国化
2016-03-25周可戈刘永志
周可戈,刘永志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51)
论鲁迅文学创作中拜伦式英雄的中国化
周可戈,刘永志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610051)
摘要:清末文坛的拜伦热给鲁迅带来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漂泊、孤独和具有反抗气质的“拜伦式英雄”已经深入到鲁迅文学创作的灵魂,他结合中国的实情,发掘其可利用的价值,在自身的文学创作中使拜伦式英雄中国化。鲁迅在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一些中国语境下的拜伦式英雄,对拜伦式英雄这一异域形象经历了由乌托邦式的憧憬到遇到卷土重来的传统势力后在妥协中求生存的转变,不同层面地展现出拜伦式英雄的质疑精神和抗争元素。其小说精心刻画的拜伦式英雄为改造国民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关键词:拜伦式英雄;中国化;质疑精神;抗争元素;改造国民性
鲁迅并不是第一个介绍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的中国人,在晚清和民国这个“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很多学者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清末文人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王国维、胡适等人在20世纪初通过图片、译介和传记等形式为国人极力引荐这位19世纪蜚声欧洲文坛的浪漫主义诗人及作品。1908年2月和3月,鲁迅署名令飞在《河南》杂志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发表了一篇介绍浪漫主义流派的美学论文——《摩罗诗力说》。“摩罗”是梵语音译,意思是恶魔,“摩罗诗力说”就是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摩罗诗派”就是浪漫派,19世纪初期盛行于欧洲,是以拜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反叛传统、斗志昂扬的浪漫主义流派。处于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时期的清末文坛刮起的这股“拜伦风”无疑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时文人对拜伦的热忱都源于拳拳报国之心。鲁迅后来撰文提到,那时拜伦比较为中国人所知,是因为“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兴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反应。”[1]220-221有学者认为,清末民初的学者对拜伦的定位停留在“反抗斗士”的形象上,文坛对拜伦本人的关注高于其诗作,因而传记类的译介远远多于对其诗歌的翻译[2]83。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忽略了拜伦的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著名文学评论家阿英指出,晚清的小说,翻译多于创作,而中国的创作就是在这汹涌的输入情形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3]180。 实际上,外来文学的传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推翻帝制以后。鲁迅年轻时读了不少拜伦的作品和关于拜伦的评论,非常推崇拜伦精神,漂泊、孤独、具有反抗气质的“拜伦式英雄”已经进入到鲁迅后来的创作中。鲁迅结合中国的实情,对“拜伦式英雄”进行了中国化改造。这里试从形象学的角度解读鲁迅早期及中期小说创作中塑造的拜伦式英雄。
一、拜伦式英雄的引入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关系的自觉意识中[4]4。 鲁迅东渡日本留学的初衷是去异域寻找救国良方,初到日本所读的外来书籍和特殊的求学经历拓展了他的视野,也使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有了全新的认识。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尼采的传,拜伦的诗……”。[5]11毫无疑问,给西方带来巨大影响的尼采超人哲学和拜伦质疑权威、不畏强暴乃至孤身奋战的精神使鲁迅捕捉到了来自精神的力量。他非常崇尚拜伦的质疑精神和反叛传统的气质,视拜伦为“精神界之战士”。众所周知,拜伦因为个人问题自1818年从英国出走后,对传统、世俗彻底失望,创作的诗都是反抗意识极强的。而同时,一度在欧洲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被神圣同盟的复辟运动淹没,主张人文主义的启蒙思潮也有倒退到基督教这一扎根于欧洲两千多年的精神枷锁的趋势。这时,拜伦敢于站出来对“万能的主”说“不”!无论是《海盗》的主人公康拉德,还是诗剧中的曼弗雷德或该隐,都不会屈从于权威,也决不委曲求全。如曼弗雷德不因自己犯下过失而被精灵引诱,更不愿向上帝忏悔,祈求主的宽恕,他说:“圣人没有权力,祈祷没有魅力,忏悔没有纯洁的形式,没有外在的表征,没有斋戒禁实,没有痛苦哀伤,也没有比这些更大的深沉绝望的内心的苦痛。”[6]85他要为自己审判,自己把握生死的权力。而诗剧《该隐》更是解构了《圣经》里的人物,上帝被刻画为嗜血的暴君,路西弗成为先知,该隐成了被他引导而觉醒的人。在上帝接受了弟弟亚伯献祭的羊羔而把他的祭品果实吹倒后,该隐质疑道:“闻见烧焦的肉香,冒气的血味,听见哀鸣不止的母羊的痛楚……耶和华他才欢饮吗?”[6]240虽然这些人物的命运不是死亡就是流浪,但他们都展现出反叛传统、不惧权威、永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是孤身奋战的英雄,即拜伦式英雄。拜伦式英雄在西方影响巨大,连著名诗人歌德都承认《浮士德》从《该隐》中吸取了力量。身处国外,又处于社会动荡时期的鲁迅也开始考虑将这一异国形象引入国内。
鲁迅弃医从文的初衷是改变人的精神,由“立人”而“立国”。“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时刻激励着他,他希望通过引进有反抗意志的作品和自己的文学创作来改造国民性。正如他在《呐喊·自序》所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因而“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1]417。鲁迅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近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状况,必须从思想领域做起。只有在思想领域引进质疑精神和抗争意识,而不是单纯从西方引进武器或进行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而反抗精神正是愚弱的国民所欠缺的,因为多年的封建专制已经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仅存奴隶的顺从。鲁迅在初期的文学创作中,已经注意到“古训所筑成的高墙”使人们“连想也不敢想”;至于百姓,只能“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就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7]81-82在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中,狂人俨然化身为一个拜伦式英雄,质疑精神已经上升到觉醒的层面。他发出了惊世之问:“从来如此,便对吗?”,又大胆地将号称“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解构为“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是鲁迅自《摩罗诗力说》以来,隐忍十年后以反叛传统为主题的一鸣惊人之作,而这次投笔落实了他在《摩罗诗力说》一文提出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主张。《药》的主人公夏瑜被捕后在监狱中说“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然而他的话被康大叔转述后却成了“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他认为夏瑜说的简直不是“人话”,夏瑜对封建权威的解构无人认可,狱卒感兴趣的只是在他身上搜刮值钱的东西,搜刮无果后便将他殴打一通。茶客们听了康大叔的讲述后无不附和,一致认为夏瑜“发了疯了”。可见封建专制下的中国“愚民政策已集了大成”[8]182。狂人、夏瑜对封建道德和封建专制的解构与曼弗雷德、该隐对上帝的反叛如出一辙。鲁迅在《呐喊》中塑造的“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其蓝本就是拜伦式英雄,他把这一异域形象吸纳进自己的小说中,让颠覆传统的异域因素进入了本土,给当时的文坛乃至思想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二、拜伦式英雄在中国的困境
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是作者创造或再创造的结果[9]210。 鲁迅对拜伦的接受“既不同于梁启超那样力图书写宏大的民族进化与竞争史,也不同于苏曼殊那样致力于表现个人灵魂创伤和整合的历程,而是在两者的巨大张力之间发现了‘现代’的若干矛盾。他义无反顾地背叛了传统,却又在‘现代’的门槛上举步不前”[10]。 辛亥革命前后多变的时局使鲁迅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拜伦式英雄在他心中的乌托邦形象渐渐模糊、淡化了。鲁迅中期塑造的英雄与拜伦式英雄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在杂文中,他把夏瑜这样的拜伦式英雄称为“天才”,然而,这样的形象是“乌托邦”式的,在中国几乎不能找到生存的土壤。鲁迅意识到,狂人、夏瑜的奋力抗争是孤独甚至徒劳的,他们只是为数不多的“独异个人”,决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奴性十足的大众已经沦为“庸众”,只能充当麻木不仁的看客,甚至还会为一己之利出卖或吞噬为他们争取自由权利的英雄。“独异个人”在“庸众”面前根本没有影响力,更谈不上与权威对抗。所以,他塑造的“独异个人”不会像查尔德·哈罗德这种“最不适合与人为伍的人”,在拜伦笔下还能生活得“并非空虚徒劳”,能“像一张无声的七弦琴”,“长留在人们记忆中。”[11]336鲁迅清晰地认识到,封建专制泯灭个性、扼杀天才,甚至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都没有,中国的国民性最缺乏“诚”和“爱”。即使帝制已经被推翻,封建专制的遗毒仍然存在。因而,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角色在《怀旧》、《药》、《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中比比皆是,狂人、夏瑜并没有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占很大篇幅,毕竟中国社会并不“尊个性”、“张精神”,个性主义总是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孤独天才在庸众中若隐若现,被归为疯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由他们率领大众推翻蒙蔽人心的旧秩序实在太渺茫了。鲁迅不屑于做孔乙己、陈士成那种旧式读书人,但却能在吕纬甫、魏连殳这类纠结于新潮和传统之间的新式知识分子身上找到他自己的影子,不无凄凉、无奈。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上……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1]167鲁迅在短篇小说集《彷徨》中塑造得更多、更为细腻的是一些受过西学熏陶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在理想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似乎已经不能孤身奋斗下去,有的(如子君、魏连殳)走向了毁灭,有的(如吕纬甫)最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向现实妥协,退回到连自己都鄙视的起点。鲁迅受19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先驱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和西方现代哲学创始人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影响,在面对残酷、血腥的现实时,对人尤其是孤独个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反思,原本怀着“我以我血报轩辕”的浪漫情怀,又不得不感叹“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2]166, 苦闷、彷徨甚至虚无成为他中期创作的基调。他本来批判屈原临死前才能“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1]69,却又把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放在了《彷徨》的扉页上。正如李欧梵所述,鲁迅“描写的精神界战士作家都是孤独天才的形象,是分开的个性主义者,是对社会流俗的反抗者。从贯穿全篇的他对文学的看法的陈述以及他自己与文学认同的表示,也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心理气质。”[13]20鲁迅中期创作的新式知识分子虽然具备反叛气质,却没能像拜伦笔下的海盗那样“去追寻那逼近的搏斗,把别人看作危险的变成欢乐”[14]161, 他们在中国语境下对世俗的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而在反叛传统的过程中呈现更多的是孤独。
三、拜伦式英雄在中国的改造和利用
异国形象并非异国情况的复制,“文学中对于异国形象的表述,重要的不是追求一个文化事实,而是发掘其可利用的价值”[15]3今天我们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下解读鲁迅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可以看到鲁迅的创作是面向未来的,这一点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风格俱存的鲁迅与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所不同的地方。拜伦对现实失望后采取的是逃离的态度,他借写诗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书写伤感孤寂的情绪,而鲁迅则在寂寞、苦闷、彷徨之后开始通过写作来治疗自己的孤寂,同时积极思考解救的方式。鲁迅希望通过引进有冲击传统斗志的拜伦式英雄,使读者在意识层面上挣脱传统道德对精神的束缚,逐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从而达到参与社会重构的目的。经鲁迅中国化改造后的拜伦式英雄不再止步于为自己的理想漂泊、流浪,而是更进一步,肩负起改变未来社会的历史使命。《狂人日记》篇末的“救救孩子”好似“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对未来呐喊;《药》在结束前鲁迅特意向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志士夏瑜的坟头添上了花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以《呐喊》命名,为的是慰藉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如何使拜伦式英雄从解构封建权威至抗争时不再孤独,把国民的从众心理变为团体合作,是他思考的问题。他认识到在改造国民性的历程中,妇女是不容忽视的,因而他的小说中也不乏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塑造得不像拜伦的诗《她在美中行》那样形而上,但确也有像海盗的女儿海蒂那样不惧权威、孤身奋斗的女性。
1925年鲁迅为《京报》附刊《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撰稿写道:“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1]264的确,单四嫂子虽然是个粗笨女人,但有了儿子后,儿子承载了她全部的希望;祥林嫂在前夫死后曾想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逃到了鲁四姥爷家做女佣;而豆腐西施杨二嫂却被他描写得很变态。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已经将妇女的地位边缘化,妇女在整个社会中已经沦为他者,没有地位,没有自由可言。鲁迅于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上借用俄国小说家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讲到,妇女除了把黄金世界预约给子孙外,还承载着未来的希望。虽然“子不教,父之过”的理念在中国已经盛行了几千年,但幼童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母亲的陪伴下度过的。没有觉醒的母亲,孩子就不会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推翻帝制后,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必须发生转变,否则社会的改变只会停留于表面。鲁迅关注妇女是他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旧式妇女,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创作《彷徨》时将拜伦式英雄的质疑、抗争元素引入后塑造了几个经历不幸却又具有反抗气质的女性,实现了拜伦式英雄在中国语境下的升华。祥林嫂虽然最终没有走出封建礼教的牢笼,但她毕竟迈出了出逃、争取自由的一步。爱姑,一个已经具有自我意识,能够叫板封建家庭,开始反抗传统婚姻的女性,主动提出与有了新欢而且有公公撑腰的丈夫离婚,结果被七大人这种代表封建家族制度权威的长辈以“和气生财”为由将她压制了下去。她理应认识到依靠封建家族制度来解决封建婚姻问题本来就是无稽之谈。最为悲壮的是子君,为了爱终于走出了封建家庭,认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2]112虽然她勇敢追求、苦心经营的爱的小窝由于经济拮据而崩溃,涓生最终还是抛弃了她,她选择的路“就像婚姻制一条灰白的长蛇”,蜿蜒地向她奔来,“又忽然消失在黑暗里”[12]129,她不得不回到封建家庭中去,但她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挑战必然给封建婚姻制度这潭死水带去微澜,也给爱人涓生留下懊悔和永久的遗憾。《伤逝》是以涓生的视角叙述的,足见死者对生者的影响。鲁迅安排《离婚》为《彷徨》的结束篇决非偶然,他在讲述这些女性的故事时也在启示读者:虽然祥林嫂还是在旧历年底死去,爱姑没能成功离婚,子君最终没能守住新式婚姻,这也是作者最为苦闷的,但如果社会上多出现几个女斗士呢?传统势力已经摧枯拉朽,封建礼教这“空虚中的暗夜”在这些女斗士的奋争下已经气数已尽,自由的曙光即将来临。
四、结语
晚清的拜伦热使鲁迅开始研究摩罗诗人,他提出了文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主张,鲁迅没有止步于从译介的层面上介绍拜伦及其作品,他更希望通过自身的文学创作使拜伦式英雄中国化。鲁迅一生也从事翻译,创作自然受到了异域的影响。当然,鲁迅的创作受到的异域影响是多元的。有学者认为,鲁迅的美学思想多受尼采哲学的影响,文学风格主要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语言风格是日式的。从表面上看,鲁迅不像徐志摩、林语堂那样较多地受到英美文学的影响,因为他不懂英文,还对英美文学怀有偏见,觉得英国作品大多是无聊的[16]812;以往对鲁迅小说的评论主要关注的也是他的现实主义风格,但鲁迅的创作同样具备浪漫主义风格,他在前期和中期小说中塑造的非正统的、具有反抗气质的人物形象还是他内心一直推崇的拜伦式英雄。他对这个异域形象的中国化经历了由乌托邦式的憧憬到遇到卷土重来的传统势力后在妥协中求生存的转变,然后竭力发掘这个异域形象可利用的价值,为改造国民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与拜伦塑造的反抗斗士不同的是,鲁迅在中国语境下苦心塑造的反抗传统、孤独战斗的斗士最终难以战斗下去,这是他自己的困惑,他自己也不能确定是否能解决,最终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读者。自写下《摩罗诗力说》以来,鲁迅自身已化身为“精神界之战士”,与陈规陋习作战,而拜伦精神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学生涯,他后期的杂文依然保持着“硬骨头式”的作风。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吴赟. 翻译·构建·影响: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国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阿英. 晚清小说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许寿裳. 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回忆鲁迅全编[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6]拜伦. 曼弗雷德 该隐[M]. 曹元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7]鲁迅. 鲁迅全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鲁迅. 鲁迅全集:第六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曹顺庆. 比较文学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10]余杰. 狂飙中的拜伦之歌——以梁启超、苏曼殊、鲁迅为中心讨论清末民初文人的拜伦观[J]. 鲁迅研究月刊,1999,(2):
[11]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M]. 徐式谷,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2]鲁迅. 鲁迅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李欧梵. 铁屋中的呐喊[M]. 尹慧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14]拜伦. 拜伦经典诗选[M].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
[15]姜智芹. 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6]鲁迅. 鲁迅书信集:下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编辑:鲁彦琪
On the Sinicization of Byronic Hero in Lu Xun’s Literary Works
ZHOU Kege, LIU Yongzh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610051, China)
Abstract:Byronic hero,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rifting life,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rebellious spirit, has penetrated into Lu Xun’s literary creation as a result of craze for Byron of the literary worl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u Xun started sinicization of Byronic hero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rebellious spirit with Chinese actual situation in his own literary works. He portrayed a couple of Chinese Byronic heroes in his early and medium-term novels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foreign image, which initially had a vision Utopia imagination but was later transformed as a result of confrontation and compromise in the face of returned traditional forces. With the questioning spirit and element of defiance, the Byronic heroes consciously created in his works take the firm step on remold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Byronic hero, sinicization, questioning spirit, element of defiance, remold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2-0101-05
作者简介:周可戈(1972-),女,成都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外语教学;刘永志(1966-),男,四川达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英美文化。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英国文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和影响”(13BZW106)
收稿日期:2015-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