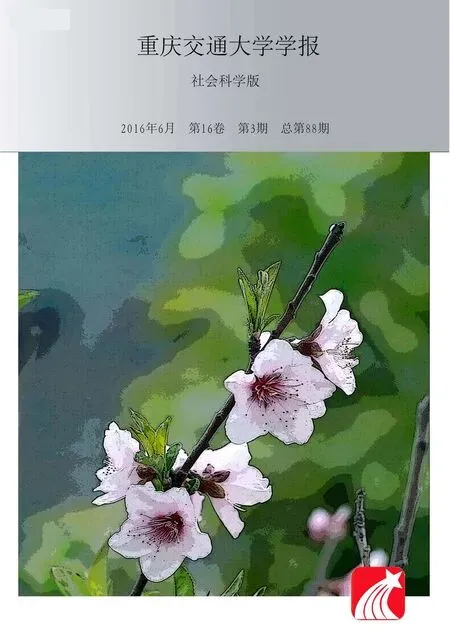《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中的新娘哥特
2016-03-23吴端明
吴端明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州 510000)
《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中的新娘哥特
吴端明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州 510000)
摘要:安吉拉·卡特的短篇故事集《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有着突出的女性哥特特质, 而其中的新娘形象更是阴郁诡异。卡特对婚礼、婚纱、新娘形象进行了突破传统的书写, 引入哥特元素,以夸张扭曲的手法书写新娘的境遇,目的是为了凸显女性在面临角色转换之际内心的巨大不安。她从女性视角出发,考虑女性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表达了对女性的关怀。
关键词:染血之室;新娘哥特;女性角色
安吉拉·卡特是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有诸多亮点,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评论家认为,“很难想象我们的文学图景如果没有了卡特(将会怎样地黯然失色),她的作品已经跳脱自身的边界而成为传奇。”[1]《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2]是卡特最为著名的短篇故事集,其中改写了读者最为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白雪公主、蓝胡子、美女与野兽和小红帽等。卡特在这些童话中大胆创新,创造了众多勇敢追求自己理想的女性角色。这些角色一改在传统童话中的扁平形象,有着丰富细致脆弱敏感的内心世界,在或诡异或恶意的外部环境中小心地探寻,去寻找自身。
《染血之室》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其中的哥特色彩。茫茫大海中孤悬的城堡、蛛网密布阴暗塔楼中的通道、颓败的古老大宅,这些都暗合了哥特公式中的“逃不出去的迷宫”要素。同时,女主角还必须面对身世可疑、性格埋藏过深的丈夫或恋人,往往带着过分的好奇心,去发掘一个不应该知道的秘密,从而面临血腥的惩罚。在对传统哥特继承的基础上,作品强调了女性特有的期待与恐惧,结合女性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从女性视角与境遇出发,表达对女性的关怀。
故事集中的两篇作品《染血之室》与《爱之宅的女主人》是哥特风中最突出的两篇,两者都涉及女性身份转变的重要时刻:《染血之室》中的平凡少女将要嫁作人妇,从女儿变为人妻,即将披上婚纱。《爱之宅的女主人》中的女主角——女吸血鬼长年穿着母亲的嫁衣,在城堡中等待她的猎物,而这一次,她等到了她的爱人。新娘身份的表面含义与深层含义,婚纱背后的深意与女性披上婚纱内心的忐忑与恐惧,在其中浮现出来。卡特在故事中似乎对珠宝与物质有一种执着,她不吝笔墨,细心地以各种华服、珠宝、配件打扮她笔下的女主角,这些珠宝对于女性而言或是一种权力的符号,帮助女性获得安全感,但是它的附着力太弱,权力总是会轻易地失去或被剥夺。婚礼发生的地点与家庭环境总是错误,让人内心不寒而栗,较之正常婚礼浪漫的背景与温馨的居家,总是令人感受到落差与断裂而重新思考婚姻与女性的境遇。
一、对女性哥特的继承与创新
关于女性哥特的起源,艾伦·摩尔曾在题为《女性哥特》的专题文章中给出了清晰的定义:女性哥特作品是指从18世纪开始,女性作家以我们所熟知的哥特元素为范式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而哥特式作品的特征就是狂想凌驾于现实、陌生胜于平常、超自然胜于自然,作者唯一确定的目的是使读者感到恐惧[3]。
女性哥特作品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注重描绘女主角的内心体验,特别放大了恐惧、绝望与无奈等情绪。第二,这种内心体验与女性的性别角色有关,与女性的生理体验、角色设定有关,与人际关系交互有关。父权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设定和寄予的责任使女性面临重重障碍和困境。第三,女性哥特作品偏好的主题是发疯、怀孕、生产、被禁锢,这些都广受评论家关注,其次是被强暴和杀害。第四,女性哥特有一些叙述范式,如备受诟病的“女性加囚禁的住所,神秘的性和超自然的威胁”[4]等情节,这些范式很容易复制,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也有一些创新。如囚禁的场所从城堡变成了幽灵似的无处不在的母亲,再到女性自己的身体。第五,从意识形态方面而言,女作家可以通过写作这一类型的作品来表达一种诉求,因为作品的一个关键词是狂想,作家可以在其中推翻男性统治的公共范畴,建构女性私人空间[5]。
从这些特征看,卡特的作品符合女性哥特传统。她的作品中有被囚禁的女性、逃不出去的居所、谜一样的丈夫、被强暴和被杀害等元素。作品中总有一个黑暗的秘密引起内心的恐惧和战栗,同时,这个秘密又和女主角的性别角色密切相关,女主角是否遵循男权社会规定的性别角色决定了她的命运。卡特对女性哥特进行了一些创新,她大胆地刻画了令人惊骇的新娘形象,把哥特元素带到婚礼中。对比之下,此前的作品大都着重女性的怀孕与生产经历,或者困难重重的母女关系,哥特的恐惧渗透到家居中。新娘哥特的构造本身充满了矛盾与巨大的反差,新娘的形象是唯美与纯洁的,传统上代表了女性生命中最光辉与最完美的时刻,而哥特是尖厉而恐怖的,将这两者并置,打破了关于新娘的幻想,撩拨开关于新娘的温情浪漫的面纱,令人反思女性从未婚到已婚的转换时刻内心的不安,以及身份转换的意义。
二、婚纱与面纱
卡特短篇故事中的新娘形象总是非常突出的,如《染血之室》中平凡的音乐少女,她结识了富可敌国的商人并很快与他成婚。他们的婚礼非常简单,在市政厅进行了公证,因为商人的前妻刚去世不久。而婚礼前一晚两人共赴剧院看剧的过程更接近传统的婚礼过程,两人在众人之中成为焦点,接受大家的注目礼。当晚,少女身上穿的是“一身轻飘飘白色细薄平纹棉胚布,胸线下横系一条银带”,正如婚礼中新娘的唯美与纯洁形象,带着开创全新生活的期待。婚纱的特殊含义在于它记载和定格了这个重要的转换时刻,女人的角色从女儿变为人妻。卡特曾经在笔记中表达过自己对于婚纱的看法:“穿上婚纱就如同少女把自己精心包装,作为礼物送出去。婚礼的这天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而她会从父亲的手中交托到丈夫的手中。婚姻是包着浪漫外衣的卖给女性的神话。”[6]38
如果戳穿婚纱表面的脉脉温情,可以看到背后的含义。故事紧接着写到了男人注视着身穿婚纱的新娘的挑剔目光。“我看见他在镀金镜子中注视我,评估的眼神像行家检视马匹,甚至像家庭主妇检视市场肉摊上的货色。先前我从不曾见过——或者说从不曾承认——他那种眼神,那种纯粹肉欲的贪婪,透过架在左眼的单片眼镜显得更加奇异。看见他以欲望的眼神看我,我低头转眼瞥向别处,但同时也瞥见镜中的自己。”卡特每次在故事中书写婚纱时都特别在意落在婚纱上的目光与不单纯心理,她的书写打破了传统上对于婚纱的唯美期待和纯洁神话。“我们以为婚纱表达的是我们,事实上它只是表达了我们的环境。婚纱上的薄纱、绸缎、花边以及所有围绕着它的浪漫氛围,掩盖了新娘的真正功能,即她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再没有其他了。”[6]108可见,她的目光具有穿透性,落在了新娘婚纱所代表的肉欲与实质的功能上。
从女性的目光出发,是对于婚纱及婚后美好生活的期待,对于角色转换的联想;从男性的目光出发,是对于婚纱背后女性身体的审视,这种目光的交错形成对比,产生了张力,即表面/内在、纯洁/堕落之间的张力。女性如果在婚姻中完全放弃对于自身的经营而沦为一个肉欲的对象,她会失去自我,而她的生活也会任人主宰。“对于那些视婚姻为最终人生理想的女性来说,穿上婚纱的这天,其实她已经死亡了。”[7]31女性在婚纱和婚姻中所寄托的过高期望,进而惟恐期待落空,成为女性内心最大恐惧的来源。
《爱之宅的女主人》中的女主角是个女吸血鬼,卡特的深厚笔力使这个绝望、无奈、麻木的女吸血鬼形象跃然纸上,“这美丽的吸血鬼之后身穿一袭古董新娘礼服,独坐在那黑暗高耸的大宅,承受画像中众多癫狂残暴祖先的眼神注视”。当误闯进城堡的男子进入她的房间,首先看到的也是她身上的衣服,“人形逐渐清晰,竟然是一身点缀蕾丝的白绸蓬蓬裙,已经过时五六十年,但显然曾是新娘礼服……那身礼服看来似乎毫无支撑地兀自悬在湿闷空气中,一袭借来的神奇外衣,一件自我表达的服装,她活在其中就像机器里的鬼魂”。
女吸血鬼在引诱猎物男子的时候身披婚纱,一直以来这个策略都是成功的。婚纱对于男性而言饱含着肉欲与性,陌生女子如此轻易把自己包装成礼物呈上,这样的诱惑不容拒绝。在引诱与接受之间,男性的目光与准则得以表露。而从女吸血鬼的角度,这套古董礼服更像是一身囚衣,象征着她不能改变的宿命,她的母亲穿过,她的祖先也穿过,指定的服装套牢了她的命运,规定了她的理想。这套礼服的古旧和穿的人的腐朽堕落相得益彰,时间不可能停止,衣服与躯体一起破败,美丽新娘的形象转化为哥特恐怖的符号。
关于婚纱与穿着婚纱的身体,卡特提出了“错误的身体”一说,她通过对她笔下婚纱意象的书写暗示一个道理:披着婚纱的躯体从来就不是“对的”,因为女性并不能达到传统新娘礼服所指代的女性理想形象。因此,身披“婚纱”的女性身体都是“错误的身体”[7]31。为了打破传统正确的婚姻叙事,故事中有时会出现令人惊骇的婚纱形象,就如《染血之室》中被行刑的前妻,“这骷髅头已完全没有皮肉,几乎无法想象光秃秃的颅骨外曾一度包裹着生命丰沛的血肉。骷髅头以一组看不见的线悬吊,看来仿佛兀自漂浮在沉重静止的空气中,戴着一圈白玫瑰,披着蕾丝薄纱,便是他新娘的最后形象”。这些前妻被残酷地处置,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过度的好奇心、独立的思考或是要求对称的感情而不能被容忍,最后都被制成不同的标本,以便定格她们作为新娘应该有的乖巧神态,从而符合丈夫的严苛标准。
婚纱总是穿在“错误的身体”上,这样的安排打破了常规的婚姻叙事,同时摇醒了女性,让她们重新审视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女性梦想与女性愿望。刻意的扭曲使人感到震撼,这样的艺术处理放大了女性内心的恐惧。在婚姻的门槛上,她们对于未来的期许、幻想、忐忑和对命运的忧患,通过新娘哥特得以恰当地展示。
《爱之宅的女主人》为女吸血鬼安排了一个理想的结局。闯进城堡的男子并没有被身披婚纱的吸血鬼诱惑,他就像照进城堡的一抹阳光,目光并没有停留在婚纱符号上,并对婚纱及其背后的一切意淫,相反,他关心婚纱背后真实的身体和情绪,“他走进起居室,满脑袋计划。我要带她(吸血鬼)去苏黎世看医生,治疗她的歇斯底里紧张症;然后去看眼科专家,治疗她的畏光,然后去找牙科医生,把她牙齿形状修整得好一点;至于她的指甲,任何像样的指甲美容师都能处理。我要把她变成不负她美貌的漂亮女孩,我要治好她所有的梦魇”。他的出现和关怀打破了婚纱的魔咒,把女吸血鬼从她的悲情命运中解放出来,尽管这样的解放对她而言或许意味着烟消云散,或许意味着她的灵魂将永远伴随他走在行军的路上,与他并肩前进。故事中这个乐观的转折抚慰了女性不安的心灵,提供了男女相处的一种可能模式。
三、珠宝与华服
卡特在她的很多故事中对珠宝与华服表现出一种执迷,她精心细致地打扮笔下的女主角,时时把她们置于豪华闪亮的大宅之中。以《染血之室》为例,其中的诸多细节安排把这些财富与珠宝推到了前景。“求婚时他已经准备好戒指,装在内衬猩红天鹅绒的皮盒里,是一颗大如鸽蛋的火蛋白石,镶在一颗花纹繁复的暗金古董戒上。”“丈夫喜欢我把火蛋白石戒指戴在小羊皮手套外,这是种戏剧化的招摇做法。但那态度讽刺的司机一瞥见闪闪发亮的它便露出微笑,仿佛这确切证明了我是他主人的妻子。”“天气很冷,我将身上的毛皮大衣拉得更紧,这黑白宽条相间的大衣是白鼬加黑貂皮,我的头在衣领衬托下仿佛野花的花萼。”珠宝与华服折射出佩戴与穿着者的社会地位,珠宝与华服加身就如同权力加身,它们甚至凌驾于主体之上,成为身份的标志。出身贫寒的女主角在这个代表财富的宫殿,时时为这些奢华的物质感到惊叹和痴迷。她看到了“水龙头全是黄金小海豚,镶着碎土耳其石的眼睛”;她实际地触摸到了“这桩婚姻让我如今坐拥神灯精灵般的何等财富——首饰、手镯、戒指……我正如此这般处在钻石包围中”。通过婚姻她正式接收了这一切,终于将娘家曾经“盘踞我们寒酸餐桌已久的贫穷鬼魂驱走”。这些物质是安全感的一部分,定义了她作为女主人的角色,实现了新娘的梦想——包装自己作为礼物送给她的丈夫,同时交换到这一切。
但是所有这些定义她的权力与地位的物质似乎并不牢固,它具有巨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它的附着力很弱,隐隐透着不祥,令她内心惶恐不安。就如她手上的火蛋白石,“不知从多久前开始,每个嫁进他家城堡的新娘就都戴过这戒指。那他是不是也曾把这戒指送给其他太太,然后又要回来?”女主角的恐惧就像灰姑娘需要留意12点的钟声,12点一过,她就会打回原形,所有华服、珠宝、南瓜车消失不见,她会重新回到灰堆中。这枚标志身份、作为婚姻契约的火蛋白石戒指,是否需要从她的手指上卸下,交到下一任手中。
故事中的两件结婚礼物——带着火蛋白石的婚戒和红宝石项链,隐隐暗示女主角的悲剧命运,透漏着杀机。“蛋白石会招厄运。”而这条“两英寸宽的红宝石项链,像一道价值连城的割喉伤口”。“逃过断头台的贵族阶级流行一种反讽的装饰品,在脖子上原先可能遭刀锋斩断的位置系着红缎带,像伤口的记忆……环绕少女喉头的猩红闪亮宝石,色彩夺目犹如鲜血。”这些贵重的珠宝是诱饵,令女主角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踏进婚姻的牢笼。同时,它们也代表着男主人对妻子严苛、高不可攀的标准,以及违背这个标准可能带来的审判和处罚。事实上,这个标准包括了安守本分、顺从和不对抗,女性应该遵从标准作为享受这些物质的代价。正因为这些华贵的物质,这些存在于主体之外的突兀的物质,时时提醒着女性正确的行为操守,像一副无形的枷锁套牢了在别样的情景下更为勇敢与叛逆的女性天性。
女主角的丈夫在蜜月之中离开城堡,她在孤单与委屈中拨电话给母亲,然后一听到她声音就哭起来,让自己大吃一惊。“没有,没事。妈。我的浴室有黄金水龙头。我说,黄金水龙头!是啊,这是没什么好哭的,妈。”抱着黄金水龙头对母亲哭诉,反映了女主角的尴尬处境,以及对自己当初不顾母亲的反对而远嫁的一丝忏悔。面对飘忽不定、想法难测、感情取舍不明的丈夫,整个城堡的物质显得越发遥远、无用和空洞,就像看不见未来的婚姻,令女性内心痛苦惶恐,感情无处寄托。
四、城堡与塔楼
婚姻中值得期待的另一部分是新居,新婚夫妇共同生活的场所。在家中各人接受既定的角色分配,新婚妻子又被寄予未来的母亲、管家、家庭主妇等期待。家居是家庭主妇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她们的阵地。在《染血之室》中,家居的宁静被打破,哥特元素引入其中。
故事中新婚妻子跟随丈夫回到新家——孤悬在海上的城堡。“他的城堡。童话故事般的孤寂场景,雾蓝色的塔楼,庭园,尖栅大门,那座城堡兀立在大海怀抱中,哀啼的海鸟绕着阁楼飞,窗户开向逐渐退去的紫绿色海洋,通往陆地的路径一天中有半天被潮水淹没阻绝……那座城堡不属于陆地也不属于海水,是两栖的神秘之地,违反了土地与浪潮的物质性,像忧愁的人鱼停栖在岩上等待,多年前溺毙于远方的情人。”城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两栖性,当潮水淹没时,与外界的联系被阻隔,而潮水退去,也必须仰仗主人的安排才能离开。男主人掌握着通往广阔世界的门匙,一旦进入城堡,成为其中的女主人,身后的大门就会轰然关上,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城堡的地理位置安排巧妙地影射了女性在婚姻中退守家庭,实际上相当于被囚禁,与外部圈子的联系被削弱,她们被要求安于家庭的角色以及绝对忠诚于丈夫。
城堡的塔楼有一处密室,是男主人的秘密所在地。卡特在描写这个染血之室时,跟前辈的哥特风稍微有些差异。以爱伦坡的作品为例,《厄舍府的没落》也是围绕一幢魅影重重的老宅,故事作了更多氛围的铺垫,以旁观者的视觉进行观察和推测,疑心逐步加重。大宅中的两个主人气色一天比一天差,病人的气数跟这个大宅一样,似乎将要走到尽头。在大宅倾颓之夜,风声雨声助纣为虐,主人的胞妹死而复生,从棺中跳出。故事作了大量的外部环境铺垫和旁观者的心理铺垫,令恐怖的氛围步步推高,从而达到极致,主人的精神崩溃,大宅也倾颓沉没。卡特的恐怖相比之下更重于对恐怖环境的直接书写,各种意象更为直观、清晰甚至尖厉。卡特在描写染血之室时,大量堆砌了所有能想象到的恐怖物件,如灵柩台、骷髅头、直立棺材、被尖钉穿刺的铁处女等等。卡特是更为嗜血的一个,她的典型哥特风是属于见肉拆骨流血的。密室所见对于前任妻子们所处的极刑是一种最为夸张和令人惊骇的表现形式,投射出女性对于男性中心家庭的困扰与对自身命运的忧虑。
在本应该温馨的居家中将哥特引入,“将哥特带到住家之中,直到居所变为最恐怖的哥特场所,以暴力扰乱家庭生活,这样的恐怖挑战了传统妻子、母亲、管家等角色,令人们关注家庭生活中功能失调的方面,同时,质疑了所有约定俗成的性别身份与社会群体构成”[8]。就这部作品而言,浪漫的海上城堡与血腥的极刑之室只有一把钥匙的距离。家庭生活场所的错置与氛围异化阻断了传统的婚姻生活叙事和家庭叙事,打破了通常的安全感,令人反思婚姻生活中女性的处境与忧虑。
五、结语
披上婚纱成为新娘,大概是大部分女性的梦想,可是联想到婚姻及其背后的一切,就会让人反思所谓的唯美纯洁的新娘形象。女性在婚姻中被寄予的高度期望——理想的妻子、母亲、管家、家庭主妇,令女性在角色转换之际不堪重压,从而有了很多落跑新娘。身穿婚纱的女性被简化为性和其他功能的符号,令渴望沟通、渴望情感交流的女性感到不安。卡特借用新童话的形式,以大胆夸张的笔画去书写不恰当的新娘形象,在故事中使用女性哥特元素,表达了女性内心的恐惧,并试图追溯恐惧的根源,表达了对女性的关怀。
参考文献:
[1]PATTERSON C.Angela Carter:beauty and the beasts[EB/OL].(2006-01-18)[2015-09-10].http://www.independent.co.uk.Access on 10 September,2015.
[2]卡特.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M].严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MOERS E.Gothic: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M].New York:Routledge,2004:123.
[4]WAlLLACE D.The encyclopedia of the gothic[M].Oxford:Wiley Blackwell,2013:235.
[5]HOVELER D L.Gothic feminism: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gender from Charlotte Smith to the brontes[M].Philadelphia:The Pennsylvania StateUniversity,1998:4.
[6]CARTER A.Shaking a leg: collected journalism and writings[M].London:Chatto & Windus,1997.
[7]GAMBLE S.Angela Carter: new critical readings[M].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2.
[8]WELLS P.The horror genre[M].London:Wallflower,2000:18.
(责任编辑:张杰)
Bridal Gothic inTheBloodyChamberandOtherStories
WU Duanming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Stories by Angela Carter embodies outstanding female gothic characteristic, with the uncanny bridal image. Carter endeavors to write totally different images of wedding ceremony, wedding gown and the bride. She uses an extremely exaggerated and tortured method in describing bride’s experience to show the uneasiness of women at the point of role transition. She uses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all the way in the stor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women’s biology and psychology, thus manages to show her concerns and sympathies for women.
Key words:bloody chamber; bridal gothic; women’s role
*收稿日期:2015-11-18
作者简介:吴端明(1980—),女,广东肇庆人,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16)03-009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