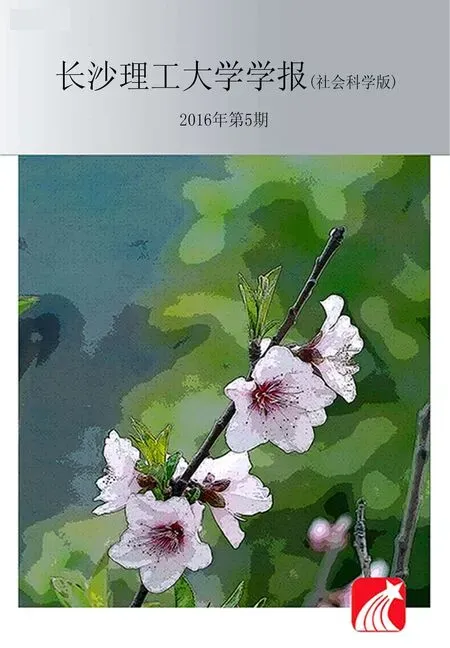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冯娜研讨小辑“词语的距离”
——关于冯娜诗歌的几种解读方式
2016-03-23张立群
张立群,吴 繁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15)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冯娜研讨小辑“词语的距离”
——关于冯娜诗歌的几种解读方式
张立群,吴 繁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15)
诗歌在今天能够给诗者和读者带来精神抚慰?!这是我接触冯娜诗歌最初的感受。在一篇名为《抚慰之一种》的“答谢辞”中,冯娜提到了自己的成长史,提到了冬季北半球星空最容易辨别的猎户座,还有“所有这一切,遥远的星辰、永不能被囚禁的自由和信念、写出的诗歌、陌生人的信赖、令人厌烦又甜蜜的婚宴、意外的奖赏……”,在冯娜看来,“都是抚慰之一种。”①也许,这些感受在其他一些读者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对于自幼就对星空感兴趣且常常用铅笔在演算本上画下简单四季星图的人来说,冯娜的感受可谓引起了多年前就湮没心底的记忆及图景。面对狮子座、天琴座、仙女座、猎户座的四季更替以及终年可见的淡淡银河,我们会用怎样的词语去形容与星辉接触时的感受?也许,只有诗人和那些永葆真心、不失自然的人,才会在意这种恩赐及领受。为此,我愿意以“词语的距离”作为解读冯娜诗歌复杂性和多义性的一条线索。在此过程中,“词语的距离”既是一种诗的表达方式,又是一种诗的构成方式。
一、“庞大的抒情”与诗歌地理
面对“祖国”,冯娜曾写下——
我怀疑 我的孱弱的身躯
如何承载一场庞大的抒情
我只想 我在世界的尽头喊妈妈
你一定会朗声地应答
我只想 你再暗夜里不眠
我就擎一盏细小的温黄 在角落
如果这一切注定要被人冠之以宏大
那我就安静坐下来陪你
什么也不说
——《祖国》
在诗人质疑自己“如何承载一场庞大的抒情”的时候,她其实已然承载了;正如她说“什么也不说”,其实一切早已尽在不言中。由此纵览冯娜的诗,《祖国》一诗其实是一次形象的概括:这位从美丽的云南丽江走出来的诗人,多年来一直写着“祖国之诗”,建构着属于自己的“诗歌地理”。高原、雪山、河流,还有听来就让人遐想的恰克图和巴音布鲁克,冯娜是一位以吟唱自然之诗而见长的诗人,她有自己的诗歌版图,对其版图中的山川、一草一木,她从不吝惜“庞大的抒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地理”既可以成为诗人的诗歌史,也可以成为诗人的成长史。冯娜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结论。写云南、写西南的风物,是冯娜诗歌的主要特色。她总是能将自己饱满的热情、独特的感悟,融于自己熟悉的地理之中:《藏地的风》《贝叶经》《青海》……“我将身体翻过来 一颗细痣迎向星斗/一切被神标记过的/那未曾走失”,诗人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她让“细痣”迎向“星斗”——对此,我几乎可以断言:这样陌生化的词句从未在汉语诗歌中出现过。冯娜的“诗歌地理”是建立于一片神奇而美丽土地上的风景,有着独特的地质风貌;冯娜的“诗歌地理”又是建构于自己思想深处的风景,拥有着怀想而又遥远的距离。她通过距离丈量自己的内心,而这或许正是她所言的“抚慰之一种”吧!
“庞大的抒情”大意灵动,犹如一个见到奇异风景的孩子,在那一刻屏住呼吸;“庞大的抒情”寂静无声,惟其如此才会抵达辽远与广阔。将很多亲身经历融入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歌地理”不乏故事元素。“听说你住在恰克图”,“我”便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心:“水流到恰克图便再也不会回头/你若在恰克图死去 会遇见一个从未到过这里的女人”(《听说你住在恰克图》),那么多铺垫,也没有确切说出到过恰克图,但结尾的正话反说却揭示了这是一个爱的故事。冯娜的诗里因此有了“人世的婉转”;“我从此再不远行 龙山白发成霜/金沙江越走越窄 所到之处水声哽咽”(《龙山的女儿》),冯娜眷恋自己的诗歌地理,并不时由己及物,龙山白发成霜,自是岁月使其变得苍老。但这一点,显然也适于不再远行的“我”——“我不再远行 亦在故事里沉醉”,这位“龙山的女儿”有着“出世的悠长”②,只想守候一方自己喜爱的土地,并不知不觉将土地作为自己的抒情对象,渐渐和其融为一体……
二、时间的忧愁:流水与流逝
阅读冯娜的诗,常常可以体味到一种较为明显的时间性或曰过程性。冯娜的诗歌是完整的,讲究叙事内在结构的前后统一。“往西去 我的姓氏有了确切的色泽”(《在生命里》),将方位指向和成长史联系在一起,冯娜写出了“一株植物的奥秘”“一个女人的魂灵”,他们在本质上并无差别,且都源于某种感受或认知。将经验嵌入过程并由此再度经验化,冯娜的诗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关于生命和时间的忧虑。“时间在这颗星球的运算方式有许多种/……人们在描述它的景观时饱尝忧虑”,作为一个“时间旅行者”,体验旅行时的感受当然与时间有关。只是在此之前,冯娜早已将这种感受看得很清楚——或许是身为一位学者型诗人的缘故,她的平静、淡淡的忧愁使其诗歌在书写上述主题时具有女诗人少有的知性与宽容。
在书写时间的忧愁以及过程性时,冯娜还常常在诗中呈现出某种“小结构”“小片段”,然后在其中融入自己对某些特定场景或特定生活状态的理解。像《澜沧江》中的 “仿佛一万年前 我的心被这一江水啄空/在此后心痛的岁月里 缓缓返还”,叩问雪域高原和生命的轮回;像《沿着高原的河流》中的“淌不尽的河流啊 沉浮在水里的爱情/它们迄今仍在我身体里雕刻”,写出深入肉体的印记和流水中的爱情……如果说“流水”是一个物质化的实体形态,那么,“流逝”就是一种感悟中的时间风景。从“流水”到“流逝”,冯娜的诗歌既有女性诗歌如水的特质,又有流逝时对于生命的感悟。或许是经历了更多的迁徙,冯娜才更愿意回望源头。通过一个个“小片段”和“小转折”,诗人实现了写作、记忆和体验的多重满足。冯娜喜欢通过“流水”以及近似于“流水”的意象,百转千回地表现其此刻的感受。然而,“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并不能涵盖冯娜诗歌的全部。如果对“流水”进行一次本源性的考察,我以为冯娜之所以多次使用它是因为后者能够自觉不自觉地隐喻出冯娜的经历甚或性格,而在此过程中,云南以及南方多河流又为冯娜诗歌的意象选择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与契机。“流水东逝”——还有什么能比此更能揭示一个游弋者的生活状态,还有什么能够表达生命的过程呢?将远游和爱情附在“流水”之上,冯娜可以更为真切、务实地丈量穿越时时间的距离。而对于后者,诗人的《偷走时光的人》中那位“慷慨 贪婪 不可捉摸”“让我们衰老得没有脾气”的人,显然是其产生时间忧虑的前提。当然,在另一面上看,“仅仅 偷走了一段光阴”又是一个结果,因为通过它,诗人表达了对待时间的态度。冯娜是一位有着较强时间观念的人,也是一个常常处于或者说渴望变动不居的远行者。她将经历和体验转化为对时间命题的理解,在我看来,这种意识是其从一开始就未陷入狭窄的性别视域并表现出诗质深邃、沉实的重要原因。
三、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对应
尽管,关于“词语”,冯娜写过“我看不见你的藏身之所”,但“我看不见你 当你露出了词语一样的样貌”却道出了词语必然要依附于某种具体的事物,才能呈现语言应有的存在形态。词语是“一座巨大的记忆仓库”,不断衍生出新的语言,成为诗歌的元素;词语不朽,可以存在于任何一种叙述之中,“现在,我把词语放在耳朵上、膝盖上/它们理解衰老和冗长的命运/——多么好,当我不在这里/你依然能看到我,在词语周围”(《词语》)。很少有女诗人像冯娜这样如此关注词语以及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也许,从出生地的角度可以解释她的语言能力,正如在《云南的声响》中,冯娜写有:
在云南 人人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
一种能将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样
一种在迷路时引出松林中的菌子
一种能让大象停在芭蕉叶下 让它顺从于井水
井水有孔雀绿的脸
早先在某个土司家放出另一种声音
背对着星宿打跳 赤着脚
那些云杉木 龙胆草越走越远
冰川被它们的七嘴八舌惊醒
淌下失传的土话——金沙江
无人听懂 但沿途都有人尾随着它
“三种语言”分别代表爱情、生命力和与自然的关系。显然,在冯娜看来,云南的语言和声音与其文化和语境有关,这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不能说它会被全部继承下来,但“生命之河”——金沙江本身就是一种人人都可读懂的语言。无论是生活还是迁移,人们都离不开这条蜿蜒曲折、落差极大的大河。应当说,通过语言和事物的对应关系,冯娜发现了命名的意义以及其背后蕴藏的生命意识。“失传的土话”只要读懂即可,未必要发出声音,通过“无言的逍遥”,《云南的声响》大有对词语进行历史和文化溯源的趋向:通过找寻,冯娜将诗质复杂化与多义化了,同时,也使其具有了立体化的结构。而词语与事物之间的距离就这样富有伸缩的弹性,它们可以近在咫尺,可以隔越遥远的时空,而其潜藏的文化密码又使语言和事物对应过程中带有一种神秘的意识。
语言与事物对应后,冯娜的诗歌常常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及相应的表现力。像《寻鹤》中通过探寻将“人/鹤”、异域中的情感和现实统一起来,讲述一个爱的故事;像《迷宫》中以白色的迷宫讲述分别带来的无言的伤痛……冯娜常常以移形换位的方式讲述自己独有的体验,并由此呈现出语言的力量和生长的状态——“词语上微蜷的毛发/指腹的螺纹——它们创造了新的词汇”,当然,这种状态本身也构成了冯娜诗歌的语言特征。
四、现实的距离感及其他
近年来,冯娜的诗歌有明显告别往日的诗歌地理,关注身边现实的趋向。她诗集《无数灯火选中的夜晚》中很多的作品似乎离其曾经熟悉的土地越来越远。她曾于《出生地》一诗中以“对话”的方式解答当下的生活状态——
人们总向我提起我的出生地
一个高寒的、山茶花和松林一样多的藏区
它教给我的藏语,我已经忘记
它教给我的高音,至今我还没有唱出
也许,我在这样判断时已远离冯娜的诗歌本意,但如果说环境的改变可以让一个诗人的创作发生适度的转变,那么,书写现实会带来另外一种距离感的说法也并不过分。远离往往会唤起诗人另一种记忆或者怀想,但就冯娜当下的诗篇而言,这种堪称“私人心愿”的内容还未大面积出现,及至成为冯娜诗歌写作的新质。
不过,冯娜依然不断在其诗歌中注入怀旧的元素: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其对诗歌本源理解所致,是其年少时仰望星空留下巨大的空间和遐想所致,同时也是冯娜诗歌最引人关注之处。“我不是藏人,我是一个诗人/我和藏人一样在雪里打滚,在雪里找到上山的路/我相信的命运,经常与我擦肩而过/我不相信的事物从未紧紧拥抱过我”(《雪的意志》)。冯娜的诗歌确如“雪的意志”一样,有透明的质地和纯净的光泽。“我不相信的事物从未紧紧拥抱过我”,在展现冯娜诗人性格的同时其实已拒绝了很多。因此,她的诗此刻虽然离现实的距离如此之近,但我仍将其视为一种必然经历的过程,一个突破坚冰、走向新领域的开始。
让一个成名的诗人始终坚持自己的写作、形成固有的风格,或许会使其“过度重复”自我;让一个成名的诗人突破自己,不断探索陌生的领域,或许会使其“过早失去”自我,这样看似辩证的论断事实上一直隐含着十分复杂的内容,并不是简单使用非此即彼或是平行并置的逻辑就能说得清楚。诗歌批评同样需要一种缘分,因为冯娜最初的声音在我这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所以,我在使用诗歌评论者习惯使用的整体性思路的同时,难免带有浓重的“怀旧意识”。“怀旧”时,“好几世了/青海的太阳 蒙着眼泪”(《青海》)和“给你一剂 致命的温柔”(《山坳里的藏报春》),读来实在令人心动。也许这就是诗人仰望星空的结果,那里有“词语的距离”,是一种只有冯娜能够体验与写出的时空状态。
[注释]
①冯娜:《抚慰之一种——2012·第二届奔腾诗人奖答谢辞》,《奔腾诗歌年鉴(2011—2012)》,总第四期,第49-52页。
②“人世的婉转”“出世的悠长”,均出自《第二届奔腾诗歌奖授奖词》,《奔腾诗歌年鉴(2011—2012)》,总第四期,第48页。
2016-08-25作者简介:张立群(1973-),男,辽宁沈阳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吴 繁(1992-),女,辽宁丹东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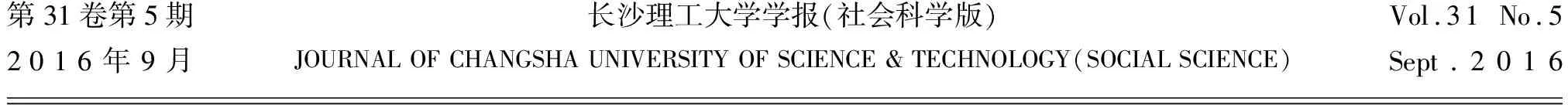
第31卷第5期2016年9月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TECHNOLOGY(SOCIALSCIENCE)Vol.31No.5Sept.2016
I207.25
A
1672-934X(2016)05-0098-04
10.16573/j.cnki.1672-934x.2016.0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