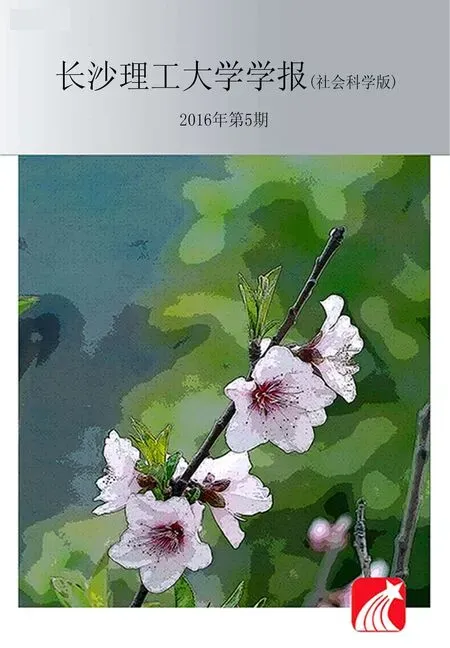构建理想的公共领域何以可能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视角
2016-03-23宋芳明
宋芳明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构建理想的公共领域何以可能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视角
宋芳明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目前我国公共领域的发展面临如何协调与政治权力关系、内部社会力量间关系的两大难题。培育公共精神是构建理想公共领域的核心,而思想政治教育不断阐发着公共精神内蕴,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就是培育公共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诉求相契合。因此,必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拓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转型。
构建;公共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
公共领域是伴随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发展起来的既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治权力掌控,又不同于纯粹私人交往范围的新兴领域。就我国社会实际而言,建设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必须重新确立起公共领域运行的“逻各斯”,规导公共领域与政治权力、公共领域内部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培育公共领域的“公共精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公共精神中的理性品质所解答的恰好是公共领域“逻各斯”的建构何以可能的问题。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就是培育人们公共精神,进而使理性的交往规则在公共领域得到普遍确立,让理想的公共领域成为现实。
一、我国公共领域的现实状况与理想图式
我国的公共领域既具有公共领域普遍的特点,又表现出我国特定经济、政治、文化影响下的特殊性,构建理想的公共领域首先要对我国的公共领域现状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
(一)公共领域概念界定
现代意义上公共领域概念源起于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中,犹裔女学者阿伦特最先提出了公共领域的理论,她认为公共领域的关键在于它的“公共性”,包括两层涵义:它是一个实体性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空间;对所有人开放,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进来或者退出[1]。哈贝马斯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丰富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认为公共领域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共舆论,它们既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又对政治权力有批判意义[2]。这样,就把公共领域看成是相对于政治权力和私人领域之外的公众理性交往的地带。
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重新调整和确立了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时至今日,虽然社会中间力量逐渐发育完善,具有组织化、自主性、公开性等特点的非政府组织具有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和能量,但是,将西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概念套用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并不合适,因为中国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生活依然没有完全分离,相反,国家和社会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既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治权力、私人领域,又和国家政治权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具有一定自主倾向的“公共性”领域,学界称为“第三领域”即中国意义上的公共领域[3]。
(二)我国构建理想公共领域的目标定位
我国的公共领域不仅具有公共领域普遍特征,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和西方学界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相一致的地方是其自主性和非政治性,我国公共领域中各类社会组织的活动均不直接受政治力量的操纵和控制;但不同的是,我国公共领域具有和政治权力的合作性和内部力量组成成分的多元性:其一,我国以政治力量为主导在制度框架内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决定了公共领域自产生之日起就和政治权力层层叠套在一起,公共领域的繁荣需要政治权力给予物质资源、法律制度的保障和理性观念的指导,公共领域也为国家政治权力做出辩护,维护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其二,由于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在公共领域内部,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组织力量共存,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呈现出多元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公共领域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生成的,既有自身的特殊性又有公共领域的一般表现。
我国公共领域的特殊性决定构建我国公共领域的目标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西方意义上彻底摆脱了国家干预和经济力量制约,质疑、抨击国家政策走向,通过公共舆论向政府施压,迫使国家权力做出妥协、退让的过度激进的理想化的公共领域,而是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缓冲地带,积极寻求和政治权力合作,在法律框架内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保持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同时,在公共领域内部的目标是寻求价值共识,形成能够普遍化的交往秩序,避免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对抗,实现共赢、互惠的公共性原则。
这样一来,在我国构建理想的公共领域的着力点就是构建一种公共领域的“逻各斯”,即一种理性的交往秩序,进言之,即通过培育以公共关怀意识、公共协商意识、公共参与意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精神,向公共领域不断地供给和输入公共性的价值观[4]。在我国,这项活动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拓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诠释与公共精神的阐发
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就是通过教育使人们的公共性品质即公共精神,培养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深切关怀意识,让人们关注公共生活,参与公共事务,从而成为乐于并且有能力贡献于国家的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成熟越来越展现出对公共精神阐发和培育的价值,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更是蕴含着丰富的公共精神教育资源。
(一)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演进
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阶级思想和阶级意识的教育,只能在阶级社会产生,产生于各个阶级有意识地将本阶级的思想政治观念灌输于本阶级成员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过程中,根本目的在于维护阶级统治[5]。从这个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政治实践活动,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开展的政治活动。这种作用于人的意识的政治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公共性的特征,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历经了从一种不完善的、狭隘的公共性到现代意义上成熟的、整体的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上:其一,教育的价值取向从少数人的公共性到多数人的公共性。在传统社会,公共关怀意识即对他人的尊重、责任和奉献精神适用对象仅仅是占社会极少部分的统治成员,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下对本城邦自由人中的男性公民进行类似于公共精神的教化活动,然而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这种公共关怀是不被适用的,对他们尊严甚至生命都可以肆意践踏;在我国封建社会,虽然政治教化被普及,公共关怀指向的对象也十分狭隘,以民本思想为内容的政治教化活动要求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社会精英阶层的人关爱普通老百姓,似乎具有普遍的公共关怀色彩,但实质上要求“科层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常规性合作,维系国家—精英之间的联盟机制”[6],从而有效维护政权稳定。这样的教育因为建立在奴役和不平等理念基础上,有着浓厚的功利主义倾向和“怜悯”“施舍”的动机,但它却使政治教化具有了公共性的意蕴。现代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在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获得政治权利的基础上,将公共关怀意识的使用对象普遍化、平等化,是对一种希望为公共事务及他人负责,站在他人的立场上保护其利益并促进其发展的道德理想的激发和培育。其二,教育的运作形式从灌输走向商谈,突出协商意识。任何一个阶级在确立统治地位之后都面临着权力控制的问题,而权力的运用一是靠武力对民众进行肉体控制,二是靠教化手段对民众实现意识上的强制。暴力镇压威胁下推行的政治教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制灌输,在封闭、单向的社会结构下,民众被剥夺了思考、判断的机会和能力,规范、信念和价值观被教条化。现代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除去了暴力的阴霾,活跃在多元、开放、自由的社会,教育的手段从灌输走向商谈,在平等的言语交往基础上,在商讨、交流、辩论中,从自我走向他人,走向人性之共同,这样的教育运作方式既是传递公共精神的载体,又不断阐发着理性、平等、宽容的公共协商精神。其三,教育的内容安排从臣民教化到公民教育,突出参与意识。传统的政治权力通过控制教育,把整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言论、行动纳入大一统轨道,而对于国家的公共事务安排,民众的角色就是做一个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的旁观者。现代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内容之一是公民意识教育,为社会成员划定权力和义务,讲究契约规则的遵守,推崇理性,具有公共参与意识养成的价值[7]。
(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广泛的公共性内涵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公共性为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公共精神提供了公共性基础。马克思哲学所求证并推崇的是一种新的理性观——公共实践的合理性,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公共社会”的合理性,探索“公正社会”的组织形式成为可能的有效机制和演进方式;马克思哲学的类群价值的本位性旨在探求人类社群公共生活的合理性[8]。也就是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为人们科学地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即人民是公共领域的主人,符合公共主体的利益,能够获得公共认同;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理论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站在全人类立场上的理性断言,塑造了最广泛而具体的公共性基础,能够团结一切利益的群体。
其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的目标对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公共精神提出了政治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在我国就是培养“四有”新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培养人们平等、尊重、开放、责任、参与等融入社会大舞台、贡献于国家必备的公共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题中应有之义,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公共人”而不是追求个人私利的精致的利己者。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发挥对人们进行政治认同教育以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和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实现人们心灵的安顿的价值,更要“规约”人们的公共性,培养人们关心、影响公共生活的意识、能力。
再次,培养公共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确证的内在要求。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普遍质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一是“无用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不对社会生活构成影响,没有学术底蕴,仅仅是执政党的“喉舌”,搞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没有真才实学,没有自己的思想,就靠耍耍嘴皮,为现行的社会政策和制度作解释和辩解,为执政党的合法性作辩护。二是“取代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存在的必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其他相关学科完全可以取代,例如完全可以用一个德育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功能[9]。从这个角度看,培养公共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自我进行合法性论证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们生成一种对国家、对自身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应该具有的公共视角和关怀精神,产生推动公共生活进步的价值;公共精神的培育亦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德育”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德育更加关注人们私人领域德行的培养,而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关注人们公共交往品质的培养。在现代开放、多元的社会中,对公德的培养显然比对私德的培养更具有价值优先性[10]。因此,培养公共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独特价值的彰显,是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的有力证明。
三、培育公共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与公共领域诉求的契合
在科学知识高速发展的今天,一切对神灵的敬畏、对终极价值的追求都化为乌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使得人们越来越以自我的满足作为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理性为“自我立法”的律令丧失殆尽,“无知之幕”终将被揭开,“商谈伦理”的践行亦困难重重,公共领域的精神涵养无法来自先验的品质和宗教的约束,也很难完全自发地在公共领域的内部产生。唯有教育这种人类特殊的手段可以将人们长期积淀下的宝贵品质用文明的、合乎道德的方式不断提供给公共领域,为构建理想的公共领域提供精神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培育公共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公共领域的完美“联姻”。
(一)规导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公共性”内容,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彰显出来的认知能力,这种理性是我们在感觉世界中经验依赖的东西,它构建出公共领域的框架并使人们进入到公共领域。一方面,公共理性左右人们对政治领域的认知能力,加深人们对“公共善”的理解和美好政策导向的识别,它“规范并控制其他所有的感觉,如果没有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特殊的、不可靠的感觉材料中”[11],从而容易产生各种偏见和成见,诱发非理性的对立情绪和盲目行为;另一方面,公共理性让人们准确理解公共领域中他人的认知立场和行为价值,获得合理的社会角色,认识到他人的利益所指,通过契约行为、理性商谈等合理的方式融入公共的共同体[12]。公共理性并非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某种先验的感觉判断抑或是通过外界不合理的手段强加于我们的,而是在我们后天的交往实践当中通过学习、练习、反思得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们的公共理性,首先要传授公共基本知识,人们只有掌握与社会他人交往的合理约定、公共领域产生的机制及与国家政治权力互动的基本规律、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方式和渠道、国家政治的运作方式等基本知识,才能以一个合格公民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再者,培养人们的公共思维能力,在人们获得一定的公共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交流、辩论、商谈、参与方式促使人们不断修正已有的判断,在自我反思和自我澄清中锻炼出人们对社会复杂情景中价值选择能力和自我道德角色的塑造能力。
(二)协调公共关系
构建理想的公共领域,从实质上看,关键需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协调好公共领域自身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关系,二是处理好内部各个力量团体之间的关系。探求秉持公平正义的“善”的精神并能最大限度满足各方利益协调规则是现实的而不是虚幻的,之所以坚信它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构建出来,是因为在正义的框架内,理想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的体现,亦与每个个体、力量团体利益相关,公共认同构成了个人认同,是人们协调交往实践的各种冲突而达成的重叠共识,因而,人们“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妥协的结果,也不是把它作为临时的协定,而是从他们自己合乎理性的学说内部出发的”[13],获得普遍的“合乎理性的学说”的认可为公共规则提供了有力的合法性支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们的协商、平等的公共精神,藉由引导人们走进正义的框架内追求普遍的价值理想进而内生出“善”的规则,并悉心呵护这种规则,通过法律、规章、管理条例等手段把它制度化,因为如果它仅仅是发生在个别情况下的没有通过客观化的制度体制变为实在的行为最多只能算作私下里的平等交往与互惠行为。只有在这种规则被制度化之后,人们才会不自觉地将这种价值关系化作自己的第二天性,这种规则才能不断地被巩固和强化,构建理想的公共领域才不是空洞、未来的东西,才能成为活生生的存在。
(三)引导政治权力可能性的界限
在调节我国公共领域和政治权力关系的既往研究中,学界有两种主张,要么倾向于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政治权力,把公共领域的一切问题都纳入到政治安排的议程中,用国家的强制力规制公共领域的构建;要么主张公共领域的彻底自由,扩大公共领域的权力,实现公共领域的自制[14]。这两种思路看似分歧很大,其实都是从静态的视角抹杀了公共领域和政治权力内在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更没有用动态眼光看到构建一种公共领域和政治国家持久共生关系的可能性。一方面,政治权力不但可以为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源扶持和法律制度保障,并且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把主流的意识形态和公共精神输入到公共领域,凝聚起公共领域的共识,协调公共领域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冲突,间接为公共领域提供发展的动力;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汇集公共辩论、公共批判、公共参与中包含促使社会进步、具有公平正义导向的公共观念并把它传达、渗透到政治领域。由此,政治权力的边界不断向公共领域良性敞开:公共领域愈发完善,俞有能力承担其管理社会的责任,将大量过去政治权力承担的事物逐步交由公共领域处理,减轻了政治权力的负担;公共领域在承担一定社会事务的过程中遵循着程序性的正义,将制度伦理中的价值取向不断纳入到自己思想意识中,塑造着公共精神。如此,公共领域实现了和政治权力持久的共生、共存、共享。
四、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转型:构建理想公共领域的必由之路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价值是培育公共精神,塑造具有公共性品质的“公共人”,而公共精神的运用领域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走出学校,因此我们亟需改变过去仅仅把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主渠道”的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重要,而是强调在公共领域日渐成熟、人们公共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心“转移到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中,通过引导人们的公共生活实现对公共性品质的培养”[15],简言之,就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转型。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能够有效走进公共领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价值是我国构建理想公共领域目标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笔者认为,除了需要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公共性品质之外,还要讲究实践方略,找到合适的路径。
(一)培育非政府组织作为构建公共领域的主体力量
非政府组织也叫民间组织,是公共领域内部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领域活动的主体,具有自治性、自愿性、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特点。在我国现代化大背景下,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强大,对公共思想意识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另外,非政府组织产生、根植于公共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利益有着密切联系,我国部分地方性非政府组织甚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获得地方民众的支持,可以说,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塑造公共领域思想意识的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情感优势,而这正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望尘莫及的。从这个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要注重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具体而言,一是转变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只代表政治传声筒的角色,站在非政府组织的立场上深入了解非政府组织的利益诉求、运作模式及与社会大系统的关系,结合其开展的具有公共精神教育意义的社会活动或者内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特别是与组织成员思想意识方面相关的问题,并抓住时机,利用非政府组织活动中发生的案例、事件对其进行公共性意识的培育;二是着力培养非政府组织中的负责人员。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和自愿服务于社会公共事业的特点决定了其发起和主要负责人员一般是具有较高的学识和道德修养,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空间和崇高的内心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公共精神特别是公共理性的培养,激发这些人公共性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彰显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引导公共性意识在社会的普遍确立。
(二)涵养公共文化作为构建公共领域的精神动力
公共文化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以公众为服务对象的文化形态,包括公益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公共文化参与主体的多元性特质决定公共文化是一种认肯人的自由、平等地位和理性判断能力的文化,它能够包容个性、理解差异,并且孕育着理解、尊重、宽容、协商的公共性价值共识,可以为公共领域求同存异、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理想图景提供内在精神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深度挖掘公共文化中内涵的公共精神因素,通过精神鼓励、物质支持的方式把公共文化中的正能量培育壮大;另一方面,将公共性意识融入到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中,使人们在参与、体验公共文化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公共精神的熏陶。如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但培育了公共精神,还为公共领域的发展构建了内生的持久的精神动力。
(三)推进法制建设作为构建公共领域的制度保障
如何保障政治权力和公共领域在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合作,如何化解公共领域内部的利益冲突是构建理想公共领域过程中最难以解决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政治权力和公共领域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公共内部社会力量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制度是其中协调的桥梁。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律制度既是这两对矛盾发展的结果,又为这两对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权威的依据。进而言之,法律制度为公共领域提供了价值导向,那么其本身是否内含者公平正义的伦理要求以及公众对这种制度伦理的理解程度直接影响着公共领域的构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宣传、讨论、辩论等教育手段把法律制度中内含的公共精神向公众揭示出来,同时将公共交往、公共参与过程中通过平等协商而产生的规则系统化、理论化,并利用自身和政治权力的联系把这种蕴含着公共善的规则运用合法的程序确定下来,从而完善法律制度,使其切实保障政治权力和公共领域的相对独立和良性互动,保障公共领域内部的公平正义。
[1][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9-41.
[2]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C].三联书店,2005:125.
[3]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66-270.
[4]卞桂平.刍议公共精神的伦理意蕴[J].云南社会科学,2016(1):23-28.
[5]李合亮.思想政治教育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6-66.
[6]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60.
[7]卢岚.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若干问题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7):410-41.
[8]贾英健.公共性视阈——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
[9]侯勇.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困境与公共化转型[J].理论与改革,2015(4):175-178.
[10]叶方兴.德性伦理果真遭遇公共化困境吗[J].伦理学研究,2016(1):72-79.
[11][美]塞瑞娜·潘琳.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张云龙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16.
[12]周谨平.社会治理与公共理性[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1):160-165.
[13][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31.
[14]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31.
[15]戴锐.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转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1):189-194.
Why Is It Likely to Construct an Ideal Public Sphe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ublicity?
SONGFang-ming
(DepartmentofMarxism,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Anhui241002,China)
At present, there exist two challenges in the public sphere development in China: namely 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al power, and 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social forces. As a core of ideal public sphere construction, the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i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ublicity. And the public spirit connotation is expounded b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antl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ublicity agrees with the public sphere appeal. Theref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ust be expanded in the public sphere to realize the publicity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public sphe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ublicity
2016-08-06作者简介:宋芳明(1992-),女,安徽淮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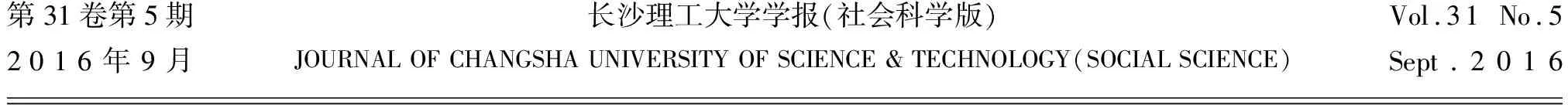
第31卷第5期2016年9月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TECHNOLOGY(SOCIALSCIENCE)Vol.31No.5Sept.2016
D630;D64
A
1672-934X(2016)05-0138-06
10.16573/j.cnki.1672-934x.2016.05.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