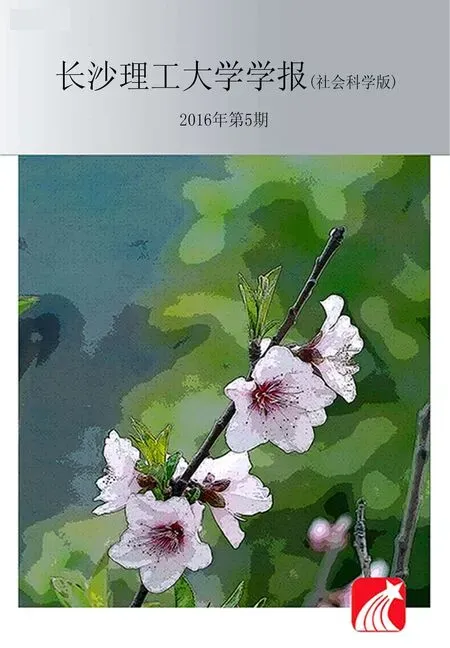论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伦理指向
2016-03-23李重明
李重明
(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论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伦理指向
李重明
(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是基于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受益性不均等提出来的,是党在新时期发展理念上的重大突破。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以提升全民获得感、实现共同富裕为主旨,着力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以推进民生建设,强调发展过程中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凸现出鲜明的公正价值取向,直指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正义等公正的三个维度。其中,权利公平是共享发展的前提,机会公平是共享发展的要义,分配正义是共享发展的手段。
共享发展;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正义;获得感
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旨在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是党在新时期发展理念上的重大突破与执政理念上的重要升华,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五大理念之中,如果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健康发展的内在诉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径,那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享则是发展的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它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主旨,致力于化解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受益性不均等问题,强调“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P13),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拥有更多获得感。从伦理视角审视,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聚焦社于会公正问题的解决以推动民生建设,凸显出鲜明的公正价值取向,直指公正的三个维度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与分配正义,它是习近平公正思想在发展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对公平正义这一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弘扬。
一、权利公平是共享发展的前提
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秉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原则,强调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社会改革和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建设成果,这就解决了发展为谁、依靠谁、由谁享有等有关发展的核心问题,无疑是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与改革发展的主体、理应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主体地位的张扬与实现。由此可见,人民主体地位与共享发展密切关联,它不仅是共享发展的逻辑始点,更是共享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又由于人民的主体地位是建立在人们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不能公平地享有基本权利者是毫无主体地位可言,因此共享发展离不开权利公平,要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共享发展,首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保证作为共享主体的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公平。
所谓权利公平,就是指每个社会成员无论其家庭出身、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有何不同,都平等地拥有人之为人、成为公民所应具有的生存、发展、享受等基本权利。具体说来,也就是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里都无差别地享有劳动权、财产权、民主权、出版权、受教育权、失业救济权等能保证每个人有尊严地活着的天然权利,这些权利是人天生就应拥有的无需与他人竞争、他人也无权剥夺的底线权利。权利公平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社会公正、消弭社会贫富悬殊的基石,主张消灭一切阶级和特权,是一种体现人们之间实质平等的初始性、核心性公平,其他一切公平如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结果公平等都由其衍生而来,没有基本权利的公平,相应地也就没有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
众所周知,正如恩格斯所强调:“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2](P144)人是生而平等自由的,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参与发展、发展自我并同时又能享受发展成果的权利,对此1986年第4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3](P305)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也无不表明,在一个人人被划分为三六九等的等级森严的国家或社会里,人们在个体的生存权、发展权、享受权等基本权利的拥有上是绝对不平等的。对于那些连基本的天然生存发展权都得不到保证的社会底层人群来说,与社会上层人群相比,其被统治、被压迫的身份地位注定他们难以获得平等地参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机会,更谈不上从这些领域里公平地获取各种利益,最终必然导致这个国家或社会出现一部人剥削压迫另一部分人、无偿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独享发展成果的局面。由是观之,权利公平是共享发展的内在前提,它保证了人们的起点公平与主体地位,使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成为可能性与现实性,权利的不公平必然导致人们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上的不公平,无权者难以享受到发展成果。
反观我国当下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已彻底根除了权利不公存在的经济根源,人们已成为国家的主人,公平地享受到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生存与发展权利。与此同时,在促进权利公平方面国家积极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这些都为共享发展成为现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诸多因素的存在导致当前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些权利不公的现象,如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享有上非均等化;性别歧视导致男女劳动就业权利的不公平;户籍制度的藩篱导致进城务工人员无法平等地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市民权利等,这些权利不公直接导致了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里的受益不平等,成为阻碍人们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实现权利公平为共享发展的切入点,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4](P96)强调要“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5](P11)并通过采取如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实施城乡大病保险制度以及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重大举措以保障全体人民在各方面的基本权益平等化,真正落实人们的生存权、发展权与享受权等,从而不断推进共享发展。
二、机会公平是共享发展的要义
对于何谓共享发展,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从四个方面对其做了全面解读。他指出共享发展就其覆盖面、内容、实现途径、推进进程而言,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以及渐进共享。这就消除了人们对共享发展的各种误读,表明真正的共享发展不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也不是一部分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巧取豪夺、不劳而获,更不是所有人坐吃山空、只享不建,而是全民的共同建设与共同享有。它强调人们既承担共建的责任,又拥有共享的权利,在共建的基础上共享发展成果。其中,共建是共享的前提,它促推共享,为共享提供更多发展成果。没有共建,就没有共享所必需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共享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共享是共建的最终目的,它引领共建,为共建提供无尽动力,没有共享,共建就会失去动力之源。然而无论是共建还是共享,它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最终都要落实到作为共享发展的实践主体人的身上,都依赖于每个人的积极参与,贡献自身最大力量,这也就涉及到每个人能否公平地获得参与共享发展机会的问题,对此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强调指出:“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1](P13)据此可见,共享发展不仅需要诉诸于权利公平,还需要诉诸于机会公平,机会公平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机会公平,罗尔斯曾做了这样的精辟阐释:“机会的公正平等意味着由一系列的机构来保证具有类似动机的人都有受教育和培养的类似机会;保证在与相关的义务和任务相联系的品质和努力的基础上各种职务和地位对所有人都开放。”[6](P278)可见,机会公平,质而言之,是指人们在获取各种社会资源、实现自我发展以及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等的机会上没有人因其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生活区域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对待,都拥有均等的机会,它是一种标志着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具有起点意蕴的公平,是实现权利公平的必要前提。如果说权利公平从法律制度层面规定了每个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平等地拥有参与权、发展权与享受权等,那么机会公平则从实践层面赋予了每个人均等地实现这些基本权利的机会,没有机会公平,权利公平只能是存留于法律制度中无法实现的条文而已。对于共享发展来说,机会公平就是要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机会成为共享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以及受益者,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公平地给予人人参与、尽力、享有的共建共享机会,共享发展只会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
环视当今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些造成社会矛盾、割裂社会认同、影响共享发展的机会不公现象,如因一些领域里存在的特权、垄断、歧视、腐败等外生因素所造成的就业升迁机会不公、享受优质教育机会不公、市场竞争机会不公等,对于这些机会不公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曾痛斥道:“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如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发展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7](P95)机会不公必然导致人的发展不公与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不公,尤其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百姓来说,不能公平地获得自我发展、奉献社会、享受成果的机会,就会被日益边缘化,最终必将造成上升通道的阻塞、社会的僵滞与阶层的固化。因此,要实现共享发展,必须注重机会公平,国家要尽大力量为每个人的生存、发展、享受创造均等的机会,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机会,都能获得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各个领域资源的机会。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4](P40)只有当每个人都能获得共建共享的机会,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激发出每个人的内潜在能与社会发展活力,进而才能使共享发展所需的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充分涌现出来,最终才能使人人全面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三、分配正义是共享发展的手段
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十分注重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将人们拥有获得感的多寡作为衡量共享发展是否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尺。获得感,即一种人的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满足后的内在充实感,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个人梦想的实现以及有尊严地活着等给人们内心带来的自豪感、归宿感、成就感等。就共享发展而言,由于“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8](P114)因此,获得感很大程度上源自收入分配,这最终关涉到分配是否正义的问题。
关于分配正义,穆勒在其著作《功利主义》中强调指出:“社会应当平等地善待所有应得到它平等善待的人,亦即平等地善待所有应绝对得到平等善待的人。这是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的最高抽象标准,一切社会制度以及所有有德公民的行为,都应当尽最大的可能达到这个标准。”[9](P63)分配正义涵括两个向度的正义,即初次分配正义与二次分配正义。初次分配正义是一种建立在个体能力基础上的“给其应得”的正义,它强调每个人的收入与自身的能力大小以及付出的多少成正比,关注的是个体收益是否公平。初次分配正义与获得感的内在关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初次分配正义强调公平基础上的效率优先,承认人们之间因自然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的合理性,这就根除了平均主义带来的活力缺少的弊病,有利于激发人的主体能动性,从而创造出大量丰富的人的获得感赖以产生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初次分配正义反对机会不均、非正当竞争等带来的收入差异,主张在给予每个人公平的发展机会、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公平环境的前提下,使每个人的收入与其能力相匹配,这就使得每个人的能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并因发挥了自身最大能力有所得、实现了自我人生价值而内心产生获得感。如若机会不公、竞争环境不公等导致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合理地拉大,有能力者发挥不了最大才能,得不到满意的收益,能力小甚至无能者反而收益过大,就会导致人们对初次分配不公的不满,也就很难使人们产生获得感。
由于强调能力、公平竞争、倾向效率的初次分配导致人们之间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一旦差距拉大到社会难以认可的范围,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就会有悖社会公平,减损人们的获得感,给社会和谐与发展带来不安定因素,因此需要通过二次分配进行调节。二次分配正义,也称矫正的正义,即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无差别地给予一切人以均等对待的正义,它是一种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观照社会公共利益与整体利益公平的正义。今天,二次分配正义通常是指政府按照建立橄榄型分配格局的要求即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控制过高收入,通过各种再分配调节机制对国民收入进行公平合理的再分配,给予弱势群体必要的补偿以切实保障其基本权益,以便消除绝对贫困,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二次分配正义有利于建立全面系统、公平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尤其是弱势群体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也能切切实实地享受到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被排除在共享发展成果之外,这能充分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获得感。
毋庸讳言,现今我国存在的行业、阶层、城乡、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非均等化等一些弱化人们的获得感、阻碍共享发展的不公现象,主要源于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不公。对于如何消除这些不公现象以落实共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好从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工作,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10]
对于如何分好“蛋糕”以使“蛋糕”更具普惠性,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其解决之道在于作出更有效的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安排,当前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0]具而言之,就是要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要做到“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1](P14)又要做到“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取缔非法收入。”[1](P76)同时还要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与帮扶力度,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全面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唯有如此,才能建立有利于共享发展、提升人们获得感的合理有序、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才能增强社会发展动力,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福祉,使每个社会成员无论智者或愚者、富者或贫者都能在共享发展中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拥有更多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国际人权文件选编[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5.
[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9][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16-05-10.
On the Ethic Orientation Of Xi JinPing's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
LIChong-ming
(SchoolofMarxism,MinnanNormalUniversity,Zhangzhou,Fujian363000,China)
Xi JinPing's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fruits' sharing and benefit during the course of our country'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t is a breakthrough of our party's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new period. Xi JinPing's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 focuses on promoting people's sense of gain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devot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mphasizes that the people must join in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together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t has distinct value orientation of justice and points to justice's three dimensions: fair right, fair chanc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mong which fair right is the concept's precondition, fair chance is the concept's tenor,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the concept's measure.
shared development; fair right; fair chance; distributive justice; sense of gain
2016-08-12基金项目:闽南师范大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SX12003)作者简介:李重明(1972—),男,安徽安庆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思想理论与文化建设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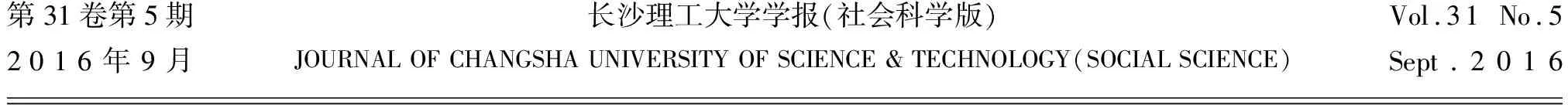
第31卷第5期2016年9月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TECHNOLOGY(SOCIALSCIENCE)Vol.31No.5Sept.2016
D61
A
1672-934X(2016)05-0071-05
10.16573/j.cnki.1672-934x.2016.0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