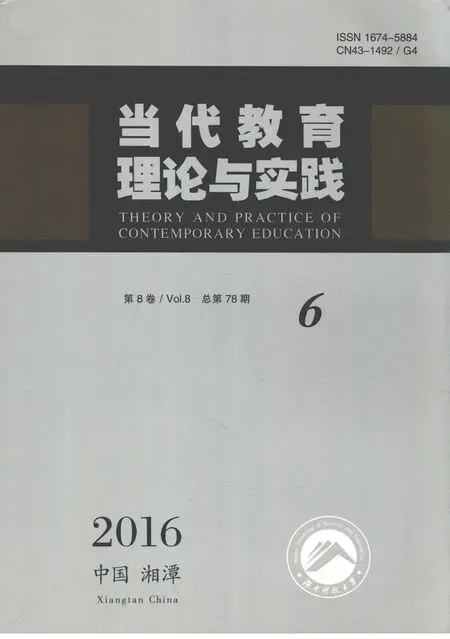论《远山淡影》中的双线叙事*
2016-03-21谌怡李尧
谌怡,李尧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论《远山淡影》中的双线叙事*
谌怡,李尧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远山淡影》是当代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处女作。小说以主人公悦子回忆故友佐知子及其女儿万理子的故事展开。回忆叙事是整部小说主要的叙事形式。主人公悦子的讲述在现实和过去中不断穿插进行,叙述记忆与创伤记忆时而分离时而汇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线叙事结构。通过这样一种双线叙事结构,悦子内心复杂矛盾的个体双重世界和分裂的性属身份得以展现。石黑一雄以其巧妙的构思和细腻的语言揭示了受创者在经历创伤后的苦难心路历程,表达了作者对于创伤和苦难人群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远山淡影》;双线叙事;回忆;创伤;性属身份
1《远山淡影》的双线叙事
有学者指出,“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位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1]106在《远山淡影》中,作者设置了双线的叙事结构:外部叙事线是人到中年、独自生活在英格兰乡村的悦子对自己近况的讲述,当时二女儿尼基到乡下探望母亲,并一起共度了5天,这时的地点为英国;内部叙事线是悦子对二十多年前日本长崎的追忆,讲述了故友佐知子与万理子的故事,地点是日本长崎。
在外部叙事线中,战争结束后几年,被战争摧毁的长崎到处都在重建。悦子在战后失去亲人,由绪方先生收养,在他的撮合下,悦子和绪方先生的儿子次郎结婚。后来悦子和丈夫住在长崎东边战后遗址重建的小区里。某年夏天绪方先生从福冈来到了悦子家,并短暂地居住了些日子。此时的悦子怀着孕,但一直恭敬地照顾着丈夫和公公。在那个夏天,悦子认识了佐知子和万里子,并卷入了她们的生活。至此都是来自悦子的回忆,然而悦子却自言道,“回忆,我发现,可能是不可靠的东西;常常被你回忆时的环境大大地扭曲,毫无疑问,我现在在这里的某些回忆就是这样。”[2]所以,对于悦子的经历,我们无法完全相信。从在英国的回忆角度来看,悦子后来应该是离开了丈夫,带着当时七岁的景子,随着在日本认识的英国记者谢林汉一起去了英国。在英国,悦子与谢林汉再婚并且生下了二女儿妮基。刚到英国的景子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整天将自己锁在房门中。两三年后,景子离家,去了曼彻斯特。六年之后的某天,景子被房东发现她一个人在公寓里自缢身亡,而发现的时候已是景子死后几天。在四月的时候,二女儿妮基担心母亲的身心状况,才从伦敦来到乡下看望独自居住的母亲,在五天的相处之中,悦子开始了此前描述的对往事的追忆。
在内部叙事线中,悦子回忆起时隔二十多年的长崎,当时偶然遇到了佐知子和万里子这对让人印象深刻的母女,由此卷入了她们的生活之中。佐知子在战争中失去丈夫,自己带着万里子颠沛流离。她们住过地道和破房子,目睹过一些可怕的事情。她们曾经看见过一个女人将自己的婴儿溺死然后自杀。这样的目睹经历给万里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后来她们寄住在伯父家,但后来又出来住在了长崎的一个小木屋里。佐知子认识了美国人弗兰克,并且决定带着万里子,随他一起去美国。佐知子虽然认为自己把孩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但是对万里子却是漠不关心,并且不顾她的反对,执意要去美国。在去美国之前,她将万里子心爱的小猫在水中溺死,给万里子造成了巨大恐惧心理。
整部小说由这两条叙事线交叉并行发展。看似悦子与佐知子有着相似的经历,但悦子那句“那天景子,我们都很高兴”,揭开了悦子回忆的面纱,由此推断佐知子就是曾经的悦子,万里子就是景子。悦子借佐知子的故事来叙述自己内心深处不可言说的创伤,将不愿意面对的事实通过另一个人的故事讲述出来。作者设置两条叙述线,在亦实亦虚的记忆碎片中,在模模糊糊的话语中,将悦子内心封闭多年的创伤世界与身份追寻的心路历程逐步展现。
2受创者的二重世界
在《远山淡影》中,两条叙事线同时发展并进,主人公在英国和长崎发生的故事在不同的时空相互映照,折射出受创者悦子矛盾而复杂的二重世界。
贾内将人类道德记忆分为叙述记忆和创伤记忆两种类型。叙述记忆是一种“社会行为”,应该是“生活的一方面,与其他经验并存”[3]163。而创伤记忆与叙述记忆不同,当人们遭遇创伤,即正常人类经验范围的恐怖事件时,就会产生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之情,而这种经历无法被规整到语言层面。创伤主角的这种创伤经历使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是创伤领域的世界,另一个是现在生活领域的世界。两个世界很难沟通。兰格尔在研究大屠杀的口头证词的时候指出,“幸存者永远也不可能加入到他现在所在的世界中。他的世界一直是双重性的,不是分裂成另一个世界的复影,而是平行存在。他的叙述不是历时的,而是共时的,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4]兰格尔的研究证明,创伤患者的记忆被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日常生活的叙事记忆,具有时间性;而另一部分是对创伤事件的记忆,具有无时性。兰格尔对于受创者的双重性世界的阐述贴切地契合了《远山淡影》中悦子在经历战争创伤和丧女之痛后无法言说的回忆。
在外线叙事当中,悦子对于景子的死因总是遮遮掩掩,我们无从知道她与景子在长崎时到底经历了什么,对景子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悦子总是梦到一个小女孩,并由此引发内线叙事中对佐知子和万里子母女在长崎时的回忆。文章中两条叙事线的并行,体现了创伤记忆与正常记忆从本质上的无法融合,由此导致的创伤受害者的“双重思维”。在悦子的回忆中,佐知子的经历看上去与悦子十分相似,但实际上是悦子将自己无法面对的创伤记忆映射在佐知子身上,使得佐知子这一角色能够作为一个载体让悦子保持安全距离来审视自己的过往及愧疚之情。由此,悦子可以小心翼翼地过滤自己的记忆,将之审视、修改、认同并完全接受。正如谢弗(Shaffer)所说,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解释,就是悦子将自身的过去苦难“投射”到了佐知子和万理子身上,悦子“试图通过寻找借口来避免受到责备和自我惩罚”[5]。与此同时,两条叙事线在并行中也有不断交汇,例如在第六章后,万里子听到母亲决定要和弗兰克去美国时,她难过而跑了出去,悦子追到河边,她们的对话如下:
“不管怎样,”我说:“你要是不喜欢那里,我们随时可以回来。”
这一次,她抬起头来,怀疑地看着我。
“是,我保证。”我说,“你要是不喜欢那里,我们就马上回来。可我们得试试看,看看我们喜不喜欢那里。我相信,我们会喜欢的。”[2]
在此,悦子反复用到“我们”这个词,就如同此时是悦子在与景子交谈一样,悦子和佐知子的身份巧妙地合二为一。两线的交汇,使得不断重复和扭曲模糊的事实逐渐清晰明了,创伤记忆在受创者的叙述中逐渐得到修补,从而自己获得一种补偿性心理暗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寻找安慰和合理性,从而使自身能够正视过去的创伤。她在长崎受到的创伤在事发后复现,却是以一种重构或移位的方式,并不是直接呈现事件本身。因此,石黑一雄运用独特的双线叙事,展现了悦子这个饱经磨难的女性在受创后的双重内心世界,体现了受创者想要通过回忆使自己与过去的创伤达成和解的艰难心路历程。
3受创者的分裂主体
悦子分裂的性别身份,一方面,是受民主思潮的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她想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在传统保守的日本父权的社会环境之下,她又被期望去履行同时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这两种矛盾的性属身份在双线叙事中得以充分的体现。所谓性属(gender),即“历史时段中,支配社会文化系统所强加在人类自然性别之上的社会性别属性,这种属性在取得普遍‘赞同’基础上,形成性别支配与被支配的意识形态和等级”[6]。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性别不总是一致或者连续的,性属与种族、阶级、道德伦理、性别以及区域形态相交织。所以,将性别与政治、文化分开是不可能的,它产生并且存在于其中[7]。
在外线叙事中,悦子感受到的是历史带来的压力与负重,依附于传统价值观和责任,她对自己的丈夫二郎逆来顺受,对公公绪方先生毕恭毕敬。与此同时,悦子更具有一种受压抑于母性身份的焦虑和恐惧。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特瓦在她的文章《女性的时代》中提到了关于孕育和母性的“根本考验”:
我的身体不再是我自己的,而是两个人一起经历,一起流血,一起感受冷暖,它也开始长牙齿,会流口水,会咳嗽,会长疹子,它也会笑。当我的小孩自己感受到快乐时,它的笑容只在我眼里。但是痛苦,来自内心的痛苦,从不分离,并且会突然毫无防备地激怒我。这种痛苦就好像是我必须去让它出生,但不愿意让它脱离我的身躯,坚持想让它回来,永远与我在一起。一个母亲不是在痛苦中让小孩出生,而是让痛苦孕育而生。一个母亲总是有着痛苦的烙印[8]。
克里斯特瓦对母性的心理解读恰好印证了悦子的母亲经历。她的女儿景子以及景子的自杀,都让悦子感到了极大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永远不会消失。就克里斯特瓦的观点而言,景子以永不磨灭的痛苦占据了她母亲的内心,且这种痛苦会逐步加重其更深的特性。
面对这种脆弱的母性身份的同时,在内线叙事中,悦子通过另一个主体——佐知子,表现出了自己坚强大胆的一面。战后的日本社会,民主与新的意识形态刚盛行,佐知子最终选择拒绝她被扼杀过的母亲角色,选择远离忠诚、责任以及同化,选择去迎接个人主义和独立民主。对当时的悦子来说,不同的选择可以让她成为另一个不同的自我。但是,这种选择使她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景子的死成为了她心中永远的伤痛,并会激起她内心深处对于母亲身份的矛盾之情与愧疚之感。
为了体现悦子作为战后受创者所遭遇的性属身份的分裂,小说以奇特的双线叙事展现了悦子连续、统一的主体身份的消解与重构。借用佐知子的故事,悦子想要表达出内心不敢面对但又压抑不住的情感,悦子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未能尽到妻子和母亲的职责,而作为一位独立女性,她对于命运的顽强抗争却带来沉重的丧女之痛。双线叙事并行交汇,相互交映,体现了受创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分裂的自我主体,以此种方式的叙述表达了对于性属身份的追寻与认同。
参考文献:
[1]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M].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 Van der Kolk, Bessel A, Onno Van der Hart. The intrusive past: The flexibility of memory and the engraving of trauma[M].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Ed. Cathy Caruth.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4] Langer, Lawrence L. Holocaust testimonies: The ruins of memor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tiy Press,1991.
[5] Shaffer B W. Understaning Kazuo Ishiguro[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6] 王晓路.性属/社会性别[M]//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7] Bulter J. Gender Troubl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lege,1990.
[8] Kristeva J. The Kristeva Reader[M]. Oxford:Blackwell, 1986.
(责任校对莫秀珍)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6.06.058
收稿日期:20151214
作者简介:谌怡(1991-),女,湖南岳阳人,硕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6)06-018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