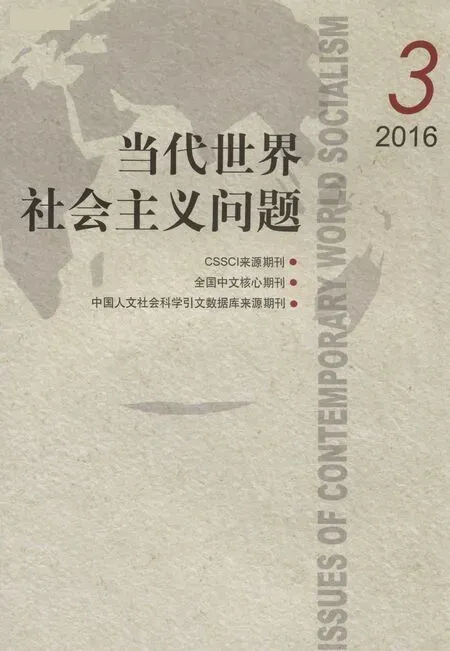在历史的阴影里
——评拉·霍夫拉格《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理查德·穆勒,一个革命工长和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兴起》
2016-03-20马嘉鸿
马嘉鸿
在历史的阴影里
——评拉·霍夫拉格《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理查德·穆勒,一个革命工长和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兴起》
马嘉鸿
在政党视角下的传统历史叙述中,191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通常被归因于斯巴达克同盟组织不力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关键时刻的背叛,这种解释框架忽略了工人群众在革命中的真实思想和行动。拉尔夫·霍夫拉格的这本书以传记形式,从一个革命工长、工人群众领袖的视角,重新审视了那段历史。通过描写以理查德·穆勒为代表的那个群体,向我们揭示了如何从政党到达群众这个通常被忽视的事实,并通过他的经历真实地佐证了德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1918德国革命;工人阶级;群众运动;自发性
一
德国洪堡大学政治科学专业博士后拉尔夫·霍夫拉格(Ralf Hoffrogge)的著作《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理查德·穆勒,一个革命工长和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兴起》,最近由德文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作者虽是一位年轻学者,但这已是他出版的第三本有关德国工人运动史的专著了。
根据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较于20世纪在东方发生的革命,经济基础更好、拥有数十年工会组织经验和第二国际中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德国,似乎更有理由摘取革命胜利的果实。然而,1918年的德国革命为什么却失败了呢?长久以来,西方自由主义者的通常解释是:革命是个坏东西,只有排除这个坏东西,才有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现。而按照苏联官方史学的观点,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则在于:一方面,被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关键时刻背叛了革命;另一方面,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的斯巴达克同盟虽然坚持革命立场,但没有建立起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组织严密、纲领明确、政治坚定、与机会主义彻底决裂的革命党,因而在革命中的政治行动能力薄弱。换言之,西欧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泛滥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软弱,断送了德国革命。这样的解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似乎已成定论。霍夫拉格的这本书则放弃了政党分析的传统视角,用微距镜头的方式重新审视德国革命,把焦点聚在了一个叫理查德·穆勒(1880-1943)的人身上。
理查德·穆勒是一名熟练的机床工人,早年在成员众多的金属业工会做到中层干部,曾在《金属业工会日报》上发表批判泰勒制的文章,认为泰勒制必将导致技术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为反对战争所造成的食品短缺,他领导工人在1916-1918年间举行过三次大规模反战罢工。1918年他担任了德国革命重要领导机构——士兵和工人委员会的执委会主席,并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并肩战斗,是“革命工长”中的一员。所谓革命工长,就是指工会领导干部,他们和工人一样供职于工厂企业,在工人中享有较高威信。这些工长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知道工人到底想要什么,在工人中有很强的鼓动和组织能力。一战期间在德国逐渐形成的革命工长群体,领导工人反战、反饥饿、要求提高工资,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影响。
在德国,工会是工人与雇主进行协商谈判的桥梁,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较强组织性的机构。对于工人自发的罢工行动,工会往往并不支持,因为这不仅是对工会领袖权威的挑战,而且会造成工会所掌握的储金的浪费,因为在罢工期间,工会需动用储金来补偿罢工工人的日用。
相比之下,斯巴达克同盟在政治上更具战斗性,其代表人物罗莎·卢森堡就曾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过激烈批判,并将群众性自发罢工视为推进革命形势的重要力量。在工会方面看来,罢工应该由工会来组织,革命工长就是联结工会和工人的纽带,可以在关键时刻为工人政党和工会开展活动提供群众支持,发起有组织、有目标的罢工行动。同时,革命工长也是工人利益的代言人,有时可能脱离工人政党和工会的掌控,自发地开展罢工活动。
霍夫拉格的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理查德·穆勒的传记,不如说是通过一位革命工长的视角,向我们呈现了那段革命历史中在传统视角下往往被忽略的事实。霍夫拉格坦言,他并不想再为德国革命史增加一个卡尔·李卜克内西或罗莎·卢森堡那样的英雄人物,而是要还原一个真实的、与普通工人联系密切的人,把理查德·穆勒的犹豫和不安、挫败和无奈置于时代的背景下,透过历史的阴影,向我们呈现一个普通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和时代烙印。
二
理查德·穆勒及其所代表的革命工长群体,既然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会在政治历史的书写中隐而不彰呢?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定期举行会议并留下会议纪要,也没有留下活动的文字记录;其次是因为他们并不掌握话语权,代表他们发声的往往是工人政党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或者是文盲,其中唯一的知识分子恩斯特·多伊米希曾担任过《前进报》编辑。卡尔·李卜克内西在1918年革命前夕虽曾多次出席过他们的秘密集会,但也从未将工人委员会视为革命组织,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下里巴人。斯巴达克同盟成员雅各布·瓦尔赫尔也曾批评道:“穆勒缺乏任何理论修养,他所领导的革命工人代表组织在促进革命的问题上也并不总是积极的,经常不能与斯巴达克同盟密切配合。”
理查德·穆勒所领导的组织虽然在政治上支持斯巴达克同盟,但二者的行事风格却完全不同,对革命的理解也不同,正如穆勒本人所言:“李卜克内西和其他斯巴达克同盟的人认为,革命应该是一个持续行动的过程……他们将俄国革命奉为教科书。”他认为,德国工人并不相信资本主义必然崩溃,也不认为遥远的俄国的革命经验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德国工人早已习惯了日复一日的工会斗争所带给他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以及世界一流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而不愿听从工人政党的号令而操练僵硬的“革命体操术”。
但理查德·穆勒无疑是一个革命者,他曾三次建立服务于革命的工人组织,不过均以失败告终。他既不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把革命仅仅当做形式上的最高纲领,也不像罗莎·卢森堡那样把革命看作推进历史进程的政治理想,在他眼中,革命更多是一种实践活动。他能清楚地判断工人的实际愿望和具体要求,不是把工人作为概念化的群众,而是与这些群众有着血肉联系,为群众所信任。他知道工人何时已准备好采取行动,了解工人的犹疑、焦虑和退却,而这正是德国革命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里,革命形势瞬息万变,不管采取什么立场和政治姿态的著名政治人物都备受关注:尚在狱中的卢森堡,拒绝参加社会民主党人控制的政府的李卜克内西,主张采取妥协策略的哈阿兹、迪特曼,实际控制着革命核心机构的艾伯特、谢德曼等。而像理查德·穆勒这样的活跃在革命一线的人物,却长期被德国革命的研究者所忽略。
在穆勒看来,1918年底至1919年初德国所发生的革命,实际上是1848年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流产。他的这种认识,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像他这样的群体在革命的记忆中被忽略了。
在1917年4月大罢工中,五万多名工人自发选举成立了工人委员会,作为代表罢工要求的领导组织。在1918年革命中,全国都成立了士兵工人委员会,作为革命发动过程中的重要领导机构。在穆勒看来,工人委员会不仅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组织日常斗争的工具,也不仅是用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机构,同时也蕴涵着通往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工人委员会是由工人直接选举产生的,是一个兼具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机构,因而可将其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政治形式。穆勒的战友恩斯特·多伊米希也认为,工人委员会可以成为代议制民主的替代性选择。但当革命的浪潮退却后,在实行阶级合作的魏玛共和国时期,这样一种打破了工会制度官僚化束缚、自发开展反战革命活动的群众组织,却演变成了企业工人的管理机构。穆勒本人也由于政治失意在二十年代前期退出了政治活动,后转战于商界,成为一名出色的企业家,并于1924-1925年撰写了三卷本的德国革命史,提供了很多一手材料,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广泛引用。他在书中写道:“这么些年里,每一个家庭都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如果失去将多么心痛。很多工人家庭已经不仅仅是小资产阶级,而是恰如其分的资产阶级。”他认为,在当时的德国,所谓统一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更多是基于政治立场而想象出来的产物。
穆勒所领导的工人委员会,在行事风格上与传统政党不同,在斗争手段上灵活多样,在行动过程中自我成长,这使它能够在革命中冲破工会制度的束缚发挥重要作用,但也会因其随意性和缺乏纪律性而随时可能涣散。关于革命工长及工人委员会运动在德国革命中的作用,可与罗莎·卢森堡有关群众罢工的思想相互印证。卢森堡认为:“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采取每一重大革命行动时的第一个天然的、具有推动作用的形式,而工业在社会经济中愈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作用愈是突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愈发展,群众罢工必然会愈是强大和愈是具有决定性作用。”她在1906年预言,局部的、偶然的冲突在危机局势下会发展为共同的阶级行动,使对于经济状况的自卫斗争上升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革命行动。这一预言在1918年德国革命中得到了证实,革命工长所领导的工人委员会运动的兴起,成为点燃革命的主要原因。然而卢森堡只猜到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局。随着劳资矛盾的缓和,工人阶级成分的多样化,工人政党领导力的下降,德国革命在掀起高潮后很快就衰退了,统一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并不像卢森堡所料想的那样坚定、牢固,能始终以自发形式保证革命的成功。
霍夫拉格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常被忽视的一个事实,即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如何才能被群众所接受。长久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撰写中,一方面强调革命领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但二者之间的纽带是谁?理查德·穆勒的经历似乎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在20世纪初的德国,现实生活中的工人阶级群众与革命家们所寄望的工人阶级群众往往并不一致,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当前利益,为这些利益而斗争,并不那么关心未来的伟大目标。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这些党的理论家似乎并不完全了解这一点,或者说,即使他们了解,也依然相信宣传教育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然而,基层的革命工长们却真正了解工人到底想要什么。要想理解真实的历史,就应关注以往处于人们视野之外的“民间史”,关注这些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普通群众,他们才是真正支配历史进程的力量。
此外,在对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方法上,本书也较有借鉴意义。当前流行这样一种历史观:把深刻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视为少数“大人物”的头脑作用于现实的结果,认为他们的良善或邪恶、正确或错误造就了历史。换句话说,就是把群众运动的历史根源追溯到少数领袖人物的动机与行动,使重大历史运动成了对少数英雄人物的表演的注脚。这种把历史事件的发生归结为偶然性或个体性因素的做法,充斥于时下不少著作特别是网络论坛,看起来很热闹、很吸引眼球,其实既肤浅又庸俗,阻碍着历史研究的深入。
相比之下,霍夫拉格这本书则试图挖掘历史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正如他本人所说:“本书不仅拒绝‘伟人史观’的方法,而且还要通过澄清个人在活动际遇中所受的局限,对这种方法予以批评。与此同时,本书并不刻意淡化理查德·穆勒的弱点和错误,但要反复展现的是他那些看上去纯属个人性质的失败,其根源却深藏于一场运动、一次革命和一个阶级的历史性失败之中。”在他看来,德国革命的发生、高潮和偃旗息鼓,都是由像理查德·穆勒及其代表的普通工人真实参与并塑造的,德国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因为这些参与其中的工人自己,当生存状况有所改善、有诸多可供选择的机会时,他们自觉自愿地放弃了革命这条道路。在偶然性事件的背后,是广大工人群众自身以必然的形式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如何将相对真实的历史从英雄人物、官方意识形态、泛滥的诗人情怀中拯救出来?在这方面,霍夫拉格本人虽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方法,在历史的阴影里进行求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分析路径。
(责任编辑:蒋锐)
马嘉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工人运动史、左翼思想史、比较政治思想(北京 100871)。
D6;D61
A
1001-5574(2016)03-01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