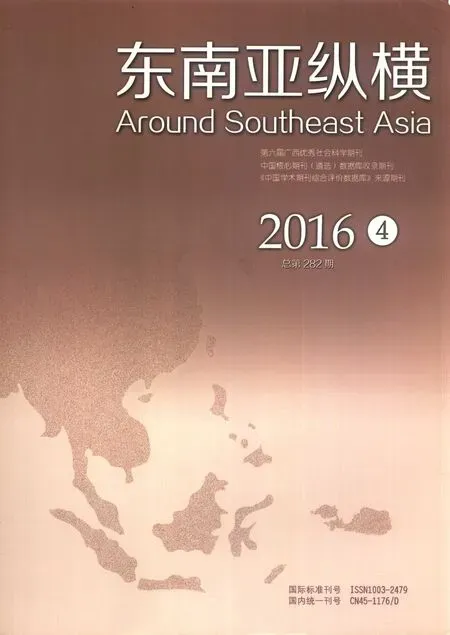地区性公民社会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
2016-03-19冯兆波
冯兆波
地区性公民社会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
冯兆波※
东盟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历史久远,并为精英所主导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实质上包含了一种东盟官方与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的博弈关系。在建设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的作用主要体现为议程创设和推动机制改革,东盟则既对公民社会力量进行吸纳,又与公民社会力量竞争。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公民社会
在东盟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地区性公民社会成为一支新兴的力量,本文选取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进程为案例,对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
关于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对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影响,学者们较为关注4个方面的内容:公民社会力量对于精英主导的“东盟范式”的挑战、公民社会力量在具体问题治理上发挥的作用、东盟成员国国内的民主化产生的公民社会如何影响区域主义以及东盟在具体政策和制度上的回应。本文选取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案例,则是基于东盟公民社会力量对于社会文化领域的问题之关注以及他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此外,有别于部分学者对东南亚各国国内公民社会力量的研究①这一类研究主要有:施雪琴:《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发展及其原因》,《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喻常森:《非政府组织与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郭又新:《非政府组织和印尼的政治变革》,《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王冲:《缅甸非政府组织反坝运动刍议》,《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等。,本文所分析的公民社会力量主要是地区性的。
一、精英主导与东盟社会文化合作
长期以来,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是东盟的工作之一。196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共同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该宣言中就有关于社会文化领域合作的表达:东盟的目的和宗旨之一即是“通过共同努力加速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在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科学和行政管理领域内,促进对共同有利的事业的积极合作和互助”①《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1967年8月8日,泰国曼谷),转引自:〔澳〕托马斯·艾伦:《东南亚国家联盟》,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10~412页。。在1976年第一次首脑会议之前,机制创建是东盟工作的重心之一,这亦可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得到反映:1967年,东盟签署了《关于加强大众传媒和文化活动合作的协议》,其中,提到了东盟成员国在文学等方面的合作内容、方式和思路;又制定了东盟人口—农村发展计划,得到了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协助;签署了一系列关于事故处理、灾害应对和毒品杜绝的协议;此外,还制定了社会发展、教育、妇女与青年等方面的合作计划②王士录,王国平著:《从东盟到大东盟——东盟30年发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6页,第133页,第143页。。
1976年,东盟在巴厘岛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议,区域协作进一步加强。东盟也通过会议文件表达了对社会文化领域议题的关注。其中,在《东南亚友好与合作条约》中,东盟重申“缔约国应当促进在经济、文化、技术、科学和行政方面的积极合作”,而经济合作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提高本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③“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Adopted bythe 1stASEAN Summit,Indonesia,24February1976,http://agreement.asean.org/media/download/20131230235433.pdf.。同样,在本次会议上签署的《东盟第一协调一致宣言》则列出了东盟在社会方面与文化和知识方面的行动纲领,并指出了东盟在这些领域所关注的问题,包括社会福利、人民发展机会、人口增长、药物毒品违法和地区观念培养等④“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Adopted by the 1st ASEAN Summit,Indonesia,24 February 1976,http://www.aseansec.org/5049.htm.。自第一次首脑会议起,东盟这种对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关怀在各种会议宣言中多次显现:1987年,东盟在马尼拉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议并通过了《马尼拉宣言》。在宣言中,东盟强调在人口劳务、控制和福利等方面加强合作,强调保护东南亚国家共同的资源和环境⑤王士录,王国平著:《从东盟到大东盟——东盟30年发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6页,第133页,第143页。。1992年,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会上通过的《新加坡宣言》也提到了社会文化领域的内容,如加强在环境保护、打击毒品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合作以及提高地区人民对东盟的认识等⑥王士录,王国平著:《从东盟到大东盟——东盟30年发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6页,第133页,第143页。。
在强调东盟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视的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东盟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过程是由精英主导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规定了东盟的机制,其中包括:由各成员国外交部长组成的外长会议;由各成员国委派大使组成的,在外长会议休会时进行工作的常务委员会;由专家和专务官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⑦《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1967年8月8日,泰国曼谷),转引自:〔澳〕托马斯·艾伦著:《东南亚国家联盟》,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10~412页。。而东盟秘书处则是于1976年东盟第一次首脑会议上通过决议成立的⑧该决议是《关于建立东盟秘书处的协议》。参见:王士录,王国平:《从东盟到大东盟——东盟30年发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4~95页。。另外,虽然以上两个决议皆通过首脑会议决议的形式达成,但在1992年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之前,首脑会议制度实质上未形成定期机制,而东盟的决策机构主要是外长会议⑨1992年,第四次东盟首脑会议通过的《新加坡宣言》规定,东盟各政府首脑每3年举行一次会议。参见:王士录,王国平著:《从东盟到大东盟——东盟30年发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50页。,这说明东盟在社会文化领域具体合作机制的缺失。因此,东盟决策模式及其在社会文化合作方面机制的缺失使得利益相关方难以进入东盟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决策过程中,从而保证精英更好地主导区域社会文化的合作。
二、社会文化合作:公民社会与东盟的博弈
东南亚语境下的社会文化合作实质上包含了一种地区性公民社会与东盟官方之间的博弈关系。
在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东南亚的官方在面对公民社会的行动时,曾做出以下几种反应:1.在公民社会力量较弱时,选择对其进行直接忽略;2.对公民社会组织进行镇压,如20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组织通过集会表达对东帝汶和缅甸人权问题的关注时,部分成员国政府的作为;3.在具体问题上与公民社会力量进行竞争,如东南亚的木材问题上;4.对这些公民社会力量进行吸纳,如将他们的倡议采纳到官方的决议和宣言中,或是通过会议和合作项目的形式对他们的专业性加以利用。
而东盟的策略选择则是基于多重因素考虑的,这首先体现为东盟作为一个次区域合作组织逐渐调整的性质上。东盟的创立是基于经济合作与共同应对共产主义“威胁”①Amitav Acharya,“Democratisa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Participatory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4,No.2,2003,pp.379.,后者更是在冷战背景下得到了西方阵营的支持。因此,在初创时期,公民社会被排除在东盟的决策程序之外。自20世纪80年代起,东盟国家放松了对外来资本的管制,加之地区相对的稳定,从而吸引了外来资本的进入,并最终导致了地区经济的膨胀。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国家的中产阶级得以成长并提出自身的主张,集中关注个人权利及自由民主的政府形式②Hewison,Kevin and Garry Rodan,“Southeast Asia:The Left and the Rise of Bourgeois Opposition”,Routledge Handbook of Southeast Asian Politics,Oxon:Routledge,2011,pp.25.。可见,彼时的东南亚的公民社会已有一定的参与空间。而实际参与到地区合作中的公民社会力量主要是经济和安全领域的技术专家,他们借助“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个“第二轨道”机制协助东盟应对两极格局的结束及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致使地区动荡,引发了对于政治和社会现状的挑战,并伴有“一个大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对于过去家长式制度的挑战”③Ahmad ,Zakaria Haji and Baladas Ghosal,“The Political Future of ASEAN after the Asian Crisi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5,No.4,1999,pp.767.。东盟国家为了应对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于1997年公布了《东盟远景2020》,倡议建立一个“关爱的共同体”。而公民社会组织则开始要求关注和改善诸如贫困人口和残疾人、少数民族、妇女、儿童等亲历了社会冲突的群体的处境以及落后的地区,并向国家和制度发出挑战④Mely Caballero-Anthony,“Non-state Reg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Economic Security:the Case of the ASEAN Peoples’Assembly,”The Pacific Review,Vol.17,No.4,2004,pp.568,pp.570.。因此,随着地区各国对于东盟的性质认知由一个维护独立和安全的合作组织发展至一个共同体,东盟官方为公民社会力量提供的参与空间将会逐渐增多。
其次,“公民社会”的规范和实践意义也影响着东盟官方对公民社会力量的策略选择。“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概念本身便是具有争议性的。安东尼指出,在亚洲的语境下,“公民社会”会被定义为:第一种是“非营利的志愿性组织”;第二种是“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及慈善组织”;第三种是“专注于社会物品供给,在国家和私人利益之上更大范围的非政府和非商业性质的市民与组织”⑤Mely Caballero-Anthony,“Non-state Reg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Economic Security:the Case of the ASEAN Peoples’Assembly,”The Pacific Review,Vol.17,No.4,2004,pp.568,pp.570.。而赫德曼则指出,典型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对于政治尤其冷漠的、志愿的和自发的横向领域”⑥Hedman,Eva-Lotta E.,“Global Civil Society in One Country?Class Formation and Business Activism in the Philippines”,Southeast Asian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Restructuring Governance and Deepening Democracy,Singapore and Copenhagen:ISEAS and NIAS Press,2005,pp.140.。另一方面,东南亚的公民社会力量往往采取和平的方式参与到地区主义当中,更多地是选择与东盟官方会议同期举行的研讨会、论坛,又或是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发行出版物、向官方提交建议⑦Kelly Gerard,“ASEAN and civil society activities in‘created spaces’:the Limits of Liberity”,The Pacific Review,Vol.27,No.2,2014,pp.274~282.。可见,东南亚的公民社会力量在规范上是和平的而不是对抗的,在实践上亦更偏好于和平的参与方式,为此,东盟官方对地区性公民社会应是更加宽容的。
最后,公民社会所关注的议题也影响着东盟的策略选择。例如,在人权问题上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地区公民社会力量施压、东盟官方回应的关系。当亚洲各国于1993年在曼谷举行会议为即将举行的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商讨共同对策时,东南亚的公民社会组织与西方的同行举行会议,批评各政府在会议期间发表的《曼谷宣言》,并公布了他们自身的宣言。随后,他们又参与到了维也纳的会议讨论中,并最终将自身的诉求反映到《维也纳宣言》当中。此后,东南亚的公民社会组织试图在东盟各国部长就人权问题举行会议时施加压力。公民社会对于人权问题的关注最终被部分地反映到《东盟远景2020》中。
相较于东盟官方,公民社会一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与官方合作,进而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影响东盟的政策,但也会有失去人民信任和间接维护了当前制度的危险;二是选择与官方对抗,可以动员支持者向官方施加压力,但这可能会面临着被监禁的危险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部分的公民社会组织对东盟的态度是冷淡的,这些公民社会组织往往通过世界性的国际组织来影响决策精英,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除了在1997年倡议建立一个“关爱的共同体”,在2000年举行的第四次非正式首脑会议上,“东盟名人小组”⑧“东盟名人小组”,即“Eminent Persons Group”.在报告中强调在构建“关爱的共同体”进程中“人们更好的参与”和“人们掌握控制权”,这表明东盟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开始发生倒转,“关爱的共同体”的建设不再是决策精英的特权,公民社会力量也开始关注东盟的作用①Alan Collins,“People-Oriented ASEAN:A Door Ajar or Closed fo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2,2008,pp.316~317.。可以说,东盟官方的吸纳意愿对于这些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的策略选择至关重要,东盟由此被视作公民社会向决策精英施压的通道。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内部就公民社会的态度产生的分歧对于地区性公民社会的策略选择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东盟内部的民主国家通常会力促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加入东盟的地区主义当中,泰国在2009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时,为了支持“东盟市民社会大会”的举行,向其提供了1000万泰铢的支持,并将公民社会代表与东盟领导人会面的时间延长至30分钟②Alexandar C.Chandra,“Civil Society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Regionalism in ASEAN”,Hosei KendyuJournalof Law and Politics.Vol.75,No.4,2009,pp.9.;而在同年的另一次会议上,缅甸和柬埔寨的政府代表则拒绝来自其国内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
议题关注也影响了公民社会力量对于东盟官方的策略选择。以社会文化领域为例,共同的议题关注使地区性公民社会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联系更为密切。《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所关切的主题表述为:“人的发展”方面,注重通过使东盟人民平等地享有发展的机会,改善生计;“社会福利与保障”方面,注重贫困的减少,增进社会福利与保障,构筑一个安全和没有毒品的地区,增强应对灾害和预防疾病的能力;“社会公正和权利”方面,注重促进诸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等处于弱势、边缘的群体的权利和福利;“确保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注重资源的保护,改善区域内水和空气质量,参与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协同行动;“建立东盟的身份与认同”方面,注重具有在多样性的各社会层次中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保护东盟的文化遗产,促进文化创新的能力③“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Blueprint”,Adopted by the 13th ASEAN Summit,Singapore,20th November 2007,http://www.aseamsec.org/archive/5187-19.pdf.。而东南亚的公民社会组织往往是“议题导向”的,即通常是基于解决特定问题而建立起来的④郭宏:《市民社会与东南亚的治理变革》,《国际论坛》2007年第5期,第74页。,例如:“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⑤“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即“Asian Forum for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Forum Asia)”,总部位于泰国。关注的议题是促进民主、人权和区域行动,“地区生态保护联盟”⑥“地区生态保护联盟”,即“Towards Ecological Recovery and Regional Alliance(TERRA)”,总部位于泰国。主要关注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环境保护问题;“亚洲原住民公约”⑦“亚洲原住民公约”,即“Asian Indigenous peoples’Pact(AIPP)”,总部位于泰国。关注的议题则是土著人的权利等⑧参见:Amitav Acharya,“Democratisa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Participatory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4,No.2,2003,pp.385.。由此可见,这些公民社会组织所关注的议题通常是政府和市场所不能单独有效解决的。实际上,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参与到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中来,能够对东盟在社会文化领域由精英主导的决策模式进行补充,不仅能够拓宽议程,还因为公民社会组织更贴近于“人”这一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主要对象而使得在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具体计划更易于实施。
三、地区性公民社会与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
(一)从地区合作文件中看地区性公民社会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
2003年,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通过了《东盟第二协调一致宣言》,宣布建立东盟共同体,其中的一个支柱是“社会与文化共同体”⑨“ 2003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Adopted by the Heads of States/Goverment at the 9th ASEAN Summit in Bali,Indonesia,7 October 2003,http://www.aseansec.org/15159.htm.。2006年,东盟公布了《东盟与公民社会组织关系的指引》,在其中指出,东盟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建立是为了“促进、加强和帮助实现东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医疗和技术领域的合作目的和目标”,将这些公民社会组织纳入机制中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促进一个以人为本的东盟共同体发展”⑩“Guidelines on ASEAN’s Relations with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CSOs)”,Adopted at the 2nd Meeting of the 39th ASEAN Standing Committee (ASC),Indonesia,18~19 January 2006,http://www.aseansec.org/18362.htm.。而在2007年签署的《东盟宪章》中也提出“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鼓励社会各部门参与并受惠于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的进程”①“Chart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Adopted by the 13th ASEAN Summit,Singapore,20 November 2007,http://www.aseansec.org/21069.pdf.。到2009年,东盟更是发布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细化了地区性公民社会组织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
由此,地区性公民社会组织开始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他们参与议程的创设;另一方面,他们也努力推动机制的改革。而由于所关注议题的广泛性和力量的分散,东盟的公民社会力量更多地是通过一种地区性的倡议网络,将各种公民社会力量召集起来,如:由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提议建立的“东盟人民大会”②“东盟人民大会”即“ASEAN Peoples’Assembly(APA)”,成立于 2000年。、由马来西亚政府委托马拉理工大学举办的“东盟市民社会大会”③“东盟市民社会大会”即“ASEAN Civil Society Conference(ACSC)”,成立于 2005 年。、《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提出建立的“东盟社会论坛”④“东盟社会论坛”即“ASEAN People’s Forum(APF)”,成立于2008年。等。
在议程设置方面,例如:2007年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人民大会”围绕《东盟宪章》的制定向第12次东盟首脑会议提交报告,其中建议宪章的制定应优先考虑人类的发展与安全⑤“ Repor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Fifth ASEAN Peoples’Assembly to the 12th ASEAN Summit”,13 January 2007,Cebu,Philippines,http://www.forum-asia.org/news/in_the_news/pdfs/2007/chairman_report_5th_apa%20.pdf.。此外,对于人权问题,地区性的公民社会力量始终保持关注,并努力将人权议题纳入到东盟事务之中,最终成为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目标,将“保护人权”“尊重人权”“强化保障基本人权”等内容分别写入《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文件中。
(二)“亚洲人民倡仪团结”“东盟市民社会大会”和“东盟社会论坛”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自2005年第一次东盟市民社会大会在向东盟首脑会议递交的报告中呼吁“重新审视东盟方式,从而采取更加快速和有效的行动来实现东盟人民的利益。在形势需要的情况下,协商共识原则不应该阻碍东盟采取有力的正义行为”⑥“Statement of the ASEAN Civil Society Conference to The 11th ASEAN Summit”,October 2005,http://www2.nesac.go.th/english/Main_highlight/pdf/ASEAN_Statement.pdf.,东盟市民社会大会一直在促使东盟变革其机制方面做出努力。2006年,第二次东盟市民大会在其声明中提出,为了满足东盟立即解决地区人权问题的需要而“挑战东盟的不干涉原则”,还提出了制定一部“东盟人民宪章”(an ASEAN Peoples’Charter)的计划⑦“ASEAN for the People”,Statement of the 2nd ASEAN Civil Society Conference(ACSC II),10-12 December 2006,Cebu, Philippines, http://www2.asetuc.org/media/Partners_Page/5_0_ASETUC_and_Civil_Society_in_ASEAN_2.pdf.。
“东盟人民大会”最初由“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⑧“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即“ASEAN-Institutes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ASEAN-ISIS)”。于1988年向东盟官方提议建立,并将它设定作为正式程序之外的人民表达和传送观点、利益的工具,这是一个由“第二轨道”的学术共同体推动的、在“第一轨道”的决策制定者和“第三轨道”的公民社会组织及其他部分之间建立的一个沟通桥梁。鉴于这一新出现的公民社会组织网络包含的成员数量较多,东盟官方不能对其忽视;同时,由于其讨论的问题在官方立场上的敏感性,东盟必须与它保持距离。因此,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于2009年结束了该组织。与此同时,自2006年起,“东盟市民社会大会”开始举行,并由“亚洲人民倡议团结”组织了2006年、2007年和2008年的会议,以期改变在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导下的“东盟人民大会”的低自主性。
“亚洲人民倡议团结”于2006年建立,旨在为那些对本地区具有利益和关怀的东南亚公民社会组织提供一个协商的场所。2005年,第十一次东盟首脑会议公布了《吉隆坡宣言》,提出要制定一部《东盟宪章》,并同时成立了一个“名人小组”。随后,“亚洲人民倡议团结”向该小组递交了一份报告,详细地分析了人权、民主、非传统安全等对于东盟来说较为敏感的问题。“名人小组”于2007年向东盟首脑会议提交了报告,随后,东盟签署了《宿务宣言》,肯定了“名人小组”的报告,并成立一个“高级行动小组”⑨“高级行动小组”即“ High Level Task Force(HLTF)”.来拟定宪章。2007年,东盟各国首脑签署了《东盟宪章》。以人权问题为例,“亚洲人民倡议团结”向“名人小组”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权和尊严是东盟所宣扬的核心价值与指导方针的一部分。对于人权和尊严的促进、保护应该成为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整合与合作进程的首要目标”①“Submission to the Eminent Persons Group on the ASEAN Charter”,by Solidarity for Asian People’s Advocacy(SAPA),17th April,2006,http://seaca.net/viewArticle.php?aID=945.。而“名人小组”向东盟首脑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则称,“成员国最终应发展成为包含有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整合3个支柱的东盟联合体,3个支柱在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些法律的规则和地区的整合所应该保护的所有个体的权利方面紧密联系和相互促进,使东盟保证所有公民的安全”②“Eminent Persons Group Report on the ASEAN Charter”,by Eminent Persons Group,December,2006,http://www.aseansec.org.19247.pdf.。最终,在《东盟宪章》中,人权问题被表述为:东盟的目的是“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这应该是东盟成员国的权利与责任”;“东盟应该建立一个东盟人权机构”③“Chart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Adopted by the 13th ASEAN Summit,Singapore,20 November 2007,http://www.aseansec.org/21069.pdf.。可见,“亚洲人民倡议团结”这一地区公民社会组织网络的倡议、特别是从前对于东盟官方而言特别敏感的议题在《东盟宪章》中得到了部分采纳。由于人权问题关涉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可见,东盟面对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参与时倾向于选择对其进行吸纳与其进行合作,从而推动这些公民社会力量在其中发挥良性作用。
另外,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进程中,官方除了对公民社会力量进行吸纳与合作,还主动创设官方性质的论坛与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进行竞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东盟社会论坛”的创建④Alexandar C.Chandra,“Civil Society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Regionalism in ASEAN”,Hosei Kendyu Journalof Law and Politics.Vol.75,No.4,2009,pp.8.。
四、地区性公民社会的参与限制
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东南亚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21世纪以来,在公民社会力量的参与下,东盟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这种“参与式区域主义”也面临着以下障碍:
首先,东盟组织内部成员间在制度、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导致东盟的地区合作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以东南亚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互动过程。在社会文化共同体有关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东盟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而公民社会力量更多地是以召开论坛和提交声明报告的形式发挥影响。
其次,东盟没有为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提供一个参与东盟决策的正式机制,这意味着东盟官方依旧保持着将公民社会力量边缘化甚至将其排除在参与过程之外的能力。以“东盟—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人权问题的研讨会”(ASEAN-ISIS Colloquium on Human Rights)为例,这一研讨会原本被设定为东盟官方与公民社会组织在人权问题上进行沟通的桥梁,而东盟国家的参与则仅仅出于对地区内人权观念的压制。随着议题的深入,参与论坛的东盟国家官方代表数量锐减,从而导致该研讨会的效力被废止⑤Kelly Gerard,“ASEAN and Civil Society Activities in‘Created Spaces’:the Limits of Liberity,”The Pacific Review,Vol.27,No.2,2014,pp.273~274.。正是这种机制的缺失为东盟的精英提供了操纵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进程的便利。
再次,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在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对于议程设置所发挥的功能有限。东盟官方严格地控制着公民社会力量的参与资格,官方活动的参与名单往往由各成员国政府拟定,这种方式往往将具争议性议程的和草根性的公民社会组织排除在东盟的活动之外,以致于有学者将参与官方活动的组织称作“政府组建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此外,东盟官方也通过把持议程设置的权力以及利用资金资助来限制公民社会力量在这些活动中的参与。地区性公民社会力量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主要是:协助促进地区认同和身份的形成和协助提高东盟在人民心中的形象⑥Alan Collins,“People-Oriented ASEAN:A Door Ajar or Closed fo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2,2008,pp.325,pp.322.,而区域性社会力量对于在决策系统中身份的机制化的期望则难以实现了。
再次,由于地区性公民社会组织各自关注的议程过于分散,往往在面对东盟官方时难以形成统一的立场⑦Alan Collins,“People-Oriented ASEAN:A Door Ajar or Closed fo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2,2008,pp.325,pp.322.,这阻碍了他们与东盟官方建立机制化关系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颜 洁)
Regional Civil Society and the Building of 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Feng Zhaobo
There has been a long history of ASEAN in the field of social-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such type of cooperation is led by the ASEAN elites.In the context of ASEAN,this social-cultural cooperation substantially contains a gam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SEAN officials and the regional civil society forces.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the 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the role of regional civil society is mainly reflected by setting agenda and pushing mechanism reform while ASEAN engage and also compete with the civil society forces.
ASEAN;Socio-Cultural Community;Civil Society
D814.1
A
1003-2479(2016)04-0081-06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