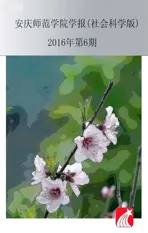认知、组织与形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实践与启示
2016-03-18徐理响
徐理响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认知、组织与形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实践与启示
徐理响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有力地打击了腐败现象。特定阶段的党情、国情与世情形塑了意识形态化的腐败认知,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及专门成立领导组织和专案组,提升了反腐组织的权力;规模化、集中化反腐运动的开展和运动式反腐形式选择,起到了“不敢腐”“不愿腐”的作用。这一反腐实践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腐败对党和国家的严重危害性,标本兼治,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提高腐败的成本;要提升制度化反腐机制的独立性、自主性,赋予与之相匹配的权力;要推进制度反腐与依法反腐,优化党和国家腐败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所发起的反腐运动,展现了巨大的威力,对于党风廉政建设,打击阶级敌人的渗透与破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和方向,推进各方面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均具有重大的意义。总结这一阶段反腐的经验教训,对于推进当代党风廉政建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反腐认知
1949年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建国的历史伟业,但随着党的生存环境的变迁,党内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消极腐化现象。一些党员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贪污腐化,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作风盛行,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损害了党的执政基础,威胁着党的执政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就意识到,因为革命的胜利,党内可能会出现一些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1]。因此,反腐倡廉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重要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就决定正式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在“高饶事件”后,以独立性程度更高、权力更大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取代之。
客观来看,腐败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顽疾,腐败现象伴随着人类的政治发展。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特定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党对于腐败现象的认知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化色彩,具体表现在:一是腐败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天然相违背;二是这些现象的滋生与阶级敌人、敌对分子的破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间的阶级斗争。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腐败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具有天然的不相兼容性。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发出过《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投机腐败分子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党在群众的威望,必须坚决地清洗这些坏分子,坚决地和不良倾向作斗争[2]。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党同样注意到当时党内和局部执政地区的政权机关内出现严重浪费、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现象,并进行了坚决的打击[3]。刘少奇在1939年就曾经指出,“共产党所代表的是被剥削而不剥削别人的无产阶级,它能够使革命进行到底,从人类社会中最后消灭一切剥削,清除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4]。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和决心,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即发动了一系列的清除腐败的运动,这无疑是党的宗旨的必然逻辑。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政治环境。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就认为,“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这些敌人包括反对我们的帝国主义,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国民党的残余、特务和土匪,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等[5]。这些敌对势力一方面通过直接的暴力或准暴力形式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另一方面也会通过隐蔽的形式潜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内,通过各种形式腐化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伺机进行破坏。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时就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6]466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也认为,刘、张不仅仅是两个普通的贪污罪犯,两个普通的窃盗,而是“像党的二中全会所预见的,他们是经不起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向敌人投降了的,并很快实际上成为反动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从内部来腐蚀党和瓦解党。”[7]1182同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实行“三反”运动的决定也直接指出,“反动统治的残余作风和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在猛力地侵蚀我们,以致我们的许多干部发生了贪污、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严重现象”,“党内干部中受资产阶级侵蚀而发生的严重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将被广泛揭露和受到制裁;党内在许多干部中所发生的不问政治和放弃阶级的右倾的错误思想将受到批判”[6]473-474。“高饶事件”发生后,党更加注意到党员干部贪污腐化等违纪行为与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间的紧密关联性。“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活动是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化和深刻化的反映”,“他们的这种反党活动无疑适应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愿望。他们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7]282。1955年之所以以党的监察委员会取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其重要原因即认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已不能适应在阶级斗争的新时期加强党的纪律的任务”[8]133。其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变化,党对于腐败与阶级斗争关联性的认知更加清晰。1962年12月28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工作报告中就特别强调,有一些同志,对于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往往不用阶级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观察和分析,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7]968。196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五反”运动时直接指出“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是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9]174
反腐与意识形态斗争、阶级斗争的相互交织,无疑促使党中央提升对腐败的认知,客观上也有助于提升党拒腐抗变的能力,有助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这也启示我们,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不断提高对反对腐败的认识,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不过,三者的相互交织,一定程度上又会影响反腐所应有的独立性,弱化了党和国家制度化反腐体制机制的作用,不利于反腐在制度化轨道内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反腐组织与反腐“真空”的化解
反腐组织的高度独立性、自主性,以及赋予与之相匹配的权力,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反腐的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基本确立了体系化的权力监督与反腐败体制。1949年9月,根据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条的规定,成立了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根据第十八条的规定,成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正式形成了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等为主要组织载体的法定权力监督与反腐败组织。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以独立性、权威性更高的党的监察委员会代替原有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虽然在党和国家内都构建了制度化的权力监督与反腐败体制,但受制于国家发展的特定阶段,这些制度化的权力监督与反腐败体制、机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没有很好地运转起来,制度化程度相对较弱,独立性、自主性程度不高,结构功能分化有限。同时,受制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党和国家内制度化的权力监督与反腐机构事实上也难以独立承担严峻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形势下的反腐重任。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与组织作用,对于反腐工作的推进就显得尤为关键。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运动的一般组织形式来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在其中发挥着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是运动的发起者、领导者,甚至是直接的组织者,在一些重大或典型案件的查办、定性以及处理环节中也都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在运动中成立的各种领导组织和专案机构则起到组织协调和具体实施的作用,是反腐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如在1951年“三反”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在党派团体、政府和军队中,都成立了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再如在新中国成立初具有标杆意义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中,由河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处理刘、张案件的专门委员会,同时在专门委员会下成立专案组,具体负责侦讯工作。
而当时党和国家中的专门监督机关,一定程度上都面临着体制独立性的困境,自主性程度相对较弱。如党的纪委及其后成立的党的监委,受附属性纪检体制的影响,监督功能实际上受到制约。1951年4月时任中纪委书记的朱德在党的全国纪检干部会议上就曾经感叹,全党担任纪律检查工作的专职干部尚不足1 500人,并且干部质量也不高。在开展工作方面,十分被动,“有些应该处理的问题未处理,已处理者亦多不及时,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7]91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文革”之前,“不是政党的组织与纪律起作用,而是政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所动员的社会大众起作用”[10]。作为行政监察机关,成立伊始,就一直面临与党的纪检组织之间的功能重叠等问题,因此,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监察部,其职能改由党的监察委员会负责。对于当时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而言,受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和法治意识的影响,其在反腐败中亦更多的是参与党所领导的各种反腐运动,主动性、自主性受到一定限制。
以刘青山、张子善案为例。1951年接到有关刘、张案件的举报后,河北省纪委先派出纪检组进行调查,后经河北省委报请华北局批准。华北局接到省委请示后,经讨论并报中央批准,决定将刘、张逮捕法办。11月29日张子善被捕,12月2日刘青山归国后亦被逮捕。12月4日河北省委经过研究,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张党籍的决议。根据华北局会议精神,河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委组织部、省纪委、河北省检察署、河北省法院、河北省监察委员会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组成,并成立专案组,具体负责侦讯工作。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华北局在接到河北省委意见后,对报告和其他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综合各方面意见,于20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处理刘、张的意见。中央批复后,1952年2月10日举行了公审大会。河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张庆春担任公审大会主席。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委副书记薛迅(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代表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诉了刘、张犯罪事实。天津专区宝坻县农民孙树林,代表遭受刘、张案直接危害的灾民和民众,在大会上控诉了二犯的罪恶。最后,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宣读了判决书[11]。从刘、张案件的立案、侦讯及处理过程来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起直接领导与组织作用,专案组是具体的实施者,党的纪委、组织部门,人民检察院、法院是重要的参与主体。
显然,这一时期反腐的高效率推进,与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以及直接领导、组织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我国在权力监督与反腐实践中一直存在“不能监督”“不敢监督”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的实践无疑证明,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以及自上而下的坚强的领导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监督真空”。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及其间成立的各种领导组织与专案机构,是特定时代或某些特殊案件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代国家的成长,应当更加重视制度化反腐机制的作用,逐步提升党和国家内制度化反腐机构的独立性及其权力的威慑性。从腐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视野看,制度化权力监督与反腐机制结构功能的受限,或不利于反腐的健康、深入、持续进行。
三、反腐形式选择与反腐绩效
“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是反腐的基本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的反腐运动,运动式的反腐形式选择,“有腐必反”的客观效应,极大地教育了广大的党员干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不敢腐”“不愿腐”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基于国家发展的特定阶段,制度反腐、依法反腐的条件并不成熟;另一方面基于对腐败性质及其严重性的认知,特别是腐败与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相互交织,使得党更倾向于通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发动政治运动,集中力量,清理贪污腐败行为。反腐运动和运动式反腐就成为这一时期反腐中的常见景观。
反腐运动,即在某一特定时段内,集中主要力量,甚或将全部工作重心转移,专门治理某些较为突出的腐败现象,形成聚焦与冲击效应。从人类反腐的实践来看,当某一阶段腐败现象较为严重,或腐败严重影响国家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健康有序发展,影响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时,集中力量清理腐败现象,也是一种常见的策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实践来看,反腐运动往往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特征,即不局限于某一层级、某一区域、某一行业、某一群体,而是在所有地区、行业、群体中普遍开展,冲击力十足。如1951年的“三反”运动就强调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在党的领导下分为党派团体、政府、军队三个系统,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发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按级相互检查。党的纪委、人民政府的监委、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军队的政治工作机关和纪委都应将这件事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党的报纸和宣传员、报告员,应积极参加这一斗争。工会、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应在自己的任务中加上检举和纠察贪污和浪费现象,并派遣自己的积极分子参加各级各系统的节约检查委员会。在机关、企业、学校、部队、农村和城市的街道组织中均应发动这一运动,依靠群众进行检查,与他们的工作、生产、学习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6]484。
当然,反腐运动并不意味着就是运动式反腐。反腐运动可以在制度化反腐机构的直接主导下进行,可以通过制度反腐与依法反腐的形式进行。而运动式反腐,往往意指通过发动各种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揭露、检查和处理腐败问题。运动式反腐往往不是通过党和国家专门的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通过规范化、程序化的案件检查,特别是依法反腐的形式,而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鼓励群众检举,以群众集会的形式进行公审,搞“人人过关”。如上述1951年发动的“三反”运动的决定中就指出要“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6]488。在其后的相关指示中再次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6]501。在1963年关于“五反”运动的指示中也强调“要普遍、深入地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提出意见,批评缺点,揭发坏人坏事”[9]187。
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在全社会,特别是在广大的党员干部中,起到了极大的震动效应,深刻地教育了广大的干部群众,一定程度起到了“不愿腐”的作用,对于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密切干部与群众的联系,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腐败分子的“从严从快”的大规模检举、检查与处理,也有助于形成“不敢腐”的威慑氛围。不过,反腐运动和运动式的反腐形式,虽然具有全面性、系统性、集中化、专门化的特征,在特定阶段也具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但并非一种可持续性、常规化和制度化的反腐形式。党和国家全部工作重心全面转移至某一运动,容易对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造成冲击。运动式反腐形式,在程序化和规范化方面有所不足,虽然冲击力、威慑力强,但如果不能予以制度化、法治化,既可能造成一些冤假错案,也难以实现制度反腐、依法反腐,难以达到“不能腐”的理想状态。
四、结语: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的成绩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运动,具有系统化、规模化的特征,冲击力十足,对党从革命环境到执政环境转变过程中出现的贪污腐化等消极现象起到了非常有效的遏制作用。如在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间发动的“三反”运动中,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31.4%;其中共产党员19.6万人,占贪污总人数的16.3%。贪污1 000万元以上的10.591 6万人,占贪污总人数的8.8%[12]。其取得的成绩可见一斑。这一时期反腐的经验需要汲取,一些问题同样需要总结,为当下党和国家的腐败治理体系的优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借鉴。
第一,对腐败问题严重危害性的认知及“零容忍”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绩效的取得与当时对腐败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联,党提升了对反腐重要性的认识,在思想上表现为毫不含糊,在行动上表现为即知即行。当然,当时意识形态化、阶级斗争化的反腐认知是特定时代和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产物,同时反腐工作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和阶级斗争化,既会影响反腐的客观性和“零容忍”,长期来看也将不利于反腐廉政文化建设。但对我们的启示是,必须要高度重视腐败对党的事业,对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严重危害性,对于腐败现象,一定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标本兼治,唯此,才能真正解决腐败这一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毒瘤”。
第二,提升反腐机构的权力独立性与自主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的高效率推进,与当时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运动中成立的各种领导小组的组织协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上述主体所拥有的权力与权威性,有力地化解了“不能监督”“不敢监督”的“监督真空”问题。但从现代腐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视角看,如何发挥制度化反腐机制的功能角色,直接关系到反腐工作的可持续性和专业性。因此,进一步提升党和国家内纪检、监察、检察、司法等制度化、法理化以及反腐机制的独立性、自主性,应当是我国反腐体制与机制改革和完善的重要问题。
第三,推进制度反腐、依法反腐。受制于国家发展阶段和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形式选择主要是依靠党领导下的政治运动,具有规模化、集中化之优势,效率较高,但同时亦存在规范化、法理化不足,主观性、随意性大等弊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纪检机关,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行政监察机构建制,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其后各项党纪、法规的颁布实施,都表明当代中国的反腐工作开始进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完善和出台了大量的党纪法规,制度反腐和依法反腐的水平明显提升。从长期来看,唯有制度反腐和依法反腐,才能深入、持续地推进反腐工作,提升反腐绩效。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反腐实践启示我们:一方面,党反腐倡廉的决心和全党的重视程度与反腐绩效存在直接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制度化反腐机制的独立性、自主性,推进制度反腐、依法反腐,以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党和国家腐败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真正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目标。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38.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82.
[3]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99.
[4]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02.
[5]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3-74.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7]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林尚立.建构民主——中国的理论、战略与议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98.
[11]王少军,张福兴.反腐风暴:开国肃贪第一战[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135..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85.
责任编校:汪沛
Cognition,Organization and Instrument:The CPC’s Anti-corruption Practi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New China
XU Li-xia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Anhui,China)
In the early stage of new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aunched a massiv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t effectively combated corruption.However,in the specific political,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the party’s cognition of corruption was ideologically characterized.The direct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s well as special leading organizations and investigation teams enhanced the anti-corruption power.The launch of large-scale centralized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and the choice of anti-corruption for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ooting out corruption.It tells us that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damage of corruption to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We should seek both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solutions,adopt a“zero tolerance”attitude to corruption and increase the cost of corruption.We need to improve the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anti-corruption and confer matched power.We should promote institutional anti-corrup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optimize the party and state corrupti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improve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early stage of new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ti-corruption
D23
A
:1003-4730(2016)06-0094-05
时间:2017-1-20 15:3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70120.1533.019.html
2016-08-25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派驻纪检组与纪检体制完善化研究”(AHSKQ2014D133);安徽大学廉政法治协同创新中心重点课题“我国预防和治理腐败体制的法制化研究”(ADLZFZ14ZD04)。
徐理响,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