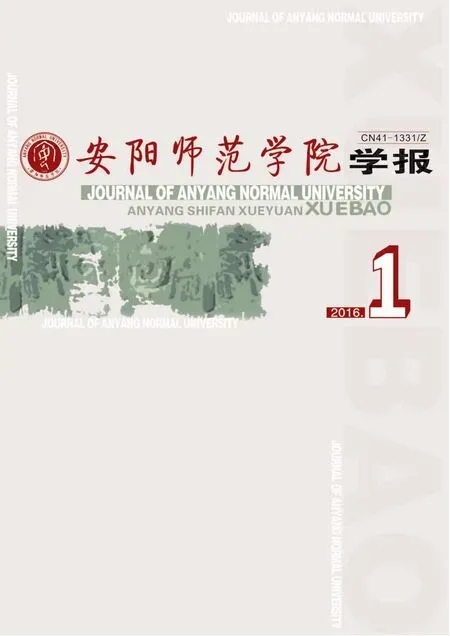论杨炳武学思想的理论支撑体系
2016-03-18杨彦明
杨彦明
(安阳市梅花拳协会,河南 安阳 455000)
论杨炳武学思想的理论支撑体系
杨彦明
(安阳市梅花拳协会,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杨炳的《习武序》的武学思想,其理论支撑体系主要有:儒学传统文脉的主导,中国道教文化的浸润,佛学文化的影响,易学法则的灵感思维,程朱理学的推演与阐发,古代兵法的吸纳和渗透,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
[关键词]杨炳;《习武序》;武学思想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无源之水,它必须有一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和强力的支撑体系。清代武学家杨炳武学思想的理论支撑是多元的,可以说是融儒释道三教之精义,汇易学之神奇法则,继承了中国古代兵法思想。虽然是多元的,但总不外乎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
一、儒学传统文脉的主导
杨炳的武学著作《习武序》从头至尾都贯穿着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儒学思想。虽然儒学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流变,但其核心是“守恒”的。例如杨炳关于“文武双修”的思想就直接来源于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家语·相鲁》)的哲语。
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核心是其“仁爱”观念,同时这也是中国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即武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习武之人最重要的就是“武德”。崇尚伦理,讲求仁义忠信,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鲜明特色。这一特色,至今仍使得中国武术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不仅是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一种途径。杨炳为习武者制定的《五戒》《五要》《习武规矩十二条》都没有超出儒家“仁爱”的范畴。
杨炳对习武者的武术精神与德行通过三个层次表现出来。
第一个层次表现“保身保家”“卫君卫国”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他要求习武者首先树立穷者保身保家,达者卫君卫国,“治四海如磐石之安,登万民于仁寿之域”的习武观,明确习武宗旨,做“尚志好学之士”“有勇知方之士”,为大众安康幸福,为社会稳定,国家强盛做出贡献,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
第二个层次表现为“尊师重道”“孝悌仁义”,及“技道并重,德艺双修”等个人的武德修养方面。他要求学生首先要“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道”。要尊师重道,孝敬父母,“不可退前落后,切忌忘师背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许“好勇斗狠”;传道之师不可重利轻艺,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习武之人要“安详恭敬”“务要沉细”,把“上马如无敌天神,下马如有道贤人”作为自己的修身目标。
第三个层次表现为集体的道德观念。他要求所有习武者“扶危济贫、除暴安良”,做到“安定”“安民”“匡扶正义”“见义勇为”等。杨炳为弟子制定的《习武规矩十二条》《五戒》《五要》既是习武者个人的行为准则,也是一种集体的道德观念。
杨炳的《习武序》是运用儒家经典解释拳理的成功之作,是拳与儒合的典范。
二、中国道教文化的浸润
武术与道教同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道教对武术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宗教,道教的宗教精神、理论和修炼方法自然被杨炳融摄于自己的武学思想之中,成为武术(特别是像梅花拳这类内家拳)的理论依据和技击原则。道教对杨炳武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尊道而贵德,习艺先学礼。老子在《道德经·德篇》中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天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道教的创始人老子充分认识到“德”在育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于是将“德”立于“道”之上、之前,有道者必具有高尚的德性,有了高尚的德性才可得道。所以,修道应以德为基,修道的先决条件就是立德,立德就要在日常不断积累功德,亦即加强自我修养,以具有良好的品德。所以,从古至今,在武林中始终流传着“未曾习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修德”和“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武林名谚。杨炳在他的武学著作中讲具体技术不多,却给弟子们立下了条条的拳规戒律。很显然这是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
其二,形神俱妙,形神兼备。道教内丹学追求个体生命的“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梅花拳《小根源经开篇》),练形存神,乐生贵生,这不仅是对生命的积极追求,而且是对肉体和精神统一性的非常注重。所谓的“形神俱妙”之“化体”是一种形、气、神高度合一的特殊的生命存在形态,合于形则显,合于气则隐,合于神则妙。中国武术既究形体规范,又求精神传意,内外合一的整体观是中华武术的一大特色。杨炳传授的梅花拳讲究“内外兼练,行神兼备”,要求做到外要练形,内要练气,以达到形气合一、内外一体,把内在精气神与外部形体动作紧密结合,直练到“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心动形随”“形断意连”“势断气连”。充分反映了中华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与道教文化的依附关系。
其三,清静无为,以静制动。“清静无为”是道家最为重要的思想。今人多错误的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对万物发展不加干预,任其发展。其实,道家的“无为”,并非不作为,只是凡事要“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按现在通常的说法,无为就是科学的作为,就是合理的作为,因而也是积极的作为。杨炳在技击中的“静待”术就体现了道家的“无为”思想。杨炳认为在技击中,“夫克者无他术,唯以静待动也,以逸待劳也,以客待主也”,要“临大敌不动如山岳”,“静如处女”“事来随应”“以静制动”。武术技击的过程,是一个顺势而为、因敌而制胜的过程,绝不是单靠个人的设想与造作所能应付得了的。要取得技击的胜利,必须掌握技击的主动权,这就需要具有能够随机应变的、无限妙用的智慧,而不是有限的僵化的招法手段。 “以静制动”,即是“以无为制有为,以无法胜有法”;“后发先至”,即是无任何预设的自然动作必然会随机应变,先敌而发出,从而做到因敌而制胜。也就是杨炳所说的“事来随应,不先事而为之备,不后事而为之留,深合时措之宜,切契内外之道,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
三、佛学文化的影响
武术自清代以来就有把佛家修行心性的禅定作为自己修炼内功方法的传统。杨炳在《习武序》中提出的“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将万物之理具于一心”的终极修炼,实质上就是吸收了佛家理论的成果,体现了拳释结合的迹象。但是杨炳武学思想与佛学关系最明显之处还在于习武为“治世”,为“度己、度人”。
杨炳的这一思想源于他所习梅花拳的“根源教义”。翻开梅花拳的《根源经》,开头赫然写道:“佛祖西域坐法台,治世干枝梅花开”,接着是“苦念归家一个字,东留梅花能度开”,“老祖栽棵梅花树,梅花普度万道开。合天诸佛浇梅花,千佛万祖浇树来。开道法名为梅花,梅花能把人度开”,“面前有棵梅花树,干枝梅花神威开”(梅花拳《小根源经开篇》)。梅花拳中的“梅花”一词不再是单纯的风骨赞美,而被赋予了神圣的开道度人的宗教情感,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容的宗教文化符号。因为“尘世间三千软红攘乱纷纷”,是一个极易迷乱人本性的社会,“酒色才气迷人性,迷住不能回天台”(梅花拳《小根源经开篇》),所以佛祖慈悲,屡派使者下凡超度原人“归家”。然而,芸芸众生能否“归家”,就在于个人的修行得道。入了梅花门就可以“得了此道能成真”,把人度回“天台”,显然是将“梅花”一词作为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佛性”象征。*详参周伟良:《梅花拳拳理功法的历史寻绎》,《体育文化导刊》,2002年,第5期。于是乎,在清代社会动荡、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乡土社会中,梅花拳的种种传文习武活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一种传统乡土社会特有的宗教情感支持。无怪乎有人将传播梅花拳称作“传道”“开梅花大道”。这种带有强烈宗教情感的“梅花”意蕴,在被称为“教门渊薮之地”的广大华北乡村中间,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在明清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梅花拳将不再仅仅以强身自卫为目的,而是以“救世度人”为开道宗旨,扩大拳派的影响,并广泛传授弟子,使梅花拳之名远播各地民间。杨炳习武与治世统一的武学理论显然与梅花拳的习武宗旨联系在一起,就是习武不仅为“保身保家”“ 卫君卫国”,而且要学菩萨那样“度人”,将万民“度化”到“人寿之域”。
四、易学法则的灵感思维
中国武术与易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周易》诞生了最早的武术观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要求人们效法天体运行那样,有一个“刚强”“康健”的体魄。《萃卦》中“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之句,更是明确地教导人们整治兵器以防不测。于是历代武学家以阴阳、五行、八卦、太极等原理阐述人性与功夫修炼的关系,创造了中华武术的技艺。然后根据《易经》象数的阴阳变化论指导武功修炼。
杨炳在《习武序》中从尚武精神到拳理功法的阐释处处闪烁着易学智慧的光芒,尤其在应用易学阴阳变化原理武装习武者头脑,开发灵感思维,洞察武术的奥妙,深窥武术客观规律,掌握习武之魂,从而登堂入室进入自由王国方面特别突出。易学不仅包括天道、地道,还包括人道,其天人合一整体思维模式在习武上的最终归宿是人,是对人道的认识,包括对人体科学、人体自然规律的认知。以易学的天人观为理论指导的武术训练,不仅仅要锻炼拳脚四肢,更要修“心”,要锻炼人的灵感思维,开发人脑智慧,在潜意识状态下由感知激发灵感,从而产生神速而有奇效的武术动作,步入神化的境界。
在《习武序》中,杨炳有一段精辟的话语:“道为太极,心为太极,万物之理具于一心,随感而应,皆合其宜,如四时行百物生,故曰圣人一太极。”他在这里说的“道”,即宇宙万物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太极”,所以“太极”学说是宇宙的一个根本的规律。他在这里说的“心”,就是指人的心、人的大脑,或者说人的思维。习武之人若能诚心修炼、深入研习,“将万物之理具于一心”,掌握了武术的客观规律,那么他的心也就成为一个“太极”,他的心就会像“明镜止水”一样“无彻不照”,没有什么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到了这时,习武者便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这时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就如同万物随着季节的运行萌发、生长一样,深合时宜,恰到好处。在与“敌”搏击中,或进攻或拦挡,或前进或后退,举手投足、一招一式,都能随机应变,既不用事前进行准备,也不用在事过之后还当之留意,而且所做的一切不但合乎哲理,而且又遵循客观规律。
五、程朱理学的推演与阐发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它集儒家思想之大成,又有选择性地吸收扬弃道家、玄学、道教,以及佛学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杨炳武学思想对程朱理学的推演与阐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杨炳把习武的说教归结为“总不外乎主敬之心、格物之学”;二是杨炳认为习武者要想使自己的心像圣人一样如“如明镜止水”就要做到“诚、神、几”。
主敬思想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求人们的内心总处于一种敬畏状态,一种警觉、警省的清醒冷静的状态,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如此方能达到去人欲、存天理、“天人合一”之道德最高境界。“主敬”是人们修养自身的前提,是涵养心性、洞察天理的必要条件。
“格物致知”这一词语源于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是儒学派为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而提出的阶段性行为目标。“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朱熹《大学章句 补传》)。“即物穷理”,是要求人们运用已知的知识,深思客观事物,达到自己内心的豁然领悟。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内省式的思考过程,通过“即物”,达到自己内心的豁然贯通。
杨炳将理学“主敬之心,格物之学”学说应用在习武上,就是教导习武者明白,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要想学到武艺,就必须加强学习和道德修养,静下心来认真地考究武术的性理,找到其规律、探源达头,勤学苦练,以掌握武术真谛并日臻完善。
“诚神几”之说出自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所著《通书》:“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道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感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杨炳将理学的这一理论在《习武序》中作了进一步地推演、发挥。他认为:一个人寂然不动、无思无为时心即诚;用灵感思维便能神妙地感知武术变化的规律,在“动而未动、有而似无”的时空中研判搏击的微妙,便能寻找到制胜的机会。
清末民初一位人士在阅读《习武序》时在此处作一眉批:“习武之道,说到主敬格物,为将为相之学,固不外此。推而极之,即为帝为王之道”(见《习武序》赘后感言“眉页阅注”)。可见杨炳的这一武学思想的确是前无古人的。
六、古代兵法的吸纳和渗透
从先秦到清代,我国的战争相当频繁。古代战争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家,于是,也就产生了大量的军事著述与兵家理论。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古兵书著录有53家790篇,可是到了清末,古代有关兵家著述目录已多达1304部,现存288部。而且古代兵法的流派众多,内容非常丰富。由于武术与军事在历史上的不解之缘,兵法既指挥了战争,也成为武术理论思想的重要内容。
兵法是古代用兵作战的战略和战术,我国的古代兵法学不仅制约和影响军队武术的发展,而且也深刻指导、影响着整个传统武术的发展。战争攻防涵义表现为消灭敌人,保卫自己;武术的攻防涵义表现为击败对手,自卫防身。中华先民格斗、作战,最初是徒手,后用石块、木棍、弓箭、刀枪等器械,其中徒手格斗技术及器械技击技术演变为中华武术。战时武术高手大都参军入伍,在实战中熟悉、发展了兵法,有的成为将领,甚至统帅。中国兵法与中国传统武术同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得天独厚,枝繁叶茂,可见兵武一家,一脉相承。武林中有谚云:“拳兵同源”,“自古拳势通兵法,不识兵书莫练拳”。形象地揭示出我国传统武术与古代兵法之间的紧密联系。传统武术技击汲取了古代哲学、兵法、中医等理论成果从而形成了被称誉为“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代兵法学最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有春秋末期孙武著的《孙子兵法》、战国中期孙膑著的《孙膑兵法》、三国时期诸葛亮著的《心书》和明代军事家俞大猷的《剑经》、著名的抗倭英雄戚继光著的《纪效新书》等。尤其《孙子兵法》与中华武术相通之处更多。杨炳在《习武序》中随处都有对上述军事理论的引用,尤其是对《孙子兵法》的吸纳、应用,继承和发展更加明显。例如兵法上的“守柔处雄”“刚柔相济”“以柔克刚”“示虚还实”“避实击虚”“奇正相生”“敢于用奇”等兵法思想都衍化为武术中的搏击技巧。我国古代兵法是杨炳武学思想重要理论支柱之一。
杨炳武学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肥田沃土,犹如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其根须触伸到四面八方,吸收了各方面的养分。因此说杨炳的武学思想是多元的,既吸收儒(包括理学)、道、释三家思想之精华,又融入了易学神奇法则的思维;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诸家兵法,又涵涉了传统医学、传统美学等。所以,其理论框架体系交叉互取,相映成辉,内涵丰富,博大精深。
[责任编辑:郭昱]
[收稿日期]2016-01-01
[作者简介]杨彦明,男,河南省内黄县人,主要从事杨炳及梅花拳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30(2016)01-00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