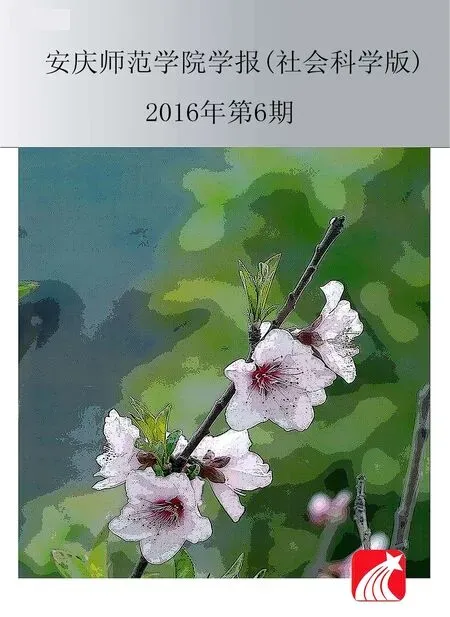略论北洋军队的用人机制
2016-03-18张彧
张彧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略论北洋军队的用人机制
张彧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北洋时期,旧军队的用人机制多与地缘、学缘、亲缘、业缘等因素有关。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军队的内聚力,但与军队在国家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不相适应。
北洋时期;军队;用人机制
晚清以降,面临严重外患内忧的清廷被迫实施了以军事近代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措施,地位得以逐步提升的军人逐渐从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心。以民国成立为基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军人扮演着极为突出的角色,各军事派系首领在政治上独断专横,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在军队管理控制上也非常混乱,在用人机制方面尤其突出,尽管有诸多规章制度,但多为一纸具文。军官的升迁往往取决于地缘、学缘、亲缘、业缘等因素。总体而言,旧军队的用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不同军事派系的内聚力,但与军队在国家治理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适应的。不同军事派系的偏狭性使得派系间的争斗、更替杂沓纷呈,无助于形成团结安定的局面,也难以组成强大有效的力量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
一
北洋时期旧军队往往以一定地域为标准选拔军官、招募士兵。
袁世凯为河南项城人,其提拔的将领主要是直、鲁、豫、安徽中北部、苏北等地域,这些地域的语言、风俗习惯等差别较小,具有较强的认同感。袁世凯一手提拔的段祺瑞为安徽合肥人,段虽不排斥北方人,但对籍贯安徽的却略有偏爱。如他之所以选择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因张是安徽人,且头脑简单,可以招之即来,绝对听话。袁世凯的另一大将冯国璋身边的武将也多是北方籍。直系大将吴佩孚比较信任直鲁豫三省的人,对山东同乡尤其青睐。在第一次直皖战争后,直军又夺取陕西,以资历、战功论都应由直系大将王承斌担任陕西督军,但直军师长阎相文极力钻营,吴与阎相文相处多年,又同为山东同乡,最终阎相文如愿以偿。
在北洋军阀统治一些南方省份时,往往从北方招募士兵。如李厚基统治福建时,所编练的福建陆军第三师士兵主要来自苏北及黄河下游所谓大同乡的河北、河南、山东。王永泉在统治福建时,士兵都是在直隶家乡招募的。王占元在盘踞湖北期间,除嫡系第二师外,又新编了一些部队,士兵都系直鲁豫人,间有少数皖北人,下级军官多系王占元的护兵、马弁,中级以上军官都由王占元的第二师调来。西北军的士兵和官佐,大多数是直、鲁、豫人,其他省份的人在西北军当将领的很少。西北军也主要是从直鲁豫三省及皖北等地招兵,具体做法是派军官回原籍招亲募友,“好处是招的兵知根知底,没有营混子,其次大家非亲即友,向心力比较坚固”[1]。张宗昌在吉林任绥宁镇守使时,所招的兵均是山东同乡。陈树藩任陕西督军时,重用陕南同乡、外省同学,号称“二同主义”[2]。晋军将领商震为河北人,尽管在山西多年,但并不信任山西人,在商的司令部,几乎全是河北人,在中原大战后商脱离晋军系统投靠南京政府。商震原来籍贯河北保定,为靠拢蒋介石,又将籍贯改为浙江绍兴。
北方军队重视地域,南方军队也不例外。曾任广东督军的龙济光乡土观念极深,在其济军中从不招募外乡人,结果他所率领的济军士兵愈打愈少,而军官愈打愈多,形成头大脚小的局面。在黔军中,地域因素表现得非常突出,黔军中的两大派系兴义系与桐梓系之得名均与地域有关。贵州督军刘显世既是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舅父和叔岳父,又同为兴义人,兴义系因此得名。在兴义系军阀衰落后,籍贯桐梓县的贵州军人掌握了贵州军政大权,黔军进入桐梓系时代。桐梓系首领周西成的乡土意识达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周所任用的文武官员,均由桐梓人担任。他把桐梓县能识字的都拉出来做官,以致桐梓乡间找个写信的都困难[3]。在周死后多年,外省人薛绍铭在贵州旅行时发现,桐梓是出官的地方。黔军大小军官百分之九十为桐梓人,文官则占半数[4]。
在旧军队或者军校中,地域有时被作为一种旗号。1910年四川新军扩编为第十七镇时,外省人朱庆澜为统制,朱提拔的中高级军官多是随同自己入川的外省人,四川籍则很少。因感觉升迁无望,众多本省下级军官及四川军校学生对朱的做法非常不满。而士兵因听不懂外省军官的讲话,加之一些军官的性情粗暴,造成士兵对外省军官也较为反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川人尹昌衡遂以狭隘的地方观念,大肆鼓吹排外。他认为四川人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排斥外省人,川籍军人才有出头之日。尹在许多场合肆意抹黑外省籍军官,有意让他们难堪,尹的做法使他在四川军人中获得了较高的声望。辛亥革命前后,外省军人朱庆澜、姜登选、程潜等受以尹昌衡为代表的川籍军人排挤,被迫离川,尹昌衡夺取了四川军政大权[5]。
不同地域的人所组成的军队,往往分歧较大,整合困难,难以形成较强的战斗力。1917年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在襄阳宣布独立,参加护法战争,黎任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第九师十七旅张联陞为山东人,所部官兵一半是山东人,张不肯附和黎天才,大大削弱了第九师的实力。[6]
不同军事派系处于敌对状态时,地域因素时隐时现,对双方的较量产生一定影响。1918年皖系首领段祺瑞设立长江上游总司令部,以妻弟吴光新为总司令,意在监视直系的鄂督王占元。吴光新总部设于荆州城内,他以所辖官兵绝大多数是直鲁豫籍,与直系部队多有同学、同乡或亲友关系,不尽可靠,因而呈准段祺瑞编练嫡系部队,在合肥一带招募新兵万余人[7]。北洋第十五师士兵多为直系首领冯国璋的同乡,军官与冯非亲即故。直皖战争时,第十五师师长刘询站在皖系一边。但该师广大官兵却不愿同曹锟直军作战,对刘询的自告奋勇,也认为是无耻的举动,在双方交战的关键时刻第十五师倒向直军。直军大将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为奉天人,在直奉交恶时处境微妙。1922年直奉大战在即,为激励王积极作战,直系首领曹锟对王许愿,打完仗直隶督军给他当。王承斌出任中路军司令,很卖力气,最终打败奉军,王也当上了直隶督军,仍兼任师长。但曹锟、吴佩孚对王在第二十三师重用奉天籍军官颇不放心,免去王的师长兼职,以旅长王维城接任。王承斌去职后,该师奉天籍的军官三十多人一齐辞职,王承斌又为他们安排了新的职务[8]。王在直系内的被排挤导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王积极参与了冯玉祥、孙岳等发动的倒直政变。
外省军人的统治往往带有武装殖民的味道,很难得到所在省域民众的支持。北洋军将领卢永祥、孙传芳在统治浙江时,浙江人有“亡省之痛”,浙军官兵对他们所依附的北洋军有着很强的离心力,在卢永祥、孙传芳遭遇强敌时,倒戈一击,加速了北洋军在浙江的崩溃。桂军在广东作战时,经常抢夺百姓财物,如衣服布匹、猪牛鸡犬等。理由是师出无名,为鼓舞士气,准许士兵发洋财。1920年粤军离开广西时,把掳得的妇女装在麻袋里,当做货物一样在梧州拍卖,按重量计价。左右江的百姓经常袭击小股的粤军,杀死后在死者头上插着写有“陈总司令炯明收”的字牌抛尸水中[9]。
二
在旧军队中,同学关系非常重要,往往相互援引、彼此借重。除同学关系外,师生关系也非常重要。师生关系在旧时代犹如父子关系,军事派系首领兴办军事学堂,既可以培养军事人才,又可以借此赢得学生的效忠,可谓一举两得。学生通过向老师效忠,获得庇护,也并不吃亏。晚清时期袁世凯在编练北洋军的过程中,设立了一系列军事学堂,主持其事的段祺瑞因拥有众多门徒,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袁世凯感受到了威胁,在筹备帝制时试图通过创办模范团以抵消段的势力,但为时已晚。北洋时期的军事派系首领为控制军队,扩充实力,纷纷兴办军事学堂,或设立学兵营。程潜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以上军官多为保定军校与士官学校出身,营以下军官绝大多数为广州大本营讲武学校各期学生,中下级军官与程潜有着师生及部属的双重关系。1927年蒋介石趁程潜赴武汉时将第六军缴械遣散。第六军大部分官兵逃回武汉追随程潜,程潜在很短的时间即重建了第六军。四川军阀罗泽洲性情粗暴蛮横,但在20世纪20年代,部队规模却在不断扩大,其重要原因是罗的军官队伍比较稳固。罗的中高级军官多是他的军官学校同学,其次是同乡、亲戚,下级军官绝大多数是罗自办的军校培养的学生。
因毕业学校不同,常常会形成所谓学系,也就是不同的山头,有的是在同一军事派系,有的则是在同一地域不同的军事派系。如川军将领按就读学校不同,分为速成系、武备系、保定系、军官系。其中速成系和武备系的势力较为雄厚,代表人物是刘湘、刘文辉。黔军内则分为士官派与保定系,代表人物分别为何应钦、王天培。浙军分为士官系、速成系、保定系、南京陆师系,士官系与南京陆师系人数较少,势力很快衰微。武备系人多势众,在浙军中举足轻重,保定系的势力稍弱于武备系。奉军分为土派和洋派,土派就读于国内军事学校,首领为郭松龄。洋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代表人物为杨宇霆。土派又有陆大系、保定系、东北讲武堂系的区分。
同学间固然可以相互借重、相互扶助,但不同学系的存在常会产生很多矛盾和冲突。在奉军内部,土派与洋派倾轧不断,郭松龄倒戈反奉、杨宇霆被枪杀均与此有关。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土派代表郭松龄与洋派韩麟春、姜登选因作战指挥产生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蔓延到级别更低的军官中。属于洋派的炮兵团长陈琛将接近郭的两位炮兵营长阎宗周、关全斌撤职。阎宗周、关全斌哭诉于郭松龄,郭一怒之下,把陈琛撤职,并令两位营长复职。双方的官司最终打到奉军统帅张作霖那里,张以大战正酣,不愿矛盾激化,命令三位炮兵指挥官一起复职。在战后瓜分地盘的过程中,洋派阵营的杨宇霆、姜登选均有所获,分别获得江苏、安徽地盘,郭松龄因一无所获,愤而倒戈反奉。郭兵败身死后,土派与洋派的争斗暂告中止。1927年奉军入河南作战,但接连失利被迫退回河北。因张学良认为韩麟春在河南指挥失误导致奉军失利,为使韩麟春难堪,张学良以作战不利为由把旅长陈琛枪毙。在土派内部也存在着派系倾轧。郭松龄先后就读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及陆军大学,他提拔的高级将领多是这两所学校的同学。中下级军官则多是保定军校及东北讲武堂出身,对郭重用自己同学的做法甚为不满。在郭倒戈反奉期间,保定军校毕业的富双英因未当上旅长非常不满,在连山战役时叛郭投向奉军。团长王迺义自恃陆大毕业,为郭的嫡系,非常骄横,因没当上旅长,对当上旅长的栾云奎(士官学校毕业)非常愤恨,有意拆栾的台,不听栾的调遣,严重贻误军机,军长霁云怕得罪陆大系,不敢处置王迺义[10]。
不仅不同学系的军人龃龉不断,行伍出身者与军校学生也相互排斥。北洋系统的高级军官多肄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中下级军官多肄业于北洋速成学堂。这两所学堂的在读时间都不长,二至三年左右,对入学者的文化要求较低,培养的质量也不高,因此北洋军系统的各级军官常给人以大兵老粗的印象。因文化水平及思想认识的差异,北洋军将领对保定军校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常多排斥。北洋时期任京畿卫戍司令有年的王怀庆对军校学生、洋学生(一般指士官学校出身)非常排斥。尤其是洋学生,他认为带有革命思想,靠不住。他宁可培养老粗和贴身副官。奉系军阀分新、老两派,老派以张作霖、吴俊升、汤玉麟为代表。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老派对军校出身颇多疑虑,认为军校出身的人,才智虽好,但是思想复杂,不能指挥如意,只能做参谋和教官,不能带兵,所谓“柳木判官,不能使唤檀香木的小鬼”[11]。奉系旁支、自诩绿林大学毕业的张宗昌对行伍出身者颇为欣赏,他认为行伍出身的将领头脑简单、人际关系单纯,是一群无知的浑小子,这些人不会离开他,永远跟着他走。军校出身的就不一样了。他们有文化、有本领,谁都需要,而且这些人同学多,认识人多,有的就在革命军队里干,只要同学一拉,就会投向革命军的怀抱,由此张宗昌得出一个结论,知识分子出身的带兵官十之八九不可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张的大部分将领为行伍出身[12]。
北洋时期冯玉祥是少有的行伍出身的军事派系首领。他对经历与自己相仿的军人也非常欣赏,“粗人自知才力不足,处处谨慎,事事小心,比较可靠”;至于军校出身者,冯认为他们靠不住,“这些人都是满天飞的,哪里有肉就飞到哪里去”,再就是他们吃不了苦,不能与他的兵同甘共苦[13]。在冯队伍里,行伍出身的将领占多数,军校出身者一般只能做参谋或教员,带兵的机会很少。
在南方军队中,排斥军校学生者主要是旧桂系。旧桂系首领陆荣廷、谭浩明、陈炳锟等多出身绿林,后接受清廷招安作了巡防营统领,在辛亥革命中夺得广西大权。陆荣廷等在用人时,首先是问曾否当过游勇,第二看曾否当过巡防营军官。他们对于军校学生是很歧视的,就是旧桂系自己办的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学生也是如此。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奉军、西北军逐渐改变了一味排斥军校出身的做法。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的失利使奉系首领张作霖看到绿林出身的奉军将领不堪大用,大大改变了对军校学生的态度,不但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尽量引用,国内陆军大学和保定军校出身的也大量录用。随着军校学生在奉军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形成了与老派不同的新派。在张作霖的嫡系奉军,新派有逐渐取代老派之势。冯玉祥在军队规模与控制地盘不断扩大后,深切感受到行伍出身将领的局限性,冯玉祥尝试着以军校学生出任高级将领,以逐渐提升指挥水平。但冯的努力没有达到奉军那样的效果。在行伍出身将领的抵制下,军校出身者的地位、影响力始终不能同行伍出身将领相比。
北洋时期在旧军队亲缘和业缘也是重要的因素。段祺瑞着意提拔其妻舅吴光新,但由于吴性情粗暴,驭下无方,未能获得大的成功。曹锳在其兄长曹锟的提拔下升任第二十六师师长,但曹锳的才能实在有限,使用的军官多是些市井无赖,二十六师也被称之为“茶壶队”。奉系军阀张作相任吉林督军时,身边任职的多是亲朋故旧。在内侄冯占海升任卫队团团长后,为安抚亲外甥王永恩,张把王永恩的骑兵营扩编为骑兵团,王也升任团长[14]。1926年奉系军阀汤玉麟任热河都统,汤的长子汤佐荣由中校团附升为都署上校参谋,不久又出任热河禁烟总局总办。次子汤佐辅则担任被服厂厂长。汤玉麟的三个弟弟均在他的手下任团长,长女婿任师参谋处书记官。贵州军阀周西成重用岳父侯家的人,当时有“周家天下侯家将”的说法。
在旧军队中业缘也非常被看重。在这方面,直系首领曹锟堪称代表。曹锟以恢宏大度著称,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就是冯玉祥这样的难以驾驭的军人也能和曹锟相处得比较融洽。曹锟对他任第三镇时的部属非常看重,常常不次拔擢他们。孙岳在清末时曾在第三镇任职,辛亥革命时到南方参加反清活动,几经沉浮。在曹锟任直隶督军时孙岳到保定见曹,说“没办法,没饭吃,才来找三爷”。曹锟以孙岳是三镇旧人,对他非常信任,把孙提升为旅长、镇守使。曹锟就任总统后,对讨论政治感到厌烦,避免多见客。一般的政要受曹锟佞幸李彦青的刁难,没有令他满意的红包,很难见到曹锟,只有第三镇的旧人例外。曹锟对李彦青说过“三镇的人是我起家的老本,你们给我得罪了一个,我就毙了你们”[15]。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将领在选拔军官时,喜欢从身边挑选,护兵、马弁、司书等提升的可能性更大。
三
北洋时期,旧军队选拔将领的标准之一就是忠顺、绝对服从命令。以袁世凯为例,其选人的标准是:“奉命唯谨、效顺矢忠”。何宗莲相貌厚重、言语质朴,为袁世凯所赏识,成为袁的亲信;赵倜体态雄壮、相貌端厚,被袁任命为河南督军。王怀庆原为淮军将领聂士成的部属。1900年聂士成阵亡于天津,王怀庆冒死背负聂士成的尸体到安全的地方,后又将其灵柩运回安徽原籍,王的忠义之名轰动一时。袁世凯对王怀庆的做法非常欣赏,破格提拔王怀庆为标统(团长)。袁世凯在用人标准为其大将段祺瑞所承袭,段的最忠实的追随者卢永祥,性情耿直、忠厚念旧,对上级绝对服从。直系选拔将领也是这个标准,“用人以顺不以才”,如萧耀南,“沉默寡言,服从恭顺,熟悉公文,一望而知是一副忠实可靠的驯服样子,得到上级信任,与同事相处的也好”。
旧军队的一些将领在提拔下属时,尤其是行伍出身的下属时,喜欢以辱骂、打军棍、打耳光的方式进行测试,若对方在测试过程中毫无怨怼,往往能获得提升。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喜欢提拔老粗和身边的副官,在提拔前要责骂或者处罚,视其能否贴然接受、有无怨言,然后决定升迁。山东督军张怀芝以粗野著称,偏好打耳光。他的同僚何宗莲曾把一王姓旧部,推荐与张怀芝,王以遇事谨慎为张喜欢。提拔前张借故申斥并打了王某耳光,三个月后王被任命为炮兵营长。张还打趣地说“你若不愿干,想干的可多了。”[16]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对部属的羞辱方式更多,罚立正、跑步,有的时候罚跪,自己掌嘴,甚至打军棍。被羞辱者若脸不变色,不发牢骚,就意味着通过了考验。
忠实于自己的上级、尤其是忠实于与自己有恩、提拔过自己的上级是一种被欣赏的品德。刘玉春原为第八师师长王汝勤的部属,驻防宜昌时,刘以旅长身份兼任鄂西陆军联合总督察处处长,负责征收、分配鸦片烟税。因刘分配烟税时较为公平,没有特别倾向于第八师,引起王汝勤的不满,于1924年将刘玉春免职。但吴佩孚对刘的善战颇为欣赏,派心腹河南省长李倬章邀刘到洛阳。吴佩孚见到刘玉春后,“慰劳备至,即日聘为高等军事顾问”,刘玉春因此对吴佩孚感激涕零,“原为之死”,自此成为吴的铁杆战将。1926年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逃至河南。吴与其大将靳云鹗矛盾重重,难以协调,靳很苦恼。靳云鹗的爱将高汝桐认为,如要有所作为,必须将吴解决。靳不同意,说“如果按照高的办法去做,在社会上看来,我靳云鹗还成个什么东西”[17]。同年吴佩孚检阅暂编第十六师时,以其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取消暂编二字,颇加奖谕。第十六师师长徐寿椿徐对吴深感知遇。1927年吴佩孚逃往四川途中,获徐殷殷招待和资助,徐还以恩上呼之[18]。若背叛自己的老长官,将会遭到普遍的批评、甚至是被孤立,处境将非常艰难。北洋时期因背叛上级而享有恶名的要数冯玉祥和沈鸿英。1924年直军与奉军大战正酣之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系政权崩溃。兵学大家蒋百里对冯倒戈的做法非常鄙视,认为别人可反曹吴,以冯和他们的深厚关系决不应该如此,为国家的纲纪着想,决不能容许以下犯上的事情发生。桂系军阀沈鸿英因背叛陆荣廷、孙中山,被视为反复无常之人,和他在一起将会玷污清白。
冯玉祥尽管有倒戈将军的名声,但在获得部属效忠方面,还是成功的。冯的大将张维玺1925年率部坐火车赴绥远途中,一新兵在火车过隧道时受惊扰摔下火车死亡。冯极为生气,张维玺被叫到张家口,被冯亲手打了几记耳光和一顿军棍。但张对冯依然非常忠诚,1929年张维玺奉命进驻汉中,蒋介石为分化西北军,派人到汉中拉拢张维玺,为张拒绝。冯闻知后,派军法处长徐惟烈到汉中进行慰问。张召集全军营以上军官当着徐的面宣誓,矢志不二地永远效忠于冯总司令。中原大战后期,冯致电给张维玺,暗示他可以突围或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以保存实力。张复电说,愿效忠到底,决不觍颜事仇[19]。还有因为长官遭遇羞辱,下属感到自己失职而自杀谢罪的事例。陕西督军陆建章被驱逐出陕西时,被陕军洗劫,妻妾女儿都受了羞辱。陆的部下包括远在四川的第十六混成旅对陕军首领陈树藩切齿痛恨。一位孙姓营长自觉未能善尽职守,致使官长受辱,愤而自杀。本来看不起他的同僚,在他死后都钦敬他有血性。
即便长官对自己不好,但在长官落难后,不投井下石被视为一种美德。时鼎岑任河南督军赵倜参谋长多年,声望很高,引起赵的嫉妒而被免职。后来赵倜因为反对直系而失去河南督军位置,直系首领曹锟起用时鼎岑,并要时负责调查赵倜的家产,时婉言谢绝。
在战场上战败投降或于形势不利时投向敌方都会被视为道德有亏,不仅难获己方谅解,也难获对方信任。1926年冯玉祥部与晋军交战于雁门关一带、冯军旅长张自忠因与前线指挥官韩复榘不睦,恐被韩所害,投向晋军。战后晋军在扩军时,对作战有功的军官不次拔擢,对作战意志不坚决的将领张剑南、黄金桂、李服膺等严加查办。尽管有人在晋军首领阎锡山面前说张自忠骁勇善战、善于治兵,但因张在战场动摇的情况还是令阎难以对张自忠产生信任。
奉系旁支张宗昌在东北时,队伍主要以山东人为主。在成为山东督军后,随着战事的日渐激烈,张宗昌大肆扩军。此时的他已与一般军阀不同。一般军阀多持门户、畛域之见,只承认一己嫡系势力,对于旁系、杂牌队伍,不是排斥便是剪除。张宗昌恰恰相反,广揽人才,不分派系,不分地域,来者不拒。但张的兼收并蓄并未能使他统率的军队有很强的战斗力。正如冯玉祥所言:“(张宗昌部)乌合之众居多,四处招集土匪队伍,欲借以抵抗我军。其指挥作战,皆互相欺哄,讳败为胜。”[20]张的部队在规模扩大后因来源的复杂而松散,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
民国兵学大家蒋百里先生认为,军队纪律之进化,可分三大段。第一阶段,纪律是靠法—也可以说是用刑—来维持的。第二阶段,军纪是依情感来维系的,这比较用刑法来维持的算是进了一步,用情感来维系军纪,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种是官长待士兵很好,上下感情融洽,士兵由于情的感动听受官长的指挥。另一种则因后来兵额扩充,兵与兵之间发生感情,或由于同乡同省的关系发生感情,来维系军纪。第三阶段,现代由于兵学革命,纪律也跟着进化到了自由—也可以说是自动—的时代[21]。北洋时期的旧军队,基本处于蒋百里先生所说的第二阶段,以情感来维系军队。当时的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对人、对地域的认同更甚于国家。因此,重视地域、学缘、亲缘、业缘也就很正常了。当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后果,其一便是军事派系层出不穷、战乱频仍,一如蒋百里先生所云:“而官长之党派乃日出而不穷,乃至同一军也而有地域之不同,同一地也而有学派之不同,同一学也而有先后之不同。以彼小强国所浸润而得之攻击精神,乃益益用之于小范围内之纵横捭阖,无暇及于外矣,此兵祸所以继续连年而不能自己也”。这些层出不穷的派系也因其偏狭而被淘汰。有一篇叙述四川军阀杨森部队的文章,对旧军队人事的概括颇为精准:“哪一个当官的没有几个以上的关系,你如果一点关系都没有,早就不能在这里立足了”;“思想狭隘、眼光短小,私心太重,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这就决定了它发展前途的局限性”[22]。
[1]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M].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28.
[2]韩维墉.陈树藩事略[G]//陕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128.
[3]陈弦秋.辛亥以后二十五年间贵州军政概述[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161.
[4]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119.
[5]陈祖武.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尹昌衡[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63.
[6]辜天保.湘鄂祸乱记[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83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23.
[7]费泽普.吴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败[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5:73.
[8]王维城.直系的分裂和二次直奉战直系的失败[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37.
[9]广西区政协座谈记录:旧桂系崩溃时期广西的一般情况[G]//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续编(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6.
[10]姚东藩.郭松龄反奉见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8:55.
[11]刘德权.第一次直奉战争见闻[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篇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165.
[12]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208.
[13]高兴亚.忆与冯玉祥的谈话[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篇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14]王希亮.抗日将领冯占海[G]//吉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吉林文史资料:第25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6.
[15]章青.曹锟的一生[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篇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48.
[16]赵荣孝.北洋军阀时期的何宗莲、何丰林、何锋钰[G]//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84.
[17]周从吾.靳云鹗侧记[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篇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69.
[18]王镜璿.小军阀徐寿椿兴亡概述[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篇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980.
[19]张宣武.西北军宿将张维玺事略[G]//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124.
[20]《冯玉祥选集》编委员会.冯玉祥选集(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16.
[21]皮明勇.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蒋百里杨杰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14.
[22]胡忆初.杨森部队特点[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篇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666.
责任编校:徐希军
K258.2
A
:1003-4730(2016)06-0036-06
时间:2017-1-20 15:3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70120.1533.008.html
2016-07-13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洋时期旧军队用人机制研究”(JAS14059)。
张彧,男,蒙古族,内蒙古阿拉善人,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6.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