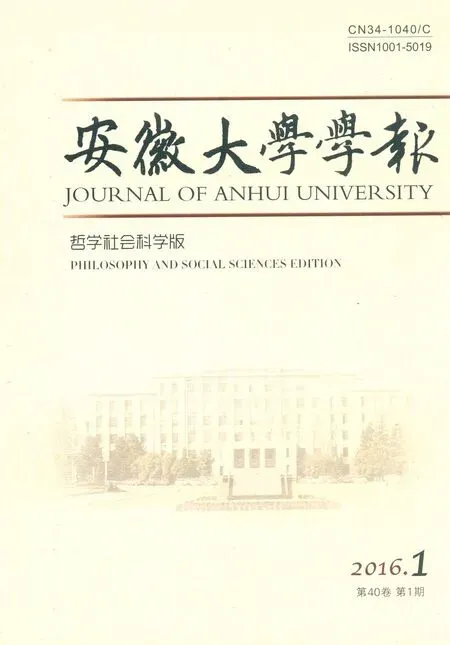马克思“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思想新解
2016-03-17王荣江
王荣江
马克思“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思想新解
王荣江
摘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试图摆脱传统、抽象、思辨的哲学研究方式,从人的现实、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以“直接的、非哲学的科学”的研究方式来表述和研究问题,实现了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转变。他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作为理论的基本前提,展开并阐述一种解决历史之谜、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一门科学”的思想便是这一理论在科学观上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从其理论前提出发必然得出的结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
关键词:《手稿》;“非哲学的科学”;感性实践;对象性;一门科学
过去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哲学的层面展开,即使是研究其中的“人的科学”,也即所谓的“人学”,或是经济学等,也没有摆脱哲学的路径。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这时的马克思更多地并且有意识地在不同于传统哲学与科学的角度和层面上研究问题。按马克思自己的说法,他要做的研究是直接的、非哲学的科学(相对于黑格尔)和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相对于费尔巴哈)研究。事实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明确地与传统哲学的研究方式划清界限,展开真正的、实在的科学研究。搞清这一点,将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手稿》,特别是理解其中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的思想。马克思有意识地给自己提出一个困难且艰巨的任务,即创立一门不同于传统的哲学人本学的新科学——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人的科学”。这一任务,在当时各门社会科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独立出来时,显得新颖而又艰难。而在这样一个问题和任务面前,阐述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一、从传统哲学研究向实在的科学研究的自觉转变及其理论基础
1.从传统抽象思辨的哲学研究向实在的科学研究的转变
马克思《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在批判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抽象思维时说:“从一方面来说,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本身,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因此,从一方面来说,黑格尔既同现实的本质相对立,也同直接的、非哲学的科学或这种本质的非哲学的概念相对立。因此,黑格尔是同它们的通用的概念相矛盾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下引该书仅随文夹注。对这段话,如果结合《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来看,我们会发现,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抽象哲学的批判,看到了抽象哲学的矛盾和问题(它“同现实的本质相对立”,也同“非哲学的科学”概念“相对立”),从而开始用“直接的、非哲学的科学”方式来研究和阐述问题。这一点对理解《手稿》和马克思这时的思想转变是极为重要的。这是马克思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式的重大转变,也说明这时的马克思明确地意识到他要与抽象、思辨的传统哲学分道扬镳*“直接的、非哲学的科学”的提法和认识,是马克思在《手稿》的“笔记本III”中明确提出的。这一提法和认识的开启,也许与《手稿》的“笔记本I、II”中对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科学研究有必然联系,即对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使马克思意识到实在的科学研究与抽象的哲学研究的根本不同。,因为他找到自己“直接的、非哲学的科学”的思考方式的出发点——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他在《手稿》中明确地说“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第89页)。我们看到,在《手稿》中,马克思着力阐述的就是人的感性、现实的实践活动,以及由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引发的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经济活动之间、人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结构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关于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将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也是在这一思路和框架下进行论述的。
马克思首先确立了“感性”在一切科学研究(非哲学的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凸显其科学研究与传统抽象哲学研究的根本不同。马克思在“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句话之后接着说:“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第89~90页)
马克思在阐述费尔巴哈的功绩时,也有同样的认识和阐述。费尔巴哈的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发的宗教……因此哲学同样应该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第96页)。上述第(1)点是马克思对抽象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谴责和排斥;第(2)点是说,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看作是“理论的基本原则”。
从上面《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肯定中,我们看到,这时马克思已明确地认识到他与传统哲学研究的不同,在肯定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的基础上,开始不同于传统哲学研究的真正的实在的科学研究。
在《手稿》之后,马克思将上述非哲学的、实在的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思想,不断地加以实施和强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将上述思想和思路进一步提炼并给予集中阐发,这标志着马克思已经摆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传统哲学,走上自己独立的、感性实践唯物主义的、实在的科学研究的道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直接阐述了他的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劳动实践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生产方式及其结构,来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总结上述认识,可以看到,在《手稿》中,马克思开始在抽象的理论研究即哲学研究与现实的、非哲学的理论研究即科学的研究之间做出区分,注重现实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的、经验的科学研究,而排斥抽象思辨的哲学研究。在他看来,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都必须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加以认识和把握;而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的彼此依赖和相互确认,使得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趋于一致和同一,使得它们“将成为一门科学”。
2.马克思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人的感性实践活动
马克思之所以能摆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传统哲学而走向具体的实在的科学研究,关键在于《手稿》中对感性实践活动的深刻认识以及它在马克思科学理论中本体论地位的确立。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并且是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他说:“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性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第85页)在这种对象性的关系中,“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本质力量的实现,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己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 (第86页)。于是,“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第88页)。
在这样的思路上,马克思认识到,理论对立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并且,“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第88页)。
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对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以及它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的强调,是对其科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确立,而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对象性的特点,又为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及其关系,以及它们在“人的自由解放”中的作用开辟了道路。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找到其科学理论研究的本体论前提和基础,并且,在这一本体论前提中,马克思也透露出其理论展开的基本线索: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彼此依赖,从而辩证地推进人和社会不断发展,推进人的科学的发展——人的解放。这就是马克思超越前人的关键之点。
马克思之所以能在其科学研究中赋予感性实践活动基础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的认识和把握。在紧接上面的引文之后,马克思说:“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和真正的科学。”(第88~89页)这里的“心理学”是费尔巴哈用语,是指认识论,“人的心理学”就是“人的认识论”,即对“人的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和强调感性实践活动(即工业)对于“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意义。
当然,在《手稿》时期,马克思处于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一切旧哲学并试图创立自己新的实在科学理论的阵痛时期。这时的马克思揭示了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及人的自我异化,并试图通过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来实现人性的复归即人的解放,也即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第81页)。显然,这时的马克思,是在扬弃人的异化的人本学的逻辑思路上,意向性地赋予了“共产主义”(不同于以前的各种共产主义学说)全新而全面的内容和结论——作为他解决历史之谜的终极结果和结论;并且他找到了实现这一运动的基础——私有财产运动即经济的运动,马克思说:“不难看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第82页)正如孙伯鍨所认为的,在《手稿》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的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后一种逻辑的基础上才能逐渐产生出来”*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不过,总体上看,不论是在《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没有真正摆脱哲学的研究方式。只有在《资本论》的研究中,马克思才成为一个现实的、具体的科学理论的研究者。当然,由于哲学和科学之间天然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具体的科学研究也离不开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也是如此*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马克思《资本论》理论(科学的理论)的基础。参见阿尔都塞《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关于“感性实践活动”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和方法论意义,学界论述得比较充分,在此不作赘述。本文强调的是:正是在感性实践活动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视域内,我们可以很好地认识和理解《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的思想。
二、《手稿》视域中的“人”和“自然界”及“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
在以往对马克思《手稿》中关于“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解中,似乎“自然科学”概念是自明的,不需要加以界定和说明,而“人的科学”概念却要进一步加以界定和说明。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没有对“人的科学”作具体的界定和说明,并且还给出许多不同的表述和说法。其实,在笔者看来,情况恰恰相反,在《手稿》中,“人的科学”的概念是相对清楚的,就是指研究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学科,虽然马克思对之有一些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意思和指向是明确的。恰恰是“自然科学”概念才是相对模糊的。
在《手稿》中,马克思先是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阐述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来界定人和自然界。这里的“人”和“自然界”就构成马克思“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过马克思把更多的笔墨花在前者上,而把后者看作是自然而然、不言自明和顺理成章的,没有也不需要加以说明和强调。而一般学者往往用自己头脑中固有的“自然科学”包括“人的科学”观念去理解马克思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概念,这就导致对《手稿》中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理解的困难。事实上,马克思是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关系中理解人和自然界及其相应的“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的。
1.自然界及“自然科学”
《手稿》中,马克思所界定的作为其“自然科学”对象的“自然界”,不是在人之外孤立存在的、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无关的、抽象的自然界及其全部,而是进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并被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介和作用过的自然界。
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生活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第89页)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界,不是抽象的、自为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而是在人类生活的过程中生成的、人的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中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以这一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才是人的生活与人的科学的基础。在这样的自然界与人的社会实践的统一中,才能说“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这里的“人本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科学”——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的科学。
正是感性实践活动的对象性的“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关系”(第86~87页),人与对象(现实的自然界)彼此规定、彼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展现历史的发展和人性复归的人的解放运动。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看到,在《手稿》时期,马克思首先强调人的感性实践的本体论地位和作用,并主要从感性实践活动的角度和范围,来理解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自然界不是指在人之外的、与人无关的、孤立的、自为的自然界,而是与人的感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相关的、人的活动介入的、对象化的、现实的、人化的那部分自然界。并且,这部分的自然界,通过人的感觉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以自然科学的形式,通过工业而得到展示和确证。因而,工业成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本质地位的确证和展示,自然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在人的活动的发展即人的科学的发展中得到显现。
显然,马克思并没有在一般或全部的自然科学与以他所界定的“人化”的自然界为对象的自然科学之间做出明确区分(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因为已经存在和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参与的结果,都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结果,因而都是人的科学)。只是从他的论述线索和对自然界的界定中,我们可以说,其自然科学主要是指以人化的自然界为对象的那部分自然科学。马克思强调的是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的那部分自然科学及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作用,这可以从马克思对自然科学在工业社会中运用和发展的表述中清晰地看到。
总之,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科学”概念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自然科学概念是有差异的,它是指与人和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的自然科学。这与马克思对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界的认识和界定有关。马克思明确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离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第116页)自然界一定是指与人及其活动相联系的自然界,是社会、工业中的自然界,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中对象性的自然界。马克思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社会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第83页)
2.人及“人的科学”
《手稿》中,马克思多次使用“人的科学”的说法,但对“人的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指认和界说。
对人的科学的研究,必然要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关键是如何把握人的本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表现出不同于以前思想家的独特之处。我们应该看到,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是真正科学的典型形式,但对人的科学研究还停留在抽象的哲学人本学或者说自然科学的人类学的水平,这是马克思在思考和研究人的问题时所不满意的。通过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及其自然科学在工业中的运用,马克思看到,人的本质在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中即在对象性的感性实践中得到对象性的展开和展现,自然界不再是脱离人的感性活动的、孤立的、自在的自然界,而是打上人的实践印记的、人的本质力量展现的、感性的、现实的自然界;人也不是脱离外在自然界的孤立的人,而是通过人的对象性的感性实践活动,在感性的自然界中展现自身本质的人。于是,马克思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的实践关系及其现实的工业中,来阐述人的科学。这种在感性的实践活动中、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的关系中对人的研究,脱离了过去哲学的抽象人本学,使得对人的研究成为真正的、现实的、实在的科学——“人的科学”(相对于研究自然的“自然科学”)。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科学”还有其他表述,类似的说法还有“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人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现实的科学”“真正的科学”等(有的学者把它直接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但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论述来看,“人的科学”肯定不是指抽象的哲学人本学,而主要是指人的解放的科学研究及其理论*这是《手稿》的主题,是马克思在《手稿》中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类似说法,如“现实的科学”“人的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就容易理解了:其实它们就是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现实的、感性的、实践的人及其解放的科学。至于把“人的科学”说成是“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如果我们从《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感性实践基础上)的论述来看,也是容易理解的。说到底,在马克思看来,要建立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必须在感性实践的基础上,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内在本质关系及其实践中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内在关系,从而为“人的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因此,在马克思的科学研究视域中,他特别强调的是“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对感性实践活动的依赖,以及在此基础上两个对象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和相互作用。马克思说:“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一般自然界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说法。”(第90页)在这里,马克思一是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存在物。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的科学”就是“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即“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这些都是“同一个说法”。二是强调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的、对象性的、人化的、“人本学”的自然界,而不是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无关的、外在的、抽象的自然界,这样的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无”,就是非存在,因而现实的自然界就是“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
事实上,《手稿》中,马克思是在与自然科学并列的意义上提出“人的科学”概念及对它的自然科学式的研究的。这说明,马克思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对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把握走上真正的、现实的“人的科学”的研究,而不再在传统哲学的抽象、思辨的意义上研究人的问题。这一研究主题和方法的改变,在马克思后来的理论研究中越来越明显,最后集中到《资本论》这一专业经济学的研究上来,并最终完成从哲学研究向具体科学研究的转变。
三、实在的科学研究及“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关系
《手稿》中,有关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及其关系的论述,是在“笔记III”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加以阐发的。该部分的主题就是论述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所“生成的社会”(第88页)能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开辟道路,其主题就是人的自由解放——人的科学。
马克思发现,在工业社会之前,虽然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哲学*这时马克思用的是“哲学”而不是“人的科学”概念,在他提到工业及其作用后,才用“人的科学”概念代替此时的“哲学”概念。这说明,在马克思的思维中,原来的哲学中含有对人的认识,如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马克思没有用人本学这个概念,《手稿》中只有三处以“人本学”形容词的形式出现),但这种对人的哲学认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科学”,仅仅是抽象的人本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想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第89页)。在这里,马克思一下子就抓住了旧哲学中科学观的局限,即作为哲学基础的科学观的二元分离(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分离)。
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第89页),因而有关人的解放的事业——人的科学,就不能无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工业社会的应用及其对人的生活的作用,它构成了人的科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说:“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说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第89页)
于是,在工业“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中,从全部历史发展来看,研究人的科学是不能离开自然科学的;并且,通过工业,不但使得研究人的科学不能离开自然科学,而且也使得自然科学更加趋于研究现实的感性自然界。所以马克思说“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出发,只有从自然界(指现实的自然界——引者注)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马克思总结说:“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的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第90页)
这里需要注意马克思表述中使用的“往后”和“将是”两个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在他所阐发的理论思路上,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工业成为“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中,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面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因而,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彼此结合、相互作用和包含,其“将是一门科学”。这是从人的感性实践及其发展和解放即人的科学的角度来说明自然科学的作用和意义,并不是说两门科学可以相互取代,就是一门科学了,也不是掩盖和抹杀两门学科的界限及其各自学科的功能和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业成为自然界与人之间,因而也成为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如果把自然界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人作为“人的科学”的对象,那么,由于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融合和统一,使得现实的人已经不是原来与自然界隔离、对立、孤立的个体,现实的人成了现实的自然界中的人,人和自然在工业中融合而统一起来,因而作为“人的科学”对象的“人”,在工业实践上展现了他与自然、社会、历史之间不可分离和互为一体的丰富内涵,人的本质已经不是抽象的人本身,而是一个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在现实的自然、社会和历史中的人的内在力量的展现。自然界也因进入人的实践领域而变成现实的自然界、人类学的自然界;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成为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因而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这时,生活的基础和科学(包括人的科学)的基础只有同一个——自然科学(工业之后的)。
这样,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的科学都是以感性即“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为基础的科学。在感性活动的意义上,人和自然界不可分离,在这样的意义上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必然同样不可分离,即“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事实上,马克思是从人的科学的对象和自然科学的对象之间的作用关系来把握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一方面,“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通过工业,“直接的感性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成了“直接地”“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另一方面,“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通过工业,人的科学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就是感性;并且“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这时,“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了。
所以,正是通过工业促成的人和自然界的融合和统一,使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不能分离,成为一门科学。其中自然科学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人的科学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也成为真正的、现实的科学。这一切都是在人的感性的、实践的工业中实现的,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以异化的形式实现的。
四、余论
在以往对《手稿》中关于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关系的研究中,要么是对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作字面上的生硬解释和阐述,从而显得很牵强;要么是把这一思想直接运用,把它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合统一的根据,并没有真正注意到马克思论述二者关系的理论背景、基础和思路,更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论述中“将是”二字的含义和用意。
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有关于“唯一历史科学”的论述,即他从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看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及“人的科学”的发展,不过这一论述又被马克思自己划去了。在之后《资本论》的研究中,马克思主要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来思考和解决人的解放问题,其中用到许多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经济学的自然科学性质。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之后对资本的研究中,虽然没有明确坚持和贯彻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但是,他仍然坚持了这一思想的一些要点,包括:(1)人的解放的事业首先是“人的科学”的事业,即“人的科学”必须为人的解放事业提供科学的理论准备;(2)人的科学的对象——人——不是孤立、抽象的人(性),而是在实践活动中、在与自然界的对象性的活动和作用的关系中确立和发展的;自然科学通过其在工业中的运用而作用于人并铸就人;因而,研究人的解放的“人的科学”就必须依赖并借助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就是“人的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3)人的科学的研究,必须摆脱抽象、思辨的哲学,用实证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建立实在和真正的人的科学的研究,《资本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WANG Rongjiang, professor of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yin, Jiangsu, 223001.
责任编校:余沉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Karl Marx’s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 Science Will Be a Science”
WANG Rongjiang
Abstract: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Marx tries to get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abstract and speculative philosophy research through a critique of Hegel and Feuerbach’s philosophy. He starts from realistic and perceptual practice and adopts the approach of direct and non-philosophical science in expression and analysis,thereby realizing the change of his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Establishing perceptual practice as the precondition of his ontology, Marx illustrates his solution to the mystery of history and 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communism aiming at human freedom and liberation. His idea on “a science” is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his scientific theory and is also aninevitable outcome of his ontology.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 science will be “a science”.
Key Words: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non-philosophical science; perceptual science; objectivity; a science
作者简介:王荣江,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 淮阴223001)。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1-0007-08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