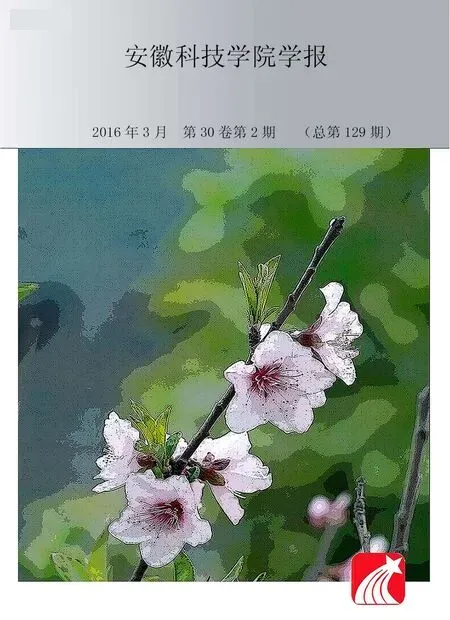浅论《红高粱》的文化叙事
2016-03-17王启伟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王启伟(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浅论《红高粱》的文化叙事
王启伟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红高粱》作为莫言的成名作,创作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文化大碰撞时期,代表着当代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精神实践的一部分,浸淫着厚重的文化蕴含。《红高粱》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文化具有主体体验的功能,乡土文化对于西方来说充满了神秘性,另外,母题的传承与创新使得作品更具故事性。对《红高粱》文化的阐述,有助于读者从宏观上对莫言作品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文化认知。
关键词:《红高粱》;历史文化;乡土文化;母题
对莫言作品的研究始终伴随着他的创作过程,而诺奖的获得则掀起了莫言研究的热潮。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对莫言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五四时期反映现实、刻画人性相似的主题;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特色;运用比较文学的视角探究与海外及国内作家作品在各方面的异同;历史空间及民间立场等。比如杜克将五四时期小说主题与莫言作品主题进行对比;钟雪萍论述了莫言作品中“种”的退化;王德威认为莫言将历史想象和叙事构成一个三维空间,在历史流动的坐标中设置小说的事件、人物等。近年来,也有学者借助西方文论研究莫言作品,例如李均认为莫言创作的独特价值在于始终如一的新历史主义立场和“作为老百姓写作”[1];温儒敏把莫言作品中的历史叙事描述为具有“野史化”[2]的特征。本文选取莫言的《红高粱》作为切入点,探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主体体验式的历史文化、充满神秘但真实的乡土文化以及传承与创新视角下的母题文化。
1 主体体验:新思潮下的历史阐释
新历史主义思潮萌芽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加州大学史蒂芬·格雷布莱特首先使用该词来描述当前文艺的动向,葛林伯雷使用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来形容这一思潮。在文学批评实践领域,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化与历史转轨,提出构建“回归历史情境”和“触摸历史肉身”的文化诗学。《红高粱》作品发表在1986年的《人们文学》杂志,可以说是中国最早践行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作品。
莫言写《红高粱》的初衷是通过文学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刻画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战争中人性的变异[3]。瑞典皇家科学院诺奖评审委员会认为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是“当代知识界人文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当代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精神实践的一部分。”[4]历史叙事是莫言擅长的写作方式,《红高粱》取材于日本侵华时期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历史事件。莫言在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中坦言:“《红高粱》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所住的村庄的邻村。先是游击队在胶莱河桥头上打了一场伏击战,消灭了日本鬼子一个小队,烧毁了一辆军车,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胜利。过了几天,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回来报复,游击队早就逃的没有踪影,鬼子就把那个村庄的老百姓杀了一百多口,村子里的房屋全部烧毁。”对比抗战的整个过程,这一历史事件的确微不足道,但是莫言正是对这一系列历史上的小事件、小人物的描述,唤醒了当代历史主体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或者来自父辈的讲述,或者来自民间传记,甚至有可能来自儿时对那段历史的幻想。《红高粱》的文字唤醒并强化了这种“集体意识”,莫言呈现在当代主体面前是另一视角的历史阐释,这种历史阐释“首先表现为当代主体在文本层面对于时空情境和文化意义的整合和重构过程,其次呈现为在个体视角、群体意识和历史情境之间的记忆和回忆形式”[5]。这种阐释让当代主体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去“重温”、去体验那段“集体意识”中的历史。莫言通过个性化的历史阐释方式,使当代历史主体将普遍认同的历史印象和《红高粱》中的“历史”加以比对,产生历史陌生感和新奇感,在阅读过程中甚至会穿越时空,追随着余占鳌率领的众乡亲,趴在胶莱河旁的高粱地里打伏击战。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要求今天的人们要冷静的去重新审视已经变成灰色的历史,要看到书本之外的“小历史”。历史长河中,还有诸多事件进不了“四库全书”。如何让读者通过文学阅读的形式去了解战争、了解历史?“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听过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跟鬼子拼过刺刀但在电影上见过”[6]的莫言做到了这一点。他通过对湮没于正统话语之外的“小历史”的叙述,让读者能够感受到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在《红高粱》作品中,莫言在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将历史剥去了“过去时态”的外衣,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作者主观感受的“现今感”的描述。这一处理方式虽然少了一些对历史理性的思考,但对读者而言,它唤醒的是一幕幕渐去渐远的历史,也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固有的程式化的历史。《红高粱》的主人公余占鳌是个土匪头子,在人们的概念中,土匪乃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以勒索、抢劫为生,为所欲为,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缺乏政治远见,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民族危难之时也都表现的唯利是图等等。莫言描写的不是叱咤风云、正义化身的英雄,而是革命年代有血有肉、平凡普通“身边的人”。“……那些乌龟王八蛋,仗着期号吓人,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变我?我还想改编他呢!”[7]。这样的描述对当代主体而言,既有陌生感,也有熟悉感;陌生的是土匪“精忠报国”,熟悉的是人们对土匪固有的思维模式。这样的历史阐释无形中拉近了当代主体与历史主体的距离。无论作者是在还原历史,还是创造历史,莫言创作过程中,在历史叙事上选取的切入点,都能让当代历史主体“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去体验、去感受历史。正如荷兰历史学家安科斯密的论述:“生活在某一历史特定时期‘感觉怎么样’的观念正是历史书写者尝试各种形式,希望传递给我们的,他们传递的主要内容并不是疏离我们和过去的某种连贯,而是透漏给读者那些直接和间接关于过去的某种‘经验’”[8]。《红高粱》中的历史书写关注的是历史主体的战争经历,是当代主体的感觉经验,作者传递给读者的是二者之间的连贯。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作品中的历史阐释不仅仅是一种再现历史情境或还原历史真相的模式,更是历史主体以及当代主体追忆历史图景、体验历史活动的构建过程。
2 神秘与真实:东方神秘主义视阈中的乡土文化
东方神秘主义是指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中难以理解的、超自然现象学说流派的总称。在西方人看来,“玄乎其玄”或者带有浓厚东方特色的一切也被称为东方神秘主义。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铸就了神秘主义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儒家文化强调“天道”、“天命”的宇宙观;道家文化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9]的神秘境界。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必然带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莫言作品不乏反映东方神秘主义的描述,《生死疲劳》是典型代表,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力草灰蛇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中国农民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
陈建国在《鬼怪的逻辑:论中国当代文学想象中的鬼怪和幻景》[10]指出莫言作品中鬼怪形象的应用。对鬼怪等形象的描写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透视神秘现象,为作品添加神秘色彩。从莫言的作品中,可以清晰的看到《聊斋志异》对他的影响。在诺奖致辞中,莫言讲到:“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奇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颗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11]。莫言把自己当做蒲松龄的传人,的确,蒲松龄对莫言的影响深入骨髓,他把逸闻趣事,历史传奇,鬼怪妖狐,战争英雄写进了作品,让整个世界聆听“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莫言曾坦言从《聊斋志异》中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获取灵感,塑造敢爱敢恨的“我奶奶”的形象。《红高粱》中罗汉大叔被剥皮描写,……幻化出美丽动人的故事。不难看出,该情节的描写也有《聊斋志异》的影子。当然,莫言作品吸收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但这是一种中国式的魔幻写法,它披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纱。他坦承:“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语言的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12]。在“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莫言把历史传奇、鬼怪狐妖、英雄土匪柔和在一起,“运用民间的信仰、奇异的动物意象、不同的想象性叙事技巧以及诸如国家和地方的、官方和民间的历史与现实,并将它们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奇特的、令人兴奋的文学”[13]。
莫言在《红高粱》里展现了震撼力极强的乡土文化,通过对带有充满神秘色彩和梦幻气氛的民间传说的描写,建构了“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的乡土文化根系和血脉传承下的民族精神,还原了“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的民风、民俗和民情。“颠轿”和“哭丧”的描写对土生土长的高密东北乡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对于遥远西方国度的读者来说,绝对是无法理解的异质文化。东方神秘主义的实质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而造成西方人对异质文化理解上的障碍,从而造成心理上的神秘感。莫言对作品中颠轿的描写如下:“轿夫抬轿从街上走,迈的都是八字步,号称‘踩街’,……踩街时,步履不齐的不是好汉,手扶轿杆的不是好汉,够格的轿夫都是双手卡腰,步调一致,轿子颠动的节奏要和上吹鼓手们吹出的凄美音乐。”[7]轿夫们要把轿子颠地像风浪中的小船,让新娘屁股坐不住座板,双手也抓不住座板,直到吐个天昏地暗,出声求饶。本来迎亲嫁娶是何等欢乐的时刻,新娘更是典礼的主角,为何要如此折磨出嫁的新人呢?除了颠娇,齐鲁大地上的哭丧文化对于异质文化的读者来说则更是无法琢磨。“我不得不告诉您,我们高密东北乡女人哭丧跟唱歌一样优美。民国元年,曲阜县孔夫子家的‘哭丧户’专程前来学习哭丧腔。”[7]哭丧是一种古老的丧葬习俗,以哭的形式表达哀思。而哭丧要跟唱歌一样优美则要追溯到执绋者唱挽歌送葬的汉代习俗。挽歌的代表作品是《韭露》和《嵩里》,前者是为王公贵族出殡时唱,后者是为士大夫和一般百姓出殡时唱,挽歌入礼,在汉晋时代兴起,到南北朝时期更加流行,逐渐演化成今天的“哭丧要像唱歌一样优美”。如何理解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蒙着神秘面纱”的民风民俗呢?这绝不是为了取悦西方读者而有意为之,莫言只是还原了高密东北乡的乡土文化。“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其上。”[14]乡土文化的精神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永远与后来人维持着某种内在联系。伴着豪迈、粗犷的歌声,踏着高低不平、尘土飞扬的黄土路,轿夫们无拘无束、肆无忌惮的换发着勃勃的生命力,浑然天成的传达着一种乡土神韵。
3 母题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莫言的《红高粱》回归了小说的本质,那就是讲故事。作品中,“我爷爷、我奶奶”等一系列语言的运用,让人仿佛置身于路边说书人精彩的故事情节中。作为一个精彩的故事,诸如“英雄”、“义仆”、“异类幻化”等母题几乎成为必不可少的范式。作者不仅传承了上述母题的核心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还对其进行了变异与革新。若从作者创作的角度来考察,我们首先要考虑母题表象与“文学寄意”之间的关系。“文学寄意”是指附着在某一具体母题之上的传统“意涵”因子。作家在使用某一母题时,“一般不会‘休整’表象,至于‘意涵’因子,则会随其‘艺术所需’有所‘灌注’,而附着在原母题之上的东西可能被他‘置换’掉。”[15]
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之所以不断的涌现出各式各样的英雄,从本质上讲,是在寻找理想生命的典范模式,探寻一种拯救生活危机与困境的途径,达到一种人格的高度和生命的力度。《红高粱》中,作者塑造了余占鳌这一“英雄”形象,虽然我们难以从道德层面上接受土匪出身的余占鳌等人为英雄,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无法拒绝对他们那种充满阳刚之气的生命的崇拜,正如作者在《红高粱》开始的论述:“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7]作者在传统英雄母题的框架之下,按照主题需要,改变了其中的某些母题因子。土匪出身的余占鳌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绿林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是符合传统的母题规范。但《红高粱》中上演了一幕余大牙强暴民女玲子而被其亲侄余占鳌枪毙的情节,诸如“英雄杀妻、英雄杀嫂”的母题因子在文学范畴中随处可见,但“英雄杀叔”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却是不多见。作者为塑造人物形象,符合故事情节结构,服务作品主旨,将“英雄杀嫂”这一母题因子置换成“英雄杀叔”。
莫言在《红高粱》中塑造了“义仆”刘罗汉的形象,我们将目光转到罗汉大爷身上。刘罗汉在东家工作了几十年,烧酒房里的大小事务他全权负责,另外,是带着东家的公子,这里指的是文中的叙事者“我”在墨水河捉螃蟹等情节,还有女东家面临危险时,罗汉大爷从拒绝接受日本人的差遣到勉强接受,可以说,莫言对罗汉大爷的描写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仆人的特征。书中的罗汉大爷被强抓去修建公路,他虽然痛恨日本人,但我们从罗汉大爷咒骂语言中,可以清晰的看出,罗汉大爷更恨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甘愿充当日本人走狗的“监工”。八十年代的文学,“伤痕”、“反思”文学居多,《红高粱》是抗战文学作品,书中塑造了“自私自利”的监工形象,他为保全自己性命,为在乱世中生存而欺压同胞,践踏国人尊严,这为忠义的罗汉大爷所不齿。时代在变化,“义仆”母题不仅仅局限在“义仆救主”或“托孤义仆”等类型,作者为实现创作目的,让“义仆”拥有了家国情怀,时代背景是“义仆”变体、更生的内在推动力。
“异类幻化”母题,或称为“变形”母题,表现为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外在形体的相互转换。有学者指出,这一母题是基于“那种自然与社会混同一体的宇宙生命观”,就是我们常说的“万物有灵论”,体现的是“足够充分的生命能量”[16]。在上古人们的意识里,“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生命的社会。……生命在其最低级的形式和最高阶的形式中都具有相同的生命尊严。人与动物,动物与植物全部处在同一层次上”[17]。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在人类意识中逐渐分化,但“异类幻化”母题的内涵却一直演化而来,并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在他者的声音中,莫言的作品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若站在文学传统的视角下,可以说是作者继承了“异类幻化”的母题。《红高粱》中最为明显的“异类幻化”是描写是罗汉大爷死后化为一个美丽的传说,另外,关于“高密东北乡”动植物或地理环境具有灵性的描写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时至今日,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分界线相对泾渭分明,如若强拉硬拽的把“异类幻化”母题置于抗战题材的作品,则会失去其应用的价值。莫言作了灵活处理,没有正面描写“变形”母题,而是插入了国人都普遍接受的“万物皆有灵性”的描写,哪怕写罗汉大爷幻化的文字,也仅仅用了“竟成了一个美丽的神州故事”,实写“异类幻化”,却不直接点明,留读者以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既向传统致敬,又完成了进一步的超越。
4 结语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莫言是那个时期新历史主义创作的践行者,再加上《聊斋志异》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莫言的作品拥有了传统的影子和新思潮的痕迹。《红高粱》正是两者影响下的作品,其“野史化”、“民间化”的特点成为莫言触摸历史肉身的手段,民俗的描写以及酷刑中罗汉大叔美丽的幻化使作品披上了神秘的外衣,母题文化的继承与革新让作者成为了最会“讲故事”的人。独特的叙事视角、恣意汪洋的语言、主体体验的历史文化,小说中的神秘东方以及作品中母题的的灵活运用让《红高粱》成为莫言的代表作、也让“高密东北乡”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李钧.新历史主义的立场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深层原因探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8(2) : 36-42.
[2]温儒敏.莫言历史叙事的"野史化"与"重口味[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38(4) : 22-28.
[3]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J].养生大世界,2015,29(1) : 76-79.
[4]张清华.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18(2) : 35.
[5]王进.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1) : 204-207,227.
[6]任南南.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版图上重读《红高粱》[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 59-65.
[7]莫言.红高粱[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2.
[8]ANKERSMIT F.Historicism: an attempt at synthesis[J].History and Theory,1995(3) : 143-161.
[9]周昌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渊源[J].探索与争鸣,1999,26(10) : 35-36.
[10]JIANGUO C.The logic of the phantasm: hunting and spectr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J].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02(1) : 78.
[11]莫言.讲故事的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演[J].当代作家评论,2013(1) : 4-10.
[12]舒晋瑜.莫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原因[N].中华读书报.2010-02-03(11).
[13]葛浩文,吴耀宗.莫言作品英译本序言两篇[J].当代作家评论,2010(2) : 193-196.
[14]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36.
[15]王政.关于中国古典戏曲母题史的研究[J].文艺研究,2012(8) : 119-122.
[16]叶舒宪选.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65-68.
[17](德)恩斯特·卡西尔,甘阳.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15.
(责任编辑:郭万红)
On the Cultural Narration of Red Sorghum
WANG Qi-w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 235000,China)
Abstract:As Mo Yan’s masterpiece,Red Sorghum was created in the cultural collision period of 1980s.It steeped in profound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represented humanism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In Red Sorghum,historical culture contains the function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 local culture,the function of mysteriousness; motif,the function of narrativeness.Through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Red Sorghum,readers can have a more profound cultural awareness of Mo Yan’s works.
Key words:Red Sorghum; Historical Culture; Local Culture; Motif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772(2016) 02-0114-05
收稿日期:2015-09-2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4SK24)。
作者简介:王启伟(1981-),男,山东省临沂县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文学及翻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