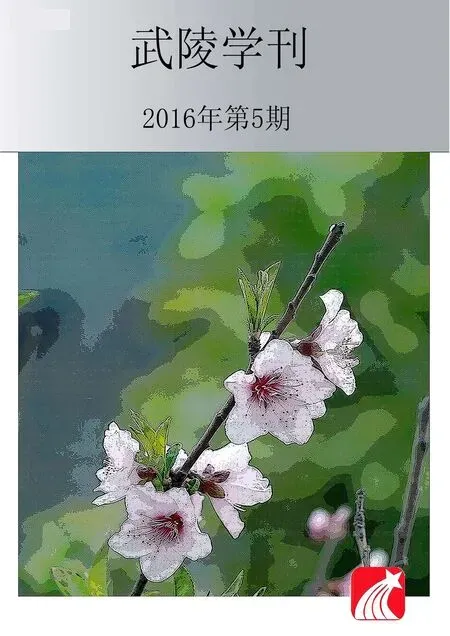外语课程的后现代主义映射
2016-03-17白臻贤
白臻贤
(湖南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外语课程的后现代主义映射
白臻贤
(湖南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现代主义课程观是具有科学主义倾向与控制取向的,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前者的道路,它以多元的特质构建自己的课程标准。后现代主义映射下的外语课程转向人本主义取向,以尊重学生的方式进入语言教学。在外语课程教学中,突出语言与语言教学的体认性是对学生在语言中的成长与生命意义建构的倡导与关怀。
外语教学;课程;语言;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从科学那里获得启示,然后,科学只顾说明世界,却不关心人生意义,正所谓“科学不思”。现代主义课程观被指缺乏人本精神与人本情怀,教学理念相对落后,应试倾向明显,把外语仅当作工具的传统外语课程更是如此。后现代主义课程观不是反科学的,它也从科学的最新进展那里获得营养,汲取新养分的后现代主义课程观于是有多重理由对现代主义课程观进行批判与超越。
一、现代主义课程观的行迹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有些含糊的矛盾的概念,一般来说,它是指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的特性。现代性是一种现代意识,是一种理性精神,它代表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强劲的变革逻辑,它的本质就是变革。现代性的核心是主体性,它是理性的大旗得以高高飘扬的动力之源。现代性是肇始于西方的术语,它的时代意义从西方文明的视角来说,可以囊括自16世纪以来发生的所有伟大历史事件,诸如宗教改革、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文明等等[1]13。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它给社会带来进步和福音的同时,也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里面装有祸害、灾难和瘟疫,现代性也就成了危机与困惑的代名词。现代主义是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各个反传统的流派、思潮的统称。它所表达的最基本的东西是对人类理性精神的信仰与崇拜、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
课程理论从来就受“主义”或哲学思想的影响,现代主义的“幽灵”毫无疑问会渗透到课程观中,现代课程理论与现代主义一定会有瓜葛。在现代主义的大背景下,课程理论的发展如果没有打上现代主义的烙印,这反而会是件奇怪的事。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拉尔夫·泰勒(R.Tyler)的经典之作《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中提出的课程的目标、课程的方法以及基于科学主义理念的统一化标准概念是现代主义范式的核心[2]103。泰勒原理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关于确定目标,那就是学校应该努力达到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其次,关于选择经验,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恰当的教育经验,以便达到教育目标;再者,关于组织经验,教育经验如何才能有效地被组织起来;最后,关于评价经验,人们如何确定教育目标达到与否。泰勒的过人之处是要用一种合理、综合的方法为不同性质的课程建构出合乎逻辑的整齐划一的东西。
泰勒原理极富魅力,在当时背景下,它的含义就是科学、现代化与变革,从课程设计与开发的目标预设、过程实施到结果评价,它是具有控制取向与科学主义倾向的,它是一种最精致的课程发展范式。泰勒原理旨在向人们提供一个“可控的”课程,像现代化工厂的流水线,流水线上被加工好的成品与其原初设计是吻合的,大体不会走样,中间的生产过程也是程序式的、可控的。不仅如此,课程的内容、要传授的知识都是可以具体化和量化的,操作性强。可以说,只要开动起来,现代化机器般的课程应该也能够使“毛坯”学生变成合乎标准的“成品”学生。
外语教学研究与实践有本体论层次、实践论层次与方法论层次之分,对于这3个层次,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是绕不开的:一个是外语教学意味着什么,另一个是外语教学应该怎样进行才最有效。前者涉及的是对语言的本质特征和外语教学本质特征的认识与理解,后者涉及的是人们对外语教学本质的理解对外语教学实践的影响,包括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认识与理解[3]30。在我们的传统外语教学中,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较为常见的解答是:将语言看成工具,外语学习也就是一门工具的学习,课堂上语言知识的讲授成为了主线。当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一种交际手段时,外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就设定为语言意念、语言功能、语言技能、语言情景、语境等的学习与掌握。课堂教学的实施过程是语言知识单向地从教师传向学生,教学活动注重语言的应用。考试时对语言知识点的掌握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学生学习成绩的标准,也成为了评判一门外语课程教学成功与否的标准。
由于泰勒原理与现代主义语言观的叠加,外语课程教学中“讲授”“练习”“输出”的模式是最普遍采用的,这一模式就是所谓的PPP(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模式,这一模式认为,向学生提供一定量的语言结构知识,让他们进行大量的实践练习,就会使他们具备语言的生成能力。分析这一模式会看得更清楚,其优点除开不说,问题有不少方面。首先,从课堂的实施来说,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教师有生杀大权,语言知识的传授以教师讲解为主,讲授什么、讲授多少、如何讲授,都是教师说了算,而学生一般不能参与这些过程的决策,在课堂上处于弱势,自始自终是被动的接受者。其次,PPP模式成为应试的导向,课堂教学中主要由教师讲授相关的语言结构的知识,学生则被要求通过一定的操练来记忆这些语言规则,以应付考试。再者,学生课堂接触到的不是真正的语言交际样本,也不是实际的语言交际活动,其外语输入是非常有限的。此外,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学生对语言学习本质的理解,误导了学生学习外语的方法[3]156-157。PPP外语教学模式虽然大行其道,但其对有关语言学习本质的误解不容置疑,这些误解主要有:学生按照所教的顺序习得外语,语言仅仅是一个知识的系统,语言知识会自动转化为语言技能,仅靠课堂实践就能培养语言交际能力。
把教学的目的看成是对知识的占有,把教育的对象当作是被改造的对象,课程的组织与实施忽视学生的个体发展、个体知识和个体价值。传统外语教学模式之殇内在的根源在于现代主义课程观。其目标的先验性与外在性,从目标到结果的线性,基于科学主义理念的统一化标准概念,都是现代主义范式的核心,这些也是后现代主义范式以各种形式对其发起挑战和谴责的对象[2]104-105。
二、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转向
从哲学发展史来说,后现代哲学鼻祖是尼采,是他发明了后现代性。他不认同自笛卡尔以降的西方哲学所强调的主体性及理性精神,对现代性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尼采抛开与理性相关的意识、真理及道德,颂扬狂喜、欲望、享乐等人类本能,通过开辟一条独特的精神逃亡之路,破解理性的权威,与现代性展开厮杀。尼采之后,拉康、福柯的怀疑论与海德格尔、德里达的形而上学批判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两个主攻方向,前者驳斥主体化理性,后者抨击形而上学的基本谬误[1]23。
任何理论或主义,无论是所谓“现代的”“后现代的”抑或是“超现代的”,都只可能具有“有限的合理性”,超出其适用的时空及领域范围而赋予其普遍有效性,其被当成普遍真理,必然贻害无穷。人们指责“现代主义的贫困”,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一点。现代主义总是让人们相信,概念、公式、观点等可以一劳永逸地作为现实,最终指向某种固定的、封闭的、可命名的东西上,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4]。现代主义不可能是万能的,一旦人们认清其阴暗的一面后就会抛弃它。说到后现代主义,它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与超越。首先,其批判的火力瞄准的是传统的“主体性”、理性至上意义、传统的形而上学、以普遍性和同一性压制个体性与差异性的传统思想模式。然后,其对现代主义的超越表现在把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归结为人的审美生活——自由生活的彻底实现[5]。
因为现代性的局限与困境,被现代主义摆弄的课程领域进入末路是迟早的事情。后现代性哲学随着其发展的进程,表现出多重特质:首先,它体现人本性、批判性;其次,它体现为反传统、超基础、去中心、非理性、后人道、多元化、破坏性、解构性;再者,它表现为建设性、体验性[6]440。跟着后现代性哲学的步伐,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课程观用拒绝科学主义、拒绝理性主义、拒绝结构主义的做法来解构现代主义的先验的外在的目标、线性方法以及基于科学主义理论的统一化标准概念范式。它以丰富性(Richness)、回归性(Recursion)、关联性(Relations)和严密性(Rigor)来建构自己的课程标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超越是讲究策略的,它拒绝科学主义,但不是拒绝科学,而是换一种眼光看待科学,并用科学阐释自己的东西。它拒绝理性主义,但并不拒绝理性,只是不把理性当成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是给理性一个较合理的位置。它也是拒绝结构主义的,但不是完全拒绝结构的东西,该给结构的还是给结构。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不是一刀两断,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对现代主义有合理的继承。在后现代课程论者提出的一些方案和策略中,并不是完全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后现代主义课程观事实上从科学那里寻求过支持[2]119。
与现代主义课程观相比,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对课程的理解发生了深层的变化。课程从静态的知识体系的载体成为了动态的发展过程,课程的重要参与者包括文本、教师与学生,课程具有创造性,课程的发展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尊重价值观的差异性与多元性[7]。如果课程的目的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世界”,那么好的课程给人提供的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一个生活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知识的“世界”,一个可能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确定的“世界”。
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质量观表现在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和严密性上。课程是丰富的,课程的维度是立体的,其意义的层次是丰富的,有多种可能性与多重解释。课程中的适量的不确定性、异常性、无效性、模糊性、不平衡性、耗散性与生动的经验等是课程的必要营养成分,课程内在的疑问性、干扰性、可能性赋予课程以丰富性,带来存在乃至亲在的意义[8]。课程是回归性的,每一个终点就是一个新的起点,每一个起点来自于前一个终点,一个人通过与环境、与他人、与文化的反思性相互作用形成自我感。课程是关联性的,课程中的联系赋予课程以丰富的模体或网络,课程是文本、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一种立体的互动,不是单向的从文本到教师,再从教师到学生。课程也是文本、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一种平等的对话,没有文本的权威与教师的权威,文本、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相互作用。课程是严密性的,它有目的地寻找不同的选择方案、关系和联系,是对非线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的把握。这种严密性区别于现代主义的“有序的、理性的、线性的、科学的程序”,是用阐释性与不确定性发展的现代主义框架下的严密性。
就外语课程而言,后现代主义的转向还涉及到一个特别的“在者”,那就是语言。语言在后现代的视野中已由自缚的茧蜕变而成自由飞舞的彩蝶。语言不再是那个表达思想的简单工具,语言已从“奴仆”变为“主人”。从“语言使思想出场”“语言没有统一的本质”“语言具有体验认知性”等表达式,人们能够明明白白看清其“主人”的地位与身价。语言哲学家提出的经典名言“语言使思想出场”,彻底改变了语言的命运。对于“语言使思想出场”这一表达,可以有多重理解:语言使得思想清晰,使人出场;语言本身就是思想,就是存在;语言本身就是主体,不是工具[6]89。对语言认识的改变自然会给外语课程的教学带来影响。
三、一种体认的模式
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秉承了后现代哲学否定先验论与绝对本质、反对中心主义、倡导多元化的特质。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提出“现实—认知—语言”的原则,对语言持有的是“体验人本观”,这与索绪尔的语言先验论与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语言没有统一的本质,充其量只是具有多元的本质,这个多元本质包括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语言的体认性、人本性、象似性、差异性、构式性与整合性等[6]471。语言的体认性强调在对语言的认识和表达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在强调语言是客观事实的陈列时,不要忘记语言总会打上主观要素的烙印。
当人们说“a week consists of 7 days,a month 30 days and a year 365 days”“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and sets in the west”时,人之外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的世界——那个客观外界,并不存在一个以7天、30天与365天为刻度的时间单位,也没有东、西、南、北这样表示方位的空间概念。这些时空的划分完全是人为规定的,它们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而只存在于人们的共识之中。因此,对语言的认识不能忽略了“人的作用”。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在对现实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表达是在人的“体认”作用下形成的。这既是人的实践性与人本性作用的结果,也是多重互动(主客互动、客主互动、主主互动)的结果。对语言与外语课程的不同认识和理解会对外语教学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应该是没有人会质疑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外语教学目的、原则的制定、教学方法的设计及教学的组织实施与评价等。
在后现代主义课程观与语言观的双重作用下,外语课程教学应该是有温度的而不是冰冷的。有温度的课程首先是课程价值取向转向人本主义。课程是围绕着人来进行的,其起点与归属也是人,不要忘了课程实践中最重要的是作为“学生”与“教师”的人。语言教学,必须考虑到学习主体的生理和心理基础,考虑学习者的生活实际。必须把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来教给学生,因为在实际交往过程中,学习者才能真正理解学习语言的目的,从而更加自觉地对待语言。必须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来教,因为只有通过对语言规律的把握,学习者才有可能更快更有效地学会语言。必须考虑学生的发展与可能的生活,学习一门外语也意味着学习跨文化的交际,学习另一种思维方式,也意味着进入一个不同于自己母语文化的异域文化世界,与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接触碰撞,原有的人生轨迹有可能被改变。
走向人本主义也意味着以人本的方式对待语言。既要看到语言有静态的一面,也要看到有动态的一面,语言除了是工具,有形而下的特质,也是主体,有形而上的特质。“语言既是敞开世界的方式,也是世界自身的内容”[9],语言是我们的房屋住所,也是我们的家园。语言是产生自我认知的重要途径,是自我身份的内在标志,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在外语课程实践活动中,语言和世界融为一体,语言的意义在与师生的互动中不断更新。
有温度的课程其价值取向也是过程性的,过程性与人本主义是一致的。“课程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过程是课程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10]。过程性意味着不确定性和尝试性、创造性和生成性、经验性和开放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生态性与平衡性等多种特性。过程性蕴含着多种品质,从过程性的课程中人们可以理解的是:课程目标注重发展性与生成性,课程结构强调多样化与选择性,课程内容倡导经验性和开放性,课程实施指向整体性与开放性。课程中最重要的是学生,上面所有这些都要围绕学生进行,过程性的课程要以一种生态的、整体的观点对待学生。过程性也凸显体验认知的特性,学生从体验认知走向意义世界的生成。就学生而言,外语课程是他们参与、生成、建构知识的活动过程,是他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逐步建构意义世界的过程。意义不仅通过认识和评价活动得到体现,也通过体验与实践而生成[11]。通过外语学习,学生体验认知不同民族或者族群独有的文化与智慧,以一种不同于本民族文化与智慧的视角感悟生命的意义,拓展生命的深度。
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探讨外语课程的特质与实施,是为了更好地提升外语课程教学质量与更好地实现外语的课程价值。外语课程教学中突出语言的体认性与语言教学的体认性,是对学生在语言中的成长与生命意义建构的关怀。学生的成长是课程的起点、依据和落脚点,通过外语课程学习参与世界与成就自我的活动,学生在追寻意义的同时也不断建构多样形态的意义世界。
[1]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达[M].北京:三联书店,2007.
[2]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4]大卫·史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46-147.
[5]张世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1):43-48.
[6]王寅.语言哲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王红宇.新的知识观与课程观[J].比较教育研究,1995(4):20-24.
[8]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50-251.
[9]陈亚军.“世界”的失而复得——新实用主义大家的理论主题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7-47.
[10]许锋华,岳伟.课程即过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1):53-56.
[11]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
(责任编辑:刘英玲)
G64
A
1674-9014(2016)05-0134-04
2016-07-29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外语课程价值取向与价值实现研究”(XJK12YYB002);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复杂系统思想映射下的外语教学目标实现研究”(湘教通〔2016〕400)。
白臻贤,男,湖南南县人,湖南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语言学和语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