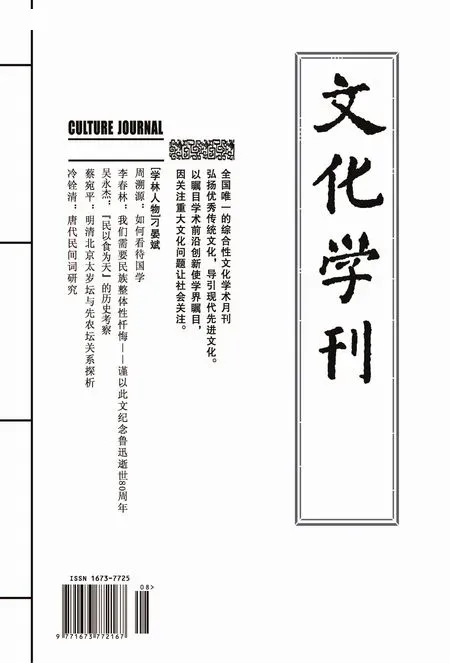晚明社会的文化心态:从万历怠政到文官集团的“名节”行为
2016-03-17刘黎
刘 黎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文史论苑】
晚明社会的文化心态:从万历怠政到文官集团的“名节”行为
刘 黎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曲靖 655011)
本文以万历皇帝怠政为视角切入点,把张居正改革身死名败及其与万历皇帝关系的变化、“争国本”事件进行串联分析,剖析明代文官集团的文化心态,在这一系列事件背后所表现的是虚妄的“名节”,缺乏对实际问题解决的思想和实践,一种焦灼和不知所谓。
制度;关系;矛盾;静止;调适
朱元璋创建明帝国,御宇期间所主持设计的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制度框架,对后世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体制创制设计随着时间及人事变化发生了偏离设计者的初衷理念,或者说是制度设计者缺乏长远目光,以落后的财政思想着眼于经济发展,僵化的体制和思想意识形态管理全国民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变化考虑不足,导致制度发生负作用,钳制了社会、国家人与事的适时变动。
一、张居正与万历关系的解读:从元辅张先生到敌人的转变
万历皇帝9岁登基,而本朝体制不允许藩王、即皇帝的叔伯堂兄等代为摄政,换言之,皇帝缺乏皇族中人的支持。张居正既是皇帝的老师,又是帝国的实际主宰者。他的权力远远超越前代任何一个丞相,但他的权力不是法定的,或者说不是儒家政统认定的,而是靠关系与人情维持。万历八年,万历皇帝与太监酗酒,遭到了其生母李太后的严厉责骂,继而李太后拿出《汉书·霍光传》,皇帝明白这其中的深意,霍光废立过皇帝。事后,张居正代皇帝写了《罪己诏》。十八岁的皇帝对此洞若观火,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导火线。在万历皇帝心中,我是皇帝,为何会被一个臣下所挟制?这勾起了皇帝早年的另一事件,“初,上在讲筵,读《论语》‘色勃如也’,误读为‘背’,居正遂厉声日;‘当读作勃!’上悚然惊起,同列皆失色,由此上益心惮居正。时比之霍氏骖乘云。”[1]这些事件连在一起,皇帝的不满、忿恨和厌恶在膨胀,继而指向最高权力的争夺。张居正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每况愈下,从元辅张先生变为一个敌人。这与万历五年张居正因父亲去世“夺情”,皇帝下诏再议论张居正夺情者格杀勿论,已是天壤之别了。随着皇帝日益成长,而张居正却手握属于他的权力。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在他成长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现代教育观点来看,她的教育方式客观上对皇帝产生了巨大的误导性。万历八年张居正在皇帝醉酒事件后,提出辞职,在她的授意下,皇帝下诏不允许张居正辞职,此时,皇帝早已18岁,按理应该临朝亲政,但她却要皇帝“与张先生说,……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30岁,那时再作商量。……”①《张文忠公全集》卷四四《谢圣谕疏》转自林延清,《李太后与张居正改革》,《南开学报》2005年第5期。皇帝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皇帝的母亲或是错误估计了儿子的心理态度,或是她不能洞悉帝国权力人事关系的厉害。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十二月皇帝便开始了对张居正彻底的清算,这是皇权体制下的必然,他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才能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这也是文官集团的看法。
二、晚明社会的文化心态:制度与文化、经济发展的逻辑矛盾
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去世后进行了彻底清算,他以激昂的斗志保持对皇帝职责的履行,万历十一年,京畿地区大旱,皇帝以步行的方式到天坛祈雨。这是一种态度,一种信念,他要把这个帝国治理好,这是对清算张居正的一种回应,可这一行为没有能保持他御宇帝国的始终,从万历十四年下半叶开始至万历十五年,皇帝开始逐渐发生了性情改变,以各种理由推脱不出席皇帝应该出席的各类活动,最后深居简出,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长期消极怠政。
万历五年,按照本朝惯例,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他要回家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但改革刚刚进入秩序,张居正如果离开,改革事业必将陷入停顿,于是只能选择“夺情”。在这次“夺情”事件中,张居正的两个门生,赵用贤和吴中行上书弹劾张居正,被皇帝下令处于梃杖。在这次事件中,文官集团的“名节”行为或被历史学家们所忽视,赵用贤的夫人在丈夫受刑后,从丈夫被梃杖打落的臀部碎肉中挑选了一块制成腊肉挂于家中,以戒示后人,同时更重要的是表达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在他们心目中,上书弹劾张居正是“天理”,因为张居正违背了“人伦”,“天理”不可更改的。当时张居正已是权倾朝野,看似无人能撼动,但当事件出现时,这只是表面现象。他的两个门生的行为在道义上代表了整个文官集团,及其所信仰的儒家道学。或许在客观上,他的两个门生是真情实意的希望老师能归乡守制,但在巨大的文官集团的背后这样的意思其实不尽实然,反对“夺情”的背后是权力的争夺和利益的追逐。更有甚者,后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和王锡爵竟然径自到张居正的府邸,王锡爵把张居正逼迫得拔剑欲自刎。十六年后,任内阁首辅的王锡爵因为“三王并封”,赵南星上门逼迫他,相信他感觉到了当年张居正的难处,进退维谷,他变成了另一个“张居正”。在这些看似“光明”的行为背后,不尽实然,用继任首辅申时行的看法即是整个文官集团的阴与阳的平衡距离越来越远,在“阳”的背后是“阴”的涌动,即私欲的膨胀,“阳”的实质不是内心的理念,而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万历皇帝在这种网状的困境中无法突破,最后他只得选择长期消极怠政,与群臣进行无声的对抗。“争国本”事件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事件。他欲立自己心爱的郑贵妃之子,即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恭妃王氏已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泰昌帝。皇帝与群僚对抗了十几年之久,牵动了整个帝国的朝局,几位内阁首辅被迫离职,数百位高级官员卷入其中,而皇帝的心理也随着这样的无助心灰意冷,对整个文官集团最终失去了耐心和信念,皇帝和群僚的关系最终变得不可弥补。关于皇位继承人,从永乐皇帝开始从法理上就不具备长子继承的合法性,永乐皇帝用武力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从法理上讲,万历皇帝可以从诸子中选择一人继承自己的地位,皇长子和其他诸子地位是平等的。那么其先祖永乐皇帝的地位就是非法的,这对于文官集团来说是一个不能言语的症结。于是这个继承问题被转化为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帝国的行政理念不是以法治理天下,而是以道德和礼仪。在“争国本”事件中各大小官员前赴后继的上书与皇帝对抗,最后皇帝只得妥协,立皇长子为太子,皇三子到河南之国。万历皇帝心灰意冷,他无法以一身之力量对抗整个文官集团,他用道家的“无为”为幌子与群僚进行对抗,他不补缺官员的缺额,意味着这一职位的利禄将被作废,官员的晋升之路就被阻塞,他不能提拔自己喜欢的官员,但他可以选择罢黜自己厌恶的官员,这是他唯一的手段,但这样最终结果乃是帝国政治行政体制瘫痪和崩溃。这样看来,“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2]
在万历皇帝消极怠政的背后,可以窥见整个文官集团的文化心理,在他们“名节”行为的背后,不尽全是一种“阳”的理念,而是私欲的牟取。一方面这是宋明理学“内圣”与“外王”,即“礼”和“仁”分化所形成的结果。原生儒学是“礼”和“仁”的双重合一,“礼”是一种外在的规制和原则,“仁”是一种情感的交融,至宋明理学发展时期,“仁”的地位和内容被扩大的深化,融入的佛教的概念,而外在关乎社会现实的“礼”,即现实社会规范被边缘化或被置于“仁”的统领下而遭到弱化,“内圣”的心性修养超越一切,到王阳明的心学发展到了顶峰。“外王”是基于“内圣”为出发点。另一方面是体制的缘故,本朝的体制建立在文官集团的基础之上,以宋明理学朱熹的儒家道统为开科取士的标准,而且本朝官员俸禄极低,“内圣”的修养缺乏外在“礼”的规制,这样导致人的文字道德与社会道德相分离,即在物质利益的吸引下,人的精神人格分离。万历皇帝消极怠政是对此极大的无声抗争,因为他洞悉这一切,“争国本”的背后就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因为拥立天子是不世之功。文官们上书直言犯上,表面看似是“天理”的一种坚持,即做所谓的诤臣,因为外在“礼”的规范的弱化,这变成了一种近似低俗的“吵骂”,翻阅明代言官的上书史料,这样的表现比比皆是,太过注重“名节”,而不注重社会实际,逐渐演变为一种沽名钓誉。群臣的争吵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后当李自成的大军兵临城下,帝国的大臣们作鸟兽散,崇祯皇帝身为儒家信徒,只能无奈的选择殉国,不妥协,不投降。万历皇帝的难处就在于他要做一个近似宗教徒“先知”一样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文官集团们则是对这种行为的监督,双方日益成水火之势,而不可协调。
帝国传统体制限制了经济发展所促进的文化观念的转变,中央集权的体制和内圣的文化观念,导致权力顶端需要的仅仅只是一个道德和礼仪的木偶,而不需要太多的主观能动性的和多重性格的皇帝,皇帝的行为被程式化、标准化,对此万历皇帝无能为力,他只能选择长期的消极怠工,导致帝国的臣僚们相互攻讦,形成党争,致使帝国政局一发而不可收拾。晚明社会的文化心态是焦灼和惶恐的,文官集团的名节行为也是一种不得已为为之的行为,面对残酷的现实,不能解决,只能用所谓的心的体验来掩盖内心的不安。因为体制的高度程式化,近似于宗教的设计,使得阴与阳的文化心理距越来越远。这预示这一种体制即将崩溃,长期的社会革命将不可避免,而且是撕心裂肺的革命。体制改革和适应对一个社会、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体制应当跟上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张居正的改革和万历皇帝的长期消极怠政对体制和文化、经济发展的同步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1]夏夔.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2.1582.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86.
【责任编辑:董丽娟】
G09
A
1673-7725(2016)08-0209-03
2016-05-05
刘黎(1981-),女,云南曲靖人,主要从事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