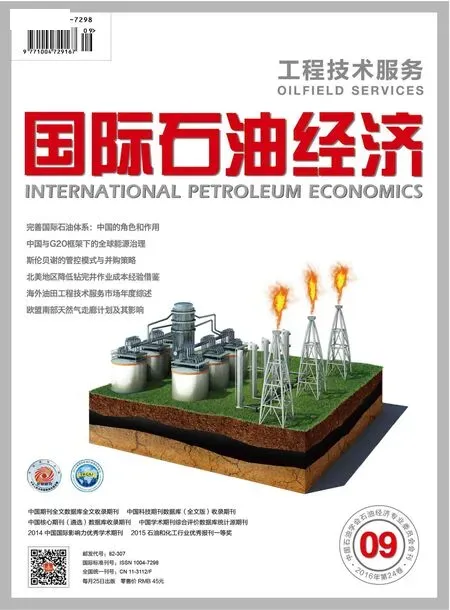中国与G20框架下的全球能源治理
2016-03-16何兴强
何兴强
(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
中国与G20框架下的全球能源治理
何兴强
(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
尽管与现有的主要全球能源治理机构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中国目前仍然主要依靠传统的双边和地区合作的方式即地缘政治战略确保海外能源供应安全。从能源供应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可被视为双边和地区能源合作的加强版。自21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寻求更多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并致力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碎片化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既不具备权威性又缺乏信誉,国内能源治理的相关机制也制约了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基于当前的国际能源治理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全球能源治理应该着眼于有限的目标,例如改善国际油气数据共享机制,提高透明度,加强全球清洁能源合作,稳步推进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而不是追求有约束力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G20为各大国进行协调并管理国际能源市场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制安排,是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良好平台。中国应利用自身在G20的相对重要地位,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全球能源治理;能源安全观;G20;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一带一路”倡议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海外油气资源的日益依赖,开展国际能源合作、保障能源安全开始成为国内共识。中国加入了一些全球和地区性的国际能源合作组织,包括国际能源论坛(IEF)、清洁能源部长会议(CEM)、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等,并与国际能源署(IE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能源宪章条约(ECT)等主要的国际能源组织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早期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主要着眼于双边模式,支持国有企业“走出去”,同时力图建设海外能源运输通道。“走出去”战略①“走出去”战略最初指的是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向海外寻找石油供应,其主要方式是购买海外石油资产,获取权益油。2000年10月提出的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正式提出并加强了“走出去”战略,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主要在非洲、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得以发展;三条陆上能源运输通道包括东北(中俄)输油管线、西北(中亚)油气管线以及西南(中缅)油气管线建成并向国内输送油气,作为传统海上油气运输通道的重要补充。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到2014年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国家对外战略,其中能源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的线路与中国主要的油气进口通道基本重叠,并将与俄罗斯、中东以及中亚的主要油气生产大国联通。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传统的国际双边能源合作的加强版,并得到大力推行。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对国际油气市场依赖的不断增强,要求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呼声又高涨起来。有些国内学者主张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加入国际能源治理,认为加入国际能源治理有助于中国取得国际能源定价权,并在国际能源组织中参与规则制订,更好地保障中国能源安全[1-3]。
本文探讨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纯进口国之后,在寻求海外能源供应安全、参与国际能源合作过程中所持有的主要观念和实践。尽管中国与现有的主要全球能源治理机构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国目前仍然主要依靠传统的双边和地区合作的方式来保障海外能源供应安全。本文认为,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符合国内积极治理空气污染的政策方向,也契合中国倡导的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的做法。鉴于中国在G20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可以利用该平台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1 中国的新能源安全观:参与全球治理
1.1中国传统能源安全观念及实践
中国传统的能源安全观强调地缘政治和战略因素,强调国家安全特性,而不是依赖国际能源市场。相应地,中国政府倾向于直接控制尽可能多的石油产量,并修建更多的陆上输油管道将其运输回国内,避开可能为战略弱点的主要海上交通阻塞点,例如马六甲海峡。“走出去”战略的创立和执行能够为中国获取更多的能源资源。这种传统能源安全观反映了中国的一种信念,即比起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购买,中国公司在海外生产和获取油气和其他能源资源更为安全。
中国对能源供应的不安全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直接控制能源生产、运输的思路,仍然是大部分中国领导人和精英阶层的选择。最近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十年来不断与相关国家签署双边能源供应协定、构建陆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2014年11月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注脚。在国际合作方面,该计划的中期海外能源目标将重点放在能源投资和贸易,以及修建和维护海上及陆上能源运输通道上;重点突出了扩大能源进口通道的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该计划还继续鼓励企业执行“走出去”战略,推动地区能源市场的形成。对于全球能源治理,该计划只是简单提及“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并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性的具备规范和有效监管的全球能源市场”,并没有具体和有意义的举措跟进。
按照这种战略,中国崛起为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可能在许多方面对现存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构成挑战。中国通过外交途径签署能源生产和供应协议来保障能源需求的方式,让部分国外人士觉得有损自由贸易准则,违背被广泛接受的投资协议[4]。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依靠高于市场价格的出价和附带大量社会和经济投资承诺的独特投资方式,引起了国外公司对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怀疑甚至是不信任,他们认为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决策是中国政府的决策,其投资更多是服务于中国的大战略而不是能源政策,而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是中国地缘政治大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且,基于地缘政治的能源战略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政治挂帅的战略思路和沿线国家较差的投资环境决定了“一带一路”含有巨大的经济风险,有可能给中国带来巨额经济损失。尽管追求能源多元化的战略无可厚非,但如果囿于“马六甲困局”的地缘政治思路,过分强调不惜一切代价修建困难的陆上能源运输通道,忽略其可能的巨大经济和政治风险,则可能引起更多麻烦,无助于提高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
1.2中国的新能源安全观
事实上,中国的能源安全主要还是依赖从国际能源市场上购买所需能源,主要进口能源也是依赖海运,而不是“走出去”战略以及战略石油输油管线和陆路运输,市场规律仍然发挥主导作用。2012年,中国国家能源局首次宣布中国公司在海外生产的权益油90%以上都在当地出售,此举为国际石油市场和稳定做出贡献[5]。
2006年以来,一种主张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新能源安全观逐渐发展起来。当年7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呼吁通过更多国际合作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有必要进行主要能源出口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对话;他强调通过集体努力来维护主要产油区的稳定并确保国际能源通道的安全,呼吁能源安全问题的去政治化以及能源技术和研究的发展。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强调通过国际多边合作保障来解决能源问题,这与他三年前关于“马六甲困局”的说法相反②据报道,在2003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主席表达了对中国石油进口安全的担忧,指的就是所谓的“马六甲困局”。参见:石洪涛.中国能源安全的潜在威胁:过度依赖马六甲海峡. 新华网2004年6月15日报道。http://new s.xinhuanet.com/w orld/2004-06/15/content_1526222.htm。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石油进口安全有可能在海上交通咽喉要道例如马六甲海峡被切断,面临着重大风险。这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能源安全观对中国能源安全挑战的认识。。尽管胡锦涛主席在八国集团的讲话更多是理念宣扬,缺乏具体的措施,但这仍旧标志着新能源安全观在中国的出现。
2011年7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席、前副总理曾培炎在“博鳌亚洲论坛”关于“能源、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会议”上提出,在G20框架下建立能源资源的全球稳定机制。2012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第五届世界能源大会上倡议,在G20框架下建立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由G20主要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组成;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和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并通过协商和对话发展早期预警机制、价格协调、金融监督以及紧急机制。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就全球能源治理提出具体建议,并清楚表明在G20框架下构建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思路。
自2007年左右开始,国内学术界质疑中国传统能源观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学者们认为,马六甲海峡及其他能源运输通道的真正危险来自和平时期的海盗、恐怖主义和海难事故,而不是美国的战时封锁,因为后者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是非常不可能的,属于假问题[6-9]。一些一直持传统能源观的学者也开始认为,应该停止争论,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寻求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来源,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10-11]。
自温家宝总理于2012年提出在G20框架下构建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后,政府内部学者开始研究并出版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计划,讨论中国如何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特别是在G20框架下的能源治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出版了在G20下“构建大宗商品能源资源全球治理机制”的报告,认为G20的权力结构和机制构成有着很大的成本优势,以G20为核心构建全球能源资源市场治理是可行的[12]。2014年2月,国家发改委下属的能源研究所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研究所联合发布了关于“全球能源治理与中国的参与”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认为G20能够通过成立新的能源工作组,为全球能源治理改革提供领导力;G20能够为领导人讨论能源问题提供一个重要的代表性平台。该报告还为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如何制订更具国际视野的能源政策,以及更好地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的能源政策以促使其客观地理解这些政策等,提出了政策建议[13]。国家发改委的研究团队由政府内部学者和退休官员组成,报告的建议表明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态度。
新能源观的发展对于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意义重大。胡锦涛主席2006年的讲话和温家宝总理2012年的倡议分别建议中国参与G7/G8与G20的全球能源治理,代表着两个关键的政策转变,表明了中国日益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态度。
1.3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中国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从另一个方面代表着新能源安全观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成为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逐渐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高速发展伴随着巨大的低效的化石能源消耗,特别是中国对煤炭资源的严重依赖,使得中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日益增大的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压力,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更增加了这一压力。所有这一切都推动着中国寻求更为灵活和现实的途径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在一些关键领域,中国表现出来更为积极的态度。中国改变了此前对于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所持的怀疑态度,也改变了其一直坚持的观点,即发达国家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以应对气候变化,转而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来获取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14]。中国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也表现出来更高的热情。在中国看来,打造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希望的领域之一。
在2007年发布的第一份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中,中国将气候变化定义为一个发展议题[15]。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努力的动力源泉主要来自国内的经济发展目标。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中国可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同时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这样一种战略下,中国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在水电、风能发电和太阳能发电方面均取得很大进步。
中美两国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宣布了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声明,标志着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进展。毫无疑问,中美气候变化声明将鼓励世界其他国家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经过两周艰苦的谈判,各国最终于2015年12月12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会议,即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中国目前鼓励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能源战略调整,将保障中国在中美气候变化共同声明中的承诺能够实现。强调转型和创新发展的经济“新常态”模式,表明中国领导人接受了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而环境保护和清洁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构成了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新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什么提倡发展低碳经济。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保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中国大部分城市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以及公众对此问题日益密切的关注和不满,推动着中国领导人近些年来将环境保护的目标提升到最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上对所谓的“APEC蓝”做出的正面回应,也表明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加强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的认可和支持。
2 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情况
为消解中国通过地缘政治战略寻求能源安全所带来的怀疑和不信任,一个合理的应对策略是中国广泛加入现有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国已经表现出加入其中的愿望和意愿,并开始付诸行动。目前中国已经与几乎所有的国际和地区能源治理机制建立合作关系,但普遍来看,这是一种一般性和低层次的合作;与主要的国际能源机构,例如IEA、OPEC以及ECT的实质性的有效合作关系还没有建立。
阻碍中国实质性加入全球能源治理的原因包括:第一,中国的主要重心还是在通过地缘政治战略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一带一路”加强了这一战略,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目标还没有提高到同样的高度。第二,中国对于全球能源治理的有效性及其可能给自身带来的益处还持怀疑态度,这使得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意愿不强。目前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由于其自身的不足,例如碎片化,缺乏执行力,主权国家能源政策安全化和政治化,以及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从而导致缺乏权威性,信誉不高。第三,国内油气利益集团也限制了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中国加入全球能源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起步是参与全球油气数据共享和透明机制,但当前几大国有石油公司几乎垄断了国内原油和成品油市场,更多的透明度将对其垄断地位形成威胁。换句话说,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将进一步推动国内油气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3 寻求全球能源治理的有限目标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碎片化、缺乏权威性和信誉不高的特征表明,该体系要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还存在很大困难。然而,国际油气领域中市场力量和规则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构成了全球能源治理最为重要的基础,表明全球能源体系有着发挥有效治理的潜力。地缘政治和重商主义的分析框架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石油市场的波动。此外,主权国家也有着建立有效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需要和要求。国际能源组织所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往往是稀缺资源,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具有极高价值[16-17]。主权国家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来实施同样的标准,提升数据的质量,增加各国能源政策的透明度,最终降低交易成本[18]。
以上现实表明,追求一个全面且有约束力的全球能源治理或许不是一个现实目标,而寻求建设一个有限目标的全球能源治理协调体系更为合理。
3.1寻求有限的协调目标
建立一个有约束力的、新的、全面的国际能源治理组织并不现实,全球能源治理的“有限目标”应该是有效协调政府间的政策,保障稳定的能源供应和能源可获得性,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总体来说,这种协调目标能够保障最为基本的能源治理因素:市场机制纠错;提高市场透明度,并进行信息共享以降低交易成本;应对外部事件的冲击;为市场交易制度和规则制订标准。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协调各政府间的能源政策,强调主权国家和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互动,以及各大能源国际组织例如IEA、IEF、OPEC、G7以及G20之间的合作。
然而,现实情况是有效的国际能源协调机制多数情况下仍然难以实现,实际可实现的协调目标还应该更具体和更小范围。近期可着重于提高国际能源市场的透明度,提高政府间、国际组织间、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的可信度。这种协调机制的目的是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在执行机制层面,全球能源治理应该着眼于“软性”规则和制度,即在不同国家领导人之间构建政治共识,自愿承诺,同行审议压力,以及提供激励。
3.2将重点转向清洁能源和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治理问题
转向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治理这两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可以为全球能源治理提供持续的动力,虽然它们本身也会加剧全球能源治理的困难和复杂程度。气候变化问题同时涉及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治理中的最根本问题。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领域安全性相对较高,经济民族主义相对较弱,并可以适当减轻由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作用增强而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以条约为基础的治理机制,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发挥重要作用,更多有约束力的目标也是可以期待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消费中比重的提高,将极大地促进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虽然全球环境治理的统一组织仍然缺失,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框架下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有192个成员,除了美国之外的191个成员都已经签署③参见:http://new sroom.unfccc.int/about/.。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要规则的制订者。自从《京都议定书》签署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谈判,已经在气候变化治理方面取得不小进步,但仍然需要一个国际治理机制来有效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各种目标和框架,推动低碳政策和技术的发展和扩散。2014年11月,中美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之间达成的气候变化协议,为全球碳排放消减目标的达成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激励。最终两国为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签署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庞大产业,能够为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问题上,主要关注点应该是如何塑造一个机制来推动该行业发展,提供基于知识产权保护之上的技术传播。在这方面,可以使用一些现存的机制来促进此目标的达成。一个考虑是将2014年7月发起的WTO环境商品协定(WTO 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谈判扩展到包括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这样的话,新的能源技术将能推动能源安全和减轻气候变化。
4 推动G20框架下全球能源治理的有限目标
4.1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与成就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迅速崛起。这为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作为联系各大国的一个全球高端论坛,G20被认为是能更有效地协调各大国之间的政策和行动,协调各国际组织,突破机制制约的合适平台[19]。该组织的三个特点证明了为什么G20能够在全球能源治理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一,通过发表公开声明,G20能够提供关键的政治共识,鼓励行动意愿。G20成员中包括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到全球GDP的85%。第二,G20灵活的机制安排是其发展成为有效的全球能源治理舞台的另一个优势。G20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之间灵活的机制安排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为处理全球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这为未来全球能源治理的合作机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线图。换句话说,G20与IEA、国际能源论坛等的机制合作或协调将是未来全球能源治理的一条可能的捷径[20]。第三,G20成员包括了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众多重要角色,以中国、印度和美国为代表的最为重要的能源消费国,以及沙特、俄罗斯为代表的最要的能源生产国。它包括了全部G7成员,它们大都是能源消费大国。
自从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论坛以来,G20与其他国际能源组织之间的合作已经为其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良好基础。IEA从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就开始为G20提供支持。2011年以来,抑制国际石油市场、天然气市场以及煤炭市场的价格波动成为了全球能源治理的首要问题。IEA、IEF以及OPEC一道,于2011年7月向G20提交了如何提高联合组织数据机制(Joint Organisations Data Initiative, JODI)数据库的质量、时效以及可靠性的报告,并于当年10月提交了呼吁G20将抑制石油市场波动性的工作延伸到天然气和煤炭市场的报告。2012年6月,这三家机构再次向G20财政部长提交了关于增加国际天然气和煤炭市场透明度的报告④以上三个报告参见IEA网站:w w w.iea.org/aboutus/globalengagem ent/g20/ieacontributionstotheg202009-2015/.。2014年7月,JODI天然气国际数据库正式启动⑤J ODI天然气国际数据库包括全球能源数据供应链上数百家利益相关者所进行的有度沟通和协调。随着J ODI石油机制的成功,J ODI天然气机制代表着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话的另一个具体明确的成果,将进一步提高能源数据透明度,推动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源安全。更多信息可参见J ODI网站:www. jodidata.org/new s/official-launch-of-the-jodi-gas-w orld-database.。
就像在全球金融领域一样,G20具有在最高层次的能源政策方面成为领导地位的潜力[21]。它能够为未来的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现代和有约束力的战略,惠及所有国家[22]。截至目前,G20已经在两个重要的全球能源治理方面取得成就。一是在遏制石油价格波动以及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市场透明度方面做出的努力,具体来说就是JODI机制的建立和改善。二是在分阶段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方面做出的努力。化石燃料补贴被认为全球变暖的一大原因,每年耗费发展中国家大量资金。
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是G20在全球能源治理领域取得的另外一个成就。它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由美国倡导成立。这个多边机构从2011年戛纳峰会开始向G20提交报告。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一年,清洁能源部长会议响应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关于核安全行动计划的号召,在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宣言中宣布,建立一个多边合作的全球核能责任机制。这些成就对于解决全球能源治理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4.2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局限
2011年以来,G20与其他国际能源组织的合作进展不大。目前,通过G20平台提高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透明度和改善信息共享机制,是相关国家合作的一个主要方面。相关国家进一步的政治支持对于改善JODI数据的可靠性和相关度非常重要;G20成员国为JODI研讨会的召开提供资金支持对该机制的发展也很重要。简单来说,一个包括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的全面的权威的JODI数据库可以有效提高全球能源治理水平,它应该成为全球能源治理机制近期的主要目标。
实现分阶段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目标进展缓慢。它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就已经成为确定目标,此后尽管每次G20峰会都会敦促达到此目标,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被看作是G20失败的一个例子,被用来反对G20卷入全球能源治理。在2012年G20洛斯卡沃斯峰会上,各国财长被要求建立一个自愿的同行审议程序。它要求各成员国之间进行自愿的评价,但该程序由于其自愿特征,在设立之后进展缓慢。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发表共同宣言,同意就低效的化石燃料补贴共同进行同行审议。这是该程序的一个有力推动。随着中美两国第一轮同行审议的进行,涉及其他国家的第二轮同行审议在2015年中期开始启动[23-25]。
无论是JODI能源数据机制还是取消化石燃料补贴都进展缓慢,其背后的主要原因与G20本身的机制属性有关。G20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机制,在碎片化的全球能源治理领域,它无法像一个真正的政治执行委员会一样去行动。此外,能源被赋予了战略和安全涵义,各国政府都不愿积极参与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正式多边能源国际机制,而更愿意加入包括自愿参加的、程序非正式的能源国家集团组织。G20本身并未将能源议题列入其最为重要的议程上,这样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所需要的政治意愿也就更小了。
部分学者建议成立一个G20能源专门工作组,负责制定全球能源治理的战略性规划,一方面制订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代表能源领域具有重要责任的国家提供政治激励,解决全球能源问题⑥Lesage 2011。也有学者建议建立一个常设但灵活的机制网络,由G20以及多边能源组织的官员组成,类似金融稳定委员会(FSB)[26]。但G20面临的以上限制因素使得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全球能源治理需要找到新的驱动力,或许中国更加积极地加入全球能源治理能够为其提供所需要的动力。
5 中国通过G20框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通过参与G20峰会,中国进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舞台,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中国需要在G20上发挥领导作用,为国际能源合作创造一个政治框架。在G20框架下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可能给中国带来低成本的巨大收益。
首先,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选项。G20已经显示出它在全球经济增长、金融治理、能源和发展方面的成就,G20框架下的能源治理展示了保障能源集体安全的可能性。比起地缘政治战略来,它的经济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也没有政治风险。它最需要的就是领导人和精英阶层转变观念,投入更多的智力和人力资源,以及更多的政府机构的参与,它所能取得的潜在成就远远高过地缘政治战略。
第二,通过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可以平息对此前“走出去”战略为代表的地缘政治战略带来的对中国意图的怀疑和不信任,改善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形象,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中国由于其巨大的油气进口量、独特的投资方式以及较少参与国际能源市场治理,被认为是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巨大挑战。如果中国能够在G20框架下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这将成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信号,表明中国可以成为全球能源治理上的一支建设性力量。
第三,中国应利用主办G20峰会等机会,寻求通过G20平台,将能源治理列入优先议程,并加入国际能源机构IEA。在全球能源治理的众多国际组织中,IEA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发展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最终组织”。有学者认为,尽管有着成员资格的限制,IEA仍然处在全球能源治理许多问题的中心⑦Florini 2011.。作为非成员的伙伴对话国,中国目前与IEA在许多方面有合作⑧中国科技部与IEA建立了政策研究和良好的沟通渠道,与其下属40多个研究中心有着国际科技合作协议。截至2013年,中国的科研机构参加了19个IEA的能源技术合作执行协议,并定期参加IEA的高级技术委员会。。IEA曾经表达过让中国加入其中的意愿。IEA前总裁曾表示,如果中国有强烈意愿加入IEA,IEA可以考虑修改成员国资格的条款[27]。换句话说,加入IEA的关键条件之一——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国⑨另外两个条件是:战略石油储备达到90天;成员国间的数据收集和共享。——将不会成为绊脚石。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加入IEA意味着能源供应安全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接受依靠国际市场和全球能源治理来保障中国能源供应安全,需要较大的决心和意愿。
第四,实质性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能够帮助中国取得一直追求的国际油气市场上的定价权。中国能源进口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在国际市场上总是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油气。有几种方式可以帮助中国改善现状:1)协调战略石油储备,实质性加入全球能源治理机制;2)将“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升级为“上海原油期货交易中心”;3)参与国际原油交易⑩2014年12月,中国证监会批准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其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进行原油期货交易。。以上三个途径都可以通过G20这个平台来实现。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实质性的动作,包括在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上同意公布石油库存数据,同意与美国率先开展低效化石燃料补贴的同行评议。如果中国更多地在G20下参与联合组织数据机制(JODI)建设全面的油气数据透明机制,将有助于“上海原油期货交易中心”建立透明的机制和有效的监管。
第五,通过参与全球合作,有利于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交流和创新方面获益,并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目标。能源技术特别是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与转移对于实现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非常重要,而G20正是推动能源技术合作的理想平台。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以及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IPEEC)都是致力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合作以及提高能源效率的国际机制,它们正在构建或者已经通过G20能源效率行动计划建立了同G20的工作关系。
6 结论
比较目前保障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的两种途径,无疑地缘政治战略仍然是主要手段。且不论哪种战略更具优越性,对于当前的决策者来说,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如何协调两种途径。最新的“一带一路”战略虽然仍是加强版的“地缘政治战略”思路,但也包含了一些可以促进中国更多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的因素。如果中国能够在有效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作用,这样既能满足中国联通沿线各国、构建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能帮助沿线国家。
G20作为全球治理平台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通过与国际机构资源和力量的协调来推动自身议程的建设,例如G20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关系。同时,G20是为数不多的中国可以发挥领导作用的国际机制,中国可以借助G20平台比较快捷地参与到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中来。中国应该推动G20能源工作组与主要的国际能源组织——IEA、OPEC、ECT等建立起密切联系,建立起全球能源治理的基本框架。考虑到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碎片化、缺乏权威性的现实,建议优先着眼于有限的目标,例如改善国际油气数据共享机制,提高透明度,加强全球清洁能源合作,稳步推进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等,而不是追求有约束力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
[1]管清友, 何帆. 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国际能源合作[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11).
[2]徐斌. 市场失灵、机制设计与全球能源治理[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11).
[3]于宏源. 全球能源治理的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J]. 国际安全研究, 2013(15).
[4]GOLDTHAU ANDREAS, WITTE JAN MARTIN. The Role of Rules and Institutions in Global Energy: An Introduction[M]// GOLDTHAU ANDREAS, WITTE JAN MARTIN (eds.).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The New Rules of the Gam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2010.
[5]王小聪. 国家能源局:中国海外权益油90%以上当地销售[EB/OL]. 财新网,2012-12-3. http://companies.caixin. com/2012-12-03/100468168.html
[6]赵宏图.“马六甲困局”与中国能源安全再思考[J]. 现代国际关系, 2007(6).
[7]ZHANG Zhongxiang. Why Are the Stakes So High?Misconcep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China's Global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 2012.
[8]MCKAY Huw, SONG Ligang. Rebalancing and Sustaining Growth in China[M]. ANU e-Press, Canberra, Australia. Co-published with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Beijing, China. 2012.
[9]廉薇. G20框架下我国的国际经济战略[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3-08-26.
[10] 杨泽伟. 中国能源安全现状暨战略选择[J].人民论坛, 2009(276).
[11] 吴磊.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战略形势与对策[J]. 国际安全研究,2013(5).
[12] 范必, 等. 构建大宗商品能源资源全球治理机制[J]. 财经,2012-03-31.
[1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研究所.《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与中国的参与》征求意见稿[R]. 2014.
[14] 张海滨. 中国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J]. 国际政治研究, 2007(1).
[15]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EB/ OL]. 2007-06-04. http://www.ccchina.gov.cn/WebSite/CCChina/ UpFile/File189.pdf.
[16] HARKS ENNO.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 and the Mitigation of Oil Market Risks[M]// GOLDTHAU ANDREAS,WITTE JAN MARTIN (eds.).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The New Rules of the Gam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D.C. 2010, 247-267.
[17] VICTOR DAVID G, YUEH LINDA. The New Energy Order[J]. Foreign A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0.
[18] BACCINI LEONARDO, LENZI VERONICA, THURNER PAUL W.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Trad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J].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013(39): 192-216.
[19] DUBASHN AVROZ K, FLORINI ANN. Mapping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J]. Global Policy, 2011,2(9) special issue.
[20] FLORINI ANN.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J]. Global Policy, 2011,2(9), special issue.
[21] HIRST NEIL. The Reform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R]. Discussion Paper, No 3, Granth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2012.
[22] LESAGE DRIES. The Time has Come for a G20 Energy Task Force[R]. G20 Cannes 2011. The G20 Information Center,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1.
[23] G20 Brisbane. G20 Energy Sustainability Working Group 2014 Co-chair's Report 2014[R]. November 10, 2014.
[24]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15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Joint US-China Fact Sheet - Economic Track[EB/OL]. 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 Pages/jl0092.aspx.
[25] IEA, OECD. Update on Recent Progress in Reform of Inefcient Fossil Fuel Subsidies that Encourage Wasteful Consumption[R]. Submitted to G20 Energy Ministers' Meeting, Istanbul. October 2,2015.
[26] VICTOR DAVID G, YUEH LINDA. The New Energy Order[J]. Foreign A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0.
[27] 王尔德, 危炜. IEA需要中国, 中国也需要IEA[N].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07-09.
编辑:王立敏
编审:萧芦
China and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under the G20 framework
HE Xingqiang (Alex)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anada)
China retains a bilater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pproach or a geopolitical strategy to secure its energy supply security, while it has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with major institutions in the existing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ergy supply, China's new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tributes to a 2.0 version of its current bilater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pproaches. China has sought to participate more actively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and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and developed clean and renewable energy since early in the 21stcentury. But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was afected by the fragmented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s neither authoritative nor credible and the lack of willingness or impetus for its own domestic energy institutions to join the system.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fculties and problems of current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t is reasonable to pursue the limited goals such as improving data-sharing mechanisms, promoting its transparency and steadily pushing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clean energy governance for coordinating regimes instead of creating coercive global institutions in this feld. The Group of Twenty (G20), should provide a signifc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coordinating major powers'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s and climate change, as an appropriate platform for achieving the goals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China, with its relatively important status at the G20, should participate more actively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energy security concept; G20; renewable energy; climate chang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16-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