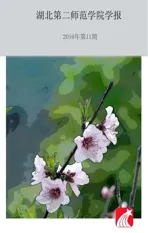环境法与环境伦理的关系:美国环境法学界研究的状况
2016-03-16曹胜亮
黄 莎, 曹胜亮
(武汉工程大学 法商学院, 武汉 430070)
环境法与环境伦理的关系:美国环境法学界研究的状况
黄 莎, 曹胜亮
(武汉工程大学 法商学院, 武汉 430070)
自环境法诞生四十多年来,环境伦理给环境法多大的支撑、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等理论与经验问题在美国环境法学界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而梳理这些讨论,也有助于我国环境法学界思考环境法与环境伦理的关系问题,并进行沟通与对话,进而建立制度和措施来促成研究的实践效应。
环境法; 环境伦理; 自然权利
自环境法诞生以来,环境法与环境伦理的关系就是学界的一个重点研究问题。这可能缘起于法律与道德的密切关系及其衍生的经典对话,如著名法学家富勒与哈特的辩论。①四十年来,环境伦理给环境法多大的支撑、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等经验与理论问题在美国环境法学界一直是一个讨论的热门话题。我国法学界虽然也对美国学界的这些动态有所讨论,但是还没详细的梳理。而观察、梳理和总结美国环境法学界的研究状况,有助于我国环境法学界思考环境法与环境伦理的关系问题,并进行沟通与对话,进而建立制度和措施来促成研究的实践效应。
一、斯通教授开天辟地的贡献
1972年,正处于一个导致环境法诞生的骚动和变化的时代中,美国著名法学家、环境法学的奠基人克里斯托弗·斯通(Christopher Stone)教授发表了一篇迅速成为经典的论文——《树是否应该有诉讼资格?——朝向自然客体的法律权利》。[1]在这篇论文之前,已经有一些论者提出自然应当具有伦理地位。例如,美国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就是其中一位。他可以说是斯通教授的上一代人,在散文集《大地伦理》(The Land Ethic)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呼吁。[2]斯通的文章阐述了一些关于道德立场的重要见解,如必须智能化地关爱自然。[1]但他的开创性贡献不仅于此,而更在于他强调了法律的作用。质言之,斯通将环境伦理引入环境法的核心贡献在于为把自然的伦理权利纳入法律提供了一个框架。
利奥波德强调土地所有者的伦理责任,而这种责任需要通过社群规范、社会压力和内在良心的运作来实现。[2]209然而,斯通并不认为这些实施机制是充分的。他认为法律能够也应该承认自然客体有价值和尊严,从而也有权利。他认为,自然实体如果要成为合法权利的拥有者而不是权利的对象,那就应当具备三个基本要素。[1]首先,自然实体必须能够发动法律程序,即有资格在法院提起诉讼。其次,在确定赔偿时,法院必须直接考虑对自然实体本身的伤害。最后,所给予的法律救济必须按照自然实体的利益来运作而不是按照与之无关的人的利益来运行。
斯通指出,即使完全采纳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承认自然实体的固有法律权利,在许多情况下也是有益的。除此之外,承认自然实体本身承载权利,将有利于坦诚交流,而现有的法律是抑制性的,即限制了法律权利的主体范围。而且自然实体的权利可以作为一个法律拟制,有利于聚集高度分散的人之利益,其中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与功利主义的论点不同,斯通认为,即使缺乏支持者的认可,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毫不避讳地讨论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人的利益应该尊重甚至让位于自然的权利。更进一步,斯通宣称,法律修辞从人之权利转向自然的权利,将使法院乃至整个社会本身都会选择更好地保护环境。[1]斯通的论述预示着后来的法学表达、文化以及构成要素的变化。②
斯通教授绝不是在象牙塔里从事纯学术活动,他写作的背景是重要的现实世界的事件。当时,美国林务局刚刚授予沃尔特·迪斯尼企业(Walt Disney Enterprises)许可证,允许其开发矿产国王峡谷(Mineral King Valley)一处滑雪胜地——一个未开发的荒野区。美国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认为这一开发许可会破坏当地环境,因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许可证。美国第九巡回法院拒绝了塞拉俱乐部对该许可证的挑战,理由是塞拉俱乐部缺乏诉讼资格。[3]当最高法院同意审查该案时,斯通赶紧完成上述论文,希望它能影响法院的考量。矿产国王峡谷案提供了一个及时的机会,让法院认可自然本身的权利,由其保护者塞拉俱乐部来代表,而不是坚持这一立场:塞拉俱乐部必须展示其成员利益受到伤害而获得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资格。
从整体上说,法院并没有采纳斯通的理论,[4]但也有一丝浮出地平线的革命。道格拉斯(Douglas)大法官在他的异议书中明确赞同斯通的分析。③而且《树是否应该有诉讼资格》在美国参议院得到热烈讨论,并重印在国会记录中。美国似乎要走向世界前沿,准备将道德和法律推理和谐地结合,以保证严格地保护环境。
自从《树是否应该有诉讼资格》发表以来,许多变化出现了。人们已经认识到,对待自然实体时应超越过于狭隘的自然可能会给人类提供经济利益这样的观念。这股环保热潮催生了联邦和各州的保护环境部分,包括空气、水、海洋哺乳动物、濒危物种、湿地和野外河流的法律和法规。这些立法大大拓宽了法庭应当考量的利益范围。这些立法并不总是要求自然的利益优先于人类利益,恰如斯通在1972年所指出,权利不需要绝对实在。[1]
斯通给予自然实体法律权利的其他两个标准没有得到完全实现。在美国某些案件中,法律补救办法特别专注于自然实体。例如,石油污染法和超级基金法要求自然资源损害赔偿金只能用来恢复或补救自然系统的损害。[5]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违反环保法律的处罚必须上缴到国库。因此,美国公民诉讼尽管可以获得制止有害行动的禁令,但是不能获得金钱赔偿来扭转这些影响。
在斯通所提出的三个标准中修辞上最强有力的一个标准——允许自然物体本身具有诉讼资格,所取得的进展也相当有限。在法庭上解决人们保护自然的多样化或非经济利益的实际问题方面,已大幅改善。在Sierra Club v. Morton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明确指出人类的非经济利益可以使起诉者具有诉讼资格,即娱乐和审美利益受损也可以提起诉讼。环境立法中的公民诉讼条款扩大了法律保护利益的范围,而且通过允许获得律师费用而降低了诉讼的经济障碍。但是,环境法尚未承认自然物体自身的权利,及其基于这种权利而拥有受保护的法律利益。
二、曲折复杂的议论
自1972年以来,向政策制定者所提出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显著改变。当时讨论的关键问题,也是最基础性的问题:缺乏明显的经济价值的自然是否应当得到认真对待。今天,这个问题可能已经过时了。这样的自然事务已经司空见惯了。很难想象当代美国政客竞选的主题是我们应该坦率地忽略我们的行为对自然界的影响。[6]而自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境立法高峰期之后,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
针对这样的情形,1996年,美国环境法学家丹·塔洛克(Dan Tarlock)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环境法和环境管理应该主要从科学而不是从伦理中获得政治权力和合法性。[7]塔洛克教授还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故意挑衅的宣称,因为它与环境法的多元正当性相悖。多元主义认为环保主义可以平等地从多种合法性资源中获得支持。例如,我们可以借鉴科学、对自然的浪漫传统以及新康德伦理学来正当化环境保护。因此,多元主义有助于环境运动。如果科学不支持,就转而求助于浪漫主义思潮,如果还不够,可以再寻求道德哲学的支持。然而随着环保主义的成熟,合法性问题变得更重要,环保主义的多元主义基础也更有问题,因为其合法性太具有偶然性了。
塔洛克教授继续论述道:由于环保主义是异于西方传统的,所以应采纳合法性问题的多元主义路径。这种价值多元主义是对环境法合法性来源贫乏却符合逻辑的创造性反应。迅速地接受环境保护作为政府管制的合法性基础改变了意识形态争议和政治行动的规范关系:行动先于理论。关于环保主义基础发展出丰富、多样和矛盾的理论文献是为大众主权提供事后的合理化依据。公众看上去无条件地接受环境管制,这免去了环境运动艰难的合法性问题。[7]
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已经没有推出任何重大的环境立法,这也使得有人惊呼环保主义已死(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8]面对环境伦理与环境法这种貌合神离的状态,美国环境法教授霍莉·多利摩斯(Holly Doremus)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微妙:何种自然面貌值得考虑,考虑到哪种程度?何时可以明确人类的物质利益应该服从大自然的福祉?谁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又如何构建一个恰当保护大自然的社会?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道德与法律推理。我们正处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环境法交替的时刻,是时候问一些关于环境道德和环境政策之间关系的问题了。我们的环境伦理观念已经进步到何种程度,是否足以支持我们做出艰难的政策选择?在环境决策中,环境伦理究竟扮演什么样的不同于经济或自然科学的角色?我们是否有将环境伦理纳入到政策选择中的合适途径?如果我们关于伦理问题缺乏共识时,我们还能够找到共同政策的基础吗?我们是否要寻求一些务实的妥协,或者说找出更具体的道德直觉来构成我们的选择基础是否重要?是否只存在从伦理到法律的单向路径,还是说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回馈环,让政策选择也在伦理发展中发挥作用?[6]
2003年4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聚集了一些著名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以及相关议题提出看法。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环境伦理与政策:让哲学脚踏实地”。会议的发言人不仅有法律学者和哲学家,也有来自政策制定和实施领域的实践专家。会议论文后来发表在《加州大学戴维斯法律评论》和《加州大学戴维斯环境法律与政策杂志》上。
在这次会议上,斯通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为研讨会定下了基调。在演讲中,他问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关伦理何事?[9]他指出,作为一个经验问题,使用电脑数据库就可以确定法院和立法机关在何种程度上公开参考了环境伦理的理论和原则。他的结论是:在公共决策中,环境伦理,尤其是非人类中心的那一支,所发挥的作用要小于其他哲学流派。他认为其原因在于,环境伦理学家没能从事界定自然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基础的一系列工作,从而为必须面对艰难的现实抉择的决策者提供充分的参考方案。
另一个主题发言人是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艾莉森·弗卢努瓦(Alyson Flournoy)教授。她提出了强有力的观点,认为环境伦理应该在环境政策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决策背后的伦理必须加以澄清。[10]弗卢努瓦教授基本上同意斯通教授的这一观点:环境伦理学在环境法的精细结构的发展方面起到的直接作用不大。[11]她认为,没有谈论价值是环境政策的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理解我们寻求保护的事物的价值,我们是不可能有效地保护他们的。为了突出环境伦理,弗卢努瓦认为,我们应着眼于“进步阶梯”,从人类中心的功利主义边际变化开始,而不是要求一个统一、连贯的环境伦理一步取代功利主义。小的变化就能突出关键的伦理议题,进而引发富有成效的社会辩论。而这样做还可以帮助那些在其他方向步履蹒跚、缓慢前行的人们,他们已经对传统的功利主义隐约不满或开始质疑。
哲学家布莱恩·诺顿(Bryan Norton)赞同斯通教授的观点,即环境伦理在政策领域并未发挥重要作用,并认同弗卢努瓦教授的观点,政策领域将受益于关于价值的公开讨论。他将这种现象归咎于环保哲学明显无视这一事实:环境冲突的双方已经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思想承诺而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他们可能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从而可以提供务实的妥协基础。诺顿认为,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环境伦理学家痴迷于“道德 vs. 钱财”命题,力图建立自然的内在价值,与人类中心的功利主义形成尖锐冲突,而这在政策领域已被证明事与愿违。他主张更务实和多元的方案,在其中,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们都愿意承认相互冲突的价值各自的合法性,但他们可以一起审议出富有成效的政策。[12]
与诺顿一样,环境法教授巴兹·汤普森(Buzz Thompson)也关注“财迷”与“卫道士”之间关于环境的刻板观念所引发的尖锐矛盾。在刻板印象中,经济学家只考虑狭义解释的财富的最大化,而道德主义者只考虑不容玷污的固有权利,不容许市场入侵。诺顿敦促道德主义者扩大他们关于合法价值的视野,而汤普森进一步建议他们应该拓宽关于合法的有用工具的观念。他解释说,即便一个人拒绝规范运用经济学来确定社会目标,但经济学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用来识别环境问题的成因、提出减轻环境损害的措施,也有利于克服因政策变化而来的政治阻力。此外,他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以经济为基础的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实际上可能鼓励保护环境利他主义,从而推进环境道德主义者的伦理目标。[13]
美国著名的公法学者丹尼尔·法伯(Daniel Farber)探讨了关于环境问题的科学理解如何能够在决策伦理中发挥作用。大量的科学不确定性是环境问题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一点得到广泛认可。但是,法伯解释说,即使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然而理解不确定性的形态对于我们做出良好的政策选择至关重要。他指出,一些环境问题符合“幂次法则(power law)”分布,在这种情形下,方差极其高,而极端事件就会比常规(钟形曲线)分布下更有可能出现。如果我们能合理地预测哪种环境影响符合幂次法则,那么常常受到批判的风险评估中的保守行为以及运用更强的预警原则就是正当的。[14]
大卫·施米茨(David Schmidtz)和伊丽莎白·威洛特(Elizabeth Willott)在他们的文章中以南非的寂砂禁猎区(Sabi Sand Game Preserve)为案例,展示了从私有财产到共同财产制的自愿转换。他们注意到,与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提出的流行观念不同,[15]共有财产制有时比私有制能够更好地促进合理的环境管理。有限的公有化能够提供管理上的规模经济化,而在有些地区,由于单一所有权规模太小而不能在实践上坚持。施米茨和威洛特研究发现,在寂砂禁猎区,土地所有权人在成功地形成共同的大规模管理的同时还维持了本质上私人小规模管理。他们指出,在这个案例中,共同管理同时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环境利益。他们建议,治理环境的机制应当始终坚持满足生活其间的人们的经济需求。[16]
伦理学家劳拉·韦斯特拉(Laura Westra)为诺顿所批评的环境伦理学的内在价值进路做了辩护。韦斯特拉反对将以经济为基础的条件价值评估和偏好总和作为决策的基础,而这恰恰映证了诺顿的观点,即环境伦理学家倾向于内在定义,而反对经济分析。尽管她呼吁环境权不应因人类偏好来评估,但是她没有将这些权利与人类权利对立起来。相反,她认为,生态完整性的权利,既是大自然的权利,也是人类的权利,因为运转良好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的关键。[17]
哲学家克里夫·雷希特萨芬(Cliff Rechtschaffen)对斯通与诺顿反对伦理学家的观点做出批判。他的具体例证是将环境正义理论的伦理洞见纳入政策决定。他认为,除非将分配问题明确纳入环境决策,否则环境正义无法实现。那么如何将分配问题明确纳入环境决策呢?他的建议是:在制定管制标准时要考虑人们的现实行为以及对敏感人群的保护;应用预防原则并仔细审查替代方案,以减少严重影响到穷人和少数族裔生活水平的活动;在土地使用决策和区域规划时应当公平分配环境影响;在环境影响评估和反应敏感的环境分析过程中设计便于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公众参与的程序。[18]
来自实践领域的李·塔尔博特(Lee Talbot)在联邦环境政策形成时代的尼克松政府中任职,具有丰富的政策经验。他的论文也是对斯通教授的观察的一个回应。他提醒大家注意立法辩论中公共领域以外的因素的重要性,以及斯通教授的研究的局限性。他认为在那个年代,几个关键参与者的伦理承诺对环境法的重要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在有关的历史纪录中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19]
霍莉·多利摩斯回到斯通在1972年论文中率先提出的主题:环境政策的重要影响远远不限于对当前活动的直接管制。多利摩斯认为今日的环境政策必然会影响明日的环境价值,而这些影响也在我们的政策选择中发挥作用。为了确保我们的继任者有机会了解和分享我们的环境价值观,我们应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构建他们的物理环境,让他们能够常常接近大自然;鼓励健全的关于环境价值的社会讨论;突出有害于环境的个人选择,并提供替代这些选择的方案;当我们采用基于市场的政策时应当注意其对这些价值的潜在影响。[20]
行政法学者安·卡尔森(Ann Carlson)聚焦于一种别样的州和联邦管制之间的辩证。她以加州管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例,认为即使在多种冲突的标准无法共存时,我们也应该允许某个州采取更为严厉的管制以鼓励其进行富有进取心的管制实验,而在实验成功后就可以推向全国。[21]
2003年的与会者达成的共识是:道德考量应当在公共政策选择中发挥作用,但是怀疑主义仍然普遍存在。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沟通是良好的伦理决策的基础。真正尝试与他人沟通,特别是是那些基本假设或价值观不同的人沟通,可以帮助消除意识形态的隔绝和对反对立场的妖魔化。[6]
三、新近的讨论
2008年,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罗伯森(Heidi Gorovitz Robertson)教授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生命伦理学从理论哲学演变成一个应用领域,卫生和医疗科学的决策者做决定和制定政策时都会考虑生物伦理学。与之相反的表现是环境伦理学。虽然人们研究环境伦理学,但是主要局限于哲学研究,环境伦理学家并不参与决策。因此,罗伯森考察了环境伦理学和生物伦理学各自的发展,特别是法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生物伦理学中,从伦理原则到行为法则转变的关键是“贝尔蒙报告”(Belmont Report)。
1974年,美国成立了保护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受试者国家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这个委员会经过四年的研究,于1978年发布了“贝尔蒙报告”④。贝尔蒙报告总结了涉及人体试验的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和指导方针。贝尔蒙报告肯认了三条基本伦理原则——尊重个体(respect for persons)、善行(beneficence)和公正(justice),同时具体指出三个应用领域:告知后同意(informed consent)、风险与利益的评估(assessment of risks and benefits)和受试者的选择(selection of subjects)。简言之,贝尔蒙报告为人体实验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道德框架,而且被美国生物医学界普遍接受,后来成为美国人体实验研究行为规则的基础。[22]更进一步,美国医疗侵权案件中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也采纳这一报告所宣布的道德法则,最为典型的是“告知后同意”法则。[23]而这样的法则在我国法学界近些年来就医疗纠纷处理事务问题也常常被提及。[24-25]
罗伯森教授从生物伦理学的贝尔蒙报告得到启发,认为环境伦理学家没能提出一个像生物伦理学上的贝尔蒙报告那样的简洁、一致的指导实践的原则宣言。因此,他认为应当归纳出这些原则,从而指导立法,也有助于鼓励环境决策中环境伦理学家的参与。[26]然而,罗伯森的愿望是美好的,环境伦理学的“贝尔蒙报告”却始终没有出现。因此,依然需要新的理论。
2013年,杜克大学教授杰迪戴亚·普迪(Jedediah Purdy)指出,四十年前,环境法诞生之时,法律和哲学领域的杰出人物都断言,环境伦理学将与环境法这一新领域紧密相连。然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个领域却戏剧性地分开了。普迪教授诊断了这种分离,并推荐二者重归友好。随着公共价值观念的变化,环境法成长起来。由于这样或那样一些原因,如果没有伦理学,环境法不可能发展起来。在环境政治领域中的大量开放式问题上,法律与伦理最为彼此相关:立法者只会在伦理观念清晰浮现时才采取行动,而法律本身又会协助伦理发展。这一过程在一系列新兴议题中都有真实的表现,如食品安全、动物权利以及气候变化。普迪教授观察到:小到人们的日常言语与行动,大到政治选举口号和公共辩论话语,环境伦理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其中,而这反过来又影响食品安全、动物权利与气候变化法律的兴起。他从哲学、历史与心理学角度对这些新兴领域的伦理变化做出了考察,并提出法律改革建议以培育这些伦理发展。他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到新型时代,需要对环境伦理与环境法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即围绕人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来建构伦理命题和法律制度。[27]
普迪教授试图克服环境伦理学长期面临的两大困难:(1)环境伦理学与自由市场主义、功利主义的长期战斗;(2)环境伦理学内部关于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之间的流派争议。他尝试回归伦理学以人为基点的思考,从而融合上述分歧,进而将抽象的思辨转化为法制实践。
普迪教授的研究可以说是对过去40年来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关系问题的经验观察的总结,而且他借助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普迪教授的论文出版后,在2014年被美国环境法律与政策年度评论(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Annual Review,ELPAR)收录为年度最佳环境法学术论文。⑤尽管普迪教授的研究立意高远、论述宏阔,受到广泛好评,但是就基本原则的归纳与具体制度的设计而言,还是显得不足。或许,这些是他后续研究的着重点。我们拭目以待。
四、结语
纵观美国环境法学界的讨论状况,我们可以简短地概括出其基本特点:
1. 环境法确实需要环境伦理作为支撑。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环境伦理都给予环境立法与实践相当的助力。早在美国环境立法的高峰时代,正是由于环境伦理思潮兴起,才使得环境立法获得大众强有力的赞同,也才有各种环保团体针对污染行为的大量诉讼。
2. 环境法与环境伦理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尽管环境伦理为环境法提供了正当性(justification),但是环境伦理如何从信念与原则转换为具体的法律制度与规范,其实环境法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而正是对这种转化的制度渠道的认知不清,才使得人们感概,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分道扬镳了。
3. 环境伦理自身也存在各种弱点,使得其不能为环境法提供基础理论的“脚手架”。由于环境问题的复合性与不确定性,环境伦理自身分裂为各种对立的流派,使得环境伦理并没有出现大一统的理论,因此,环境伦理并不能像启蒙思潮那样为现代法治提供奠基性框架。环境伦理常常表现为口号和标语,并不能有效转化为操作规则。
正是在上述基本特点之下,笔者认为,当下的美国环境法并没有从环境伦理学那里获得更多、更强的理论启迪和思想支援。尽管如此,美国环境法学界还是热切希望能够从环境伦理那里获得强有力的支撑,也不断反思与探索环境伦理与环境法的互动关系。与美国环境法学界对环境伦理与环境法之间关系的讨论之热火朝天相比,我国环境法学界虽然也有诸多论著讨论该问题,但是颇为冷清的是,既没有热烈的专题讨论会,也没有针锋相对的辩驳。中国环境法学与环境伦理学之间仿佛隔着一堵墙,声音相闻,却各说各话。即便在环境法学界内部,也是各位学者各提自家之言,很难见到相互呼应与对话。更成问题的是,学界研究与法律实践的隔绝。
注释:
①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②See generally,e.g.. Holly Doremus, Constitutive Law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22 STAN. ENVTL. L.J. 295 (2003); Richard H. Pildes, The Unintende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Public Policy: A Comment on the Symposium, 89 MiCH. L. REV. 936 (1991); Cass R. Sunstein, On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of Law, 144 U. PA. L. REV. 2021 (2000).
③See Morton, 405 U.S. at 741-42 (Douglas, J., dissenting).
④该报告的全称是“贝尔蒙报告:保护研究中的受试者的伦理原则和指南”(the Belmont Report: Ethic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Research)。
⑤美国环境法律与政策年度评论由美国环境法所与美国范德比尔特法学院(Vanderbilt University Law School)联合举办,每年4月召开。每年,范德比尔特法学院的学生在美国环境法所组织的专家指导下选出该年度对紧迫的环境问题提出最佳的法律与政策解决方案的论文。
[1]Christopher D. Stone. Should Trees Have Standing? - Toward Legal Rights for Natural Objects[J]. 45 S. CAL. L. REV. 450 (1972).
[2]ALDO LEOPOLD. The Land Ethic, in A SAND COUNTY ALMANAC 201 (1949).
[3]Sierra Club v. Hickel, 433 F.2d 24, 33 (9th Cir. 1970).
[4]Sierra Club v. Morton, 405 U.S. 727, 738 (1972).
[5]33 U.S.C. § 2706 (2000); 42 U.S.C. § 9607(f)(1) (2000).
[6]Holly Doremus.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Law: Harmony, Dissonance, Cacophony, or Irrelevance , 27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1 (2003).
[7]Dan Tarlock.ENVIRONMENTAL LAW: ETHICS OR SCIENCE?, 7 Duke Envtl. L. & Pol’y F. 193, 1996.
[8]Michael Shellenberger & Ted Nordhaus. The 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 Global Warming Politics in a Post-Environmental World, available at http://www.thebreakthrough.org/PDF/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pdf.
[9]Christopher D. Stone, Do Morals Matter? The Influence of Ethics on Courts and Congress in Shaping U.S. Environmental Policies, 37 U.C. DAVIS L. REV. 13 (2003),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27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13 (2003).
[10]Alyson C. Flournoy, In Search of an Environmental Ethic, 28 COLUM. J. Envtl. L. 63 (2003).
[11]Alyson C. Flournoy, Building an Environmental Ethic from the Ground Up, 37 U.C. DAVIS L. REV. 53 (2003),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27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53 (2003).
[12]Bryan Norton. Which Morals Matter? Freeing Moral Reasoning from Ideology, 37 U.C. DAVIS L. REV. 81 (2003),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27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81 (2003).
[13]Barton H. Thompson, Jr.. What Good Is Economics?, 37 U.C. DAVIS L. REV. 175 (2003),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27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175 (2003).
[14]Daniel A. Farber, Probabilities Behaving Badly: Complexity Theory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37 U.C. DAVIS L. REV. 145 (2003).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27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145 (2003).
[15]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62 Sci. 1243 (1968).
[16]David Schmidtz & Elizabeth Willott. Reinventing the Commons: An African Case Study, 37 U.C. DAVIS L. REV. 203 (2003),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27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203 (2003).
[17]Laura Westra. The Ethics of Integrity and the Law in Global Governance, 37 U.C. DAVIS L. REV. 127 (2003),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27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127 (2003).
[18]Clifford Rechtschaffen. Advanc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Norms, 37 U.C. DAVIS L. REV. 95 (2003),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27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95 (2003).
[19]Lee M. Talbot. Does Public Policy Reflect Environmental Ethics? If So, How Does It Happen?, 37 U.C. DAVIS L. REV. 269 (2003),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27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269 (2003).
[20]Holly Doremus. Shaping the Future: The Dialectic of Law and Environmental Values, 37 U.C. DAVIS L. REV. 233 (2003),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27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233 (2003).
[21]Ann E. Carlson, Federalism, Preemption,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37 U.C. DAVIS L. REV. 281 (2003),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in 27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281 (2003).
[22]Vollmer Howard,Sara George. Statistical power, the Belmont report, and the ethics of clinical t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16 (4): 681 (2010).
[23]罗秀,蒲川,王轶.美国法中的“告知后同意”理论[J].川北医学院学报,2008,(3).
[24]黄芬.告知后同意规则的法律构造[J].时代法学,2012,(6).
[25]汪冬泉.医疗中告知后同意法则之研究[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26]Heidi Gorovitz Robertson. Seeking a Seat at the Table: Has Law Left Environmental Ethics Behind, as it Embraces Bioethics?, 32 William & Mary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Review, Vol. 32, p. 278, 2008.
[27]Jedediah Purdy. Our Place in the World: A New Relationship for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Law, 62 Duke Law Journal 857-932 (2013).
责任编辑:陶 晖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Law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tatus of Research in the Environmental Law Academia of the United States
HUANG Sha, CAO Sheng-liang
(Law and Business School,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over 40 years ago, many theoretical and experience issues have been heatedly discussed in the environmental law academia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how much does environmental ethic support environmental law, what role should it play, how to better make use of it. Review on these discussion would facilitate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ethic support environmental law for China’s environmental law academia, and prompt communication to establish institutions or tak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environmental law; environmental ethic; nature right
2016-09-09
黄 莎(1982-),女,法学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为环境法。 曹胜亮 (1974-),男,法学博士(后),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法。
D922.6
A
1674-344X(2016)11-0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