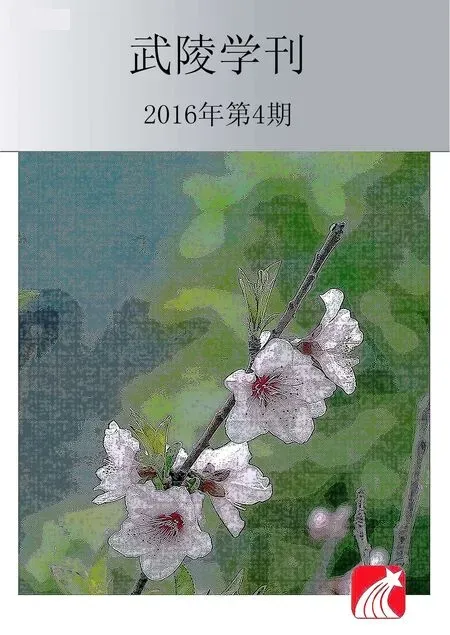常德会战研究综述
2016-03-16周勇
周勇
(湖南文理学院 文史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常德会战研究综述
周勇
(湖南文理学院 文史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战役,常德会战研究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部分。70余年来的常德会战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从时间上看,可划分为初兴期、沉寂期、复兴期和勃兴期四个阶段;从格局上看,研究者和研究内容、领域等方面,都具有开放性和层次性。常德会战研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都是明显的。
常德会战;抗战史研究;综述
1943年11月初至次年1月初,侵华日军对湘西北重镇常德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政府组织军队顽强应战,双方伤亡甚巨,战事之激烈残酷为抗战以来所少见,史称常德会战。常德会战是由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22次重大会战之一,对中日双方的战略、政略都具有一定影响,在军事、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关于常德会战的研究已成为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方面,自常德会战结束7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广度与深度均有拓展,对之加以梳理分析,实为继往瞻来之必具,本文即欲于此稍尽绵力。
一、研究阶段及著述特点
纵观70余年来的常德会战研究,从成果涌现的多少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兴期(1944—1949年)、沉寂期(1949—1984年)、复兴期(1985—1999年)和勃兴期(2000—2015年)。每一时期的研究特点都是鲜明的。
初兴期成果只有6项,数量虽不多,但颇具史料价值。其中,徐浩然的《常德抗日血战史》[1]尤其值得重视,因作者抗战时曾在第57师师部工作,是常德会战的亲历者,故其叙述不仅真实而且具有全局性。此书为其后的同类史著提供了基本的史实框架。黄潮如是战时常德《新潮日报》的副社长,他以实地亲见亲闻的资料而作《常德守城战纪实》[2],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徐、黄二氏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常德会战史著,作者皆是事件中人,其近距离视角在提供真实性的同时,也有缺乏历史反思的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前以爱情小说驰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也被常德会战中守城将士之义勇所感动而创作了纪实性作品《虎贲万岁》[3],此书根据大量一手史料写成,高扬中国军人铁血卫国的民族精神,读来令人振奋。此书于1946年由上海百新书店印行,但建国后因政治环境所限,长期不为人知,直至2007年方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国共两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长期对立,大陆对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正面战场甚少提及,学界研究自然极为沉寂,30余年几乎没有任何成果出现。此间值得注意的成果是由交战双方政府组织编写的系统性战史著作,即由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刊的《抗日战史·常德会战》[4]和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刊的《昭和十七、八年的支那派遣军》[5]。如果说前述徐浩然、黄潮如二人的私家战史之作以战事细节的具体、真实取胜,那么台、日双方的这两部官修战史则侧重于战略决策、战术运用、战事经过、战果总结等整体性、全面性的叙述、分析和评价。这几部战史因视角不同,叙述与评价时有差异,相互参看当有明史之效。
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两岸政治空气的日渐缓和,常德会战研究与其他抗战正面战场的研究一样,出现了升温之势。至20世纪末,见之于期刊的研究论文有12篇,其数量虽然尚不算多,但已经充分注意到常德会战在抗战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如毛申先的《常德会战述评》[6]、郑立的《论常德会战在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7]、龙子的《常德保卫战考辨》[8]、徐伟民的《开罗会议后第一个大捷——常德会战论略》[9]等均对战役进行了全面的肯定评价。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出现了周询的《抗日时期常德会战》[10]和龙佑云主编的《孤城血拼——常德会战始末》[11]两部较全面论述常德会战的史著。较之上一时期官修战史的“以史代论”,周询、龙佑云的著作明显加强了论的成份,研究性更强;比之徐浩然、黄潮如之作,则更具理性色彩,可谓后出转精。长期致力于地方史志编纂的叶荣开于1995年主编了常德会战资料集《中日常德之战》①,资料收罗丰富,亦有创见,是一部资料纂辑与研究并重的著作,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相当的便利,但限于当时条件,此书只以内部资料发行,未经出版社出版,故影响受限。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成果仍以整体论述居多,对战事各个侧面和细节问题较少深入涉及。
本世纪以来,常德会战研究逐渐受到关注,成果明显增多且视角多样,学术性亦显著提升。10余年间共发表报刊文章74篇,涉及会战各个方面。发表这些成果的主要阵地有三:一是《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现名《武陵学刊》),是常德唯一的本科院校主办的学术期刊;二是《黄埔》,是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主办的双月刊;三是《常德日报》,是中共常德市委的机关报。这说明,常德会战研究在传播、影响方面具有较明显的地方性特点,这也正是学术研究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的体现。这其中,《湖南文理学院学报》刊发的常德会战研究论文,最具学理性。不仅有全面论述之作如罗玉明的《常德保卫战简论》[12],更有深细多元论析的好文,给人以启发性,如樊昌志《常德会战中常德守军的战场传播》[13]、朱清如《试论日军在常德会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14]、陈致远《常德“抗战碉堡”质疑》[15]等。《黄埔》杂志和《常德日报》所刊发的会战文章以人物研究和史事钩沉为主,作者不仅关注到了余程万、彭士量、孙明瑾、柴意新等将领,还将目光投射到会战中的一般将士,如叶荣开的《常德会战中英雄营长杨维钧》[16],刘凌《常德会战中的西班牙主教》[17]。这些成果对于突破既有的战争人物研究是有益的,它使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走近战争中的人,从而理解战争。
专著方面,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朱清如历时10年精心结撰的《常德会战史研究》[18]于2014年出版。作者在查阅、比勘文献资料和实地寻访遗迹、人物的基础上全面还原了战争过程,探索了战争发生的背景、缘由,对中日双方的政略、战略、战术做出了力求贴近历史的研判。全书共12章,内容完整丰富。朱清如认为:常德会战从属于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常德会战中,中国军队打出了军威,提高了中国军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国际威望,增强了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基本粉碎了日军实施“常德作战”的真正意图,客观上与敌后抗战相呼应;常德人民对中国守军的大力支持也是会战后期日军被迫北撤、中方最终获胜的重要因素。该书是继徐浩然、黄潮如、周询、龙佑云等人所作之后又一部关于常德会战的专门战史研究著作,尤以资料详实、考辨精细见长,是常德会战研究最新的重要成果。
二、研究层次与关注焦点
常德会战发生距今只有70余年,作为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常德会战研究与现实社会文化的关系是密切的,即如建国后30余年的研究沉寂期,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出现的状态,其实也是一种研究状态,是社会文化的反映。所以,会战研究与其他近现代史研究一样,呈现出面向社会的开放性。我们在审视常德会战研究成果时,需要考虑这种开放性以及因这种开放性而产生的研究层次的问题。
首先,我们注意到成果作者的层次。初兴期的研究者,多是与会战有直接关系的人。徐浩然自1938年即在国民党第57师工作,常德会战时他正在军中,是此次会战的亲历者。黄潮如是常德《新潮日报》的战地记者,也亲历了战争。他们的记述现场感强,史料价值应该肯定。
建国后的研究者,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业研究人员。湖南尤其是常德本地的一批高校教师长期关注常德会战,如湖南文理学院的陈致远、朱清如等人,都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的研究属于严谨规范的历史研究,注重学理价值。第二类是从事地方文化建设工作的人员。他们或为党政文宣部门的职员,或为党群团体的成员,或为热心桑梓文化的离退休干部。他们以其特有的使命感进行工作,特别注重社会效应。有些人潜心于挖掘、整理史料,如叶荣开编纂的《中日常德之战》,是首部常德会战资料集。有些人致力于建构宏观叙述,如周询所撰《抗日时期常德会战》,是建国后首部常德抗日战史。龙佑云主编的《孤城血拼——常德会战始末》则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第三类研究者身份颇杂,有媒体从业人员如一些采写深度报道的报刊记者,有烈属如孙明瑾将军之子孙瑞星,有爱好军事的社会各界人士。他们的写作兼顾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其文字不以学理高深取胜,而以通俗普及见长,充分体现了会战研究所具有的开放性。
其次,可以归纳出研究内容的大致类别并藉此看到大家关注的焦点所在。一方面,常德会战研究成果在内容上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层次性,其预设的读者受众从精英学者到普罗大众,从皤然老者到热血青年,涵盖面颇广。另一方面,如对具体研究内容加以类聚区分,则大致可分为“整体述论”“史事考辨”“人物研究”“亲历记录”等几个方面。
“整体述论”类成果数量最多。多数研究者以时间为经、以问题为点对常德会战之过程进行全面论述。其中,既有《常德会战述评》《开罗会议后第一个大捷——常德会战论略》《常德保卫战简论》《常德会战全过程》[19]等学术论文,也有《常德:一寸山河一寸血》[20]、《常德会战》[21]、《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22]、《1943:他们共同喋血常德》[23]等学术随笔。此类文章叙、议结合,在叙述战事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日双方的战略得失,关于日军发动常德作战的意图以及会战胜负的评价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研究者们从较实际的方面看,认为日军侵常旨在掠夺滨湖经济资源以及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以牵制中国军队在缅甸的反攻。从较大的战略角度来看,则认为日军此举在于为进攻长沙做准备,以图打通粤汉路,完成其蓄谋已久的大陆交通作战。而在政治上,也能起到振奋国内民心、鼓舞在外军心的激励作用。
“史事考辨”类成果多聚焦于常德会战的某一方面某一环节进行考证、阐发,开口小而挖掘深,专业性较强。研究者或着眼于事物,如樊昌志《常德会战中常德守军的战场传播》、朱清如《试论日军在常德会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陈致远《常德抗战“碉堡”质疑》等;或着眼于人群,如陈志文《常德之战中的五十八军》[24]、佚名《常德会战双方参战兵力》[25]、刘凌《常德会战中的西班牙主教》等。这些论题看似无关宏旨,实则有利于深化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如对中日参战兵力及伤亡人员的衡估,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牵涉到战争规模、参战序列、涉战地域等方面,甚至影响到对战争形势的研判。对此,研究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些差距还很大,形成了争论。
“人物研究”是常德会战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主要关注会战中守城主将余程万及殉国的许国璋、彭士量、孙明瑾、柴意新等四位将军。对后者,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褒扬他们的忠烈精神,而对坚守常德城的主帅余程万的相关研究则要丰满得多,不仅对其平生经历有更为完整的梳理,对其治军、备战、守城、突围等重要事迹详加分析评价,甚且涉及其家庭关系、战后结局等方面,达到了一定的研究深度,如韩隆福《论余程万在常德会战中的作用》[26]。
三、研究不足与致力方向
70余年来的常德会战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为抗日战争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个案性范例,但其间的不足也是明显的。
一是相关研究史料、研究成果零散,在基础资料方面给研究者造成一些困难。目前所见关于常德会战的史料集,尚只有叶荣开所编《中日常德之战》一种,此书所收资料既有限,出版时间亦在20年前,且是内部印行,印数和影响都极有限,除常德一地的学者外,基本没有在学界流通。这一状况使研究者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精力爬梳史料,从而限制了研究进度。想要成为一个较成熟的研究领域,则在基本文献方面应有所建设。呼吁学界建立常德会战研究史料、著述集成,广泛搜集大陆、日本、台湾等方面的所有文献史料和研究成果,汇编成集。易见而篇幅较大者存目,难见难得者一概全文收录,档案实物文献以照片或影印形式收录。如此一编,嘉慧学林,可以助推成果的涌现。
二是由于资料使用的缺陷,造成研究者在视角和一些具体问题上可能出现偏颇,许多论述因而给人陈陈相因之感。现有研究侧重于使用国内可见资料,对于日方和台湾国民党相关资料,则只限于已公开出版的较少部分。这就使得一些研究难免带有先入为主、以我为主的缺失,一些问题不免有自说自话之嫌。如在日军发动常德作战动机、日军伤亡程度、日军退出常德之目的等问题上,应该说,综合考量日军主观意图和战事客观后果是评价常德会战胜负得失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学界还需要深入挖掘中日双方高层史料,尤其应对双方决策过程进行精细研究,草率地称此役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或者突出其在抗战历程中的转折作用并不合适,也不具有学术价值。但是,这一状况的改变主要有待于学界之外的客观条件之改善,如日方、台方若干涉秘档案的开放程度以及政治关系、意识形态互动的状态,不是个别学者可以左右的。
三是研究重点失衡。常德城保卫战固然是整个常德会战的核心和重点,但不是会战的全部,现有成果对常德城区战事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而对外围战事则往往一笔带过,少见专论,对于策应战事则几乎没有涉及。这种研究格局不能反映会战全貌,影响了研究深度。“人物研究”方面也主要集中于会战指挥者(师、团级军官),对于更高层的战略决策者和更低层的战事实施者(一般兵士)关注较少,如能自上而下多层次地研究会战中人,将使我们对战争的把握更为丰富、立体。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研究者在使用常德会战和常德保卫战这两个概念时不够严谨。常德会战应指在1943年11月2日至1944年1月5日两月之间,以常德为中心并涉及周边较大地域范围的中日之间的交战,而常德保卫战则是11月18日至12 月3日半月之间日军攻击常德城与中国军队守卫常德城的战事。常德保卫战是常德会战的一部分,其概念内涵小于常德会战,但一些研究者似乎以常德保卫战来概称常德会战,这是不够准确的。
而在对常德保卫战的研究中,对于主帅余程万的评价问题,也是敏感而有争议的。常德城易攻难守,以八千士兵坚守16日之久,实属难得,在弹尽粮绝的情形下,是全部牺牲才叫“与城共存亡”?还是突围带领援军迅速收复常德?突围求援是否就是逃跑?余程万为什么要受到审判?又为什么一再从轻改判,最后又再担任74军副军长?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更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四是研究领域较为集中,有欠全面。作为一场复杂而重要的战役,可从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情状等多方面深入探讨,而现有成果大多数皆属军事研究,侧重于对战争过程的厘清与描述,对战术、技术等论之不多,对战争的其他丰富面相,如民众支援、战争动员、粮食运输等问题则更少涉及,几为空白。其实,如果说国民党战败的一项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密切联系群众,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那么,战争中的民众以及军民关系问题就是抗战史研究中应予以关注的重要方面。另外,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当时的常德是通往陪都重庆的门户,也是国民党军队的粮食供应基地,日军发动常德作战的目的之一,即是劫夺滨湖粮食资源,因此有必要对常德会战中的粮食问题进行研究。
总体上看,有关常德会战的研究,既取得了可观成果,也存在明显缺失,应思考如何深入探讨,克服片面性,拓宽研究领域与视角,加强专题性研究。相信随着学术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上述状况将发生变化,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常德会战研究方面出现更多更优秀的成果。
注释:
①叶荣开《中日常德之战》,载《常德市志》(内部印行),1995年。
[1]徐浩然.常德抗日血战史[M].上海: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51.
[2]黄潮如.常德守城战纪实[N].新潮日报,1945-10-21.
[3]张恨水.虎贲万岁[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4]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常德会战[M].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63.
[5]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八年的支那派遣军[M]//派遣军作战(一)华中方面军作战.吴文星,译.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
[6]毛申先.常德会战述评[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8(4):81-84.
[7]郑立.论常德会战在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J].武陵学刊,1995(2):10-13.
[8]龙子.常德保卫战考辨[J].武陵学刊,1995(2):5-9.
[9]徐伟民.开罗会议后第一个大捷——常德会战论略[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6(3):27-29.
[10]周询.抗日时期常德会战[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11]龙佑云.孤城血拼——常德会战始末[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12]罗玉明.常德保卫战简论[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1):16-20.
[13]樊昌志.常德会战中常德守军的战场传播[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5):80-82.
[14]朱清如.试论日军在常德会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4):8-11.
[15]陈致远.常德“抗战碉堡”质疑[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7(5):39-42.
[16]叶荣开.常德会战中英雄营长杨维钧[J].黄埔,2013(6):24-25.
[17]刘凌.常德会战中的西班牙主教[N].常德日报,2014-12-24.
[18]朱清如.常德会战史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19]叶荣开.常德会战全过程[J].黄埔,2013(6):10-13.
[20]吴珏.常德:一寸山河一寸血[J].湘潮,2005(6):31-33.
[21]李伽.常德会战[J].源流,2009(12):72-73.
[22]高峰.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J].党史纵横,2011(3):60-61.
[23]毛剑杰.1943:他们共同喋血常德[J].看历史,2012(3):108-115.
[24]陈志文.常德之战中的五十八军[J].云南档案,1995(5):31-32.
[25]佚名.常德会战双方参战兵力[N].常德日报,2010-03-17.
[26]韩隆福.论余程万在常德会战中的作用 [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1):20-26.
(责任编辑:田皓)
K265.3
A
1674-9014(2016)04-0110-04
2016-05-07
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常德会战与常德文化精神之建构”(14K067)。
周勇,男,四川泸州人,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常德抗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