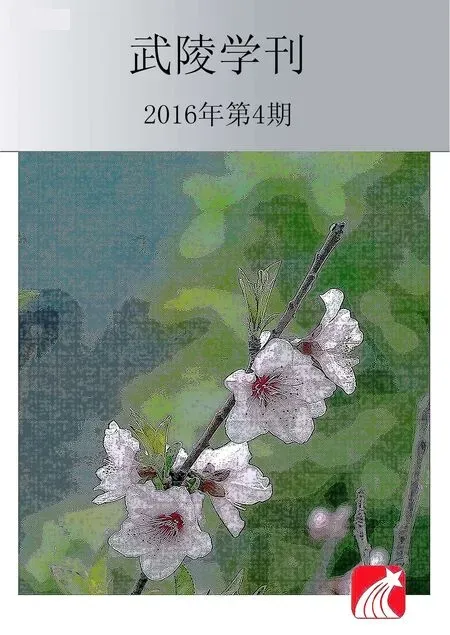晚清官刻书流通特点及成因
2016-03-16王晓霞
王晓霞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社科部,天津 300222)
晚清官刻书流通特点及成因
王晓霞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社科部,天津 300222)
19世纪中叶,地方督抚纷纷在各省设立书局,招揽硕学名流,刊刻卷帙浩繁的传统经典著作。这些官刻书主要在传统的体制内流通,并部分参与商业活动。这与地方书局设立的初衷、官刻书的内容与质量、传统士人对书籍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正逐渐丧失知识生产的最高控制权,而地方逐渐掌握了文化重建的话语权。
晚清;地方书局;官刻书;流通
晚清地方书局是各省地方督抚倡导并设立的官方刻书机构。咸丰九年(1859年),胡林翼在湖北首设书局,开地方书局之先河。此后,地方督抚纷纷在各省设立书局,招揽硕学名流,多方搜寻传统经典著作,进行重新编排刊刻,试图重建地方文教事业,重构清廷的统治理念。地方书局刊刻卷帙浩繁的传统经典著作,推动着传统文化知识的标准化生产和传播。考察官刻书的流通特点及成因,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对晚清地方书局的认识,亦有助于思考晚清时期传统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官刻书流通特点
官刻书的流通分为两类:官方系统中流通和商业参与。前者包括或上呈朝廷,或呈送各中央机构,或颁发各地书院,或在各局之间调取;后者包括或自设发行所销售,或由书局代售。
(一)官方系统中的流通
官刻书在官方系统中的流通,包括上呈朝廷、颁发各书院、官方的调取、书局的馈赠、朝廷赏赐官员等。
上呈朝廷,如送国子监、军机处、史馆、礼部、总理衙门等。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设立广雅书局,主张将所刊书籍运送国子监,“将来各书刊成,当随时刷印咨送国子监,以备在监肄业者考鉴之助”[1]383-384。光绪年间,清廷下令由礼部列明清单,广泛搜罗书籍,“查同治年间,江南、浙江、湖北、广东等省,曾将各种书籍,设局刊板,流传已久,所有场中备用各书,拟由礼部开单咨取”[2]。
颁发各书院。地方书局初设之时,各省督抚皆以各地战后无书可读、民风凋敝为由,倡导刊刻书籍,以便士人诵读,淳化民风。书成之后,书籍流向各地书院,用以充实书院的文库。同治八年(1869年),李鸿章倡议各省合刊《二十四史》,主张将所刊书籍分发各书院,说道:“现在浙江、江宁、苏州、湖北四省公议,合刻《二十四史》。……俟各书刻成之日,颁发各学院。”[3]417光绪四年(1878年),云南书局主张将官刻书分发各书院,“将随带书籍酌捐数十种,当即公同检阅,分发两书院存储,藉资讲习。并拟择其尤要者,饬司酌筹经费,陆续校刊,分发各学”[4]675。光绪七年(1881年),直隶书局主张将所购官刻书存储书院,便于学子阅读,“查书籍交各州、县发卖,固可以广为流布,但寒士仍属无力购买。惟买书存书院,俾肄业者得以借观,最为培植寒畯良法”[5]291。光绪十四年(1888年),江苏学政王先谦设局刊刻《皇清经解续编》,主张将官刻书颁发书院,并将“板存江阴南菁书院”[6]。
官方调取。清廷及地方督抚通过行政命令,调取各省的官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贵州设立书局,学政严修恳请调取江南各省的官刻书,“今年以来,如江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各省书局刻本精博,蔚为大观。相应请旨饬下江南等省督抚臣,将局刻经史子集等书每种刷寄十部,以作式样”[1]564-565。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主张设立藏书楼,调取各省官刻书,“自京师及直省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版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古今中外有用之书,官书局有刻本者,居十之七八,每局酌提数部,分送各省”[7]。
官员馈赠。官刻书经常作为“礼品”在官员、学者之间流通,或官员向书局索要,用于阅读和收藏;或作为报酬,答谢士人送书;或赠送友朋,交流感情。金陵书局刻书籍质量较精,颇得士人好评。官员们亦纷纷向书局“索要”。据《曾国藩复马谷山制军函》载:“去年所刻马、班、范、陈四史,因提调无人,至今尚未定刷印确期。本年正月,宝佩蘅索赠此书,弟许以不久寄赠。枢廷诸公同声索取,亦皆允许。”[8]5又据其《复宝佩蘅大农》载:“前在枢廷,阁下谈次偶索敝处所刻四史,旋经函商毂山制军,顷《前后汉书》始刊校成,由江南运到,谨奉上一部。余四部即请尊处代呈恭邸、博翁、经翁、兰翁四处。其《史记》、《三国志》,俟刻成后续行奉寄。”[8]5光绪七年(1881年),刘坤一向淮南书局洪汝奎写信,请求赠与官刻书:“弟两度江南于淮南书局所刻各籍……此次解官归农不再出山,拟请尊处于书局所刊各籍,酌送二三部以壮归装。”[9]。光绪五年(1879年),山西总督的曾国荃在书局创办之初,向士人广征书籍,并承诺以官刻书作为酬谢:“郡县专用一板,必致模糊,书局定章,如有善本发刻,核对既定,将来即以初拓数部奉酬,仍以原书奉缴定议缮写。”[10]
图书馆储藏。新政时期,各地设立图书馆,书籍主要来源于调取或购买各地官刻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黑龙江省设立图书馆,“广购经、史、子、集各种,并东西各国图书,暨译印各精本,其在京各衙门及各省官书局刻印各书,拟咨由各处寄送以饷边区”[1]618。宣统二年(1910年),广西设立图书馆。时任巡抚张鸣岐主张将旧有地方书局的书籍,移送至图书馆,“将桂垣书局旧有书籍,移置该馆储藏,东西政艺诸篇,一面博采兼收,以期国粹保存,新知沦濬”[11]。
政府其他机构收藏。不少官刻书流向政府的其他机构,如驻外使馆、山东曲阜衍圣公府等。曾纪泽出使英国时,请求:“调取江宁、江苏、湖北、浙江局刻书籍,分储两国使馆,以备查考而壮观瞻。”[8]光绪二十年(1894年),王懿荣主张将各省官刻书赠给曲阜衍圣公府,“曲阜衍圣公府自近岁不戒于火,旧藏书籍、图箓焚毁一空。现在各省设立书局以官钱刻书者,三十年来珍籍善本,灿然大备”,请求将“各省督抚有书局者,无论新旧诸刻本,亦以一分解交山东巡抚转行曲阜,作为恩赐衍圣公孔令贻敬谨储藏,以为诵法之资”[12]。
(二)官刻书之商业参与
晚清地方书局参与商业活动,始于何时,难以考察。早期地方书局几乎很少直接涉及商业活动。但随着业务的发展,书局的出版量、出版种类不断增多,市场参与度逐渐增加,书局的商业参与越来越频繁。不少书局制定了明确的管理章程,设立发行所,与书肆、商铺合作,销售官刻书。
书局奏请允许坊间刻书。同治六年(1867年),鲍源深上奏请求刊刻经史类书籍,建议书籍刊刻之后,“颁发各学,并遵旧例,听书估印售”[3]407。光绪四年(1878年),云南书局主张将所刻书籍允许坊间书贾印售:“……将随带书籍酌捐数十种。当即公同检阅,分发两书院存储,藉资讲习。并拟择其尤要者,饬司酌筹经费,陆续校刊,分发各学。仍遵旧例,听坊间印售,以广流传。务使边鄙士风蒸蒸日上。”[4]675当时不少书肆售卖官刻书,如苏州扫叶山房书目、上海抱芳阁等均发售官刻书。当时北京最大的书籍销售地琉璃厂,成为官刻书重要的销售地。读书人能够比较容易购买官刻书。据《缘督庐日记钞》中所载:“十六日购局书数种,又购通志堂释文一部……(三月)廿六日,购局刻子书数种,又汉书地理志校正一部。”[13]
官方设立售运书局。光绪七年(1881年),直隶设立书局,以转运南方各省官刻书为主要业务,“于保定省城及天津设运书局……由省志局酌定应买书籍数目,开单移交招商局赴各省书局购买,轮运至津,转运省局发卖”[5]293。劳乃宣建议书局以九五折购买书籍,及时了解各省书局的书目,说:“由省局将总书目并摘要书目及售书章程刊刻告示,通行发给各州县张贴,俾绅民一律周知。”[5]296光绪八年(1882年),《申报》记载了直隶书局的情况:“津门虽为通商马头,百货骈集,然书坊甚少,藏书家亦不多觏。目下当道诸公深念经籍为士类必需之物,特就鼓楼南问津书院设一官书局,由南购运各书,平价发卖,牙签玉轴,出色当行,郡人往购者……趾踵相接,嘉惠士林,洵非浅鲜矣。”[14]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云南省奏请设立书局,购买各省官刻书,规定平价发售,“将经史子集、国朝掌故暨一切有裨时务实学诸书,择要开单,由各省采买运滇。即在省城设立官书局,随购随售。只照原价酌加水脚、薪工等费,并不格外取赢。使书值较廉,多士易于购置”[3]436。
各省书局主动商业参与。金陵书局后期面临裁并的困境,希望通过销售官刻书,缓解经费紧张的问题。据《申报》载:“金陵向有书局,刊印经籍,发往各省,久已不胫而走……上年有人建议撤局,以事由制府主政,不果。今逢大比,左丞相以都人士观光者众,宜力求广益以备购取,筹款从事销售,果胜于往昔。议者遂一意振兴。”[15]光绪年间,金陵书局改为江南书局,注重官刻书的销售和发行,设立通信章程:“本局出版各书,均按书目定价出售,不折不扣。如有远道汇洋函购,须代寄者,包皮邮费,照刊定书价,另外加洋一五成,以便代寄。如该寄费有多退还,少仍函知购者补足,以免亏耗,并不得以邮票抵价,合再声明。”[16]291
不少书局专门设立发行所,制定销售章程,规范官刻书的销售。山东书局售卖官刻书,注重随时核查书价,及时告知读者书价的跌涨,还提醒读者“购木板书时,务请照本局目录详细指示,祈勿含混。外埠函购,则请详细誊录,因一种书而有数种板本,稍一减便则易致不清”。书局还发送优惠证,规定“凡持有长期有待证者,一律按定价八折,如购书书价超过二百元者,即无有待证,亦照八折,满一千元者折扣随时商定”[16]293。湖北书局要求读者负担邮费,挂号汇款,对交易的货币亦作出明确的规定和说明:“本处印行各书,无论零售批发,概照定价大洋发售,不折不扣,以武汉通用银币计算;如武汉不能通用之银币或钞票,按照市价折算,其小洋照市贴水,官票通元亦按市价合洋计算,书价在一元内者可以一分或三分之邮票代用,超过一元者只作九五折计算,购书如需夹板,每副大洋三角,包裹及挑力,归买主付给。书籍出门,概不退换。缺叶照补,本埠函购书籍,须将书名纸色部数及通信地址详细开明,其书价并寄费交足,方能照寄,有余照数退还。”[16]294光绪十八年(1892年),浙江书局发告示降低官刻书的价格:“近来书籍售销日广,成本较敷周转。蒙抚宪体恤寒畯,仍恐购读不易,饬再酌减。本局遵按现行书目刊本核作八折至九五折不等,禀明抚宪减定。其现今读刻各书及将来续刊各书,即照此次减定价目核价。……凡购书者,仍径赴官书坊购买可也。”[17]
二、官刻书流通之成因
由上可知,晚清官刻书主要在官方系统中流通,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起初,官方允许官刻书部分参与商业流通,“准书肆刷印”,后期地方书局主动参与商业活动,制定售书章程,设立发行所。但其商业活动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用副朝廷教育人才至意”[3]408。这种流通特点与地方书局设立的初衷、书籍的内容、士人对书籍的态度有关。
(一)地方书局设立的初衷
太平天国所到之处肆意焚毁和删改儒家经典著作,致使儒家传统颜面扫地,严重挑战了儒家文化的权威。文化危机引发了清廷的政治危机,清朝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戡乱”之后,地方督抚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地方文教,以肃清异端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向读书人传播忠孝仁义的传统价值观念,重新树立清廷的统治权威。而当时各地出现不同程度的“书荒”,各府州县学书籍、私家藏书均遭受到“灭顶之灾”,出现无书可读的状况。鉴于此,各省督抚奏请开局刊书。同治六年(1867年),鲍源深上奏:“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而且“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乱后虽偶有书肆,所刻经书俱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以致出现“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的状况,“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谅亦相同。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3]406。同年,马新贻亦奏请道:“浙省自遭兵燹,从前尊经阁、文澜阁所存书籍均多毁失。士大夫家藏旧本,连年转徙,亦成乌有……士子虽欲讲求,无书可读。而坊肆寥寥,断简残片,难资考究,无以嘉惠儒林。自应在省设局重刊,以兴文教。”[3]413同治八年(1869年),李鸿章上奏:“惟楚省三次失陷,遭乱最深。士族藏书散亡殆尽、各处书板全毁,坊肆无从购求。”[3]417
不惟如此,地方上出现大量“禁书”,社会风气日下,亟需鼓励士人读经史著作,以净化士林风气,教化人心。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禁止邪说传奇,查禁小说,以端正士习民心,“目前人心不古,书贾趋利,将淫词邪说荟萃成书,编水浒传奇。略识之,无如探秘笈。无知愚民平日便以作乱犯上为可惊可嘉,最足为人心风俗之忧。臣在吴中业经严禁。诚恐此种离经畔道之书,各省皆有。应请旨饬下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加禁毁,以隐戢人心放纵无所忌惮之萌,似亦维持风化之一端”[3]412。当时读书人中还普遍存在着“求名之心太急”的心态,“往往四书五经未能成诵,而即读肤浅考卷,学为应试之文。既务应试,则束书不观。专取文艺数十篇,揣摩求售。叩以经义,茫然莫辨。且有并句读不知者”,教书先生尚且如此,还“以为教弟子如是以为学”,以至于出现“求所谓淹通经史者,盖鲜也。求所谓砥砺行修者,益寡也”,“寒畯之士不读书而临场蹈怀挟之弊;素封之子不读书,而倩代恃抢冒之为。人心日浮,则风俗愈敝”的状况,“此等弊风,始犹以为郡县偶然耳,及询之各直省,大率类然。何惑乎文风未振,真才不出乎”,因此“今欲改此锢习,莫若杜人徼幸之心,而引之专意读经”,“尽务实学,而士习可赖以挽救,亦整饬学校,正本清源之一道也”。游百川上奏请求“崇尚经术”,以期“天下士子读书明理”[3]404-405。可以说,各省地方书局的设立是地方督抚振兴地方文教、正本清源的必要之举。所以,官刻书刊成之后,大量流向官方机构、书院等,在官方系统中流通,并“准许坊间刊售”,便于传播正统的价值理念,维护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二)官刻书内容和质量决定了其流通方式
官刻书的种类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尤其强调经史类著作的刊刻。鲍源深强调:“深于经者,窥圣学之原,深于史者,达政事之要”,“士子读书,以穷经为本,经义以钦定为宗”,建议刊刻“世祖章皇帝御注《孝经》;圣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诗、春秋三经传说汇纂》;世宗宪皇帝《御纂孝经集注》;高宗纯皇帝《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钦定三礼义疏》”,认为唯有如此,“使穷经之士不淆于众说,得所指归”[3]407。李鸿章亦认为,“除四书十三经读本为童蒙肄习之书”,应重点刊刻“钦定七经、御批《通鉴》”“集经史之大成,尤为士林圭臬”等经史类书籍,还应刊刻“《说文》、《文选》、牧令,政治等”,“切于日用书”[3]417。其所倡导浙江、江宁、苏州、湖北四省合刊《二十四史》,成为晚清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丁日昌认为应刊刻吏治、农政、学政类书籍,“凡有关于吏治之书,著为一编。如言听讼,则分别如何判断,方可得情言;催科则分别如何惩劝,方免苛敛;胥吏必应如何驾驭,方不受其欺朦;盗贼必应如何缉捕,方可使之消弥。他如农桑、水利、学校、赈荒诸大政,皆为分门别类,由流溯源。芟节其冗烦,增补其未备”,“刊刻一竣,即当颁发各属官各一编,俾资程式。虽在中材,亦可知所趋向。譬诸百工,示以规矩,则运斤操斧,悉中准绳。庶几士习民风,因之起色”[3]411。从中可知,各省督抚严格限定官刻书的选择标准,首重经史类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是传统士人和靠科举为生的读书人。成书之后,官刻书理所当然地流向官方机构、书院等。
而且,刻书质量较优,刊刻的纸张、版本均属上乘。曾国藩主张所刊《汉书》上添加戳记“金陵书局仿汲古阁式刻”,并提出刻书的标准:“刻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方,以结体方整言,而好手写之,则笔画多有棱角,是不仅在体,而并在画中见之;粗,则耐于多刷,最忌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则此字不与彼字相混,字边不与直线相拂;匀者,字之大小匀,画之粗细匀,布白之疏密匀。”[18]同治八年(1869年),金陵书局的张文虎给曾国藩的信中提到《史记》的刊刻:“刊书机会实为难得,当略治芜秽以裨读者,文虎等禀承此意,不揣弇陋,冀会合诸家,参补未备,求胜旧本……但求校雠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8]由于较高的要求和学者们严谨的态度,官刻书质量较优,受到官员和士人们的追捧,甚至一度成为“礼品”在官员之间流动。
为了参与商业活动,地方书局也尝试采用不同纸张刊刻同一本书。以《四书》为例,江南局采用“官堆纸”,售价为“五百六十文”;江苏局采用“连史纸”“毛边纸”“毛太纸”,售价为“七百四十文”“六百三十文”“五百二十文”;湖北局采用“竹连纸”“官堆纸”,价格为“七百九十五文”“六百六十六文”;江西局为“连泗纸”“官堆纸”“吉连纸”,售价为“八百八十文”“六百二十文”“四百七十文”[16]40-78。不同纸张的印刷,显然便于读者多样化的选择。而官刻书的定价与坊刻书相比较,仍属高端。以《史记》为例,山东书局刊刻为十六册,“粉连纸”售价为“十四元”“赛连纸”售价为“洋七元”。湖北书局为二十四册,“竹连纸”售价为“十二元一角”,“官堆纸”售价为“九元六角四分”。而扫叶山房所售《史记》为四本,售价为“洋一元八角”,鸿宝斋刊刻的《史记》售价为“每部一元八角”。相比较,官刻书在版本、质量上较优,但价格不菲,是坊刻书的10倍以上,这非普通读书人所能承受。这从侧面反映出官刻书主要读者对象是当时有一定社会地位、收入的士人。
可以说,无论从书籍的内容和质量来看,官刻书首先注重政治层面的诉求,关注的是官刻书所承载的传统价值理念的传播,强调官刻书流通所产生的政治效益。其参与商业活动非为获利,而是扩大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后期书局频繁商业活动,主要与经费紧张有关,多属权宜之策。
(三)官刻书的流通特点还与士人对书籍的认识有关
有清一代,官方严格控制书籍的刊刻活动,书籍的种类被严格地限制。清廷“认同”的书籍具有“合法”的地位,成为正统的“标识”。对官刻书的拥有、收藏、阅读,往往被视为对现有政权和统治秩序的认可。读书人通过参与地方书局刊刻活动,尤其重新编排经、史类著作,或者阅读官刻书,获得了掌握正统文化资源的机会,这在无形中强化了士人与政权之间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官刻书被贴上了“权力”的标签。不可否认,晚清时期士人们对官刻书的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对官刻书背后的“权力”的“敬畏”。
此外,书籍对士人具有社会和文化的双重含义。不少士人认为书籍“所以载道纪事,益人神智者也”[19]47,认为书籍有助于人的心性锻炼。不少学者将书籍视为关乎民智、国运的关键,“图书之关乎民智,讵不大哉”[19]158!还有不少读书人受“积金不如积书”[20]观念的影响,认为书籍“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21]。更有不少士人赋予书籍以道德的含义,认为书籍是衡量和评价士人社会名望和地位的重要标准。在此种种观念影响之下,官刻书受到官员们的推崇,士人的青睐,实属情理之中。
余论
19世纪中叶,为缓解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清廷在文化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试图通过重新整合传统文化资源,重建清廷的统治权威,重构清廷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在此背景下,晚清地方书局迎来了兴盛时期。虽然各省书局发展程度不一,但在刊刻经典著作方面,显得“不遗余力”。官刻书在体制内流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地方文教的重建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强化着士人的地方认同。这种流通方式看似清廷在文化领域具有主导权和控制权,实则不然。在地方书局的建立、发展过程中,地方督抚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其权力在无形的博弈中不断扩大,在晚清政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清廷的统治日渐式微,正逐步丧失在知识生产方面的最高话语权。除上呈中央外,地方督抚在知识生产方面有更大的话语权,对官刻书显然有着更大的支配权和处置权。1895年之后,各省书局主动设立发行所,主动参与商业活动,更说明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逐步减弱。
可以说,晚清地方书局刊刻传统经典著作之举,是知识领域应对政治危机的因应之策。虽然官刻书可圈可点,但已是“落日余晖”,从表面上看,官刻书的流通确实满足了重建地方文教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但因主要在体制内流通,影响范围也极为有限。特别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严重动摇了传统政治的文化根基的情况下,其影响可见一斑。这也从侧面说明:晚清时期,传统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已发生变化,而清廷尚不自知,仍沿用传统的政治思维,未及时更新知识体系和把握知识生产的主导权,亦未能抓住改革的机会,以至走向最终的历史命运。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1477.
[3]宋原放,汪家熔.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朱寿朋,张静庐.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675.
[5]梁长洲.关于劳乃宣建议直隶售书事[M]//汪家熔.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6]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五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5:463.
[7]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94.
[8]柳仪徵.国学书局本末[J].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1930.
[9]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八[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6528-6529.
[10]曾国荃.曾忠襄公书札:卷十二[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256.
[11]张鸣岐.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广西建设图书馆摺 [N].学部官报,1910-03-20(123):3.
[12]刘承幹.重疏前请整理孔子祀田并淸查地产疏[M]//王懿荣.王文敏公遗集·奏疏:卷二.吴兴求恕斋,1923:28.
[13]缘督庐日记钞:卷一[M].上海:上虞罗氏蟫隐庐,1933:34.
[14]佚名.创设书局[N].申报,1883-10-28(3).
[15]佚名.书局更员[N].申报,1883-10-29(2).
[16]朱士嘉.官书局书目汇编[M].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1933.
[17]浙江官书局书目[M].浙江官书局刻,光绪十八年:5.
[18]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四[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15338-15339.
[19]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0]叶德辉.总论刻书之益[M]//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观古堂刻本,1920:2.
[21]张之洞.书目问答[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3.
(责任编辑:田皓)
K252;G239.29
A
1674-9014(2016)04-0105-05
2016-04-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晚清官书局再研究”(15YJC770036)。
王晓霞,女,山西运城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社科部讲师,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出版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