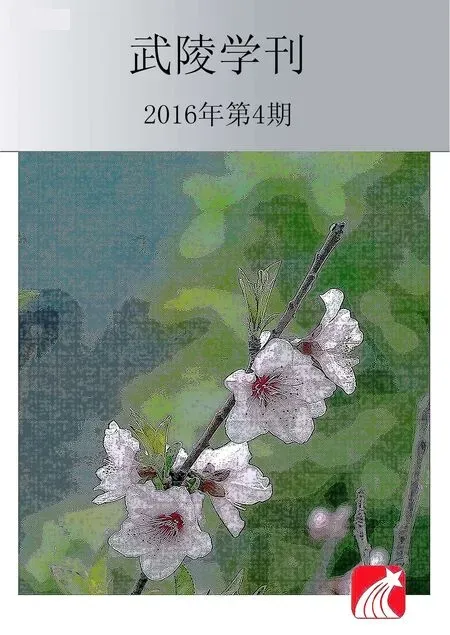“飞蛾扑火”者的精神雕像
——评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
2016-03-16陈娇华
陈娇华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CHEN Jiaohua
(School of Humanities,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 215009,China)
“飞蛾扑火”者的精神雕像
——评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
陈娇华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是最得丁玲神韵的一部传记,它精准地概括了丁玲孤傲、倔强和反抗的精神个性,并把这一精神个性特征贯穿到对其革命经历、文学创作及文坛交往等方面的阐述中。一方面,它细致地梳理和阐述了丁玲及其创作与革命的关系,以体现其精神个性,也呈现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与文学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丁玲不同时期作品思想内蕴和人物精神的阐释,及对丁玲坚持不懈创作精神的发掘来体现其精神个性;同时,还从丁玲独特的精神个性角度及其所形成的对创作的执著精神和对革命的坚执信念等方面解读其与文坛的恩怨纠葛。而这些都是以一种质朴、平实和节制的写实风格呈现出来,这样一来,看似普通平实的传记书写实则蕴含着一种内在精神气韵,真正做到了深情而不纵情,平实而不平淡。
丁玲;倔强;反抗;革命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女作家,不仅创作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优秀作品,还在延安整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等遭到审查和批判,尤其是她的文学创作与革命活动缠绕一起,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复杂过程,这些不仅反映中国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折射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艰难曲折历程,更映现了中国文学与革命的错综复杂关系,值得后人深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丁玲文学思想与创作的研究(包括极“左”年代对其的批判)一直没有间断。“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现在的30多年里,有关丁玲研究的论文两千四百余篇,著作四十多部,其中,评传类或传记类的著作就多达近二十部。”[1]536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一批丁玲评传类或传记类著作,如周良沛的《丁玲传》(1993年)、丁言昭的《丁玲传》(1998年)、杨桂欣的《丁玲评传》(2001年)、涂绍钧的《图本丁玲传》(2012年)、秦林芳的《丁玲评传》(2012年)、彭漱芬的《迷人之谜:丁玲》(2013年)等的出现,学术界对丁玲思想与创作的研究掀起又一波高潮。这些著作或以资料引证的真实严谨见长,或以对丁玲思想与创作研究的学术性取胜,或以书写体式的新颖独创而别致,或以图文并茂、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而著称等。然而在这众多的评传类或传记类著作中,李向东和王增如2015年出版的《丁玲传》(以下简称“王本《丁玲传》”),却以看似一般传记式的平铺直叙实则最得丁玲神韵,即以平实节制的写实风格刻画了一幅“飞蛾扑火”者——丁玲的精神雕像。换句话来说,王本《丁玲传》不仅精准地概括了丁玲孤傲、倔强和反抗的精神个性,并且把这一精神个性特征贯穿到整个传记写作中,即灌注到对丁玲的革命经历、文学创作及文坛交往等的叙述与阐释中,使看似普通平实的传记书写蕴含一种内在的精神气韵。
一、丁玲精神个性在革命经历中的外现:坚执的革命信念
传记作者在《丁玲传·后记》中指出:“丁玲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中,有三个鲜明特点:孤独,骄傲,反抗。它们源之于她幼年丧父,寄人篱下,小小年纪就体尝到世态炎凉的经历;源之于母亲及向警予身上坚强与自立的做人准则;源之于她敏感与聪慧的天生禀赋。孤独,骄傲,反抗,这是‘飞蛾扑火’的原动力,也包含着为革命所不容的所谓个人主义内质,它们贯穿丁玲一生,是她大起大落处境遭遇的主观内在原因。”[2]774这段话精准地概括了丁玲的精神个性特质。事实上,不少研究者也谈到过丁玲这一精神个性,秦林芳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丁玲“表现出了湘西文化所赋予的那种泼辣、倔强、执着的‘蛮’性文化特征”[1]3。丁言昭也认为丁玲“傲气十足”,瞧不起一般的人[3]9。王本《丁玲传》更是在丁玲的日常交友和学习生活中发掘这一精神个性,认为“冰之交友,看重精神与情感世界,看重格调与品位,她能看上眼、精神相近气质相投的,当数新结识的谭慕愚”。而慕愚“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4]36。对丁玲与王剑虹友情及其在学校舞台上扮演丫鬟角色的诠释也是如此,“人之高低贵贱不在舞台上的角色,不屑与俗人争抢才显出清高孤傲”[4]30。正是这种孤傲、倔强和反抗的精神个性,决定丁玲不会轻易追慕流俗,更不可能轻易相信和盲从某些思想言论;相反,一旦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和认定某种思想和信念,便会执着地追随和坚守,不会轻易变更。性格即命运,丁玲与革命的关系当作如是观。对此,李向东也说过:“丁玲这一辈子,从湖南到上海,从北京到杭州再回上海,从南京到延安,一旦她认为是正确的路,她就死不回头。”[5]
首先,传记细致地梳理了丁玲与革命的渊源关系,发掘其坚定的革命信念及其对革命一往情深、始终不渝的原因。丁玲与革命的关系经历一个由观望游离到热情支持,再到积极参与和执着奉献的发展过程。她很早就接触到共产党人向警予、瞿秋白等并深受他们影响,但在上海和北平游学时期,她“远离共产党人的圈子”[4]25,“只想自由自在”[4]26。这个时期她对革命是观望游离的。1930年初,丁玲理解和支持胡也频的革命活动,也频牺牲后,她思想急剧“左”转,创办并主编《北斗》。这是丁玲“第一次接受‘组织’分派的工作,是丁玲走出书斋投入实际工作的转折”[4]80。特别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是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可见,左联时期丁玲是满怀激情,积极参与革命工作。延安时期是丁玲革命信念成型与坚定时期。她担任文艺协会主任,强调战争要枪炮,也要“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笔”[4]154!她要求参加红军,真实了解红军的内在生活。特别是整风运功后,丁玲脱胎换骨,真正把革命思想与精神个性、创作实践与革命活动融为一体,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个人的思想,和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4]319,因此,即使在“十七年”和“文革”中挨整和受批,新时期回到文坛,她依然强调“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强调作家的政治立场和作品的思想倾向,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2]657。可见,王本《丁玲传》真实而深刻地阐述了丁玲与革命由观望游离到理解支持,再到积极参与和执着献身的复杂关系,而每次发展变化的关头都是其倔强、反抗的精神个性在起关键作用。正如论者所言:丁玲由否定不合理社会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作家发展成为革命作家,是符合丁玲的性格特点的。其根本的一致之处就是“那种不向黑暗社会妥协,不向庸俗和卑污投降的倔强精神”[6]239。高华也指出:“丁玲是坚强的革命者,根据地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她曾长期生活的上海不啻相差万里,她没有动摇,更没有幻灭。”[7]
其次,作者还深入阐述了丁玲创作与革命的关系。鲁迅曾说:“丁玲女士才是惟一的无产阶级作家。”[8]关于作家与革命文学的关系,鲁迅指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9]换言之,作家的思想立场决定其创作的革命与否。丁玲的思想立场一开始并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性,但如前所言,其孤傲、倔强和反抗的精神个性伴随时代社会发展必然会发生相应变化,即必然会由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转向反抗阶级压迫的政治革命。同时,丁玲精神个性的这一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文学思想与创作中,形成其革命的文艺思想及创作内容。传记深入地阐述了丁玲创作与革命的关系经历了由疏离革命到转向革命,再到服务革命和与革命水乳交融的发展过程。20年代后期,丁玲因不满社会黑暗,内心苦闷找不到说话对象走向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系列作品属于“五四”后觉醒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与思想的自我表现。这个时期丁玲创作与革命关系处于疏离阶段。30年代“左联”时期,丁玲开始真正转向革命书写,并被视为“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4]143。其较早与革命发生联系的作品是《韦护》,虽然“还没有跳出恋爱啊、革命啊的范围,但它已是通向革命的东西了”[4]65。也频去世后创作的《一天》,是丁玲书写革命的开始,“写出了革命的艰难和革命者面临的困难”。主人公最后决定要表现“一种在困难之中所应有的,不退缩、不幻灭的精神”[4]78,显然有着丁玲孤傲、倔强和反抗个性精神的印痕。标志丁玲创作真正转向革命书写的,是《水》《田家冲》《某夜》等“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要写工农”的正面书写革命斗争的作品,特别是《水》,被誉为丁玲创作的一个突破,“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决的理解”[4]92。不过,由于作者对革命者和革命生活不是真正熟悉,这些作品难免给人以公式化和概念化印象。40年代延安时期至新时期,是丁玲革命文艺思想的成型与坚守时期,也是丁玲创作服务于革命且与革命水乳交融时期。到了延安,丁玲深入前线,有了切身的群众生活经历和体验,特别是通过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学习、领悟,开始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这在整风后的《三日杂记》中可以看到。传记指出:《三日杂记》体现丁玲创作“颠覆性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大量使用了农民的口语对白,努力适应工农兵的阅读习惯。其次,这是丁玲第一次深入工农兵,终于实现了她一年之前就‘要下去’,‘要写农村写农民’的心愿。”[4]318尤其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和出版,是丁玲“创作的又一个重要转点……让她进一步懂得了,光有方向还不行,光有生活还不行,还要懂得政策,要按照党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来分析生活处理题材”[4]375-376。换句话说,这时的丁玲创作已不仅是题材和手法的大众化,也不仅是世界观和创作立场的大众化,而是整个创作思维和艺术观念的大众化与革命化,创作与革命至此交融一体。为此,不难理解新时期丁玲把重写的《杜晚香》作为重现文坛的“见面礼”;也不难理解尽管《“牛棚”小品》发表后好评如潮,但她仍坚持以后要写《杜晚香》等“鼓舞人,激励人奋发向上的作品”[2]632。这是丁玲对融入到其精神个性中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文学观念的执着坚守,也是其作为一个革命作家的自觉而又本能的坚守。
王本《丁玲传》对丁玲及其创作与革命关系的梳理和阐述,理性地回应了学术界对丁玲或左或右的判别,生动地体现了丁玲一以贯之的革命信念,真实地呈现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与文学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而丁玲及其创作与革命复杂关系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丁玲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个性决定的。丁玲是湖南人,深受湖湘文化影响。有论者指出: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力行践履的道德原则、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群体参政意识及卓厉敢死、强悍炽烈、百折不回的士风民气等在丁玲身上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记[10]158。加之,丁玲自幼丧父跟随母亲生活,丁母是一位坚强自立,追求自由民主的新女性,课余常给丁玲讲秋瑾、罗兰夫人等的悲壮故事,这些都影响丁玲精神个性的形成,使她由最初的追求个人自由幸福转向后来的追求集体自由解放。另一方面,也与丁玲身边中共领导人的影响和鼓励分不开。从早年的向警予、瞿秋白,到后来的冯雪峰、鲁迅及毛泽东等,丁玲与他们交往较多,深受他们思想影响。尤其是冯雪峰,正如王本《丁玲传》所言:“雪峰是抽打丁玲的鞭子,是丁玲不断向前走的推动力……胡也频之死对于丁玲确然是一种巨大的刺激,但加速丁玲转变而左倾的却是雪峰,他对丁玲的影响更大。”[4]90-91彭漱芬也谈到:“雪峰写了一些文艺理论、文艺评论论文,丁玲可能看得较多,常常运用他的理论观点去进行创作”[10]165,深受其理论影响。总之,家庭的、时代的、社会的及个人的等种种因素纠合一起,形成丁玲及其创作与革命的不解之缘,而丁玲又是“一条道走到底”,革命到底的。
二、丁玲精神个性在文学创作中的渗透:坚持不懈的精神意志
王本《丁玲传》还把丁玲孤傲、倔强及反抗的精神个性贯穿到丁玲的整个创作活动中,不仅通过对丁玲不同时期作品的细致解读,包括对其思想内蕴和人物精神的阐释体现出来,还通过发掘丁玲对创作的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精神呈现出来。众所周知,不同于一般名人传记,作家传记的写作不仅要尊重历史真实,写出传主复杂丰富的个性特征,还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作家的创作,并对这些创作进行独到的解读与阐释。在这方面,王本《丁玲传》做得相当出色。一方面,它把丁玲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恰当地嵌入到其经历和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真实地再现了丁玲的革命思想及其实践与文学创作之间互动的复杂关系状况;另一方面,又把对丁玲重要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分析放置于丁玲创作的整个发展历史中,进行艺术性评价和文学史定位,不仅生动地呈现了丁玲文学创作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更使丁玲的精神个性在创作中得以完整地贯穿和体现。
首先,王本《丁玲传》善于发掘贯穿于丁玲作品中的那股强烈的奋起反抗、毫不妥协的精神意志,这既是丁玲精神个性特质的外现,也是其为人生的“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体现。传记通过对丁玲创作历程的梳理,发掘出丁玲自30年代创作转型后,作品就大多充满一种奋起抗争、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如写也频就义的《某夜》,“结尾仍是革命者高唱《国际歌》的壮烈场面”,写自己生活感情的《从夜晚到天亮》,也是让“她”意识到要“忘记一切吧!……现在只应该振作’,并立即动笔去写文章”[4]127。即使是创作于南京囚禁时期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团聚》等,虽然弥漫着抑郁苦闷和孤独无助的情绪氛围,但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4]48。而《泪眼朦胧中的信念》中那个遭日寇蹂躏的陈老太婆,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控诉鬼子的残暴罪行,目的也是要凸显和强调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精神。还有写于挨整受批时的《风雨中忆萧红》,借忆萧红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抑郁,“但‘人的伟大也不只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一向主张自强的丁玲,不肯向这讨厌的环境屈服”[4]285!更不用说《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所体现的不苟从流俗、乐观坚定及孤傲倔强的反抗精神。
其次,传记还从丁玲的系列人物性格中发掘和呈现丁玲的精神个性特征。传记作者指出:“丁玲由于幼年的家庭变故、母亲的影响和成长经历,形成孤独、骄傲、富于反抗的性格,这三种特质也一直贯穿于她的小说创作,她说过:‘我们写人物常常摆脱不了自己的经历。’丁玲到陕北过集体生活以后,一直压抑着这些情绪,革命队伍尤其是西战团的生活也在磨蚀着改变着这些情绪。但是毕竟本性难移,她内心的孤独、骄傲和反抗非但磨蚀不掉,反而经常要跳出来,与革命队伍的生活抗拒。”[4]245-246因此,她笔下系列人物都打印上了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关于这点研究者谈论较多。彭漱芬认为:丁玲笔下的系列女性形象梦珂、莎菲、曼贞、陆萍、黑妮等,都“脱离了脂粉气与闺秀气,具有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对鄙俗和虚伪的社会充满着反叛情绪。……究其原因,是她们身上渗透了丁玲的个性气质,渗透了作家的审美体验。”[10]182而王本《丁玲传》在解读丁玲作品时,更是着重发掘和凸显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丁玲精神个性特质。如对《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分析,认为作者虽然没有像莎菲那样的生活,“但是完全懂得莎菲,她在湖南家乡就已埋植,后来又在上海、北京萌发生长的傲岸而独立不羁的人格,注重人品、重视精神需求等特点,都在莎菲身上有细腻的表现”[4]49。对《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的分析也是如此,认为“在丁玲全部的文学形象中,贞贞是最贴近作者自己的,是她最为欣赏的,她用‘我’来反衬贞贞,贞贞比‘我’更孤独,更强悍,不要一丝怜悯”[4]246。还有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黑妮的分析同样如此,认为:“黑妮和丁玲一样,都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地主女儿,她‘是作者曾经熟悉过的人物,喜欢过的感情’……”可见,“虽然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表示要脱胎换骨,但深浸在她血液中的那种孤独、傲气和反抗精神,却终其一生都挥之不去,始终要顽强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4]372-373。
此外,作者还以丁玲对创作的执着、痴迷来体现其倔强、反抗的精神个性特质。一方面,以丁玲的思想言论直呈其对创作的执着坚持和毫不懈怠精神。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系列作品登场文坛后,一直专事创作。但也频的牺牲对她的生活和思想影响很大,她编刊物、参加集会演讲,甚至去前线劳军。并且努力创作,创作了《田家冲》《水》《从夜晚到天明》等作品。到了延安,特别是建国后,随着行政职务的不断升高和增多,革命挤占创作时间,丁玲创作焦虑越来越严重,不断表达希望专事创作的愿望。传记作者谈到:延安时期,“丁玲不大愿意去文协管事,她想要写作。”[4]216并引证丁玲不同时期日记和信件直呈其创作的迫切与焦虑。如1949年5 月24日的日记写道:近一年来,“四处奔波,成绩太少,以后应抓紧时间,多写,多读,多所思索,毋为一不学无术之作家”[2]415!1950年10月给陈明的信中又说:“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写点文章,而且明年一定要写长篇。”1951年8月给周扬的信中也说:“我实在希望我能创作,我要创作,我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对创作有刻骨的相思。”[2]461请求周扬:“不要分配我其它的工作,让我少开会,让我留在家中创作。”[2]462到了新时期,丁玲念念不忘的还是创作,她在1977 年10月给蒋祖剑的信中说:“写点东西,真不容易。多坐一会腰痛,多写一点,手腕痛。想多了,就失眠……可是我们还得努力下去……怎么样也要在生命结束前拿出点东西来,贡献给人民、以求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自己就行了。”[2]589一直到逝世前,丁玲还在“惦记自己的创作,嘴上说她要再活5年,再写5年”[2]756。可见,通过对丁玲不同时期思想言论的梳理,传记作者呈现了丁玲对创作念兹在兹的执着精神。另一方面,传记作者又以丁玲对他人鼓舞话语的独特理解来体现其对创作的痴迷和执着精神。如对《田保霖》受到毛泽东表扬的理解,认为:“那篇文章有什么好呢?……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4]325显然,这是丁玲从自己创作的急切心情出发理解毛泽东的鼓励,充满一种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进取力量。还有,对冯雪峰的批评和鼓舞,丁玲也是从正面吸取前进的力量。传记作者认为真正支撑丁玲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下去的还有雪峰,她要不负雪峰”[4]358。而冯雪峰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高度赞评更是鼓励着丁玲,使她重读雪峰盛赞的“果树园沸腾起来了”,“下决心要修改它(大的修改不可能),至少要把文字上修理得少些缺点或错误”[4]359。可见,丁玲善于从正面吸取有益于创作的鼓舞和力量,积极创作,不断提高。这其实也是其孤傲、倔强精神的鲜明体现。
王本《丁玲传》对丁玲精神个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发掘和呈现,一方面深刻地诠释了丁玲创作艺术个性——主观抒情色彩的成因。可以说,正是由于丁玲将自己的精神个性特质灌注于创作中,形成了漫洇其中的抒情潜流,不论是早期作品的孤独感伤,还是30年代后作品的昂扬奋进等,都使作品染上了一层鲜明的情感色泽。另一方面也深刻地阐释了丁玲之所以成为“男权统治的挑战者”(秦弓语)的原因。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由于鲜明地烙印上了作者倔强、反抗的个性特质,她们鲜有沦为逆来顺受、凄惨悲哀的弱者,而是孤傲、倔强反抗的强者,她们自有内心法则,蔑视陈规流俗,即便遭受不堪的凌辱、摧残,也要从摧残和不幸中反抗出来,呈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同时,还鲜明地体现了丁玲创作与革命信念水乳交融的原因与境状。丁玲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倾向,不仅是她经过漫长探索和实践的结果,更是其精神个性投射到创作中,且随着时代社会发展而走向深入的水到渠成的结果。如前所述,由于丁玲精神个性的投射,其创作始终洋溢着一股强劲的积极向上、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她信守文学应有益于社会人生,促使社会向善、向美发展,应给人以鼓舞和振奋的精神力量,这既是丁玲精神个性与“五四”现实主义精神相契合的地方,也是决定其创作最终趋向革命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因。因此,革命文艺观对于丁玲创作不是外在律令,而是其主体内在性情、气质决定的必然选择。当然,丁玲的这种选择可能会给其创作带来某些影响,但传记或许出于为尊者讳较少触及,是以为憾。
三、丁玲精神个性在文坛交往中的体现:坚忍不拔的精神力量
如前所言,丁玲与人交往看重的是精神和情感世界,而在丁玲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一是创作,二是革命。丁玲一辈子痴迷创作,对创作充满激情和信心。延安时期,她有段时间创作少,心里焦虑,但仍充满信心解释道:“我需要学习新的写作方法,表现新的内容……我很快就会有新的作品问世的!”[4]320“文革”后期刚恢复自由,她便信心百倍,给祖林写信道:“我准备从明年一月就开始重起炉灶,保证平均每天600字……”[2]586当於梨华邀请她去美国大学讲演,她对祖林夫妇说:“祖慧极力主张去,相信有些人说的,中国人不识才,如有外国人捧了,中国人也就捧起来了……但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不靠外国人,我靠的是自己的写作。”[2]681这些都显示了丁玲对创作的充分自信和激情洋溢。同时,丁玲还一辈子念兹在兹地执着追求革命,坚守革命信念。1984年7月恢复名誉的通知下来时,丁玲在协和医院,她激动万分地说:“40年沉冤终于大白了,这下我可以死了!共产党的名誉比生命还宝贵,这等于是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啊!”[2]723李锐在追悼她的文章中也写到:“通知高度评价了她为党做的工作,赞扬她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是的,比起她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着的爱,即使她有过什么过失,又何足计较呢。”[2]722丁玲最不能容忍的,是对她创作的妨碍、革命信念的质疑及革命文艺思想的漠视。可以说,王本《丁玲传》正是从这些方面阐述了丁玲的文坛恩怨纠葛。
首先,与周扬的恩怨主要缘于创作方面原因。传记清晰地梳理了丁玲与周扬结怨的经过。他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周扬比较看重丁玲,有意重用她。两人关系交恶始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丁玲把书稿交给周扬看,请他在出版前提意见,周扬却压着书稿不让出版,丁玲不甘心创作成果被淹没,两人关系自此结下疙瘩。丁玲在日记中写道:“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小人是没有办法的!”[4]397建国后,因为行政工作繁重,加上没有周扬那样的行政能力,丁玲有时焦头烂额,曾在文协机关当着茅盾的面哭诉:“都是周扬,他现在土改去了,什么也不管,叫我来揩屁股。”[2]447丁玲甚至写信请求周扬给她少安排工作,让她有时间创作。1951年8月18日给周扬信中就说:“我实在不愿东做做西做做……你不要分配我其它的工作,让我少开会,让我留在家中创作。”[4]46但她的计划还是流产了。正如传记分析的,丁玲不服从工作安排可能也得罪了周扬,而周扬不断给丁玲安排工作以至其创作计划无法完成焉知又不使丁玲恼怒?终至两人结下不解之怨。
其次,与沈从文的恩怨缘于丁玲担心自己革命信念的被质疑。丁玲与沈从文本来关系很好,特别是也频牺牲后,沈从文陪同丁玲把幼子送回湖南老家。正如传记所言:“在丁玲最困难时,沈从文挺身而出,全力相助,豪侠仗义,患难中见真情。”[4]77丁玲对沈从文产生芥蒂,缘于有人告诉她两件事,一是上海“左联”为营救她曾托人请沈从文共商营救事宜,但被沈从文冷淡拒绝;二是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路过常德,没有去看望丁母。这些后来都得到了丁玲谅解,而沈从文也“始终钦佩丁玲的为人与才华,但只能以文人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愤慨与悲哀,且后来的态度受到胡适影响”[4]124。建国后,两人也一度友好交往。两人关系交恶始于《记丁玲》。丁玲为什么对沈从文好意写作的《记丁玲》如此愤慨?“按丁玲在《也频与革命》中的说法,主要是‘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2]646传记认为,这其实只是原因之一,用丁玲的话来说:“我从来不同沈从文谈政治,我向来忍受不了他对革命的嘲讽。”[2]647事实上,这里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文中提及丁玲与冯达的关系,这是丁玲避之唯恐不及的,“当时因为周扬们死死揪住她的‘历史问题’不放”[2]650,质疑她的革命立场。“而《记丁玲》对于冯达的描述可能给她的申诉造成新的困难”,因此,“她把满腔火气发在沈从文身上”[2]651。沈从文自然也很生气,两人自此结怨终身。
另外,与新时期文坛的复杂纠葛很大程度上缘于丁玲“不合时宜”的革命文艺观。如对“伤痕文学”的批评。丁玲强调:“‘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不少作品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切中时弊,‘这是很好的’,但是,‘还要写出一个强有力的东西,与这个坏,有对比,有斗争’,‘应该把世界写得更有希望一些。’”[2]656-657认为:“不要把整个社会写成一团漆黑,毫无希望,令人丧失斗志,而要把处在苦难中的人物写得坚定、豪迈、泰然,把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亲密、庄重、神圣、无私。”[2]660如前所言,这其实是丁玲孤傲、倔强和反抗的精神个性特质和“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在文艺创作中的反映,也是贯穿其整个创作的强劲精神意志。即便是晚年的《“牛棚”小品》,“也毫无悲切哭啼的调子,通篇洋溢着‘黑暗中的光明’,更有一个乐观昂扬的结尾”[2]660-661。总之,“丁玲回顾风雪世界时,总是着眼于人间温暖,即便回顾‘文革’遭遇,关注点也总在人性的闪光点上”[2]672。又如对待新、老作家的态度,丁玲也是满怀激情,以革命文艺思想去要求和关注他们。她关心呵护青年作家,关注鼓励老作家,大胆如实评价当红作家。她在家里开新、老作家聚会,为他们创造交流机会,但丁玲期待的无拘无束的热烈交流并未实现。她以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时对待徐光耀、陈登科、李纳那一批学员的方式,处理同青年作家的关系,但80年代的青年同50年代的青年大不一样,丁玲一遍遍苦口婆心教诲的要深入生活,要到群众中去,要刻苦炼人,青年人也不大感兴趣,反倒敬而远之,丁玲所期待的融洽和谐关系始终没有实现[2]718-719。等等。可见,丁玲与新时期文坛的复杂纠葛更多源于她对革命文艺思想的坚执信守,而这体现的显然是其贯穿于创作与革命中的精神个性特质。
总之,王本《丁玲传》从丁玲独特的精神个性角度解读其文坛恩怨纠葛,一方面以雄辩的事实和依据还原和阐释了丁玲与文坛恩怨纠葛的某些真相,显示了传记作者在这些问题上的独到发现;另一方面也驳斥了历来在某些问题上学界对于丁玲的各种猜测和诬陷,比较切合丁玲的精神个性特征及其毕生的志业追求实际。
四、丁玲精神个性的艺术呈现:《丁玲传》平实节制的写实风格
王本《丁玲传》谈到张得蒂的“丁玲印象”“是所有丁玲塑像中最完美的一尊”:“长发飘逸,双臂修长,两手支颐,一双大眼睛射放出聪慧、灵秀和满不在乎睥睨一切的傲气,……捉到了丁玲的神韵。”[2]713事实上,王本《丁玲传》也是现有丁玲传记中最得传主神韵的一部,它抓住和呈现了丁玲的精神个性特质:孤傲、倔强和反抗。传记开始不久,传记作者就提到瞿秋白鼓励丁玲的“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及“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认为这些话“极为准确地预见了她的一生”[4]32。因此,他们紧紧抓住丁玲这些精神个性特质在其创作、革命及文坛交往中的体现,并以一种质朴、平实和节制的写实风格呈现出来。
首先,王本《丁玲传》“把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和传记写作,从传奇意气的浪漫主义套路推进到实事求是的写实主义路径,这种求真务实的学术追求是很难得的”[4]2。传记在结构体式、表现手法和修辞用语等方面没有什么新奇出彩的地方,相反却显得中规中矩、土头土脑。它平铺直叙地从丁玲的出生开始写起,然后按照时间顺序,把她一生的思想、情感、活动和经历叙述出来,将其不同时期的作品穿插进相应的叙述中。但由于两位作者始终紧扣丁玲的精神个性特质来叙述,不仅丁玲精神个性的孕育、成型得以真实具体地再现,而且也正是传主精神个性这一贯穿线使得枯燥、僵硬的生平资料和重要事件等得以温润地清晰呈现。如对丁玲与陈明恋爱婚姻事件的叙述,作者引证了《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萧军日记及一些谈话资料等。丁、陈两人因为年龄、经历与地位相差悬殊,恋爱招来许多非议。陈明感受到了丁玲炽热的感情,也敬佩和爱慕丁玲,但对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却取逃避态度。“丁玲却紧追不舍,不肯放弃。”[4]208后来,陈明与席平结婚,丁玲很痛苦、感伤,但她“一面感伤着,一面又努力克服感伤,想要振作自己。她在窑洞里贴上裴多菲的一段格言:‘我要同运命来决战,它不至于就完全征服了我,人生是如何的优美啊!我要聚千古生命于一身地生活下去。’”[4]225两人最后勇敢走到一起,白头偕老。从作者质朴、平实的叙述中不难感受到丁玲那股倔强、反抗的精神力量。又如对1943年“丁玲延安时期最压抑的一年”的叙述。作者引证《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延安日记》等史料,努力再现那段特殊历史背景下丁玲的艰难处境:由于“历史问题”被揪住过不了关,“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在日记中写下:“夜不能寐,奈何!”[4]307但同时又自我鼓劲:“我要坚持对党的信念我才能得到平安。党终会明了我的……我应该与平日一样的尽一个做党员的本分,那末生活着,那末工作着才对。”[4]308可以说,正是丁玲倔强、坚韧的精神个性帮助她度过了那段难熬时光,使那些枯燥、生硬的历史资料发散着温润的人性光泽,也使今天的读者在压抑、阴郁中感到一丝振奋。这种平实质朴的写法体现了传记文学写作要求与作者创作风格追求的统一。传记文学是如实书写传主一生的经历事迹,这就要求做到不虚美、不隐恶,不能因为艺术观念和创作手法的新奇变幻而导致历史失真。而两位作者所追求的,正是通过对丰富材料的分析、剪裁、取舍,“梳理出传主的思想和情感脉络、思想和情感发展的历史”,以写出“丁玲的所思所想,心路历程”[2]773。这种以丁玲精神个性作为贯穿线的平实写法使读者“由文及人,深入了、贴近了丁玲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2]774,从而呈现了一幅丰富立体的丁玲雕像。
其次,王本《丁玲传》情感真挚而有节制,做到了深情而不恣情。传记作者王增如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与传主有过长时间亲密接触,对传主有着较深厚的崇敬和钦佩情感。而且传主又是一位情感丰富、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作家,写作传记时情感火候如果掌控不当,便会流于研究者所言及的“浪漫传奇的叙事作派”或者“感情主义的论事态度”[4]4。但传记作者在这方面处理得相当成功。一方面,作者以平视而非仰视的态度体验和书写了丁玲的思想、情感与经历。如对丁玲初到陕北生活经历的叙述。传记作者先是体验式地叙述丁玲初到陕北时并未受到礼遇,由于她对红军生活什么也不懂,红军当时也不太懂得团结知识分子,因此她受到了冷遇。然后又超拔出来概括道:“丁玲的境遇其实很正常,部队行军打仗,非常紧张和危险,女同志来,近乎添乱,而且红军战士们也不知道这个著名女作家到底是干啥子的。在革命的实际中,文人的特别敏感和格外自尊是需要纠正的——当真正变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就不会那么敏感于别人怎么对待自己了。”[4]157可见,传记作者采取的是既置身其中又出于其外的冷静审视立场,而没有流于与传主同样的失落情绪。又如对新时期周扬阻碍丁玲历史问题平反的叙述,作者先直接征引贺敬之接受他们采访时的谈话资料,谈周扬等人对于中组部文件的态度和做法,然后评论道:“周扬是丁玲两次冤案的主要责任人,在丁、周关系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但是他在丁玲平反问题上始终坚持错误,对于一个被整得伤痕累累的革命女作家没有丝毫忏悔表示,‘一个对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人,一个提到自己整人的历史就流下眼泪的人’,在丁玲这块试金石面前,暴露出灵魂深处的阴暗。”[2]724后半句是引证他人话语作结,情绪的流露适可而止。可见,传记作者在情感的把握和调控上相当讲究,适中、节制。另一方面,对于丁玲复杂的情感经历,传记作者用笔也是适度节制,没有落入编织浪漫传奇套路。丁玲可以“算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不仅其创作曾数次引领文坛风骚,而且其人生也曾几度坎坷、备受磨难,并且个性倔强、感情丰富,爱情婚姻生活颇富浪漫性和戏剧性,这一切原本是可以大书特书的浪漫传奇之事。”[4]4确实,有的传记就专以女作家的情感世界来编织传奇故事吸引读者眼球,但王本《丁玲传》有别于此,它以“朴实的叙述和平实的叙述语调”“本真地勾画出丁玲坎坷一生的生命历程和一以贯之的性格本色”[4]4。在展开丁玲情感婚姻叙述时,先以一段总述奠下全书情感言说的基调,“丁玲与雪峰的恋爱,是一生中情感最炽烈的一次,也是没有结果的一次。此前她与也频,还没有尝到恋爱的滋味就直接步入同居,‘我和他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没有不安过’。此后她与冯达,主要是过日子的伴侣,谈不上多少感情色彩。再后来与陈明恋爱时,她已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理智得多,沉稳得多,显出一种成熟者的恋爱”[4]88。后来关于丁玲的恋爱婚姻叙述便紧扣其精神个性特征如实叙述,适可而止,绝不枝蔓。如前所述的丁玲与冯雪峰的情感便是紧扣雪峰对丁玲的鞭策和鼓舞来书写。还有对丁玲与冯达关系的叙述也是如此,传记作者设身处地从当事人角度出发,引证不同时期史料,复原历史情境,然后做出客观公允、合情合理而又不失人性温情的叙述与评价,真正做到了深情而不纵情,平实而不平淡。
综上所述,王本《丁玲传》没有什么花样翻新的噱头,也没有对浪漫情感的猎奇,而是紧紧抓住丁玲的精神个性特质在其革命活动、文学创作及文坛交往中的具体呈现,以质朴而诚挚的情感、平实而节制的叙述为我们镌刻了一幅“飞蛾扑火”者——丁玲的精神雕像,为推动丁玲思想与创作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研究。
[1]秦林芳.丁玲评传·后记[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3]丁言昭.丁玲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4]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5]李向东,王增如.无奈的涅槃——《丁玲传》作者访谈录[J].社会科学论坛,2015(11):144-156.
[6]杨桂欣.丁玲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239.
[7]高华.从丁玲的命运从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J].炎黄春秋,2008(4):55-62.
[8]转引自丁言昭.丁玲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46.
[9]鲁迅.鲁迅杂文全集:革命文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302.
[10]彭漱芬.迷人之谜:丁玲[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田皓)
Review of Ding Ling’s Biography Written by Li Xiangdong and Wang Zengru
Ding Ling’s Biography written by Li Xiangdong and Wang Zengru expresses Ding Ling’s charm the most.It not only summarizes accurately Ding Ling’s solitary and proud,stubborn and rebellious spirit,but also impenetrate this spirit throughout her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tacting with others in the literary circle,and so on.On the one hand,it carefully combs and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ng Ling and her creation and revolution and show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revolution and literature in twentieth Century.And on the other hand,with the explan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and the spirit of the characters in Ding Ling’s works of different periods,and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Ding Ling’s persistent spirit of writing,it shows Ding Ling’s spirit.Moreover,it also explains the feeling of gratitude or resentment in the literary cir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ng Ling’s unique spiritual personality which has formed her persistence in writing and belief firmly in revolution. And these are presented in a simple,plain and controlling realistic style,which makes the seemingly ordinary and plain biographical writing contain actually an inherent spirit.
Ding Ling;stubborn;resistance;revolution
CHEN Jiaohua
(School of Humanities,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 215009,China)
I206.6
A
1674-9014(2016)04-0071-08
2016-05-12
陈娇华,女,湖南郴州人,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