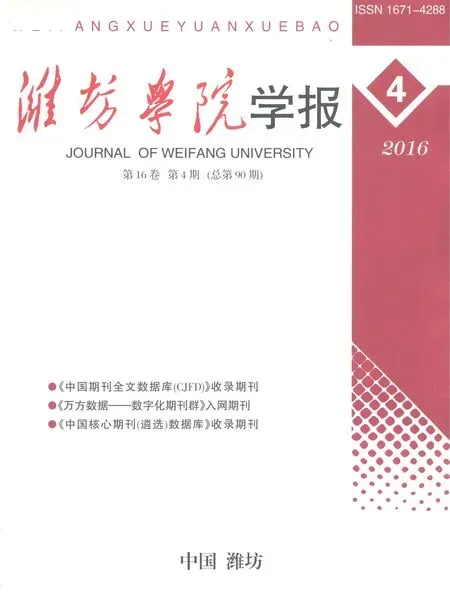客观归责还是中国特色
——兼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致人死亡
2016-03-16郭自力陈文昊
郭自力,陈文昊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客观归责还是中国特色
——兼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致人死亡
郭自力,陈文昊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中被害人自杀的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归入“致使被害人死亡”调整。客观归责理论是对以“条件说”为轴心的归责体系的限缩,无论根据“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还是“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都倾向于不将被害人自杀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但这一结论在我国不能不假思索地加以套用,考虑到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和司法实践的做法,客观归责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将被害人自杀结果归责于行为人有一定道理。在我国,可以适用类型化的归责体系。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客观归责理论;被害人自我答责
一、问题意识
毋庸讳言的是,近年以来,德日刑法理论对我国的渗透是空前的。如果说我国以苏联体系为轴心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自甫建以来一路高歌、披荆斩棘,那么在德日体系的大刀阔斧之下已经犹如投入石子的水面,而变得波澜顿起、鱼龙混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现在在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之上运用德日理论进行犯罪构成理论的修正,内部之间并不匹配。我们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就像一辆车,发动机是桑塔纳的,轮子可能是捷达的,方向盘是奔驰的,各种零件不匹配,知识混杂”。[1]就以客观归责理论来说,近年以来在我国可谓气势汹汹、难以抵挡;由该理论生发的理论大厦雄伟瑰丽、叹为观止。然而,在这样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理论转向”背后,却似乎缺乏这样的思考: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抑或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客观归责理论得以植根的土壤?不难发现,我国对于客观归责理论的探讨大多游离于总则的框架性层面。问题在于,放眼冰山下的潜藏辽阔海域,如何通过客观归责理论对分则中的罪名进行解构与剖析,以便理论的“公器”能够指导司法实践中的正确运作,并非一个不言自明、不争已明的问题。
我们不妨以一个案例作为切入点:李某与有夫之妇郭某存在不正当关系,并要求其离婚。郭某不从,反而提出与李某断绝关系,李某便因此经常打骂郭某,强迫其离婚。2001年11月5日,李某又一次到郭某家对其施暴,导致郭某头破血流。2001年11月28日晚,郭某因受到长期恐吓与羞辱服毒自杀。法院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4年,赔偿经济损害2万余元。[2]
毫无疑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了《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致使被害人死亡的”的法定刑。换言之,法院认为,被害人自杀的行为也被视为“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加以调整。无独有偶,在其他的一些罪名中,将被害人自杀的结果归咎于行为人的做法并不罕见。例如吴某某犯侮辱罪中,法院也指出,由于行为人引起被害人自杀的严重后果,在量刑上应当予以考虑,因而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两年。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将被害人自杀归责于行为人的做法似乎是不容理论置喙的,然而根据德日刑法理论,尤其是客观归责理论,被害人自杀的结果能否解释进入“致人死亡”的范畴之内,进而归责于施暴的行为人,非常值得怀疑。本文就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为切入点,首先剖析传统教义学的分析框架与结论,而后进行能否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的本土化反思。
二、客观归责理论的分析框架
刑法是一套具有大脑与理性的工具。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对规则的“泛化”与“神化”,而对规则背后目的理性的“弱化”与“淡化”似乎是借鉴德日理论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危险领域。正如玩游戏的小孩,执着于输赢,却忘了玩游戏的目的;犹如构建大厦的工人,着眼于构建,却不知楼宇的用途。客观归责理论在我国就是一套被“泛化”与“神化”的理论体系。
其实,一言以蔽之,客观归责理论建立伊始的旨趣就在于限缩归责的范围。从本质上说,刑法理论就是一套改头换面的归责体系,因此,如何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是整套刑法理论的核心命题。传统理论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以条件公式为核心展开。在具体判断上,“条件公式”完全采纳概念法学的进路,“如果没有A,即没有Z,则A是Z的原因”的因果法则标示着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分析范式。这就犹如在经典力学之中,知道了太阳系组分的位置,就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和解释太阳系的运动行为。同样的道理,看到了背后有刀的被害人以及握刀的行为人,就可以当然地肯定因果力的作用。因此,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归责的落脚点是可能被归责的个体,而基本的归责方式是运用“条件公式”及其一系列的修正公式进行检验。
这种因果律的判定固然简单易行,但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处罚范围无限扩大的问题。一开始,学者对于“条件公式”的问题只是通过各种“修正理论”零敲碎打地修修补补,但最终发现,来自自然科学的因果律及其修正理论最终无法与作为评价体系的刑法理论完全弥合,在这种背景下,客观归责理论应运而生。例如,在德国刑法理论中,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范围有过分扩张之嫌,提供毒品导致他人死亡的情况下甚至也可以被认定为本罪。而客观归责理论的内核就在于限制处罚范围,防止犯罪圈的过分扩大,削减过失致人死亡罪范围过于宽松的归责范围。
事实上,倘若客观归责理论与传统因果关系理论逐一比较,可以发现其中最闪亮的两颗明珠在于规范保护目的的检视与自我答责理论的渗透,它们在对因果关系的限定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无论根据其中的哪一套理论,都可以将被害人自杀的情况排除在归责圈以外。
(一)规范保护目的理论
罗克辛教授举了两个例子用以说明规范保护目的在客观归责理论上的判断功能。例如,两辆没有照明的车辆一前一后行驶于黑暗之中,前面的车发生车祸,如果后面的车点亮车灯,结果就不会发生。再如,牙医为被害人拔牙时没有按照规定找麻醉师进行麻醉,结果被害人因心脏有病而死亡。事后确定,这种病麻醉师也不可能检验出来。[3]
在这两个案件中,罗克辛教授指出,“不允许性风险的实现永远与限制许可风险的谨慎规范的保护目的休戚相关,而非与刑法的行为构成的保护目的有关”。[3]在上文的案例中,要求车辆打开照明灯的规范目的在于约束驾驶者自己的行为,防止因为视线不清发生事故,这一规则的旨趣不在于要求驾驶者开灯为前方的人照明。同样的道理,规定必须由麻醉师实施麻醉的规范也是旨在防止其他医师在实施麻醉中的不当操作,并非为了防止他人在麻醉过程中因心脏病而死亡。因此,在这两个案件中,行为人虽然制造了不容许的风险,但该风险与相应规范的保护目的扞格不入,因而不应当被归责。
将被害人自杀的情形放到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框架之下检视,不难否定因果关系的成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只有违反注意规范所造成的风险才具有客观上的可归责性,[4]毫无疑问的是,“致人死亡升格处罚”的法定刑配置都是旨在防治危害行为本身的危险性。例如,抢劫致人死亡相对于抢劫罪而言进行了法定刑的升格,是为了对抢劫行为本身的致人死亡的危险性进行强调,换言之,只有在抢劫行为本身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场合能够适用加重情节的法定刑。再如,破坏交通工具罪中的“致人死亡”一定是与破坏交通设施行为本身休戚相关的、与交通工具毁坏、倾覆危险之间相勾连的结果。倘若行为人在撬动铁路的过程中,飞起的铁片将路人砸死,无论如何也不能以“破坏交通设施致人死亡”的法定刑相绳。
因此,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就决定了,与危害行为本身相脱嵌的被害人自杀结果,并不落在创设规范的旨趣之内。如果根据文义管窥规范的保护目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所保护的是被害人的自由权,因此“致人死亡”这一档法定刑的适用也应当是在侵犯被害人自由的过程中发生的,被害人自杀的行为并不能被囊括于归责体系以内,因此行为人不对被害人自杀的结果承担任何责任。侮辱罪、诽谤罪、虐待罪的规范也是如此。
(二)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
规则理论归根到底解决的是“如何进行风险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面对业已发生的损害结果,如何将风险分配给相应当事人的问题。在被害人明知风险而接受结果发生盖然性的场合下,分配给行为人的责任显然更少,而被害人因自我答责承担更多的责任。不难发现,现代社会的法秩序是构建于自我决定基础之上的,而自我决定权又是自由的核心,个人通过其自我决定而感受并实现自由。[5]因此,一个法治国家不应当基于“家长主义”的泛滥褫夺公民的自主决定权,在被害人能够自我决定的情况下,只要这种处分不损害公序良俗,就应当被尊重。正如康德所指出的,“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依据,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6],自我决定是自由的核心命题,也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石而存在。[7]
例如,在“梅梅尔案”中,乘客明知在恶劣天气摆渡有船体倾覆的风险,仍然不顾船工劝阻,搭乘该船,最终船覆人亡,在这种情形下,因为在恶劣天气乘船背后的风险在一般人看来都是明确的,考虑到两方信息的相对对称性,就可以认定被害人的自我答责。在日本的“赛车案”中,赛车经验丰富的被害人指导行为人以一种危险的方式驾驶赛车,最终赛车失控,被害人死亡。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被害人在信息的获取上与行为人具有相同、甚至是更为优越的地位,因此被害人对所造成的结果自我答责。
已如前文,德国刑法中形塑客观归责理论的价值意涵之一在于限缩实践中过于宽泛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因果关系认定。对此,罗克辛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行为人自我负责和已经实现的自我危险行为并不属于一种身体伤害或杀人犯罪的行为构成,一个仅仅造成、使其能够和要求自我危险的人,不会因此受到刑事惩罚”[8]。因此,行为人将毒品给上瘾者,上瘾者在吸食毒品后死亡的,根据客观归责理论,行为人并不对此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同样的道理,被害人在受到侵害之后死亡的,也属于被害人的自我答责,因此不应当将死亡的结果归咎于行为人。
三、具有本土特色的归责思维
客观归责理论否定将被害人自杀的情形归责于实施危害行为的行为人,这点在德日的教义学体系中结论几乎别无二致。例如,“禁止溯及理论”认为,异常的介入因素阻断了危险的现实化进程,因而切断了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脐带。正如山口厚教授所指出的,在一般治疗就容易治愈的疾病的成和,介入了被害人及其不恰当的行为,导致病情急转直下直至死亡的,应当否认因果关系的成立。[9]因此,通说在结果加重犯的划定上,都认为需要满足“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这一要件[10],否则不能适用加重犯的升格法定刑。
但是值得反思的是,无论是客观归责理论,还是禁止溯及理论所得出的结论,都可谓是在德日刑法理论的土壤上开出的花朵。因此,它能否直接移植到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并作为引领司法实践航向的指挥棒,实在是存疑的。进一步讲,无论是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还是被害人自我答责体系,只有明确在我国植根的依据,才能“名正言顺”地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得以生发。
在此之前,不妨对我国对“被害人自杀”这一结果进行规制的司法解释进行简单扫描:《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六条对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立案标准进行了界分: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枉法裁判,致使当事人或者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由这两个司法解释来看,被害人自杀的情节在某些罪名中完全可以被归责于行为人。刑法理论中也一般认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中的“致被害人死亡”包括了因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而直接引起被害人自杀身亡;虐待罪中的“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也包括被害人不堪忍受虐待而自杀、自伤,造成死亡或重伤。[11]
由此可见,我国的归责体系与德日刑法中运用客观归责理论抑或是“禁止溯及原则”得出的结论是相左的。那么,这样的归罪体系是否存在合理性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不得不考虑我国司法的民众接受程度及本土现实情况。
例如,在冯军教授所举的搜集睡衣被毒案中,行为人发现有人入室偷睡衣就将桌上的水杯中投入毒药。窃贼潜入房间后因口渴喝水身亡。本案中,冯军教授指出,“只要行为人不应当知道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闯入自己家中,就不对被害人的死亡承担责任,被害人对自己的死亡承担责任”[12],这显然是运用自我答责理论得出的结论。但是,在我国,这样的结论很难被一般人接受。在司法实践中,在自家种的西瓜中下毒导致偷瓜者死亡的案例基本以故意杀人罪相绳,邵基敏投放危险物质罪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由此可见,在我国,被害人自我答责的理论在司法实践中至少没有得到完全的肯定。在被害人自杀的场合,将被害人的死亡归责于行为人,可以说具有相应的社会根基存在。
(一)民意为中心的刑法观
刑法不应当囿于精英之中,而是芸芸众生的晴雨表。为避免立法者的专断,国家权力应当受到制衡,相应地,刑法应当从一元体制转入包括国家、社会、个人的多元价值体系。[13]在此意义上说,刑法的社会属性不应当被无视甚至抹煞,[14]正如卢梭所说,道德、习俗、信仰,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它不是刻在大理石上或铜表上,而是人民心中,形成了国家真正的体制。[15]
“社会是刑法走不出的背景”[16]。因此,一方面,必须打破仅仅依赖成文法的桎梏,恢复习惯法在刑法中的“话语权”,因为如果仅仅依赖成文法,难以在最大程度上伸张正义,弥合社会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鸿沟与裂痕。另一方面,刑法价值追求的实现需要充分汲取外部的知识供给,由“以牙还牙”转变为“为了没有犯罪”的价值诉求,为长期受到国家捆绑的社会解绑。[17]正如劳东燕教授指出的:“在刑法领域,公众对于安全的现实需求会汇聚成刑事政策上的压力,并通过目的的管道传递至刑法体系的内部,驱使刑法体系向预防目的的方向一路狂奔”[18]。
由此可见,教义体系的形塑无法与一般民众的观念相脱嵌,换言之,教义学中的归责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规范保护目的,还是被害人自我答责原理,都并非亘古不变的铁则,相反,他是一套流动的、类型化的工具。因此,教义学体系会结出怎样的果实,与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环境、民众观点、社会氛围都是密不可分的,试图用一套“铁板理论”解决所有问题的做法,甚至是对国外理论的照搬照抄,只能是自欺欺人的“鸵鸟思维”。
(二)积极一般预防理论
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将民众作为规范维持的社会心理基础,将民众心理的安抚作为刑罚的目标,在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主张者眼中,刑法不是“大棒”,而是救济社会生活利益侵犯的最后也是必要的手段。[19]
毋庸置疑,依照消极一般预防理论的观点,国家直接将这种刑罚权指向了权力的来源,这无论如何难以令人接受,因为被害人或者民众应当受到的待遇是安抚而不是提防。[20]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则是将视野从预防转向了安抚,更加契合公众的法期待。
如果说司法的机能之一是抵消犯罪不良影响,消弭公众怒气的话,那么刑法机能在这一点上具有更鲜明的体现。杜格尔·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写道:“在中国,人们自杀不是因为厌倦生活,也不是因为想从耻辱或悲伤中解脱的怯懦想法,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愤怒,或者他知道他的死会陷对手于不义”。[21]从唐福珍,到陶兴尧,到钟如琴,一起起自焚血案表明,自杀相对于被杀对于公众而言更加容易撩动引起公众的敏感神经,一起自杀案件所产生的社会不良影响绝不亚于一起致死事件。因此,为了更好地消除犯罪行为的社会不良影响,将被害人自杀的结果归属于实施实害行为者并不违反一般民众的法感情。
四、类型化的归责体系
由此可见,在归责的问题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生搬硬套德日的客观归责理论抑或禁止溯及原则,因为只有适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理论才是最好的理论。在此意义上,将归责原则予以类型化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类型化的思维意味着,不同的案件不会适用同一套着手时点的判断体系。换言之,针对特定案件中的规范范围,适用不同的类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至于应当纳入何种标准之中加以考量,则需要进行具体的、个别的探讨,考虑到对具体罪名中构成要件的解释,以及刑事政策的合理需求。
毋庸讳言,就一个行为而言,如果它的处罚必要性越高,就意味着对因果链作用力的要求越弱,也就意味着规范的范围越大。因此,如果以P表示处罚必要性,以Q表示归责范围的话,那么可以用P/Q=a来表示对因果关系强弱的要求受处罚必要性影响的关系,在特定时期,a是一个恒定的常数,P与Q成正比。
在类型化思维的道路上,劳东燕教授的观点也许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她将因果关系分为“造成型因果关系”、“引起型因果关系”、“义务型因果关系”、“概率型因果关系”四种,因果关系的关联力依次递减。可处罚性越高时,对关联力的要求就越低,如此一来,就实现了因果关系的类型化处理。[22]
以“盖然性”归责为例,它对因果关系的作用要求极低,入罪极其容易,因此只能适用于极其严重的犯罪。例如,日本1968年的“富山骨痛案”中,裁判所就是运用了“疫学因果关系”的分析进路对无法切实查明、但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被告公司进行了归责。本案中,能够查明的事实仅包括:第一,在被告排放镉的地区有骨痛病发生;第二,镉排放越多,骨痛病发病人数越多;第三,镉排放少的地方,骨痛病患者少。判决最终指出,从骨痛病的病理上说,主要的因果关系是可以被确立的,虽然不否认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查明和研究的课题。[22]该案的判决对日本因果关系理论的推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是“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得以运用的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当时的一种意见认为,在镉排放较多的场合骨痛病的发病率高,这表明骨痛病的发生极有可能是由镉导致的,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了其他未知的因素导致了这一结果的发生,而以当时的科技无法查明病发的切实原因,因此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当认定为没有因果关系。但是,考虑到公害犯罪的严重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做到完全的“排除合理怀疑”,但是近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还是可以被采用。
“风险升高理论”也是采取了概率型因果关系的认定进路,但与“疫学因果关系”所不同的是,在“风险升高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即使确定地不满足“条件公式”的要求,只要行为本来能够实质性地降低危害结果出现的风险或者概率,还是可以肯定因果关系。这一立场体现在在德国著名的“卡车超车案”中。本案中,卡车司机以0.75米的距离违规超越被害人的自行车,因而违反了交通规则中1.5米的安全距离。超车的过程中,醉酒的被害人从自行车倒下,被卡车轧死。后来查明,即使保持1.5米的安全距离,仍有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本案中,如果采用“风险升高”理论,就应当认为,由于卡车司机的行为提升了被害人死亡的风险,这一点足以使得卡车司机为被害人的死亡承担责任。在笔者看来,“风险升高理论”是作为传统因果律的补强规则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当刑事政策需要对严重的犯罪进行处罚,而在单纯因果律上无法满足“条件公式”要求的情况下,考虑到结果发生风险这一抽象指标的提升,就可以对相关行为进行归责。与“疫学因果关系”不同,“风险升高理论”解决的往往是直接针对法益创设风险的情形;但与“疫学因果关系”一致的是,他们都试图通过对传统因果律的修正与补强回应刑事政策的要求,以解决结果归责的问题。
五、结语
一个民族只有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刑法学者也要时刻仰望星空,俯身触摸心中的道德戒律,始于守望、终于信仰,刑法学才有希望。而我们所仰望的这片璀璨的星空绝不仅仅是厚可盈尺的德日理论,更是纷繁复杂的植根于我国的社会光影。
我国现行理论对于归责问题的探讨,大多是附丽于德日理论的鹅行鸭步、东施效颦,因而很难创建出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无论是客观归责理论,还是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不仅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而且难以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接洽。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中的“致使被害人死亡”在判例中可以包括被害人,以及我国一系列的司法解释中将“被害人自杀”归责于行为人的做法,都是这一点很好的注脚。
[1]陈兴良.刑事法评论:第14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95.
[2]李翔.刑事疑案探究:第2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20.
[3]许永安.客观归责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62.
[4][9][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56,264.
[5]陈兴良.教义刑法学: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324-325.
[6]冯军.刑法中的自我答责[J].中国法学,2006,(3):93.
[7][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9: 2.
[8][12]冯军.刑法问题的规范理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4.
[10][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63,81.
[11]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69,817-819.
[13]张明楷.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J].中国法学,2006,(4):24.
[14]利子平,石聚航.统合宪政建设模式与刑法社会化的实践阐释[J].法治研究,2010,(11):47.
[15][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徐强,译.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7:137.
[16]利子平.刑法社会化:转型社会中刑法发展的新命题[J].法学论坛,2013,(1):27.
[17]陈文昊,王利峰.走向开放体系之路——刑法思潮的跌宕与流变[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1):54.
[18]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J].中外法学,2014,(1): 81.
[19][20]陈金林.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113,116
[21]海青.始于自杀,终于“自我”[J].读书,2010,(6):32.
[22]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4-145.
[23]赵红艳.环境犯罪定罪分析与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1.
Objective Imputation o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Comment on Violent Intervention in Marriage which Causes Death
GUO Zi-li,CHEN Wen-hao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Committing suicide of the victim of violent intervention in marriage is considered into‘cause the death of victims’.Objective imputation is the restrain of the system centered on the‘but-for’rule.No matter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protection of regulation or self-responsibility of the victim,committing suicide of the victim of violent intervention in marriage can’t be considered into‘cause the death of victims’.But this conclusion should not be transplanted into our country without consideration.Considering the accepting degree of general people and operation in juridical practice,objective imputation can’t be used totally in our country,considering committing suicide of the victim of violent intervention in marriage into‘cause the death of victims’is reasonable on some degree.In our country,the typification of imputation system can be considered.
violent intervention in marriage;objective imputation;self-responsibility
D924.3
A
1671-4288(2016)04-0058-06
责任编辑:王玲玲
2016-06-22
郭自力(1955-),男,河南焦作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刑法;陈文昊(1992-),男,江苏镇江人,北京大学法学院2015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