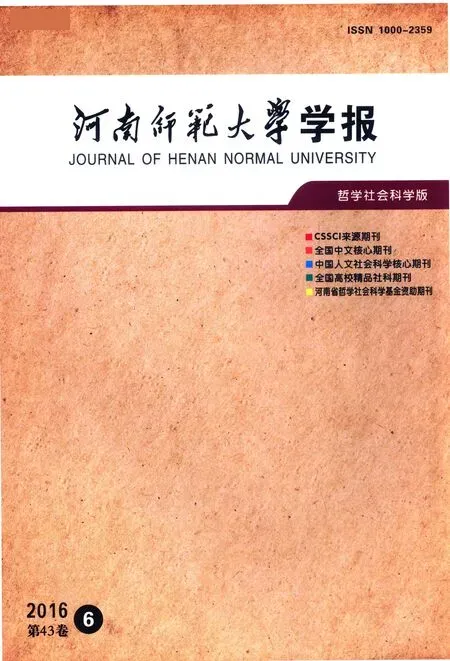试论世纪之交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
2016-03-16于沐阳
于 沐 阳
(延边大学 人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试论世纪之交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
于 沐 阳
(延边大学 人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世纪之交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大体上从几个向度上进行。第一个向度是指向当下,关注的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在社会急剧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呈现的是原有价值体系的崩塌,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建立起来的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们的集体迷失。第二个向度是指向历史,作家站在1990年代后的立场去挖掘、再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关涉中国革命道路,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改造”等重大问题,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在反省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表现、人性表现;透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再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期间既包括曾经的精神磨难与苦痛,也有进入到转型期后精神取向的下行;世纪之交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分化与丰富,既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商业化的世俗社会中寻求生存和尊严的艰难与多样性,同时又突显了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努力。
世纪之交 知识分子 人文精神 历史反思
殷海光曾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己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1]中国知识分子注定是命运多舛的,五四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为辉煌的时代,他们倡导的启蒙、科学与民主理想,生发出开放、包容的现代意识,使中国在真正意义上走向了现代化之路。这之后,启蒙的诉求逐渐被民族救亡与大众翻身的现实所覆盖,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从人民大众的启蒙者变成人民大众启蒙的对象,这种角色的转换,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从人民大众的“立言者”、“代言人”逐渐成为权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直到新时期,才重新接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试图恢复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和价值精神。但是199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世俗欲望与拜金主义的兴盛及风起云涌的大众文化的席卷,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历史上的坎坷、磨难与精神上的痛苦、失落之后,角色认同与话语方式又一次面临危机,再一次陷入到了失语的窘境。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面对的精神图景是革命想象的瓦解、乌托邦理想的破灭、权威神话的终结。在巨大的精神失落与惶惑中,曾经坚定不移的信念、理想遭到怀疑、解构,新的价值趋同始终无法建立起来。在这场深刻的社会、文化转型中,中国知识分子价值立场、文化理想、人生追求和身份角色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陷于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城市与乡村、理性与欲望、沉沦与救赎之间的冲突与挣扎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路在何方,精神家园何以重建并确立,在时代浪潮中能否创造性地完成传统性格的现代化转型。是坚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操守与批判精神,在物欲至上、价值失范、信仰危机中保持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人生关怀与终极关怀,还是逃离,放弃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与人格操守;是遁隐,以宗教的情怀回到内心,还是认同,淹没于物欲的横流之中。借助于对小说中知识分子精神向度与心路历程的梳理、辨析,本文将力求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文化的等多种视角去思考这些问题,努力索解可能存在的答案。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对于“存在”的“发现”和“询问”。它的使命在于使我们免于“存在的被遗忘”[2]16。“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他还说,“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他画“存在的图”[2]42。文学作为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与记录,是社会思潮、时代特征、民族性格的艺术副本。社会历史的演进,时代风貌的变化,人的精神世界的波澜都会真切地反映到文学之中,其间也必然会留下了知识分子的投影。文学形象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参照物,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作家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理解与精神认同,是文学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精神的印记,形象的解读必然要涉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机制、外在影响与作家自身的身心历程。因此,探讨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学之关联,考察小说创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无疑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世纪之交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从整体上看几乎涵盖了全部知识阶层,教师、作家、医生、记者、科技工作者等等,无不是纯正的社会知识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他们“存在”的追问正是使我们免于“存在的被遗忘”。他们的生存图景预示了在我们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知识分子并没有解决身份认同、价值选择、精神归宿等等关于人的存在的基本问题。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身份认同的矛盾与多变,价值选择与精神归宿的迷茫与困顿。 纵观世纪之交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大体上从以下几个向度上进行。
一
第一个向度是指向当下,关注的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社会急剧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知识分子也迅速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投身于市场,很快与世俗合流,呈现出物欲化、世俗化的走向。一部分则保持着胆小、谨慎的本性。而形象的演进也呈现出随时间的递进体现不同特点,1990年代初的清贫人生以及之后的物欲认同。
在1990年代初期,从物质层面上说“陆文婷们”并没有消失,在知识分子群体里,他们依然大量的存在着,生活着。《焚书》中的楚教授、《木樨地桥》中的马岱、《后顾之忧》中的余庄藻、《放飞的希望》中的老校长、《行云流水》中高人云与妻子梅洁文、《多恼河》中的王晓兰、《城市生活》中的杜立诚和宋玉兰、《学者之死》中的吴谭,等等。他们的生活平庸而琐碎,现实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决定了累、恼、烦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由于被现实潮流所排斥,而常常生出巨大的空洞感。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在社会环境的挤压下,知识分子物质上的困窘与精神上的沉重、痛苦和理想的失落。在风起云涌的市场大潮面前,他们感受到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后深深的无奈。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无法真正融入当代现实环境的困窘与焦虑,传统的道德观念与自身的弱点使他们卷缩在自己营造的围城里。在这个越来越注重物质利益的时代里,他们的精神成果不仅无法与经济受惠联系起来,甚至没有机会面世。他们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里,孤独地品尝着精神的寂寞直至崩溃。他们是1990年代初期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主体,所谓现代化的诉求与实践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我们无法要求他们在躁动社会的与扑面而来的世俗之风中仍然保持一颗平静之心,独善其身的道德要求对于他们而言只能是最基本的底线。同传统一代知识分子相比,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同样要面对生活的各种压力与烦恼,但与老一代的失落、无奈不同的是,他们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困顿、焦虑与彷徨,如《生活无罪》中的何夫、《怀念一个人》的姜辰、《心灵安居》中的庞蕤、《打工实验》中的秦天白,等等。他们以知识者的身份走进商海,加入到“掘金者”的行列,却在迈出第一步的一刻放弃了知识者的身份属性,形成了身份与行为的分离。他们的放弃与重新选择,一方面源于物质生活的极度困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曾经与老一代知识分子清贫物质生活相伴相随的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虚假性与脆弱性。他们不屑于与不愿去守住那份苍白的精神高贵与道德典范挂身的知识分子标签。遂迅速地加入“掘金”者的洪流,不仅意味着要改变生活方式,更意味着与过去的精神标志决裂。无论他们愿意不愿意,市场中的沉浮正是他们当下乃至未来生活的主旋律。
在经历了19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刚刚兴起的阵痛与躁动之后,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平缓稳健。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主导下的物欲之风、世俗之风席卷一切,社会秩序以及人的道德准则、价值理想等都处于重建过程之中。就知识分子的文学表现而言,由于经济生活的急剧变化带来了精神负效应与物质的清贫状况在社会趋于平稳后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价值取向、道德操守、人格情操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精神层面的价值失范、道德滑坡与观念颠覆,如《导师死了》中的吴之刚、《异乡人古小奇》中的古小奇、《小人不可得罪》中的何友渔、《瓜田里的郝教授》中的郝教授、《热狗》中的陈维高、《你以为你是谁》中的李老师、《饶舌的哑巴》中的费定、《暗哑的声音》中孙良、《夜游图书馆》中的陈亮,等等。他们的精神状态构成了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文学表现的一道颇为耐人寻味的精神景观。在物欲的冲刷下,理想的崩毁、精神的萎顿,使友情、亲情、爱情乃至理想、信仰都发生了霉变。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告别崇高,精神光环褪去之后,走向世俗的知识分子灵魂丑陋、人格卑下、生活奢靡的精神图景。曾经的理想信念与德行操守在物质气息浓重的时代语境中幻灭与崩毁。使命、责任、终极关怀等知识分子的价值特征以及完善的道德、高贵的人格、纯净的灵魂也在欲望的诱惑下霉变、腐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虚伪、吝啬、冷酷、狡诈、油滑、卑鄙的道德水准与委琐、阴暗、自私、无聊的人格标记,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充分地暴露出来。关于人的价值、人生意义等终极性问题的思考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精神蜕变与自我堕落,折射了在世俗物欲追求中生活诗意的消逝。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知识者的人格精神与命运遭际。风起云涌的消费主义大潮冲毁了他们本就不坚定不明确不执著的信仰追求,这种精神上的失信必然会导致他们整个精神系统的空虚、悬浮、无根的状态。
与此同时,张扬“欲望”,也是1990年代以来小说形象书写的主题,如《山里的花儿》中的A君、《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博士后》中的箫志强、《桃李》中的邵景文、《欲望的旗帜》中的贾兰坡、《失眠赞美诗》中的楚博士、《废都》中的庄之蝶、《物质生活》中的韩若东,等等。他们因物质世界膨胀的欲望造成了精神世界的恐慌,唱响了知识分子人格委顿、精神萎靡的挽歌。以金钱、财富、享乐为中心的价值标准取代以理想为中心的价值标准的新秩序使他们无所适从,他们放弃了尊严,抛弃了精神上的神性思考,热衷于丰厚物质生活的享受与情欲上的满足。为我们上演的是学术上的压制、道德的沦丧、伦理的混乱、爱情的伪作,他们主动放弃了精神文化形而上的追求而转入对世俗欲望的角逐中。这是一个走向现实的世俗群体,更是一个“欲望”言说的神话,为我们展示了一则则关于知识分子当下际遇的寓言。
许纪霖曾发出过深深的忧虑:“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生存挑战……诺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斋,也难以再抚慰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在排浪般的‘全民皆商’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如何调整自己的生存姿态和心理姿态,政府部门如何制定有关战略决策,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确乎生死攸关,也许可以说,对于整个民族来说,也未必不是生死攸关。”[3]同“陆文婷们”相比,这些小说为我们呈现的形象谱系已经相形渐远,这种变化是深刻而耐人寻味的。洁身自好、任劳任怨、独立人格等等知识分子的美好品德被慢慢腐蚀掉了,曾经坚守的操守与信奉的理想信念是那么的不堪一击。这种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就像汹涌的洪水在一瞬间荡涤一切,甚至连忏悔的时间都没有。人与人之间也失去了理解、信任、谅解与包容。关于人类前景的无畏探求,崇高的科学真理,严谨的学术精神都被无情地消解掉了。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在市场大潮、物欲之风中的困顿、挣扎,展示的是一幅精神颓靡、道德失范、人格委琐、情感空虚、行为无德的百变图景,还有他们在各种重压之下灵魂的变形、人格的异化,人生坐标的迷失,为我们呈现的是原有价值体系的崩塌,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建立起来的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们的集体迷失。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出现重大危机,身份特征的认识出现重大偏差,他们自动放弃了价值、意义、终极关怀等形而上意义的思考与探求,转入形而下层面的物欲认同、世俗认同。正如阎真所说:“在市场的高歌猛进中,我看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逆向过程,一种遮遮掩掩甚至无需遮掩的溃败。这种溃败在每一个角落发生。一方面是责任、人格、心灵的理由和信仰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功利、名望、生存的需要和虚无主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巨大的价值悖论。”[4]
总体上说,小说中鲜有精神旗帜、道德楷模、行为典范式的人物,不能不说是世纪之交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一大遗憾。小说中大量无行知识分子形象的出现充分证明了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自然具备崇高的精神,良好的道德情操,坚强的意志,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与忧患意识,更不能保持独立、自觉的精神品格与身份意识。正如毛泽东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无法摆脱来自于时代、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身份特征、精神形象必须在上述因素合谋下才能完成。“正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开始慢慢走向宽容、慢慢告别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才为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投身专业的工作环境、自由思考的精神缝隙;也正是因为人们日渐尊重人性的丰富性、尊重日常生活的合法地位,知识分子才脱离单一的面貌,实现了自身的多元化。——除了继续坚持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之外,知识分子现在也面临着大规模俗世化的趋势。一些知识分子在心灵攀援、精神追问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卷入市民社会,成了大众文化的支持者和消费者;前一种知识分子正在萎缩,后一种知识分子却在不断地扩展。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之一。面对这种无法阻止的知识分子的俗世化运动,我们仅仅出示一些‘人文精神’的空洞法则、或者以平庸和媚俗为借口对其大加批判都是无济于事的,惟一的办法是,正视知识分子的这种内在变化”[5]。韩少功在《性而上的迷失》中讲到的:“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的巨大张力中燃烧和舞蹈。‘人性趋上’的时风,经常会造就一些事业成功道德楷模君子淑女;‘人性趋下’的时风,则会播种众多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浪子荡妇。”[6]君子淑女也好,浪子荡妇也罢,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文化符号,指代的是人的放纵与节制两级的取向。知识分子的价值相对主义、价值体系、价值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妥协性、依附性决定的。这里的相对是社会环境的变化衍生出了社会风尚与价值诉求对于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新的要求,当意识到无法践诺自己的信念与原则时,便改弦易辙,迅速地适应,这是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因为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无论是固守理想主义,还是与现世趋同融合,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与权利,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例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清”也好,“浊”也罢,只要是水就可以为我所用,最重要的是适应,是根据需要去选择,这是生存之本,更是生命的哲学。但如果知识分子也采取这种相对主义的话,人类也就失去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灯塔,失去了灵魂归入何乡的终极追问,失去了校正社会前进方向的路标。
二
第二个向度是指向历史,作家们站在1990年代后的立场去挖掘、再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关涉中国革命道路,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改造”等重大问题,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在反省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表现与人性表现。
新世纪以来,一些作家将笔触引向了建国之前,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知识分子与政治、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与个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反思与探寻,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精神。《露莎的路》是韦君宜晚年所著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表现的是延安整风时期,在革命的召唤下来到延安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真实地记录了延安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们经历的精神磨难与思想的转变。露莎可以说是延安整风时期千万年轻知识分子的缩影,通过她在延安拯救运动中的遭遇来对知识分子革命道路进行深刻反省。在延安抢救运动的遭遇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种种苦难的必然,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肉体与心灵磨难的源头与真正的开端实际上在四十年代初期的延安已经开始了。它培养了知识分子说假话的习惯,采取种种违背良知的行为以求得自保。作为老资格的中共党员,长期在党内从事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韦君宜,她的深刻反省令人深思。她披露的种种事实,目的不仅仅是让世人得知她的经历与心路历程的演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敦促我们应该有勇气面对历史,敢于将历史的本来面目还世于民,要的是一份真诚与良知。长篇小说《花腔》中的主人公葛任是一个文人加革命者的形象。小说以极具先锋品格的叙事形式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史”中“红色”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关注。以革命/反革命、进步/倒退为价值标准来解释历史发展的教科书模式曾经普遍流行,葛任的死亡“悬疑”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就是“红色”知识分子信仰与命运同政治意识形态、“革命正史”叙述的深层关联。实际上是对“革命正史”合法性与教化解读强烈的质疑。
上述人物展示的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前的境遇与经历,他们被定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成为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文化符号,“革命”的意义被质疑、拆解、改写。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人生面貌、定位与经历被重新想象,与经过“改造”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笔下的革命选择与革命叙述有着很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感悟到回到历史本真面目之后的深深震撼。毫无疑问,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人物都是清醒者,他们是在革命话语遮蔽下中国知识分子本真的存在状态。从他们身上追根溯源,我们能够找到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种种磨难的最初起点。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我们始终无法在历史的这面镜子中照清自己,是因为我们所熟知或被讲述着的历史本身就是模糊的。这些人物的存在也在提醒现实中的我们,历史虽不能假设,但也绝不能亵渎与遮蔽。站在历史的原点看待现实,对于很多事情也就很容易找到答案。他们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革命道路的重新书写,是抛却信仰、理想、乌托邦等等崇高的修饰后呈现出的真实,为思索并重新解读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提供了一种文学参考。
还有些小说中的形象书写摆脱了新时期之初知识分子苦难叙事的忏悔模式、自恋情结。从作家身份来看,除王蒙等是苦难的经历者外,很多作家表现苦难,但本身并没有苦难的经历,他们更多的是从他者的角度去审视、反思那段历史,不仅对知识分子的苦难做了真实的摹写,对造成苦难的深层历史动因也作了挖掘。同时将笔触引向受难者的灵魂世界,追问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定型的过程与动因,如《夹边沟记事》中的众多“右派”人物、《中国一九五七》中的周文祥、《乌泥湖年谱》中的丁子恒,等等。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使他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而作为被“改造”的主体,他们的身心在经历磨难的同时,文化人格也处于重塑与再造的过程之中。我们无法忽略这些政治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新的文化人格特征形成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新时期。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复杂与丰富,从苦难中走出的他们,身上不仅标示着苦难带来的深深印记,同时也放大了本就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历史积习下来的种种文化符号。在反省历史,追思往事的同时,审视、扣问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与人性的原型在经历了外部的强力扭压之后呈现出的变异与裂变,从而确认、反省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演进轨迹。在现实表现中追思历史,在历史表现中探寻真相,从而还原命运多舛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文化人格的本真。
可以说,曾经的受难者没有完成的使命在进入世纪之交后,那些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作家们进行了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受难者蒙难的原生形态,对他们进行文学立传。这是文化的批判,也是历史的批判,敢于大胆追问谁应该为这些苦难负责,谁才是真正的黑手。同时,反思指向深入到了受难者的内心,更多追问的是造成创伤的历史文化成因。这种深刻的追问、反思,结论的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仅看独立的主体意识与清醒的理性批判意识的严肃姿态已经彰显了价值。“知识分子如果在批判社会的同时不把自己当作反思的对象,就不会获得关于社会反思的真理性认识,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世界有什么作为”[7]。 这些表现苦难记忆的文本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历史进行的一次理性的梳理。小说中的“历史人物”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参与人,同时也在被历史塑造与改写。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危机进行展示和反省。这种历史的追问,既有对政治强权的诘问,又有精神建构的悲悯。既有悲愤的责问,又有深切的同情,还有悲苦的自恋。小说中的受难者形象体现了作家对于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严肃思考,为我们留下了无法忘怀的生命镜像。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家对历史的冷静审视和深沉反省,凝结着关于人的具有终极意义指向的命题,显示出文学不同于政治学、历史学的意义与价值。小说中这些“历史人物”的存在,一方面丰富了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谱系,拓展了以往历史受难者文学表现的深度、广度,为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起死亡档案,表现出一种深沉的文化思考与历史批判意识。另外,还能够让我们走进人物的内心,真切地体悟他们精神受辱、肉体受难,最终导致人格异化、精神矮化的内在轨迹。他们的存在是对新时期之初表现这一苦难的不足的有力反拨与补正。同时,也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无信、无为、无德追根溯源,提醒着我们知识分子的精神病症已经存在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当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判断、价值取舍。通过自审与反省,寻找民族之痛、知识分子之殇的真正精神之源、历史之本,这才是这些受难者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才是走出历史轮回,实现民族振兴与精神重建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才是通过文学进行历史反思、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建构、民族精神救赎与建构的使命所在。
三
透过世纪之交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我们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期间既包括曾经的精神磨难与苦痛,也有进入到转型期后精神取向的下行。现代知识分子诞生以来,对民族的道德崇拜而产生的负罪感已经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历次政治磨难中,除了外在强压的巨大冲击外,内在的与生俱来的血液中流淌的忏悔因子也是他们甘于“改造”的内驱力之一。尤其是投身革命的所谓先进知识分子,出于政治、革命的要求,使他们非常自觉、主动地寻求在思想上、意识上、精神上与工农相结合,常常以自身的自私、懦弱、动摇去反衬劳动人民的英勇、坚定、机智。以思想意识、道德水准的差异来凸显民众的伟大与自己的渺小。在改造中求得社会、“人民”和党对自己的宽恕,完成自我救赎,以此来完成灵魂的超度。这也成为建国后知识分子精神受难的心理基础。在革命的统摄下,他们都沦为被改造被批判甚至被嘲弄的对象,巨大的精神创伤使他们无法完成肉体的解脱和精神的超越。“由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折磨,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应有的自信,而且失去了原有的高风亮节,一方面越来越麻木不仁、谨小慎微,从而不求上进只求自保;一方面又越来越猥琐卑劣、目光短浅,从而不图大业自相倾轧。这种近传统比之于古传统更加让人怵目惊心,它使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人的自尊,仿佛被侮辱了几十年之后,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真的认可了这种侮辱,真的认可了这种损害一样!”[8]在“改造”主题词的统招下,他们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沉重深渊之中。曾经的理想信念、价值诉求被无情地摧毁,人格尊严、独立精神、自由品格丧失殆尽,在永无休止的批判、检讨、反省、揭发中,在对别人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自己也失去了基本的人格尊严与道德良知。“改造”的结果是他们成为一群“非人”。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这些本应坐在书斋、办公室中的知识分子们的身体遭到严重的损害。而政治上的打击,同事、朋友间的攻击,爱人间的背叛等等造成的心灵的创伤更是难以弥合。“改造”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人格重塑的过程,结果是,历经磨难后的知识分子变得或谨小慎微、明哲保身、惊弓之鸟,或虚伪矫饰、趋炎附势、两面三刀、落井下石,难言人格的独立、精神的高贵与思想的自由。现代知识分子诞生后培养起来的启蒙意识与批判精神在经历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后已经所剩无几,在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合力作用下,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曾经的人文光彩,生命得以保存,精神、灵魂、人格却被阉割,变得唯唯诺诺、平庸委琐。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短暂的昂扬与自信之后,随着社会背景的深刻变化,很快就又陷入到集体的无语状态。这种精神经历的轨迹呈现出某种必然的联系。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内核与生俱来的缺陷。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个独立的阶层,自现代知识分子诞生以来就缺乏坚定的信仰,软弱与摇摆不定成为挥之不去的软肋,先天的“软骨病”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爆发;其次,经历了建国后历次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之后,知识分子已经普遍缺乏关怀意识,明哲保身、落井下石、相互攻击等将他们身上恶的一面全面暴露出来,自私、委琐、冷漠等等越来越成为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第三,社会巨变的深刻影响,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幕的开启,对社会生活、行为习惯、思想意识、价值诉求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知识分子自然无从幸免,面对无孔不入的商业信息与物欲刺激,他们也很难做到洁身自好,加之转型初期种种不合理现象,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自身社会地位不高,知识不受尊重等等也助长了知识分子的蜕变与退化。社会语境的深刻变化带来了知识分子沉重的幻灭感、失重感与挫败感。知识分子身份的突然位移产生了悬空之后坠地的严重的躯体震荡与心灵的紧张。为曾经神圣的理想信念守灵就如梦一样虚无缥缈,更多的知识分子放弃了总有痛苦相伴的灵魂的拷问与对终极意义的探寻。市场以其巨大的解构力量吞噬了知识分子曾经的精神立场与价值理想,撩拨起知识分子作为人的原欲,开始了世俗浮华中的狂欢。
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自身身份意识的悬疑与迷失。现代化以来,尤其是建国后,随着对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的“改造”,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已经非常淡化,经历了短暂的1980年代后,随着1990年代世俗功利主义的兴起,知识分子迅速与世俗、拜金合流,社会责任感普遍缺失,无法肩负起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特殊阶层独立自省、社会批判等责任与义务,更无法站在一定的高度超然度世。作家张炜曾说:“如果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声音被一片最廉价的喧嚣所覆盖,这就不仅令人痛心,而且还令人惧怕。一些既通俗又流行的谬误大行其道,久而久之让那些以思想力著称的一部分人先是无声,进而也开口应和起来。我们总是一再地强调人的独立性,因为没有独立性就没有思想,也不会思想。一个人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权利,剩下的事情就是重复街上的声音。有人以为街上的声音你传我递,一般是不会错的,其实正好相反。要知道任何在风中吹动的声音都是合成的,而任何深刻的见解都不会是合成品。……有谁在顽强地揭露物质主义,谁在坚持阐述自己的不安和继续表达忧愤的心情,很少了,很少有人做这些不合时宜的事情了。”[9]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众多低俗、堕落、失范的知识分子形象预示着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遭遇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精神价值趋同的危机,曾经的精神家园已是昨日黄花。世纪之交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分化与丰富,既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商业化的世俗社会中寻求生存和尊严的艰难与多样性,同时又突显了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努力。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文学活动必须以审美的方式与社会生活发生关系,即以揭示人生意蕴、表现情感世界。而由此产生的感受、体验和领悟往往不是抽象的概念所能捕捉、传达和穷尽的,联结主客体的一个重要纽带就是人物形象。可以说形象是作家传达审美意识和读者接受文学作品的媒介与桥梁。在文学形象中,不仅有经过主体创造性想象加工过的客观事实,而且还包含着主体对其所表现的对象的审美态度,包含着他的个性和他的理想。不管作家将自己的情感和身影隐藏的多深,作品中最重要的形象依然是作家自己的反映和折射。他们的价值立场与创作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人物的人性表现、情感形态与道德操守。作家的创作精神在于渗透在作品中的关注现实、正视现实、忠于现实的思想态度,是力求通过文学创作及其作品把握现实的一种文学见解、审美主张。这种文学精神具体表现为按照作家自己观察到、感受到、把握到的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创作。“生活经验固然重要,但生活经验并不天然具有文学性,如果作家不能从生活经验中建构和发现文学性,那么‘生活经验’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10]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发掘出社会生活及人的精神状态的本质属性,就是文学所要传达出的声音。世纪之交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书写,一方面是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观照,另一方面也是作家们普遍陷入到一种悲观、绝望的状态。从小说中形象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作家倾注的情感与理性,或批判,或悲悯,或同情,或认同。他们在批判、审视笔下人物的同时,自身也处于痛苦的拷问与思考之中。中国知识分子究竟路在何方,种种情与理、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欲望的冲突与挣扎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立身之本、精神之乡的过程,这一过程还远没有结束,这正是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谱系所要告诉我们的,也是作家心灵挣扎的结果。
一贯以弘道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如何在市场化的社会里保持自身的独立品格与批判立场,怎样在整个社会的逐利价值趋同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一个理想化的目标是他们以掌握的理想、知识去促使市场经济的健康正常发展,矫正市场的各种负面影响,进而带动整个社会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正如曼海姆所说,知识阶层“所共同关心的唯一事情是智力过程:继续致力于清点、诊断、预测,当选择露头时发现它,理解和确定形形色色的观点的位置而不是拒斥它们或被它们同化”[11]。诞生于当代的文学,其肩负的使命不仅在于要书写当代,更在于它应因当代而写作。怀着这样一个目的进行的文学工作才更具有当代性,才更能体现出文学的价值。作家的文学创作应该针对时代里或隐或现的各种问题去展开文学的思考与回答,其价值不在于提供济世的良方,而是一种深邃的人文关怀指向。这才是一个作家具有时代使命感、责任感的真实含义。
[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543.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3]许纪霖.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J].读书,1988(9).
[4]阎真.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说说《沧浪之水》[J].理论与创作,2004(1).
[5]谢有顺.消费时代的暖色幽默——《桃李》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转型[J].南方文坛,2002(4).
[6]韩少功.性而上的迷失[J].读书,1994(1).
[7]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J].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92.
[8]李劼.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重构和自我选择[G]//祝勇.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331.
[9]张炜.像泥土一样质朴[N].解放日报,2004-09-09.
[10]吴义勤.自由与局限——中国“新生代”小说家论[J].文学评论,2007(5).
[11]郑也夫.“皮毛理论”与知识分子[G]//祝勇.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154-155.
[责任编辑 海 林]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6.026
2016-01-08
I206.7
A
1000-2359(2016)06-0169-07
于沐阳(1969-),男,黑龙江双城人,文学博士,延边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思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