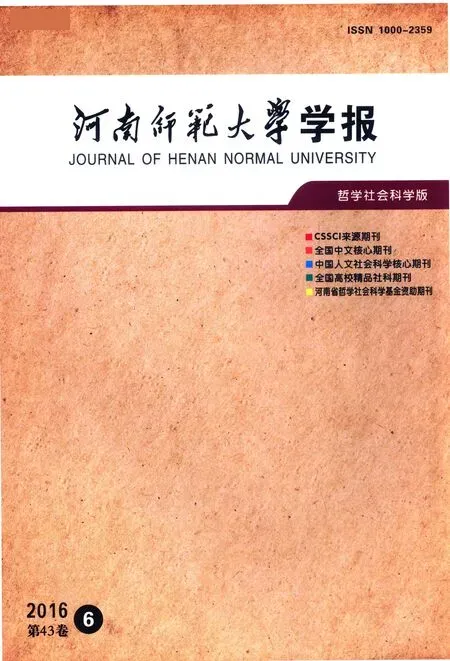论茅盾创作心态的矛盾与变化
2016-03-16聂国心
聂 国 心
(广州大学 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论茅盾创作心态的矛盾与变化
聂 国 心
(广州大学 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写作《蚀》三部曲时,茅盾有着“悲观”与“自信”的尖锐矛盾。他对社会历史的认知是悲观的,对自己的创作则相当自信。“左联”时期,茅盾的创作心态进入了一个“自信”与“怀疑”,“光明”与“悲观”相互矛盾的状态。他对自己的创作能力仍然自信,但对自我认识社会的能力却表现出怀疑,突出的表现是积极追求排斥自我的创作转型。结果是他一方面着力表现光明,一方面却无法抹去作品的悲剧气氛。
茅盾;创作心态;矛盾与变化
一
茅盾的文学创作,就其追求真实地反映历史,以达到褒贬现实,指导人生的目的而言,从《蚀》三部曲到《子夜》,都是一贯的。 茅盾的创作心态,则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简单地由此及彼,而是始终充满着矛盾。当然,在变化的过程中,矛盾的具体内容以及何者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表现。 写作《蚀》三部曲时,茅盾有着“悲观”与“自信”的尖锐矛盾。那时候,他是在“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1]176-177之后才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他写作时的“思想情绪是悲观失望”[2]206。但所谓的“悲观失望”,是指他对社会历史的认知而言。就他对自己的创作来说,他的政治资历、文学水平和作为那段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历史的亲历者,都使得他对自我抱有高度的自信,相信自己能够真实地将大革命的历史再现出来。他尊重自己的感性认知和对社会历史的亲身体验,写作时努力“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并且要使《幻灭》和《动摇》中的人物对于革命的感应是合于当时的客观情形”[1]178,就是其自信的一种表现。后来,他面对创造社太阳社对《蚀》的严厉批评,不仅积极辩驳并带有许多情绪化的语言,而且还继续创作了一些与《蚀》相类似的作品,如《野蔷薇》等,也都是其自信的一些后续表现。
“悲观”与“自信”的矛盾,尤其是创作上的自信,使得茅盾能够在《蚀》三部曲中“很老实”地表现自己“幻灭”、“悲观”、“消沉”的“思想和情绪”[1]180,真实地再现他所亲历的大革命的生活气息,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茅盾心境的一个独特层面。
但茅盾是主张“无产阶级艺术”的。当他的处女作遭到来自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阵营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批评时,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时代”的要求和他自己创作的实际状况。检测的结果是,他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了创造社太阳社的批评。
他不仅创作上开始寻求转型,《虹》《路》《三人行》就是这种转型过程中的产物,而且明确申明要突破自己原有的创作“模型”。他说:“一个从事于文艺创作的人,假使他是曾经受了过去的社会遗产的艺术的教养的,那么他的主要努力便是怎样消化了旧艺术品的精髓而创造出新的手法。同样地,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他的苦心不得不是继续地探求着更合于时代节奏的新的表现方法。”[1]226
在这段广为人知的话语中,茅盾用的是“新”、“旧”对立的五四式思维,说的又是艺术“表现方法”的创新问题,很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同。但茅盾所说的创作转型,却绝不是一个艺术“表现方法”所能概括得了的。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其创作转型的努力方向,是“探求着更合于时代节奏”。也即是说,茅盾更为重视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情调的转型。 这一点,茅盾在1928年7月写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就已经说过。茅盾说:“我希望以后能够振作,不再颓唐;我相信我是一定能的,我看见北欧运命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1]186当年与茅盾一起东渡日本并与茅盾有过一段亲密关系,对茅盾的创作转型产生过影响的秦德君也回忆说:《蚀》三部曲遭到激烈的批评后,茅盾“想写一部新小说来扭转‘三部曲’在文坛上给自己造成的影响”[3]。
那么,茅盾是如何来转换其原有的创作“模型”的呢?
茅盾的选择,先是按照主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要求写“光明”指“出路”的思路来创作,把自己“感得”的“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收起来,着力描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虹》中的梅行素,《路》中的火薪传,走的都是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路。《三人行》也是以两个否定性人物如个人主义的许和虚无主义的惠,来反衬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肯定性人物云。
虽然茅盾激烈地反对过创造社太阳社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光明指出路的思想,但他所反对的只是“昧着良心说自己以为不然的话”[1]181,以及“把未来的光明粉饰在现实的黑暗上”[4]522的做法,并不笼统地反对写光明指出路本身。他接过创造社太阳社的这种理论来促使自己创作的转型,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茅盾切身体验和感受到的生活,并没有光明和出路。他用来指导自己创作转型的,是一种有异于自己切身体验和感受的理论。他曾经还激烈地批评这种理论是一种盲目的“以‘历史的必然’当作自身幸福的预约券”,是“沙上的楼阁”[4]523,现在却要努力使自己的创作向这种理论靠拢。这一方面当然在表层意义上迅速改变了他作品中的悲观情调,一方面却在实质意义上严重损害着他的创作自信力。
建立在排斥自我,不相信自我的基础上的创作转型显然不可能彻底,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沙上的楼阁”。《虹》《路》《三人行》的发表,就既没有获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界的喝彩,更没有引起像《蚀》那样的社会轰动。如果说,《虹》还保留着茅盾“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5]271的宏愿,还保留着许多像《蚀》那样的细腻的女性心理描写,还有一些社会意义和文学性的话,那么,《路》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只是一种浮雕,缺乏饱满的血肉”[6],茅盾自己也“觉得做的不好”[5]381。到《三人行》,则充满着政治理论的演绎。瞿秋白当年就批评《三人行》“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的”,其“创作方法是违反第亚力克谛——辩证法的”,“这篇作品甚至于非现实主义的”[7]。茅盾自己也认为“这一作品的故事不现实,人物概念化,构思过程也不是胸有成竹,一气呵成,而是零星补缀”,是一部“失败”[2]207之作。
不过,茅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创作转型的方向。他在遭受第一步的努力失败之后,虽然对写光明指出路的具体思想有所修正,但仍然坚持文学创作需要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茅盾的思维特点,希望用文学形式记录历史的理性精神和透彻认知社会现象的愿望,都决定着他必然这样做。茅盾说:“一个作家不但对于社会科学应有全部的透彻的知识,并且真能够懂得,并且运用那社会科学的生命素——唯物辩证法;并且以这辩证法为工具,去从繁复的社会现象中分析出它的动律和动向;并且最后,要用形象的言语、艺术的手腕来表现社会现象的各方面,从这些现象中指示出未来的途径。”[1]331-332
理论上说,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去分析现实问题也存在着个体的差异。但因为茅盾的创作转型不是在保持自己的切身体验和个性化感知的基础上来接受“时代”的要求,而是在急于表明自己“不落后”的心态下,向外寻求社会科学理论的帮助,所以就茅盾的主观倾向而言,他不是坚持这种个体的差异,而是在努力消除它。如果把鲁迅与茅盾的创作心态作一比较,则可明显看到,鲁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替,其本身仍充满着鲁迅的个人意识和个人色彩;而茅盾的矛盾,则主要表现在“自我”与“超我”的博弈,其本身就存在着排斥“自我”的预期。
当然,茅盾经历了创作转型的第一步努力失败后,并非没有反省。他看到了完全排斥自我,简单地依从他者的理论是一条死路。于是他在特别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去分析现实生活的同时,又特别强调要充实自我的新生活。写作《子夜》时,就既有为了写作去经验人生的过程,也有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整理所得的材料”的过程,并在“用过一番心”的“构思”[8]553之后才写成。这个时候,他所强调的是,“我们必须以辩证法为武器,走到群众中去,从血淋淋的斗争中充实我们的生活,燃旺我们的情感,从活的动的实生活中抽出我们创作的新技术!……我们必须改变以前的生炒熟卖,取巧偷懒,盲目自信的态度,我们必须忠实地刻苦地来创作新时代的文学!”[1]308
也即是说,茅盾既继续坚持用异己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转型,走的仍然是否定自我的路,又强调要丰富自我的生活体验,并要求作家要“从繁复的社会现象中分析出它的动律和动向”。当茅盾提醒作家不要耳食一点社会科学理论就“盲目自信”的时候,客观上又有着尊重自我的因素。
二
于是,茅盾的创作心态进入了一个“自信”与“怀疑”,“光明”与“悲观”的相互矛盾的胶着状态。他“左联”时期的创作鲜明地烙下了这种矛盾的印记。
首先,茅盾认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却又不能够创作出歌颂无产阶级的优秀作品。 茅盾1925年就发表了《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一直都是无产阶级艺术的赞同者和倡导者。但即使在他向创造社太阳社的理论靠拢,主张描写工农题材,而且其创作题材也确实发生了转换的“左联”时期,他不仅在转向工农题材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犹疑,而且最终也未能写出歌颂无产阶级的优秀作品。
《子夜》被学界公认为是茅盾“左联”时期乃至他整个创作生涯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继《蚀》三部曲之后茅盾最具影响力的创作。《子夜》与《蚀》之间存在的差异有很多,其中题材的不同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按茅盾主动适应“时代”要求的逻辑来看,他抛弃自己所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题材后,应该转向“时代”所要求的工农题材。但事实上,茅盾花了很大的努力才实现的题材转换,却是首先转向了民族资产阶级。
《子夜》的创作“野心”,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8]553。构成茅盾观察“中国社会现象”的中心人物,是都市中的民族资本家。《子夜》即是选取大都市上海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人物,来展示19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的。作品写得最成功的人物,也是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的形象。 《子夜》之所以写成这个样子,按茅盾的说法,是因为天气的酷热损害了他的健康,因而改变了他原定的写作计划。因为按照茅盾的“原定计画”,《子夜》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不但写都市,还要写农村。但了解了茅盾的“原定计画”后便可发现,他所谓的更大规模的描写,也只是扩展写到“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整部《子夜》的“总结构”还是“现在这本书”[8]553-554的样子,仍然是以民族资本家为中心,并没有计划重点写工农。
虽然作为茅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子夜》也写了工人反抗和农民暴动,但大多采用“暗示和侧面的衬托”[9]55,学界普遍认为写得“不能算是成功”[10]。 茅盾是坚决反对“‘脸谱主义’和‘方程式’的描写”的。他批评蒋光慈的创作,指出《地泉》的缺点,都集中在其“‘脸谱主义’地去描写人物”和“‘方程式’地去布置故事”[1]335这两个基本点上。
应该说,茅盾在写《子夜》时,非常注意避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中流行的这些通病。他写的民族资本家有不同的类型,写的工人也有不同的类型。既有组织黄色工会,维护民族资本家利益,破坏工人内部团结的桂长林、钱葆生,也有保持质朴的本色,大公无私,坚决反抗资本家剥削的朱桂英、张阿新、何秀妹。而且,这些人物中前者还因为其所处的派系不同,后者因为个人的生活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出一些细微的差异。就茅盾的主观构思来看,他并没有因为《子夜》中的工人形象处于次等地位而将其想象成一个脸谱。
但《子夜》中塑造的工人形象,尤其是作为工人中的觉悟者的形象却仍然摆脱不了茅盾所坚决反对的“脸谱主义”和“方程式”的弊病。作为工贼的桂长林和钱葆生,分别是国民党中汪派和蒋派的代表。他们无一不是勾心斗角、奸险狡猾和奴颜婢膝的化身。作为工人中的先进分子的朱桂英、张阿新、何秀妹等人,则都是立场坚定、正气凛然、大智大勇的神性人物,其概念化的缺点尤其突出。 后来,茅盾为了弥补未能写进《子夜》中的“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又先后写了《林家铺子》《春蚕》《秋收》和《残冬》。《林家铺子》的取材可以与《子夜》归入一类,暂且不论。《春蚕》《秋收》《残冬》则是以农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从茅盾创作题材转换的角度来看,至此算是完全实现了他希望转向主要描写工农的预定目标。
与茅盾所写的工人形象相比,茅盾所写的农民形象要成熟得多。但所谓成熟得多的农民形象,也是指与流行的左翼文学理论相去甚远的“落后”的农民形象,如《春蚕》中的老通宝;而根据流行的左翼文学理论创造出来的“先进”的农民形象,则仍然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如《残冬》中的多多头。 茅盾原本是想侧重描写“先进”的农民形象的。 他把勤劳忠厚而又保守迷信的老通宝,看作是既值得同情又应该批判的“落后”人物,认为这种人物应随着历史的进步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他把公而忘私,觉醒反抗的多多头看作是应该极力歌颂的“先进”人物,认为这种新人的出现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农村三部曲”由“春”至“秋”到“冬”的设计,即是想要说明农民从保守迷信的苦难中走向觉醒反抗的历史过程。 但写成的作品却事与愿违。相对而言,茅盾想要批判的人物老通宝,写得血肉丰满、生动自然;想要歌颂的人物多多头,则写得干瘪枯瘦、苍白无力。
其次,茅盾强调文学要写光明指出路,但其作品却仍然是悲剧居多。尤其是,作者对其作品中的悲剧主人公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心态:要么主观上想展开批判,事实上却流露出深厚的同情;要么主观上想寄予同情,客观上却展示出深刻的批判。
不能够创作出歌颂无产阶级的优秀作品,并不是茅盾一个人的问题,那是左翼文坛的一个普遍现象。“左联”接过创造社太阳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但在否定作家的个性问题上却比创造社太阳社做得更为彻底。创造社太阳社理论上否定个性,其表述理论的方式却仍然充满着个性色彩;创作上存在“脸谱主义”和“方程式”的弊病,其作品却还是保留着浓郁的主观性浪漫想象。“左联”时期的左翼文坛则连这种表述方式中的个性色彩和作品中的主观想象也要铲去。
当然,彻底的“无我”是做不到的,尤其是在像茅盾这样优秀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之中。这正是茅盾不同于一般的左翼作家的独特之处。茅盾在倡导“无我”的历史氛围中追求自我创作的转型,他抛弃“自家亲身经历过的‘旧题材’”[1]408,抛弃自我亲身体验到的幻灭、悲观的思想情绪,本想以此来脱胎换骨,创造出一种既有艰辛的斗争过程又有光明的前途和出路的新型作品,但事实上其成功的作品仍然是悲剧性作品,其成功的人物形象仍然是悲剧性人物形象。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在这些作品和人物形象中仍然潜存着作者的自我因素。
《子夜》和“农村三部曲”的创作都是遵从主流的左翼文学理念,“先从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开始”[11]215,既有明确的理论分析的意图,也有确凿的理论分析的表现。但是,这两部最能代表茅盾“左联”时期创作成就的作品,却并不完全符合主流的左翼文学理论。至少,它们所呈现出的悲剧色彩,以及作者对几个主要人物的处理,都与主流的左翼文学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按茅盾当时的想法,《子夜》的创作目的是为了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其主题“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茅盾“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9]54-53后来,“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这条线未能展开,可以忽略不计。仅就他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设想来看,显然是想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社会中这两个阶级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大背景下的矛盾和斗争。按照主流的左翼文学理念,其重心理应放在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上。茅盾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他的解释是“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起来,就不能出版。”[9]55
这当然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却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看,甚至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子夜》非但没有重点写工人,而且还没有塑造出一个成功的工人形象;非但没有突出乐观的歌颂性内容,反而呈现出浓郁的悲剧色彩;非但没有引起人们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的同情,反而对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表示同情。 特别是主流左翼文学理论主张批判,茅盾也在设想中作为批判对象的吴荪甫,事实上却让人们产生深厚的同情这一突出的矛盾现象,当年从整体上肯定《子夜》的瞿秋白也已经看到了。瞿秋白说:“在意识上,使读到《子夜》的人都在对吴荪甫表同情,而对那些帝国主义,军阀混战,共党,罢工等破坏吴荪甫企业者,却都会引起憎恨”[12]92。
瞿秋白当然不相信茅盾会同情资本家,他看到了茅盾已经在“尽量描写工人痛苦和罢工的勇敢等等”,主观意图是想将同情放在工人一面。于是,瞿秋白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修改《子夜》的结尾。他认为:“假使作者从吴荪甫宣布‘停工’上,再写一段工人的罢工和示威,这不但可挽回在意识上的歪曲,同时更可增加《子夜》的影响与力量。”[12]93且不说“再写一段工人的罢工和示威”的建议,与茅盾已经精心考虑过的要回避“检查”的设想相矛盾,即使可以完全照改,恐怕也无法改变小说中已经定型的人物格局。
茅盾把自己塑造民族资本家形象比较成功而塑造工人形象不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对相关生活的熟悉与否。他说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活比较熟悉,“是直接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而对“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则很生疏,“仅凭‘第二手’的材料”[2]208。 这当然也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对生活的熟悉与否,其实只是一个条件。关键还在于作者的情感和态度。如果对自己熟悉的人和事非常反感,就绝对不可能将他们写成悲剧性的让人同情的人物。吴荪甫之所以偏离茅盾的设想成为一个悲剧形象,而且那么感人,显然与茅盾的精英意识、创作自信和政治上文学上连续遭受挫折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一心一意从事政治活动,却被时代的风云甩出了政治斗争的中心;他退而想用文学形式继续自己未竟的政治事业,却一开始就遭受到他所向往的政治力量的严厉批评。
有学者即使从整体上否定《子夜》,称“《子夜》读起来就象是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但认为“吴荪甫这个形象仍然是成功的”。其理由也在于“在吴荪甫这个形象里,无意之中多少寄托了一点茅盾的政治境况与文坛境况”[13]。 与《子夜》的悲剧色彩相类似,《春蚕》也呈现出浓郁的悲剧气氛。不过非常有意思,茅盾在理性层面同样将造成主人公悲剧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外在的帝国主义侵略,但在情感层面,却对预想批判的吴荪甫寄予着深厚的同情,对预想同情的老通宝却展开了扎实的批判。
本来,茅盾将老通宝塑造成一个既思想保守又有着勤劳忠厚优点的农民形象,主观上是想说明老通宝的悲剧主要不是由他个人所引起,以此引导人们去憎恨那个造成众多悲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老通宝的那种与外在环境的压迫苦苦挣扎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的人生历程,与吴荪甫的悲剧一样被渲染得相当感人。但可惜的是,茅盾的这种意图贯彻得不像《子夜》那么彻底,他同时又高高在上地写了老通宝的许多“落后性”的缺点,特别是当茅盾将这些缺点与他自己极力想歌颂的多多头的觉醒反抗的“先进性”优点对照起来写时,实际上是在传达一种主流左翼文学的理念。这不仅极大冲谈了已经营造出的悲剧气氛,给人的印象,老通宝的悲剧是由他自身保守的性格特别是他“落后”的思想所造成,而且使得老通宝形象以至于整篇小说的精神氛围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况。老通宝是值得同情的,又是应该批判的。他既与启蒙小说中的主人公相类似,而《春蚕》又不具备启蒙小说强调个性解放、人格平等的精神特征。
就茅盾的主观认识来说,在当时的江浙一带,像老通宝这样的农民并不多见。茅盾说:“太湖区域(或者扬子江三角洲)的农村文化水准相当高。文盲的数目,当然还是很多的。但即使是一个文盲,他的眼界却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的事物。”[11]213老通宝显然是茅盾违背自己的主观认识,为了歌颂多多头这类“先进”的农民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一类对比性的农民形象。 由于描写“先进”的工农形象是茅盾创作转型的预定目标,作者在老通宝这类“落后”的农民身上所寄予的情感发生裂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再次,茅盾相信自己的创作能力,却又往往盲目听从他人的指导意见。
茅盾是一位“有着巨大的企图”[14]的作家,对于自己的创作能力,不仅在创作《蚀》三部曲时充满着自信,后来在追求创作转型的过程中以至于完成转型之后也充满着自信。无论是“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还是“企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以至于一再冲破“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苦心”“探求着更合于时代节奏”的题材、主题和表现方法,都表明他对自己的创作能力始终保持着自信。
但在“左联”时期,茅盾的创作又往往盲目听从他人的指导意见。这不仅表现在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时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机械论思维,而且表现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甚至连一些违反人物身份的细节性修改意见也言听计从。最典型的是对《子夜》的修改。据茅盾自己说,瞿秋白在看过《子夜》后曾提出意见,认为“‘福特’轿车是普通轿车,吴荪甫那样的资本家该坐‘雪铁笼’”,“大资本家到愤怒极顶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茅盾对这两点意见都“照改,照加”[15]。
瞿秋白的意见显然是从“资本家”必然奢华并具有兽性的概念出发提出来的,与茅盾所要塑造的一个有着发展民族工业雄心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因素的吴荪甫形象并不相符。按照吴荪甫“就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8]89的设想,按照吴荪甫雄心勃勃的事业心,过着一种简直就像是打仗一样的生活,以及随时注意保持一种有教养的绅士风度的习惯,他未必一定奢华,更不会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去强奸一个自己家中并无姿色,他也从未关注过的女仆。
茅盾在多种场合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性,但对这种明显违反人物性格和身份的修改意见却不加分析地予以接受。这一方面当然表现出他对瞿秋白的学识修养的崇敬,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他对自我的能力缺乏自信心。
严格说来,这种不自信,也不是针对着他的创作能力,而是针对着他对现实社会的认知能力。创作《蚀》三部曲时,茅盾既从现实社会中感得幻灭悲观的思想情绪,也敢于将这种思想情绪如实地表达出来,表现出对自我认知社会的一种自信。后来接受“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追求创作的转型,他发现自我的感知与外在的理论差距极大。由于他向往“社会科学理论”,尽力向这种理论所预示的“光明前途”靠拢,他就不得不压抑甚至排斥自我的感知。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对自己认知现实社会的能力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对自己的这种不自信基本上是满意的。他虽然对自己在“左联”时期的创作也有过批评,但总体评价是在不断地进步。他“不肯妄自菲薄”,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他在追求“社会科学”的过程中,不仅不断地感到“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有了认知社会的进步感,而且能够不断地突破自己原有的创作题材和主题,有一种“没有被自己最初铸定的形式所套住”[1]409的成就感。因而,茅盾的这种不自信,其实又包含着许多自信的因素。这与鲁迅对自己转型后的《故事新编》不满意比较起来,其间的差异,很耐人寻思。
[1]茅盾.茅盾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茅盾.茅盾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秦德君,刘淮.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J].百年潮,1997(4).
[4]茅盾.茅盾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5]茅盾.茅盾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黄侯兴.茅盾——“人生派”的大师[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94.
[7]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48-454.
[8]茅盾.茅盾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9]茅盾.茅盾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0]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50.
[11]茅盾.茅盾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3]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J].上海文论,1989(3).
[14]韩侍桁.《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G]//孙中田,查国华.茅盾研究资料(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10.
[15]茅盾.忆秋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0.
[责任编辑 海 林]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6.023
2016-01-0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ZW056)
I206.6
A
1000-2359(2016)06-0153-06
聂国心(1960-),男,江西武宁人,文学博士,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