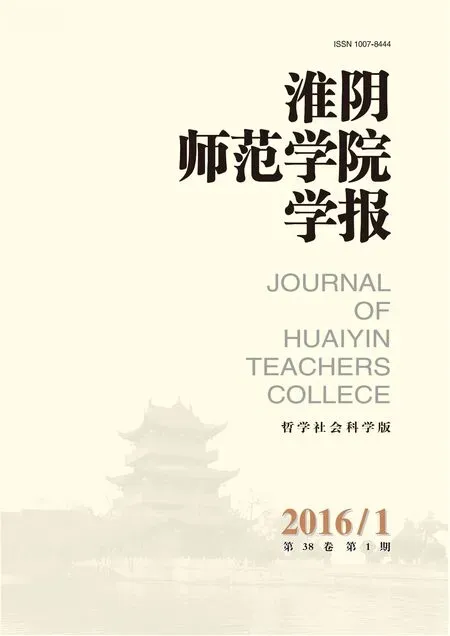明清时期杭州地区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2016-03-16胡梦飞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明清时期杭州地区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明清时期运河沿岸地区金龙四大王信仰极为盛行,位于运河最南端的杭州亦是如此。相比其他地区,杭州地区金龙四大王庙宇的数量和分布并无明显的规律,与运河、漕运亦无密切的关系。钱塘安溪为传说中金龙四大王谢绪的桑梓之地,钱塘安溪谢氏家族视其为祖先神,积极倡导和推动信仰的传播。金龙四大王信仰的盛行对区域社会和民众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地官员和民众视其为乡土神和地方保护神,体现出明显的宗族化、世俗化和本土化特征。
关键词:明清;杭州;漕运;谢氏家族;金龙四大王信仰
京杭大运河作为沟通我国南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在促进沿线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对沿线区域民间信仰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运河的流经所带来的漕粮运输和河漕治理活动导致了水神信仰的盛行。水神信仰不但种类众多,而且分布地域广泛,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和祠堂遍布运河沿岸各州县。在众多的水神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黄河河神、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的祭祀和崇拜。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不仅是一条繁荣的商品经济带,同时也是一条密集的水神祭祀带。杭州地处运河最南端,既是漕粮的重要输出地,也是商品经济、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其所属的钱塘安溪更是传说中金龙四大王谢绪的桑梓之地。*明清时期杭州地区属杭州府管辖,行政区划并无太大变化。本文所指的杭州地区特指明清时期杭州府管辖下的钱塘(县治在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小营、湖滨、清波街道及紫阳街道北部)、仁和(县治在今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武林、庆春、天水、长庆、潮鸣街道)、富阳(今浙江省富阳市)、余杭(县治在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临安(今浙江省临安市)、於潜(县治在今浙江省临安市于潜镇)、新城(县治在今浙江省富阳市新登镇)、昌化(县治在今浙江省临安市昌化镇)8县及海宁(州治在今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1散州。本文依据相关史料,以明清时期杭州地区为视角,论述当地金龙四大王庙宇分布及管理情况,分析其传播及盛行的主要原因,探讨其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以求为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地域分布
金龙四大王,名谢绪,南宋诸生,杭州钱塘县北孝女里(今浙江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安溪村)人,因其排行第四,读书于金龙山,故称“金龙四大王”。作为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除具有防洪护堤、护佑漕运的功能以外,民间也赋予了保障航行安全、掌管水上生死等职能,既为河漕官员、漕军、运丁所崇祀,也为船工、水手、商人所供奉。明清时期更是不断被官方敕封,其最后的封号多达四十余字。
杭州地区是传说中金龙四大王谢绪的桑梓之地,也是其影响和传播的重要地区。*明代大学士陈文《重建会通河天井闸龙王庙碑记》记载济宁天井闸旧有金龙四大王庙,“凡舟楫往来之人皆祈祷之”,建时不详,正统十三年(1448)重修;《明英宗实录》卷231亦记载景泰七年(1456)四月,“建金龙四大王祠于沙湾,命有司春秋致祭,从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奏请也”。可见,早在正统、景泰年间,金龙四大王信仰就已出现并极为盛行,但对于金龙四大王为何人,起源于何时何地,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有关金龙四大王为谢绪,其故里为钱塘安溪的记载直到嘉靖、万历年间才出现,其诸多神迹和传说亦都出现于这一时期,这无疑与文人对金龙四大王形象的改造以及钱塘安溪谢氏家族的附会有着莫大关系。故钱塘安溪只是传说中金龙四大王谢绪的桑梓之地,其信仰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仍有待考证。繁忙的漕运、众多的文人和商人以及钱塘谢氏宗族为其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表1便是笔者依据相关史料,对明清时期杭州境内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分布情况所做的简要统计。
资料来源:(民国)齐耀珊、吴庆坻等:民国《杭州府志》卷九《祠祀一》、卷十二《祠祀四》、卷十三《祠祀五》,《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1)》,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400页;明清杭州各州县方志及相关资料。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杭州境内共有金龙四大王庙宇10座,其数量和分布并无明显的规律,有些庙宇甚至建于偏远的乡村,与运河、漕运也无密切的关系。修建庙宇的主要为当地士绅和民众,较少有漕运官员和地方官员参与的记载,当地官员和民众更多地将金龙四大王视为乡土神和民间俗神。相比山东、苏北地区,杭州地区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更多地体现出民间化、本土化的趋势。
二、金龙四大王庙宇的管理和祭祀
有关金龙四大王庙宇的日常管理,学界鲜有研究,清人仲学辂《金龙四大王祠墓录》中有关钱塘安溪金龙四大王庙《祭田收支规则碑》的记载,无疑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杭州钱塘安溪金龙四大王庙有专门的祭田,由钱塘知县秦炌购置,其经费来源于雍正五年(1727)淮徐道康弘勋的捐助。雍正六年(1728),秦炌《置祭田记》云:“雍正纪元之四年,河清万里,皇帝敬隆秩祀,以答神庥,诏发帑银,建金龙四大王庙于江南之皂河。而浙江钱塘县金龙山之阳,神之祠墓在焉。奉旨整而修之,殿堂门庑,金碧腾光,荆棘攸除,鸟鼠攸去。工程既竣,而淮徐道康公,藉神之佑朱家海,大工告成,愿捐资三千两,以一千五百两置祭田于江南,以一千五百两置祭田于钱塘,俾世奉烝尝,而以其余,为岁修之费。……炌材力弗逮,谨承宪意,买本县调露十五图陈黄氏征田二百二十亩一厘八毫三丝五忽,委本县儒学曹廷献,履亩以稽,于是正其广轮,总其岁入,守之于官。凡牺币之数,岁修之费,书之于籍,使千百年嗣守兹土者,永有法则。”[1]678
对于祭田的使用和管理,雍正十年(1732)十一月,钱塘县儒学《祭田收支规则碑》云:“杭州府钱塘县儒学,为知会事,雍正八年十月十六日,奉杭州府正堂加二级在任守制乔宪牌,雍正八年十月初七日,奉总督部院兼管巡抚事李批本府议,详金龙四大王祠祠田,年额征收,支给各项规则缘由,奉批如详,饬令勒石永遵。其经收官吏胥役人等,如有额外需索,从中侵蚀情故,该府县立即详明察究,毋任滋弊,缴册存查,等因批府下学奉此,遵将宪定规条,勒石永遵,施行须至。”[1]678碑文对祭田的来源、佃户的遴选、田租的征收及各项支出都做了极为详细的记载。
祭田的来源为置买陈黄氏征田,“丈实共得二百二十亩三分五厘二丝三忽,每年应征额租计米二百二十石三斗五合二勺五杪,永为本祠祀产。印契著令该县出具收管,放存入册交代。仍立碑永禁质典、侵盗情弊,违者,卖、买各治以罪。”关于佃户的选择,碑文记载:“务选诚实农民,佃种租息,按时完纳,俱令当堂具认,查验明确,批准盖印,始予承种。如有奸细,捏名私租,私顶滋负,欠拖延宕,立时详革,究追治罪,以清积弊。”对于田租的征收和管理,碑文亦有明确的规定。“既近乡都,每年收租,需添船只、袋口、人工、饭食、搬运诸费。今议本田系膏腴之产,应自雍正八年为始,将所完租息,酌量折中,每亩一石,定折征银九钱九八平色,令佃户及期赉赴管收衙门收纳,出给印串收据。如无印串,即系私混,仍著追完,不得额外加耗,亦不许以歉岁再行请减,久远著为定规。”对于征收上来的田租,则委派专人进行管理:“(田租)折价征收,奉宪饬行委员专理。第省会杂职等官,不时有差委及分巡之责,今本府查得钱塘县教谕,堪委董理斯任,候批示日,饬令征租完纳给串,仍将所收租银,解贮钱邑县库,遇有支用,移明给发。除每年额定应用之项外,多者存为修葺祠宇。各费统于年终,该教谕造具出入数目,移县报销。”[1]679-680
田租的使用以及庙宇的各项支出在碑文中亦有详细的规定。关于祭祀所需祭品及各项支出,碑文记载:“(租田)原以置供祀产,该县原详,每祭动用二十两,春秋二次,共银四十两。买备祭品,及俎豆、牲醴、楮帛、果寀、香烛等项,庶为适中。临期,本府委员往祭,听子孙自行散胙,以沾宪恩。”庙宇日常所需灯油、香烛、维修以及庙内僧人的日食口粮等项,碑文亦有明确规定:“(神祠)朔望晨昏,香烛灯油,该县议每岁给银七两二钱,遇闰月加银六钱。查香烛等项,原以昭诚敬而肃瞻仰,应如所议按给,但寺僧不得扣减侵渔,致滋亵渎,察出究追。”[1]680“祠宇地处水滨,易于伤损,除上年雷雨损坏之处,现饬该县估价,俟收租后修整外,嗣后遇有坍缺,该奉祀禀报该管官,随时勘报请修,毋致积久,日损多费。”[1]680“守祠僧智远专司看守祠墓,启闭洒扫,一人不足管理,许其收徒一名,协同承应,每年每名给米六石,两名共给米一十二石,遇闰各加五斗,以资日食口粮。”[1]680除此之外,因钱塘安溪为金龙四大王谢绪桑梓之地,每年还要在物质上给予谢氏宗族一定的优待,以示体恤:“奉祀嫡裔谢,逢时每岁给米拾石,稍资膳读,俾得世守蒸尝。又经管后裔谢,正朝纳粮,办祭监修祠宇,稽查出入,不无劳费,应照奉奉祀例,亦给米十石,使之并沾祖泽。”[1]680
由于钱塘安溪是谢绪桑梓之地,作为金龙四大王的祖庙,其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碑文对祭田的购置、佃户的筛选、租息的交纳以及庙宇的日常管理和祭祀情况都做了详细规定,由此也可以看出,清朝官方对此庙的重视。虽然这块石碑早已湮没无存,但碑文的内容却得以被后人收录,流传至今,因而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为保护金龙四大王祠墓不受破坏,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钱塘县专门发布了《钱塘县束告示》,内容如下:“为永禁事,照得本县境内,孝女北乡,土名下墟湾,向有金龙四大王祠墓,历朝敕加封号。雍正五年,奉旨发帑兴修,每岁春秋,由钱塘学官主祭。另给祀田,将每年租息,作为时祭及殿宇岁修等费。案照头门碑记,经办多年,至咸丰庚申、辛酉岁,叠遭兵燹,庙貌倾废,祀典阙如。光绪十四年,山东巡抚张(曜),准浙江绅士函商重建,特捐廉银二千两,奏请修复。奉部咨明浙江巡抚,饬照章认真办理等因。遵将头门、正殿、寝宫,并金龙山茔墓,神之先世灵惠祠,尽行建竖。计费工料,合纹银五千余两,祠墓乃得焕然一新。查该祠前对西险大塘,经绅士丁丙、仲学辂,谨择要区,设立险塘,岁修公所。据称,该祠系奏明兴修之处,与寻常社庙不同。诚恐无知乡愚,寄顿什物柴草,不顾体制,以及外来游痞,托言逃难,盘踞旅宿,非特损伤墙屋,亦且亵渎神明,殊非朝廷设祀崇祠之至意。为此,合行出示永禁,仰诸人等知悉。尔等须知,金龙四大王忠肝义胆,身后不磨,灵迹所昭,岂惟河渎,凡有血气者,咸宜尊敬,况下墟湾谊关桑梓,更不待言。嗣后,倘有前项情弊,许公所董事暨管庙司事,鸣保禀县,以凭究办,决不姑宽,毋违特示。”[1]688-689《告示》回顾了庙宇修建的经过,重点论述了发布《告示》的原因,在保护庙宇不被破坏的同时,亦起到了教化民众的作用。
三、金龙四大王信仰传播的原因
明清时期漕运和河工关系国计民生,备受统治者的重视,金龙四大王作为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因具有护佑漕运、防洪护堤、御灾捍患等功能,不断得到官方的加封。正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正月,杭州织造敖福合在其《修建金龙四大王祠墓募疏》所言:“寰宇之神,莫重于岳镇海渎,而岳镇海渎之神莫显于黄河,盖自江浙,上供服御、羞珍、器用,以及七省数百万粮储悉由此贡帝都,浩漭澎湃,冲决不时,总非人力所可御。自兴朝定鼎燕冀,千里澄清,两基奠定,业已早献其祥。皇上御极以来,百灵呵护,而藻火增华,共求悉达,称盛治矣。然要其涸而能通,危而能安者,虽圣天子之生灵,亦金龙四大王之神佑。所以朝廷锡爵建庙,御制祭文,而士民亦崇祠遍河滨也”。[1]673在神灵信仰的发展过程中,官方的政策和态度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官方的倡导和重视推动了金龙四大王信仰在民间的传播和盛行。
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受到了历朝统治者的推崇,士绅阶层和普通民众对儒家思想也给予了高度认可。经过文人改造之后的谢绪,成为忠义的化身,这无疑也是其传播和盛行的重要原因。“明朝奉行儒教原理主义的祭祀政策,重视人格神生前的义行,明初被列入王朝祀典的人格神几乎都是先帝、明王、忠臣、烈士之类。明中期,儒教原理主义祭祀观念更为盛行,原本属于忠臣、烈士的人格神迅速走强。”[2]187-188金龙四大王的人物原型谢绪忠于宋室,于南宋灭亡之际投水而死,属于忠义之士,谢绪在吕梁洪之战中显圣大败元军的传说更突出了其忠义形象,迎合了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在儒教原理主义的影响下,金龙四大王谢绪的忠义形象得以推广。
明代文人徐渭在其《金龙四大王庙碑记》中云:“自洪武迄今,江淮河汉四渎之间,屡著灵异。商舶粮艘,舳舻千里,风高浪恶,往来无恙,佥曰王赐,敬奉弗懈。各于河滨,建庙以祀,报赛无虚日。九月十七日,为其诞辰,祭赛尤盛,非王忠义之气,昭昭耿耿,光融显赫,而能然乎?嗟夫,宋社既屋,于今已数百年矣,铜驼荆棘,故宫茂草,而王之神灵,独磊磊落落,常在天地间。生而忠义,殁为神明,与文山、叠山诸公,并垂不朽可也。宋末谢皋羽翱,为文丞相客,丞相殉国,皋羽每哭之恸,竟死其忠义,至今犹传诵之。王之忠义,不减皋羽,而姓氏湮没,行事尤不概见,其敬畏而奉祀之者,徒以其为江河之神,于风涛汹涌中,死生呼吸,仰其庇佑而然耳。夫岂知其忠义而崇奉之欤!”[3]《西湖二集》云:“世上人不知道金龙四大王的出迹之处,略表白一回,多少是好。话说这位大王姓谢,单讳一个绪字,是晋太傅谢安次子琐之裔也。住于台州,一生忠孝,谢太后是他亲族。……看官,你道这位大王死了百年,不忘故主之恩,毕竟报仇雪耻,尽数把这些躁揭狗驱逐而去,辅枯我皇家,你道可敬不可敬!”[4]
金龙四大王为漕运保护神,往来于运河之上的漕军、运丁成为传播金龙四大王信仰的重要媒介。漕军、运丁负责漕粮的运输,往返于运河之上,涉江过河,艰险无比,故建庙祀神,祈求保佑。《金龙四大王碑记》云:“至我国家长运特仰给于河,而役夫皆兵,沙梗风湍,岁以为患,四百万军储舳舻衔尾而进,历数千里始达京师。缘是漕储为命脉,河渠为咽喉,兵夫、役卒呼河神为父母,蔑不虔戴而尸祝之”。[1]676乾隆《杭州府志》云:“凡舟行黄河者神应如响,宿迁、吕梁及凡有漕运之地并立庙。”[5]虽然没有漕军、漕帮参与修建杭州当地金龙四大王庙的记载,但来自杭州的漕军、漕帮却在外地修建了多所金龙四大王庙。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杭州右卫指挥使蔡同春参与邳州直河口金龙四大王庙的重建[1]693;乾隆二十八年(1763),嘉兴府石门县金龙四大王庙亦为杭州漕帮所重建[6]167。
钱塘安溪谢氏宗族在信仰传播过程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宋末元初人徐大焯《烬余录》记载谢绪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家世不详。明代中后期,谢绪被塑造成安溪谢氏的祖先神。据学者考证:“安溪谢氏迁自浙江台州,始迁祖或是谢长一,明代安溪谢氏追述始迁祖时可能攀附到谢达一支,谢绪被附会为谢达之孙,被纳入安溪谢氏谱系。”[7]安溪谢氏宗族为宣扬祖先神迹,在祭祀、祠墓维修等方面不断寻求官方支持。康熙年间,河神谢绪第十七世裔孙谢裕高请求官方重修祠庙,其《请修祠墓呈文》云:“先神金龙四大王,姓谢讳绪,晋太傅文靖公讳安之三十一世孙也。宋末生于钱塘孝女北乡,痛宋室倾覆,赋诗二首,投苕水而殁,附葬金龙山祖茔,附祀,宋敕建灵惠祠,郡邑志乘,昭然可考。……先神生葬所在僻处乡隅,庙倾像毁,坟墓荒芜,裕高等子孙中落,力难修理。窃念先神,忠等屈原,功追神禹,司河源之通塞,祠民社以无虞,扶危定倾,猝然立应,是以四百万国储,七省漕艘,悉倚先神为系命。凡舟航南北者,望空且为祭赛。况先神生身之乡耶,如岳武穆、于忠肃诸公,凡有功前代者,无不立庙,而先神功绩著于兴朝,护佑及于军国,今祠宇荆榛,丘垄倾颓,伤心惨目,仁孝同哀。……为此驰吁大宗师,轸念神功,……酌委官员,修葺祠墓,以崇祀典,以妥先灵,则河漕永奠、军国呈瑞。”[1]684
钱塘安溪谢氏宗族与官方将安溪塑造成金龙四大王祖庙所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安溪谢氏宗族又参与杭州北新关金龙四大王行祠的修建,敖福合《修建金龙四大王祠墓募疏》云:“今诸绅士同其后裔更择于北关水口创建行宫,则烟火万翕,舳舻千里,漕艘行商,咸得以时申虔祷,皆知神灵所栖而加焉。”[1]673许延邵《募建金龙四大王行殿引》亦云:“钱塘谢生名崧高者,获请于当事,祠墓并建,更募建行宫于北新关,次而吾邑,故友行之之。令侄谢生,名天荷,令孙谢生,名廷恩,合志以光祖烈。集其宗人,奔走从事,后先不怠。”[1]673乾隆二十八年(1763),杭州漕帮于嘉兴府石门县建金龙四大王庙,“适有王之二十四世孙谢掌纶持画像募修复墟祠,僧曰此地正拟造庙,盍留像以垂久远”[6]168。钱塘安溪谢氏宗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龙四大王信仰在运河沿线区域的传播。
四、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功能及影响
金龙四大王信仰在扩大社会交往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官员出于扩大与地方社会交流等目的,在修建庙宇过程中,往往发动士绅及民众广泛参与。杭州北新关有金龙四大王庙,光绪十四年重建。清人俞樾《杭州重建北新关水口金龙四大王庙记》记载:“神姓谢,讳绪,钱塘安溪下墟里人,宋理宗谢太后族侄也。……下墟里故有神庙,而杭之人以其僻远,瞻礼非便。康熙中,建行殿于北新关水口,其地闠闤骈坒,舳舻辐辏,居民行旅罗拜其庭,若节春秋,敬承祀事,楹桷有赫,俎豆维虔,神歆其祀,民蒙其福。庚申、辛酉间燬于兵燹,赪廊碧殿,荡为瓦砾,祠倾像毁,过者尽衋然。永康应敏斋方伯时寓武林,谋于城中缙绅、先生及里父老,即旧址而重建焉。众议允谐,群力咸集,地故米巿,按斛集赀,积微成巨,鸠工庇材,不日而成。材美工巧,有加于昔。落成之后,灵瑞咸臻,邮签津鼓,逖被休嘉,船车楫马,靡不利赖”。[8]正是因为金龙四大王信仰在杭州当地民众中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庙宇才得以重修。
由于钱塘安溪是传说中金龙四大王谢绪的桑梓之地,故杭州当地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宗族化、本土化趋势亦很显著。不仅钱塘谢氏家族奉谢绪为自己的祖先神,当地士绅亦视金龙四大王为乡土神灵,倍加崇奉。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为太平军所攻占,郡人丁丙躲藏于杭州万安桥田家园大王庙中,得以逃过一劫,事后为报答神灵的佑护,发起重修杭州北关和钱塘安溪大王庙,并作《金龙四大王灵感记》,详细记述了此事的经过。光绪二十五年(1899),丁丙去世,其侄中翰发起重修田家园大王庙。长沙人张濬万所作《杭州田家园重建金龙四大王碑记》云:“金龙四大王庙祀遍于淮、黄之间,而杭州安溪下墟湾,神故里也,有墓有祠。其行祠则又有二:一在武林门外北新关,一在城中万安桥之田家园。……当粤贼之初入也,泉唐丁君松生与其兄之子修甫中翰相失也,夜祷于田家园神祠,得异征,遇于祠之庑下。次晨,相携从水门出,故敬礼尤逾常人。既与仲广文学辂兴修下墟湾祠墓,又与应敏斋方伯重复北新关旧宇,念田家园一祠为昔日灵感之地,犹未及事,耿耿焉,自谓无以答神贶而内信于心。尝语中翰宜勉成之。岁戊戌,方议庀材而君已病。今年三月七日起工,越二日,君归道山。中翰怆怀夙命,愈益亟亟,缩板树栌,百匠来集,昼夜经营,阅月而竣。崇墉广陛,丹雘照耀,国人瞻礼裸献,鼓钟以虔以肃。”[9]
金龙四大王信仰在当地民众中间也颇为盛行,形成了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祭祀活动。杭州北关湖墅镇米业发达,商人和民众经常演剧酬神。《湖墅小志》云:“西粮泊桥之北,有金龙四大王庙在焉。……国朝乾、嘉、道、咸四朝以来,湖墅米业甚盛,凡酬神演剧皆在乎此。”[10]393清人魏标《湖墅杂诗》云:“江淮贩米泊粮帮,争赛金龙四大王。台下人观蜂拥至,乱弹新调唱滩簧。”[10]483此外,每年农历七月二十四,塘栖、安溪当地的民众还会自发举行金龙四大王出巡的“龙王会”[11]。钱塘安溪金龙四大王庙建成后,每年春秋二仲地方官员和民众开祭于大王庙。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王庙祭祀仍被列为杭县活动事项之一[12]。
运河沿岸的金龙四大王庙宇不仅是官民的祭祀场所,同时也是运河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众多庙宇成为当地名胜。钱塘安溪金龙四大王庙自建成后,成为众多文人游览、凭吊的场所。清代学者吴焯《谒金龙四大王祠》:“千古灵胥气未销,青霓曳曳下云翘。巫师但击灵鼉鼓,更有何人赋大招。”[1]682清人龚士荐《谒金龙四大王庙》:“激荡中原气,灵光万古留。位非同相国,志已在春秋。封怒含沙尾,云横落远洲。丹青英爽近,极目大河流。”[1]683清代诗人陈文述《安溪吊谢绪》:“竟以安溪作汨罗,三宫行矣事如何。陆张有志终沉海,韩岳无人孰渡河。终古金龙垂祀典,也同白马溯江波。孤山正节还祠庙,从古书生报国多。”[1]683
五、结语
每一种信仰的产生和盛行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明清时期杭州地处运河南端,为传说中金龙四大王谢绪的桑梓之地。有关金龙四大王信仰的起源地虽有待考证,但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钱塘安溪逐渐成为江南金龙四大王信仰的中心。在这其中,文人和钱塘安溪谢氏的演绎和附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相比运河沿岸的其他地区,明清时期杭州地区金龙四大王庙宇的数量和分布并无明显的规律,与运河、漕运也无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金龙四大王虽为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但在杭州地区,其防洪护堤、护佑漕运的职能并未得到展现,其正统性特征也不是极为突出。当地官员和民众更多将其视为乡土神和民间俗神,使得信仰呈现出显著的宗族化、民间化和本土化特征。
参考文献:
[1]仲学骆.金龙四大王祠墓录[M]//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5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2]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87-188.
[3]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98.
[4]周清源.西湖二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545-546.
[5]郑溶修,邵晋涵:乾隆杭州府志[M]//续修四库全书:第7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36.
[6]余丽元,等.光绪石门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7]褚福楼.明清时期金龙四大王信仰地理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0.
[8]俞樾.春在堂全集:第4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485-486.
[9]丁丙.武林坊巷志:第5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44.
[10]孙忠焕.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1册[M].杭州出版社,2009.
[11]王心喜.杭州运河集市[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196.
[12]俞建中.苕溪轶事[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46.
责任编辑:仇海燕
“科学技术哲学”专栏稿约
本栏目以科学技术哲学为选题范围,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研究等。来稿既可是单篇文章,也可是一组文章(对论题作不同视角和层面的讨论)。文章篇幅在10 000字以内,关键词3—8个,摘要200字左右,提供打印件及电子文档(E-mail:wrj6363@163.com)。本刊热诚欢迎各地学人和作者不吝赐稿。
本刊编辑部
【民歌整理与研究】
主持人语:近年来,民歌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各级各类基金项目增多,相关著述不断问世;在实践层面,一些地区性、专题性民歌被列入非遗传承与保护名录,人们对民歌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但对研究者来说,民歌整理与研究薄弱环节既多,可供深化拓展的空间亦大。笔者就此略陈鄙见如次。
一是旧有命题仍有讨论的必要。如卓珂月给明代民歌下了“我明一绝”(陈宏绪《寒夜录》引)的断语,然而“我明一绝”“绝”在何处,也即如何认识这个判断,迄今鲜有正面详尽的回答。私心以为,对“我明一绝”的理解,有纵向、横向两个维度。纵向上,由《诗经》起,传统民歌的演进脉络相当清晰,两汉乐府、敦煌曲子都是其中的代表,到了明代,《挂枝儿》《劈破玉》等的兴起将民歌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一是民歌的数量和种类远超前代;二是参与者众,覆盖面广,几乎成为公共文化事件;三是与文学的关系较为特别——一方面,民歌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强势地影响了当时的文人创作,尤其是在晚明文学新思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为特别的一点,是明代民歌无论是具体内容、蕴含的精神还是表现形式,都与前代民歌拉开了距离,内容上包罗丰富,精神上具有鲜明的近现代人文启蒙的色彩,表现形式上则开始脱离齐言韵文的束缚,开启了后代民歌与民间戏曲贴近甚至合流的先河。横向上,按卓珂月的本意,“我明一绝”的前提,是在有明一代,“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相形之下,唯有“《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纽丝》之类”(《寒夜录》),称得上是代表性的文学样式。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一绝”,是与同时代的诗词曲比较而言。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尽管流派纷呈,作手众多,明代文人的韵文创作确乎笼罩在前人成就的阴影之下,量的扩张难以掩盖质的孱弱。理失而求诸野,文人创作呈现疲态,生于闾巷的民歌则在自由生长,而且一旦遇着合适的机遇,便会焕发出勃勃生机。明代民歌恰恰遭逢此种机遇。纵向横向详细展开,则是相当费力的事,有心者尽可敷衍。
二是个案研究有待加强。个案研究是整体研究的细化和深化。如婚嫁歌谣,作为民歌的一种,是民歌中的异数;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它又承载了丰赡生动的历史细节。如障车习俗,论者以为或有两种,即“婚姻之家自为和婚姻之家以外其他人家所为”,然亦有女家障婿车、男家障妇车等的不同。检诸《全唐文》《唐会要》等文献可知,障车或尚有第三种解释,即女家以帷幔装饰(遮拦、围)婚车,今人以鲜花、彩带饰婚车,即旧时“以帷障车”的遗存(详见拙著《喜歌札记》有关内容)。换言之,由婚嫁喜歌切入,可以尝试解开诸多婚俗史研究中的疑点,亦可从整体上促进民歌、婚俗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又如晚清小说《风月梦》,“写扬州妓女生活,颇能写实,可以考见乱前扬州的风俗”(胡适《扬州的小曲)。《风月梦》中的跌博、花市、撩标等场景,确是“乱前扬州的风俗”;小说中还穿插了近20首《满江红》《劈破玉》《南京调》等民歌时调,与故事情节融为一体,尤其引人注目。传统小说中夹杂韵文,原是一种创作手法,作者希藉此增加小说的可读性,毛宗岗《三国演义·凡例》即指“叙事之中,夹带诗词,本是文章极妙处”,《风月梦》中成规模汇入“当下”色彩浓厚的时调小曲,则从客观上被赋予了独特的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意义,盖因在讨论明清民歌不同特点的时候,一般以为清代民歌与公众日常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风月梦》中人物多是妓女,身份特殊,其张口即来的《满江红》等,俨然成为“联系紧密”的最好注脚。此外,《淮红调》《南京调》等区域特征明显的时调,也是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材料。此一方面,可做工作尤多。
三是空白领域亟须填补。从前辈学者郑振铎、关德栋诸先生至今,传统民歌的整理与研究存在事实上的断层,常规研究接续艰难,空白领域的填补更是紧迫。如在明清民歌整理与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之后,近现代民歌的系统整理与研究也需提上日程。与前代不同,近现代民歌与文学、文化、社会发展的关系愈加复杂,在不同时间段落有不同的表现,典型案例如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的歌谣收集与研究运动,何以成为难以复制的学术盛事?《时调新曲》《时调大观》等曲集的一版再版风靡全国,其中蕴藏着怎样的背景、动因?凡此种种,都可深究。另如在民歌音乐研究方面,借助现存史料,学者们已经对《挂枝儿》《劈破玉》《满江红》等时调俗曲的传承传播路径作了一定程度的复原探究,但是在共性规律的总结与个性特征的分析上,仍有不足,有多位专家谈及,依据已有曲谱与田野调查所得,梳理同名(同宗)俗曲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存在形态,就有无穷文章可做。
综而言之,民歌整理与研究领域固然需要价值与意义一类的宏论,更应提倡脚踏实地解决或大或小的问题。私心以为我辈任重道远,责无旁贷,且与同好者共勉之。
主持人:周玉波: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传统文学与文化研究。
The Religion about Jinlong Sidawang in Hangzhou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 Meng-fei
(Institute of the canal Research,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 Shandong 252059, China)
Abstract:The religion about Jinlong Sidawang in the region along the canal, including Hangzhou which wa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most end of the canal, was extremely prevail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mpared to the other areas along the canal, the numb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Jinlong Sidawang’s temples in Hangzhou had no obvious regularity, and had no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anal and the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Anxi of Qiantang was said to be Xiexu’s homeland. Xie’s family in the Anxi of Qiantang regarded Xiexu as ancestor god. Xie’s family actively advocated and promoted the spread of the religion. The prevalence of the religion about Jinlong Sidawang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gional society and people’s lives. Local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regarded the Jinlong Sidawang as the god of homeland and the god for local protection. It reflected the clear features of lineage, secular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ngzhou;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Xie’s family; religion about Jinlong Sidawang
作者简介:胡梦飞(1985-),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9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1-0091-06
收稿日期:201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