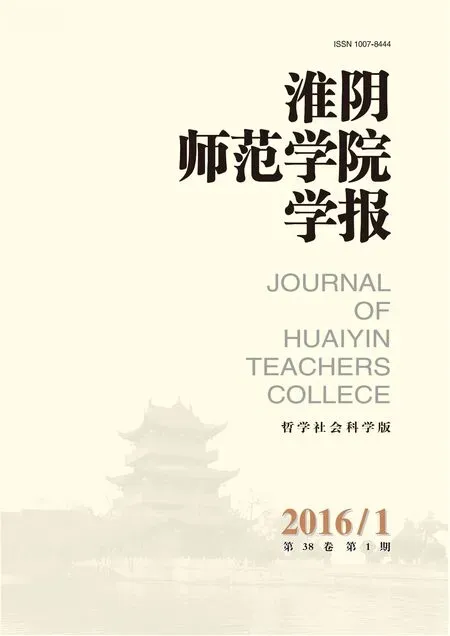“麦克马洪线”的炮制者——英国人贝利侵藏述论
2016-03-16梁忠翠
梁忠翠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学院 欧美国家边界争端与化解研究中心, 江苏 淮安 223300)
“麦克马洪线”的炮制者——英国人贝利侵藏述论
梁忠翠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学院 欧美国家边界争端与化解研究中心, 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集军官、间谍、生物学家和探险家于一身的贝利是荣赫鹏远征拉萨过程中的重要参谋,也是《拉萨条约》的策划者之一。其担任英国驻江孜、亚东商务代办前后,作为鄂康诺的重要助手运作了九世班禅赴印事件。1913年5月至11月,贝利伪装成旅行者潜入西藏东南地区,以欺骗手段进行了半年多的秘密调查,其测绘的数据即为之后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的重要参考。其担任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期间又致力于笼络十三世达赖,修补所谓的“英藏关系”。
关键词:贝利;西藏;麦克马洪线
弗雷德里克·马斯汉姆·贝利(Fredrick Marsham Bailey,1882—1965,一说1967),生于英属印度,其父为上校军官和皇家工程师,曾在英印海军部门服役[1]。他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学院和皇家陆军军官学校,曾服务于英印军队和英印政治部。贝利自幼非常聪明,颇具语言天赋,精通藏语等多种南亚邦国语言。贝利在数十年的涉藏职业生涯中,不仅是一名军官、间谍和政客,也是有名的生物学家和探险家。
贝利于1905年12月—1906年12月、1907年8月—1909年6月两次担任英国驻江孜商务代办,期间1908年7月—1909年6月兼任英国驻亚东商务代办;1921年6月—1926年5月、1926年12月—1928年10月,共约6年9个月的时间,任英国涉藏的重要职官——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期间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到访了拉萨。[2]1贝利曾于1915年获印度帝国三等勋章(C.I.E.),但终生没有被封爵士,最高军衔中校,著有《无护照西藏之行》等。
一、笼络九世班禅
精通藏语的贝利是荣赫鹏远征拉萨过程中的重要参谋之一,参与了不少战斗,也是所谓的《拉萨条约》的策划者之一。
因荣赫鹏急进式武装侵入拉萨,没有完全按照英国内阁的行军计划进行,并且占领拉萨扰乱了英国的亚洲战略布局,所以荣赫鹏撤离拉萨后,英国开始改变对藏政策:既要维护西藏自治,又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使西藏噶厦政府与清政府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自此英国开始更改单纯依靠武力的对藏策略,转而侧重在西藏上层培植势力来攫取利益。荣赫鹏进攻拉萨造成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所带来的拉萨政治真空给了英印政府以可乘之机,且此间十三世达赖的抗英姿态强硬,使英印看上了未曾与其正面冲突且距离印度较近的九世班禅。英印边境骨干官员、高级间谍鄂康诺主张,对西藏喇嘛教两大领袖“分而治之”,以九世班禅对抗十三世达赖喇嘛,为英国牟利。
1905年11月,鄂康诺开始谋划蛊惑九世班禅访问印度的活动,鄂康诺的得力助手贝利全程参与了引诱九世班禅访印的活动。
最初,鄂康诺、贝利等人着手笼络九世班禅系统的汉官、藏官,并向清驻藏大臣有泰隐瞒了他们拜访九世班禅的真实目的。在日喀则的一个月当中,鄂康诺、贝利通过与九世班禅等人交往,最终得出驻藏大臣对九世班禅的管理日渐松弛的结论。于是他们采取威逼、利诱、欺诈的方式,以九世班禅赴印会晤英国王储为由,迅速将九世班禅系统大部于1905年11月带出国境,一时间,清政府对九世班禅的管理失控。
在引诱九世班禅离境赴印的过程中,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贝利时年23岁,九世班禅22岁,二人年龄相仿,加之贝利的间谍素质,使得九世班禅对他倍感亲切,二人交谈甚密。
因为新任英印总督明托等人在九世班禅赴印一事上不甚热情,加之清政府的外交抗议等,结果鄂康诺等人没有达到充分挟制九世班禅留印进行侵藏的目的,最终九世班禅于1906年1月又被贝利等人“护送”回了日喀则。这一来一去,贝利和九世班禅的关系愈加密切。贝利等人离开日喀则时,九世班禅做正式的告别会见,贝利在九世班禅居处献上了厚礼,但未被接受,理由是贝利是客人只能接受班禅的礼物。九世班禅介绍了许多他的珍藏,并谈及许多话题。九世班禅返回日喀则一周后,贝利等人离开。
无论九世班禅后来的思想如何变化,他于1905年至1906年间未经中央政府批准擅自赴印是客观存在的。英印政府的蓄谋已久以及鄂康诺、贝利等人的机警灵活手段促成了九世班禅赴印。九世班禅赴印成行,也是英国笼络西藏政教上层新模式的一次尝试。然而,清廷对鄂康诺、贝利等人蛊惑、裹挟九世班禅赴印之事的最终处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这引得后来者效仿,特别是为之后的十三世达赖出境、倚求英印庇护提供了“先例”。
九世班禅虽然从印度回到日喀则,脱离了英国人对他的直接控制,但英国政府仍对他保有浓厚的兴趣。九世班禅刚回到日喀则,1906年1月24日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就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提出:“必须指示英驻江孜商务委员(贝利)和其他英国官员,在与班禅喇嘛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须将通信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3]贝利也笃信荣赫鹏曾告诫他的话:“我们将来有所收获的唯一机会是现在稳重行事,别走太快,要避免明显的政治活动,确保情报的传递仍然是至关重要的。”[4]为此,贝利依然和九世班禅保持着密切接触。比如,为显示英国的现代化程度,深谙笼络之道的贝利赠送九世班禅手摇留声机,并在聚会上为他演奏手风琴,共赏欧美音乐。为表现基督教英国在佛教问题上的包容,在贝利等人的策划下,1906年初英国在殖民地印度策划举行了“佛教大会”,推举九世班禅为大总管。1906年9月九世班禅邀请贝利再次访问日喀则,贝利虽表现出兴趣,但被英印政府拒绝。贝利返回甘托克后向英印政府报告称:九世班禅“对我敞开了心扉。他想要独立于拉萨之外,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英国政府商谈”[5]72。10月张荫堂到拉萨查办藏事,九世班禅立即致函张荫堂,提出前、后藏的分治问题,此似可以作为贝利等人教唆的佐证。总之,九世班禅系统在贝利等人的影响下一度有违规之举。
二、“麦克马洪线”的炮制者
自“荣赫鹏的远征改变了西方人有关西藏那朴素而美妙的田园诗般的形象”[6]211后,英国一直在考虑重进西藏的方式,希图有新的收获。清王朝覆灭前后中国社会的动乱为英国达成其图谋提供了机会,他们一方面拉拢西藏上层亲英分子,另一方面多次派出勘察队,公开或不公开地勘测、考察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和喜马拉雅山区,为长期侵占西藏做准备。民国初年,贝利极为秘密地潜入了西藏,调查测绘,其所谓的研究“成果”影响至今。
1904年秋,荣赫鹏撤离拉萨时组织了数支勘测考察队,旨在继续搜集西藏的情报,贝利参加了其中的罗林上尉勘测考察队,此事加深了他对西藏的了解。荣赫鹏急进侵藏后数年,作为荣赫鹏亲信的贝利没有直接进入西藏进行调查勘测的机会,直至1911年发生的威廉森被杀事件为贝利提供了机会。
1905年英印政府新任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诺埃尔·威廉森于1907至1911年间多次违反规定溯洛希特河而上,到西藏察隅附近进行所谓的考察,甚至穿越米什米人居住区行至察隅和瓦弄。1911年1月初,威廉森一行在未获得任何正式批文的情况下,一意孤行,沿着洛希特河行走。3月,威廉森不顾当地人反对,强行通过德亨河,向共森进发,结果引发共森附近阿波尔人的愤怒,阿波尔人起而将包括威廉森在内的多人杀死。
英印政府罔顾威廉森等人的侵略事实,只是单纯认定“威廉森及格雷戈森医生,最近在该地(指阿波尔)被杀害”[7],决心报复,“这样一来,从阿萨姆一侧进入西藏的可能性多年来首次得以实现了。对阿波尔、迪嘎鲁和楚里卡塔密西密土地的系统勘测计划即将制定”。敏锐的贝利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想方设法成功地捞到一个参加讨伐阿波尔人的委派,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冬季被派去为威廉森之死报仇。”[8]12此时,贝利也得到了英印政府外交大臣亨利·麦克马洪的支持,被派到楚里卡塔调查情况。贝利认为“此事是把由愚昧无知所致的错误连在一起的结果”[8]14。
不过仓促开始此次间谍之行的贝利,未能完全达到目的,而是在途中折回,主要是因为阿萨姆政府警告贝利“没有二十五名武装警卫开路就不要随便走动”[8]14,以免出现类似威廉森的事件。
1912年秋,正在西姆拉准备法律和财经考试的贝利接到了要他返回阿萨姆的电报,他被任命为“比去年更大的派遣团(指为威廉森复仇的派遣团)的指挥官,将率团直接进入楚里卡塔地区”。但贝利更中意于专注勘测西藏地理,不愿承担指挥官职责,他请求麦克马洪指定他为谍报官而不是指挥官。于是麦克马洪指定了内维尔上尉为派遣团团长,贝利以谍报官身份随团行动。麦克马洪还特意以英印政府的名义称“在有关勘测方面尽最大可能发挥他(指贝利)的才能”。麦氏的这句话被贝利理解为一种暗示,“即允许我进入西藏”[8]15。贝利长久以来再次进入西藏的想法终于实现。
1913年2月7日,贝利和一支驻扎在麻通河谷朋里村的英印军队一起沿河谷上行,数天后到达邻近中国西藏的米培。兴奋的贝利想沿着他早就拟定好的路线向西藏进发。这时他与英印政府指派的在印度测量局有着六年经验的“敏捷、能干,而且特别能吃苦耐劳”[8]21的间谍亨利·摩斯赫德结为搭档。贝利梦想着很快就能进入西藏了。
但内维尔等到的命令是:“我们同意,但勘测队不宜进入西藏。”可见英印政府对进入西藏态度较为模糊。不甘心的贝利、内维尔等人开始“讨论这一迷惑不解的命令的含义何在”。他们得出两种解释,其中一种是“如果命令发自麦克马洪——不知是否如此——那就是说,他同意我们的计划,命令中第二句话不过是作为我们遇到麻烦时的掩饰词罢了。”不过几天后他们又收到了一封电报,要求“没有进一步的命令不准前往”[8]22。
进藏心切的贝利极不愿同内维尔一起折回,他非常担心收到英印政府取消进藏的命令,于是与摩斯赫德谋划一个被迫前往西藏的办法,即:“在离米培十二英里处有两座山——卡龙迪和得森迪,从米培即可看到两山的山头,摩斯赫德必须使用这些高地搞测点。我们达成协议:如果来电取消我们的考察,他就点燃烟柱作为信号,我一看到烟柱就立刻动身到西藏去。这至少能使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有机会及时离去……我们从伊鲁普到米培所走的路是从河西到河东的一个地方,然后再返回到河西的一个地方。假如河上有一个桥被冲毁,就会受阻于米培。这样,我可以说是被迫进入西藏的,因为上述路线是回印度的唯一道路。不久我了解到,沿河西岸有一条弃之不用的小路,在那条小路上摩斯赫德可以和我相遇,但有一个桥断了,怎么断的很难说。”[8]22-23
至5月初,贝利认为“我们出发越快,就会解脱被召回印度的危险,就会愈加保险。否则,摩斯赫德将回到他在德哈拉登的办公室里,我将坐下来从事一些使人失望的、难以忍受和令人厌烦的研究工作”[8]25-26。5月15日摩斯赫德按计划离开米培,16日贝利离开,二人在巴萨姆会合。贝利称:“一离开米培,我们就有所到之处和所见之物都很重要的感觉。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新的鸟类、花草、动物,每一个三角测量点,或者沸点测高读数,都是对人类总知识的增添。”[8]70这样,贝利便开始了私人性质的西藏间谍之行。
两名外国人在西藏随意走动自然遭到怀疑。为隐藏身份,费尽心机的贝利一路上不断编造谎言。
比如8月14日在嘎查的贝利和摩斯赫德收到了藏军来信质询,贝利回信谎称是自费旅游者,取道回印度。他甚至谎称为达赖喇嘛工作,9月29日二人到达错溪卡沿白河右岸上行时,来到吉松代巴家里,代巴询问“为什么要在村上无人及人们都在山上放牲口的时候到马果去”?贝利解释说“是从白马岗远道而来绘制界图的,假如我们完不成地图的绘制工作,达赖喇嘛会气愤的……他问我们有无护照,我说我们的旅行不用护照。则拉宗本七十天以前就给拉萨写信说过我们的情况”[8]167。不过机敏的吉松代巴拒绝为贝利供应乌拉差役。
第二天,贝利和摩斯赫德再次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贝利不仅掏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照片,而且拿出枪和望远镜展示给他们家人看,最终,贝利得到了“信任”。10月12日,在行至德让宗时,贝利如法炮制,解决了德让代理宗本的“信任”问题。
很快,狡猾的贝利找到一种更能博取藏人好感的方法,他自言:“沿途所经之地,人们找我们要药。我们从不拒绝治病的要求,但我们既没有技术,也没有治愈任何病人的药物。可以吹大话的是,从未因为用了我们的配方而吃死人的,这就比合格的江湖医生强得多。也许因为我们用定心丸使人们暂时解除了痛苦,这对我们来说关系不大,因为次日又要上路,等到发现我们的药没有用时,我们已在好多英里之外了。”[8]197-198这种屡试不爽的伎俩竟然使贝利二人在一些藏人心中留下了“神奇般的治病名声”,贝利的间谍之行一时间没有被识破。
此外,贝利还意识到整个旅行的成功将取决于能否劝说当局拨给一笔支派乌拉差役的补贴,所以他“决定尽力表演一出最勇敢的戏……由于我们在此地没有权威,最好的战术就是表现得好像有权威一样”[8]40。在乌拉差役供应遇到反抗时,贝利会哄骗或强势逼迫。比如6月初在金珠宗,当宗本表现出乌拉差役由波巴王后的代表聂巴负责时,贝利说:“我们不可能等到波巴王后的代表抵达之时,我敢说达赖喇嘛也是会同意我的。”[8]44这些话最终使得存有戒心的宗本屈服。
6月13日在麦日,金珠宗宗本派来的索朗群培再次询问贝利并示意他们离开,贝利强硬拒绝。
10月13日,行至李村时,因为藏民拒不提供粮食,贝利再次施展骗术,他大怒称:“我们在西藏已经游历了五个月,从未受过这么无理的待遇。我晃动着则拉宗本的‘护照’,给他们看藏政府的信戳和扎寺喇嘛像,并威胁说,假如对我们不以礼相待,天上的神也会生气。他们被打动了,举起信来,把邮戳贴在脑门上,然后跑去拿来一只鸡,供我们晚餐享用。”不过,第二天仍没有派乌拉的迹象。于是贝利继续佯作暴怒,最终头人称将于当天把贝利送往申隔宗,再过一天就可以到江村。贝利把手里的信戳拿给头人看,还展示噶伦喇嘛从宿瓦送给他们的信,但没有让他看信的内容,贝利诈称:“要看信的内容,也该是宗本,不是你这样的人。”[8]178-17910月15日到色拉后,这里的头人亦拒绝为贝利二人提供乌拉差役,贝利端着枪威逼,最终达到了目的。
总之,自1913年5月至11月,贝利一路上通过坑蒙拐骗竟然潜行西藏半年,从事间谍活动,行程达1 500英里。
这一路贝利可谓“收获”颇多:首先他非法获取了许多珍稀动植物、矿物标本,虽然这些所谓的科学研究收获颇丰,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都是未经西藏噶厦和藏民同意私自得到的。1916年,贝利因在西藏边境的探险而获得奖章,其所著《西藏东南部哺乳类和鸟类》在2007年时仍被研究者认为是“有关拉萨地区鸟类学最好的英文资料”,“是这一地区鸟类学信息的主要来源”[9]。
不过贝利此行最具影响的还是绘制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历史上中印两国之间的东段边界存在着一条传统习惯线,这条线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与喜马拉雅山南麓交接处,长约800余公里(含今缅甸一部)。传统习惯线以北地区一直归中国行政管辖。然而在一些英国人眼里,“从不丹西面,沿阿萨姆东部和北部边境,直到与中国交接处,西藏与不丹远离城镇的地区之间的边界从未划定过”。并且认为“幸运的是,在西藏与印度之间八百五十多英里的艰险地区确定这样一条边界,证明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在方圆一百英里的印度平原上就会有一条固定的边界背脊。介入其间的土地是由险要的山丘和河谷所组成,正因为如此,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屏障”[5]155。为了划界,英国很早就以“探险”为名,派大批测量探险队,化装成僧人、商人、探险旅行者等,窜入西藏地区,进行大量活动。
民国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管理后,英国人担心这将使印度平原处于中国的直接威胁之下,于是便想从印度东北部向北推进,重新划定一条稳固的中印边界线。贝利潜藏的最主要目的也即在此,贝利自称:“要是搞清了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地理状况,可以在两国之间划一条边界线……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旅行除了科学上的意义外,还必须取得极为实际的利益。”[8]序言
虽然贝利标榜自己是“业余的探险者”,“没有配置贪求名声的制造商们免费提供的笨重装备,没有仔细地制定路线或选择季节”[8]原著序,但却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测量仪器,比如他在山顶用沸点测高仪,测量后的结果“都对照印度气象站的观测结果检查过,以校正我们测得的高度”[8]35。贝利也非常仔细地测量和记录了所经之地的海拔、山脉、江河流向、地质地貌、村庄、人种、物种,等等。
贝利妄图通过“科学”的测量,为即将召开的西姆拉会议提供“依据”——“在边界土地还没有测量制图的时候,任何有价值的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回到藏布江上游来,至少到泽当,以便回去给麦克马洪提供一张图,好让他根据种族和地理情况在图上划界”。为达目的,贝利不惧死亡,如8月23日贝利听说距离拉绥一英里半的藏布江大转弯处瀑布有约三层楼高,很是危险。贝利虽有所担心,但“考虑到大吉岭会议或者如我们所知正在召开,或者很快就会召开,在地图上把那些定界时要付诸讨论的地形标绘出来,显然更为重要”[8]127。所以他铤而走险,决定仍沿西南山脉的南面走,以后转回弯头处再取藏布江方向前进。“我和摩斯赫德写报告、记笔记、收集标本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纵情享受社交生活的乐趣……我们两人各有分工。摩斯赫德集中搞勘测和制图,我负责旅行的组织工作,探询各种各样的事情,并收集野生标本……我始终关心的是对印度政府有用的事实,避免由于这一旅行使我们遭受严重谴责。”[8]原著序最终为绘制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准备了一大批资料。
1913年11月12日,贝利回到印度,麦克马洪很快召见了他,然而当时的英国和英印“报纸没有非常详细或者准确地记载我们的所作所为”,大约是英国人顾及将要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不愿过早暴露已经做过的准备,以赢得谈判优势。直到1914年6月22日,贝利才对皇家地理学会“详细报告了我们勘测队深入的最远点和所走的确切路线”[8]212。当时的西方人就称贝利是“现代所有西藏探险家中最有名的”[8]序言。
贝利为英国侵藏获取了极为实际的利益,他毫不讳言:“我们解开了藏布江峡谷之谜,并绘制了该国地图,勾画出西藏与阿萨姆之间的地理界线。”[8]原著序正如英国人在制定侵藏计划时所说,“要考虑到该地区民族部落等因素和前人诸如贝尔、白尔利(贝利)等人对西藏的研究”。
1914年2月“西姆拉会议”休会期间,麦克马洪立即通知贝利带着勘测的资料前来,并重点参考了贝利的详细勘测结果来绘制新的中印边界线,这条线即著名的、影响深远的“麦克马洪线”。此线西起不丹边境,沿分水岭和喜马拉雅山山脊至云南的独龙江流域,即向东伸延至西藏察隅,从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向中国境内延伸了100余公里,将中国享有管辖权、税收权和放牧权的约9万平方公里领土都划进了印度。虽然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但此线自此却给中国边界问题带来了很大影响。
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西姆拉会议”上,“英国、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华民国一致同意首先将西藏的边境对西方人(旅行家、探险家、学者和传教士)关闭,惟有一两名常驻江孜的外交代理人除外。这样一来,西藏又成了一个禁地,而且是比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禁地”[6]209。这样的言论只是臆想,贝利之后又有不少西方所谓探险家潜入中国西藏,从事间谍活动。
三、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贝利干涉中国西藏内政
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是英国非常重要的直接侵略中国西藏的职官,英国通过侵藏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取得的驻江孜、亚东商务代办均受其领导。首任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怀特靠外交讹诈和武装侵略侵害中国西藏;鄂康诺极力主张将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分而治之”谋取侵略利益;贝尔则是通过操纵十三世达赖为英牟利,不过最终因为“武装西藏”计划遭到西藏人反对而被驱逐出藏。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的任命,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是否参加过荣赫鹏的侵藏远征军,有此经历且得到荣赫鹏和鄂康诺赏识的贝利躲过了“在军营度过幽闭而无人知晓的日子”。[2]5
贝利担任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期间,西藏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其插手西藏事务的图谋得逞。
1923年11月九世班禅因与十三世达赖嫌隙日深,被迫出逃内地寻求支持。而此一时期十三世达赖亦采取了两面政策,既不开罪中央政府,也不排斥英印政府。在英印政府的施压下,1924年3月十三世达赖表示“希望贝利4月到江孜后能携夫人一起访问拉萨,以增进英国与西藏之间的关系”[11]。5月19日贝利将此消息上报英印外交部,并请求从访问费用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购买礼物。之后因贝利夫人的父亲在事故中丧生,贝利希望回英国陪伴夫人,提请推迟时日访问拉萨。在英印政府拒绝贝利提请后不久,他在十三世达赖挑选的(所谓的吉日)7月16日抵达拉萨,进行“非正式的访问”[12]。
贝利到拉萨后受到了“非常大的欢迎”。[13]他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九世班禅出走问题。他意识到九世班禅出走已在西藏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后可能会动摇十三世达赖的地位,人们会将“西藏发生的任何灾难归诸于他的离藏”。贝利向十三世达赖提议,由英印政府充当中间人,为噶厦履行九世班禅返藏要求作担保,劝说其返藏。这应该是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首次向十三世达赖提出调解九世班禅返藏问题。但十三世达赖没有回应。贝利向十三世达赖强调,“在与中国谈判问题上,听从英印政府的一切建议,才是唯一的建立永久和平的方法”[14]。当然,这时候的噶厦和十三世达赖抱怨贝尔“武装西藏”的计划已使他们的财政不堪重负,迫切希望能与中央政府达成保证西藏安全的协议,这才是英国最为担心的。但是笃信“武装西藏”政策的贝利却依然鼓动噶厦最好在军事上组织起来,建立一条防御战线。贝利与英印政府的通讯中多处可见训练藏军、武装藏军的电文。
至于“武装西藏”产生的财政问题,贝利坚持噶厦自行解决,噶厦则顺势提出为筹集军费,英国应允许西藏对印藏贸易征收关税,噶厦的要求遭到贝利的拒绝。贝利的此次会谈最终使得十三世达赖和噶厦都认识到英国不可能为西藏的花销买单,于是噶厦对英国的认识发生转变,贝利也开始怀疑“达赖不愿意或者不能领导西藏到英印政府的利益所需的方向上去了”[15]。
贝利明白,“一个政治专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与他们工作的当地首领的直接的、友好的个人关系”[16],于是开始在拉萨寻找其他可能支持“武装西藏”计划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主张在噶厦内部另选人来分享十三世达赖的大权。他想到了曾协助十三世达赖流亡、现为藏军总司令的擦绒。贝利几次与擦绒秘密会谈,拉拢擦绒继续支持英印的计划。为了坚定擦绒亲英,贝利还称:“白厅(英国内阁)不可能派印度军队到拉萨,建议达桑(即擦绒)在印度存钱以备流亡之用。”[17]“后来贝利返印后擦绒也前往,由贝利陪同前去朝拜,还会见了尼泊尔和印度的领导官员,包括印度总督。”[15]110不过这都引起了十三世达赖的警觉,果断地将擦绒及其势力打压下去。贝利拉拢擦绒的计划最终遭到彻底失败,他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眼中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英国人。
1924年8月16日,贝利离开了拉萨,他在10月28日的拉萨之行报告中称:“西藏政府希望印度政府为其内部事务的解决提供帮助,但我尽量避免让印度卷入其具体事务中。”但11月26日,贝利又称十三世达赖“试图借助印度政府的力量迫使班禅返回”,“西方人认为,如今的西藏政府非常无能”等。[18]其报告书重点表达了十三世达赖系统不按英印意图办事的意思。
贝利访藏未取得显著成果,标志着英国“武装西藏”计划受挫,也标志着所谓的“英藏关系”进入暗淡期,英国人又开始认为十三世达赖回到了其流亡印度前的“执拗”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九世班禅在寻求中央政府支持返藏前,曾希望借助英国势力向十三世达赖施加压力。1926年9月7日,九世班禅在会见访问北京的英国王子乔治时,提醒乔治注意英国曾承诺向自己提供保护,乔治向九世班禅保证将由英印政府对此事进行调解。1927年5月,九世班禅通过其代表察色康向贝利转交了一封信,请求英国政府“劝告西藏政府不要压迫他”。贝利的答复是“他不能够插手西藏的内部事务,但由于九世班禅与英国长期存在的传统友谊,所以假如希望他做什么,他会尽可能提供帮助”[19]。后来贝利于1928年5月5日奉命致函十三世达赖,建议他致信九世班禅,信件可由英国驻华外交机构转交。然而,十三世达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和解姿态,他在6月8日致函贝利时指出:“我希望你能够记得,按照《西姆拉条约》,英国政府不应该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20]为保持与九世班禅的关系,贝利转而向英印政府建议,应该为九世班禅在印度提供政治避难,显然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英国此时之所以要十三世达赖允许九世班禅返藏,而不是去印度避难,原因有三:一是担心九世班禅长期在内地,有可能为民国政府所利用,成为汉人的积极同盟者;二是十三世达赖和西藏僧俗各界日益增长的反英情绪令英印政府感到不安,这时如果让九世班禅返藏的话,可以抵制十三世达赖的反英政策。第三,英国政府此时已经见识到十三世达赖“一呼百应”的巨大权威,不想另起炉灶,再次扶持九世班禅系统;他们不但担心引发十三世达赖的强烈不满,还担心开支过大。
但是不管怎样,贝利担任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期间,九世班禅被迫离藏,且其无力解决的藏务“遗产”——九世班禅返藏问题也在此时正式开始成为中英两国政府和噶厦之间漫长的话题。
综上所述,虽然贝利远不如荣赫鹏、贝尔等人在英国侵藏史上那样有名,但是综观贝利漫长的一生,尤其是涉藏的数十年里,他确实影响了中国历史:其一,他参与荣赫鹏侵藏,是英国武力侵藏的直接实行者。其二,他参与引诱九世班禅赴印,是英国企图控制西藏宗教领袖侵藏模式的开创者之一。其三,他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的最先绘制者。其四,他是笼络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重要人物。其五,他是近代史上九世班禅返藏问题的阻挠者之一。总之,贝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侵藏人物。
参考文献:
[1]IOR.MSS Eur F157-142.Bailey’s school and college reports.
[2]Arthur Swinson.Beyond the Frontiers,The Biography of Col.F.M.Bailey,Explorer and Secret Agent[M].London,1971.
[3]Foreign Office Files.India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January 24,1906.FO.535.Vol.Ⅶ,No.8,p15.
[4]IOR.MSS Eur F157-144,Younghusband to Bailey,6 February 1906.
[5]Charles Bell.Tibet Past and Present [M]. 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4.
[6]米歇尔.泰勒.发现西藏[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7]张玉堂为印军向东部边境集结及西藏东南部族动乱被平息等事致安格联半官方性函,1911-10-31第66号[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下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1184.
[8]F.M.贝利.无护照西藏之行(内部发行)[M].春雨,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
[9]陈耘,张林源.西藏珠穆朗玛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状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人类未来——第二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8:155-160.
[10]郝时远,格勒.纪念柳陞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457.
[11]IOR.L/P&S/10/1113.From the People Congress To Bailey,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Dated10th March 1924.
[12]IOR.L/P&S/10/1113P.3398/1924.Telegram No.1188-S.From Secretary of State to India Government,Simla To Delegate in Nepal.Dated25th July 1924.
[13]IOR.L/P&S/10/1113,P.2979/1924.Telegram No.11618.From Viceroy,Foreign and Political Office to India To Secretary of State.Dated17th July 1924.
[14]张永攀.英帝国与中国西藏(1937—194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85.
[15]Alex McKay: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M].Richmond:Curzon Press,1997:107.
[16]IOR.L/P&S/7/237-526,Manual of Instructions for Political Officers,by S.H.Butler.1909.
[17]IOR.MSS Eur F157-214,Bailey’s mission diary,September 1924.
[18]IOR.L/P&S/10/1113,P.4604/1924.Telegram No.631-P.Bailey.Dated 28th October 1924.
[19]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M].杜永彬,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257.
[20]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M], Roxford Books, Hertingfordbury:Roxford Books,1989:169.
责任编辑:仇海燕
作者简介:梁忠翠(1983-),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更迭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演变轨迹研究”(13BMZ032)。
中图分类号: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1-0084-07
收稿日期:201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