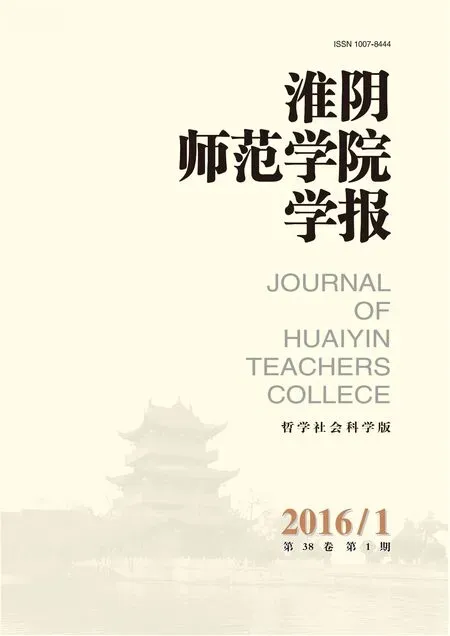“如何认识科学”(十四):科学管理与加拿大鳕鱼业的兴衰——大卫·凯里对迪安·巴文顿的访谈
2016-03-16迪安巴文顿大卫凯里
迪安·巴文顿, 大卫·凯里
“如何认识科学”(十四):科学管理与加拿大鳕鱼业的兴衰
——大卫·凯里对迪安·巴文顿的访谈
迪安·巴文顿,大卫·凯里
摘要:19世纪80年代,加拿大鳕鱼被认为不可能捕捞殆尽。在科学介入鳕鱼业之前,捕捉鳕鱼是基于鱼钩和鱼线的捕鱼方式。自19世纪50年代起,随着工业资本经济的发展,科学家对鳕鱼的种群和最大可持续产量进行了界定。自19世纪晚期起,新的捕鱼工具和方法得以引进,小型拖网渔船的使用引起了捕鱼业规模的真正改变,因为其使用的广泛性和持续性,1968年鳕鱼的捕捞量达到了顶峰,之后捕鱼数量急剧下降,引发了捕鱼业的危机。加拿大政府为了解除这一危机,通过建立和管理专属经济区和渔业现代化,使得大规模鳕鱼捕捞业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得以恢复;但是因为科学预测出错、科学家轻视渔民看法等原因,80年代晚期,加拿大渔业已经无鱼可捕,继而导致了1992年渔业的崩溃和停止。针对渔业科学管理的失败,渔业学家迪安·巴文顿提出应该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待鳕鱼及其生存环境,认为应该回归传统的捕鱼方式,以此维护鱼类生存、保护渔民正直品性。
关键词:加拿大鳕鱼业;科学管理;小型拖网渔船;专属经济区;生态系统
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尽管这一宣告如人所料,但是仍然引起了震惊,当然,还有愤怒。昨天,渔业部部长约翰·克罗斯比(John Crosbie)宣称,近20 000名曾经以捕鳕鱼为生的纽芬兰人在以后的两年中将面临失业。
克罗斯比:我所做的决定是为了确保北方鳕鱼作为一个物种得以存活。
肯尼迪:1992年7月3号,渔业部部长约翰·克罗斯比宣布暂时禁止捕猎北方鳕鱼。那是加拿大历史上失业人数最多的一天——成千上万的渔民一下子没了工作。这一禁令预期执行两年后再恢复捕鱼权。然而,鳕鱼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数量,因而长达15年之后,这一禁令仍然未能消除。多年精心科学管理的捕鱼业怎么突然就崩溃了呢?这一问题便是我们系列节目“如何认识科学”在此所要讨论的重点。这是《思想》栏目的制片人大卫·凯里。
凯里:15世纪末,水手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航海抵达纽芬兰。他后来说,这片海域鳕鱼密集,降低了他的船速。直到19世纪80年代,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伦敦举办的渔业展上发表演说,宣称鳕鱼产业将会持续千秋万代。当时,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而赫胥黎却给出了理由:“这些鱼多得不可思议”,任何捕鱼产业都不会正儿八经地影响其数量。然而,这么不可思议的数量是如何消耗殆尽的呢?其中,科学起着重要的作用。起初,人们相信科学能够全盘掌控渔业运作,可是,随着渔业的崩盘,这一信心逐渐被削弱。结果,现在整个局面都变了。一方面,渔业科学变得更加平常,更加具有尝试性,更加关注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鳕鱼都是在养鱼场人工养殖,它们的生命周期就是“从鱼卵到餐桌”,如行业所描述的那样——一项将管理提升到全新层次的工程。
迪安·巴文顿是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学者,致力于研究人类成功管理或者无法管理的方式,人类的天性以及实施管理的不同科学模式。他于2005年在劳里埃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主要研究了他自身也感兴趣的鳕鱼业。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一直在纽芬兰半岛北端生活并捕钓鳕鱼,他的父母在当地的格伦菲尔慈善医院工作。最近我曾和他谈起在鳕鱼业兴衰过程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他打开了话题,告诉我在科学管理介入鳕鱼业之前的几个世纪内人们是如何捕鱼的。
巴文顿:年复一年,渔民外出去特定的渔场捕鱼,在同样的地方使用同样的捕鱼方法,如果第一年能够捕到很多鱼,那么下一年就捕不到几条鱼。这样的地方每年都在变化。在纽芬兰,人们通过改变职业来应对丰年和荒年。因而,你不能只捕猎鳕鱼,而应该在捕捉鳕鱼一段时间后转而捕捉别的鱼类。捕捉鳕鱼是一个季节性的事情。剩下的季节,最好在陆地活动。这种类型的捕鱼迎合了被称之为重商主义的经济体系,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商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们捕鱼是为了一己之需或是为了生存。他们将多余的鱼卖给商人,或者从商人的店里交换商品。直到19世纪50年代,在纽芬兰,人们所能交换到的商品数量也是极少的。捕鱼所需的大部分材料渔民可以自己制成。
因此,渔业的大部分历史是基于鱼钩和鱼线的捕鱼方式。无论是在近礁还是远礁,在鳕鱼追寻它们的主食毛鳞鱼而迁移的短暂时期内,这种方式照常实施。渔民跟随在远礁产卵的毛鳞鱼后面去捕捉那些追逐毛鳞鱼的鱼类。渔民捕获毛鳞鱼,把它们切开,做成诱饵,然后放在鱼钩上。鳕鱼一旦饿了,就会去咬鱼钩。
然而,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重商主义开始逐渐变成工业资本经济。大约在1850年到1950年期间,这种转变在渔业得以体现。随着这种转变的发生,新的捕鱼技术得以引进,人们得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这些新设备。所以,投资渔业的商人和银行家们开始意识到鱼类栖息地的波动是个问题,因为这样就不能保证他们的投资有回报了。外港国家出现信贷危机,不仅仅是纽芬兰,西欧和北欧国家也是如此。各国政府(挪威是首个搞鳕鱼业的国家),对自然历史学家说:我们需要弄明白这些波动的来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建立现代渔业,这种现代渔业能够依靠稳定、可预测的自然资源流程。
凯里:迪安·巴文顿认为,鱼应该养在野外的要求是现代渔业管理的开端。在此之前,人们把鱼看做商品,他们购买鱼,对鱼分门别类,并且通过航运方式把鱼运入外国市场。但是,对于如何管理野生鱼类,他们一无所知。
巴文顿:鳕鱼的天性和行为不在人类的控制范围以内。它们存在于大自然中,就像上帝的旨意。妄图消灭它们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所认为的主要转变——你也许会说是管理时刻——正在将波动、衰退以及鳕鱼自身的流动转变成一个问题,人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一些形式的干预得以解决,这与只存在于事物天性、我们必须去适应的问题截然相反。
凯里:迪安·巴文顿说:“人们要求鱼的栖息地稳定、可预测,这是多方力量的产物。旧式商业经济逐渐转型为产业制度。生活成本促使渔民捕捉更多的鱼;银行家和投资者想让他们的收益得到保障;政客想要发展国民经济。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人们都寄希望于科学。”
巴文顿:政府开始要求自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解释这些波动的起因。答案的第一部分是要把鱼类看做特定动物种群——拥有自己动态的单一物种种群。鳕鱼以及我们对于它们的认识都要重新组织。关注的焦点从单个一条鱼的形态学转变成种群的聚集规模。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种群范例已经成为理解和研究鱼类的标准方法。
凯里:如今,人们认为把鱼类看作种群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很难想象还能从什么角度看待鱼类或人类。然而,19世纪晚期之前的自然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迪安·巴文顿所说的形态特征,即研究生物的形状或形式。他们的学科在于描述一条典型的鳕鱼,或是一条典型的青鱼。种群是个很不一样的概念——抽象、精确、管理。他的观点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种群使人们易于处理鳕鱼的概念,它使大量鱼类转变成可理解的集合。他说:“但是,有趣的是,真正构成鳕鱼的一个种群究竟是何物,迄今为止未达成共识。”
巴文顿:所谓的“主合派”和“主分派”是有分歧的。主分派在哪里都可以找到种群。他们说在不同的海湾和入口有大量繁殖性的独立种群单位。主合派说真的只有一个生殖单位。两者关于鱼的种群应该存在于哪种规模单位的争论到如今愈演愈烈,许多与鱼类生命周期的阶段有关,在这个阶段,鱼的种群得以确认。例如,当鳕鱼产卵时他们形成这些集中产卵的集成体,大部分是离岸的,在远海礁石。然后,它们迁往近岸。所以,即使在春夏季节,它们散布各处,相距甚远,它们都不是隔离的种群,因为它们会迁徙回去产卵。
凯里:对。那样就不能有助于主合派最终解决争论吗?
巴文顿:是的。你可能会这么想,并且很多年来人们也这样假定。但现在我们发现实际上这比我们想得更复杂。虽然有许多近海鱼群——这些鱼类不会迁移到远礁产卵,但实际上它们在近海海湾之间迁移,在近礁产卵。因此,1992年捕鱼业崩溃之后的研究显示鱼群结构更加多样化、更像主分派所声称的那样。
凯里:鳕鱼种群,现在已经被发现比主合者所认为的更多样化、更本地化。许多在近海钓鱼的人自始至终都明白这一点。这种情况——本地人有时候知道得比科学家更多——还会继续发生,就像迪安·巴文顿继续讲述的故事一样。然而,与此同时,在人们完全管理鳕鱼业之前,另外一个观念必须被添加到种群模式中,那就是承载能力。概念一旦确定,便可以采用种群特征——繁殖力、自然死亡等诸如此类——环境承载力的因素——可用食物等——确定剩余的数量及最大可持续产量,年复一年,这些都可以从种群中获得。
巴文顿:最大可持续产量是一个概念,据说能让你计算出每年能从鱼群中捕捞多少条鱼,而鱼的总量,得益于鱼储量的再生,会在一年内反弹到前一年的水平。因而,最大可持续产量出现的目的在于审察种群内在的动态性,体现在生物总量或者存储鱼的重量上,与正在被取走的鱼的个体无关。这一现象必然会发生,因为它涉及环境承载力的某些知识。能够获得多少食物是一个制约因素。困扰着渔业管理的假设便是种群潜在的变量可以保持不变。有一个假设,自然死亡率——被其他鱼类所食或者年复一年自然死亡的数量——和种群的再生率——那就是每年雌鳕鱼产卵并存活的数量——都是常数。所以最大可持续产量视自然为一台平衡机,这台机器产量过剩到让人年年对其完全无视。最大可持续产量这一观点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种群模式刚刚建立,直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才得以完全建立。
凯里:最大可持续产量的观点显示了对渔业科学的信心。综合模型可由鳕鱼及生存环境组成。在这一理论高度下,开发鳕鱼的能力取决于技术,也许技术是最重要的因素。自19世纪晚期开始,新的工具和方法被快速引进渔业,其中最先引进的便是鳕鱼滚钩。鳕鱼滚钩基本上都有一个或者好多个重钩子,能够使诱饵上下跳动,以便抓住鱼身的某个部分。如今,它既古朴又传统,但在当时,它跨越了一个关键的天然门槛。此前,鱼不咬钩就意味着渔业的结束,现在,即使鱼儿安逸地躺在水底依然会被捕捉。渔民快速地意识到这是多么重大的改变。
巴文顿:当初引进鳕鱼滚钩时,很多渔民认为它并不合适。他们担心其所造成的浪费,因为即使一边钩住了鱼身并不能确保鱼儿一定会落入船中。一旦有浪费,政府就收到了许多投诉信件,要求禁止造成浪费鱼类的此项技术。还不止这些,他们还宣称鳕鱼滚钩会吓走鳕鱼,从而导致来年鳕鱼不会返回渔场。在这些信件中,有众多有关鱼类在观察这一工具的谈论。此外,他们还担心这样的捕鱼方式会对渔民个性造成影响。人们认为有些事情与这种新技术是极为不相称的,因为它违背了猎人与猎物之间的正常关系,不符合渔民开始用这种方式进行捕鱼的个性。因此,用当代眼光来看,引进这种工具是种惯例,你必须抵抗许多渔民的抗议,他们宣称这种工具影响着渔民自身角色认可,且同样影响着鱼类。
凯里:根据迪安·巴文顿研究发现,纽芬兰大多数渔民都坚决抵制那些使他们感到既危害到鱼儿数量又有辱渔民本质的捕鱼技术。他们向女王、政府和大购买商请愿,请求禁止极具破坏性的捕鱼工具。此举与1376年的渔民反应同出一辙。当时,英国渔民就请求爱德华三世下令禁止沿着海底拖网捕鱼。这种拖网只是19世纪末出现的众多新型捕鱼工具的一种。那时还有新型的拖网、曳网(即拖地大网)、刺网,先进的储藏技术以及配有许多诱饵的长线网,这种长线网取代了单纯的手工制鱼线。20世纪中期,这种反对的声音达到了顶峰。
巴文顿:真正程度上的大规模改变,尽管与捕鱼初衷相反,出现在第一批小型拖网渔船的到来,就是1954年出现在大浅滩名叫“公试”(Fairtry)的英国拖网渔船。从那时起至60年代末,这种渔船出现在全球多达20多个不同国家,并被持续使用——在所有时间中,所有气候情况下。因此,在1968年,鳕鱼的捕捞量达到顶峰,且从未被超越。当时,共捕获了80多万吨鳕鱼,绝大部分都是用小型拖网渔船捕获的。
凯里:那么小型拖网渔船是如何捕鱼的呢?
巴文顿:网版拖网,拖拽的主要方式,借助大铁轮的重量将渔网沉入海底。大铁轮在海底一直滚动。由于鳕鱼属于一种底栖鱼类,所以只要你基本上将渔网下到业已确定的鳕鱼聚集地,网住那群鱼——基本上就是舀起它们,然后将网升到海面。这种方法曾经被一些人指为是扫荡海底。因为它将碰巧在那儿的所有东西都一网打尽。这种捕鱼方式——不仅需要被拖出水面进行施工的渔网本身与液压绞车,而且也包括寻鱼技术和钢筋船体——都在战争期间得到了主要发展与应用。战后,寻找潜水艇的技术被用来解决定位和捕鱼的问题。因此才出现了小型拖网渔船,其最高捕捞量为80万吨。1968年以后,捕捞量急剧下降。
凯里:20世纪60年代的丰收引发了捕鱼业的危机。解决办法是,将加拿大管辖区扩大200海里,以此排除了外国船队对大浅滩的觊觎。1977年,加拿大宣告了对此200海里的界限。但是,又出现了意外。当时,国际法要求,一个国家裁定的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必须允许其他国家进行部分捕捞,禁止独占。通过此举,设置虚拟关税,最大化使用资源。为了恢复鱼类存储量,必须减少近几年的捕鱼活动。一旦存储量恢复,据估计,每年鱼产量应该在30万吨到50万吨之间。因此,加拿大海洋渔业部开始了对其新领地的管理。
巴文顿:那他们又是如何管理这块新领地的呢?他们每年在近海拖网并进行调研,然后据此推断鱼的总量。通过此举,不仅会知道有多少鱼,而且能了解鱼类的鱼龄分布——一年鱼有多少,两年鱼有多少,三年鱼及以上年龄的鱼有多少。据此,他们能够估算出已经增长了多少鱼,并推算出能够捕捞多少鱼。一旦放开商业捕鱼,他们就将上述数据和商业船队数量进行结合,所形成的数据便是“单位捕捞努力的渔获量”,其所基于的假设是捕捉定额的鱼类变得容易且鱼的存储量还不断增长,而后他们将这两组数量结合起来,得到“总的允许渔获量”。问题在于1968年以后,近海渔业的确从未得到恢复。尽管人们购买更多的渔网和工具,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捕鱼,他们也未曾发现捕鱼变得更为容易。然而,在近海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并没有纳入管理结构。所以,1977年后的情况是,在进行调查捕捞3到4年之后,这一调查开始预示鱼类存储量在增长,估计出20世纪80年代早期可捕捞的鱼群数量远远超过加拿大传统捕捞量。因为要实施这一充盈鱼群的规划,再加上国际条约规定加拿大必须允许其他国家捕捞它不捕捞的部分,因而渔业现代化成了重中之重。为此,两家国家级渔业公司,国家海产公司和国际渔业制品公司,在加拿大政府的帮助下得以建成。两家公司拥有近海小型拖网渔船和沿海加工工厂。1977年之后,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因为我们即将摆脱海洋管理的无秩序状态,建立起基于加拿大小型拖网渔船而不是外国渔船的理性渔业。
凯里:在这一基础上,大规模的鳕鱼捕捞业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得以恢复。近海的渔民持续面临寻鱼之难,他们的协会把政府告上法庭,试图禁止拖网渔船,这一案件从来没通过州际法院。但近海渔业的确看起来暂时回升了。
巴文顿:带有拖网的渔船越来越容易捕捞到鱼。在80年代早期,拖网勘测的结果表明鱼儿总量处于上升阶段。恰好在1988至1989年间,他们开始意识到商业渔船捕捞量和拖网随机调查指数之间的不符。后来,科学的近海拖网勘测表明鱼儿储存总量出现问题,而且之前的估测数目过高。然而,依赖于陆上加工工业的商业渔船发现他们的“单位捕捞努力的渔获量”在上升。这两组数据说明了不同的问题。海洋渔业部门决定取这两组数据的平均值。两年后,拖网渔船出发试图捕捉定量之鱼却无鱼可捕。此时,渔业部长约翰·克劳斯比刚结束“里约地球峰会”归国。在会议上,他提倡保护和可持续性地发展海洋环境。可是,回国一看,渔业却无鱼可寻。危机由此出现。因此,1992年7月3日,渔业停止。这一假设与1977年的不谋而合——只要停止捕鱼几年,鱼类存储量就会恢复。但是两年之后,鳕鱼量没有恢复,五年之后也没有,甚至过了十年都没有恢复。
(1)根据杂交结果,_____(填“能”或“不能”)判断控制果蝇有眼/无眼性状的基因是位于x染色体还是常染色体上,若控制有眼/无眼性状的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根据上述亲本杂交组合和杂交结果判断,显性性状是_____。判断依据是_____________。
凯里:鳕鱼渔业的崩溃,引发了众多基于科学假设的问题。将鱼类种群和他们的海洋环境模拟成简单的机器似的系统,但这似乎忽略了太多的因素。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的鳕鱼种群结构便被忽视了。
巴文顿:人们现在明白了捕捞顶峰带来的永久性影响,正如人们所说的——巨大的捕捞量于1968年达到顶点,之后就下跌了。事实证明鱼群的持续繁殖需要大量成熟的大型雌鱼。雌鱼越大,它们产卵就越多,成活的几率就越大。1968年之后,鱼群基本丧失了这种成熟的鱼类——不论是雌性还是雄性。他们都已经被捕捞殆尽。但是渔业模型的假设认为,用渔业术语来说,允许“增添鱼群数量”,只要鱼群中能产生后代的鱼被允许存活到生殖年龄,也就是6到7岁,只要它们能达到这个年龄并产卵一次,之后便可以被捕捞了。它们已经完成了繁衍下一代,维持最大可持续生产的使命。但事实并非如此。1968年之后发生的事情都不利于真正恢复鱼类存储量。破坏已经形成。
凯里:这迟到的科学发现有一个有趣之处:渔民担心对其称之为“母亲鱼”的伤害可以追溯至19世纪50年代。在引起渔业暂停的那段期间,根据迪安·巴文顿的研究,最先发现这一现象的便是近海的渔民。他们发现,首先难以找到鱼,接着还发现所捕的鱼比正常鱼龄的要小——我所要重述的要点是——他们清楚近海拖网正在捕捉产卵的雌鱼。
巴文顿:在鲟鱼产卵的季节,它们会聚集起来。事实上,正因为它们在渔场的分布不是那么随意,所以才更容易捕捞。那些还原被拖网捕捞并在其内产卵的鳕鱼故事,没有什么意义——允许此事发生。因此,在鳕鱼产卵前和产卵后,他们提倡禁止近海捕捞,这似乎也是常识。那为什么管理者不采用这种做法呢?原因是,从能够进行捕捞作业来看,近海渔业可以得以控制,但是这源于对鳕鱼产卵认识不够全面——人们认为鲟鱼已经产完卵,可以捕捞,但实际上它们还没有。鲟鱼每年产卵的时间都在变化,也不会在同一时期产卵。因此,这些管理措施没有与鱼的生命机理统一起来。关于这一点,近海渔民似乎要比远海渔民知道了解得多。
凯里:迪安·巴文顿的观点是,总体上,近岸渔民了解更多的与其说是被允许的那些成为近海渔业权威的科学模型,倒不如说是鲟鱼种群的多样性。这一认识无论是从产卵时间而言还是从种类组成而言都是正确的。这一允许捕捉、可持续生产的认知模式,基本上把鲟鱼看做一个单一的库存,而纽芬兰的当地渔民则可以识别出各种类型的鲟鱼。
巴文顿:在当地方言中,鲟鱼的说法有六七种,而科学性的命名,大西洋鳕,只是一个单一种类,在近海就有六七种不同的叫法来区分不同海湾的鲟鱼。这些叫法基于可以区别鲟鱼的某些特点,比如,鱼的颜色,鱼的口味,鱼到达的时间,等等。因此,北方的鳕鱼被视为单一库存、一个大种群,对此,近海渔民并不理解。他们看到有些鳕鱼停留在近海,有些则会在海湾之间迁移,因而这一认识,不只局限于近海鱼类,而是对鱼类的形成有了更细致的理解。
凯里:那么,科学家们如何将渔民们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的呢?
巴文顿:他们做到那样的方法就是,把近岸渔民的知识叫做轶事。这些是无法被证实有效的故事,它们没有数据支撑,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认可。它并未全面展示未来将发生什么。近海渔民的知识不仅被贬作轶事,而且在管理者看来也是一团迷雾。唯一被认为可靠的信息便是在近海区域通过科学调查拖网作业得来的数据。他们如商业船队一样,使用相同的技术——小型拖网渔船,以此获得数据。因此,这些知识一方面遭到轻视,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未知领域,根本就不是知识。
凯里:在1992年之前,近海渔民的知识并没有被赋予和科学知识一样的地位。“轶事的”一词就可以概括那种轻视。这些仅仅是故事,而科学知识则是完整的、可靠的、公正的。不过,回想起来,迪安·巴文顿认为,这两种认知有着明显不同的风格。
巴文顿:被表达为轶事的近海渔业与地域有很大关系,而特殊的地域,又与感官有关。你在拉网或用钩线捕鱼时,所看到的、所品尝到的、在外面的水上所经历到的,都会影响你的感官认识。与这个相反的是对渔业以图表形式呈现在数量上的各种陈述,它们在电脑上会显示,会有在某段更长的时间过去后的可见趋势,这又与管理相互结合。事实上,在刚开始时,渔业并没有纯粹和应用的科学之分,它一直是一门应用科学。一开始设立这门科学是为解决特殊的问题,即达到顶峰时的数字波动。人们认为科学能够走出去,使海从远处变得清晰。在这里之外还有多少可以捕捞的鱼呢?这个数字成为每个渔业管理者的焦点。
对此有几个问题。首先,为了获得那个数字,科学家们需要固定许多变量——假设它们每年都是相同的。没有这个平衡假设,模式计算起来就过于复杂。而且科学家们也不可能每年都外出来查明局部种群的出生率和繁殖率。因此他们依赖平均数值。平均鱼由此开始出现。平均每尾雌鱼产出的鱼卵中有平均数值的鱼卵可以在平均时间内存活,等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平均的假设是将自然进行人工概念化。自然区域表面上是无法掌控的,但是就像平衡机一样,至少在思想上是可以理解和控制的。于是捕鱼量是唯一不定的因素,而且,通过限定捕鱼,通过变更总的允许捕捞量,我们可以规范渔业。因此我认为,这种简易的自然野生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允许一定程度的过度推广。我们控制捕捞力度,保持其他变量不变,便可以就未来鱼类存储量进行规划,并基于此,规划如何发展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这与在此阶段之前应对和适应鳕鱼的动态性是不同的。似乎正如渔民们一直指出的,这种动态性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鱼类的表现与我们在独立的海湾和河湾所发现的并不相符。
凯里:巴文顿说,渔业科学家从一开始就受到环境影响,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工作。迫切想要维持就业率的政府和迫切想要保持工厂满负荷运行的从业者是每年休渔期会议上确定允许捕捞量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可持续最大捕捞量的计算和依赖莫须有的自信,导致了鳕鱼业的衰落。1992年渔业歇业引起了对渔业科学的重新思考和对巴文顿认为应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待鳕鱼和其生存环境的观点的采纳。
巴文顿:从生态系统角度来看,对鳕鱼的生态系统的认识使人意识到所有被假设保持恒定的变量实际上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物种间的互动——猎手和猎物之间的动态性是重要的,捕鱼的行为,曾经被假想为除去多余鱼群数量,实际上改变的不仅是环境——扰乱作息——也改变了鱼群本身的基因组成。所以,你想想看,捕鱼最终是捕完所有的大鱼。从一条鱼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想要在渔场中幸存,你就不想长得很大。你想要小到足够可以穿过网格。你想要在脱离水域之前就能够传递自己的基因。因此,科学家们发现遭到严重捕捞的种群,比如说北方鳕鱼,倾向于在越来越小的年龄和越来越小的尺寸就成熟和繁衍。这是非常新的科学。这发生在过去的几年里。对我而言,有趣的是,我们曾经将捕鱼和鱼类的关系视作一体,在这种关系中,我们能够使种群正常同时捕捉一定数量的鱼类而鱼类性质却丝毫不受影响。随着这种新科学的发展,焦点已经转移到关系和互动上,而不是目标思想或者是像机器一样进行生产。鳕鱼生长的环境被理解为是动态的、变化的。这种立场来自于科学家们所言,我们不能给出最大可持续产量。我们所要处理的误差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为管理者提供有用的东西。因此,好像我们对于鳕鱼了解得越多,这些知识对于管理就越没有用。更复杂的情况出现了,渔业生态之所以被广泛提出,原因在于我们无法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真正建立起理性渔业。这导致了一种应对和适应的态度,其完全有别于1992年之前那种更为自信的科学。因而,我认为对于野生鱼类我们应该保持更为谦逊的态度。
凯里:野生在此是重要的限定词,因为自从1992年就转向了驯养和渔场养殖。而且这种转变,在迪安·巴文顿看来,与他在野生鱼类研究中所看到的新的谦卑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一些小规模的水产养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企图驯养像鲑鱼和鳕鱼之类的鱼类,相对于过去渔业管理的尝试,则需要对自然有着更为综合的管理。他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便源于鳕鱼,如鲑鱼一样,属于食肉动物。它们以其他鱼类为食。
巴文顿:我们经常听到的水产业的争论是水产业的扩张会真正地帮助到野生存储量,即野生鱼类存储量,因为你不会再出去抓捕它们。你在养殖鱼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要养肉食性鱼类,你就必须用其他的鱼来喂养它们,因此如若想要养殖一英镑的鲑鱼,你就必须喂它们三英镑的野生鱼。这些野生鱼主要不是来自你真正用来养殖的水域,而是来自南部水域中被捕捉的鱼群。秘鲁有一个很大的凤尾鱼种群,那儿的凤尾鱼会被捕捉然后制成鱼粉。这种鱼粉还会和鱼油以及其他一些原料混合,去喂像鲑鱼那样的食肉性鱼类。因此,从长远来看,如果你养的是被称作“海洋里的老虎”的肉食性鱼,鱼类养殖就不能减轻野生鱼群的压力。当你在吃肉食性鱼的时候,就相当于在吃用牛喂养的老虎。
凯里:养殖肉食性鱼所费掉的食物比养殖所得还要多这个事实,仅仅是迪安·巴文顿和其他的许多人遇到的与新技术相关的众多问题之一。与在陆地上养殖的动植物的发展速度相比,鱼类养殖的发展速度实在惊人。渔场向野生鱼类传播疾病,还吸引捕食者如海豹、水獭、鸟类——导致了这些动物的死亡或离开。逃脱的动物与野生种群交配造成了不可预估的后果。而且,迪安·巴文顿说,在纽芬兰,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在两个仅有的能够满足鳕鱼养殖所需的无冻环境的海湾——西南海岸的普拉森舍和财富湾——生长着数量最多的生机勃勃的野生鳕鱼。此外,迪安·巴文顿说,鱼类养殖似乎正在改变整个渔业,因此即使是在野生环境中捕到的鱼类现在也会被认为是养殖的。
巴文顿:近来渔民讨论的方法是成为收鱼者而不是捕捞者。在纽芬兰,依然存在的野生渔场已经转向其他物种——主要是螃蟹、小虾和龙虾。现在,那些想要继续待在这个行业的渔夫,已经变成了所谓的职业收鱼者。为了有获得其他物种的捕捉许可证和指标,他们必须真正地去上大学,去获得证书。所以,我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争相驯养正在将渔民的身份转变为可以独立拥有某种特定物种捕捉指标的收鱼者。在1992年的前一段时期,主要是国家、加拿大政府成为鱼群的所有者,而你所拥有的便是被称之为的“生存捕鱼之罪”。因此,如今在纽芬兰,为了一己之私去捕捉鳕鱼是违法的。如果我小时候在安东尼从事过这类的捕鱼活动,换做现在我可能会被逮捕。如果所乘用的船、汽车或者卡车,目的是去捕鱼,那么人们就会被逮捕、控诉及罚款,所有这一切都会被没收。我现在发现存在的问题是:捕鱼来吃是非法的,可是其他捕捉商业鱼群的行业却允许捕捉鳕鱼。当你扔下拖网,所捕的不只是一种鱼,而是各类不同鱼种的混合。那些想要小虾的人可以有一定的捕到鳕鱼的比例。因此,现在的鳕鱼捕捉变成了伴随性捕捉。
凯里:出于兴趣,迪安·巴文顿基于人类对自然采用的不同立场,开始研究鳕鱼产业。几个世纪以来,纽芬兰的渔夫只有在鳕鱼游来咬饵的季节才会捕捉它们。他们把捕鱼成果的波动看做天意。他们使自己适应鱼的习惯,并有保存着以捕鱼为生的荣誉感。之后的商业、经济、科技的变革导致了150年左右的鳕鱼王这一物种的毁灭。最近,一份来自达尔蒙西大学的备受尊重的研究团队的报告预言,以目前的开发比率来判断,全世界的商业渔业将于2050年达到同一状态。
根据历史以及这一前景,迪安·巴文顿得出了一个结论:管理已然失败,也许是时候回归这样的捕鱼方式,它能够维护鱼类生存、保护渔民正直品性。最后他说,但是迄今为止,他在人类对于管理自然的欲望上看不到任何的消减。
巴文顿:管理话语似乎持续变化着并建立在以往失败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是我对于当今渔业管理真正倍感惊讶之处。鳕鱼业管理的失败,或者是渔业管理能力产生预防功效,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限制管理设计与管理计划的延伸。渔业中存在的主要讨论都围绕着这样的观点,即我的经营方法比你的好。渔业管理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理念——管理控制的目标不再是鱼类,而是渔民。虽然技术仍被排除在外,但是渔夫确实成为管理目标。
对我而言,更为有趣的是,在这一点上,应慎重思考近海渔民所言,他们认为,我们拥有的技术基本上毁灭了所有鱼类,消解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因而,我们需要做的便是重新用饵钩和鱼线并保持下去,确保其完全不同于鱼类养殖和鱼类丰收。此外,我认为也很有趣的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在1992年之前,近海渔民基本上被拒之门外,之后,他们说:“没有鱼了,运用这种技术在近海进行管理,停止渔业,肯定哪儿出错了,我们捕不到任何鱼了。”可是科学家当时却说有很多鱼。如今,他们却说基本上没剩什么鱼。鳕鱼正濒临灭绝。应该宣布它们面临绝种。而此时,近海渔民却说:“不,还有鱼。虽然不能为商业渔业提供足够多的鱼,但是近海却有足够的鱼供我们捕捉部分来食用。”不同海湾有不同数量的鱼,这也很有趣。科学家与渔民观点仍然相左,渔夫们说有鱼,而科学家们却认为没有。我认为,能够摒弃这些相左的观点,形成沟通的唯一方式便是认真对待捕鱼技术。管理却解决不了此问题,只要技术仍然被认为“如果管理得当,便是可持续的”。技术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如何行事,还在于我们如何生活。钓鱼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但是自从1949年纽芬兰加入加拿大,渔业便被看做——我们用以达到更高发展阶段的梯子,然后摆脱它——抛弃它,而未认可其在现代生活方式中的有所作为。
(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赵曦译,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荣江校。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责任编辑:王荣江
Key Words:science; gender; language; wording; gene Canadian cod fishery;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dragger;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cosystem
How to Think about Science(XIII):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the Vicissitude of Canadian Cod Fishery
Dean Bavington, David Cayley
Abstract:In 1880s, Canadian cod was considered as impossible to be fished out. Before fishing was under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cod fishing was primarily based on the hook and line. From the 1850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t economy, the scientists defined the cod populations and the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new tools and method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fishing. The wide and continuous use of draggers caused the real change of the scale of the fishing. In 1968, the peak of cod fishing was got. Later, there was a precipitous decline, which led to a crisis of the fishing.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Canadian government made a large scale of the cod fishing resumed at the beginning of 1980s by establishing and managing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fisheries moderniz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scientists’ wrong predictions and disregards to the fishermen’s opinions, in the late 1980s, there was no fish to catch in Canada. It led to the collapse and stop of the fishery in 1992. On the failur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the fishery, fishery scholar Dean Bavington proposed an ecosystem view on the cod and their environment; He thought that it may be time to go back to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fishing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existence of the fish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fishermen.
作者简介:迪安·巴文顿(Dean Bavington),加拿大尼普森(Nipissing)大学首席科学家,有关科学和管理生态学在捕鳕渔业崩溃中作用的博士论文作者。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ZX023)。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1-0061-07
收稿日期:2015-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