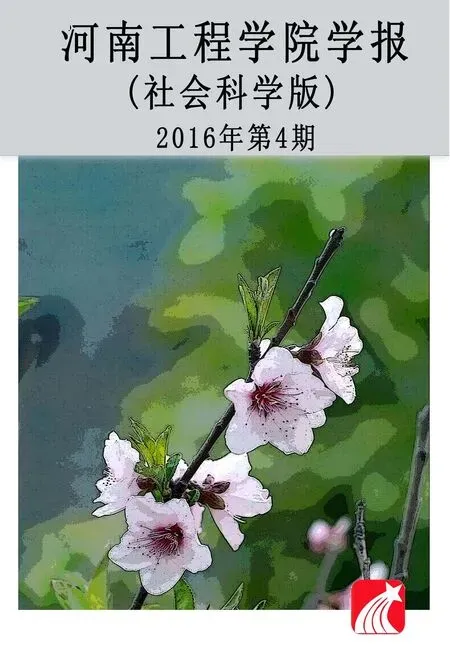从六赃到德日财产犯罪
——我国贿赂犯罪的分层立法建言
2016-03-16陈文昊
陈文昊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871)
从六赃到德日财产犯罪
——我国贿赂犯罪的分层立法建言
陈文昊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871)
六赃中的“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以是否“枉法曲断”为界限进行划分,在法定刑上有所差异。德日刑法理论中关于受贿罪的法益之争分为“不正当必要说”与“不正当不要说”两大阵营。前者将不正当行使职权视为受贿罪一般情形,正当行使职权的行为视为危险犯;后者将行使职权的行为作为基本犯,而不正当行使职权系加重受贿罪。无论采用何种学说,枉法受贿罪与不枉法受贿罪界限分明,且在德日刑事立法中均有所体现。我国将受贿罪侵犯的法益定位为“廉洁”,但这样的定位不仅模糊不清,且未体现出受贿罪中“不正当行使职权”与“正当行使职权”的界限。我国应当区分受贿罪与枉法受贿罪,并在法定刑上体现两者的差异。
六赃;受贿罪;不正当利益
就我国的刑事立法而言,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既可以是正当利益,也可以是不正当利益。[1]前者基本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正当履行职务的情形,后者可以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的情形。我国刑法在法定刑设置上并未体现二者的区别。在笔者看来,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与“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性质上大相径庭,应当通过法定刑配置的差异加以体现。无论从历史沿革,抑或国外立法来看,区分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与“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两种情形都实有必要。
一、六赃中的“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
自《唐律疏议》中“六赃”的概念被提出,至明清的一千余年中,我国封建法典普遍采用这一立法成果,并不断加以完善。[2]六赃主要针对官吏犯罪而言,“赃”即非法获得的财产。张斐在《晋律》注中指出:取非其物谓之盗,货则之利谓之赃。[3]《明例律》第33条规定:“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4]其中,与受贿最为紧密的为“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两罪。
“受财枉法”,即“受有事者则而曲法处断者”[5]。该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该罪主体为监临、主司,“统摄案验为监临”“行案典吏为主司”。换言之,该罪的主体限于官吏。二是该罪的成立以“枉法曲断”为要件,即必须是行为人违法履行职务。与此相应,“受财不枉法”是指“虽受有事人财,判断不为曲法”[5]的情形。“不枉法者,谓虽以财行求,官人不为曲判者。”[4]
唐六赃得到宋朝法典的全盘保留,时至明清,“六赃”的内容发生了相应变更,但“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两罪名及其内容得以保留,构建起明清受贿罪的基本框架。自唐六赃起,对于受贿罪的规定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受贿罪的成立不以违法履行职务为前提,因此,并不在渎职犯罪之列。正如有学者指出,“枉法”与“不枉法”罪名的设立目的在于维护法律权威,使全体官员整齐地按照法律来实现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2]
其二,“枉法”在量刑上比“不枉法”更重。《职制律》第138条规定,“诸监临官受则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一匹加一等,二十匹加役流”[5]。就最高刑来看,“受财枉法”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而“受财不枉法”最高判处加役流;就同样数量的贿赂而言,“受财枉法”的量刑高于“受财不枉法”显而易见。综上所述,唐六赃对“枉法”与“不枉法”在性质上做了严格区分,在量刑上体现明显。
其三,法网严密,打击面广。以“枉法”与“不枉法”为核心展开,《唐律疏议》还规定了其他形式的受贿罪。例如《职制律》第139条的事后受贿,“诸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则者,事若枉,准枉法论”[5]。《户婚律》第153条的出入课役以赃入己,“诸里正及官司妄脱漏增减以出入课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赃重入己者,以枉法论”[5]。《户婚律》第173条的非法赋敛以赃入己,“半非法而擅赋敛,及以法赋敛而擅加益,赃重入私者,以枉法论”[5]。《断狱律》第472条的主守受囚财物,“诸主守受囚财物,导令翻异;及与通传言语,有所增减者,以枉法论”[5]。这些条款实质上是受贿罪的特殊形式,其设置的目的在于严密法网,加强对官吏受贿的打击力度。
由此可见,唐六赃对是否枉法这个要素是非常重视的。
二、日本刑法中的贿赂罪侵犯法益之争
关于受贿罪的法益,一直存在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的对立。前者认为,贿赂罪所侵犯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后者认为,贿赂犯罪保护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6]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受贿罪的成立是否以公务员实施违法或不正当的职务行为为要件。以此为标准,对贿赂罪侵犯法益的界定分为两大阵营:“不正当必要说”认为,受贿罪的成立必须要求行为人不正当的职务行为;“不正当不要说”则不认为不正当职权的行使是受贿罪的必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不正当必要说”虽然认为受贿罪的法益在于职务行为的纯洁性,但并不代表根据该说,只要正当行使职务行为必然不成立受贿罪,这一点将在下文做详细论述。
(一)“不正当必要说”
“不正当必要说”主张受贿罪的实害犯以不正当行使职权为要件。该阵营内的学说包括信赖保护说、纯洁说和国家意志篡改说。
日本刑法以信赖保护说为通说,认为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对公务员职务的公正性的社会一般信赖”[7]。日本最高裁判所1959年12月9日的判决指出,保持公务公平性的必要性自不待言,倘若职务行为伴随着金钱或其他利益,显然丧失了公民对职务执行的信赖。*参见〔日〕《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13卷第12期3186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受贿罪的处罚根据在于,受贿行为会使得公民怀疑:公务难道不是已经被贿赂所左右了吗?[8]因为信赖保护说落脚于职务行使的公正性,故而根据该说得出的结论更倾向于纯洁说。所不同的是,该说以公民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为保护法益。既然如此,针对正当职务行为、过去职务行为的贿赂,同样会使得公民对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从而为以上两种情况提供了可罚性依据。[1]
纯洁说作为信赖保护说基础上的有力学说,认为“信赖”的内容过于宽泛模糊,难以把握[9]。该说认为,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或不可侵犯性。[9]针对纯洁说的责难在于,《日本刑法典》第197条之一的受贿罪并不以行为人违反职务为成立条件。与之相反,《日本刑法典》第197条之三将受贿后实施不正当行为的情形规定为加重受贿罪处罚,表明了正当职务行为也可能成立《日本刑法典》第197条之一的受贿罪。面对以上非难,纯洁说的主张者提出,第197条之一的受贿罪并非作为实害犯,而是作为对公务公正性的危险犯,因此,上述的批判并不成立。[10]
国家意志篡改说是德国刑法理论以往的有力学说。该说认为,受贿罪的处罚依据在于国家意志受到无端阻挠和违法篡改。[6]该说将国家意志的篡改作为受贿罪的成立条件,认为即使没有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也成立受贿罪。这种学说遭受的批判是,根据该说,只要国家意志被篡改,就具有可罚性,行为人违法行使职权后未收受财物的也成立受贿罪,但该结论显然不妥当。
综上所述,“不正当必要说”并不否认正当行使职权的行为可能成立受贿罪,但将行为人不正当履行职务的情形作为受贿罪的一般完整形态,在此基础上构建受贿罪的体系框架,扩张处罚范围。“不正当必要说”需要解释的问题除了正当行使职权也成立受贿罪以外,还有事后受贿的问题。因为根据“不正当必要说”,行为人对其后的贿赂抱有期待,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未能切实行使裁量权,应当认为行为人确定无疑地“违法行使职权”。在此情形下,修正的学说认为,在实施职务行为之前所能认定的“已想到的贿赂对职务行为的影响”,可事后通过贿赂的授受确认这种影响的存在,从而为事后受贿提供可罚性依据。[7]
(二)“不正当不要说”
“不正当不要说”主张受贿罪的成立不以违法行使职权为要件,以不可收买说为代表,清廉义务说也属于该阵营。
不可收买说认为,公务员的职务行为具有不可收买性,法律禁止公务员获取与其职务具有对价性的利益。[11]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处罚受贿罪的基本理由在于不可收买性,即公务员除固定薪金以外,对其所执行的职务行为,不可收受财物。[12]
在笔者看来,不可收买说与纯洁说的争论焦点之一在于,不可收买性与职务公正性孰为表、孰为里。支持纯洁说的学者指出:如果追问为何不可以将公务作为利益的对价,答案最终会是,因为可能会引起不公正的职务行为[13]。与之相反,不可收买说的支持者提出,职务行为的合法、公正性首先取决于其不可收买性,倘若职务行为可以收买,可与财物进行交换,那么权力将会带来各种利益。因此,保护职务行为的合法、公正性,首先必须保证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1]由此可见,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与公正性谁为因、谁为果,谁为本质、谁为现象,是讨论受贿罪法益之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不正当不要说”的另一观点清廉义务说由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主张,认为受贿罪侵害了公务员应当清廉的义务。[6]清廉义务说主张受贿罪的成立不要求收受财物与职务行使之间具有关联性,将受贿罪的入罪范围过分扩大,因而在日本刑法理论中已经过气。
(三)两大阵营的争议焦点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有关“不正当必要说”与“不正当不要说”异同的几点结论:
第一,除了清廉义务说以外,均要求收受财物的行为与行为人的职务之间存在关联性,这一点两大阵营并不存在差异。换言之,日本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单纯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并不成立受贿罪。而根据我国的“廉洁说”,此类行为可能成立受贿罪,这一点将在下文做详尽阐述。
第二,“不正当必要说”并不否认正当行使职务的行为成立受贿罪,但一般将其作为危险犯看待。通常而言,不正当行使职务的行为可以等同于违反职责的行为,以及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因此,“不正当必要说”将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为构成的犯罪视为受贿罪的一般形态,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为视为危险犯。与之相对,“不正当不要说”将不正当行使职务的行为视为受贿罪的加重情节。
第三,“不正当必要说”与“不正当不要说”均承认事后受贿罪,但理由不同。“不正当必要说”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职务行为之时,对将来可能获取贿赂怀有期待,由此影响职务行为的行使,产生不公正行使职务行为的危险,一旦事后受财的行为证明了这种影响的存在,即具有可罚性。“不正当不要说”认为,事后受贿的情形下,公务作为利益的对价,并未突破受贿罪侵犯的法益,因而具有可罚性。
第四,对于受贿又违法行使职权构成犯罪的,是否另行成立犯罪,两种学说可能存在差异。根据“不正当必要说”,因为在受贿罪的法益中已经包含了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因而以受贿罪一罪论处即可。与之相反,根据“不正当不要说”,受贿罪只处罚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的对价关系,并不包括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本身,因而应当数罪并罚。
(四)日本刑法中受贿罪的双层次体系
虽然日本刑法在受贿罪的法益上存在以上争议,但有一点十分明确,那就是在受贿罪的问题上形成了双层次的理论体系。详言之,“不正当必要说”与“不正当不要说”的探讨均以区分受贿罪中的正当职务行为与不正当职务行为为前提。无论是将违法履行职务的情形作为一般受贿罪的加重情节,抑或将合法履行职务的情形作为受贿罪的危险犯,二者的区别在危害性上均有所体现。
除此以外,《日本刑法典》也采取了区分的立法模式。《日本刑法典》第197条规定之一第一款规定,公务员就职务上事项,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的,处五年以下惩役;实施上述行为时接受请托的,处七年以下惩役。第197条规定之三规定,公务员犯前两条之罪,因而实施不正当行为,或不实施适当行为的,处一年以上有期惩役。[14]
《日本刑法典》第197条规定之一前段的单纯受贿罪不要求违法行使职权,但要求具有“要求”和“约定”的行为。所谓要求,是指做出让对方提供贿赂的意思表示;所谓约定,是指针对将来提供贿赂、收受贿赂的旨趣达成合意。[7]换言之,只要具有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的行为之一,且与职务具有关联性,即可成立第197条规定之一前段的受贿罪。第197条规定之一后段规定了受托受贿罪,在收受、要求、约定贿赂的基础上增加了接受请托的要件。受托受贿罪之所以适用更重的法定刑,是因为在存在请托的场合,贿赂与职务行为之间的对价更加明晰,职务行为受贿赂的影响更大。[15]这里的“接受请托”既可以明示,也可以默示,以存在执行职务的意思为要件。[16]《日本刑法典》第197条规定之三的枉法受贿罪则设置了更高的法定刑,因为如前文所述,枉法受贿罪的行为人不仅收受了作为职务行为对价的贿赂,而且实施违法行为侵犯了职务的公正性。换言之,“不正当不要说”与“不正当必要说”的争议焦点体现在立法中,就表现为如果坚持“不正当不要说”的立场,单纯受贿罪就是一般条款,受托受贿罪就是单纯受贿罪的加重情节;相反,如果坚持“不正当必要说”的立场,单纯受贿罪就是一般条款,受托受贿罪就是单纯受贿罪的减轻情节。
由此可见,详细来说,日本刑法对于受贿罪的规制形成了鲜明的三档法定刑:单纯受贿罪、受托受贿罪、枉法受贿罪,法定刑依次提高。无论是“不正当必要说”还是“不正当不要说”,无非观察的视角有所差异:前者将枉法受贿罪作为一般形态,将单纯受贿罪与受托受贿罪作为危险犯看待;而后者将单纯受贿罪作为一般形态,将受托受贿罪和枉法受贿罪视为单纯受贿罪的加重情形。无论如何,三档法定刑的形成已然明晰。当然,就对我国刑法的借鉴意义而言,可以将单纯受贿罪与受托受贿罪合并,与枉法受贿罪形成双层次体系:不枉法受贿与枉法受贿。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也采用了这样的区分。《德国刑法典》第331条第一款规定,公务员或对公务负有特别义务的人员,针对履行其职务行为而为自己或他人索要、让他人允诺或收受他人利益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第332条第一款规定,公务员或对公务负有特别义务的人员,以已经实施或将要实施的、因而违反或将要违反其职务义务的职务行为作为回报,为自己或他人索要、使得他人允诺提供利益或收受他人利益的,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17]第331条和第332条以是否“违反或将要违反其职务义务的职务行为”为界,将受贿罪分成了枉法受贿与不枉法受贿两类,不仅在条文位置上,而且在法定刑上有所体现。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在受贿罪的法益确定上争讼颇多,但无论在学理上还是立法上,德日刑法对枉法受贿与不枉法受贿的双层次划定无可非议。这样的划定理由在于前者还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危害程度更高,因此,当处以更重的刑罚。
三、困境:我国受贿罪的法益偏差
关于受贿罪的法益,我国早期观点认为: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即正确执行国家机关对内对外职能任务的一切活动。[18]“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说”的缺点昭然若揭:一方面,该表述过于模糊,缺乏针对性,因为渎职罪的法益也可以定位于“国家机关正常管理”,二者的区分未能体现。另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所说,受贿罪的既遂标准并非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受到破坏,且该罪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对“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受到破坏”具有认识。[1]
基于“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说”的缺陷,“廉洁说”应运而生,认为“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19]。但该学说的问题也十分明显:
其一,“廉洁说”在表述上过于抽象,难以把握。“廉洁”本身是一个模糊的词,在理解上有所不同。例如有学者指出,受贿罪中的廉洁是指公务员的廉洁制度。[20]但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几乎所有收受财物的行为都成立受贿罪,并且“廉洁说”与日本刑法理论中的清廉义务说别无二致。但问题在于,受贿罪的成立不应当脱离职务关联性的考虑,认为一旦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即成立受贿罪的主张显然不当扩大了入罪范围。就我国立法文本而言,也并非只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即成立受贿罪。
其二,“廉洁说”可能导致受贿罪的成立范围狭窄。“廉”在新华字典中的意义为不贪污,“廉洁”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与财物挂钩。虽然我国立法中的贿赂限于财物,但在学理上如此界定并不妥当。在日本刑法中,贿赂不限于财物,不论有形还是无形,只要能满足人的需要或欲望的一切利益均是贿赂。[20]例如在日本刑事判例中,贿赂包括了金融利益、代偿债务、宴请招待、会员权利、肉体关系等。[7]在笔者看来,我国刑法将贿赂限于财物与将受贿罪的法益界定为“廉洁”不无关系,但这样的界定显然不当限缩了受贿罪的成立范围。
其三,根据“廉洁说”无法划清枉法受贿与不枉法受贿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廉洁说”在“不正当必要说”抑或“不正当不要说”的对垒中属于哪一阵营并不明确。因为如上文所述,“廉洁”是指职务本身抑或公务员制度,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尚无定论。法益界定的模糊导致更多问题无法解决:一方面,处罚事后受贿和不枉法受贿的理论基础在“不正当必要说”与“不正当不要说”的理论框架下大相径庭,在“廉洁说”之下事后受贿和不枉法受贿的处罚依据莫衷一是。另一方面,受贿罪在罪数问题的解决上捉襟见肘。如上文所述,对于受贿的同时违法行使职权构成犯罪的情形是否实行并罚的问题,“不正当必要说”与“不正当不要说”的结论并不一致,前者倾向于以受贿罪一罪论处,后者倾向于数罪并罚。不仅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受贿罪的罪数问题,而且“廉洁说”态度暧昧,导致实践中受贿后违法行使职权构成渎职罪的判决难以一以贯之。
四、贿赂犯罪的分层立法规制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显然,我国《刑法》只区分了索贿与收受贿赂的情形,没有区分不正当行使职权与正当行使职权的情形。这与继承了1979年《刑法》的立法模式不无关系。因为1979年《刑法》第1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997年《刑法》采取了与1979年《刑法》相同的模式,没有区分不正当行使职权与正当行使职权的情形。
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现行《刑法》,均将“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作为受贿罪的加重情节,但“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并不能与不正当行使职务的行为相等同。另外,抛开“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不谈,我国《刑法》对于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单一,仅以数额为尺度,可谓“一维的量刑体系”。相较而言,日本刑法中的受贿罪除了数额以外,在单纯受贿罪的基础上,以受托受贿罪、枉法受贿罪为二维视角,以事前受贿罪、事后受贿罪为时间视角,建立三维的量刑标准体系。笔者认为,这样的量刑体系较为全面系统。
有学者建议在对我国受贿罪立法上废止“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提倡“单纯受贿罪”,即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利益的,即构成受贿罪。[21]对此笔者并不赞同,因为如果认为一旦公务员没有正当理由而收受财物的均侵害了公民对于公务公正性的一般信赖,则滑入了日本清廉义务说或我国“廉洁说”的危险领域,[7]这显然不妥。实际上,索贿和非法收受财物在性质上南辕北辙。在索取财物时,财物与职务之间的对价关系十分清楚;但在他人主动向国家工作人员交付财物时,该财物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具有对价关系,难以确定,[1]因此,需要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加以限制。
基于枉法受贿与不枉法受贿的社会危害性差异巨大,笔者建议在现行受贿罪的条款之上区分枉法受贿罪与不枉法受贿罪两种情形,并在法定刑的配置上有所体现。按照这一设想,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可以设计如下: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贿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不正当行使职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贿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第一款是关于一般受贿罪的规定。一方面,如果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但正当行使职权或做出此承诺的,成立第一款的受贿罪。另一方面,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但无法查明行为人是否不正当行使职权的,以第一款处罚。在此意义上,第一款规定的是堵截构成要件。第二款是针对枉法受贿罪的规定,行为人违法行使职权一般可以与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价,在此情形下,应当按照第二款的加重法定刑处罚。
所谓“不正当行使职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排除了受益人本应得到该利益,行为人通过正当的途径为其实现利益的情形。例如,国家工作人员甲本应为A立案登记,但甲一开始不为A进行立案登记,收受了A的贿赂后方为其立案登记。在此情形下,甲只能成立一般受贿罪。
综上所述,我国对于受贿罪的立法过于单薄,并未体现枉法受贿与不枉法受贿在社会危害性上的差异,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受贿罪法益的确定,进而引发诸如受贿罪罪数等更多问题。贿赂犯罪的分层立法对以上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在技术层面上德日刑法是较为成熟的范本,值得我们借鉴。
[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程天权.从唐六赃到明六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6):91-95.
[3](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928.
[4](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王立民.中国法制史(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7]〔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第六版)[M].王昭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8]〔日〕曾根威彦.刑法各论(第四版)[M].东京:弘文堂,2008.
[9]〔日〕荻原滋.刑法概要(各论)[M].东京:成文堂,2003:236-237.
[10]〔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二版)[M].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1]〔日〕木村龟二.刑法各论[M].东京:有斐阁,1957:288.
[12]〔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295.
[13]黎宏.日本刑法精义(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43.
[14]张明楷.日本刑法典(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73.
[15]〔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各论(第三版)[M].东京:创文社,1990:142.
[16]〔日〕中森喜彦.刑法各论(第二版)[M].东京:有斐阁,1996:340.
[17]徐久生,庄敬华.德国刑法典[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67.
[18]高铭喧.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601.
[19]林亚刚.贪污贿赂罪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97.
[20]赵长青.经济犯罪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563.
[21]梁根林.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立法完善[J].中国法律评论,2015(2):164.
From Six Booty Crimes to Property Crimes in Japan and Germany——The Suggestions for Layering of Bribe Crimes in China
CHEN Wenhao
(LawSchoolof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ccepting property with or without preverting the law in six booty crimes is divided from trying a case unjustly, and thus different punishment is taken. Legal interests of property crimes in Japan are divided into two theories, the difference is if unlawfulness is needed or not. The former sees the act of preverting the law as the basic act, and the act of discharging one′s powers as the potential damage offense. The latter sees the act of discharging one′s powers as the basic act, and the act of preverting the law as the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No matter what theory it takes, the difference of accepting property and preverting the law with accepting property without preverting the law is obvious. In China, the distinction of the two is blurry. We should distinguish the situations of accepting property with preverting the law or not and set different punishment.
six booty crimes; aggravating bribe crimes; illegal interest
2016-04-17
陈文昊(1992-),男,江苏镇江人,北京大学法学院2015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D924.392
A
1674-3318(2016)04-003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