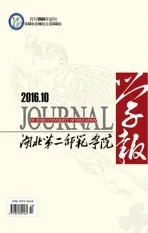创造主体的创造思维规律探寻
2016-03-15夏玲,陶陶
夏 玲, 陶 陶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a.文学院; b.湖北方言文化研究中心,武汉 430205)
创造主体的创造思维规律探寻
夏 玲a,b, 陶 陶a,b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a.文学院; b.湖北方言文化研究中心,武汉 430205)
创造主体写作创造的行为过程其实是一个由“物”到“感”到“思”,再到“文”的转化生成的立体动态的递变过程。任何写作活动都是写作主体作用下的多元复合的整体性行为,并且在具体的递变过程中表现为感知、构思、行文物化三个互逆互动、互约互生的递变过程。如果说把写作创造思维的基本规律提炼出来,本文认为主要体现在主客交融境界、主体与客体的适宜、文本赋形建构三个方面。
主体创造思维; 主客交融境界; 主客和谐适宜; 文本赋形建构
任何实践都要上升到理论,任何理论同时也是实践的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写作也是一样。不注重理论的系统学习和掌握,写作要有所突破很难,终究成不了“大器”。写作行为过程其实是一个递变理论。古代《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其实就是指写作是一个由“物”到“感”到“思”,再到“文”的转化生成,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递变过程。任何写作活动都是写作主体作用下的多元复合的整体性行为,在具体递变过程中,表现为感知、构思、行文物化三个互逆互动、互约互生的环节。这个过程中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点。感知积累,是由“物”到“感”的阶段,是写作主体将“外物”转化为“内物”,将外物内化为主体大脑存储信息的过程。构思,是由“感”到“思”的阶段,是主体在写作意义上的目标定向思维的启动,围绕写作题目或范围,将内化了的信息“意化”为各种概念和意象。随之,思维展开,立意勾画,孕育精神产品。行文物化是由“思”到“文”的物化过程。它是通过文字符号的编码组合,将孕育成型的精神产品物质化的过程。可见,物感、思文是一个纵向发展,而且是一个各个环节互逆互动、互约互生的复杂递变过程,同时又受横向的各种因素影响,制约着写作技法的作用。写作的基本规律主要体现在主客交融境界、主体与客体的适宜、赋形建构三个方面。
一、主体思维的主客交融境界
主客交融境界的内容,包括物我交融、多元交融、言意交融三个方面。
(一)主体的物我交融
所谓主客交融的物我交融是指写作客体与写作主体高度融为一体,古人在写作实践和艺术创造活动中早就认识到写作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互为一体,才是写作创造的最高境界。就像庄子所说“指与物化”,郑板桥所说“心与竹化”一样。文从自然物的色彩、花纹,交错变化而来的。《楚辞·橘颂》曰:“青黄杂糅,文章烂兮”。后来,刘勰又发展了先人的这种思想,他在《原道》篇中说道:“文之为德也夫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次盖道之文也。”刘勰认为文本来自于文人对天地文章的参悟,对叙事形式法则的某些探究、把握、细加体察的结果。物,是外部世界,是作者的认识和表现对象,与写作主体发生相互作用;“我”即主体,写作实践的能动性的自我意识的作者。主体与客体互相作用、有机化合的过程,也就是物我交融的过程。正如列宁所说:“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就像“鹰比人看得远得多,可人的眼睛识别的东西远胜于鹰”(恩格斯语)。美学家利普斯讲道:“移情作用所指不是一种身体感觉,而是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之中去。”对象就是我自己,也就是说,自我和对象的对立消失了,这种状况就是金圣叹所讲的“化身千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能够结合以往积累的经验对它所看到的现象加以鉴别、筛选、分析、综合,“好的眼光不仅是凭‘肉眼’观察,而且依仗心理来审视”(鲁枢元) 。茹志鹃曾说,刘白羽有一次到大庆生活了一个月,却写不出东西,直到他忽然悟到大庆的生活中,有部队的气氛,因为他曾是部队记者出身,所以他感受到这个东西以后,他能写了,能动笔了。可见,主客体相互交融才可能触发写作潜能。
我们更进一步来看写作中主客交流是如何发生的,在先秦《礼记·乐记·乐本》中已有“物感”之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1]。这是强调人心所动是“物使之然”,感于物而动,由自然、社会触动人的情感、思想。后来晋代陆机《文赋》又对其作了阐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2]这里也是强调作者感于外物,引发人心思动,让内心感情变为外在感情行为。
后来刘勰在《诠赋》与《物色》篇中对主客观交融的两种形式作了总结性的分析。《诠赋》中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
《物色》中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从这两节中,可以找两对在意义上相近的关键中心词:“情以物兴”与“随物以宛转”,“物以情观”与“与心而徘徊”。可以把这两组词义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即“物感”与“情观”论。这其实就是写作主体由物到思到文的创造心理过程中的心、物双向交流活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方面是从主体情感的产生,来源于物的感应,主体情感发生于外物对人心的触发,情感从外物移出投射到主体内心过程,这就是“情以物兴”、“随物以宛转”。
另一方面是从主体构思动笔时情感投注于外物并与之融合,是主体情感从内心移入到对象之上的过程。强调主体总是以自己之情去观物,强调的是主体,这就是“物以情观”、“与而徘徊”。这种主体观物,物亦有主观之情,物有感情化,进入到主体性情之中,是主观对象化,是感情的移入。这种过程是与感情移出是同时进行的,即“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思》)
“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一方面是以物为主,另一方面又要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写作者的劳动包含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过程。一方面作者不是被动屈服于自然、生活,他要按照美的规则改造自然材料,从现象、个别中提炼主旨,创造形象,让艺术文本打上作者的个性特质。另一方面,自然、生活对作者来说它是独立的,它以自己的规律去制约写作者的主观性,并要求作者的想象活动服从于一定的客观真实,按现实人生的物理轨迹展开。这二者并驾齐驱地同时影响对方,仅以心为主,用心去想象,驾驭物为我用,就失之真实,走向虚假乃至荒诞;如若让位于物为主体,主体迁就物象,会陷于自然主义,照抄生活,“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就是说明两者有矛盾,应该统一起来,以物我对立为出发,以物我双流融合为最高境界。[3]
后来,童庆炳用“物理境”和“心理场”的概念去替代这一组主客概念范畴,实际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主客交融的融合状态的。[4]他所说的物理境是指事物原初的样态,他所说的“心理场”是指人的经验感受外物的心理反应,这类似于西方叙事学所讲的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即变异的世界及物象。刘勰的“感物”是指对物理境的如实表现,作者要悉心在物理境中体现并把握它们。但是,这些物象必须转化为心象。于是,刘勰又提出“情观”,让客体物象转入心理场,即“与心而徘徊”。这就是让作者以心去融合外在物象,让外物服从于人心,让心物交融,情景交融的想象境界。由此看来,从创作来看,“物以情兴”到“物以情观”,是指情感的发生外在物象对人心的触动,同时写作者总是以己之情去观察外在物象。
主体与客体对立与交融,在写作中是以主体情感运动的双向展开,即德国美学家立普斯所说的“移情”——移入和移出。物我交融化有两种主要融合形式:即由物及我、由我及物。
首先,由物及我的感物而动的移入:“情以物兴”、“随物以宛转”。 由物及我就是指生活对象触发了写作主体的精神、思想、个性、气质的变化,并且这些特征也影响或者融化到主体观察、感受、体验的客观对象之中,让客体对象影响了写作者的精神特征。刘勰曾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就是由物及我的这种融合的最高境界。
主体之情的产生由物而触发,物引出写作主体的情感,主体情感从外在物象、生活移出并投射,影响主体内的情感。“物兴”是指由物而起兴、感兴、勃发,所谓睹物兴情,与物会心,情以物兴,是主体心灵极度活跃状态,是主体由物想象、联想到审美意趣、文化意义,乃至象外、言外、韵外的诗意境界。可见,客观物象与生活的特征影响了写作主体的精神状态,改变了写作主体的精神状态。
写作主体从自然、生活中获得诗意,获得情思,由丰富多样的自然物象触发产生人的情感变化。刘勰曾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物色》)各种自然风景变化引起人的审美情感的产生。
不仅是自然,同样,社会生活的人事变动更能激发作者的种种内心情感。钟嵘论诗的产生,分析了这种相联的审美关系:“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品序》)
自然社会生活对主体的触发往往是“移情”(立普斯)的,是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之中去的。”(立普斯)。法国·波德莱尔曾描述过这种感物而兴的审美经验:你注视着一棵身材亭匀的树在微风中荡漾摇曳,不过顷刻,在诗人心中只是一个很自然的比喻,在你心中就变成一件事实;你开始把你的情感欲望和哀愁一起假借给树,它的荡漾摇曳也就变成你的荡漾摇曳,你自己也就变成一棵树了。同理,你看到蔚蓝天空中回旋的飞鸟,你觉得它便表现得超凡脱俗的一个亘古不变的希望,你自己也变成一只鸟了。
苏轼被贬嫡在黄州,多少已感到人生易逝。可当他无数个日夜观察、体味长江之后,心有所寄,客体触发心中之情。人生易逝,宇宙、自然永恒,“哀人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在物我两相对照中,深深感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于一粟”的感想,将我置于宇宙天地化归一体,瞬间化为永恒:“自其变者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无尽也。”主体的孤寂,失意的心灵之痛,在这种主客交流中被消解,被诗化。当他面对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水光接天的清幽画面和清朗之气,内心涌起“凭虚御风”、“羽化登仙”的心灵感应和向往。这无限的月夜星光,寄寓着作者旷达人生情怀,风清月朗的江天之景象,感应着诗人遗世独立的心灵,人被物所感化,物景染上了个人色彩。
其次,由我及物的情观的移出,“物以情观”。写作主体的情感从人心移入到客体,投射到世界,即是“物以情观”。这就是主体情感、思想个性、气质特征的移入投射到观察、感受、体验的生活物象之中,让对象有了写作者的精神特征。就像刘勰所说“目既往返,心亦吐纳”、“神与物游”: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作者情感精神移入的最高境界。
这与德国立普斯所说的移情有异曲同工之妙:移情作用就是这里所确定的一种事实:对象就是我自己。根据这一标志,我的这种自我就是对象,也就是说,自我与对象的对立消失了,或者说,并不存在。[5]
法国的一位诗人波德莱尔也曾经描述过这种现象和规律:“你注视一棵身材亭匀的树在微风中荡漾摇曳,不过顷刻,在诗人心中只是一个很自然的比喻。在你心中要变成一件事实:你开始把你的情感和哀愁一齐借给树,它的荡漾摇曳也就变成你荡漾摇曳,你自己也就变成一棵树了。同理,你看到在蔚蓝天空中回旋的飞鸟,你觉得它便表现得超凡脱俗的一个亘古不变的希望,你自己也变成一只鸟了。”
刘勰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就是说作者的情感已充满山间,充溢于水中,山水与人一起共游,山水已变异为有主体之情的山水,不是纯客观的山水。
李白诗中描述主客体交融: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李白将自己怀才不遇,寂寞愤世的情怀移入到宣城的敬亭山上,与山融为一体,因而“便觉山亦有情,而太白之风神,有非尘俗所得知者,知者其山灵乎。”[6]
这就道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敬亭山才会看李白,与之相看不厌,并且“两不厌”。诗人的生命感兴跃动,情思勃发,山与人两相交融,互为欣赏,互为情变所运。
在诗人的感受体验中,当客观物象、生活与己融为一体,物我都勃发了生命的精神,其虚实相生,情物共生的诗情画意就产生了。
所以,谢灵运从自然中感受到:“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客观的白云,能抱隐僻的山石,绿竹能对流水媚笑,实则为作者将自己的悠然自得的情思投注到这些白云、幽石、绿竹、流波之中,是诗人作家赋予它们不同的情韵,诗的意蕴、境界就产生了。
物以情观,人观花,花观人,诗人和花融为一体,所以有陆游的境界:“只身化作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人和梅花共同展示那不同于世俗的清孤和坚贞。人观花,花为媒,所以就有金圣叹的诗心: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金圣叹《鱼庭闻贯》)刘勰“情往以赠,兴来入关”不正是这种主客相融融洽的境界?
写作者的心与物相融正是“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来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正是许多写作家的心灵之感。
中国现代美学家朱光潜谈到自己观赏古松的体验时,他说玩味到聚精会神时,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把自己心中的清风亮节的气概贯注到松树上,同时又把松的姿态吸收于我,于是古松俨然变成一个人,人也俨然变成一棵松。我投入了大自然,大自然也投入我。我和大自然达成一气,一块生活,一块震颤。
法国作家乔治桑曾讲过自己与物化合为一体,其实也就是朱光潜所描述的那样共同的感受、体验,也是金圣叹所说的“化身千百”,俨然变成一棵植物。我觉得自己是这种颜色或是那种形体,瞬息万变,来去无碍。我时而走,时而飞时而潜,时而吸露。我向着太阳开花,或栖在叶背安眠。天鹅飞举时,我也飞举,蜥蜴跳跃时我也跳跃。莹花和星光闪耀时我也闪耀。总而言之,我所栖息的天地仿佛是我自由伸张出来的。[7]
主体的物以情观其实类似庄子所描述的庄生梦蝶的境界。主体与对象完全消融了,没有边界。当你进入到这种体验之时,不知不觉地凝视、观看中,自我的情感不知不觉灌注到对象之中,对象被主体情感浸润,人与自然万物往来无碍,真正进入到一种庄生梦蝶的神游之境。你可以驱義和驾车,与太阳共辉,与月亮起舞弄清影,随浪花飞溅,随鱼儿潜游,与鱼儿对话。你是蓝天白云,是细雨斜阳,是天地万物的一起……诗心勃发,物我一体,诗兴的境界,文意的境界,画意的境界也就产生了。
物以情观不仅是主客交融的情感问题,也是主体审美活动形成的机制、规律。物以情观,既有感受情感体验,又有评价、思理贯注其中,达到“志思蓄愤,吟咏情性”(刘勰),超越“极貌写物”、“模山范水”、“图状山川”、“影写云物”的那种写实之美,进入到审美的深层之情感。杜甫:“古木参天二千尺,双皮溜雨四十围”、“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包含有情感评价。
主体与客体交融产生冲动激情,穆青《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中曾谈到这种主客体交融的体会:
“每当吴吉昌对我们谈到他那困难的遭遇和不屈的斗争以及我们提笔写到这些时,我们就抑止不住内心的愤慨和激动。在采写其他先进人物通讯的时候,也时时遇到这种令人的激动的情况,焦裕禄的事迹我们是流着泪采访、流着眼泪写的。……多少年来,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和英雄人物思想感情上的息息相通。水乳交融,有时是掺和着血和泪的。它往往产生一种无论如何都抑制不住的冲动和激情,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简直是一种魔力。它能使你如呆如痴,睡不着觉,周围的一切好像都不存在了一样……这种激情,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像一条无形的鞭子,鞭策着我们去克服一切困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它写好。”
由我及物就是把写作主体的精神、思想、个性、气质的特征融化到观察、感受、体验的生活对象之中,让对象有了写作者的精神特征。刘勰曾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就是这种融合的最高境界。
(二)主客多元交融
所谓主客多元交融,是指写作主体多种素养、多种能力互相交合,是主体的人生阅历、心理特质、思想、知识、语言的技巧相互发生影响所致。诸如司马迁的《史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样伟大的著作,无不凝结着主体的多种知识积累和潜能。冈察洛夫曾说,有人建议他写长篇小说,他却说“我不能,我不会啊……”,他说他没有观察到,没有深切关怀的东西,是他的笔杆接近不了的。泰纳说过,一个艺术家没有哲学思想,便是一个供人玩乐的艺人。所以,清人刘熙载提出“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所以“只有第一等襟怀,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沈德潜语)。要写作,必须“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方能达到多元交融的境界,写出得心应手的文章。
(三)主体言意交融
所谓言意交融,主要指主体表达与内容、形式的内心构思,达到内孕与外化的有机统一。高尔基曾说:语言把我们一切印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它是文学的基本材料,文学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造型艺术。内容或者是思维的构思的完美性能否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古人陆机曾经感到困惑,“恒患文不逮意,意不称物”。语言不能完全传达思维成果,即写作的心灵产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又不得不借语言的有限性去表达内容的无限性.这就要求主体要努力锤炼语言的运用能力。就像王蒙所说,在没有写到纸上,变成作品的定稿以前,构思仍然是不清晰、不成熟、不鲜明、不生动的。因此,言意交融的目标就要努力寻求用适当的语言表达内孕的作品,使之达到相谐相生。因此,交融律的体现,一则是三个交融的相互关系,物我交融是感知阶段,多元交融是内孕阶段,言意交融是外化物化阶段。正像郑板桥画竹,是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个阶段,互为一体,不可分割。二则是“交融”只能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不可纸上谈兵,空对空。
二、主体与客体的和谐适宜境界
万物相宜才构成和谐,所以昔人挚虞曾说“文章者……以究万物之宜者也”,写作文章也是探究万物的内部规律和本质,不违背其特征,表现在文章中也就是意称物,文逮意,像贺拉斯所说的那样:“或遵传统,或则独特,但所创造的东西要自相一致。”文章写作的适宜主要是外部适宜和内部适宜。
外部适宜,一则符合客观规律的内在联系,“若像阳物,宜于刚,若像阴物,宜于柔”[8]。文章外部符合客观规律,就像刘勰所说“随物宛转”,描写一个事物,必须符合事物的特征和规律,不违背它,这就是符合事物的内在规律和联系,因为一篇作品既是描写一个事件,那事件本身就具备一个进行的规律,一个存在的规律,作者抓住了这个规律,写出这个规律,使它鲜明,便是作品的基本结构(孙犁)。二则符合历史发展变化。古人云,“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这就是写作的文章要符合时代新生事物的发展变化和特征,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文章也最能感染读者,为读者所喜爱。
正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文学“就其本质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述者”。三则符合本民族的习惯。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的接受欣赏习惯和接受心理倾向,只有写出了符合这种习惯和心理倾向的文章,才算把握了读者的接受审美习惯和特质。
内部适宜主要指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写作成品的完美境界就是内容与形式的适宜。不同的内容才能选择不同的形式,形式总是为内容服务的。文章的主题意蕴,情节结构,乃至文章中的人事不能离开形式而存在;内容是熔铸到一定形式中去的内容,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主体总在为内容而寻找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并使之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写作的适宜律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其一,适宜是写作最佳效果,并按内在美的造型尺度。其二,适宜是动态,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李渔),正是体现适宜永远是相对的,动态变化的。正像赵翼所云“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这是写作独创性的一条重要规律和法则。
三、创作文本赋形建构的修辞境界
文本的赋形规律主要是指重复与对比的赋形。所谓“重复”赋形,就是指文本主题,主旨的展开,诸如文本材料生成、文本结构生成,起草行文物化等写作过程中,选择那些和自己的写作主题、文章立意和主题信息、性质、意思、情调相同、相似、相近的文章因素(材料、结构单元、段落、语段、句子)进行谋篇、结构、构段、选词、行文,以增其文的感染、说服力,说明性程度。
所谓“对比”赋形思维,就是指主旨主题展开过程中(材料、结构、起草行文),选择那些和自己写作主题、文章立意的主体性信息、性质、意思、情调的相反、相对、相背的文章因素(材料、单元、段落、语段、句子、词汇)进行谋篇、结构、段落、造句、行文,以增强(或反衬)文章感染力、说服力、说明力的清晰度,或称反差。
重复与对比,广义上是修辞性艺术思维的行为。重复与对比的目的性是展开文本主题、主旨,是对文章主题感觉的强化。它们在文章的宏观、中观、微观的思维中均可作为操作模型。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两种人格的对比。李白《早发白帝城》、杨朔《海市》、韩少华《温馨的风》、鲁迅《藤野先生》等就是赋形思维的起承转合的典范作品。
中国古代诗歌重章叠句是比较典型的赋形,马致远的《天净沙》其整个构思思路与结构安排却遵循着重复与对比反衬之规律:“枯藤,老树,昏鸦”与“小桥,流水,人家。”这组意象形象构成重复对比,同时,上下又构成反衬;“古道,西风,瘦马”与“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构成对比重复格局。这种不断反复对照的形式却将那种浪子之孤寂、落寞、迷茫的浪子情怀充分展示出来了,让读者读之却能感觉到一叹三咏之味,所抒之情亦具有回环婉转之美。
更为整饬的重复与对比文本在冰心的散文《笑》中尤为典型。文中一开始叙一种苦雨孤灯之清美图画,重复渲染了一幅凄美孤寂而又徬徨之氛围。继之,文本又叙转过身看见墙上画中的安琪儿“白衣天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我微微的笑,”这是承上开头构成对比反衬。而后再追叙五年前,十年前两个时空中的微笑画面情景;五年前的画面是“古道之旅中见到孩子的微笑,——是她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地笑。”十年前的画面是;雨后初晴见到老妇人的笑——是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我微微地笑。可见这两组画面情景是构成对照,又是重复。而到了文本结尾,却凝练着诗意感怀;眼前浮现出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心下光明澄澈,如登仙界,如归故乡。这是对前文的重复对照,全文层层扣紧笑的情景画面,反复强化其内容,深化其文意,强调其美感特征。
重复对比构篇赋形上,鲁迅的《故乡》堪称典范。该文本开篇叙初回故乡,今之故乡的凄凉、落后与往昔的故乡之美丽、平和构成了对比,以昔之美比今之悲,使其悲者更悲。继之叙第二天所见至第六天所想是对比重复。文中叙所见“西风,断茎,枯草,老屋与凄凉的母亲。”此其承上节重复其悲凉的所思所想,是儿时小英雄闺土,儿时与闺土的欢乐。亦是承上反衬对照,以此显示今之悲伤与凄凉。
第七天所见所想所感所忆又不断地进行着过去与现在的反复对照、重复,更显其悲凉。文中先是所见所想:圆规似的杨二嫂的今日之悲,杨二嫂年轻时被人称为豆腐西施之魅。继之是叙所见:现在的多子多病多老多木纳的闰土;所感:见到闺土时的心理、文化、地位的隔膜与距离,以及闺土的善良、杨二嫂的奸狡。
鲁迅的《野草·题辞》比较典型地运用了重章叠句反复赋形形式: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
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田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这首散文诗歌不仅在结构形式上运用重章叠句反复,而且在内容上,或者相似意义的重复对照对比,或者相反的意义的对照对比,从而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艺术魅力。
自从李渔提出赋形理论以来,创作者不断地深入地认识到这种思维规律特征。在叙事文本中的赋形往往是文本所要表现的主旨主题,常常是某种理念、精神、哲理,或者是形象、性格、命运等等进行重复对比。叙事文往往是通过文本中的人物行动、细节、语言、形象、心理,以及事件情节环境、景物的情调色彩寓意等的叙述、描写,以达到对人物的性格等因素的复叙与对照对比.
抒情文本的赋形常常是对所要表现的主旨寓意,从某种情思,某种感觉、感受,某种情绪、情感体验,某种意象、意境,韵味,某种玄思、哲理等等上面予以复沓对比对照。因此,对这些内容的传达主要是将诗人主体的创作时那突发而生的情绪感觉、心理体验、联想想象、幻觉幻想、思索顿悟,乃至对景象、细节的即景会心、现量摄取,从而形成诗的感觉、韵味、意蕴意境。
提高写作能力的关键在于训练思维,使之灵活、简洁、流畅,具有独创性。写作的能力是智力、专门能力、创造力的一种;写作能力又是人的感受力、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力的综合。因此,写作能力既体现为一种智力,也体现为一种专门的能力和创造力。所谓智力是人认识事物并能解决问题的能力,表现在写作活动过程中主要是能融铸于感知力、运思能力和物化能力之中。专门能力是不同专业领域的某些特殊能力,在写作中主要表现为观察力、思维力和文字表达力。创造力是善于解决新问题、独特创新的能力,在写作中它主要表现为想象能力、联想能力和感悟能力等。写作培养全能素质,归根结蒂要养成自己的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格精神,把自己塑造成人格完美的作者,并影响他人,这才是最终目的。
写作的技巧 、技能的掌握非一日之功,总是按照一定阶段、阶梯在逐渐成熟,从简单的作文到比较熟练地掌握,乃至达到某种完美的境界,体现着渐进性。名家往往从学习写作的起步到成为大家都是渐进性的,没有谁能离开基本的技能的掌握,就写成了大家,写出传世的名作的。这就是写作的渐进性。与此同时,写作又是递进性的,写作的一个阶段突破他人和自己,超越前人和过去,写作才能有发展创造。这两者互为关联,互为因果。渐进性是基础,递进性是更高的飞跃。
怎样才能在写作活动中体现写作的渐进性的规律呢?一则是要循序而进。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阶段,写作也体现由模仿到独创,由规矩到熟巧,由简明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二则是由多种途径,或得力于广泛的阅读,或得力于丰富的生活,或得力于学识渊博,或得力于技巧娴熟。
[1]先秦两汉文论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60.
[2]张少康.文赋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4.
[3]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4-75.
[4]童庆炳.从物理境“转入”心理场——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的心理学解[A].童庆炳谈文心雕龙[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5]立普斯.论移情作用[A].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汇编(下)[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848.
[6]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A].韩兆琦.唐诗选注汇评[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240.
[7]朱光潜.印象与回忆[A].朱光潜全集(一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239.
[8][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M].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
责任编辑:彭雷生
Creation of the Main Rules of Creative Thinking
XIA Ling, TAO Tao
(a.School of Liberal Art,b.Hubei Dialect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 China)
Writing is a process from “thing”, “sense” ,“thinking”to “article”, which is abstract and dynamic. Any writing is a comprehensive and holistic activity by writer, and in such process perception,conception, and writing are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basic laws of writing creativity are the fus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e harmon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nd formation of text.
subject’s creativity; fus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harmon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formation of text
2016-09-05
湖北省人文社科学研究基地湖北方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夏 玲(1974-),女,湖北黄冈人,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写作学。 陶 陶(1965-),男,湖北黄冈人,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
I01
A
1674-344X(2016)10-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