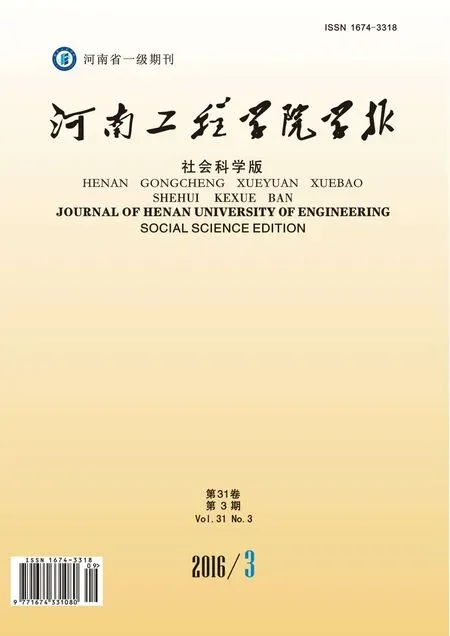《诗经》所见河洛地域婚恋诗的情感特征及文化内涵
2016-03-15冯源
冯 源
(1.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2.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诗经》所见河洛地域婚恋诗的情感特征及文化内涵
冯源1,2
(1.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2.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诗经·国风》中河洛地域婚恋诗的情感特征及文化内涵有以下几点:一是崇尚“挚而有别”的情感,以和美婚姻为旨归。在河洛先民的意识里,真挚而专一的爱情是婚姻的起点,婚嫁以时是爱情的归宿,而婚后和洽的夫妻之情更深为河洛先民所崇尚,反映出河洛先民以婚姻为指向的情感观。二是青年男女之情热烈浪漫,折射河洛民风民俗。热烈浪漫的男女之情,大量存诸婚恋诗中,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上古时期河洛青年男女上巳节相会、赠物结情、以舞挑情、以歌传情的风俗。
《诗经》;河洛地域;婚恋诗;情感特征;文化内涵
综合学界对《诗经》地域的研究成果及对河洛地域及其文化圈范围的界定可知,《诗经·国风》中完全隶属河洛地域的诗歌有《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魏风》《唐风》《桧风》等,此外,《周南》中的一部分诗歌亦为河洛地域作品。据此,可大致统计出《诗经·国风》中以歌咏爱情为主题的婚恋诗出自河洛地域的约有51首,占《诗经·国风》全部婚恋诗的71%左右。[1]学界对《诗经·国风》中婚恋诗的研究成果颇丰,然结合河洛地域来探讨其情感特征和文化内涵的研究却较为稀少。为此,本文立足于《诗经·国风》中的婚恋诗,结合周代礼制及河洛地域的民风民俗,试图探讨河洛地域婚恋诗的情感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一、情感“挚而有别”,指向和美婚姻
河洛地域婚恋诗的发端之作是《周南·关雎》,此亦为《诗经·国风》的首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窹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2]
《关雎》中正和乐的情感基调深为孔夫子赞赏,被誉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此后,历代注《诗经》的学人多以此为基点,从不同角度对其内涵进行阐释。《毛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2]562《毛传》:“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笺》云:“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2]570朱熹《诗集传》:“窈窕,幽闲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毛传云:‘挚字与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汉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4]1-2闻一多《诗经通义甲》:“案本篇传云‘挚而有别’者,雌雄情意专一,不贰其操之谓。《淮南子泰族篇》曰:‘《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不乖(王念孙谓乘之误,非是。有说别详)居也。’不乖居犹言不乱居。《后汉书·明帝纪》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曰‘雎鸠贞洁慎匹’,慎匹即不乱其匹,亦犹《素问·阴阳自然变化论》曰‘雎鸠不再匹’,张超《诮青衣赋》曰‘感彼关雎,性不双侣’也。凡此并即专一之意……此皆‘有别’二字之确解也。”[5]291-292
综合以上注家所论,自郑玄、朱熹以至闻一多,虽然对《关雎》的阐释有不尽统一之处,但他们皆认可毛公对《关雎》情感特征的概括:“挚而有别”,即夫妇之情既真挚又专一,得性情之正,正所谓“不贰其操”。
此种对感情的真挚专一,在河洛地域的婚恋诗中多有反映,如《郑风·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2]
闻一多先生《诗经通义乙》注曰:“《传》:‘綦巾,苍艾色,女服也。’《说文》引《诗》作巾,云:‘未嫁女所服。’”[6]214据此,此诗系男子思恋意中人所作。诗人反复吟诵东城门处“有女如云”“有女如荼”,此处 “云”“荼”系指东门游玩女子的衣色,“衣色白,故曰如云也。二章如荼,亦切下缟衣言。《考工记·鲍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注》:‘当如茅秀之色。’《国语·吴语》‘白裳,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注》:‘荼,茅秀。’《汉书·礼乐志》‘颜如荼’,《注》引应劭曰:‘荼,野菅白华也,言此奇丽白如荼也。’……《诗》曰‘如云如荼’,取义相同,皆形容女衣之词”[6]213。此处为郑地,是殷商部族的旧地,女子以着白色衣服为美,反映出“殷人尚白”*《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礼记正义》卷六,2763页上B—下A。的文化传统在此地的延续。诗人面对东城门如云的美女,并不为之所动,他所牵念的乃是缟衣綦巾的女孩,而“缟衣綦巾,女服之贫陋者,此人自目其家室也”[6]519-520。可见,在诗人的心中,真挚而专一的爱情最重要,并不在意女孩的家境是贫陋还是富庶。
《鄘风·柏舟》中女子的呼诉,历来被认为是对爱情坚贞的誓言:“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2]朱熹《诗集传》云:“旧说以为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则在彼中河,两髦则实我之匹,虽至于死,誓无他心。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极,而何其不谅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时独母在,或非父意耳。”[4]28朱熹所谓的“旧说”,是本《诗序》而来,对此说,清人姚际恒多有批驳:“序谓‘共姜自誓’,共伯已四十五、六岁,共姜为之妻,岂有父母欲其改嫁之理。至于共伯已为诸侯,乃为武公攻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则《大序》谓共伯为‘世子’及‘蚤死’之言尤悖矣。故此诗不可以事实之;当是贞妇有夫蚤死,其母欲嫁之,而誓死不愿之作也。”[7]朱熹与姚际恒所要争论的焦点是诗中女子是否为共伯之妻,他们一致的观点则是此女子为贞妇,此倒颇合道学家的路数。而在理论上还存在一种可能,即诗中女子是为现实中所中意的男子盟誓。不论怎样,其坚贞的情感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王风·大车》中女子的指天誓言,亦表现出对爱的坚贞:
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
大车啍啍,毳衣如璊。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毂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2]
此为一首相约出奔的诗,诗中的女子不仅爱得坚贞,亦爱得果敢。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畏子不敢’……《广雅释诂》:‘敢,犯也。’敢谓犯礼,不敢犹不犯也。畏子不犯即谓不犯礼以奔,与下章‘畏子不奔’同义。”[8]244女子指着太阳起誓,“毂则异室,死则同穴”,此处的“毂”,《毛传》注曰:“毂,生。”[2]704意谓生不能同室,死亦愿意同穴。《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9]1580只要适婚男女于仲春之月相奔,是不会犯礼的。而由诗中来看,两人的相奔却有犯礼之处,故而女子担心男子不够勇敢。
在河洛先民的意识里,真挚而专一的情感固然值得赞颂,而其最后的归宿,必然是指向和美的婚姻。《关雎》中的男子“发乎情”,思慕窈窕、淑善的女子,而“止乎礼”,以礼乐成其婚姻之美。此种情感特征及温柔敦厚的做派,深为儒家推崇,自毛公以至朱熹,皆认为《关雎》是在歌咏周文王与后妃,其德操可以“风天下,正夫妇”,体现着儒家的文化理想。当然,对于《关雎》是否真的在歌咏周文王与后妃,学界仍存有争论,而其中所流露出的对礼乐婚姻的褒赞情感,却客观而真实地存在。《周南·桃夭》中对婚嫁以时的歌颂,即体现着河洛地域先民的婚恋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2]
此诗以桃起兴,以桃树之少壮、桃花之美盛喻女子美好的青春与容貌,以桃之累累果实、繁茂之枝叶喻女子子女昌盛,包蕴着先民对婚嫁以时的喜悦与祝福。
此种情感亦反映在《邶风·匏有苦叶》中: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有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
嗈嗈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昂须我友。[2]
关于此诗的诗旨,古代注家多不脱《毛诗序》影响,认为是一篇规讽之作。当代学者中以余冠英先生为代表,认为此诗系言情之作,他在《诗经选译》中阐释:“一个秋天的早晨,红通通的太阳才升上地平线,照在济水上。一个女子正在岸边徘徊,她惦着住在河那边的未婚夫,心想:他如果没忘了结婚的事,该趁着河里还不曾结冰,赶快过来迎娶才是。再迟怕来不及了。”[10]18笔者认同此种观点。诗中所用物象多含有婚嫁意蕴:起兴用的“匏”,成熟之后可用作渡水的工具,《国语·鲁语下》:“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11]诗中所谓“匏有苦叶,济有深涉”,即有夫妻共济之喻,且“匏”剖开后名“卺”,可用作古代婚礼上的礼器,《礼记·昏义》:“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孔颖达疏云:“卺为半瓢,以一瓠分为两瓢,谓之卺,婿之与妇各执一片以酳。”[12]3648诗中的“雁”亦为古代婚姻六礼中必备之物,《白虎通·嫁娶篇》释义云:“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13]“雉鸣求其牡”中的“牡”,为雉鸟中的雄性。显然,雌雉求偶之象,喻表着女子对心上人的期盼。此外,最后一段的“招招舟子”,郑玄《笺》云:“舟人之子号召当渡者,犹媒人之会男女无夫家者,使之为妃匹。人皆从之而渡,我独否。”[2]639整首诗的意象及情感,无一不传递着女子对爱的坚贞及对婚姻以时的热烈期盼。
《唐风·绸缪》亦折射出河洛地域先民对美好婚姻由衷的喜悦之情: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2]
关于此诗的诗旨,《诗序》以为“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2]722。朱熹承其旨而申之曰:“国乱民贫,男女有失其时而后得遂其婚姻之礼者。诗人叙其妇语夫之词曰:方绸缪以束薪也,而仰见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见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谓曰:子兮子兮,其将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庆之词也。”[4]70马瑞辰则以为:“此诗设为旁观见人嫁娶之辞。‘见此良人’,见其夫也;‘见此粲者’,见其女也;‘见其邂逅’,见其夫妇相会合也。”[8]346他并不认为此诗为“自庆之词”,并做了进一步阐释:“《传》:‘绸缪,犹缠绵也。男女待礼而成,若薪刍待人事而后束也。’瑞辰按:……诗人多以薪喻婚姻。《汉广》‘翘翘楚薪’以兴‘之子于归’,《南山诗》‘析薪如之何’以喻娶妻。此诗‘束薪’、‘束刍’、‘束楚’,《传》谓以喻‘男女待礼而成’,是也。”[8]345全诗充盈着幸福与喜悦的基调,不论是诗人自庆,还是旁观者之辞,都使人感受到洋溢其中的对新婚爱情的赞美与歌唱。
真挚而专一的爱情是婚姻的起点,和美的婚姻则是爱情最完美的归宿,而婚后和洽的夫妻之情更是河洛先民们乐于歌唱的题材。先看《郑风·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 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2]
朱熹以为:“其相与警戒之言如此,则不留于燕昵之私可知矣……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馈妇人之职。故妇谓其夫既得凫雁以归,则我当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饮酒相乐,期于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静而和好。其和乐而不淫可见矣。”[4]51余冠英先生以当代人的视角,指出“这诗以诗中人物的对话写出一对夫妇分担劳动,互相恩爱,和谐温暖的共同生活”[10]49。不同时代的学者着眼点虽不同,但均一致认为此诗以对话的形式勾勒出夫妻琴瑟和谐的生活画卷:男女各司其职,和乐而有度,日子恬美静好。
《王风·君子阳阳》亦在歌咏夫妻的和洽之情:“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君子陶陶,左执翿,右招我由敖,其乐只且!”[3]朱熹认为,“此诗疑亦前篇(指《王风·君子于役》)妇人所作。盖其夫既归,不以行役为劳,而安于贫贱以自乐,其家人又识其意而深叹美之。皆可谓贤矣。岂非先王之泽哉”[4]43。其中,“阳阳”“陶陶”皆和乐貌,“皇(簧)……舞师拿着的一把五采羽毛,跳舞时自己盖在头上,藉以装扮鸟形。房,《房中》,骜,《骜夏》,皆舞曲名”[14]469。夫妻且舞且乐,欢洽之情自在其中。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在河洛先民的意识里,真挚而专一的爱情是婚姻的起点,婚嫁以时是爱情的归宿,而婚后和洽的夫妻之情更深为河洛先民所崇尚,反映出河洛先民以婚姻为指向的情感观。
二、情感热烈浪漫,折射民风民俗
在《诗经·国风》所见河洛地域的婚恋诗中,除了表现上述“挚而有别”的婚恋之情外,热烈浪漫的男女之情,亦大量存诸诗篇当中,这些诗篇均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河洛地域的民风民俗。试看《郑风·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2]
《韩诗》认为,此诗所反映的为郑国特有的风俗,“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两水(溱水、洧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15]371。“方涣涣兮”,《韩诗》释云:“谓三月桃花水下之时至盛也。”[15]371此后,历代学人多承韩说,如当代学人余冠英先生即认为此诗“写三月上巳之辰,郑国溱洧两河,春水涣涣,男女在岸边欢乐聚会的盛况”[10]55。
对于诗中的“观”字,闻一多先生释云:“读为灌,与濣音义同。《素问·脉要精微论》注:‘灌谓灌洗也。’《西京杂记》上:‘(高祖与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边灌濯,食蓬饵以祓妖邪。’《续汉书·礼仪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灾为大絜。’与此诗可互相发明。”[6]218在此,闻一多先生将祓褉的习俗与上巳节联系起来。推究祓褉的习俗与殷商部族有关。汉代《史记》及《列女传》等文献中,皆有载殷人先妣简狄“行浴”的事迹: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逖取吞之,因孕生契。[16]
契母简狄者,有娀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17]
孙作云先生指出:“这‘行浴’,我以为即祓褉(洗涤)……古人相信:简狄生子由于行浴、吞卵,而简狄又为高禖,可见古人祓褉(行浴)求子之俗与祭祀高禖有关,事实上即于祭祀高禖时行之。”[18]291此处所谓的“高禖”,“是管理人间生育的女神。‘高’言其大、其重要,‘禖’即‘媒’字,实亦即‘母’字(古从‘母’之字多从‘某’);高禖神就是管理结婚与生子的女神,亦即‘大母之神’”[18]288。《礼记·月令》有祭祀高禖的记载:“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郑玄注曰:“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变‘媒’言‘禖’,神之也。”“天子所御,谓今有娠者”,“带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12]1361。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简狄被殷人奉为高禖,与其祓褉时吞玄鸟卵而生契有关,《诗经·商颂·玄鸟》所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是对这一事件的印证。因此,殷人后嗣祭祀高禖(简狄)时,最强烈的意愿就是祈求生子,并且希望生男孩。正如孙作云先生所指出的:“祭祀高禖的节日或行事,在后代演变为三月上巳节的祓褉求子之事。首先说,我认为‘上巳’的‘巳’字即‘子’字,‘上巳’即‘尚子’(‘上’、‘尚’古通用);正名定义,上巳的最初意义就是为了求子。”[19]
“士与女,方秉蕑兮”,《毛传》曰:“‘蕑’,兰也。”[2]732在郑地,兰有着特殊的意蕴。《左传·宣公三年》载:“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20]郑文公妾燕姞因梦兰而得以侍寝生子,郑文公宠幸燕姞时亦赠之以兰。可见,在郑人的观念里,兰不仅为生子之征,亦喻示着行夫妻之事。因此,闻一多先生指出:“《笺》曰:‘男女……感春气并出,托采芳香之草而为淫逸之行。’此说虽不尽是,而以秉蕑与淫逸之行有关,则得其实。”[6]217
“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玄《笺》云:“伊,因也。士与女往观,因相与戏谑,行夫妇之事。其别,则送女以芍药,结恩情也。”[2]732
明白诗歌所依托的文化背景后,我们再回到诗歌本身。《溱洧》所呈现的是上巳节男女于溱、洧河边戏耍的热闹场景,青年男女的“秉蕑”、女子大胆的相约、男女祓褉、戏谑,直至男赠女以芍药,以结恩情。整个过程皆渗透着郑地浓郁的民风民俗。上巳节祓褉,包含着拂除不祥、求偶、求子、赠物结情等多种意蕴在里面。渗透其中的原生态的男女之情,自由、热烈、浪漫,与郑地特殊的民风民俗深为契合。
即使在周礼中,对此种民俗亦给予充分的尊重。《周礼·地官·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郑玄注曰:“无夫家,谓男女之鳏寡者。”[9]1579-1580即在周礼中,媒官掌握着万民的婚姻,而仲春二月,适婚男女及鳏寡者皆可以私自结合。礼本缘情而制,周礼的这一条,必是有其现实的依据,郑地本为殷商部族旧地,原殷商之地所遗存的自由恋爱的习俗当为其考量的重要因素。正是在此种礼、俗的背景之下,一幕幕热烈、浪漫的爱情故事得以轰轰烈烈地上演。先看《郑风·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2]
关于此诗的背景,郑玄《笺》云:“蔓草而有露,谓仲春之时,草始生,霜为露也。《周礼》: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2]732“邂逅相遇”的“遇”,闻一多先生释为“配合”之义,并征引大量文献来印证:“读为偶。遇偶古通。《史记·佞幸传》‘善仕不如遇合’,《集解》引徐广曰:‘遇一作偶。’是其比。偶有配合之义。《易·姤彖》‘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与《泰彖》‘天地交而万物通’,《咸彖》‘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归妹》‘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语意同,遇亦读为偶。《吕氏春秋·音初篇》:‘禹行水(今作功,从毕沅校改)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案既曰见,又曰未之遇,则育非逢遇之遇,明甚。遇当读为偶,亦配合之谓也。”[6]216诗人以深情的笔触歌咏与情人不期而会的经过,情感深挚动人。
《郑风·褰裳》刻画直爽的郑地女子对情郎的戏谑:“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2]闻一多先生《风诗类钞甲》云:“见爱曰惠。溱洧皆郑国的水名。未娶的男子曰士。”[5]459诗中女子泼辣而又多情的形象跃然纸上。相似的情感还见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2]诗中女子因心上人不与其讲话、共进餐而寝食难安,戏骂对方为狡猾的小坏蛋,于戏谑中见出其绵邈深情。
《王风·丘中有麻》表现出妇人对与其所私者的盼望之情:“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2]朱熹《诗集传》阐述其诗旨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不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4]47闻一多先生释“施”云:“行雨为隐语,意谓交合。施义亦然……然则施今本作施施者,盖小儒恶其言直而伤雅,遂私改之耳。”[6]190男女合欢以后,男子赠女子以佩玉,表现出的是赠物结情的习俗。
《邶风·静女》所反映的则是女子向男子赠物以结情的场景: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2]
此为一首男子与心上人幽会的欢歌。静女所赠之物“彤管”“荑”,据闻一多先生考证,二者当为一物:“《传》:‘荑’,茅之始生者。’刘大白云,彤管即荑,郭璞《游仙诗》‘陵冈掇丹荑’, 丹荑即彤管也。董作宾云,管读为菅,《说文》菅茅互训,是菅即茅矣。案刘董二说并是。今谓彤管、丹荑疑即藑茅……藑茅又名香茅。考古男女相赠辄以香草,此诗之赠彤管,亦其一例。”[6]99余冠英先生亦持相似之观点:“‘荑(音题)’,初生的茅,彼女从野外采来作为赠品,和彤管同是结恩情的表记。”[10]24
《卫风·木瓜》是对男女之间互赠信物以定情的记载: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2]
闻一多先生《诗经新义》云:“《木瓜篇》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当是女之求士者,相投之以木瓜,示愿以身相许之意,士亦嘉纳其情,因报之以琼瑶以定情也……意者,古俗于夏季果熟之时,会人民于林中,士女分曹而聚,女各以果实投其所悦之士,中焉者或以佩玉相报,即相约为夫妇焉。”[21]
《诗经》所见河洛地域的婚恋诗中,除了折射出春日男女相会、赠物结情的风俗外,还反映了以舞挑情、以歌传情的习俗。《邶风·简兮》记载了一种对古代女子极具诱惑力的舞蹈——万舞: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
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2]
此中“西方美人”所跳的万舞及其功能,闻一多先生有较为细致的梳理:“万舞,似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模拟舞之总称,两种,(一)曰武舞,用干(盾牌)戚(板斧),是模拟战术的,(二)曰文舞,用羽(雉羽)籥(一种小笙),是模拟翟雉(一种与神话有关的长尾野鸡)的春情的……全套的万舞总归是以武舞开始,以文舞收场的。这里‘有力如虎,执辔如组’二句指武舞,‘左手执籥右手执翟’二句指文舞。舞者一手拿着翟雉的羽毛,以象征那种鸟形,一手拿着那名籥的三管小笙,边舞边吹着,以模拟雉的鸣声。这种舞容,对于熟习它的意义的,是颇有刺激性的……‘山有榛,隰有苓’是稳语。榛是乔木,在山上,喻男。苓是小草,在隰中,喻女……西方似指宗周。美人就是上文称为硕人的舞师。就第三章看,这诗的作者无疑也是一位女子。《左传》载楚令尹子元曾想用万舞来蛊惑新寡的夫人(庄二十八年),足见这种舞对于女性们可能发生的力量。我们从本诗第三章里听到的那热恋的呼声,完全是一二两章所叙的那场舞艺应有的效果。”[14]460-461
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已有对万舞的记载,卜辞中的“万”,皆指万舞,其用途为祭祀祈雨。《商颂·那》中的万舞,亦用于祭祀先祖。萧兵先生根据甲骨卜辞中“万”字为蝎子形状,推导出万舞是“蝎子图腾氏族的专有舞蹈”。“原始的蝎子舞(万舞)……很可能模仿蝎子交配前的跳舞以挑逗、诱致异性。”[22]《墨子·非乐篇》载:“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 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 ,天用弗式。’”[23]据此,夏代夏启时已有万舞,《墨子》在这里是将“万舞翼翼”作为夏启“淫溢康乐”的表现来叙述,可见,此处的万舞是作为其原初形态呈现的。《邶风·简兮》中的万舞已被分为武舞和文舞,舞容、舞饰较前代有了进一步的改观,较之原生态的万舞,有了礼乐化的倾向,尽管如此,对于了解万舞所包含的原始文化信息的女子来说,仍然具有巨大的诱惑性。诗中的女子为旁观者,观看壮美男子的万舞表演,由其情不自禁所发出的欢叫来看,改良后的万舞仍然具备诱惑女性与之恋爱的功能。
在上古河洛先民的生活中,对歌是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此点《诗经》中多有反映。如《郑风·子衿》中痴情女子的吟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2]闻一多先生释“嗣音”曰:“《笺》:‘嗣,续也。’音谓歌声。不嗣音犹言不以歌相答和也。古者男女以歌通情,故妻不见爱于夫曰‘不见答’。《日月序》‘伤己不见答于先君’,《硕人序》‘庄姜贤而不见答’,《竹竿序》‘适异国而不见答’,不答犹言不嗣音矣。德音之音,意亦准此。”[6]210在此,闻一多先生联系《邶风·日月》《卫风·硕人》《卫风·竹竿》来证明上古时期男女以歌传情的普遍性,不仅如此,他还将《郑风·有女同车》中的“德音”释为“值音”,即对唱:“上世之人相遇每以歌通意,男女之定情也如是,宾朋之交欢亦如是。德音之语,盖肇于此。德音即值音,犹今言对唱矣。《礼记·月记》:‘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鹿鸣》一章‘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三章‘我有嘉宾,鼓瑟鼓琴’,二章‘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明德音与歌乐有关矣。《假乐》‘威仪抑抑,德音秩秩’,威仪谓礼,德音谓乐,此礼乐对举也。”[6]204事实上,“德音”不仅有“乐”的意项,即以《郑风·有女同车》来说,朱熹即有不同的阐释:“德音不忘,言其贤也。”[4]52但是,结合上古河洛地域对歌传情的风俗来看,闻一多先生的释义确有可采纳之处。
由以上分析亦可看出,对歌作为传情达意的手段,已内化为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歌传情并不仅仅局限于未婚男女之间。《郑风·萚兮》即为夫妻间以歌传情的实例:
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2]
此为情感热烈的妻子的歌唱,邀请其夫与其和歌。《诗序》曰:“萚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2]朱熹指出:“萚,木槁而将落者也。女,指萚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词,言萚兮萚兮,则风将吹女矣。叔兮伯兮,则盖倡予、而予将和女矣。”[4]52除去朱熹的卫道士面孔,他对此诗的理解远较《诗序》更接近诗旨。闻一多《风诗类钞》云:“女称夫曰叔伯。要,会也。歌者以声相会合即和。”[24]此诗勾勒出一幅夫妻互相唱和的和乐画面,唱和之契,生动感人。
由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大量存诸《诗经》中的承载热烈浪漫的男女之情的诗篇,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河洛地域的民风民俗:其一,上巳节祓褉的风俗,包含着拂除不祥、求偶、求子、赠物结情等多种意蕴;其二,以舞挑情的习俗;其三,以歌传情的习俗。
综合以上对《诗经·国风》中出自河洛地域的婚恋诗的考察,可较为清晰地看出河洛地域婚恋诗的情感特征及其文化内涵。《诗经》中的这些篇什,为我们进一步认知河洛先民的婚恋观及民风民俗,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冯源.《诗经·国风》中婚恋诗在河洛地域的分布情况考略[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77-81.
[2](唐)孔颖达.毛诗正义[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3](宋)邢昺.论语注疏[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5360.
[4](宋)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闻一多.诗经通义甲[M]//闻一多全集(第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6]闻一多.诗经通义乙[M]//闻一多全集(第4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7](清)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71.
[8](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余冠英.诗经选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1]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183.
[12](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清)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457.
[14]闻一多.风诗类钞甲[M]//闻一多全集(第4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5](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汉)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82:91.
[17](汉)刘向.列女传[M].张涛,译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9.
[18]孙作云.《诗经》恋歌发微[M]∥孙作云文集——《诗经》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19]孙作云.关于上巳节(三月三)二三事[M]∥孙作云文集——《诗经》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308.
[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673-674.
[21]闻一多.诗经新义[M]∥闻一多全集(第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74.
[22]萧兵.万舞的民俗研究——兼释《诗经》《楚辞》有关疑义[J].辽宁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5):39-40.
[23](清)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261-263.
[24]闻一多.风诗类钞乙[M]//闻一多全集(第4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509.
2015-01-07
冯源(1974-),女,河南方城人,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I207.222
A
1674-3318(2016)03-007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