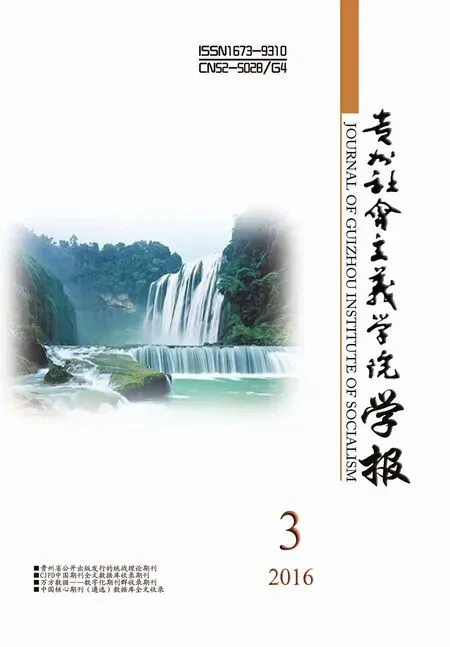中央红军在贵州的民族结盟
2016-03-15张中俞
张中俞
(黎平会议纪念馆,贵州 黎平 557300)
中央红军在贵州的民族结盟
张中俞
(黎平会议纪念馆,贵州黎平557300)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为顺利通过情况复杂的民族地区,党和红军坚持正确的民族观,以民族平等为基础,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政策,成功地争取到少数民族的支持,为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红军;长征;民族观;民族结盟
历史上,由于统治阶级实施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对汉族充满疑忌甚至敌视,造成民族隔阂。因此,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能否顺利通过情况复杂的民族地区,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严峻考验。面对这一大难题,党和红军坚持正确的民族观,以民族平等为基础,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政策,成功地争取到少数民族的支持,为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提起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民族结盟,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在今四川冕宁县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彝族果基部首领小叶丹达成的彝海结盟。“果基”又译作沽基、沽鸡,“小约丹”又译作“小叶丹”。其实,党中央和红军早在广西、贵州境内即已提出相关民族政策并践行了民族结盟,曾为长征中的红军顺利地穿州过府发挥过特殊的历史作用,只是有些史实鲜为人知罢了。
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的中央红军长征,一路上能攻城拔寨,除了中共中央不断实事求是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红军指战员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战胜难以言状的自然险阻、克服吃住行的超常困难外,还与在民族地区成功地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征,群众工作即民族工作,民族工作即群众工作,二者不可截然分开。
依笔者之见,长征中的群众工作主要有以下方式:与民方言交流,接地气易沟通;陆续出台并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力所能及做事,细节决定成败;宣传革命真理,百姓明辨是非;召集群众大会,当众惩恶行善;送礼物给群众,快速拉近距离;打土豪分浮财,标明红军所为;及时收兑苏钞,保护群众利益;严格带路规定,解除后顾之忧;和气公平交易,往往多付银钱;沿途扩充红军,壮大革命队伍;安置重伤病员,保存革命力量;切实保护民房,谣言不攻自破;强调民族自决,结成民族联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方式虽有别,但目的却相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以便能顺利完成战略转移、宣传革命真理、最终北上抗日。本文试谈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民族结盟,旨在抛砖引玉。
随着中央红军不断向西转移,长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1934年1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在湖南蓝山县发布了长征以后首个民族政策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在最初的时期即使个别的亦是宝贵的,政治部对于这些分子在生活上、政治上、教育上都应加以特别的注意。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并特别注意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1934年11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广西全县(1959年改称全州县)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内容涉及到提倡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并与其订立政治、军事联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国民政府和军阀的种族歧视政策,在少数民族中宣传共产主义等诸多方面。其中,《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瑶民(或称瑶子)、苗民(或称苗子)等是散布在广西、贵州、湖南西部、云南等省的弱小民族,总的人口不下千万。他们历来受着汉族军阀官僚地主商人财富老的残酷的民族压迫与剥削,这促成了他们对于汉族的民族的仇恨,与他们内部的团结。”“我们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与瑶民的彻底的民族自决权(通俗些说,即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去决定,汉人不得干涉,并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在这一基本主张之下,争取瑶民弱小民族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拥护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协同动作。这一基本主张,各级政治部必须照各地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化通俗化。”“我们苏维埃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同他订立各种政治的、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1]1934年12月6日,红三军团某部长征来到广西龙胜时,发现在龙舌岩(位于今泗水乡瑶寨)下躲着五个参加桂东北瑶民起义(1932年、1933年爆发,遭到国民党镇压)的小头领。首长知情后,立即派人前往龙舌岩看望和慰问,并与他们座谈,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他们不要惧怕敌人,继续坚持斗争。红军还送给他们一些武器,并在岩壁上题写了“红军绝对保护傜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等标语。
1934年12月12日,红一军团转战至贵州黎平县牙屯堡(1951年划归湖南通道),开始进入黔东地区。据《红军在黔东南》载:朱德在黎平洪州分县牙屯堡的一块油茶树山地里,向中央警卫团(即政治保卫团)的指战员作报告。他谆谆告诫大家,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后,我们既要遵守群众纪律,又要执行民族政策。历代统治者称贵州为蛮夷之地,居民多数是少数民族,他们受苦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少数民族的礼俗不尽相同,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在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2]尤其在团结少数民族头人(上层人士)的过程中,采取灵活策略和联合方式,不打少数民族土豪,以尽可能减少长征阻力和争取民族群众的支持。1934年12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在黔东剑河县发布《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切实保护民族利益:“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更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1935年1月,在黔北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指出:“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于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汉族的地主财富老的压迫。”1935年4月10日,《红星》报刊文《注意争取夷民的工作》指出:“不打夷族的土豪,对于夷民群众所痛恨的夷族土豪,也要发动夷民群众自动手的来打。”5月21日,《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关于加紧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指出:“绝对不打蛮夷民的土豪。”
早在1934年7月,红三军即在黔东颁布了《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提出要:“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承认他们有同中国脱离,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国家的权利,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和脱离苏维埃联邦;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住居在苏区的苗家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维埃公民的一切权利。”[3]进入贵州后,据红九军团司令部参谋处文书林伟写的《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得知,红九军团司令部参谋长郭天民曾给琴松(今贵州黔东南剑河县岑松镇所在地)一刘姓土豪修书一封,清楚表明红军只是为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反抗日本侵略而取道北上:“十二月二十一日,阴天。今天我军团在这个贵州苗族人民众多的剑河县城休息一日。军团政治部进行扩兵工作,经过宣传,就有苗家青年160人参加了红军,编成了一个新兵连。……十二月二十二日,晴。清晨就出发,整天沿山区小路前行,这一带都是苗族区域,爬山走小路,天气寒冷。一路上战士们惊异地望着那些拥挤在道旁的苗家干人,他们穿的褴褛不堪,房屋也是凋零破旧,竹片和草篷的。下午四时我军进抵琴松镇宿营。这里是一个苗族大市镇,约有五百户人家,这里有一个苗民秀才姓刘的,为这一带最大的土豪劣绅,又是民团团总,很反动,有团丁上千人,枪有三百多枝,据说还有机关枪二挺,闻我军到剑河时,昨晚即亲自率领民团上山扼守南门寨(这是苗家抵御军阀官兵入境的城堡),地势险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过,号称‘一人守关万夫莫敌’。我们进入镇内宿营后很快就调查了这一情况,同时我们到镇远去唯有走此道路不可,首长考虑到为顺利使我军按指定时间内占领镇远,不为途中这些反动地方武装骚扰所耽搁,花去了四十圆银币请了一个汉民送信给那个刘秀才,藉以劝说和平过境。郭参谋长起了一个草稿,要我用毛笔书写在八行一篇的信笺上面,信中说:
刘老先生勋鉴:
迳启者:弟于今日率部由剑河出发,于下午四时进抵琴松。久闻先生为台拱苗族人民领袖,待人温和,斯民景仰。汉苗民族,同我中华素来和睦。敝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军队,为拯救祖国,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此次北上,取道贵境,本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推翻欺压我瑶、苗、夷、侗四个少数民族之国民党反动派,本一贯之主张,肃清我国民族败类,拯救我苗夷同胞。闻先生惶恐,未悉我军政策,乃误会率众兵丁扼守南门寨,以图阻止敝军前进,弟日前曾有尺素,闻仍未悉,今将再修书前来,谅先生洞察实情,盼望今晚来弟处一晤,共谋大事,并望为弟觅得熟悉向导,帮助带路,今后夺取大城市,没收卖国贼的金银财宝,定予重赏,切不食言,专函怖悃,不禁依依,把笔搁置,无任神望,顺致安康。红军第四军军长黄魁政委陈蒙。古历十一月十六日晚十九时于琴松军部。”[4]
虽然红九军团(信中的部队和首长均用代名)最终未与刘先生结盟,但这封信肯定起到了一定的宣传和相当的震慑作用。据林伟《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载:“通过南门寨时未发生任何情况,一路无事。我们经过南门寨时巡察了这里的地势,确实险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折叠式坡形上山,如有守兵确实很难攻取。但不知道这个苗族秀才、猾奸的老家伙,不知为何弃守撤逃,也未回信。中午时分我军已顺利经过了这个著名的险地,于下午五时安抵金铺镇。晚上就在这个镇上宿营。”金铺镇即今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金堡乡所在地。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后,主力西进云南。现据《杨尚昆年谱 1907—1998·上》[5]《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6]《红军长征追踪·上》[7]《瀑乡镇宁的红色往事》[8]等书记载,将红三军团首长与镇宁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签订协定这一长征佳话简述于后。1935年4月中旬,中央红军右路军红三军团转战来到地处要冲、多民族聚居的镇宁。当地群众长期以来饱受滇黔军阀蹂躏以及官府残酷压榨,曾多次自发进行抗兵、抗粮、抗捐斗争,形成了陆瑞光、王仲芳(陆瑞光妹夫)等几支武装。其中,1901年生于关岭县六马弄染(今属镇宁)的陆瑞光,到20世纪20年代初拥有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控制六马一带,成为劫富济贫、保卫家乡的农民领袖。若处理不好民族关系,强行通过此地,有可能会发生武装冲突。红三军团首长亲自拜访陆瑞光,耐心细致地交谈。陆瑞光深受启发,认识到受压迫的民众只有团结起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能推翻反动统治,于1935年4月16日与军团首长签订了《反对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才苛捐杂税的协定》。红军赠给陆瑞光一面红旗、36支步枪及一些弹药,留下十多名指战员和伤病员,以开展武装斗争。当天17时30分,彭德怀、杨尚昆给军委发去一封汇报式的电报:“沙子周(沟)百数十里,有夷兵约千,有师团营组织,一首领名陆瑞光,我们已与其订立作战协定:反蒋、王、犹国民党及苛捐杂税。留有一批伤病员,赠步枪三十六支,并留一批工作人员。”红军离开弄染时,陆瑞光带了二十多人一直送出很远,才珍重道别。临别时,红军首长又赠给陆瑞光一架望远镜、三挺机枪和一些手榴弹。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势力卷土重来。1937年,陆被捕并被杀害于贵阳。1989年,民政部批准陆瑞光为革命烈士。1997年,杨尚昆为镇宁题写了“陆瑞光纪念馆”六个大字。
红军通过弄染后,奉令先行的红11团来到六马板乐时,碰到了头人“王司令”派人武力把守隘口。显然,红军要避免损失和赢得时间,必须得借道,开展统战工作。因为他们要限时赶到北盘江白层渡口以控制渡河点,舍此别无捷径。“王司令”即王仲芳,害怕有人劫掠他的地盘,派了一个连守关把口,见有人马进入即开枪。红军获悉此情,就通过关系找到了何炳仁当向导。何是王仲芳堂侄女的丈夫,长年从事贩运,见多识广,对红军有好感。当山上有人向红军开枪时,何就喊话道:我是何炳仁,兄弟们,这是红军,是好人,他们不打我们,你们也莫打啰!不一会儿,山上枪声停止,部队继续前进。红11团政治处主任王平和特派员吴信泉来到王仲芳住地,与王进行交涉谈判,希望他和陆瑞光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王仲芳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同意借道,并作了一些安排;红军给了他10多条汉阳造步枪和一些子弹。据《王平回忆录》载:“我向王司令宣传红军的政策,说明我们只是借路到北盘江渡口,保证不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司令犹豫了一会,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他派他的副官给我们作向导,负责和沿途的各布依族关卡交涉,并交待对红军后续部队也不要阻拦。王司令还慰劳红军许多白米、猪肉。部队安全通过该地区后,我们再三感谢王司令对红军的友好态度。”
此后,红军较为顺利地来到北盘江边。4月17日至18日,中央红军分别从贞丰县坝草、白层、者坪3个渡口架设浮桥渡过北盘江;随后,占领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县县城。4月23日,以红一军团为左翼,军委纵队居中,红三军团为右翼,红五军团殿后,迅速向云南省曲靖县境的黄泥河及其以西地域前进。24日,中央红军先后从兴义县威舍离开今贵州黔西南州境,进入云南省平彝县(1954年改称富源县),向沾益、白水、曲靖一线集结。
综上所述,在长征的民族结盟中,尽管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彝海结盟,但弄染结盟的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它比彝海结盟要早一个多月;陆瑞光与小叶丹一样,都是为红军北上抗日让道,使红军赢得时间顺利通过连敌人都估计有难度的民族地区,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为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奠定了基础;两人都开展了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医治保护过红军伤病员,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它记载了红军和少数民族的鱼水情深,见证了党和红军民族政策的成功运用;在民族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火种,点燃了各少数民族革命的星星之火,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红军是各民族自己的军队”,起到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它也是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是贵州各族人民特别是镇宁布依族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贡献,增进了民族感情,消除了民族隔阂,给艰难的万里长征增添了极其重要的一笔。
显而易见,长征中红军的民族结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民族政策的光辉典范,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新中国建立后制定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
[1]总政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二)[M].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52页.
[2]中共黔东南州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军在黔东南[M].1985年7月版,第110-111页.
[3]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98页.
[4]林伟著: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79-80页.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杨尚昆年谱 1907-1998·上[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 页.
[6]费侃如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58页.
[7]罗开富著:红军长征追踪·上[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338-339页.
[8]政协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编:瀑乡镇宁的红色往事[M].2013年版.
责任编辑:方飒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e and the Chinese Red Army faced unprecedented difficulties in minority areas in the Long March,to go through the complicated ethnic minority areas smoothly,the Party and the Red Army adhered to the correct concept of nation based on equality,took targeted measures,successful won the support of minorities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entral Red Army;the Long March;national view;national alliance
2016-05-05
张中俞,男,民建黔东南州黎平支部会员,贵州省黎平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D633.0
A
1673-9310(2016)03-0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