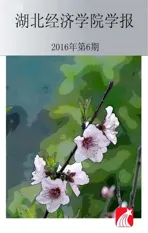《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东方宗教文化思想的踪迹
2016-03-15郜进
郜进
(蚌埠医学院 公共课程部,安徽 蚌埠 233030)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东方宗教文化思想的踪迹
郜进
(蚌埠医学院 公共课程部,安徽 蚌埠 233030)
《麦田里的守望者》讲述了16岁的霍尔顿被学校开除后浪迹纽约,历经磨难,最后走向顿悟的一段心路历程。主人公身上隐含的佛教禅宗思想倾向,体现了塞林格希望通过东方宗教文化拯救战后青年精神危机的人文关怀。
生老病死;自我修行;痛苦与磨难;顿悟
二战后,西方社会消极颓废的主流文化使许多年轻人完全被束缚。他们面临认同危机的困惑,推崇自我张扬的个性,肆无忌惮地抨击一切,美国社会充满压抑和精神危机。这也引发了塞林格的焦虑和思考,他对给予西方人精神寄托的基督文化予以质疑。霍尔顿明确表示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嘲弄人们对耶稣的膜拜,厌烦十二门徒,质疑牧师步道时慷慨激昂的架势,指责基督精神早已被商业化的演出所亵渎。那个时期,佛教对美国文化的影响也在逐渐深入,清净顿悟等观念使备受精神折磨的西方人得到了宁静与解脱。塞林格试图通过汲取东方宗教的文化价值,把人们从精神危机中解救出来。卢斯和霍尔顿的对话,反映了塞林格对东方宗教文化的关注与憧憬:“我只是刚好发现东方哲学比西方哲学更让人满意”。①(P147)
一、生老病死
据《大善权经》记载,释迦牟尼时常感叹生命无常,表白:“但畏生老病死,为除断故,来至此耳!”他出家修道,试图解脱人类生老病死的痛苦。和释迦牟尼一样,霍尔顿也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对现实世界中生命和死亡的思索既有忧虑又有恐惧。在他的眼里,斯潘塞老师象征着老和病。“穿了件破旧不堪的浴袍,大概他生下来穿的就是这件吧。我不是很想看老头儿穿睡衣加浴袍的样子,老是露出坑坑洼洼的胸膛。还有腿,在沙滩上还有别的地方见到,老头儿的腿上总是白白的不长汗毛”。①(P9)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部小说,墓地不断出现。艾里是完美儿童的化身,失去艾里让霍尔顿体验到刻骨铭心的疼痛,对艾里精神上的依恋即便在他成年后也存在。心情沮丧的时候,霍尔顿就装作和弟弟艾里大声说话,相信死去的弟弟能够拯救他被现实社会压抑的灵魂。在霍尔顿的心里,艾里的纯洁和淳朴似乎在死亡中得到了永久保留。当他一个人呆在博物馆看木乃伊时,“我还有点喜欢那样呢。那儿很不错,很安静”。①(P204)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霍尔顿对死亡的思索变得更严肃,甚至直接面对。他不断地产生被子弹击中肚子的幻象,浑身流着血,他甚至想到自己有可能患肺炎或癌症死去。在斯潘塞老师的考卷中,霍尔顿更关心可以让死人脸部经过无数个世纪不腐烂的药物配方。惧怕美好与善良事物的毁灭,留恋成为历史的东西,这恐怕就是塞林格的禅悟。他认为“那座博物馆最好的一点是里面无论什么,都会保持原样不变,什么都不会改变地方”。①(P122)霍尔顿最后想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中找到精神家园,获得灵魂的新生。他对生老病死的畏惧和思索也由远及近,由浅入深。
二、自我修行、淡泊名利和禁欲主义
觉海慈航中曾这样描述:“念佛的人不贪求、不吝啬、深信因果,戒杀素食、生活节俭、亲近自然、少欲知足、心怀慈悲、利乐有情等等”。[1]自我修行、淡泊名利和禁欲主义的东方宗教文化刚好迎合了二战后美国民众的普遍心态,使他们从世俗世界的喧嚣中解脱出来。塞林格受东方宗教文化的影响,深居简出,逃避世俗生活。他主张禅定,从各种思想的束缚中解放自我,实现自我解脱。霍尔顿想到风景很好、阳光明媚的西部某个地方找个活干,装作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他幻想和一个又聋又哑的美丽女孩儿结婚,一起住在木屋里,表达了他追求禅宗的孤独、自然和宁静的愿望。霍尔顿不喜欢斯特拉德莱塔,甚至为维护简的完美性和他打架。但是在小说结尾他却宽容地说“我有点儿想念我所提到过的每一个人,例如甚至斯特拉雷德和阿克利这两个家伙”。①(P213)这种宽容也契合了佛教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的思想。梅洛庞蒂断言:“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曾几何时,身体被打上了恶的印记,而恢复其合法地位乃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一次伟大胜利”。[2]塞林格看到了这种超越的局限,批判纵欲主义。霍尔顿对性爱是好奇、惧怕和想入非非,渴望与漂亮姑娘约会。后现代社会的压抑和绝望使他把性爱当成自我拯救的一种途径,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他一时冲动,违背自己的原则,召来妓女桑妮。他说:“我那时心里的沮丧感远远超过性冲动”,①(P95)反映了霍尔顿对人性中童真的守护,颠覆了西方以欲为本的生命超越。卢斯说:“东方哲学比较好,他们只是刚好把性看做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体验”。①(P147)塞林格思想隐逸纯真,渴望通过以情为本的生命超越来达到拯救的途径,但是他的这种救赎方式在西方文化视角下遭遇到了压抑和绝望。
三、痛苦与磨难
佛教认为,一切都是变迁不息的,变化无常的,广宇悠宙,不外苦集之场。人生充满着苦,人的生命和生存就是苦![3]霍尔顿经历的痛苦与磨难更多是精神层面上的,其实质就是寻求自我的过程。他的父亲一心只顾赚钱,在小说中没有露过面;母亲在弟弟艾里死后有些神经质;哥哥创作低级趣味的作品迎合市场,与他关系疏远。亲子关系的缺失使霍尔顿的孤独感无法得到排解。霍尔顿所在的名校潘西中学有的也不过是势利小人瑟默校长,里面全是些装模作样的家伙,整天聊天除了谈女孩儿、烈酒和性就没别的。①(P132)霍尔顿无法融入其中,找不到归属感。他对潘西那儿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喜欢,平日里他身着奇装异服,满口脏话,玩世不恭,时常发出“我感到很孤独”的感叹。霍尔顿被开除后不敢也不愿意回家。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逃避,走向社会去找寻归属感。他在纽约游荡,出入酒吧和夜总会,喝酒召妓,想以此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和孤寂。他被人殴打敲诈,亲眼看到穿戴女装的男人,寻欢作乐的男女等令人作呕的行为。成人世界的一切让他简直恨透了,最后决定逃离这个人间地狱。询问中央公园湖里的鸭子去何处过冬,隐喻了霍尔顿在社会中无处生存的困境。“可我真正想干的是自杀,我觉得我想从窗口跳下去”。①(P105)他被精神流浪的种种磨难折磨得自我迷失快要崩溃,揭示了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对人性自由的压制,也注定了理想追求在现实中只是虚妄。“我是说在还没做一件事情之前,又怎么会知道将来怎样做呢?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我觉得我会。可是我又怎么能知道?我敢说,这话问得蠢”。①(P213)这颇有点禅宗隐喻的味道,表达了他对现实世界产生幻灭感和失落感的绝望,暗示着生活的不可捉摸。
四、顿悟
佛教禅学认为顿悟是“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4]以直觉把握心性的顿悟,只要心领神会,即刻就能成就佛道。霍尔顿天真纯洁,处在青春期向成人期过渡的成长拐点,按照自己的天性行事。“我要定下一条规矩,就是不管谁来看我,都不许做虚伪的事,谁要做就别待”。①(P205)。潘西里面全是些虚伪自私的家伙,那里的一切都让他简直恨透了。在纽约游荡了一夜,成人世界的堕落让霍尔顿厌恶至极,现实社会中的假恶丑和他内心的真善美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历经一番精神磨难之后,霍尔顿对自我的认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为他最后的顿悟做了坚实的铺垫。霍尔顿看着妹妹菲比坐在旋转木马上,这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使他顿悟了,他不再像以前选择逃避,终于明白“对小孩儿就该那样,他们要是想抓金环,就只能让他们抓好了,别说什么。他们摔下来就摔吧,可你要是对他们说什么就不好了”。①(P210)霎那间他拨开迷雾,领悟到禅宗顿悟所要求的顺其自然与平静,看到消除与世俗对立痛苦的可能。尽管他最后被当作精神病送进医院,但是通过禅学的“悟”消除了内心世界的痛苦和精神世界的漂泊无依,实现了自我救赎。儿童世界成了他那躁动不安生活中的避风港,精神获得了回归。霍尔顿也想向佛祖那样普度众生,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维护孩子们心灵的纯洁,避免受到成人社会的污染。这和禅宗教义对人性的光明意识是契合。
五、禅宗文化色彩的象征
佛教禅学中有大量的“心印”故事,心印的影响是超逻辑的和非理性的,不以信徒的意志为转移。霍尔顿在纽约游荡了一夜,还莫明其妙地询问司机,“你知不知道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里的鸭子?就是那个小湖?也许你知道那些鸭子在湖水结冰后去哪儿了”?①(P61)鸭子前后出现过几次,每一次出现,人物的心理都变得比上一次更加急迫和抑郁,然后突然转折,进入清澈透明的境界。像鸭子那样“原来在哪儿还在哪儿”,喻示着他对保持自然纯真天性的眷恋,同时又向往能生存于虚伪的世俗世界,透露出作家的禅悟。作品中还出现过“炸饼圈”的影射:“我进了一家看样子档次很低的餐馆,要了份炸饼圈和咖啡,只是没吃炸饼圈,因为我几乎无法下咽。问题是你为什么事特别沮丧的时候,就真他妈无法下咽”。①(P197)“无法下咽”象征着他处于两难之境地,想要咽下炸饼圈意味着想解决所有的矛盾与冲突。霍尔顿崇尚个性的自由,想停留在无忧无虑的儿童阶段。儿童成为救世主的象征,他们像佛一样引领着迷途中的人们,解决他们的精神危机。旋转木马的场景也是个影射。霍尔顿看着妹妹菲比坐在旋转木马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使霍尔顿淋得像只落汤鸡。“我突然感到太他妈的开心了。说实话,我他妈几乎要大喊大叫,感到太他妈的开心了”。①(P212)这种突如其来的狂喜类似禅宗的一种生命体验,而霍尔顿的“我他妈几乎要大喊大叫”则是禅宗开悟的前奏。悬崖一侧的麦田带有明显的宗教文化色彩,是霍尔顿内心更真诚更容易沟通的精神家园,这和佛教环境优美、世外桃源似的极乐世界相似。霍尔顿想逃避“虚伪的成人世界”,逃往西部遁入自然,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普渡众生”。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身上明显隐含塞林格佛教禅宗思想的踪迹。主人公霍尔顿身上强烈的幻灭感和失落感的绝望表现了塞林格对颓废主流文化的思考和焦虑。崇尚自我修行和淡泊名利,肯定自然纯真的天性,向往与世无争的生活,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塞林格对东方宗教文化价值的认同。他试图借助东方宗教哲学的理念,寻求精神价值,为战后青年精神危机找到消解对立的出路。
注 释:
① 文中所引原文采用的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
[1]何保林,论佛教思想对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补充与深化[J].湖北社会科学,2010,(10):114.
[2]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7.
[3]姚萍,佛教思想对心理治疗观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5):735.
[4]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M].中国出版社,1992.137-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