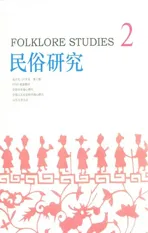“复礼”抑或“从俗”:论宋代家礼中的婚礼
2016-03-15杨逸
杨 逸
“复礼”抑或“从俗”:论宋代家礼中的婚礼
杨逸
摘要:“礼”与“俗”是宋代家礼的基本范畴。早期道学家多由“以礼论俗”出发,进而要求“因礼废俗”,通过礼学考证与道学思辨,批判与抵制各种鄙俚婚俗。同时,宋儒也“以俗合礼”,将自以为合乎经义、不害义理的婚俗纳入礼文,进行“合礼化”。在这方面,程颐、司马光导夫先路,吕祖谦集其大成。然而,这种做法却遭到朱熹的反对,其著《家礼》以经义为本,“以礼化俗”,赋予古礼以新生。由“复古”到“从俗”而归于“复古”,宋儒的家礼立制完成了一个类似“正反合”的圆圈,为考察宋代家礼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关键词:古礼;民俗;宋代;家礼;婚礼
经历了“礼崩乐坏”的五代乱世,宋代士大夫十分重视儒家礼仪的重建,希望以此接续孔孟道统,恢复三代之治。然而,当时社会去古已远,民间礼俗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冠昏丧祭”之礼或是缺而不讲,或是与古迥异,或是杂于佛老,或是溺于流俗。就婚礼而言,其重构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当时形形色色的民间婚俗。对此,司马光(1019-1086)、程颐(1033-1107)、吕祖谦(1137-1181)、朱熹(1130-1200)等宋代家礼撰述者的态度不尽相同,由此导致了其所制婚礼仪文的具体差异。唯有加深对宋儒礼俗观的理解,才能更好地分析诸家礼书中的婚礼仪文,进而对宋代家礼有更为全面的认知。
关于宋代婚礼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民俗研究的路径,即将宋代婚礼中的“礼”与“俗”作混一考察,运用正史、笔记等材料为宋代士庶婚礼提供一幅“全景画”。①如方建新:《宋代婚姻礼俗考述》,《文史》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徐吉军等:《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37-399页;曲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民俗研究》2002年第2期;[美]伊佩霞:《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86页,等等。该方法的局限在于未能反映“礼”与“俗”之间的区别与互动,以及宋儒制定婚礼仪文时的复杂态度。另一种是礼学研究的路径,通过家礼文献梳理与文本释读,建构两宋间家礼不断“从俗”的历史叙事。②如杨志刚:《〈司马氏书仪〉和〈朱子家礼〉研究》,《浙江学刊》1993年第1期;安国楼、王志立:《司马光〈书仪〉与〈朱子家礼〉之比较》,《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王美华:《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等等。这种观点虽然为宋代家礼提供了过程性、体系化的诠释,但却对宋代家礼著作的多样性与仪文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具体仪文的比较与考订亦不免疏误。有鉴于此,本文以礼俗关系为切入点,采用司马光《书仪》、程颐《礼》、吕祖谦《家范》、朱熹《家礼》等文献资料,对诸家婚礼仪文进行细读与比较,进而为反思宋代家礼的演变过程提供一种新范式。
一、从“以礼论俗”到“因礼废俗”
据《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文献记载,宋代士庶人的婚庆习俗异彩纷呈、热闹非凡,从草帖议婚到大小定聘,从迎娶新妇到合髻、交卺,婚礼的各个环节都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然而,不少士大夫却对此表达了忧虑,吕大防(1027-1097)上书说:“夫婚嫁,重礼也,而一出于委巷鄙俚之习。”朱光庭(1037-1094)也奏陈道:“鄙俗杂乱,不识亲迎人伦之重,则是何尝有婚礼也?”*(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33页。在宋代士大夫看来,鄙俚婚俗的流行正是婚姻六礼衰落的时代表征。因此,宋儒往往能够深刻反思婚礼的性质与意义,“以礼论俗”,对婚姻论财、仪式用乐、结发、簪花等俚俗展开批判与抵制。在此,“礼”不但是反思“俗”的标准,还是批判“俗”的利器,为审视当时婚俗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考据视角。
(一)批判财婚现象与“拜金主义”择偶观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富在宋代婚姻中的地位越发突出,从而形成了极具时代特色的“财婚”现象。据有关研究,当时士族娶妻的一般费用在50贯以上,嫁女的一般费用在100贯以上*程民生:《宋代婚丧费用考察》,《文史哲》2008年第5期。,这意味着,一次婚礼往往需要花费一个中等士族之家多年的积蓄。在巨大的经济压力碾压下,即便是以礼法自持的士人也难于免俗。于是有被富商大贾“榜下捉婿”者,有娶妻不问门楣而径直论财者,以致“男夫之家视娶妻如买鸡豚,为妇人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1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577页。,造成了种种夫妻离异、亲家反目的社会怪象。
以“铺房”为例。这种习俗本为古礼所无,但盛行于宋代。按照此习俗,女家需要在新妇过门的前一天前往男家布置新房。一般来说,床榻、荐席、椅桌之类由男家置办,床上用品、衣服被褥等则由女家置办。由两家人一起为新人置办新房本是一件十分温馨和谐的事,但却往往蜕变成一种炫富的恶俗。司马光《书仪》记载,前来“铺房”的女家人往往将所有财物——衣服、鞋袜、被褥、帷帐等等,无论是否为当时所用一律陈列在外,以便“矜夸富多”*(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页。。据说,北宋名臣范纯仁(1027-1101)娶妻时,女家“铺房”便十分奢靡,乃至以罗绮为帷幔。其父范仲淹(989-1052)得知后十分生气,说:“罗绮岂为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至吾家,当火于庭!”*(宋)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上,《吕祖谦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页。这段轶事被不断转述,屡次出现在后世的家训、家范著作中,不但寄寓了士大夫对于先贤高风亮节的追慕,更反映了士人对当时种种财婚现象的反思与批判。
与“财婚”现象密切关联的是“拜金主义”择偶观。宋儒认为,士庶人之所以屈服于这种畸形择偶观念,乃是因为未能坚持儒家传统的婚姻观,对婚姻论财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如司马光在《书仪》中分析指出:
文中子曰:“昏娶而论财,鄙俗之道也。”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页。
在此,司马光将世俗婚姻与士大夫婚姻对举,言辞激烈地称世俗婚姻为“鄙俗之道”“鬻奴卖婢之法”,表达了宋代士大夫群体对婚姻论财的深恶痛绝。不过,司马光也对此给出了理性分析。他认为,婚姻论财是在短期利益驱使下的不明智行为,并不符合家族的长远利益。这样的婚姻不但没有幸福美满的可能,还往往使亲家结为仇敌,酿成种种家庭悲剧。从女家嫁女的立场来说,如果女家的许诺没有得到兑现,男家便会埋怨、虐待新妇,乃至于以其为质求取女家更多的资装。从男家娶女的角度看,如果出于爱慕女家财富而娶之,新妇往往仗势欺人、傲视家长,不能奉养舅姑以尽孝道。*(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页。
有鉴于此,宋代士大夫普遍要求将“贤”作为娶妇嫁女的新标准,以代替隋唐盛行的门阀标准与当时世俗所行的财富标准。以娶妇而言,宋代士大夫所谓的“贤”不但包括忠贞、勤俭、顺从、守礼等传统妇德,还体现为相夫教子、严明端肃的种种正家、治家行为。*邓小南:《“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可以说,宋代士大夫对以“贤”择偶的提倡,不但是对财婚现象与“拜金主义”择偶观的批判与回应,更是其重构家庭伦理关系的前提,寄寓了儒者“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
(二)否定婚庆仪式用乐
按古礼,婚礼不用乐。对此,《礼记》中有两种不同解读。《礼记·郊特牲》说:“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将婚礼不用乐解释为对阴阳冲突的回避。《礼记·曾子问》则道:“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把婚礼不用乐的理由归结为对接替父母主持家政的严肃态度。对于这两种不同说法,宋儒普遍批评幽阴之说的附会牵强,认同《曾子问》对于婚礼义理的阐发。程颐就曾有这样的评价:“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此说非是,昏礼岂幽阴?但古人重此大礼,严肃其事,不用乐也。”*(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44页。
然而,这一蕴涵严肃大义的古礼仪文并未得到一贯遵行。随着社会的动荡及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的深入,南北朝时民间已出现“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第615页。的现象,并影响波及皇帝纳后之礼,以致“婚礼用乐”成为皇帝大婚时群臣讨论的焦点问题*关于纳后仪中是否用乐的争论,初见于东晋升平元年(357)八月。见(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1673页。。对此,儒家士大夫多能以古礼为依据,抵制种种举乐从俗之论;史官也往往运用春秋笔法,在历史书写中委婉表达自己的态度。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纳后仪式中举乐的最早案例——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大婚:
初议婚礼,诏中书舍人徐铉、知制诰潘佑与礼官参定。婚礼古不用乐,佑以为古今不相沿袭,固请用乐。又按《礼》,房中乐无钟鼓,佑谓铉曰:“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非房中乐而何?……议久不决,唐主命文安郡公徐游详其是非。时佑方有宠,游希旨奏用佑识,游寻病殂,铉戏谓人曰:“周、孔亦能为祟乎?”*(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212-213页。
在这场争论中,徐铉(916-991)惟古礼是依,自视为周、孔之道的捍卫者;潘佑(生卒年不详)则力主从俗,认为“古”与“今”绝非一脉相承。这一论争固然包含许多政治因素,但聚讼的重要原因仍是对“返古”与“适今”、“循礼”与“从俗”矛盾的不同理解。有趣的是,虽然潘佑取得了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但“同党”徐游之死却被戏说为从俗变礼、不遵圣贤之道的应得“报应”。无疑,这一叙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仍是儒家对古礼的坚持。
至宋代,婚礼用乐已是沿袭已久的民间习俗,“礼”与“俗”的矛盾更加凸显。例如宋哲宗(1077-1100)大婚:
元祐大昏,吕正献公当国,执议不用乐。宣仁云:“寻常人家,娶个新妇,尚点几个乐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钦圣云:“更休与他懣宰执理会,但自安排着!”遂令教坊、钧容伏宣徳门里。皇后乘翟車甫入,两部闌门,众乐具举。久之,伶官辇岀赏物,语人曰:“不可似得这个科第相公,却不教用!”《实录》具书纳后典礼,但言婚礼不贺,不及用乐一节。王彦霖《系年录》载六礼特详,亦不书此。*(宋)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18页。
执政吕公著(1018-1089)对婚礼不用乐的坚持并未得到宣仁太后、宋哲宗乃至伶人的理解,在这里,民间婚俗反而成为规约儒家古礼的标准。在宣仁太后看来,皇帝大婚应比民间婚姻更加喜庆热闹,否则难以突显皇家的无上权威与地位;宋哲宗则进一步表达了对拘泥古礼的儒家士大夫的烦恼情绪;甚至连身份卑微的伶人也敢于公开发表自己对于宰执的意见。由此可窥见宋人对用乐婚俗的普遍态度。尽管如此,《实录》《系年录》的作者却采取了“为王者讳”的春秋笔法,隐讳了元祐大婚中的用乐事实,试图将这一仪式书写为合乎婚姻六礼的典范。其中隐喻的儒家价值取向表达了如吕公著般宋代士大夫的集体声音。
为维护古礼严肃之义,矫正婚俗中的嬉闹气氛,宋儒不但力争于庙堂,还编次家礼,明文规定婚礼不可用乐。司马光《书仪》、吕祖谦《家范》都认为“今俗婚礼用乐,殊为非礼”,明文规定婚礼“不用乐”。*(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页;(南宋)吕祖谦:《家范》,《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吕大钧(1029-1080)《乡仪》将“妇或以声乐迎导”作为必须剪除的“流俗弊事”之一,认为凡是“有意于礼”者都应加以变革。*陈俊民辑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580页。张浚(1097-1164)在《遗令》中仍不忘以礼范家,告诫家人“婚礼不用乐”*(宋)刘清之:《戒子通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页。。
(三)反对婚俗中的其他“猥仪鄙事”
在宋代士大夫看来,当时不少婚庆仪式不合经义、于古无稽,是必须去除的“猥仪鄙事”*陈俊民辑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580页。。除结婚论财与仪式用乐之外,这类鄙俚婚俗尚有不少,颇能窥破宋代家礼背后的思想世界。例如,当时有所谓“合髻”的婚俗,据《东京梦华录》记载:“男左女右,留少头发,二家出疋叚钗子,木梳头须之类,谓之‘合髻’。”*(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480页。可知,“合髻”是将两位新人的少许头发梳理、绾结在一起,以象征合二为一、同舟共渡、白头偕老之意,故又称“结发”。五代时刘岳曾将合髻礼编入氏著《书仪》之中,遭到欧阳修(1007-1072)的批评:
刘岳《书仪》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不知用何经义。据岳自叙云以时之所尚者益之,则是当时流俗之所为耳。岳当五代干戈之际,礼乐废坏之时,不暇讲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时世俗所用吉凶仪式,略整齐之,固不足为后世法矣。*(宋)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34、35页。
在欧阳修看来,作为“流俗”的合髻礼根本没有经义根据,是五代乱世不得已的苟且之法,不能成为治世婚姻之礼的典范。在此之后,儒者多循着欧阳修的进路,以考证方法证明“合髻”“结发”的荒谬。程颐说:“昏礼结发无义,欲去久矣,不能言。结发为夫妇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结发事君,李广言结发事匈奴,只言初上头也,岂谓合髻子?”*(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页。司马光说:“古诗云‘结发为夫妇’,言自稚齿始结发以来即为夫妇,犹李广云‘广结发与匈奴战’也。今世俗有结发之仪,此尤可笑。”*(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页。这些考证都以《汉书·李广传》为据,澄清古诗“结发为夫妇,恩爱两不疑”中“结发”的涵义,从而揭示古时婚礼并无“结发”之礼的真相。凭借这种审慎的学术批判,宋儒划清了“礼”与“俗”的边界,申明了去取婚俗的礼义标准。
宋儒所谓的古礼经义,本质上是强调婚礼有“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18页。的重大意义,以及代替父母参与、主持家庭事务的严肃心情。因此,宋代士大夫往往表现出对婚俗中过分娱乐化倾向的警惕,批判其有失古礼郑重严肃的大义。当时,随着男子簪花习俗的普及,婚俗中开始出现新郎戴花胜、上高坐的仪式。*谭艳玲:《宋诗中男子簪花现象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众客就筵,三杯之后,婿具公裳,花胜簇面。于中堂昇一榻,上置椅子,谓之‘高坐’。先媒氏请,次姨氏或姈氏请,各斟一杯饮之,次丈母请,方下坐。”*(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480页。尽管上高坐的仪式在南宋时已经不再流行,但是戴花胜却是贯穿两宋间新郎的基本装束。对此,司马光的态度颇显复杂:
世俗新婿盛戴花胜,拥蔽其首,殊失丈夫之容体。必不得已,且随俗戴花一两枝、胜一两枚,可也。*(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页。
宋代婚礼中新郎所戴之花竟然多到“拥蔽其首”的地步,由此可以想见其妆容之盛、场面之大。司马光认为,这种妆容有失传统男子的容止形象,与本应庄重严肃的婚礼格格不入,若实在无法免俗,也只可随俗戴一两朵。可见,即便是如此信而好古的笃实君子,在面对“礼”与“俗”关系的复杂性时也不得不顾及人情世故。相比之下,朱熹《家礼》的禁断态度就显得坚决明快得多。
二、从“以俗合礼”到“以礼化俗”
在婚姻典礼中,亲迎礼(俗称成婚)是最为隆重的仪式,集中体现了儒家“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18页。的婚礼大义。这一典礼也同样是宋代婚俗的“重头戏”,承载了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在此,“礼”与“俗”又一次交织在一起,矛盾十分突出。这意味着,如果坚持追求家礼的实践与传播,宋儒便不得不对繁琐的古礼仪文做必要调整,即所谓“参古今之道,酌礼令之中,顺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页。。从北宋司马光《书仪》、程颐《婚礼》开始,宋代家礼的撰述者不但以讲求古礼为目标,从“以礼论俗”出发进而“因礼废俗”,还有意识地“以俗合礼”,将部分不害经义的“俗”纳入“礼”的范畴。至南宋,“复礼”与“从俗”的两种倾向进一步演进并趋于彻底化,导致了吕祖谦《家范》与朱熹《家礼》在婚礼仪文上的巨大分歧。
(一)司马光、程颐的初步尝试
司马光《书仪》是现存宋代家礼中最早编修婚礼仪文的著作。该书以“六礼”为纲,以《仪礼》为据,对宋代婚礼的重构有开创之功。不过,《书仪》对于《仪礼》并非简单照搬,而是充分借鉴当时婚俗,创造性地将其纳入婚礼仪文之中。例如,当时有“拜先灵”的习俗,即在成婚当天迎回新妇后,新郎携新妇入男家影堂告拜祖先。其具体仪节为:
壻先至厅事,妇下车,揖之,遂导以入,妇从之,执事先设香酒脯醢于影堂。无脯醢,量具殽羞一两味。舅姑盛服,立于影堂之上。舅在东,姑在西,相向。赞者导壻与妇,至于阶下,北向东上。无阶,则立于影堂前。主人进,北向立,焚香,跪酹酒,俛伏兴立,祝怀辞,由主人之左进,东面,搢笏出辞,跪读之,曰:某壻名以令月吉日,迎妇某妇姓婚,事见祖祢。祝怀辞,出笏,兴,主人再拜,退复位。壻与妇拜如常仪。出,撤,阖影堂门。古无此礼,今谓之“拜先灵”,亦不可废也。*(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36页。
在《书仪》中,司马光将“拜先灵”的习俗正式“收编”,向背曲折莫不中于礼,可谓婚俗的“合礼化”。然而,这一仪式却与古礼相矛盾。按《仪礼》,成婚三个月之后要行见庙之礼,新妇将第一次拜见男家祖先,通过参与祖先祭祀,正式获得家庭身份,得到家人的认可。世俗的“拜先灵”仪式客观上也可起到三月庙见的作用,使之失去了存续必要。于是,《书仪》“以俗合礼”的创新终于滑向“因俗废礼”,司马光在《妇见舅姑》条的小注说:“若舅姑已殁,则有三月庙见之礼。古有三月庙见之礼,今已拜先灵,更不行。”*《书仪》:“若舅姑已殁,则古有三月庙见之礼,今已拜先灵,更不行。”马端临《文献通考》:“婚礼妇见舅姑条下注‘若舅姑巳殁,则有三月庙见之礼’,此《仪礼》说也。”据此补入。意为,只有在舅姑双亡之时才会行《仪礼》奠菜之礼,否则,这一迁延时日的古礼将因“拜先灵”的替代而被废止。
与司马光《书仪》相似,程颐所定《婚礼》也是以《仪礼》为宗主,折中于当时婚俗。虽然他坚持《仪礼》奠菜礼,对世俗“拜先灵”之礼未加理会,但是,程颐仍然对古礼仪文作出调整与变通。例如,在新郎至女家亲迎时增加了见庙等仪式:
主人肃宾而先,宾从之见于庙。见女氏之先祖。至于中堂,见女之尊者,遍见女之党于东序。赞者延宾出就位,赞者以女氏之子姪为之。卒食,兴辞。介以宾辞。主人请入戒女氏,奉女辞于庙,至于中堂。*(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622页。
按《仪礼》,新郎在亲迎时应至女家门外等待,待新妇行醮礼毕,再入见女家主人奠雁,迎接新妇返回家中。然而,程颐的《婚礼》仪文显然与古不同:它不但要求新郎入女家家庙拜见其先祖,还要求在中堂见其尊长,至东序遍见女家其他成员,并在主人的招待下宴饮尽欢。这一规定虽然合乎人之常情,却有违古礼经义,恰是《书仪》针砭之事:“亲迎之夕,不当见妇母及诸亲,亦不当行私礼、设酒馔,以妇未见舅姑故也。”*(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页。
可见,虽然司马光《书仪》与程颐的《婚礼》在婚礼具体仪文的设计上不尽相同,却都能够注意“礼”与“俗”的辩证关系,将自认为合乎经义、不害义理的婚俗纳入其家礼体系。尽管他们在去取折中之时未免有所不当而背离初衷,但是,两部北宋家礼著作的尝试毕竟为南宋家礼的撰述积累了资料、准备了条件。
(二)吕祖谦《家范》与朱熹《家礼》的分歧
在现存的南宋家礼著作中,吕祖谦《家范》与朱熹《家礼》是两部结构相对完整、思考较为严密的著作。两人虽同为道学大师,交游甚密,所见却常有不同。就婚礼的亲迎仪式而言,《家范》与《家礼》不但在仪式过程的设计上差异显著,还在礼俗关系问题的认识上产生了根本性分歧。这些分歧基本延续了北宋家礼的相关讨论,将宋代家礼中“以俗合礼”与“以礼化俗”的不同倾向推到极致。
吕祖谦《家范》卷二《昏礼》分为《陈设》《亲迎》《妇见尊长》三部分,集中讨论了婚礼亲迎仪式的各个环节。《陈设》一节基本取自司马光《书仪》,将亲迎前一天所需要准备的器物悉数列出。关于成婚仪式,《亲迎》《妇见尊长》两节有详尽规定,仪式过程大体为:新郎于家庙(或影堂)告迎,启程前往女家亲迎;新郎来到女家,入见主人于家庙,拜见女家祖先,见女家尊长,宴饮尽欢(此处采自程颐之《婚礼》);新妇辞于家庙,受醮礼后启程;至男家,先入拜家庙(或影堂),拜见男家祖先及舅姑(此处采自司马光《书仪》);行交卺礼,出烛脱衣;礼宾;第二天,于堂上拜见尊长。
如果我们以古礼的眼光审视这些礼文,那么,《家范》将不免有溺于流俗、不合于礼之讥。考其与古礼相异之大端有四:其一,采用程颐的《婚礼》,新郎亲迎时拜见女家祖先及家人,不合古礼男先女后之义;其二,采用司马光《书仪》,新妇至男家先“拜先灵”,从而取消了三月庙见之礼;其三,“拜先灵”之后即见舅姑,与古礼第二日见舅姑馈食之礼相龃龉;其四,自创新妇辞于家庙的仪式。可见,《家范》的一系列婚礼仪式并未遵循《仪礼·士婚礼》的仪文,而是广泛吸纳了司马光《书仪》、程颐的《婚礼》中的各种变通从俗之处,尽可能将迁延日月的繁琐典礼浓缩于一天完成,可以说是北宋家礼中“以俗合礼”倾向极端发展的结果。
与《家范》相似,《家礼》的婚礼仪文也以司马光《书仪》、程颐之《婚礼》为范本,所谓“前一截依温公,后一截依伊川”*(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1页。。然而,吊诡的是,朱熹与吕祖谦对于两书所定婚礼仪文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如果说《家范》全部吸收了其中“从俗”的部分,那么《家礼》则将这些仪文悉数剪除,一返乎《仪礼》。对此,朱熹解释说:
人著书,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痛。司马与伊川定昏礼,都是依《仪礼》,只是各改了一处,便不是古人意。司马礼云:“亲迎,奠雁,见主昏者即出。”不先见妻父母者,以妇未见舅姑也。是古礼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这不是。伊川云:“婿迎妇既至,即揖入内,次日见舅姑,三月而庙见。”是古礼。司马礼却说,妇入门即拜影堂,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妇,次日方见舅姑。盖先得于夫,方可见舅姑,到两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见祖庙。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须第二日见舅姑,第三日庙见,乃安。*(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4页。
在此,《仪礼》仍是朱熹评价礼书的不变标准,礼文可以随时损益,礼义却是不容轻易改动的“大本大原”。因此,无论司马光《书仪》中的“拜先灵”仪式,还是程颐《婚礼》中新郎遍见女家诸亲的仪文,都被认为是撰者私意的表达,违背了古礼经义,属于“非礼”的范畴。从礼义的角度看,这些新定仪文的问题并不止于变动古礼仪文,更在于其变乱古礼之“序”,从而根本上无法生成新家庭“女从于男”、孝敬舅姑的礼经大义。因此,虽然朱熹《家礼》也为了便于施行,将三月庙见之礼改为三日,却坚持纠正了司马光与程颐礼书中的两处“错误”,使用古礼的仪式次第,制定了一套本于《仪礼》而稍加损益的新时代婚礼。
可以说,由“以礼论俗”出发,折中“以礼废俗”“以俗合礼”,进而达到“以礼化俗”的境界,是朱熹《家礼》开辟出的一条具有宋代特色的礼仪复兴之路。这条进路是以北宋家礼的立制与实践作为重要参考,以同时代的家礼著作作为对话文本,深刻反思宋代礼仪复兴中礼俗关系的结果。它不但在“硕果不食”的礼仪困局中重新肯定了《仪礼》的价值,还为古礼文本意义的再生产提供了垂范。
三、宋代家礼中的“礼”与“俗”
“礼”与“俗”是宋代家礼研究的基本范畴,集中体现了宋儒在考礼、制礼、行礼过程中的思想观念,为这些礼仪实践活动提供了终极理据。面对纷繁复杂的市井俚俗,宋儒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是以何种标准来反思、评论这些民俗;其次,是采用何种态度来扬弃(保存还是剪除)它们;最后,是以何种方法损益古今,制成自在圆融的新时代礼书。从“以礼论俗”到“因礼废俗”,从“以俗合礼”到“以礼化俗”,宋代家礼在这方面的探索由“复古”到“从俗”而复归于“复古”,经历了一个类似“正反合”的思维圆圈。考察这一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有利于理清宋代家礼中的礼俗关系,并为研究家礼提供一种新范式。
“以礼论俗”,即以古礼的礼义与礼文作为标准,划定“礼”与“俗”的边界,论定种种习俗的是非得失。其特点是,以古礼之文考证世俗仪式,以古礼之义思辨流俗观念,用学术视角检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例子在宋代家礼中有很多,除前文列举的结婚论财、仪式用乐、结发簪花等婚俗批判外,尚有不少。以丧礼为例,宋儒对于世俗大作佛事的批判,往往含有对于佛教轮回之说的仔细分析,其中不乏以《礼记》所载鬼神观为依据的高深思辨*(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55页。;对于世俗因迷信风水而择时择地以致久不葬亲的批判,要点常常在于对于古礼三月而葬、葬不择地的礼学考证*(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75、76页。。通过这种方式,儒家得以重新思考、评价民众日常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为礼仪重建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因礼废俗”,即剪除不合礼文、有伤礼义的种种恶俗。这一态度是将“以礼论俗”的观念付诸实践的必然结果。既然那些习俗猥琐鄙俚,与古礼相矛盾,那么,最直接、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便是废而止之。北宋家礼的撰述者多持此种观点,并认定这是回归三代治世的必由之路。据说,张载(1020-1077)之所以从太常礼院辞官回乡,其主要原因是在冠昏丧祭之礼的讨论中,与其他“安习故常”的礼官发生争议,执意坚持施行古礼的缘故。*(宋)朱熹:《伊洛渊源录》,朱杰人编:《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95页。程颐也表达过对礼官清闲无为、一味循俗的不满,认为朝廷中“礼官之责最大”*(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77页。,必须谨慎考礼、制礼。因此,锐意复古、力行古礼的行为与“茧袍高帽”、深衣大带的装束相得益彰,成为司马光、张载、程颐等早期道学家的集体印象。当然,“复兴古礼”毕竟只是重建儒家礼仪的理想进路,一旦与复杂的现实生活遭遇,道学家的“复古”理想势必受到冲击与挑战。

“以礼化俗”,即以“复礼”为终极目标,坚持以古礼经义作为去取习俗的标准,“仿古人之礼意”制作新时代礼文,以期化成极具人文美的良善风俗。这种观念以“以礼论俗”为认识论基础,是对“因礼废俗”“以俗合礼”两种倾向进行折中的结果。在现存宋代家礼著作中,朱熹《家礼》可谓“以礼化俗”的典范之作。尽管该书大大简化了司马光《书仪》婚姻“六礼”的架构,但从具体的仪文上看,《家礼》较《书仪》更为复古,对不合经义的“俗”也更不宽容,其不可动摇的终极标准仍是古礼的礼义与礼文。如果说程颐、司马光、吕祖谦的家礼著作更多地希望“以俗合礼”,将不害义理的婚俗纳入家礼体系的话,那么朱熹《家礼》则展现出一种不同进路——通过对古礼之“理”的格致展开对于民俗的批判与吸收,重建儒家古礼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意义,最终达到外在之“礼”与内在之“理”圆融不二、坟典之“礼”与市井之“俗”安顿整齐的理想境界。“复礼”与“从俗”在《家礼》中兼而有之,看似矛盾,实则张弛有度,体现了朱熹变通古礼经义以制作新礼的卓越努力。
[责任编辑王加华]
Reviving Ancient Ritual or Following Customs: A Research on Wedding Ceremony in Family Rituals in the Song Dynasty
YANG Yi
Ritual(li) and custom (su) are two fundamental categories of family rituals in the Song dynasty. Early moralists mostly commented on customs from the standard of ancient rituals and required to abolish those that were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m. Through textual examination on ancient rituals and critical thinking, they often criticized and boycotted various kinds of wedding customs. In the meantime, Confucian scholars of the Song dynasty incorporated customs into ancient rituals and ritualized those wedding customs that they considered in conformity with ancient meanings. Cheng Yi and Sima Guang were pioneers in that and Lv Zuqian epitomized the trend of ritualization. However, Zhu Xi objected that way. Instead, he compiledFamilyRitualsbased on ancient rituals and tried to change customs with ancient rituals. From reviving ancient rituals to following customs and then back to rev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ards of family rituals made by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similar to the path of a compass, which provided a new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family rituals of the time.
Key Words:ancient ritual; custom; Song Dynasty; family rituals; wedding ceremony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家礼研究”(项目编号:15BZS05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逸,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 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