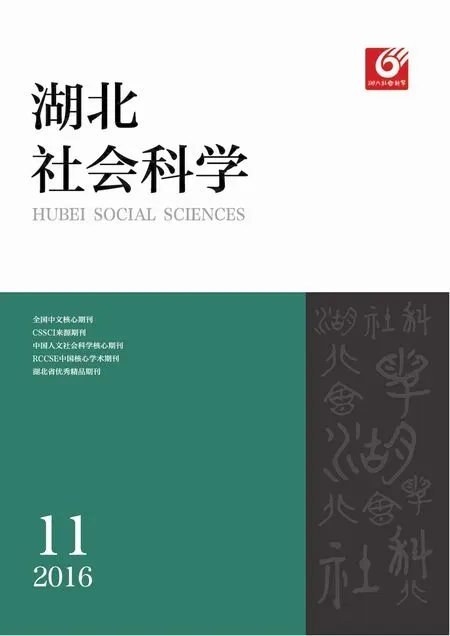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为君之道
2016-03-14刘荣
刘荣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为君之道
刘荣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王夫之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君道政治思想,惜乎前人多不察。三代圣王之道是为船山心目中理想的君道典范,包括取天下以道、扶进人才、能安敢言者和从容调御几个方面。三代以下君主之治道当效法三代之王道,并因时损益和斟酌,君主之政治品格、知人之哲、用人之道、纳谏之道、辱大臣为辱国及立嫡与豫教并行等是为君主理政之道,即为君之道。王道在本质内容上仍然属于君道。王夫之之重视为君之道,一来在于他仍未走出“圣君贤相”之政治理想,二来是为将来社会提供治道之借鉴,“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为君之道;王道;《读通鉴论》;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学者呼之为船山先生,明清之际湖南地区的一代大儒。他一生著作等身,晚年写有历史评论著作《读通鉴论》,该书自晚清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过,历来针对《读通鉴论》一书所做的专门、系统研究甚少,且以历史观、民族观与政治思想三个维度为习见的研究重心。[1]就研究范围而言,本文所论是书的为君之道无疑属于政治思想的领域。但综观《读通鉴论》的学术研究史,政治思想维度上也罕见有对为君之道这一面向的探析。因此之故,本文以船山的《读通鉴论》为文本凭据,尝试梳理和挖掘其中所包蕴的为君之道这一自来鲜有人涉猎的内容。经此不仅可以丰富该书的政治思想内涵,同时得以扩大并深化《读通鉴论》一书的研究领域,从而进一步丰富船山学的研究视野。
何为为君之道?为君之道指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或皇帝在经国方面所具备的带有普遍性、一般性和共通性质的道理和做法。船山认为这些原理型做法应当并且可以适用于中国历史的任一阶段,它们就是每位君上政治观念、行为与活动的指针与范本。我们对船山为君之道的阐发将从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所议论之具体政治事件或制度中提炼出来。不过,在论述具体的君道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理想的君道,即王道或圣王之道,先进行讨论。应该说,王道是船山心目中的理想型或完美型君道,以夏、商、周三代先王之政治理念和作为为原型的王道本质上是三代以下君道之惟一典范与终极目标。虽然《读通鉴论》中船山一再慨叹三代以下鲜有合乎三代王道者,但我们仍然从中发现了以东汉光武帝为代表的符合圣王之治道的典范人物,以及船山间接涉及的遵循了三代王者政治理念的一些政治活动。以下分述之。
一、王道或圣王之道
圣王之道指以儒家所推崇之夏、商、周三代中的明王,如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以他们的政治功绩为来源和模范的治道。圣王自然就专指三代明君,而其道则为治道,但此治道根本上讲具有根本
适用性与恒久性。三代之道由此也可以被用来指代圣王之道。不过,在船山看来,就三代以下中国历史的实际来看,圣王之道其实鲜有被真正践行过,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王道实际上是一种很难企及的政治目标。难以企及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三代以下的历史情境相比于三代以上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郡县之与封建殊,犹裘与葛之不相沿矣”,[2](卷三·汉武帝一)而后世却没有能够在精确理解三代王道精意的基础上因时损益与运用,这不仅造成了王道难以化成于秦汉以后之历史,还有时损害了王道理念。第二,世易时移,三代以降之历史进程中出现过好几种可与王道相抗衡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如老庄(或黄老)之教、申韩之道与佛教等。他们的政治理想各不相同,每一种都足以作为王道政治的强大对手。其中,申韩之道与王道相去甚远,船山因之对申韩之道的抨击最为猛烈,也不时在经由与王道政治相互较中予以批评,并借此凸显王道政治之真确。船山曾这样评价:“盖尝论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2](卷十七·梁武帝二十五)其中,老、庄之教“王道虽不足以兴,而犹足以小康,则文、景是已”;[2](卷十七·梁武帝二十五)浮屠乃“充塞仁义者也”,“故浅尝其说而为害亦小”,[2](卷十七·梁武帝二十五)不足为深患;“若申、韩,则其贼仁义也烈矣”,[2](卷十七·梁武帝二十五)故而“祸至于申、韩而发乃大”。[2](卷十七·梁武帝二十五)以下我们对《读通鉴论》中圣王之道的论述就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对申韩之教的比照。
1.取天下以道。
卷六之“光武取天下以柔道”与卷二十之“高祖不遽取天下”两论表明后汉光武帝和唐高祖之荡平四海乃合乎王道之举,深为船山欣赏。就光武帝而言,船山以为他之得天下实较汉高帝为难,因彼时强敌环饲,其所资以有为者仅河北一隅耳。船山分析汉光武帝成功的原因:“乃微窥其所以制胜而荡平之者,岂有他哉!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猛而已。帝之言曰:‘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非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柔者非弱之谓也,反本自治,顺人心以不犯阴阳之忌也……然则光武所以屈群策群力而独伸焉者,舍道其何以哉?天下方割裂而聚斗,而光武以道胜焉。”“呜呼!使得天下者皆如高帝之兴,而无光武之大猷承之于后,则天下后世且疑汤、武之誓诰为虚文,而唯智力之可以起收四海……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不无小疵,而大已醇矣。”[2](卷六·后汉光武帝八)他的答案是:以道胜。此道为柔道,即是王道,顺应人心是也,“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猛而已”。船山这一结论无疑就是通过与申韩之崇尚智力与诈谋而夺取天下的做法比照中得出的。船山的意思是,光武之得天下,实乃顺天应人之举,与汤武革命相仿佛,故静审时机,从长计议,缓图之而非以暴力革命的方式亟取,如此可保生民不受战争之蹂躏。船山由是赞叹光武有大猷,其举动可与三代圣王之商汤与周武王匹配,为三代以下所罕见。王道制胜便是他的法宝。
卷二十之唐高祖更是应天顺人以顺利得天下的典型。“《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圣人知天而尽人之理……得天之时则不逆,应人以其时则志定……唐之取天下,迟回以起,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而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高祖意念之深,诚不可及也。”“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规取天下者,夺之于群盗,非夺之于隋也。隋已亡于群盗,唐自关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然而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不贪天方动之机,不乘人妄动之气,则天与人交应之而不违……隋已无君,关东无尺寸之土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自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2](卷二十“唐高祖一)
应天顺人即为取天下之王道,汤、武当之。所谓应天,即是恰当把握住天时,顺应天之规律,不早图之也不去与天争命。所谓顺人,即是顺应人心之归,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当是时,天下苦隋久矣,群盗起而亡隋,杀伐不止,民不聊生,而“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起,顺理成章地取隋已有之天下,同时赢得了人心。这跟光武帝一样,同样是以柔道即王道取天下之典范,所谓“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
与上述以王道兼并天下的两例相反,申韩之术崇尚通过智力和诈谋以及一切无常之招数赢得天下,秦朝即是一例:“秦起西戎,以诈力兼天下,蔑先王之道法,海内争起,不相统一,杀掠相寻,人民无主。”[2](卷二十二·唐玄宗一九)秦朝不以王道而以悖离王道之诈力兼并天下、统一四宇,其结果却也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此乃师法申韩之术的结果。
总之,“君天下者,道也,非势也”。道即为三代圣王取天下之道,为船山所推崇;而势实为申韩之术之代称,泛指靠诈力与不义兼并天下者。
2.扶进人才。
船山尤其重视人才之选拔和登进,“王者以公天下为心,以扶进人才于君子之途为道”。[2](卷十一·晋武帝一一)扶进人才是为王道之一端。行王道者,必然早作夜思,重视人才之培养与储备,以为国家之用。
“蒋琬死,费祎刺,蜀汉之亡必也,无人故也。图王业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险要财赋之谓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谓也,得其贤也。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矣。故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勤于耕战,察于名法,而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2](卷十“三国三二)
王者建功立业,必有贤人相佐。此意为,不仅有当世之贤臣,尚能及早发现并培育有潜力之贤人,以为将来之用,从而使人才队伍绵绵不绝,为国家效力,这是王者之道。三国蜀汉则不然。一二大臣殁后,朝中再无贤人,致使国家覆亡。何以如此?习于申韩之道故也。“诸葛公之志操伟矣,而学则申、韩也”。诸葛亮主政期间,以申韩刑名之术理政,“勤于耕战,察于名法”不正是法家的主张吗?以上船山无非想说明,培育并扶进人才之王道当被奉为治理之圭臬,不可不察。为了加强说服力,船山又概举了历史上其他因疏于此道而亡国之朝代:“管仲用于齐,桓公死而齐无人;商鞅用于秦,始皇死而秦无人;无以养之也。宽柔温厚之德衰,人皆踞蹐以循吏之矩矱,虽有英特之士,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尚奚恃哉?诸葛公之志操伟矣,而学则申、韩也。文王守百里之西土,作人以贻百年之用,鸢飞鱼跃,各适其性以尽其能,夫岂申、韩之陋所与知哉!”[2](卷十“三国三二)战国之齐国与秦朝皆为师法申韩之术而亡国之前车之鉴。最末一句则为反证,周文王于人才之养育有百年之虑,各类人才各尽其性,周代得以郁郁乎文哉!王道之大用当如此哉!
3.能安敢言者。
历来有为之主,多鼓励臣下直言进谏,以此可以收到从谏如流之美名。不过,在船山看来,即便君上有纳谏之诚意,但从历史上看,能够敢于谏诤者其实并不为多。船山的分析如下:“非徒上无能容之也,言出而君怒,怒旋踵而可息矣,左右大臣得为居间而解之;藉其终怒不释,乃以直臣而触暴君,贬窜诛死,而义可以自安且自伸也。唯上之怒有已时,而在旁之怨不息,乘间进毁,而翘小过以败人名节,则身与名俱丧,逮及子孙族党交友而皆受其祸,则虽有骨鲠之臣,亦迟回而吝于一言。故能容敢言者非难,而能安敢言者为难也。”[2](卷六·后汉光武帝二四)
两个因素导致了历来“敢言之士不数进”。第一是君主,面对直臣之谏容易动怒和不宽容,时或致使进谏之臣“贬窜诛死”,无人再敢冒险畅所欲言。二是君主身边之佞臣。他们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从中挑拨离间,“乘间进毁”,激化矛盾,也会导致进谏之臣蒙受灾祸,甚至株连族人。不管哪一种因素,都会导致臣下三缄其口、欲言又止,“虽有骨鲠之臣,亦迟回而吝于一言”。因此,船山得出了一个认识,“能容敢言者非难,而能安敢言者为难也”。允许敢言者直言非难事,善于接纳敢言者之直言才是难事。不过,船山所敬仰之后汉光武帝即有“能安敢言者”之胸襟:“光武……专用南阳人而失天下之贤俊,虽私而抑不忘故旧之道也……乃郭伋以疏远之臣,外任州郡,慷慨而谈,无所避忘,曰:‘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故旧。’孤立不懼赫奕之阀阅,以昌言于廷,然而帝不怒也……诚若是,士恶有不言,言恶有不敢哉?诸将之贤也,帝有以镇抚之也;奖远臣以忠鲠,而化近臣于公坦,帝之恩威,于是而不可及矣……呜呼!是可望之三代以下哉?”[2](卷六·后汉光武帝二四)
光武帝兴于南阳,其得天下后便多专用南阳故旧,外人之登进者则不多。时有郭伋者,非与于中枢之列,取敢于批评光武徇私以用人之举,“慷慨而谈,无所避忘”。郭伋直言不讳地向光武帝指出,应当选拔天下英才而进之,不应该只用皇帝自己的故人。郭伋敢言于庙堂,但光武帝闻此却无不悦,虚心接受了郭伋之建议。船山对光武帝之虚心从谏深为叹服。认为如果后世君主都能够做到如光武帝一般,则“士恶有不言,言恶有不敢哉?”朝政必将大治。船山最后一句感慨明显带有惋惜之意味,叹息三代以下无有如后汉光武帝一样既能容敢言者又能安敢言者的君主。无疑,能安敢言者、虚心纳谏是为三代之王道,本当值得效法。
4.从容调御为王道。
儒家王道政治的一大特点在于以礼乐德政治国,注重从容调御、潜移默化,虽有张弛,但不会操
之过急而使政治举措与运行有大起大落之巨差。申韩之道则相反,一断之以刑名之教和严刑峻法,为政之道大张大弛,不合于社会常态。
“王导秉江东之政,陈頵劝其改西晋之制,明赏信罚,综名责实,以举大义,论者韪之,而惜导之不从。然使导亟从頵言,大反前轨,任名法以惩创久弛之人心,江东之存亡未可知也。”[2](卷十二“晋懐帝六)
东晋南渡,王导秉政。陈頵劝王导骤改政制,以申韩之法行于朝廷,但王导未从。船山以为,王导之决定是正确的,若行陈頵之言,则“江东之存亡未可知也”。船山分析如下:“晋代吏民之相尚以虚浮而乐于弛也久矣,一旦操之已蹙,下将何以堪之?且当其时,所可资以共理者,周顗、庾亮、顾荣、贺循之流,皆洛中旧用之士,习于通脱玄虚之风,未尝惯习羁络者;骤使奔走于章程,不能祇承,而固皆引去。于是虔矫束湿之人,拔自寒流,以各呈其竞躁,吏不习,民不安,士心瓦解,乱生于内而不可遏矣。夫卞壶、陶侃,固端严劼毖之士也,导固引壶于朝端,任侃于方岳矣,潜移默化,岂在一旦一夕哉?”[2](卷十二“晋懐帝六)
南渡之前,晋代的政治氛围是宽松的,吏民早已习于此松弛之环境。东晋南渡,沿袭了此前之举措与做法,整体上是遵循着儒家王道之基本理念。若此时大反前轨,一任名法,社会上下将不堪此创。而且,行政必用人,当时东晋之能臣,多为随南渡而来之北人,浸淫于以往之玄虚风气久矣。若让他们骤然弃王道而行申韩,必皆不从。新擢之士虽乐意为之,则必“呈其竞躁”。吏民两不安,人心震慴,乱生于内。此种政治生态根本上是悖离王道理念及实践的,也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弛者反之以大张,大张必穷,而终之以大弛,名为王道,而实为申、商,不覆人之家国者,无几也”。[2](卷十三·东晋成帝三)总之,王道政治讲究劳来以德教、移易以礼乐,张弛不迫、从容调御。大弛以大张而病国者,北宋即是一例:“宋尝病其纪纲之宽、政事之窳矣,王安石迫于改更而人心始怨;元祐、绍圣、建中靖国屡惩屡改,而宋乃亡。”[2](卷十二“晋懐帝六)
二、君道
我们对船山《读通鉴论》中为君之道的总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君主之政治品格。
《读通鉴论》中对君主自身的政治品质的讨论并不多见,更多的是着眼于君主之于从政活动的一些基本素质要求。卷二之“文帝伪谦不终”一文强调了“谦”的政治品质对于君主政治的重要性。
“君子之谦,诚也。虽帝王不能不下邱民以守位,虽圣人不能不下刍荛以取善。理之诚然者,殚心于此,而诚致之天下。见为谦而非有谦也,而后可以有终。故让,诚也;任,亦诚也。尧为天下求贤,授之舜而不私丹朱;与禹之授启、汤之授太甲、武王之授成王,一也,皆诚也。舜受于尧,启受于禹;与泰伯之适句吴、伯夷之逃孤竹,一也,皆诚也。若夫据谦为柄,而‘撝’之,而‘鸣’之,而‘劳’之;则姑以此谢天下而不自居于盈,则早已有填压天下之心,而祸机伏而必发,故他日侵伐而无不利。黄、老之术,离诚而用伪久矣。取其‘鸣谦’之辞,验其‘侵伐’之事,心迹违,初终贸,抑将何以自解哉!故非君子,未有能终其谦者也。”
“有司请建太子,文帝诏曰:‘楚王,季父也;吴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诸父昆弟之懿亲,宜无所施其伪者。而以观其后,吴濞、楚戊、淮南长无一全其躯命者。尺布斗粟之谣,取疚于天下而不救。然则诏之所云,以欲翕固张之术,处于谦以利用其忍,亦险矣哉!”[2](卷二汉·文帝二)
所谓谦,只是诚于谦,谦则必诚,诚于中而形于外,事事物物上见为谦,此为谦也。若视谦为手段和把柄,以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则离谦远矣,此为伪谦,非为谦也。古圣先王之行禅让均是诚于谦之榜样。汉文帝则不然,厚貌深情,表里不一,以诚谦之名行伪谦之实,据谦为柄,消灭政敌,为船山所不齿。
2.知人之哲。
用人以行政,乃君主之要事。“大有为者,求之夙,任之重,得一二人,而子孙黎民世食其福矣。”[2](卷二十八·五代上一九)但要求得合适的人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船山对此深有体会,故在《读通鉴论》中屡次感慨“知人之哲,其难久矣”。[2](卷二十一·唐中宗一一)毕竟,用人的前提是识人、知人,若眼光不周、无有准则,所选拔之人则并非恰当人选,或可偾事。船山认为,汉武帝有识人之法:“武帝举(金)日磾于降胡,左右贵戚所莫测也。知人之哲,非人所易测久矣。”“武帝游宴后宫阅马,嫔御满侧,金日磾于数十人之中独不敢窃视,武帝以此知日磾,重用之而受托孤之命,非细行也。盖日磾非习于君子之教,而规行矩
步以闲非礼者也。不期而谨于瞻视焉,不期而敦其敬畏焉,不期而非所视者勿视焉,勿曰细行也。神不守于中,则耳目移于外而心不知。让千乘之国,而变色于箪豆;却千金之璧,而失声于破甑;才足以解纷,勇足以却敌,而介然之顷,莫能自制其耳目;其细致哉……贞生贞死,任大任而无忧惑,此而已矣。武帝之知人卓矣哉!”[2](卷三·汉武帝一六)
汉武帝拔举并重用金日磾,此举为左右大臣不解。实际上,当武帝阅马之时,独金日磾自敦其行不去窃视,武帝以为金氏非细行也,恰恰是其习于君子之教的自然流露与反应。武帝因此判断金日磾为守贞自律之人,足堪重用,故受之托孤之命。船山非常赏识武帝的识人才能。在他论中,船山也有提到与赞美:“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非以逢帝之欲而为尔也,以自敦其行而不失素履之贞也。”[2](卷三·汉武帝三一)
由此,船山总结了一条知人之准则,借用《老子》中的话是“以身观身”。即是说,不要以己视人,用自己已有之观念甚至成见去认识与判断他人,而要自他人本身之言行与交游去推断其人。“知人之难,唯以己视人,而不即其人之自立其身者视之也”。[2](卷三·汉武帝三一)若能做到以身观身,识人便不再是难事。对于以身观身的方法,船山有所具体阐述:“故君子之观人于早也,持其所习者以为衡,视其师友,视其交游,视其习尚;未尝无失,而失者终鲜”。[2](卷二十六·唐宣宗三)“师友”、“交游”、“习尚”皆为识人之视角。
3.用人之道。
用人之道涉及应当任用什么样的人以及不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以上“知人则哲”一条其实已经间接回答了前一个问题:任用何种人。此处船山着重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不该任用何种人。“人主之宜远燥人,犹其远奸人也。则亲亲尊贤之道,其全矣乎!”[2](卷二“汉文帝一)“袁盎请斩丞相、御史,憸人之心,不可穷诘,有如此者!或者其欲以恩私外市诸侯而背天子,挟庄助外交之心,以冀非望,未可知也。抑或憎妒大臣之轧己,而欲因事驱逐,以立威于廷,而攘大位,未可知也。文帝避杀弟之名,置盎不谴而参用其说。盎之无惮以逞,面欺景帝,迫晁错而陷之死,终执两端,与吴、汉交市,而言之不衷也显矣。盎,故侠也;侠者之心,故不可致诘者也。有天下而听任侠人,其能不乱者鲜矣!”[2](卷二“汉文帝一)
第一则材料里,君主应当疏远“燥人”,即浅薄躁动之人。船山认为燥人似奸人,绝之可矣。第二则材料中,君主应当弃用“憸人”,即奸佞之小人。袁盎有憸人之心,首鼠两端,居心叵测。船山进一步分析,袁盎原本是一侠人,侠者之心,不可致诘。侠人不可用,憸人也该弃。
除此之外,船山也赞同“不以言举人”。“是故明主……若其用人也,则不以言也;言而可听,必考其用心之贞淫,躬行之俭侈,而后授以大任也……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诚千古片言之居要矣”。[2](卷二十五·唐宪宗三)君主切不可因言选人,还要考察其言论背后之居心是否良好、个人行为是否端正等等,再决定是否可授以大任。若仅以言举人,恐有失人之危险。
4.纳谏之道。
君上善于纳谏自古以来就是一项基本和必需的政治素养,而若拒谏则被视作有违君道之举,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其所主持之朝政也多少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船山看来,纳谏同样很讲究,听言有道。“拒谏者,古今之所谓大恶也;亟取人言,而贪广听之名,其恶隐而难知……宋之中叶,上书言因革者,牍满公府,而政令数易,朋党争衡,熙、丰、元、绍之间,纷如乱丝,而国随以敝。”“善听言者,必其善于择人者也。人而善与,言虽未得,有善者存矣。人而不善与,言虽得,有不善者存矣……故君子之听言,先举其人而后采其言,必不以利禄辱贤者之操,而导不肖者以猖狂无忌也。”[2](卷十·三国三六)
拒谏不被欣赏和许可,但亟取人言同样为人费解和猜疑,因为这一行径有贪广听之名声,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真正意在听言并获取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北宋时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政府鼓励民众上书言事议政,公府之简牍因此汗牛充栋,致使官府之政令屡次更改和变易,还导致党争之出现,国事纷乱如麻、不可调和。这就是不善于听言和纳谏之后果。
船山认为,应当择人以听言。即,不是为了听言而听言,要看言论所从出之人。选择正确的人选并鼓励其进谏,君主再从中纳言。在船山看来,如果进谏之人为善人,其言偶或有失,但仍有善者之存在和利用价值。若其人非善类,进言即便有价值,仍让人怀疑其立言之居心和目的。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也是从政治大局出发,正确的做法是“先举其人而
后采其言”,选择合适的人,采纳其合适的言论。既不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大开言路以贪所谓广听之名,也不能以利禄为诱饵辱没进言者之操守。总之,择善人而纳谏。
5.辱大臣为辱国。
船山赞同明人高忠宪“辱大臣,是辱国也”之言论。“臣之于君,可贵、可贱、可生、可杀,而不可辱。刑赏者,天之所以命人主也,贵贱生死,君即逆而吾固顺乎天。至于辱,则君自处于非礼,君不可以为君;臣不知愧而顺承之,臣不可以为臣也。故有盘水加剑、闻命自弛,而不可捽。……后世之诏狱廷杖而尚被章服以立人之朝者,抑有愧焉者乎?使诏狱廷杖而有能自裁者,人君之辱士大夫,尚可惩也。高忠宪曰:‘辱大臣,是辱国也。’大哉言乎!”[2](卷二·汉文帝一四)
基于封建王朝之君臣关系,君主有对臣下有生、杀之权力,也有对臣下之官爵予以升、降之权力。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死贵贱本自天命,人主也只是奉天行事;即便君主这么做的时候不符合事实,甚至出现了误判,臣子也只能因乎天也,处之泰然,听天由命。不过,君主不可侮辱大臣。君若辱臣,则错在君主,是君主无礼,“君不可以为君”。面对侮辱,臣下应当羞愧,若不知愧且甘愿承受,则错在臣子,则“臣不可以为臣”。总之,“臣之于君,可贵、可贱、可生、可杀,而不可辱”。辱大臣视同辱国。
6.立嫡与豫教并行。
秦朝以后之中国历代王朝,嫡长子继承制作为皇位继承的基本制度总体上一直被贯彻执行。但东汉一朝时或有废立太子一事,且所立之人年少即位,为外戚和权臣所左右,朝政不得安宁。
“光武以郭后失宠而废太子强,群臣莫敢争者。幸而明帝之贤,得以掩光武之过,而法之不臧,祸发于异世,故章帝废庆立肇,而群臣亦无敢争焉。呜呼!肇之贤不肖且勿论也,章帝崩,肇甫十岁,而嗣大位,欲不倒太阿以授之妇人而不能。终汉之世,冲、质、蠡吾、解渎皆以童昏嗣立,权臣哲妇贪幼少之尸位,以唯其所为,而东汉无一日之治。此其祸章帝始之,而实光武贻之也。故立嫡与豫教并行,而君父之道尽。过此以往,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而又奚容亿计哉!”[2](卷七·后汉章帝六)
光武帝为始作俑者,虽然因明帝之贤明而得以掩饰,但却在后世章帝朝发祸。章帝之后,继位者年甫十岁,朝政把持于外戚之手。自此之后,嗣位者均乃童昏,朝政无一日之治。船山认为,立嫡固然重要,但同时还要做好豫教的工作,即对太子甚至小皇帝的教育培训工作。不如此,则这些童皇帝日后不仅难以胜任作为一名君主的基本要求和素养,还为宦官、外戚把持朝廷埋下了隐患。因此,船山建议,作为君主,应当视立嫡与豫教为同等重要,二者并行不悖,则“君父之道尽”。
三、结语
以上便是对《读通鉴论》中为君之道的呈现。从内容上讲,王道仍然属于君道乃至更广意义上的治道范畴。区别只在于,前者之主体为儒家政治思维中所极力推崇与向慕之三代明君,其政治言论与行动一直备受后世儒者所仰望并以此作为政治生活之标的,具有神圣和理想化的特征;而后者之主体则主要是三代以下历朝之君主,他们作为王朝政治活动的最主要责任人,在政治素质上参差不齐、高下有别,不仅需要以三代明君之治道为理政之样本和典范,同时更要在体察和领会王道政治精意的基础上形成合乎时代和时势要求的治道,即君道。二者在追求有效、有序与合理的朝政治理方面则是一致和统一的。由此看出,王夫之对古代中国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政治素养之基本要求是全面的、高标准的,从奄有四海之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到扶进、任用人才再到皇位继承人之确立,无一不有其道,而又无一不取决于皇帝,因此共同汇聚并构成为君之道。王夫之之所以相当重视为君之道,根源还在于他的政治理想仍然没有走出古代中国一直以来的“圣君贤相”的终极标准。其次,王夫之对为君之道论述目的在于“述往以为来者师也”,[2](卷六·后汉光武帝一〇)他寄希望于将来社会之君主能够借鉴和吸取以上所论之君道,并以此作为经国理政之良策。
[1]刘荣.近百年来王船山《读通鉴论》研究述评[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4).
[2]王夫之.船山全书(10)[M].长沙:岳麓书社,2011.
责任编辑 高思新
B249.2
A
1003-8477(2016)11-0093-06
刘荣(1985—),女,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