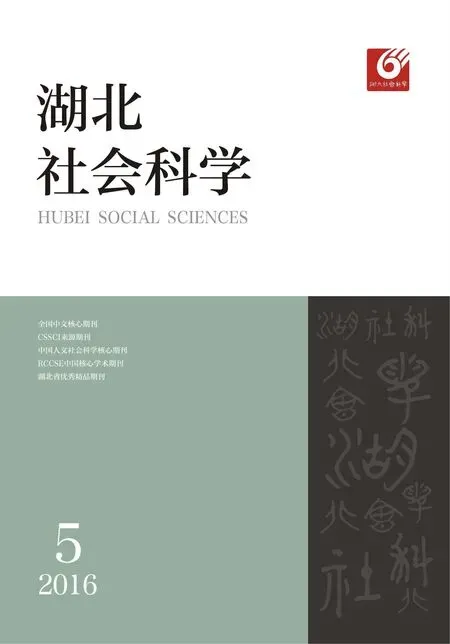市民社会中“经济事实”的还原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经验性方法的考察
2016-03-14高惠芳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101
高惠芳(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101)
市民社会中“经济事实”的还原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经验性方法的考察
高惠芳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101)
摘要: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既表现了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对立,同时也表现了人与人的利己本质的对立。因此,市民社会是一切秘密的发源地,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无非就是对市民社会中家庭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政治经济学是为市民社会学——市民社会学即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中出现决非偶然。一方面,费尔巴哈哲学宣告了思辨哲学的逻辑学的研究前提是错误的——思辨哲学是从思辨的观念的无限性而非从现存事物的感性的有限性出发。另一方面,费尔巴哈哲学还宣告了唯心哲学的逻辑学的思维路径是错误的——感性的经验世界、经验世界的感性决不是思辨的抽象的现实化,决不是观念的容器。
关键词:费尔巴哈;思辨的哲学的逻辑学;经验的历史的逻辑学;马克思;市民社会学
1844年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摘要批注的形式部分地研读了亚当·斯密、让·巴·萨伊、大卫·李嘉图、穆勒、约·拉·麦克库洛赫等的政治经济学论著(在笔记本Ⅰ中摘引批注了斯密、萨伊,在笔记本Ⅱ中摘引了麦克库洛赫并在李嘉图和穆勒与斯密和萨伊之间进行了对比),而在《资本论》研究时期,马克思的观点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从观点的量度上还是观点的质的变化上——,这就涉及一个方法的问题,能否把《资本论》作为《手稿》的引证。在开始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及其相关论题分析以前,我们先要声明这样一个前提:我们不会用《资本论》的成熟的理论去论证1844年的马克思,尽管如此,但我们也会采用一些无关论点的回忆性表述去增强本文的说服力。譬如,在说明马克思善于发现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回忆性话语就是很好的例证。
一、本质上,政治经济学是为市民社会学
政治经济学究其本质,是为市民社会学。让· 巴·萨伊说:“经济(economy)起源于希腊语(家庭)和Νóμοζ(法),就是管理家庭的法规。按照希腊语,家庭一语含有家庭所保有的一切货物,而政治一语的应用则扩展到一般社会和国家。”[1](p15)并且,萨伊认为用“政治经济学”称谓这门学科十分恰当。事实上,马克思在1843年的几部著作中都对“市民社会”的属性进行了隐性的阐释,最为明显的是《论犹太人问题》。布·鲍威尔提出了政治解放与市民社会解放相分离的论点,人的政治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是有限的,人的解放是无限的,在现实的政治国家中,“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2](p172-173)现实的人因而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类的存在物”的政治共同体,一是作为类的个体的个人,即是说,人一方面是政治社会的公民,一方面又是市民社会的市民。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只是人的解放的一部分,“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所宣告的并不是真正的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前提必须是市民社会中的人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既表现了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对立,同时也表现了人与人的利己本质的对立,换句话说,市民社会是政治与家庭的共同体,人与国家制度、政治社会的冲突无非是人与一切人的关系的反映。因此,市民社会是一切秘密的发源地,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无非就是对市民社会中家庭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一定要在家庭和政治的全部领域中存在。
市民社会学表明自身与以往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不同的真理观与价值判断。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非批判的、非科学的,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为资本、资本的利润服务的,是功利主义的。马克思称它们为庸俗经济学。譬如,萨伊就曾直言不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性:“政治经济学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商业确是有利,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得到利益而另一个人受到损失,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上也对一切人都有利”,除此之外,“政治经济学也教导我们怎样鉴识商业的各个方法”,“至于商人,除上述知识外,还必须懂得经营他的行业的技巧”,“对于农场主、工厂主和实业家,也可适用,原因是,为获得对各个现象的因果的透彻知识,他们都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1](p16)麦克库洛赫直言:“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些方法使人类的劳动可用之于最有效地生产那些构成财富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方面,说明这些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比例以及它最有利地消费的方式。这样一门科学与社会所有有关方面的内在联系是很明显的。实在的,再没有其他的科学和人类日常的生活与事业有这样密切的关系。”[3](p6)看看杜尔哥对经院哲学家是怎么说的,您们尊崇的《圣经·福音书》中的“借给人,不指望偿还”的信条是谬误的,“借出货币的人不仅放弃了一笔货币的不产生收益的所有权,而且还失去了他本来有权用这笔货币而获得的利润。因此,补偿他这部分损失的利息不应视为是不正当的。”[4](p60-61)李斯特认为,“国民经济学探讨的是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指导和管理个人经济,限制人类经济以防止外国的限制和外国的势力阻碍本国的经济,发展本国的生产力”。[5](p3)在马克思看来,它们研究的是人和财富的关系,而非社会生产关系;它们辩护的对象是有产者阶级,而非作为无产者的工人阶级、社会底层大众;它们的目的是为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国家服务,通常信仰的是自由主义或专制政治,而非为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及等级地位牟利。
市民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对麦克库洛赫等人的庸俗观点的严肃批判中建立起来的。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直接是为个人谋利的,譬如“麦克库洛赫不过是这样一个人,他要拿李嘉图的经济学做一笔生意”,“麦克库洛赫就是凭李嘉图的经济学,才在伦敦得到一个教授位置。他的职务,本来就是以一个李嘉图派的资格出现,并参加反对地主的斗争。他一立住足,并在李嘉图学徒中取得位置,他的主要努力,就是把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经济学,运入辉格主义的界限内,并和一切为辉格党人所不悦的结论相疏远。他的最后的论货币,赋税等等的著作,不过是当时辉格党内阁的辩护书。由此,这个人就得到了发财的机会。”[6](p201-201)仅从这一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完全是非批判的、非科学的,它不具备一点儿革命性。仅仅具有的市民社会的现象学描述,却没有对现象学进行任何的批判;仅仅还原了市民社会的经验世界,却缺乏对作为前提的经验材料的前提的批判,即是说,不是把经验的感性事实作为思维的出发点而是把它当作思维的结果呈现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指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尖锐地指出黑格尔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现实性没有被说成是这种现实性本身,而被说成是某种其他的现实性。普通经验没有把它本身的精神,而是把异己的精神作为精神;另一方面,现实的观念没有把从自身中发展起来的现实,而是把普通经验作为定在”,[2](p10)这样一来,“可经验的现状的现实性也被说成合乎理性,然而它之所以合乎理性,并不是因为它固有的理性,而是因为经验的事实在其经验的存在中具有一种与它自身不同的意义。作为出发点的事实没有被理解为事实本身,而是被理解为神秘的结果。”[2](p12)市民社会的现状所描述的经验世界,一旦被思辨的思维“头脚倒置”为理性的定在,那么,资产阶级及其控制下的市民社会就成为永恒的了,它的合法性、真理性就显而易见。
市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要从市民社会的经验世界中去寻找经验世界的主体。马克思看到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外化的历史,他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外化历史的全部消除。这种消除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那里,仅仅表现为“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究其本质,“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7](p203)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政治经济学家只承认它们在思维中的悖论而不承认现实的反动性。古典的乃至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它们在哲学上的最高依据和表现,无非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哲学的逻辑学。它们是思辨的唯心主义在市民社会中的复活,仍需对它们进行彻底的哲学批判。“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7](p201)这样的哲学批判既是在马克思那里的自发的运动,也是德国人本学哲学家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启蒙的结果。费尔巴哈在《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就说:“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神学。思辨神学与普通神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将普通神学由于畏惧和无知而远远放在彼岸世界的神圣实体移植到此岸世界中来,就是说:将它现实化了,确定了,实在化了。”[8](p101)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他说:“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2](p315)我们不敢妄言费尔巴哈究竟在马克思的思维革命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在德国现代哲学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马克思极大地褒扬了费尔巴哈。如若我们的研究真正是在考察马克思的思想革命与他所处的德国现实的关系,正像阿尔都塞坚持的独特的思想整体与现实的总问题的关系原则一样,①阿尔都塞认为:“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其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因而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况且,“推动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在该思想的内部,而在它的外部,在这种思想的此岸,即作为具体个人出现的思想家,以及在这一个人发展中根据个人同历史的复杂联系而得到反映的真实历史。”显然,费尔巴哈正是“其中的一个成分”。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论青年马克思》,《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8页。那么,我们就不能采用通常的史学的目的论的研究方法并漠视它的消极后果——不久之后马克思就开始批判费尔巴哈,譬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大大降低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地位,消解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现实意义——正确的做法是,从现在起我们必须重视费尔巴哈,探究这里的马克思为什么需要费尔巴哈。
二、费尔巴哈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什么?
以往关于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国内外学界争论颇多。其争论的依据和结论,在今天看来,都有失偏颇②从马克思思想史去考察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大体包括一、“三阶段论”,黑格尔的哲学的逻辑学→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直至马克思开创了历史的科学,其代表人物是普列汉诺夫;二、“三阶段论”的进一步深化伦,不仅承认费尔巴哈阶段的存在,而且视马克思的新哲学为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奥·拉布里奥拉;三、“二阶段论”,用“黑格尔主义(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的新哲学”公式批判“三阶段论”,根本否认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影响,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理论界,我国部分学者持有此观点。参见顾伟伟:《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启蒙——论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广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顾伟伟:《考察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间关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贵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决定上述争论的实质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费尔巴哈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什么?换句话说,马克思要从费尔巴哈那里取得什么来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中直言不讳:“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2](p220)显然,马克思公开地颂扬费尔巴哈了,并为费尔巴哈遭受的非难和不公的境遇抱不平,“一些人出于狭隘的嫉妒,另一些人则出于真正的愤怒,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轶文集》中的《哲学改革纲要》——尽管这两部著作被悄悄地利用着——可以说策划了一个旨在埋没这两部著作的真正阴谋。”[7](p112)马克思具有意识并发现哲学的“优秀”成分的天赋与品质,他总是以独到的眼光重新挖掘并扬弃以往被埋葬了的哲学家的思想。譬如,一是重新评估了布·鲍威尔的宗教批判和政治解放的意义,认为宗教解放是有限度的,是人的现实的解放的一部分。“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7](p32)鲍威尔由于对基督教的批判在科学史上享有特殊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却没有为鲍威尔赢得著名哲学家的声誉,研究他的人和著作并不多见。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那寥寥无几的人中的两个。恩格斯在1882年撰写的纪念性文章《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对这种现状作了说明,《论犹太人问题》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9](p327)二是发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回忆说:“正当我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做一条‘死狗’了”,[10](p22)因此,恩格斯评价马克思发现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从黑格尔的粪堆中啄出了辩证法这颗珍珠。再有一次就是发现了费尔巴哈的真正价值,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也说:“只是在费尔巴哈废除思辨概念以后,黑格尔学派才逐渐销声匿迹”。[11](p600)实际上,马克思的每一次发现都不是无功而返,必是伴随着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和进步,细心的读者完全有理由相信,费尔巴哈必定为马克思的发现提供了一种际遇。
《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论犹太人问题》是多么的相似!它不仅表现在观点上的一致,就连话语都非常地相像。我们摘引几段话进行对比:
Ⅰ揭露哲学的逻辑学的神秘性。Ⅰ-1费尔巴哈说:“黑格尔哲学是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的扬弃……只不过这种矛盾的扬弃是在矛盾的范围以内——是在思维的范围以内。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就是存在,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宾词。逻辑学是思维要素以内的思维,或者是自己思维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或者是无宾词的主体,或者是同时兼为主体和宾词。……黑格尔将客体仅仅想成自己思想自己的思维的宾词:就是思维无论什么时候都被当作主体,客体和宗教则被看成思想的一个单纯的宾词。”[8](p114)
Ⅰ-2马克思说:“重要的是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作主体,而把本来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例如,‘政治信念’变成谓语。而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既然出发点是被当作主体、当作现实本质的‘观念’或‘实体’,那现实的主体就只能是抽象谓语的最后谓语。”[2](p14、22)
Ⅱ论哲学的开端。Ⅱ-1费尔巴哈说:“思辨哲学与神学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将实在性或有限性的规定,仅仅通过对这些规定性的否定——就是在这种规定性中,这些规定才成为这些规定——,化为无限者的规定和宾词。”“哲学的开端不是上帝,不是绝对,不是作为绝对或理念的宾词的存在。哲学的开端是有限的东西、确定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无限者是有限者的真实本质——真实的有限者。真正的思辨或哲学不是别的,仅仅是真实的、普遍的经验。”
因此,“真正的哲学的任务,不是将无限者认作有限者,而是将有限者认作非有限者,认作无限者,换句话说,就是将有限者化为无限者,而将无限者化为有限者。”[8](p107-108)
Ⅱ-2马克思说:“黑格尔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不在于他按现代国家本质现存的样子描述了它,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冒充国家的本质。”[2](p80)
“正确的方法被颠倒了。最简单的东西被描绘成最复杂的东西,而最复杂的东西又被描绘成最简单的东西。应当成为出发点的东西变成了神秘的结果,而应当成为合乎理性的结果的东西却成了神秘的出发点。”[2](p52)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7](p4)
Ⅲ批判黑格尔的思维逻辑的路径。Ⅲ-1费尔巴哈说:“思辨的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进程,是一种颠倒的进程。从这样的道路,永远不能达到真实的、客观的实在,永远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抽象概念现实化,正因为如此,也永远不能认识精神的真正自由;因为只有对于客观实际的本质和事物的直观,才能使人不受一切成见的束缚。从理想到实在的过渡,只有在实践哲学中才有它的地位。”[8](p108)
Ⅲ-2马克思说:“(黑格尔)只是把实现了的观念的意义加之于任何一种经验的存在,所以很明显,观念的这些容器一旦成为观念的某一生命环节的某种体现,它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此,在这里,普遍的东西到处都表现为某种确定的东西,特殊的东西,而单一的东西则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自己的真正的普遍性。”[2](p52)
费尔巴哈写作《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时间是1843年,我们可以想象它对马克思的影响有多么重要。马克思几乎说了和费尔巴哈完全相同的话,或者说,费尔巴哈道出了马克思的心声。我们能够肯定1844年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手稿时,已经读过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基督教的本质》三部著作了,但就相近的思想、论点的起源来说,我们很难判断孰先孰后,或许他们同时发现了共同的东西。①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谈及他对《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赞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页。无论如何,马克思赞赏费尔巴哈的地方有几个方面:一、哲学的逻辑学的起点是错误的,它不应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应从真实的、普遍的经验出发,不是从思辨的观念的无限性出发,而应从现存事物的感性的有限性出发;二、思辨的逻辑的路径是错误的。感性的经验世界、经验世界的感性不是思辨的抽象的现实化,决不是观念的容器,相反,可经验的事物的有限性蕴含着思维活动的无限性,必须在对经验世界的批判中揭示出真理的无限性来。概括为一点,现实和思维的矛盾不是在与现实分离的纯粹思维的内部加以解决的,相反,只有在纯粹思维之外的现实与思维的相互关系中,它才具有某种可能性。[12](p118)
市民社会所提供的理论上的经验事实,尽管它们不曾被以往的国民经济学家否认,事实上亦从未被他们真正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血淋淋的经验事实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学家)发现并加以宣扬的,即使对它们采取完全否定的形式,但他们依旧从未尊重过这些事实,从未尝试对经验本身作出说明;如同青年黑格尔派展开政治批判的做法一样,“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atatus quo]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即使对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2](p200-201)况且国民经济学从未表露过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的目的和实践(像上面阐释过的)只是为了社会财富的增加,为有产者的利润和社会地位牟利。国民经济学的确描述了私有财产的事实,②国民经济学精准地描述了这个事实,而后马克思转述: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有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6页。并以私有财产的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它却没有说明这个前提。马克思严厉地斥责,“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具体地说,“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7](p155)即是说,没有向我们说明这种似乎偶然外部的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本质和表现。所以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是这样一些经济事实,它们本身就是应当说明的东西,而不是被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这种研究方式不是思辨的哲学所提供的,恰恰相反,它是反哲学的逻辑学的,费尔巴哈发现了它并为此得到马克思的褒扬。
考察并说明作为前提的经济事实,把对它们的批判性分析作为研究的结论而不是当作研究的最终原因,换句话说,不满足于经验直观的有限性而要从中挖掘出无限性来,这是费尔巴哈给予马克思的第一步提示;紧接着,费尔巴哈提供了用于分析的有关异化的概念和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或许是思辨的逻辑学和国民经济学已经使用过的,但在马克思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新的标准和意义,譬如,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异化仅被认知为劳动的现实化,它所表现出的典型的所指、能指的对立却被掩盖了,马克思却从中还原了工人的非现实的本旨,这全然归功于马克思的全新的思维体系,其中费尔巴哈提供了分析的工具——类、类的异化。国民经济学忽视了一个过渡:A→B——这个过渡至关重要,它是马克思最初在市民社会领域中少有的几个精彩发现之一——,它既可以是A与B间理论思维的对立,也可以是A与B间现象学的对立。我们将A与B以原本的形式摘抄出来。
A.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2](p267)
B.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2](p269)
A→B自身表明是一种价值判断,它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简单到应该被忽视的程度,马克思却发现了这个被研究本身荫蔽了的事实。费尔巴哈的启示至关重要,马克思要表明以下几点含义:
其一,复活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财富、财富的生成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作为无产者的人与作为有产者的人及其组成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真正意义上把人从市民社会中独立出来的第一人,商品、资本、工资、地租不过是属“人”的产物,人再也不是经济事实的客体,工人连同资本家一同作为主体存在了。倒下的是关于经济活动的精神现象学,重新站立的是关于人的生产活动及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的历史的科学。
其二,人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劳动代替了商品、资本成为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对象,确立了创造财富的主体只能是人的劳动而非其他物质因素。①李斯特提出影响一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四大类:“物质资本”、“精神资本”(或“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生产环境,他认为非劳动的自然力也会创造财富。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页。麦克库洛赫也以“生产了的葡萄酒放在酒窖贮存而后价值增加”为例攻击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参见[英]约·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4页。
其三,预示着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前提的确立。从以上两点:人和人的劳动,最终必将带来思维方法上的革命,开创唯物史观的研究。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的:“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纯粹经验的方法,既是马克思思维革命的前提也是作为产物存在的方法论。
纯粹经验的方法是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产物,同时也是受到费尔巴哈的启蒙并借用费尔巴哈的概念的产物。这种方法的要旨归纳如下:以历史的经验事实为研究的前提,而不是从抽象的思辨的概念出发;针对作为研究前提的经验事实首先要进行批判的分析,并加以阐释说明,而不是把它直接作为研究的最终原因,作为普遍的经济规律来推论;有助于经济事实的分析的是概念的空间上的延伸和内容上的拓展,即是说,概念的演绎应服从于经济事实的批判性分析,而不是颠倒过来——经验事实仅是作为观念的容器的思辨思维的方法。当然,对经济事实的一般分析首先是从一般概念的思维开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详细的说明。
三、“完成的”与“未完成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
如何看待《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二版)对此作了注释:“马克思并没有从内容和逻辑上把批判进行下去,最后以黑格尔《哲学全书》的两段引文结束。”[2](p665)这句话说得不全面,究竟是由于对思辨辩证法的批判不够深入而导致马克思没有形成完整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呢?还是马克思业已形成完整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体系而仅仅由于其他原因终止了辩证法理论的书写?这句话极易引起误解,已经有后世马克思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提问。阿尔都塞就持有后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业已实现了不朽的理论的实践,但作为创始人的马克思终究未能写出唯物辩证法的光辉著作。
请注意阿尔都塞提问的前提:一、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的“颠倒”,发现了哲学的逻辑学的“合理内核”后扬弃了的理论产物;二、《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理论的实践,之后的列宁、毛泽东都对辩证法的理论的实践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三、马克思没有写出辩证法的理论的著作,“马克思也诚实地承认欠了一笔债——即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方面’”,[13](p156)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宁、毛泽东等也终究没能写出辩证法的理论著作。同时,阿尔都塞认为,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它总是与所处时代的“总问题”存在着结构性的联系,即辩证法的理论形态与它对现时代的社会发展的总批判密切联系,表现为历史上的一个个的思想整体。那么,作为阿尔都塞提问的前提与他对提问的回答是自相矛盾的。仅就《手稿》而言,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是否完成——而不仅就它的“理论”的著作而言——,阿尔都塞给出的回答:“在‘颠倒’黑格尔这一为前人没有从事过的最彻底的考验中,(马克思)写作了《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这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13](p19)——我们保守地估计,即使阿尔都塞自己对这样的回答也没有多少自信,因为他把费尔巴哈的影响和作用(在《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论青年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对费尔巴哈的“决定性”作用曾给予了过高的评价)一同抹杀掉了。难道因为马克思没有公开地与费尔巴哈决裂,没有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宣言公开反对一切旧哲学,就否定了马克思形成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历史的思想体系——我们几乎就要忘记马克思抱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逐条地格言式批判,因为这将无端地增加一个“建造体系”的帽子(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坚决反对制造体系的),这正是写在《手稿》序言中时刻警醒马克思的话语——,细心的读者不会赞同马克思对思辨的哲学进行逐条分析的。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一种浪费,有谁怀疑过马克思仅仅在对《法哲学原理》第261-313节的批判分析中就已明确地表明了立场,又有谁不对黑格尔在庞大的体系中为阐述一个早已明了的思想而喋喋不休的混乱的叙述感到厌烦。
尽管《手稿》表明它是一部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未完成的”“理论”的著作,但马克思已经论证了他的“完成的”辩证法思想。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论犹太人问题》,再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清晰地描绘了对思辨哲学的逻辑学的批判历程;直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终于实现唯物辩证法的视域的转化,对思辨的辩证法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哲学,而且随着市民社会的经济学批判,唯物辩证法毕竟扎根于新的土壤并开花结果,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费尔巴哈的“过去完成时”的启蒙和“将来完成时”的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以及针对思辨哲学的某种意义上的“整体”的批判。而这一批判的副产品就是纯粹经验的方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了它。
结语:毫无疑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巅峰之作。当然,最能体现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思想并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定形式的当属《资本论》,而且,仅就《资本论》本身而言,它也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前苏联学者维·维戈茨基认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制定他自己的经济理论,这是二者合一的过程”,“可以断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马克思本身经济学观点的成熟标准”。[14](p4)如《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未必甘愿将《资本论》视作一门新的政治经济学,以示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体现得非常突出,马克思一方面不满足于古典哲学中“思辨”与“现实”、“政治学”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以及
由此造成的“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的缺失;一方面他也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庸俗的“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深恶痛绝。因此,“市民社会”是马克思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以来思维的主要阵地兼制高点。换句话说,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哲学”研究,还是“经济学哲学研究”,抑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市民社会”始终是他的学术思维的诞生地与秘密。以此,我们可以断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了这样一个思想:政治经济学是为“市民社会学”。
同样,我们亦可以断言,真正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学”开启大门的是费尔巴哈哲学,而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马克思的理性思维从上帝的圣殿拉回世俗人间的是费尔巴哈,使马克思用经验的历史的逻辑替代思辨的哲学的逻辑,得以直观经验事实的还是费尔巴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意义正是在这里。当然,马克思即将迎来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的巅峰,这个接力棒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手中接过的。
参考文献:
[1][法]让·巴·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英]约·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M].郭家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法]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M].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5][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邱伟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6]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孔见.当代经验的代际差异与文学表达[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13][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4][苏]维·维戈茨基.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成熟标志[A].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7卷[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张晓予
·政治文明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5-0012-08
作者简介:高惠芳(1978—),女,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2015年度北京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习近平辩证法思想的总体性研究”(2015SKL021)、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青年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经验性方法”(15FKS005)、南疆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XJEDU070114A03)、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宣传协同创新中心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