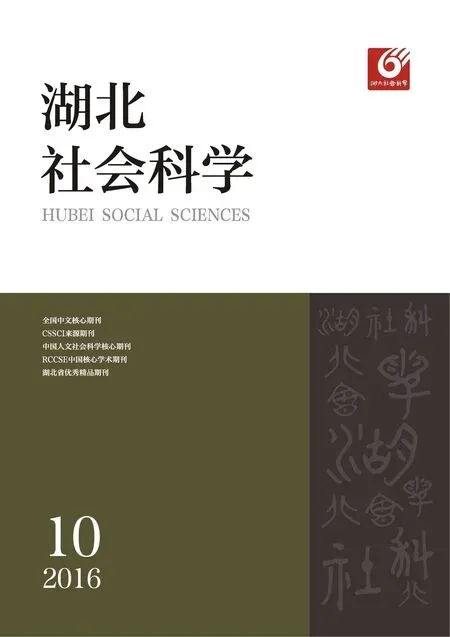曹植作品“矛盾”后的自我概念、人格及其阐释接受
2016-03-14王津
王津
(郑州轻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曹植作品“矛盾”后的自我概念、人格及其阐释接受
王津
(郑州轻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曹植作品存在诸多“矛盾”,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这折射出曹植极强的自我中心意识,此意识源于其“高效能自我感”的自我概念,此概念之确立经由早期习得、遭遇冲突和后期固化几个时期。在此概念驱动下,曹植早期的儒家思想渐次内化为稳定的儒家人格。历史对曹植儒家人格的发现是一漫长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曹植的人格精神较少关注,故而对曹植作品的深刻内涵亦少挖掘。陈寿、裴松之、江淹、萧绎、王通等对曹植精神的不断发现,纠正了曹植形象接受的偏差,指引了曹植人格接受的方向,为唐以后对曹植作品的道德阐释奠定了基础。
曹植;矛盾;自我概念;儒家人格;阐释接受
对曹植作品的研究,历来多集中于积极意义上的挖掘与阐释,而对其中的“矛盾”现象则缺乏应有的关注。马歇雷说:“真正的分析并不局限在对象之内,即解释那些已经被说出的东西,分析应该正视对象之中的沉默、否认以及抵御。”也就是“阅读不是去寻找作品内在的统一,而是去发现文本中的不完整和矛盾之处。”[1](p240)笔者在阅读三曹、七子的过程中,发现曹植作品不同于建安其他文人作品的表现之一即是文本中充斥着种种矛盾,若再加上不同文本间的冲突,“矛盾”无疑是曹植作品中的重要现象。
一、曹植作品中“矛盾”的现象层分析
曹植作品中的矛盾现象大致可归为四类:一是文本意象矛盾,二是文本意思矛盾,三是文本结构矛盾,四是不同文本间的矛盾。前三类是同一文本内的矛盾,第四类是不同文本间的矛盾。
(一)文本意象矛盾。
据笔者统计,《西北有织妇》、《美女篇》、《南国有佳人》、《种葛篇》、《盘石篇》、《鹞雀赋》、《蝉赋》、《七启》[2]等都存在意象矛盾现象,而所谓意象矛盾,指文本中的意象与其事实应具的特征有抵触之处。
《美女篇》中美女“长啸气若兰”,《西北有织妇》中织妇“悲啸入青云”,其激荡澎湃的情思在长啸之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宣泄。而啸,在先秦“是在女性间流行的一种习俗,”[3](p464)但先秦以后至东晋以前,啸多属男性行为;其次,啸有长啸、吟啸、啸歌之分,其中“长啸”,“声音宏放,有石破天惊的气势”;[3](p462)再者,在建安其他文人作品中,女性情感的表达相当婉约,她们叹息、哀歌、弹琴,奏瑟,远不同于曹植诗中如此激烈的抒怀。因此当长啸与女性相联系时,女性的阴柔气质就被来自男性的阳刚之气所破坏,也就是说,长啸与女性应有的柔美内趋性特质不相协调。另外,像《七启》中不为外物所动、与自然合一的玄机子,竟然最终为镜机子驱驰雄霸之论说服;《蝉赋》中避身皇宫,依树静处,惊魂未定的蝉,竟然以非常闲逸的心情欣赏赞美来捕捉他的“翩翩”、“容与”、“聪视”的狡童;《鹞雀赋》中鹞三日无食,饿极之下,竟然还对口中之雀彬彬有礼、同情不忍,宁愿自己忍饥受饿也不愿伤害它,等等,这些作品中的形象或前后矛盾,或与事实相错,让人觉得不合情理。
(二)文本意义矛盾。
在曹植作品中,有文本意义前后相矛盾的情况。此外,亦有文本意义与特定背景下作者的真实意图相矛盾的现象,而此又常与文本前后意义的矛盾融合于一篇之中,使得整个意义的表达在种种或明或显的冲突中产生更为激越的情感节奏。
如《圣皇篇》,写延康元年曹植兄弟赴封国的送别过程,诗中以陛下的“仁慈”为核心,写其给予诸弟玺绥累绍,赠赐倾府竭珍,护送华盛庄严。但朱乾一针见血地指出:“曹丕薄于骨肉,甫即位,即遣其弟鄢陵侯彰等就国。受禅之后,名为晋爵诸弟为王,而皆寄地空名,国有老兵百余人以为守卫,隔绝千里之外,不听朝聘。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虽有王侯之号,而侪于匹夫,皆思为匹夫而不能得。”[4](p199)有关事实,曹植《谏取诸国士息表》白之详矣。事实消解了“仁慈”,“仁慈”成为反讽词语。
而对于《责躬诗》,吴淇有精妙之论,“故此诗句句是服罪,却句句不服罪;不惟不服罪,且更跨进一步,求假兵权,词特倔强。然却字字本忠爱之道,来得浑厚不露,”[5](p109)对文本情感与事实情感的矛盾分析可谓洞见。如“济济俊乂,我弼我辅”,若结合《黄初六年令》与《写灌均上事令》,则可见曹植对所谓“俊乂”对其诬陷的无限愤慨。而下文则直言“哀予小臣,改封衮邑,于河之滨,股肱弗置,有君无臣,荒淫之厥,谁弼我身”,前后意思截然相反,这一直接对立更是把所谓的罪责、所谓的皇恩、所谓的责躬消解得荡然无存。另外,《名都篇》、《与吴质书》等亦有此类特点。
(三)文本结构矛盾。
早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即指出曹植《文帝诔》结构与文体的矛盾,“《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6](p110)除此外,曹植还有结构与主旨矛盾的作品,如《应诏诗》,其旨全在结尾,“长怀永慕,忧心如酲”,但全诗主体则写应诏赶路的紧急,待诏城阙的忧心于结尾轻轻挽结。吴淇对此甚有灼见,“通篇只是写其闻诏喜极,急急行路,冀得一觐天颜之意……乃出境一路行来,只是写速,兼带苦意。……而不意乃处之西坊,不容朝见也。”[5](p112)有些矛盾可能是无意造成的,如《游观赋》欲“游目以自娱”,“游目”往往是放眼骋望,以广阔的视野来舒展心灵的束缚,表现出内心无对立的开阔自由,而此赋则“从罴熊之武士,荷长戟而先驱,罢若云归,会如雾聚”,“奋袂成风,挥汗如雨”,突显的是阳刚之力的宣泄,与“游目以自娱”的初衷不协调。另外,《蝉赋》似乎是赞美蝉的高洁品性,但主体结构则是对其苦难之生的痛苦陈述,《酒赋》论者多以其为配合曹操戒酒令而写的宣传文章,但赋中极力铺写酒之体性,酒之功用,酒之华美,酒之乐、谐人情的妙趣,只结尾几句训诫,则过于轻描淡写,无足轻重。
(四)不同文本间的矛盾。
随着曹植人生际遇的变化及其人格方面的成长,其作品亦可相应分为前后两期,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文本间自会有许多冲突,本文所谓不同文本间的矛盾是指同一时期不同文本间的矛盾。
比如,黄初时期,曹植作品中的矛盾最多。他一面对曹丕歌功颂德、感恩殆尽,一面又在其他作品中撕破这一假象,有时他对曹丕的感恩赞美与批判怨愤甚至充斥于一篇之中(《责躬诗》、《玄畅赋》等)。又如,他一面翱翔仙域,一面用“仿佛见众仙”(《升天行》其一)暗示其虚妄,有时又直接点出“虚无求仙列,松子久吾欺”(《赠白马王彪》)。再如,他一面反复提醒自己“妄言”、“淡泊”、“守身”(《苦息行》、《桂之树行》等),一面又在作品中不停地发牢骚,有时言辞相当激烈(如《圣皇篇》),等等。
而太和时期,曹植不同文本间的矛盾现象反而减少,主要体现在自信才能卓荦而无缘报国、一片赤诚却不被信任、远身自守但无法抛弃家国责任等方面。《南国有佳人》中形象、品性稀有的佳人,却遭遇时俗鄙薄,而佳人的痛苦忧心,某种程度上讲,源于她对世俗理解、肯定的渴望。《美女篇》则相反,美女的孤独处境源于她因慕高义而对时俗的拒绝,因而美女之美与其处境的不协调在于她的价值定位与时俗对她的欣赏追求的错位。前者因外界不欣赏而被动地处于孤独的处境,后者则因清醒地看到与时俗的不同而主动选择了孤独的处境。这两个文本的矛盾正是此期曹植内在矛盾的具体体现。
在建安文人群体中,没有谁像曹植一样作品中充满如此多的矛盾,同一文本和不同文本间的矛盾错综呼应,其间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或是造成曹植作品“骨气奇高”的原因之一。基于前文具体文本的分析,下文力图透视曹作“矛盾”现象后的“自我概念”、人格。
二、“矛盾”现象后的自我概念、人格
本文以为上述矛盾现象,折射出曹植极强的自我中心意识,此心理在《斗鸡篇》已显露无遗,而在《汉二祖优劣论》中,他认为“建武之行师也,计出于主心,胜决于庙堂”,把不朽功业之建立全归功于光武一人,更是自我中心的个人英雄主义了。他前后所写诸多关涉古代帝王的赞作,突显的无不是个人的文治武功。就是他许多作品的构图方式亦多以特写形式勾画,对象几乎占据了整幅画面,比如《斗鸡篇》、《名都篇》等,曹植对特写方式的喜爱,或正是自我中心意识的无意识流露。而其对作品对象任由己心的支配与驾驭,如前文所举“意象矛盾”与“结构矛盾”中的相关内容,亦是其自我中心的表现;而那些同一文本、不同文本间矛盾所揭示的他任由己心的评论、怨愤、激切等,亦是其自我中心的体现。而无论是他对对象的支配、驾驭,还是他的激切、怨愤,都表现出一种不顾现实的任性作风,此作风贯穿曹植的整个作品与人生。下文将以此为线索,由作品中的矛盾现象延伸到曹植一生重要行迹,以透视其自我中心后的自我概念。
(一)自我概念的早期习得。
曹植的自我中心意识根源于他的自我概念。社会心理学认为,“自我概念”是人们对“自己是谁”这一问题的了解,其基础是人们的“自我图示”,它是“我们组织自己所处世界的心理模板”,它“影响我们如何感知、回忆和评价他人和自己”。自我概念“不仅包括我们是什么样子的自我图示,还包括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样子——我们的可能自我”。自我概念的形成受基因的影响,但社会经验的影响亦不可忽视,“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形成的社会同一性、我们和别人比较、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其他人如何评价我们、周围的文化”等都会对自我概念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7](p30)
对曹植而言,其自我概念的核心是才华超众、堪当大任、建功立业、流芳后世。其自我概念的形成有多种因素,比如遗传基因、曹操领袖形象影响、父母及统治集团臣僚的宠爱赞美、儒道思想的影响、时代任侠风气的激荡等。曹植由此多种因素综合而出的自我概念具有极强的“高效能自我感,”①“人们关于他们自身能否成功的信念对于自我调节过程有着极大的影响。班杜拉(1986,1989)把这些信念称为自我效能感。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人认为他们有能力获得成功、克服困难、达成目标。”[8](p118)这使他的“现实自我”往往有理想化成分。
此概念的早期习得多以他人的评价为参照,因此为确定其自我概念,曹植常有爱展示自我的一面。少年时他面对曹操的疑问,“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9](p416)之言,登铜雀台时的“援笔立成,”[9](p416)邯郸淳面前恣意表演,以致“座席默然,无与伉者”[9](p449)等,无不是对其才华的炫耀,也许某些事件含有一定的政治意图,但“大多数人喜欢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受人喜欢、有天赋的等等。通过向别人证明自己拥有这些积极的品质,他们就能更好地说服自己,这反过来也让人们的自我感觉更加良好”。[8](p142)这种自我展示,在曹植前后期作品中都有相当充分的表现。当然,后期作品中的自我展示也有说服自己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或是在困境中激励自我,同时希望获得建功立业的机会。
因为对自我概念的确认,他随之而来的高度自信在行为上往往表现出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不顾现实的任性狂傲作风,即史家所评“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9](p416)
(二)遭遇冲突的自我概念。
自我心理学认为,“即使是心理调适最好的人也常常受到与自我概念不一致的经验威胁。”[8](p287)曹植早期习得的自我概念随着他与外界的冲突而逐渐遭受挑战,这一挑战最早似来自邢颙,②邢颙在做曹植家丞时,“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魏书·邢颙》)司马孚为文学掾,“植负才陵物,孚每切谏,初不合意,后乃谢之”。(《晋书·安平献王孚传》)其次是司马孚,只是因其“自我概念与经验的不一致程度不高”,所以来自经验的挑战并不能威胁他的自我概念。
真正影响他自我概念的是建安二十一年至曹操杀杨修一段时间的经验。二十一年,太祖以植妻衣绣而赐死一事,某种程度上应是对曹植的一个警告。建安二十二年,太子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虽然曹植阵营的支持者对他美言有加,但支持曹丕的一方,人数多,地位高,多强调儒学、礼法,如荀彧、荀攸、贾诩等,[10]他们对曹丕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讲即是对曹植自我概念的否定。
太子之争以曹植的失败告终,应对曹植的自我概念产生很大影响。立太子之后的同年,发生了司马门事件。[11]论者多释之为本能冲动,而本文以为,排除可能的政治阴谋影响外,此乃自我概念受到巨大挑战下的焦虑行为,“当自我与经验之间的不一致变得十分明显时,个体的防御过程会过分歪曲和否认经验”,[8](p287)并通过采取消极的自我破坏活动获得心理平衡。建安二十三年,“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植称颂功德,发言有章,左右瞩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闲嘘唏。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信不及也”。[9](p454)此段文字绝非幼稚的炫耀,相反,这一抢风头行为,恰恰说明其自我概念深受外在经验影响,他需要凭借才华重新获得父王与群臣的赞美,从而缓解内心的焦虑,但结果并不如愿,人人“皆以植辞多华而诚信不及”反更加重其内心的焦虑。建安二十四年,杨修被杀,“植益内不自安”,[9](p417)一个“益”字点明曹植自太子之争以来的焦虑感。因此,此时的任性多是本能防御或内心焦虑的表现。
(三)自我概念的固化。
尽管建安二十一年至建安二十四年,曹植的自我概念与经验的不相容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焦虑,但此后的黄初、太和时期,虽然他备受压制,但其自我概念则较少遭遇内在的冲突,不仅如此,其早期习得的自我概念反更加牢固。①与其早期主要表达欲建功立业的热情相比,曹植晚期(主要是太和时期)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比如他深信自己的军事才能,自称“不必取孙武而暗与之合”(《陈审举表》),“若可得挑致,则吾一旅之卒足以敌之矣”(《与司马仲达书》);他深信自己的政治眼光,“若有不合,乞且藏之书府,不便灭弃。臣死之后,事或可思”(《陈审举表》);他深信自己的王佐之能,“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他深信自己的文武双备,“今臣文不昭于俎豆,武不习于干戈”(《自试表》)等。其主要原因或在于:
第一,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救曹仁,呼有所敕戒”,[9](p417)尽管曹植因醉不能受命,但可见曹操并未对他失去宠爱和厚望;第二,曹操在立嗣问题上直到临死前数月仍是动摇不定,[12]曹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9](p416)之言,陈矫“爱子在侧,彼此生变”[9](p479)之论,无不表明曹操最后的安排可能是立曹植为嗣。这些充满关爱与肯定的经验,对曹植自我概念的再度确定应有重要影响。第三,在王位之争上,曹植或有一种道德优势,尽管我们无法相信所谓的自污以让,但他以“不见袁氏兄弟乎”[9](p416)拒绝曹彰是极可能产生这样的优势感的。第四,太和时期曹植身份转为王叔,长者角色与家族使命对其自我概念的固定化或有影响。第五,曹植的自我概念与儒家思想相结合,一旦内化为自我选择标准,就表现出对天下的责任承当、舍我其谁的儒家人格,而随着其儒家人格的确立,以及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欲通过建功立业以达到生命超越的强烈追求也可能强化这一概念。
而由此自我概念而来的任性作风亦和早期保持了一致,比如黄初时他不顾礼制上表请求祭祀先王、傲慢皇使等。备受压制时,他一面歌功颂德、感恩殆尽,而另一面,则以不同方式,或隐或显地控诉曹丕对他的不公与刻薄,指责小人对他的陷害;他一面提醒自己淡泊妄言,却又在作品中不停地发牢骚,而不顾曹丕怎么想。这种任性的作风即使太和时期也有充分表现,且不说他给曹睿上的诸多书、表中的激切之言,即使看看他毫不客气地指斥边将“忘其皮之为虎也”(《陈审举表》),指责司马懿“足下曾无矫矢理论之谋,徒欲候其离舟,伺其登陆,乃图并吴会之地,牧东野之民,恐非主上授节将军之心也”(《与司马仲达书》),亦是不言而喻,尽管这同时说明他对曹魏政权的认同与自觉的宗族责任感。
综上而言,曹植的任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式、内涵,建安初中期是恃傲的任性,建安后期是焦虑的任性,黄初时是抵抗、挣扎的任性,太和时是为了宗族、国家利益的任性。这种任性根源于其自我概念,而随着其自我概念的曲折定位,曹植逐渐摆脱自我中心的狭隘而渐趋为一种更为高尚、开阔的人生境界,曹植青年时期的儒家、游侠等思想倾向发展到太和时期,与其宗族情感相交融而最终形成其儒家人格。
三、曹植儒家人格的阐释接受
曹植是一位经典作家,其经典地位之形成,亦与后世对其人格精神的挖掘相关。在文学接受研究领域,对作家人格阐释接受的研究尚需重视。下面承上文所论,以唐前资料为主,探讨曹植儒家人格的阐释接受。
首先,本文不赞同曹植具有“儒道互补”人格的说法,因为人格是指“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人际过程,”[13](p3)曹植思想中有道家的影子,但他并没有形成道家思想影响下的稳定行为方式。曹植的自我概念与其儒家思想、宗族情怀等相结合,致使功、名成为他一生的心结,其儒家人格亦伴随着他“自我概念”的曲折定位而最终确立,岁月的打磨,使他早期的儒家思想内化成了稳定的人格结构,这是曹植生命的升华,是他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然而,在南朝梁代萧绎之前,似乎没有人明确指出此点。综观现存资料,当时对曹植的看法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批评其道德。
建安时期,杨修称曹植“体旦、发之资,有圣善之教,”[9](p418)在当时“太子之争”的背景下,来自曹植党羽的评语不免有太多的政治色彩,而从奉崇儒学的汝颍人士对曹丕的支持看,对特立独行的曹植他们并不喜欢。而当时的史书,如《典略》称“植后以骄纵见疏,[9](p419)对曹植的品性颇有微词。其后,曹睿亲自下令整理曹植作品,但其诏书亦言“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14](p101)“克己慎行”与其前的“骄纵”构成对比,但在曹睿看来,那是弥补前阙的行为,而并非一种高尚的人格特质。西晋初年,陈寿在《三国志·陈思王植》中亦批评他“然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9](p431)直到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亦言“曹植悖慢犯法。”[15](p237)曹植年轻时的一段公案对人们对其道德的评价影响深远。
第二,同情其遭遇。
曹魏、两晋对曹植的同情主要表现在对曹魏亲异性疏公族政策的反思,如陈寿评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易岁;骨肉之恩乖,棠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9](p441)晋段灼《陈时宜》言:“而魏法禁锢诸王,亲戚隔绝,不祥莫大焉。”[14](p698)不过,鱼豢认为,“假令大祖防遏植等,在于畴昔,此贤之心,何缘有窥望乎?”[9](p431)则把曹植的悲剧归因为太祖的失误,此评既跳出对曹植悲剧个人品格的归因角度,亦在对曹魏宗族政策的反思之外,别开新解,侧面表现出对曹植命运的同情。此后东晋末年起有关曹植制作梵呗的故事,以曹植对宗教的回归,亦侧面表达了对其抑郁一生的同情。而到了谢灵运言“公子不知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16](p111)方从曹植个体层面揭示其生命的悲苦,明确表达出对曹植的同情之心。
第三,赞美其才华。
曹植最早以《登楼赋》赢得曹操重视,其才名在曹操时代即已确立。此后,人们对曹植才华的称赞不绝于耳。如陈寿赞其“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9](p431)鱼豢《典略》言:“余每览植之华彩,思若有神。”[9](p431)《魏氏春秋》引钟会论高贵乡公曰:“才同陈思,武类太祖。”[9](p100)直到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有关曹植七步诗的故事,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4](p95)等,都无一不着眼于对曹植才能的赞美。晋傅玄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军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14](p500)曹植的才华可大致归入“学才”类。对曹植文学才华的赞美,与魏晋时期的才性之论相关,亦与此期文学自身发展的特点有联系。
第四,欣赏其风流。
此点尤其表现在梁陈以后,影响以至于唐代。蒋寅在《主题史和心态史上的曹植》中言:“沿着历史时代回溯,我发现对青春主题的全面书写,竟然要到曹植才开始,其标志就是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最早的描绘少年游乐的作品。”[17]但在梁陈北朝的诗文中,曹植则成为文士诗文中游乐的主角,成为贵族风流浮荡生活的象征。比如“季子聊为戏,陈王欲骋才,”[18](p120)“开轩望平子,骤马看陈王,”[19](p365)“陈王金被马,秦女桂为钩”[20](p2333)等。更有甚者,如庾肩吾父子的诗文往往改变历史上丕、植的矛盾关系,虚构了二人间和谐共处的场景气氛,借建安时期曹丕、曹植与建安诸子的关系来比附君臣的和谐关系,表达他们对萧纲、萧绎的赞美与感恩之情。
由上分析看,从曹魏至两晋南北朝,人们对曹植深厚的儒家情怀与其高尚的人格尚少关注,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比如政治因素的影响、玄学思潮的影响、文士生活审美情趣的影响等,但正因对曹植道德精神关注的相对缺乏,此期对曹植诗文的解读、借鉴等更多集中于其诗文的美丽,曹作丰富深刻的内涵未得到充分挖掘,其社会层面的影响受到了局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曹植作品的解读,受限于对曹植其人的解读。
但唐以后对曹植作品道德层面的解读不可能突然而来,唐前是否已经蕴含了对曹植人格精神的发现呢?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爬梳,可以发现,曹植人格精神的发现与挖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陈寿的《三国志》,在《陈思王植》传中,他选入曹植的《求自试表》、《求存问亲戚表》、《陈审举表》等,借曹植之表,来展示曹植忧国为君的忠诚情怀及其政治思想与政治远见,表达了对曹植的同情与理解,这在曹植其人的阐释史上难能可贵。其后裴松之注《三国志》,又大量引入史料,较完整的展现了太子之争的过程及曹植人生、心境与人格成长的变化,可以说是对陈寿观念的具体化与补充。
江淹《杂体三十首》有拟曹植作《陈思王赠友》,他选择曹植的赠友诗作为曹植诗歌的代表之作,拟诗言:“君王礼英贤,不吝千金璧。……眷我二三子,辞义丽金雘。延陵轻宝剑,季布重然诺。处富不忘贫,有道在葵藿。”[21](p97)表达了曹植响应曹操的人才政策,对友人之才的欣赏、对友人的鼓励,展现了一个心怀天下、礼敬人才、知情重义、风流儒雅的才王形象。拟诗刻画的是建安时期的曹植形象,此并非曹植形象的主要方面,但它一反先前曹植被压迫的政治苦情形象,突出了曹植精神中的积极内容,此在曹植人格的阐释接受上具有重要意义,
而梁代萧绎则第一次明确指出曹植作品中的儒者之义,其言:“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也。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谴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遍观文士,略尽知之。”[22](p966)他认为曹植是一个文士,但和一般文士相比,他悉通儒家之义,虽非儒者,而实为儒者。其又言“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22](p966)这就指出曹植其文所透视的人格特质,是以儒家精义为核心的。他对曹植文士精神的揭示,为后来者走出曹植形象接受的误区指引了方向,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曹植的人格精神才在中国文学史上放出光芒,此与宗教界把曹植拉入宗教的阵营相比,其对后世的影响更远亦更有价值。
其后,隋代王通言:“子曰: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23](p54)“谓陈思王善让也,能污其迹,可谓远刑名矣。人谓不密,吾不信也。”[23](p142)这是第一次结合太子之争的历史来评价曹植的放纵行为,与历来人们针对太子之争着眼于对曹植道德、能力的批评与对其悲剧命运的同情相比,王通则看到了曹植放纵行为背后的至德。杨树达《论语疏证》言:“《论语》称至德者二,一赞泰伯,一赞文王,皆以其能让天下也。此孔子赞和平,非武力之义也。”[24](p179)德中至德是能以天下让,而让天下是为了天下的和平。王通上承萧绎所论,进一步明确曹植“悉通儒者之义”,实乃保身齐家治国之义。正是基于对曹植人格精神的深刻理解,王通知人论文,他指出:“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23](p54)既盛称曹植之德,亦高推曹植之文,在钟嵘、刘勰之外,对曹植作品的风格特征有了进一步的挖掘。隋以后,虽然人们对曹植其人之接受不脱离上文所言前四种,但经由陈寿、裴松之、江淹、萧绎、王通等的发现、挖掘,对曹植深厚的儒家情怀及其人格魅力的阐释,逐渐成了曹植及其作品阐释的主流,曹植与其作品也逐渐深入到民族的灵魂,而其悲剧命运亦在宫廷之争的内容外,拥有了更深厚的意义。
[1]胡亚敏.叙事学[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4]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三曹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清)吴淇撰,汪俊.六朝选诗定论[M].黄进德,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9.
[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张智勇,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8][美]乔纳森·布朗.自我[M].陈浩莺,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9](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0]曹道衡.从魏国政权看曹丕曹植之争[J].辽宁大学学报,1984,(3).
[11]张可礼.三曹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5.
[12]俞绍初.曹植生平若干事迹考辨[J].郑州大学学报,1982,(3).
[13][美]Jerry M.Burger.人格心理学[M].陈会昌,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14](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5]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6]黄节注.谢康乐诗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7]蒋寅.主题史和心态史上的曹植[J].西北大学学报,2010,(1).
[18](陈)徐陵撰,许逸民校笺.徐陵集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0]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1]俞绍初,张亚新校注.江淹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22](梁)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3]郑春颖译注.文中子《中说》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4]杨树达疏证.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邓年
I209
A
1003-8477(2016)10-0120-06
王津(1976—),女,郑州轻工业学院教师,文学博士。
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曹植与其作品经典化研究”(15YJC751040)阶段性研究成果,2015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唐前曹植其人接受研究”(2015-QN-539)研究成果,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基金资助项目“元前曹植接受史”(2014BSJJ099)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