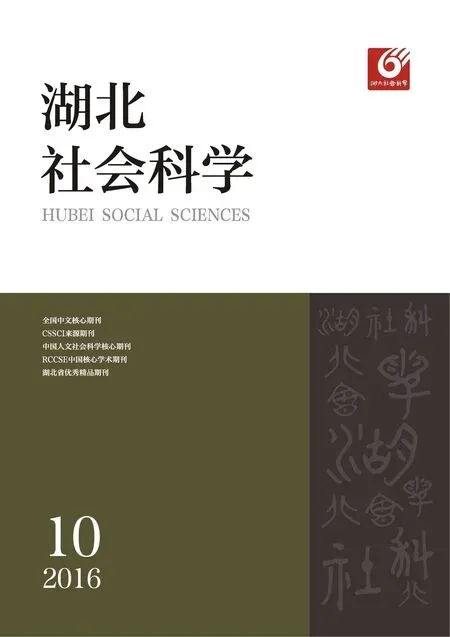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发微
2016-03-14刘玉堂曾浪
刘玉堂,曾浪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发微
刘玉堂,曾浪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在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中,范戊以白玉微圜之形不足以制礼器为喻,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礼乐教化与楚国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旨在批评楚王不谙治道。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相互参验来进一步解读此简文,经考证简文中楚王的真实身份应是楚怀王,楚国人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经济是“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应”,“君人”的安危与是否爱民、尚贤好士、隆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通过解析范戊提出“三回”之论,准确把握楚国精英阶层的治国理政思想。
《君人者何必安哉》;上博简;楚国;楚怀王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中有一篇编者题为《君人者何必安哉》的文献,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69~188页。记载楚王与臣范戊的一段对话,读来意味深长。
范戊曰:“君王有白玉三回而不戋,命为君王戋之,敢告于见日。”王乃出而见之,王曰:“范乘,吾倝(曷)有白玉三回而不戋哉?”曰:“楚邦之中有食田五贞,②“贞”,单育辰释读顷。张崇礼以为读“畛”。见单育辰:《占毕随录之七》,复旦网2009年1月1日;张崇礼:《释〈君人者何必安哉〉的“贞”》,复旦网2009年1月11日。竽瑟衡于前。君王有楚,不听鼓钟之声,此其一回也。珪玉之君,百贞之主,宫妾以十百数,君王有楚,侯子三人,一人杜门而不出,此其二回也。州徒之乐,而天下莫不语之,先王之所以为目观也,君王龙(恭)其祭而不为其乐,此其三回也。先王为此,人谓之安邦,谓之利民。今君王尽去耳目之欲,人以君王为所以嚣,民有不能也,鬼无不能也。民乍(诅)而思之。君王虽不长年,可也。戊行年七十矣,言不敢睪身,君人者何必安哉。桀、受(纣)、幽、厉戮死于人手,先君灵王乾谿云尔,君人者何必安哉。”③隶定释文参考了曹方向:《上博简所见楚国故事类文献校释》,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5月。
范戊进谏楚王,通篇以“有白玉三回而不戋(剗)”④关于“有白玉三回而不戋”,学者有很多讨论。诸家说法可参见米雁:《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综合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为喻,耐人寻味。而要准确理解范戊的旨意,必先释“白玉三回而不戋(剗)”。白玉自不用解释,其中“回”,当指微圜之形。《周礼·典同》说:“回声衍”,郑玄注:“回谓其形微圜也,回则其声淫衍无鸿杀也”。周礼认为回形之钟不符合规范,所谓“白玉三回”,应指尚未成为礼器的玉。按《考工记·玉人》所说:“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其中“射”即为剡,①孙诒让云:“说文刀部云:剡,锐利也。戴震云:琮八方,言射者则角剡出。黄以周云:射即玉人大琮射四寸之射,案戴黄说是也”。见《周礼正义》卷三十九,民国二十年湖北篴湖精舍递刻本。而剡、戋(剗)声近义同。又《庄子·马蹄》云:“白玉不毁,孰为珪璋”。琮与圭、璋均为国之重器,既用于祭祀,又用于宾客朝聘。②参见《周礼·典瑞》《仪礼·聘礼》。《白虎通德论》说:“琮以起土功发聚众何?琮之为言圣也,像万物之宗聚圣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发众也……内圆象阳,外直为阴,外牙而内凑,像聚会也,故谓之琮。后夫人之财也”。故知范戊以白玉微圜之形仍不足以制成礼器为喻,批评楚王不足以聚众治国。而此简文的关键,在于通过解析范戊提出“三回”之论,准确把握楚国精英阶层的治国理政思想。
一、论礼乐与楚国社会经济
范戊说“楚邦之中有食田五贞,竽瑟衡于前”,可谓楚国士阶层严格遵循周礼生活标准的真实写照。东周时各阶层的经济生活大约是“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国语·晋语四》)“食田五贞”看来是当时楚国士这一级别的具体生活标准。《礼记·曲礼》有言:“士无故不彻琴瑟”,楚之士君子“竽瑟衡于前”,这并非仅仅是指楚国“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墨子·三辩》)即娱身而已;更在于阐明琴瑟竽笙之声蕴含着深刻的治民理念:“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礼记正义》卷三十九)
(一)琴瑟丝声之婉妙哀怨,象征立身廉隅,喻君子不逾越其分。
范戊认为,具有士以上身份的君子要区别于小人(庶人),其义(伦理活动)应优先于利(经济活动)。楚国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严辨义利、恪守廉隅的士人。如令尹子文“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左传·庄公三十年》)陶荅子之妻称赞:“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国也,家贫国富,君敬民戴,故福结于子孙,名垂于后世”。(《古烈女传》卷二)又如大夫申包胥,曾顿地血泣于秦廷七日,请得秦师相助,为楚国立下旷世奇功。但当楚昭王返郢,论功行赏时,“申包胥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为诸?’遂逃赏。”(《左传·定公五年》)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中有一篇《邦人不称》的文献,所记楚人叶公子高的精神境界也十分相似:“……宁祸,赏之以西畈亢田百畛,(叶公)辞曰:“君王嘉臣之请命,未尝不许。”辞不受赏。命之为令尹,辞。命之为司马,辞。曰:“以叶之远,不可畜也,焉质为司马?”不取其制,而邦人不称还焉。就王之长也,赏之以焚国百畛,故为叶连敖与蔡乐尹,而邦人不称能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战国策·楚策》所记与此大致相同:“昔者叶公子高,身获于表薄,而财于柱国;定白公之祸,宁楚国之事……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叶公平定白公之乱有大功,拒绝封赏西畈亢田百畛,以为勤王是臣下本分,不应恃功求赏,足见其境界之高。当时蒙榖身上也体现出这种操守:“吴与楚战于柏举,三战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属,百姓离散。蒙榖给斗于宫唐之上,舍斗奔郢曰:‘若有孤,楚国社稷其庶几乎?’遂入大宫,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榖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榖之功,多与存国相若,封之执圭,田六百畛。蒙榖怒曰:‘榖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岂悉无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无冒。故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蒙榖是也”。(《战国策·楚策》)在国家危亡之时,士大夫均不避凶险,追随于楚惠王左右。而蒙榖尤其难得,视楚国之典如生命。当楚王要封赏时他却坚辞不受,与申包胥同样“不为爵劝,不为禄勉”。
岂独士人,在楚国,即便是“小人”(庶民),也不乏舍生取义,为国纡难的情怀。《庄子·让王》记载过一则故事:“楚昭王失国,屠羊说走而从于昭王。昭王反国,将赏从者,及屠羊说。屠羊说曰:‘大王失国,说失屠羊。大王反国,说亦反屠羊。臣之爵禄已复矣,又何赏之言?’王曰:‘强之!’屠羊说曰:‘大王失国,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诛;大王反国,非臣之功,故不敢当其赏’”。屠羊者,在吴人入郢后拼死护卫楚昭王,昭王返国后却拒绝封赏。我们知道当时“小人”(庶民)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乐其乐而利其利”,(《礼记正义》卷六十)其理财活动一般情况下优先于伦理活动,而家庭伦理承担也优先于社会伦理承担——即无论其地位身份,还是其自身能力,均难以承担超出他们日常生活的负担。市肆屠羊者遭遇战乱,“走而从于昭王”,有功不受赏。庄子或其后学援引意反讽战国时代人们多利欲熏心,目的是宣扬道家“轻物重身”的思想。这自然不足以表明楚国庶民平时都能以非正常的“清高”去放弃自己的基本利益,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①虽然史书有“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的记载,但属于特殊情况。见《淮南鸿烈解》卷第二十,四部丛刊景钞北宋本。但具有士大夫情怀者也并非孤例。
(二)竽笙箫管声音繁杂,象征揽然积聚,喻君子合会而能聚其众。
楚灵王时,大夫伍举就明确指出要“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国语·楚语上》)认为君上的娱乐消费必须符合聚众同乐的要求。长时间居住在楚地的荀子,晚年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历史的思考写出《富国》,对伦理与经济的关系这一永恒命题进行了深刻地阐述:“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溼、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荀子揭橥出人类应能聚合,其伦理观念自然形成于经济活动之中,人群的消费只有以伦理界限为准,才能利大于弊。“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于是当立名分以确保人类的利益。伦理因素在经济活动中要有其界限,只有满足人类合理的欲望,限制其不合理的欲望,才能让经济活动“明仁之文,通仁之顺”——即不同类别人都能得到合适的位置,从事合适的经济活动养活自己及家庭。如年老者虽力不及人,但其可树立典范,传承知识,故应予以尊敬和照顾,对其经济消费的供应更不能怠慢,如享受衣帛食肉,不负戴于道路等。又“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即无论是吉庆的场合,还是遭遇丧荒之事,音乐都通人之性情。“故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喜乐之文也”,(《荀子·礼论》)人们通过“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礼记·礼运》)唯其如此,方能“乐和民声”,(《礼记·乐记》)因为合理的经济分配会促进伦理关系的融洽,而丰富的经济活动也将在融洽的伦理关系中得到保护。当时楚人已充分认识到经济与伦理关系的重要性。
范戊批评楚王“不听鼓钟之声”,实有深意。楚国历代一直保持着优秀的世子教育传统,即申叔时所说的“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其志……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国语·楚语上》)楚地出土大量极具特色的乐器,反映出楚人丰富的音乐文化。说国君不能沉溺于鼓钟(俗乐及个人娱乐与消费),并不意味着忘记乐的功用。楚国尽管地处南方,也同样受到周礼的熏陶。现存较早的楚国青铜器多为乐器,如现藏日本泉屋博古馆的三件西周中晚期的楚公钟,形制与西周中晚期周人甬钟类同,策鼓纹表明已使用第二基音,其后不久楚地的甬钟都出现了调音槽。②参见袁艳玲:《楚国早期青铜器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进入东周,在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曾出土过26件王孙(诰)钟,其铭文为:“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孙(诰)择其吉金,自作龢钟。中翰且扬。元鸣孔諻。有严穆穆。敬事。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惄于威仪。弘恭舒迟,畏忌趩趩。肃臧御,闻于四国。恭厥盟祀,永受其福。武于戎功,诲不飤。简简龢钟,用宴以饎。以乐诸侯、嘉宾及我父兄、诸士。皇皇熙熙,万年无期。永保鼓之”。与此毗邻的10号墓出土黑敢钟的铭文:“黑敢择吉金,铸其反钟。其音赢少则汤,龢平均諻。灵印若华,批诸嚣圣。至诸长籥,会平仓仓。歌乐自饎,咸君子父兄。千岁鼓之,眉寿无疆”。③两处铭文祥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编:《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群》,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140~179页、第257~288页。可以看出,钟作为重要的礼器,蕴含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即在上位者在祭祀时“有严穆穆,敬事”,要“惠于政德,惄于威仪”;施政治民时应“弘恭舒迟,畏忌趩趩”,宽裕待民,祗惧敬慎;于诸侯国,应由钟鼓之声“闻于四国”、“武于戎功”,联想到如何处理好复杂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治乱持危,朝聘以时。而“用宴以饎。以乐诸侯、嘉宾及我父兄、诸士”、“歌乐自饎,咸君子父兄”更是表明钟鼓之乐能调和伦理关系,有助于经济活动的良好运行。这与周礼所言基本一致:“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周礼·春官宗伯》)故知楚王亦有听鼓钟之制度。由此,不禁使人想起楚庄王即位之初的一则轶闻:“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史记·楚世家》)良臣忧虑,冒死以谏,望庄王罢乐听政。楚庄王觉醒后痛罢淫乐,明国君之分。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庄王既成》所记与此相关:“庄王既城无射,以问沈尹子桱曰:‘吾既果城无射,以供春秋之尝,以待四邻之宾客,后之人几何保之?’沈尹固辞。王固问之。沈尹子桱答曰:‘四与五之间乎?’王曰:‘如四与五之间,载之专车以上乎?抑四航以逾乎?’沈尹子桱曰:‘四航以逾’”。①“专车以上”指晋国;“四航以逾”指吴国,后吴人果然侵楚入郢。见李学勤:《读上博简〈庄王既成〉两章笔记》,简帛研究网,2007年7月16日。庄王罢去淫乐,并非不听鼓钟。相反,他还铸造无射钟用于春秋祭祀,②鼓钟用于祭祀,在先秦颇多证据。如《诗经·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庸鼓有斁”;《诗经·楚茨》:“礼仪既备。钟鼓既戒……鼓钟送尸”。以及接待诸侯国宾客。③鼓钟用于宾客,在先秦文献中颇多证据。如《诗经·宾之初筵》:“宾之初筵。左右秩秩……钟鼓既设。举醻逸逸”。不违背礼制的同时,与邻国交好,为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故当庄王询问楚国的稳定发展可以持续多久时,沈尹子桱非常准确地预测在四五代之间。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何况一个关系复杂的大国!庄王注重礼乐,把经济活动纳入伦理界之正轨,无愧为楚国历史上的贤君明主。
身为国君却“不听鼓钟”,在周代礼崩乐坏以来已有先例,晋昭公就为此受到国人的批评,与此相关的内容保存在《诗经·山有枢》中:“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史官认为这种不听鼓钟的实质是“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将以危亡。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可见,范戊特意提出“听鼓钟之声”的问题,实际是希望楚王要修道正国,从而与民同乐,警惕邻国相侵。这番道理,孟子说得更直白:“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这里孟子说的是君王“不与民同乐”的严重后果,继而又说到君王“与民同乐”的积极效应:“‘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若君王不“与民同乐”,则无法真正养民、爱民,更不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尤其当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稷与君王都会有危险;若君王“与民同乐”,则能保障民众社会生活的稳定,通过发展经济以满足人们合理的消费欲望,从而实现理想的王道。孟子这段一反一正的论说与范戊所谏不谋而合。
二、论楚王宫内之治
周代卿大夫之“家”、诸侯之“宫”都有相当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无论何种活动,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记·曲礼》)即便是在普通家庭生活中,也有较为严格的职能区分:“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紝,多治麻丝葛绪綑布縿,此其分事也”。(《墨子·非乐上》)这种严格依性别区分内外职能的传统其实有着经济学上的考量,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曾指出:“一个有两种性别的、有效率的家庭,就会把妇女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家庭部门,而把男子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市场部门。如果男女的时间能从不同的组合中以同样的比率完全相互替代,那么,无论是男人还是妇女,都会在一个部门中实现完全专业化。只有男人或女人的居民户,其效率就较低,因为他(她)们不能从比较优势的性别差异中获益”。[1](p51)加里从现代经济学角度揭橥出的这种关于家庭男女职能分工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周代乃至古代中国的状况,楚国也不例外。
先秦时期,女性早在结婚之前就得到良好的家庭伦理教育和职能培训。所谓“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紝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礼记·内则》)即有利于这种家庭职业专业化的形成。“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礼记·昏义》)可见无论是士子庶民还是天子诸侯,都应当遵循内外别治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影响深远。
前引上博简中记范戊对楚王说:“珪玉之君,百贞之主,宫妾以十百数”。其中楚国的“珪玉之君”相当于卿大夫级别,但因楚县多为楚国灭他国后所置,大多规模仍依原诸侯国之旧,所以有宫妾十百数也不足为奇。按周礼规定,“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礼记·曲礼》)其卿大夫自然也有妾。楚竹书中的“宫妾”当指女君(珪玉之君正妻)的从属,①《礼记·丧服小记》:“妾从女君而出”,郑玄注:妾为女君之党。即那些能够接幸“珪玉之君”且地位较低的女性。他们实际上也在“珪玉之君”的家庭中从事许多繁重又复杂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以周礼中天子宫闱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宫廷中应当有相当多的女性生产和服务人员:如准备饮食的“女酒”、“女浆”、“女笾”、“女醢”、“女酰”、“女盐”,负责起居的“女冥(幂)”、“女御”,裁缝衣物的“内司服”、“缝人”,教妇学之法的“九嫔”,掌祭祀、宾客、丧纪、帅女宫而濯溉的“世妇”,负责王后之内祭祀祷祠的“女祝”,作为内秘书的“女府”、“女史”等,同时一些专门的机构如“宫人”(掌王之内寝),“内宰”(以阴礼教六宫),“内宗”、“外宗”(掌佐王后祠祭之事)等工作中,也会有女性服务人员的参与。②以上宫廷女性生产和服务人员的记载见《周礼注疏》卷七、卷六和卷十七。正如汉人所总结的:“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丧、祭、宾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寝。颁官分务,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记功书过。居有保阿之训,动有环佩之响。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闺房肃雍,险谒不行也”。(《后汉书·皇后纪上》)由此看来,“珪玉之君”家内有宫妾负责诸方面生产和服务也当在情理之中。而贵为楚王,宫内从事生产和服务的女性自然要多于此数。③《春秋繁露·爵国》所记:“故公侯……一夫人,一世妇,左右妇,三姬,二良人”。见《春秋繁露》卷八,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孟子曾引用礼书描述诸侯的妻妾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情形:“《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孟子·滕文公下》)前引上博简谓楚王“侯子三人,一人杜门而不出”。侯,何也,疑问代词;④侯、何二字声母均为匣母,实为一声之转。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秦客卿造谓穰侯章》:“君欲成之,侯不人谓燕相国”。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策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81页。数字“三”在文言中若无特别所指,实泛言众数,故“三人”即指楚王众妻。⑤《大戴礼记·夏小正》:“妾子始蚕”,子为诸侯之妻。故西汉时皇宫中女性爵有七子、八子等。见《后汉书》卷十上。而“一人杜门而不出”中之“不出”,则实有深意。前文已论说周代有“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传统,这说明对于家内(宫内)妇女来说,“不出”才最符合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规范:“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礼记·内则》)又“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记·曲礼》)”,且“教令不出闺门,事在馈食之间而正矣,是故女及日乎闺门之内,不百里而奔丧,事无独为,行无独成之道。参之而后动,可验而后言,宵行以烛,宫事必量,六畜蕃于宫中,谓之信也,所以正妇德也”。(《大戴礼记·本命》)
按理说“珪玉之君”家庭内有宫妾十百数都应该履行内治(宫妾的地位较低无法干预外政),但楚王众妻中仅有一人遵循履行内治的原则,这意味楚王之妻绝大多数没有履行好内治之职,且不以进贤女、美女为尚。这绝非无端猜测,先秦文献对此记载甚多。楚国历史上就有进贤人的传统,楚庄王的夫人樊姬就讲过这番道理:“……(樊)姬曰:‘妾得于王,尚汤沐,执巾栉,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尝不遣人之梁郑之间,求美女而进之于王也;与妾同列者十人,贤于妾者二人,妾岂不欲擅王之宠哉!不敢私愿蔽众美,欲王之多见则娱。今沈令尹相楚数年矣,未尝见进贤而退不肖也,又焉得为忠贤乎!’庄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进孙叔敖”。(《韩诗外传》卷二)《诗经·关雎》也反映了相似内容,意谓后妃、夫人要“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毛诗注疏》卷一)樊姬所说“尚汤沐,执巾栉,振衽席”,实是泛指王宫中诸多事务,这些日常管理和操作同样需要最为熟练和精干的人员。只有不断有新的、优秀的女性服务人员加入,才能促进宫廷这一复杂的经济体顺利地运转。正是因为如此,楚国史官才对贤内助樊姬的评价尤高:“楚之霸,樊姬之力也”。(《韩诗外传》卷二)
依照传统,至少每个家庭妇女必须为丈夫缝制衣物,准备食物。这两件事,自天子至于庶人的家庭妇女皆须履行。而楚王祭祀的食物、衣物,也必须由其妻妾亲自置办。①周代妇女在家庭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非常高。相关讨论见陈焕章原著,韩华翻译:《孔门理财学》,中华书局,2010年8月第1版,第99页。正可谓“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淮南子·齐俗训》)提倡天子、诸侯的妻妾参与经济活动,既考虑到贵为后妃、夫人如果努力劳动,将会激励和引导普通庶民夫妇勤劳稼穑和用心蚕桑,同时也是为确保祭祀之诚:“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礼记·祭统》)楚人观射父就特别强调了这两点,他对楚昭王说:“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刿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天子亲舂禘郊之盛,王后亲缫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摄固者也,若之何其何之也?”(《国语·楚语下》)这无疑表明,作为楚王之妻,管理内宫是主要的职责和本分。《易·家人》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故“牝鸡司晨”,宫内女性如干预外政则是最大的忌讳。范戊批评楚王仅有“一人杜门不出”,即表达了这种深深地忧虑。由此可见,在当时楚人乃至周人的观念中,君王家内事务的规范与否与国家治理的好坏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后世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范戊的旨意是既然楚王之宫内不治,因而不能治国。于此,不难看出楚人对宫内管理与社会治理关系有深刻的认识。
三、论君子小人各有乐处
前引上博简中范戊还提到楚王的另外一个过失:“州徒之乐,而天下莫不语之,先王之所以为目观也。君王龙(恭)其祭而不为其乐”。“州徒”就是州众,春秋时文献明确记载楚国曾设立州,《包山楚简》中也可见战国时楚国封君领州。范戊在此是以州徒代指楚国的基层政权。②徒有众义,如《尚书·仲虺之诰》:“简贤附势,寔繁有徒”。州徒即州众。《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陈,遂入陈,杀夏征舒,因县陈。申叔时谏,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注云:言取讨夏征舒之州。《周礼·大司马》:“乡以州名”,疏云:州是乡之属,从州至比长,故言之属以揔之云。陈伟的《包山楚简所见邑、里、州的初步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此也有论述。
州有州长,《周礼·司徒》中对其职责有较详细的记载:“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灋。以攷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灋亦如之。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丧皆涖其事”。此谓州长之职一般以中大夫担任,负责聚合一州之教治政令。尤其是每年正月州长要对众宣讲一年的政令以及十二教之法,考核本州民众之六德、六行、六艺学习和实践的情况,并劝勉州众要勤苦学习和戮力劳作以增进德行道艺,纠正州民之过错并禁戒之。①《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注疏》卷第三十一。前文已经论及社会伦理与政治、经济具有密切关系,而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楚国的州长之所以尽心尽力地实行其教治政令,正是为此而努力。州长负责“岁时祭祀州社”,即率民众主持春季的祭社,祈膏雨希望五谷丰熟;主持秋季的祭社因百谷丰稔所以报功,且聚集州民读法。这一系列活动都与教化民众以维持社会秩序有关,连节用非乐的墨子都认为保证祭祀是长久以来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为祭祀也,非直注之污壑而弃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众,取亲乎乡里。若神有,则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则此岂非天下利事也哉。’”(《墨子·明鬼下》)“合驩聚众,取亲乎乡里”正是祭祀活动中重要意义之所在。楚人在祭祀活动既非常虔诚,更嘉好亲昵。楚人观射父曾描述祭祀活动中“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的情景:“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帅其子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谗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国语·楚语下》)州长还在春秋二季“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涖其事”。在楚人心目中祭祀礼仪的社会教化功能之显著,由此可见一斑。
州长不仅仅是履行以上职责,还要负责为祭祀和乡饮酒礼准备相关的器物,《周礼·乡师》记载“州共宾器”,其中“宾器者,尊、俎、笙、瑟之属,州长主集为之。为乡大夫或时宾贤能于此州也”(州中提供乐器,这也是范戊举州徒之乐的原因)。聚合民众,在州之序、学中行乡饮酒之礼(明长幼之序,养贤)和射礼(观德行),《礼记·乡饮酒义》已指出其包含的深刻意蕴:“啐酒,成礼也。于席末,言是席之正,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此所以贵礼而贱财也。卒觯,致实于西阶上,言是席之上,非专为饮食也,此先礼而后财之义也。先礼而后财,则民作敬让而不争矣”。通过饮酒之礼,感染大家生发尊敬之心,以发扬贵礼贱财,敬让不争的精神。
正因为乡饮酒礼有着特殊的政教含义,故乐参与的重要性就显得更加特殊,这从其节目设置也不难看出:“设席于堂廉,东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后首,挎越,内弦,右手相。乐正先升,立于西阶东。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相者东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主人献工。工左瑟,一人拜,不兴,受爵……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主人献之于西阶上。一人拜,尽阶,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阶前坐祭,立饮,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众笙则不拜,受爵,坐祭,立饮;辩有脯醢,不祭。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賔,乃降(《仪礼·乡饮酒礼》)”。大意为乐正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继而吹笙之人入于堂下奏《南陔》《白华》《华黍》。笙歌结束后,堂上人先歌《鱼丽》,堂下笙奏《由庚》。其后堂上再歌《南有嘉鱼》,堂下笙奏《崇丘》。接着堂上歌《南山有台》,则堂下笙奏《由仪》。这些诗乐均含有深刻的寓意,比如其中《鱼丽》一篇:“鱼丽于罶。鱨鲨。君子有酒。旨且多。鱼丽于罶。鲂鳢。君子有酒。多且旨。鱼丽于罶。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其主旨在祈望物阜国安,不仅物产多而美厚,且合乎时令。丰美、及时的收获当然预示着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以及君子有嘉美丰富的饮食优待宾客。又比如《南有嘉鱼》讲述君子有酒,不要吝于财要与贤人共同分享。《南山有台》更是表达了君子有丰厚的财力要养贤人,使国家太平和人们安乐长寿健康的理想。最后,堂上下一歌瑟及笙合乐。如乐正歌《关雎》,则笙吹奏《鹊巢》以合之;乐正歌《葛覃》,则笙吹奏《采蘩》以合之;乐正歌《卷耳》,则笙吹奏《采苹》以合之。意蕴十分深刻,如《鹊巢》赞美夫人之德,以辅助君王;《葛覃》强调作为妻子,即使自己地位再高(贵为后、妃),仍然要亲自勤劳从事经济活动(制作葛布、衣服);即使再富裕,仍然要生活节俭。至如《卷耳》,以明“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而《采蘩》、《采苹》皆咏叹“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毛诗注疏》卷一)
这样看来,范戊说楚王“龙(恭)其祭而不为其乐”,实际上是批评楚王忘记了乡饮酒礼中乐教的真实意义。不只是州,州以下的党正也须在“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仍举行乡饮酒礼。当时祭祀蜡神有八,分别是:先啬、司啬、百种、农、邮表畷、禽兽、坊、水庸等:“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蜡祭蕴含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以报答自然的朴素感情,迎猫、迎虎为的是保证粮食的收成。孔子曾教育子贡:“‘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蜡祭乡饮酒之狂欢的意义于此不难想见。
从《君人者何必安哉》中有关“州徒之乐”的内容分析,范戊旨在批评楚王既不明乡饮酒礼之意义,也不明蜡祭时人们需要恣性酣饮,欢乐若狂的道理。荀子说:“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荀子·乐论》)这是因为当时人情醇厚,民众勤劳稼穑,而“州徒之乐”正是用一年劳苦换得一日狂欢,回报一年劳苦。这种狂欢消费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舒缓民众压力,共同分享喜悦和孕育希望。因此,范戊告诫楚王如果“尽去耳目之欲,人以君王为所以嚣”,最后必将得到小人(民众)之诅咒,有损于安邦利民,也就更不用说发展社会经济了。幸好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仍然为楚人后裔所继承,一直到汉代以降,我们还可以从《荆楚岁时记》中看到楚地保留着社日祭祀活动和岁末狂欢的习俗。①“社曰,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十二月八曰为腊曰。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其曰,并以豚酒祭灶神”。“岁前,又为藏彄之戏”。“岁暮,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见宗懔:《荆楚岁时记》,民国景明宝顔堂秘笈本。
四、简文中的楚王考实
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篇中范戊批评的楚王究竟为何人?种种迹象表明,他应该是楚怀王。②有不少学者推测范戊、范乘就是范无宇(恰好传世文献中有范姓人物范无宇),以为事在楚平王、楚昭王之世。相关讨论参见米雁:《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综合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4月。
首先,这与墨家在楚国所遇境况相合。从范戊的批评看,这位楚王是“尚俭弥贫”的典型,但与墨家之道却貌合神离。自墨翟以献书的名义见楚惠王并劝楚国不要攻宋,③“墨子至郢,献书于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寡人虽不得天下,乐养贤人。墨子辞,曰:书未用,请遂行矣。将辞王而归,王使穆贺以老辞”。见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就有墨徒开始在楚国生活。④钱穆先生考证认为墨子晚年死于楚国鲁阳县,其云:“今综述墨子生平,南至楚,见惠王,在四十前。遂仕宋昭公,见逐,当不出五十。其后殆常居鲁。其至齐,见田和,已逾七十。重游楚,见鲁阳文君,则八十外老人。(齐康元至郑康三,凡十一年。)墨子殆终于鲁阳也”。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上海书店,1992年1月第1版,第165页。其后墨家巨子孟胜依附的阳城君参与射杀楚悼王遗体,楚人逐之。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记载有一位墨者田鸠曾到楚国,靠楚王的帮助去秦国见秦惠王。⑤见《吕氏春秋》卷十九、卷十四,四部丛刊景明刊本。钱穆先生认为这位田鸠就是田俅,并推测田鸠到楚的时间在楚怀王之世。田鸠不仅是墨徒,还受学于言神农之教的许行,他与许行同样不能在楚国得用,只好周游诸国。⑥详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上海书店,1992年1月第1版,第320页。战国晚期秦人与法家、墨家之间均有十分亲密的关系,⑦参见何炳棣:《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黄长风讲座演讲,2010年5月13日。见《光明日报》,2010年6月7日。但楚人的文化背景却不能容忍墨道,从屈原在《离骚》中引用历代圣王的史实也可以看出楚人更愿意继承先王之道,学习经典,尊重像荀子这样的大儒。显然楚怀王并无墨家信仰,他的所作所为客观上使得国家和百姓愈加贫困,怀王治下的楚国正如荀子所言:“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诎,而祸乱起。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餧羸瘠于下(《荀子·正论》)”。而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的实验结果,上博简楚竹书的年代在战国晚期,其碳十四测年数据为2257±65年,①参见陈燮君:《战国楚竹书的文化震撼》,《解放日报》,2003年3月11日。大致在楚怀王时代。
其次,简文记载与文献记载楚怀王好“巫音”、“失乐之情”相契。《吕氏春秋》:“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其生之与乐也,若冰之于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吕氏春秋·侈乐》)意即怀王不听鼓钟之乐,听巫音而已,失去乐之情,使民背叛。
再次,简文所记与楚怀王宠信夫人郑袖和南后致使宫内失治相符。据《战国策·楚策》记载:“楚怀王拘张仪,将欲杀之。靳尚为仪谓楚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之无秦也,楚必轻矣。’又谓王之幸夫人郑袖曰:‘子亦自知且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尚曰:‘张仪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爱女而美,又简择宫中佳翫丽好翫习音者,以懽从之;资之金玉宝器,奉以上庸六县为汤沐邑,欲因张仪内之楚王。楚王必爱,秦女依强秦以为重,挟宝地以为资,势为王妻以临于楚。王惑于虞乐,必厚尊敬亲爱之而忘子,子益贱而日疏矣’”。郑袖的软肋被靳尚所击中,即她害怕“秦王有爱女而美,又简择宫中佳翫丽好翫习音者,以懽从之……秦女依强秦以为重,挟宝地以为资,势为王妻以临于楚”。(《战国策·楚策》)而据秦人对楚怀王所作《诅楚文》:“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实戮力同心,两邦若壹,绊以婚姻,袗以齐盟。曰:叶万子孙,毋相为不利。……而兼倍十八世之诅盟”分析,秦楚两国王室的婚姻实际上有四百余年间十八代没有间断。②相关讨论见李开元:《末代楚王史迹钩沉——补〈史记〉昌平君列传》,《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何况不久秦昭王初立,两国即互通婚姻。③《史记·楚世家》:“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郑袖尽管昏惑,应不至于不知此中关节。杀张仪后,秦人又何必继续与楚联姻,不杀张仪岂能阻挡两国婚姻?只能说明郑袖缺乏良好的品行,其在意的不是楚国的安危,而是个人私利:“秦女必不来,而秦必重子。子内擅楚之贵,外结秦之交,畜张子以为用,子之子孙必为楚太子矣”。(《战国策·楚策》)因此,当楚怀王不愿意放走张仪时,郑袖便日夜进谗言,甚至以身逼迫:“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怀王后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战国策·楚策》)怀王为郑袖所欺实属昏惑。然而郑袖非特妒贤妒能,实为贪狠欲利,丧心病狂之人则于史有证:“魏王遗楚王美人,楚王说之。夫人郑袖知王之说新人也,甚爱新人。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郑袖知王以己为不妒也,因谓新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子鼻。’新人见王,因掩其鼻。王谓郑袖曰:‘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袖曰:‘妾知也。’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曰:‘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无使逆命”。(《战国策·楚策》)魏国之女的悲剧,二千余年后读来仍令人背生寒意。“(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史记》卷八十四)作为楚王夫人,应以进贤为己任,郑袖、南后不仅不进贤德,反而卑猥算计;岂独只在宫内作威作福,甚至串谋佞臣逼走屈原,干预国政。这一行为不只是违背“内外之别”的原则,更给楚国带来重大的灾难。怀王宠信郑袖与南后,不能进贤女,正坐实了“侯(何)子三人,一人杜门不出”的记载。反映当时楚国不尚贤好士,亲佞小人的史实。
最后,简文所言与文献所记楚怀王“隆祭祀”、“士民为用之不劝”相若。史载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汉书·郊祀志》)”,又“见士民为用之不劝也,乃征役万人,且掘国人之墓(《贾谊新书·春秋》)”,因役使民众不力(民不乐为所用)竟“掘国人之墓”。怀王不能照顾到和乐之群情,在经济生活上俭天下以满足自己奢欲。这恐怕正是范戊所谓“君王龙(恭)其祭而不为其乐”的真实背景。①至于秦昭王晚年“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反映的是楚怀王之后的楚王在特定时间内因极为重视决定秦楚生死的军事活动,而无意于个人私欲的消费。这与楚怀王“尚俭而弥贫”不宜相提并论。其事见《史记》卷七十九。
此外,简文所言也与文献所记怀王时代的社会背景相吻合。简文之末范戊称“先君灵王乾谿云尔,君人者何必安哉”。则事在楚灵王之后无疑。“先君”一语非仅指上一代君王,其后代均可以称先代君王为先君。如《左传·僖公四年》记载管仲对楚人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是齐桓公时人可称姜尚为先君,先秦文献中类似例证甚多,不具引。且“君人”一语,战国以前较少使用,仅《左传》见之两例,战国以后文献中则多见。在文献中我们发现有关“君人”与“安危”问题的讨论,②传世文献所见,另外一条记载是《说苑·建本》中有引管仲之语:“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只有长期担任兰陵令的荀子阐释得最为精到:“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荀子·王制》)其又说:“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荀子·君道》)“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好利多诈而危。”(《荀子·大略》)是知当时观念中君人之安危与爱民、尚贤好士、隆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中,范戊的三个批评同样反映了君人(为人君者)要爱民、好士尚贤、隆礼的思想。
范戊直谏实为难得,楚国人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应”。(《荀子·富国》)这种思想其实渊源已久:“公叔文子为楚令尹三年,民无敢入朝,公叔子见曰:‘严矣。’文子曰:‘朝廷之严也,宁云妨国家之治哉?’公叔子曰:‘严则下喑,下喑则上聋,聋喑不能相通,何国之治也?顺针缕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实仓廪,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尝有所不受也”。(《说苑·政理》)所谓“严则下喑,下喑则上聋,聋喑不能相通”,意即没有和乐,将使国家上下之情不能相通。这又让我们想起楚昭王时代,自昭王十年吴师入郢,十二年“吳伐我番,楚恐,徙鄀”,(《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楚人已对吴国产生巨大恐惧。等到昭王二十二年时,“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左传·哀公元年》)面对楚国大夫的恐惧心理,唯有子西颇为乐观:“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不知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说苑》卷十三)子西分析吴国阖闾与夫差父子在治国、治军、治民以及生活消费等方面的前后差别,指出吴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楚国,在于以前吴王阖闾能够“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不知旷”,而今吴王夫差“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楚人善于汲取历史的教训,认识到“恤不相睦”,不与民同乐,国将自败。只有君子、小人各得乐处,才能使社会经济得到真正和谐地发展。信哉斯言!
[1][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责任编辑 唐伟
K852
A
1003-8477(2016)10-0103-10
刘玉堂(1956—),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浪(1989—),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