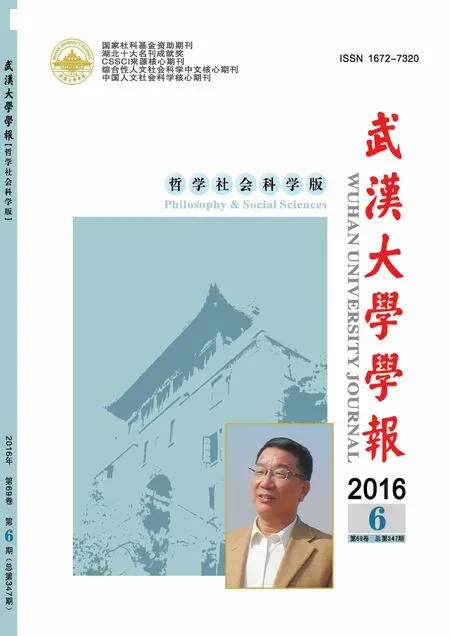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的论争与立法回应
2016-03-13高海
高 海
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的论争与立法回应
高海
对经济学界最早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承包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部分法学学者尚存质疑。梳理并反思经济学界与法学界对“两权分离”论争的三个焦点,可以发现“两权分离”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但是经济学界关于“两权分离”之经营权抵押和承包权归属于成员权的表述尚需修正,法学界部分学者对“两权分离”适用范围以及承包权的解读亦应矫正。简言之,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既是对农用地流转实践的一种发现、提炼,又是今后一段时期引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入股、担保,乃至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等诸项改革的发展主线。
土地承包经营权; “两权分离”; 承包权; 经营权
经济学界最早提出的家庭承包之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是指基于承包与经营两个因素、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解为两个独立的权利:承包权与经营权;承包人享有承包权,规模经营主体享有经营权以及以经营权为客体的抵押权。在经济学界及国务院农村工作部和国土资源部,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者甚多(韩俊,2013:5;陈锡文,2014:12;刘守英,2014:7),而且“两权分离”已经以“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表述,被写进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和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亦要求“界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关系”。但是,在法学界,即使有学者肯认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蔡立东、姜楠,2015:31;李国强,2015:184),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者也不在少数(温世扬,2014:12;高圣平,2014a:155;丁关良、阮伟波,2009:8)。为了更好地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理当梳理经济学界与法学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论争的论据及焦点,并强化法学视角的透析与解读,促进经济学学者、政府官员与法学学者之间的沟通乃至共识的达成。
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论争的论据
(一) 支持“两权分离”的论据
首先,“两权分离”事实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大规模流转即主要是由承包人自己经营的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两权”是合而为一的。但是,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两权分离”的客观事实。“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流转面积已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3.9%*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该比例已达33.3%。参见韩长赋:《土地“三权分置”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新》,载《光明日报》2016年1月26日,第001版。。其中转包土地占流转总面积的47.2%,出租占30.7%,股份合作占6.7%,转让占3.8%”(万宝瑞,2014:4-5)。显然,就普遍被视为发生“两权分离”的转包、出租的比例而言,已达流转总面积的77.9%;如果再加上能否被视为发生“两权分离”尚存争议的股份合作,则高达84.6%。以至有专家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次分离有强烈的社会诉求和深厚的实践基础”*参见王立彬:《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将释放巨大改革红利——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谈土地承包经营权“再分离”》,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9/c_118753978.htm。。
其次,经营权抵押创新论。支持“两权分离”的学者普遍认为,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并以经营权抵押,“有望为解锁农地抵押困局创造最为关键的制度基础。因为经营者到期不能偿还抵押债务,债权人也不能取得承包方的地位,只能是以土地经营获得的农产品收入或地租收入优先受偿”(张红宇,2014:12),“农民失去的也不过是几年的收益,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承包权”(冯华、陈仁泽,2013:2)。显然,上述观点主张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经营权、并以经营权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客体,一旦债权到期债务人无法偿还,也无须拍卖、变卖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主要是通过收取土地流转收益实现债权。这样,既可以消除抵押可能导致农民失地的担心,又能恢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担保功能。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抵押客体还是从抵押权的实现方式看,经营权抵押都不同于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通过拍卖或变卖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抵押权的传统观点,故可将经营权抵押视为农地担保创新论。
再次,保留承包权之农民利益保护论。有学者提出,在“承包农户因担心丧失土地承包权,只得将经营权向熟识的人流转,影响土地的经营效率”的情况下,“对承包权与经营权进行政策上的分离,有利于承包户将承包地放心地流转”(刘守英,2014:7)。“农户对本集体土地的承包权,是他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体现。以土地的经营权抵押、担保或入股,即使经营失利,农户也不会失去土地的承包权”(陈锡文,2014:12)。即认为通过“两权分离”,分割归属于集体成员的承包权与经营主体的经营权,不仅可以消除农民“流转承包地会失去承包权”的后顾之忧,促进承包地流转,而且可以明确规模经营主体的经营权,推进农业经营体系创新,还可以激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增值功能,保障承包人基于承包权享有流转权、收益权、征收补偿权及承包人之继承人的继承权,使承包人可以“带地进城”,增加其财产性收入。
(二) 反对“两权分离”的论据
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利无法分解。有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个完整的民事权利,无法分解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内容也无法界定”(丁关良、阮伟波,2009:6);“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单一的独立的用益物权形态,不是承包权和经营权两者相加,并不存在所谓保留承包权、流转经营权之分离现象”(温世扬,2014:12)。还有学者认为,“‘两权分离’无法在法律上得以表达。流转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是土地经营权。转让的法律后果是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认为流转的仅是土地经营权,土地承包权仍由原农户享有的观念,难以自圆其说”(高圣平,2014b:84)。由是观之,上述论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视为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权利;而且在未区分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债权性流转还是物权性流转的前提下,仅阐释了以转让方式流转情形下的“两权分离”“难以自圆其说”。
其次,经营权抵押缺乏法理根据。有学者指出,“不允许承包权只允许经营权抵押,不仅无法理依据,而且债权性的租赁经营权也不具备成为抵押权客体之条件”(陈小君,2014:11-12)。还有学者认为,不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颇值商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可以通过抵押权实现方式的创新避免农民失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出租)给他人,以转包收益来清偿债务”(高圣平,2014a:155-156)。据此认为,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经营权抵押,既违背法理又无太大必要。
再次,承包权属于成员权,不因农地流转而丧失。有学者主张,“承包权是指农户承包土地的资格,是农户作为集体成员之一对集体土地享有的成员权,在法律上当属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容,而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范畴”(高圣平,2014a:154)。农户保留承包权,“保留的是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以期在下一轮农地发包中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其他因成员身份可以享有的权利。转出方失去的仅为有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其成员身份”(温世扬,2014:12)。由此可见,一些学者将承包权归属于成员权,并基于成员权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来论证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承包权缺乏法理根据;或者基于成员权不会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当然丧失、仍有权于下一轮土地发包时分享土地承包经营权,来论证通过“两权分离”刻意保留承包权没有必要。
二、 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论争焦点之辨
据上,经济学界与法学界的论争更多地体现在分析思路上的差异:经济学界主要从事实或实践切入,而法学界更多的是从法理或法规范入手。而且,支持者的三个论据与反对者的三个理由分别针锋相对。
(一) “两权”是否已经或者能否分离
“两权”是否已经或者能否分离,可以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和物权性流转两个方面予以考察。
首先,基于债权性流转的辨析。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以转包、出租方式大规模流转,是客观事实,而且这些流转方式已经被《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肯定,亦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大力提倡。显然,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债权性流转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分离出相对独立的经营权——不仅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的统计数据予以支持,而且亦有土地经营权证颁发之实践予以佐证。2014年8月笔者在安徽小岗村调研时,已经见到县政府为承包地流入方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土地经营权证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存,并分别颁发给不同主体——经营人和承包人,足见土地经营权与土地承包权分离的事实。反对者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承包权与经营权无法分离,与事实相违。当然,所谓的“两权分离”并非新现象,实质上仅仅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的一种概括。
其次,基于物权性流转的辨析。就“两权分离”的目的之一即农民通过保留承包权,仍享有承包地的流转收益权和征收补偿权(实质上是不丧失承包地提供的社会保障)而言,“两权分离”应仅仅适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物权性流转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整体转让,无法分置出承包权和经营权。因此,不能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发生的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后果,来否认“两权分离”。
据上,“两权分离”之经营权的法律性质已经清晰,当然应属债权。“两权分离”并非创新,更非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创设权利用益物权。而且,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与出租形成之“两权分离”的过程,直接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现有规定即可。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和出租后,流入方享有的权利是明确的、可以界定的,那么经营权亦应能够界定。
(二) 经营权抵押的创新是否科学
“两权分离”的支持者将经营权抵押的创新作为一个有力论据,而反对者则认为经营权抵押的创新缺乏法理根据,由此引发的焦点是以经营权抵押是否科学。
无论是《国务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国办发〔2014〕17号)中“推广以承包土地收益权等为标的的新型抵押担保方式”的规定,还是学界将经营权作为抵押客体的主张,均不甚科学。理由是:(1)债权性土地收益权和经营权不宜作为抵押客体——目前大陆法系普遍不允许债权成为抵押客体只能作为质押客体。(2)将经营权作为抵押客体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因为实践中往往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债权性流转收益权为担保客体,采取的债权实现方式也并非拍卖、变卖经营权,而仅仅是收取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收益。因此,经营权抵押的提出,虽然兼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殊性,但是并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并服务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担保。
此外,主张“直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客体、再创新抵押权实现方式”,即如果抵押债权到期,不是以作为抵押标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价款、而是以强制收取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债权性流转收益的方式实现债权,也不科学。因为这种抵押权实现方式的创新,实际上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的支配;由此,不仅僭越了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之间的界线,而且模糊了二元权利担保体系下权利抵押与权利质押之应然差异——权利抵押的客体不能是债权,而权利质押的客体可以为债权。由是观之,应当慎提经营权抵押,更不宜将债权性经营权抵押写进法律文本。
在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且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更好调控效果的前提下,肯定并暂时维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功能,可以弥补政府公共调节之不足,实现城乡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乃至实质公平正义。因此,当前还不宜放任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抵押可能导致的农民失地;而且在经营权抵押的创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抵押之实现方式的创新均不甚科学的情况下,若激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担保功能,尚需另辟蹊径。
(三) 承包权与成员权的关系
无论是“两权分离”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大多认为承包权可归属于成员权。但经济学界认为承包权是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的“两权”之一、不分离出承包权的承包地流转可能损害农民利益,而法学界部分学者主张承包地的流转不会导致农民丧失承包权,甚至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本不包括成员权性质的承包权、更谈不上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承包权。显然,论争焦点在于对承包权的不同理解,即混淆了作为成员权内容之一的土地承包权(实质上是承包资格)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中的承包权——由此也引申出承包权在两种场合下的不同含义。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构造及“两权分离”的目的而言,“两权分离”中的承包权不宜归入成员权,更非作为成员权内容之一的土地承包权即承包资格。
首先,不宜将“两权分离”中的承包权归属于成员权。成员权虽然包括集体成员承包集体土地的资格,但是成员权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的前提,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一旦产生即独立于成员权。如,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承包人并不丧失成员权,仍然可以参加下轮土地承包、有权分享集体红利。再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甚至可以转让给非本集体成员,可以继承尤其是“不宜将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排除在继承人之外”(刘凯湘,2014:27),都说明基于成员权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产生时起便脱离了成员权,否则具有身份属性其不仅不能转让、继承,且受让人和继承人更不能是非本集体成员。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具有身份属性,那么将“两权分离”中的承包权归属于成员权便缺乏根据。
其次,“两权分离”中承包权的内容不同于成员权。成员权既包括承包农用地请求权、分配宅基地请求权、分享集体收益等自益权,也包括集体事务提议权、表决权、监督权、代表诉讼权等共益权。而“两权分离”中的承包权主要包括流转收益权、征地补偿分配权*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根据《物权法》第121条分享的补偿,并非农民集体组织对所有集体成员平均分配土地补偿费时所分享的份额。、继承权、担保权(以债权性流转收益权为客体的质押)、转让权、流转合同管理权等。显然,从权利内容上分析,“两权分离”中的承包权既不同于农民集体成员的成员权,也不同于作为成员权内容之一的土地承包权即承包资格。
再次,不丧失成员权并不意味着不会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中保留承包权以避免农民不失地,并非是担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流出方无权再参与下一轮土地承包;主要是担心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物权性流转后,至下轮承包期间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再享有基于承包权的流转收益权、征地补偿权、继承权、担保权等。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语境下——主导政策制定的部分官员已经建议“承包期要延长为70年”(叶兴庆,2014:10),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物权性流转会导致农民在更长的时间内失地。仅就现有30年承包关系到期如何处置而言,根据学界“可自动延续”(陈小君,2014:13)甚至“应当自动续期”(朱广新,2014:37)的主张,在本轮承包期间已经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人,虽然不丧失成员权,但是不仅在本轮承包到期前失地,而且在下轮承包期内依然失地——如果下轮承包期延长为70年,会在未来70年内继续失地。
三、 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立法回应
(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的重述
据上,就“两权分离”的论争而言,经济学界提出的“两权分离”虽有现实基础,但一些提法尚需修正;法学界对“两权分离”的质疑虽存在一定误读,但亦不乏警醒之言。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一定程度上还扮演着社会稳定器的角色,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进城成本高企,特别是实现入城农民的安居乐业更需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承包人对于流转特别是物权性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仍有诸多顾虑。因此,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比例远远高于以转让方式流转,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往往表现出债权性流转的事实,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后流入方享有的权利概括为经营权,将流出方享有的剩余权利提炼为承包权,实际上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大规模流转以及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背景下,根据实践经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进行的再分解。有学者指出,农地立法应“在价值取向上以自由为目标、以平等为基础、以秩序为前提、以效率为手段,最终实现公平”(耿卓,2014:98)。显然,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中的承包权重在保障农民的平等权与社会秩序,而经营权则旨在追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自由与土地经营的效率;“两权分离”有助于在兼顾自由、平等、秩序和效率的基础上,实现最终的实质公平正义。
尽管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就承包权或经营权的名称而言,可能并非十分严谨,但是只要正确理解“两权分离”仅适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两权分离”中的承包权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置出经营权后剩余权利的简称——应具有用益物权属性,并将“两权分离”置于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改革趋势中,才能避免误读甚至否定“两权分离”。当然,肯认并重述“两权分离”也要理清承包权与成员权的关系:首先要区分两种场合下不同含义的承包权,“两权分离”中的承包权既不能简单归属于农民集体成员的成员权,也不能等同于作为成员权内容之一的土地承包权即承包资格;其次应当明晰分离出承包权的目的不是要剥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性——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具有身份性也无法分置出成员权性承包权,而是在农民社会保障不足的当下,要保留承包人基于承包权可持续获取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承包地对承包人的保障功能。
(二) “两权分离”视野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系统改造
综观中央政策文件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的论述,可以发现“两权分离”已经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发展的主线。首先,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和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可以为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债权性流转奠定基础;其次,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则是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必然要求;最后,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权、担保权,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宜继续贯彻“两权分离”的思路。
1.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及其效力
《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均不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是,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流转(尤其是允许工商资本下乡参与流转)的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无需登记亦可产生公示效果的熟人社会的社会根基已经改变。而且,在诸多地方已经对土地经营权登记颁证、经营权证又具有公示证明等功能的情形下,作为其母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尚未登记,或者会加大经营权证颁发前的核查成本,或者会加剧纠纷的复杂性。因此,在大力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以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已经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基础上,应当借编纂《民法典》之机,修改相关规定,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与变动采取登记生效主义。
2.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实现形式
提倡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流转,需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趋势下,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也会进一步强化“两权分离”。“长久不变”的实现形式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后还要不要有个期限?如果有期限,那么多长合适?二是如何与本轮承包相衔接,即承包关系到期是重新发包土地还是自动续期?对于第一个问题既有建议不要期限限制的,也有建议延长为70年或保持30年不变的。就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而言,最好是有期限限制,以契合他物权为有期限物权的特征。至于期限的长短与第二个问题直接相关:如果承包关系到期重新发包土地,保持30年更合适——可以避免重新发包成为待地人群难以企及的期盼;如果承包关系到期自动续期,即在不考虑调整承包地的情况下,那么70年更便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业经营体系创新。
承包关系到期,承包地应当重新发包还是自动续期?关键又归结为是否要调整承包地,对此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从保障新增待地人群分享集体土地的角度看,显然重新发包更有利于回归集体土地对所有集体成员提供保障之集体所有制的本质属性;但是,从促进规模化、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的形成,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角度看,又不应让重新发包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规模经营主体的经营规划。在农民对农地保障的依赖程度已经下降、更重视农业规模化经营效率的政策选择下,基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严格限制调整以及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出台,应倾向于自动续期。而且,就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大规模流转且会加快流转的事实而言,为了保障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经营的稳定性,采取到期后自动续期的方式更为简单妥善——尽管有流转事实倒逼自动续期之嫌。
当然,随着整村或整组土地承包经营权“反租倒包”到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入股到社区股份合作社的发展,乃至于部分地区农用地确权确股不确地之承包方式的创新,已经为既不影响规模经营主体经营的稳定性,又可通过承包权利的“账面”调整、保障新增待地人群分享集体土地利益提供了便利。因此,“长久不变”的实现形式可以是:在本轮承包到期后,承包关系自动续期为70年;但是在不影响农地流入方规模经营的前提下,允许集体成员经民主议定决议是否对承包权利进行“账面”调整。
3.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方式之选择
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不仅可以进一步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而且在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还会增加承包权的权能,彰显承包人保留承包权的重要性。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方式,有学者基于避免承包地碎片化的考虑,建议“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属于农业人口的继承人,可以优先分得农地使用权;……继承人均为非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非农业人口的,在继承农地使用权后一年内,应将农地使用权转让给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者”(梁慧星,2004:264)。还有学者建议,“把初始分配时平等赋予集体内部单个成员的承包地面积视为‘最小耕作单位’。当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数量超过可继承的‘最小耕作单位’土地数量时,首先由具备农户内部成员身份的继承人享有最优先的继承资格;……最后才轮到集体以外的从事农业经营的继承人”(汪洋,2014:147-148)。
如果上述建议在农用地普遍由承包人或继承人自己经营的年代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发生大规模流转,而且提倡农业规模经营的背景下,上述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方式的规定值得商榷。首先,“继承人均为非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非农业人口的,要求其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干预过度之嫌——限制了继承人以转包、租赁等方式流转的选择;而且,也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中“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的政策存在冲突。其次,在家庭承包分散经营已呈现规模过小之弊端的情况下,“最小耕作单位”并非农业生产的合适单位,以此为标准限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人的顺位,并不能防止农用地细碎化或者无法实现农业经营规模优化。再次,如果被继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两权分离”,那么各继承人应当维持经营权现状只享受承包权,根本无须担心会因为继承而导致农用地经营的细碎化。显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继承方式不宜由法律限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之继承权的充实,会进一步促进“两权分离”,而“两权分离”也为平等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了便利。
4.农地入股合作社的制度解析
学界对入股的法律性质是物权性流转还是债权性流转尚存诸多争议。就实践特征而言,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实际上遵循了“两权分离”的逻辑,呈现出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理由有:(1)《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等诸多规范性文件规定入股的仅仅是承包地的经营权或预期收益,合作社终止时承包地要退回原承包农户。显然,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并非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整体让渡给规模经营主体,而是通过债权性流转为规模经营主体创设经营权。(2)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往往采取“固定保底收入+浮动分红”的利益分配方式;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鼓励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利益分配方式。由是观之,具有租金性质的“固定保底收入”,亦使入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租赁即债权性流转的属性。(3)即使合作社经营亏损,也只能以入股者的其他财产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承担责任,而不能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破产财产,使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类似于《企业破产法》中可以行使撤销权的租赁财产。由此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实际上是使规模经营主体取得经营权,承包人仍保留承包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可以分解为两个阶段:一是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创设经营权,二是将经营权出资于规模经营主体,这两个阶段使入股兼具出租与出资双重属性。而且从整体上看,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应当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流转;所谓土地经营权入股的表述,只能反映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第二个阶段,却无法揭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第一个阶段即经营权的产生。
惟有按照“两权分离”的思路,才能合理解析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实践中的下列制度:(1)出资制度。即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产生的经营权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整体入股。(2)股权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股获得的固定保底收入,因为需要纳入经营费用,不同于从净利润支付的优先股股息,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不宜被设置为优先股。(3)利益分配。固定保底收入实际上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之双重属性中的租赁属性产生的交易的对价,而浮动分红则是将租赁属性视为一种特殊惠顾的惠顾返还。(4)组织属性与立法模式。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之债权性流转的法律性质与“固定保底收入+浮动分红”的利益分配方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之双重属性中的租赁属性视为一种特殊的惠顾,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合作社契合了合作社惠顾返还的本质规定性,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合作社纳入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乃至修订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具有了正当性。
5.农地担保方式的选择与规则设计
激活土地承包经营权担保功能的具体方式,应按照“两权分离”的改革路径,宜修正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债权性流转收益权质押(高海,2012:115),并以“收取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收益”为质权实现方式。理由是:(1)债权性流转收益权系债权,根据权利抵押与权利质押的应然差异,只能采取质押的担保方式。而且,可以在不违反《担保法》、《物权法》禁止耕地抵押之现行规定的前提下,直接将债权性流转收益权质押纳入《物权法》第223条“应收帐款可以质押”的名下,使其获得《物权法》上的明确法律依据。(2)债权性流转收益权质押仍然是对收益权交换价值的支配,可以避免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客体、以“收取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收益”为抵押权实现方式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对担保物权支配标的物交换价值”之基本法理的违背。(3)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既然《决定》将抵押与担保并列表述,显然在抵押之外,亦不排斥质押等担保方式。事实上,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以质押命名的实践,如2011年湖北省襄阳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贷款办法(试行)》等。由此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债权性流转收益权质押的存在,既阐释了《决定》将担保与抵押并列规定的现实意义又是对担保权能的具体化。当然,在“两权分离”思路的指导下,既要从宏观上构建农地金融、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三位一体化”的嫁接机制完善质押权人,又要从质押人和质押标的范围、质押标的价值的确定、贷款期限的限制、质押公示方法、质权实现方式等微观方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收益权质押进行系统构建。
6.农地流转的多种经营模式之创新
《决定》提出“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农用地经营模式。除合作经营主要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形成之外,就家庭经营与企业经营取得农用地的流转方式而言,应主要指转包、租赁,不宜包括入股。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不仅被一些学者视为是物权性流转,而且优先股制度也难以诠释入股实践中普遍采取的“固定保底收入+浮动分红”式利益分配规则——优先股股息的支付以有可分配盈余为前提,而保底收入之保底则意味着无论有无可分配盈余均须支付。显然,家庭经营与企业经营主要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租赁取得农用地,契合并贯彻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
集体经营农用地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反租倒包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或者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到社区股份合作社经营;二是通过将未分包到户的集体土地按股量化,组建社区股份合作社经营。两种形式中,第一种形式之反租倒包更体现并贯彻了“两权分离”。由是观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鉴于反租倒包在促进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集体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越性,应当重新反思《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中发[2001]18号)和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制止乡、村组织‘反租倒包’”的规定,宜肯定承包人自愿基础上的反租倒包。
四、 结 语
对经济学界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应在慎思法学界论争基础上,进行准确解读及修正。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既是对农用地流转实践的一种发现,也是贯穿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入股、担保,乃至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等改革的发展主线。通过法律逻辑有效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事实,有利于在农地改革中提炼符合社会实际的法律规则。
[1]蔡立东、姜楠(2015).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构造.法学研究,3.
[2]陈小君(2014).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思路与框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相关内容解读.法学研究,4.
[3]陈锡文(2014).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几点考虑——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党史研究,1.
[4]丁关良、阮伟波(2009).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三权分离”论驳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保留(土地)承包权、转移土地经营权(土地使用权)”观点为例.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5]冯华、陈仁泽(201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底线不能突破——专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人民日报,2013-12-05.
[6]高海(2012).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收益权融资担保.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7]高圣平(2014a).农地金融化的法律困境及出路.中国社会科学,8.
[8]高圣平(2014b).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法学研究,4.
[9]耿卓(2014).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的观念转变及其立法回应——以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为视角.法学研究,5.
[10] 韩俊(2013).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与政策展望.中国农村经济,1.
[11] 李国强(2015).论农地流转中“三权分置”的法律关系.法律科学,6.
[12] 刘凯湘(2014).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北方法学,2.
[13] 刘守英(201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及其实施.法商研究,2.
[14] 梁慧星(2004).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北京:法律出版社.
[15] 汪洋(2014).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研究——对现行规范的法构造阐释与法政策考量.清华法学,4.
[16] 万宝瑞(2014).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与建议.农业经济问题,4.
[17] 温世扬(2014).农地流转:困境与出路.法商研究,2.
[18] 叶兴庆(2014).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离”——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过去与未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6.
[19] 张红宇(2014).三权分离、多元经营与制度创新——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一个基本框架与现实关注.南方农业,2.
[20] 朱广新(2014).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期限和继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4.
■责任编辑:李媛
◆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Debate and Legislative Response
GaoHai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Some legal scholars still doubt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which was initially proposed by economists.Through neatening and rethinking three considerable controversies on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in economics and law,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theory of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has solid practical foundation.However,the opinion should be modified that the management right of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can be mortgaged and the contractual right should belong to the member right.Meanwhile,the viewpoint of some legal scholars on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ractual right should be corrected.In short,the theory of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is not only the discovery and refinementof the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land circulation,but also is the main future direction which guides the agricultural land reform,such as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the longtime unchanged of land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the inheritance,shareholding,and guarantee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and the innov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contractual right; management right
10.14086/j.cnki.wujss.2016.06.0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FX084)
■作者地址:高海,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Email: gaohai4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