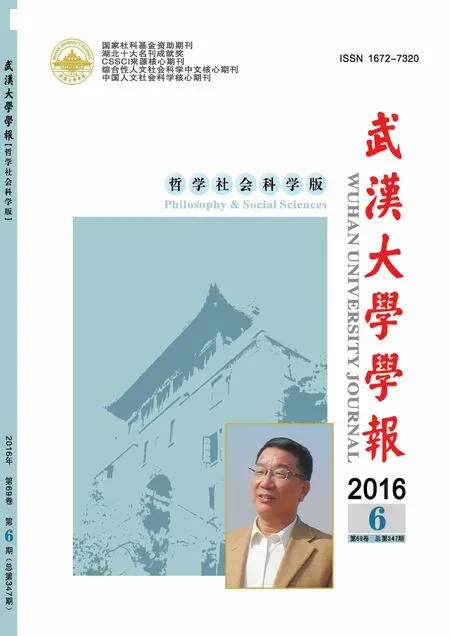从族商的兴衰看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以闽西四堡印书业族商的兴衰为例
2016-03-13戴腾荣郭熙保蔡立雄
戴腾荣 郭熙保 蔡立雄
从族商的兴衰看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以闽西四堡印书业族商的兴衰为例
戴腾荣郭熙保蔡立雄
制度和技术创新对企业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四堡刻书业是在家族内组织进行的,由于商业关系对传统的家族治理结构的渗透,最终在家族内部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经济单位,由此,族商就兼有血缘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双重特点,宗族力量与工商业力量互相支撑、互相联结、互相强化。以族商制度创新为基础,四堡刻书业进行组织、市场、产品、分配等方面的创新,实现了宗族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和工商业上合作,成为一支有影响力的书商集团。但工商业与宗族力量的过于紧密捆绑使族商在商业化社会与技术环境变化面前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其反技术进步、反社会信用、违背商业利益的资本投向、弱激励倾向与生产要素使用上的过度僵化等,导致了刻书业在急剧的社会变革面前迅速崩溃。族商的兴衰表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成就了族商的辉煌,创新不足也导致了族商的衰亡。关键词: 制度创新; 族商; 四堡刻书业
从人类发展史可以发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创新,都只是特定时期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创新的经济效应最终会耗尽,从而使经济回复原有的增长速度,这已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证明。并且当一国或某一产业长期处于发展的前沿,再进行创新需要更高的甚至是全新的条件,满足这些条件所需要的时间与资金成本会使创新变得困难,若加上创新的技术与市场风险,创新意愿会进一步减弱。如摩托罗拉公司、诺基亚公司、柯达公司的衰落就是当代经典的案例。在国家方面,泰勒·考恩(2015)提出创新技术高原现象是美国经济陷入停滞的重要原因。
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在现代社会中得到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也大量存在,如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在古代社会,经济上的创新是由各类企业家(这里企业家采用的是熊彼特的定义)完成,企业家在组织、技术、市场上的创新决定了其所经营产业的命运。福建闽西四堡在明清时期是中国重要的刻书中心,但在清代末年却忽然衰落以至崩溃,其兴衰过程为后世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可为当代企业家思考其管理与技术创新提供借鉴。四堡刻书业是在家族内组织进行的,由于商业关系对传统的家族治理结构的渗透,最终在家族内部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经济单位,其商业组织形式就具有血缘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双重属性,笔者把这种产业组织形式称之为族商。由于族商在中国古代社会地方性商业组织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四堡刻书业族商因其在明清两代规模大、经营范围广、资料也保存较为完整,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族商和印书业的重要案例。笔者的研究以四堡代表性刻书商——邹家和马家书商为研究对象,试图解释族商制度与四堡刻书业的组织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的关联性及对产业兴衰的影响。
四堡印书业家族企业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创新精神的先进企业的代表,它的兴衰与其创新意识的强弱有直接关系。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企业理论表明,企业的建立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四堡印书业族商的创建在降低信息搜寻、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方面的交易成本是成功的,但同时由于家族企业固有的缺点使之无法扩大企业规模并向现代公司制转变,同时其创新意识逐渐淡薄,在市场竞争中最终被淘汰。对四堡印书业族商兴衰的分析也是以制度和交易成本为基础的,以中国经济史中的族商这种近代企业组织形式为案例,分析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 族商与族商制度
族商可以说是现代家族企业的早期形态,在经济史中,族商或家族企业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社会中,家及其扩大的群体家族(或宗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秦汉以降,虽然中央政府屡屡对大家族进行打击、拆分,但乡土社会中聚族而居的情况并没有改变;继承制度虽由长子继承制转为诸子均分制,析产分户由此成为主流,这种财产析分不断制造出独立的小农,使之与土地紧密结合,这与封建的社会治理要求是相一致的,其产业导向更多是农业。但也存在诸多“同居共财”现象,而“同居共财”符合占社会主流的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由此一些士大夫和乡绅地主更倾向于累世同居和共业经营。为了家族的发展,大家庭内部往往实行分工,部分人专门读书以期走仕途之路以维持家族荣光;部分人则从事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不限于自给自足的农业。事实上,由于工商业和商品性农业的收益较高,出现了一些面向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家族,即族商。由此,我们认为,族商是指以家族内部人力资源为主导或主体力量在较长时间内面向市场开展工商业经营,经营成果也主要在家族内部进行分配的商业家族;族商以整个家族经营某一非农产业为主导,是否共产并不重要,但毫无疑问,所经营的产业以从属整个家族经济为特征;族商在商业运作中,将宗法与商业规则高度结合,在家族经济内部,商业规则从属于宗法*这一定义与最早研究族商问题的陈支平教授的提法有所不同,他认为:“族商,应该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而不应当是一个有着十分严格空间和时间界限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那些与本土家族、乡族保持比较密切关系的商人,可以称之为族商。这种所谓的比较密切的关系,也有两重的含义:一是同家族、乡族的族人、乡人外出到某地经商或从工,大家可以利用家族、乡族的关系,相互扶持、相互协作,形成某种形式的内部运作机制;二是工商业者们虽然离家千里,甚至远涉重洋,但是他们的经营范围,基本上是以本土的家族、乡族为核心据点的,外出的工商业者不仅与故乡保持紧密的家族组织、乡族组织的关系,而且在经济经营方面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参见陈支平:《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我们认为:陈支平的定义不强调家族主导产业,也不强调宗法在工商业经营中所起的作用,未免失之于过宽。。
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族商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商业组织形式,其有关资本组织、内部控制、经营管理和剩余分配的行为规则就是族商制度。从资本组织形式上看,族商的资本最主要来自家族内部,由同一或高度关联的家族共同出资或互相提供信用进行组建,家族成员掌握最多的股份。从族商组织的内部控制上来看,其主要决策权和关键岗位的管理权均由家族内部成员控制。从族商组织的经营管理上看,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合一,家族成员高度参与组织的生产、销售、采购等经营活动。从剩余的控制与索取权上看,家族决定剩余的分配权,其分配目标主要是服务整个家族,而不是组织的发展。
族商这一组织形式与社会信用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相适应。如地中海地区的马格里布商人在这一方面与中国族商具有共同的特征。在中国,族商的兴起还与儒家所倡导的关于“家”*“家庭只是社会圈子中的一轮……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 1页。的理念相一致。在社会信用体系缺乏的社会中,兴办工商业所需的资金不能通过社会渠道获得,因为“在一个信任资源缺乏的社会里,社会交往是家庭式的”(Redding & Gordon,1991: 30-47),为此必须通过其天然的信任网络——家族组织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其工商网络扩张的过程,经营的安全性需要亲情来对超出本乡土之外的经营活动进行支持。由此,一人一家之事业最终往往发展为一族之事业,进而工商业活动也与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族商也就成了乡土士绅与商人的结合体,商人既受商品经济规则的约束,也受乡土道德或族规的约束;他们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而且参与乡土社会事务管理。
族商作为古代社会民营经济的一种代表,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当时比较有效的一种经济组织。
1.族商对市场变化高度敏感。族商的经营效益高低与家族每个成员的利益高度相关,而族商的效益又取决于市场的选择,家族成员的目标高度一致,因而家族成员高度关注市场变化的情况,并能努力搜取市场信息传回家族以实现信息共享。
2.族商决策与执行速度快。族商的经营中宗法和族长有高度的权威,从而形成一个事权高度统一决策中心,能及时作出经营决策;同时,由于其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为一体,家族特有的差序结构是一个有强大凝聚力的良好信息沟通机制,使得决策一旦形成立刻能执行,从而大大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
3.族商的委托—代理成本低。委托—代理问题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族商中基本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原因在于族商代理人同时也是委托人,资产所有者、管理者与员工均是企业的主人,他们的收益均来自于剩余的分配。
4.族商能快速集聚创新与发展要素。在宗法社会,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家或族的集体利益。企业是家族共同的事业,因而它能将家族中人力、物力、财力等创新要素和发展资源迅速集中起来办事业,而不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契约形成过程。
5.族商特有的集体学习机制使创新因素能传承。族商中每一个家族成员的成长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工艺、管理和经营的过程,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了父辈和同伴的创业过程,务工、经商的基因从而得以传承。同时,企业的创始过程中,企业的组织、工艺、市场网络等均是新创。从乡村传统农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族商,在创建和初始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经营活动都是一个新的探索。
6.族商制度有助于降低创新的风险。族商事实上有一个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而且还有农业作为托底产业,其社会结构也没有因经商而改变,因此,虽然创新的过程充满风险,但对族商而言,创新或经营失败的风险不过就是回到原有发展轨道。灾害学中社区韧性理论认为:如果社会结构保持完整,那么灾害的影响将被减轻(Bolin & Stanford,1998)。
正因为族商制度的不断创新,以及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使族商成为中国在那个时代效率较高的经济组织,从而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二、 四堡刻书业兴起的原因分析
在明代中晚期兴起的四堡坊刻采取的组织形式就是族商形式。四堡族商依坊刻而生,并随坊刻的衰落而消亡,因此,四堡的族商史同时也是四堡的坊刻史。但学界对四堡印书业兴衰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于一些史实的整理和比较分析,其研究也多限于印书业本身,较少探究族商制度与四堡印书业兴衰之间的关联性,更多强调自然禀赋、社会环境变化与外部竞争等外部原因,而对于商业活动以家族形式存在的原因,家族制度在商业活动中作用,家族制度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对商业活动构成制约乃至最终导致这一商业组织形式的崩溃则研究较少,或语焉不详,影响了其解释力。笔者认为,对四堡印书业的分析应从其基本的组织或制度创新上进行分析,研究印书业的族商组织和这一组织的基本影响以及组织结构多年不变的重要原因。
四堡(旧属长汀县,今属连城县)位于闽西长汀、连城、宁化、清流交界处,是个偏僻的山区小镇,四周丘陵合抱,交通并不顺畅,人口集中度不高,从地理、交通、人口等方面考察,四堡缺乏大商业发展之条件,但在其鼎盛时期,在这弹丸之地,从事印书业的男女老少不下1200人,约占总人口数的60%,分布在雾阁和马屋二村世代相传的大书坊至少有100家,而充作书坊的房屋更是星罗棋布不下300间,并逐渐向刻版、印刷、包装、销售一条龙规范化发展*参见马卡丹、曾玲:《连城风物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92页。 包筠雅(Cynthia J.Brokaw,2007)根据民间文献和实物资料估计,至17世纪末,四堡共有13家书坊;至19世纪初,当地涌现出了46家新书坊。。四堡书坊数量略少于北京的近120家,但多于苏州(57家)和广州(25家),是当时一个名副其实的印书中心。1956年,郑振铎在厦门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将北京、汉口、四堡、浒湾列为清代最著名的四大基地。
关于四堡印书业的起源时间,普遍认为始于宋代,清人杨澜在《临汀汇考》一书中提到:“汀版自宋已有。”*参见(清)杨澜:《临汀汇考》卷四,《物产考》。民国《福建通志》也有记载:“长汀四堡木雕刻本始于宋代。”*参见民国《福建通志》第四十八册,《版木志》。在元代由于蒙古贵族对闽西掠夺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从根本上破坏了闽西经济基础,人口大量减少,百业萧条,民间刻书业也基本消失。到了明代中晚期,由于经济恢复和人口的重新集聚,山区商品性工农业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刻书业再度兴起,并在随后的三百年间保持发展,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急剧的衰落。
明清时期,闽西人口增多和交通的改善,商业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利用山区物产解决生活问题进而致富的重要方式,而稍有影响、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多采取族商形式,代表性有造纸的邓家、制作烟刀的林家、生产烟草的江家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印书商邹家和马家。两大姓氏既世代联姻,又在商业上形成竞争关系。四堡印书业兴起,是宗族对光宗耀祖的使命感与宗族组织对自然的比较优势条件利用的一种结果。
1.崇文重教的传统成就了印书业的兴起。闽西历史上是个移民地区,是著名的客家祖地,其开发与中原移民潮密切相关,中原战乱之际恰是闽西发展的契机,其文化活动表现,除因顺应和改造新的环境而须吸纳土著文化之长外,更多的还是客观上大山的阻隔促使了对中原文化传统的固守与承袭。能克服旅途中重重的关隘与困难、通过长途迁徙来到闽西的先民主要是中原大族,其文化程度较高,对在异地重现祖先的荣光的责任意识较强,教导子孙读书就是其重要途径。而古代社会书籍一向是奢侈品,闽西又避居东南一隅,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相隔遥远,由此,早期居民为保存文化,利用当地资源发展造纸、印书业,这也是宋代以后在福建出现福州、建阳、四堡三大有全国影响的印书中心的重要原因。印书业的代表家族邹、马两家均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世代以儒商自居。
2.工商业的发展使印书业得以繁荣。闽西是个比较偏僻的山区,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最终超过了山区农业生产所能容纳的极限,发展工商业便成为解决人地矛盾的基本途径,明代此地山区商品性工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中一些世家大族本能地将重文传统与工商业结合起来,形成儒、商并重的工商家族。据马、邹两家族谱记载,两家印书业的创始人均为官员,进入印书业的目的均是将发家与教育子弟相结合,马家的马驯是明成化年间的副都御史,据说为刊刻族谱、印刷诗文而将汉口的印书业传回家乡;邹家的邹学圣是明万历年间的杭州仓大使,为解决辞官回乡后子女的教育问题,购置了全套雕版印刷设备,在雾阁村开书坊“镌经史以利后人”。
3.宗族组织与科举制度使印书业最终得以勃兴。邹氏和马氏二族盛行大家庭制度,往往数代人聚居。聚居互助使书坊有最初的资本,家族内部分工又使书坊有了组织者和从业者。当时邹、马两家族子弟首要选择是读书科举,若科举不成则要转业,或工或农或商,获利以支持其他人再走科举入仕之途,形成家族内部分工。据统计,从明中叶至清末,四堡邹氏家族共有169人获得科举功名,但仅有12人考上举人,其余均为生员、监生和贡生,这些既获得科举功名又不能入仕的读书人“业儒不就”,往往转而“弃儒经商”,利用雾阁、马屋四周盛产枣木、梓木、梨木和小叶樟等自然资源制作出纸张、烟墨和刻版等雕版印刷所需的原材料以刻书、印书为业,正如四堡马氏后人马卡丹先生所论及,“翻开邹、马二族的族谱,有关‘弃儒经商’的记载比比皆是,……正是这些落榜学子的转型,转出了四堡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代”(马卡丹,2007:153-157)。这些书坊,都是家庭作坊,以家族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一家几代四五十口,甚至七八十口人,按体力强弱能力不同进行周密的组织分工安排到各个工序中。
四堡刻书业的创办过程创造性地引入族商制度,这一制度在自然经济占主导的社会中不啻为是一种先进的商业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利用天然的信用体系集聚生产要素,体现宗族成员之间互助的性质,继承了客家宗族在长途迁徙中形成守望相助的信念;它将宗族敬祖崇宗理念与发家致富的诉求结合在一起,符合当时价值取向,从而有效降低制度变迁的摩擦成本;它利用天然宗法制度集中全宗族力量办事业,以宗法准则组织工商业运行,从而使工商业运行效率极高;选择刻书业为主业从商,符合从中原迁入的客家人诗书传家的传统理念。正因为有这些特点,宗族制度以务农为主向以经商为主的转变能有效降低变迁的组织、信息、摩擦、学习等方面的成本。同时,四堡刻书业对族商制度的引入并非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进行创新,与一般的族商全族只经营一家企业(可以有诸多分部)不同,四堡族商以宗法为共同信守的准则,但企业是由多家分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组织的,这样有助于调动各家族成员的进行版刻工艺、产品、市场创新的积极性,也使刻书业的规模能迅速膨胀;宗法和族老只起协调作用,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方式,无疑更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
三、 四堡印书业族商的制度创新
四堡印书业的持续繁荣了近三百年,族商制度支持下的系列创新在其中居功至伟。
(一) 生产组织创新
在传统小农为主的社会中,普通的家族办大商业是极其困难的,面对的资金等方面的门槛极高,四堡族商利用成员对家族责任与天然信用网络建立生产组织,保障了印书业的生产要素供给。刻书业的生产要素除竹木等自然资源外,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和资金。印书业引入四堡之后,自始至终都是整个家庭乃至宗族的共同事业(陈支平等,1988:93-109),体现出全族深度共同参与性质。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男女老少齐上阵,“按体力强弱、能力不同进行周密的组织分工安排到各个工序中。版面设计、底本考据、书写成形、雕刻、印刷、订线、包装……等20多道工序到最后发运、布点联络等,均有专人负责。”(汤露,2005:60-61)。在资金供给方面,最初的资本由返乡的官员提供,随后的发展壮大则更多来自于家族内部的共同筹措,乡土中家族的天然信用网络与互助保障资金筹措的顺畅,具有明显家族互助性质和宗法嵌入色彩。
(二) 分配与扶助制度创新
传统社会中的财产分配主要是差序的分配,产业则主要由长子掌管。四堡族商的财产分配不限于差序,而扩展到同一序列的兄弟之间,也不限于资金分配,还包括生产工具的分配。亲族的互助也不限于资金,还包括经商经验和工艺等。这种分配制度与亲族间互相扶助制度使书商群体不断壮大。族人在经商有成积累庞大资本后,按儒家传统对子孙实行均分的析产制,如邹继云“凡构造书板,继置田庄,悉本公之勤劳以致之。……厥后丁口浩繁,兄弟分籍,其所五之业,条分缕析,无此厚彼薄之虞。”马文澳“牵车服贾,因而家益殷实。及析著,凡物悉与诸弟均之,而囊无一私钱”。可见,邹、马两家产的析分不仅表现在资金的族内分配,还包含生产工具(刻版)的分配,由此使经商传统持久不衰。
客家地区作为一个移民地区,亲族互助的传统源远流长,在经商、移民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如清代的客家人移民台湾,永定下洋中川胡氏家族(胡文虎家族)下南洋等,均表现为先行者携带后辈而成为一种持续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活动。邹、马两家也有此传统。据两氏族谱载:邹南峰“诸侄扶如己子,予以本,教以贸易,终身不怠”。邹子瑶“与伯兄龄轩公同贸易于豫章之樟镇,筹画经营,屡获重利”。这种扶助,不仅有利于传递商业经验,同时也降低了后辈子弟在入行之初的门槛和融入成本。
(三) 产品与市场创新
四堡刻书拥有广大的市场,鼎盛时期有“垄断江南,行销全国”(陈微,2009:166)之称,行迹遍及13个省100多个县。市场的拓展除了产品的准确市场定位外,宗族成员共同努力是关键。生产的分工最后走向市场分工,出现专业的商人和专门市场,这是为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业发展的一般轨迹。书籍生产的目标市场不是地方性的,闽西山区文化人群的规模不足以容纳四堡所刻印的全部书籍,为此,四堡书商通过肩挑、车载、船运沿汀江、闽江水运和赣南通道向区域外销售书籍。售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比生产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工作,需要专门的人员进行市场开拓,由此,专业书商与生产者同时出现在四堡地区。同样由于信任和节约资本的考虑,书商是家族内部分工的结果。为了开辟市场,四堡族商采取了产品与市场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包筠雅在《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在销售区域选择方面,“四堡书商选择的是腹地的府城、县城和集镇,它们靠近但并不处于广东、广西、江西和湖南省的都市核心”(Cynthia J.Brokaw,2007:231),也就是说,避开大都会中心又接近人口较集中的腹地是其与其它地区的大书商展开差异化市场营销竞争的重要法宝之一。
在产品种类差异选择方面,四堡坊刻本“对出版的文本进行审慎的选择”,他们刊行的是“确认无疑的畅销书”,那些“精挑细选的普及性和实用性都得到充分证明的著作”(Cynthia J.Brokaw,2007:305-306),重视出版教育考试类和文艺类等畅销书,而对那些艰深晦涩的学术著作则较少关注*四堡所印书籍种类繁多,从族谱、账册及现存书板中统计,四堡刻书见到实物或有文献记载的有667种,除各种重复外,共489种,其中有《四库全书》、《四书集注》等儒家经典105种;有《千金翼方》等医药类58种;有《人家日用》、《弟子规》等日常实用类65种;有《文心雕龙》、《楚辞》等文学类80种;有历代文人诗文、宋词、元曲、小说等51种;有地理堪测占卜星算等42种;有启蒙读物41种,可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甚至明、清的禁书如《金瓶梅》等,亦有刊本。。
在产品销售对象选择上,四堡书商所针对的不是高端消费群,而主要面向下层读书人,是“由充其量是小康之家构成的相对广泛的受众”(Cynthia J.Brokaw,2007:522)。不少四堡坊刻本或是在小开本的版面内尽量增加文本的内容,或是为文本提供断句,或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相对艰深的文字,它们面对的虽然是不同阶层的读者,却格外关照文化修养不高却又为数众多的下层读书人(刘永华,2008:82-187)。
在成本与价格控制方面,由于四堡所印的书籍主要针对下层的社会居民,所以对质量要求不高,以达到成本控制和低价销售的目标,“四堡坊刻本多半开本很小,版面排字拥挤,误字漏字时有出现,印在廉价的毛边纸上,雕刻的质量本来就不好,又因过度磨损而字迹模糊”(Cynthia J.Brokaw,2007:514-518)。“这些书籍的价格,常常不及其他地区刊刻书籍的一半,就连贩夫走卒也买得起”(刘永华,2008:82-187)。低成本、低价格不仅是竞争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发挥当地技术水平不高、就地所取的原材料质量较差的优势。“这样一种经营策略,让四堡书商克服了四堡本身作为经济、文化腹地在出版业中的不利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其他区域性出版中心的竞争,从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收益和发展机会。这种经营策略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四堡的销售网络渗透到区域市场系统的下端——集镇和乡村,尤其是渗透到过去的书籍销售网络可能从未触及的华南、西南的内陆腹地和边疆地区”(刘永华,2008:82-187)。
四堡印书业规模的扩张与商路的开辟是互相强化的。销售网络的延伸导致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四堡的声誉大涨,从而在四堡出现了专业书籍批发市场和在部分城镇建立起专业书店。四堡商人的专业市场与专业商店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家族共同的行为。乾隆戊戌年(公元1778年),为便于交易,邹氏各房在四堡设立族墟。设立族墟不仅方便了书籍的交易,也有利于更好地获取流通收益。同时,在主要的书籍销售市场,四堡的书商也通过设立书店等方式实现了由行商到坐商的转变,从而能更有效地占据市场并降低交易成本,而这种书肄之设,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宗族合作的产物。此外,由于长期在外经商,部分商人移居外地,在客家的移民史中,商路同时也是移民路(如邹韬奋先生的祖上据说就是由四堡因经营书籍而移民到江西的),这批商人群体壮大后,据客家人崇先敬祖的传统在新的定居地建起了祠堂,这种祠堂不仅是祭拜祖先的场所,同时也是族人交换商业信息、协调商业活动的场所。
(四) 协作组织创新
刻书业准入门槛低,其主要销售对象是低收入的读书人、收藏家、儿童及从事医学、风水等各行业的人,面对的顾客群复杂多样、多变与有效应对市场竞争,必须及时了解并把握市场信息。四堡两族的书商在家族内部建立起必要的信息沟通机制。据调查,四堡书商在贩书的过程中,如果自己不能满足客户的要求,就必须把有关信息通报同族商人,以免被其他书商夺走市场。
四堡印书的主要销售区域不是竞争激烈的大城市,而是中小城镇和乡村,薄利多销是其主要手段。因而如何降低经营成本、防止过度竞争以保障利润是其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印书业的固定成本主要体现在雕版制作上,为防止同一刻版的重复制作从而避免同一书籍的供给过剩和降低总体出版成本,邹、马两家族通过制订族规来协调生产,其中最著名的是“岁一刷新”*岁一刷新指在来年正月之前,各书坊须将明年出版销售的所有图书品种全部刷印出清样(版样),贴在各自书坊门墙之上,如遇品种重复,由家族中的族长或有威望的长者出面调节,尽可能在族内解决供求矛盾,避免族人之间的商业竞争。的规定,它体现了商业规则与宗法高度协同,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商业利益。宗族的组织与协调降低了无序竞争风险和信息成本。
五、 族商制度与四堡印书业的衰落
四堡雕版印书业在兴盛了三百年后,在咸同以后出现断崖式衰败,四堡雕版印刷业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走向衰落,结束了其作为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的辉煌,这是内外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主要是:太平军在汀州和连城与当地清军和地主武装进行激战,毁坏了四堡大量的印书房。更致命的一击来自近代出版机构的迅速发展,伴随着石印和铅印技术的出现,上海点石斋、广西拜石山房、广东同文书局等近代出版机构崛起对旧式印书业的替代,近代印刷技术所产生的刻书质量、效率是传统雕版印刷技术望尘莫及的。1906年科举制的废止,也使大量四书五经等方面的刻书无人问津。
内部因素则主要来自于固化的宗族制度不能因应时代的进步。宗族制度最初对商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实现了成本与时间的节约,但宗族制度与商业制度的规则毕竟有极大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不兼容的,这种不兼容性在技术与商业不发达的社会表现并不明显,但当技术进步和商业环境发生明显的变化时,把商业与宗族捆绑在一起就是致命的。
(一) 族商制度阻碍了资本积累
商业始终从属于整个宗族经济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重要特征。在儒家的价值观主导下商人对家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商业利润首先用于满足家族、宗族成员的日常消费与各种礼仪活动,用于置田、造屋、子弟入学,而不是主要用于商业本身的发展;经商有成之后,商业资本积累因分家析产(不只用于直系亲属间分家析产,还承担同宗亲属的扶养、创业责业),如马权亨创办的经纶堂在100多年间先后分析出文萃楼、湘山堂、务本堂、同文堂、鹤山堂、在兹堂、念兹堂、文兹堂、文林堂、枕松堂等堂号,单个商人资本处于膨胀和收缩的循环之中,社会再生产始终只是小规模简单再生产的循环,当外部环境要求其需要转型、引进新设备新技术时,族商无法拿出充足的资本去购置昂贵的新机器。
陈支平等(1988)提出,四堡坊刻采取族商的形式,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也不利于技术进步。曾玲等(2000)也认为“在家族内以手工劳动为特征、以家庭为主要经营单位的书坊,其生产规模本不可能很大,随着家庭中下一代年龄的增长、分家问题的出现,作坊的生产规模便只能缩小,无法扩大,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以致在长达二三百年时间里,家族刻印的生产规模难以有本质上的变化,无法从家庭手工业步入工场手工业的新台阶。”
(二) 族商制度阻碍了技术进步
族商制度作为儒家制度的一种内嵌制度,具有儒家求稳防变的社会治理导向,在本质上是反技术创新的,具体在生产领域则是重视生产效率改进和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而不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引入新要素等,如黄宗智(1985,1993)在其过密化理论中所阐述的一样,固定的技术条件使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这种商品化不能导致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也不能拉动农村变革。具体在四堡印书业的族商中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的过密化投入。族商制度将书籍的生产集中于四堡地区,在印书业兴盛的300多年间,人口不断扩张的情况,虽有部分人外出经商,但多数人口密集于四堡这一小村落的印书业中,不可避免导致劳动力与资本在印书业中的过密化投入,而“‘过密化’可能带来的发展是有限的,生产越是密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上通过资本化提高生产率的道路”(侯且岸,1994:96-101)。何况在四堡地区,由于资本被大量用于诸如维持家族公益、家族责任、炫耀性消费如建房等方面以及家产析分,从而单个书坊的资产规模小,过密化更多表现为劳动力的过密化使用,这就使生产方式或技术变革的能力进一步减弱。
二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非生产化导向。在传统的乡士社会中,“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等观念被视为士绅阶层安身立命之本,而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则强化了以科举为提升宗族地位的理念。作为中原大族移居而来的客家人对此尤为看重,因而,读书为先的理念根深蒂固。为此,宗族子弟的最初选择是业儒,当科举晋身无路时才选择工商业,也就是,其人力资本的投资并非是为生产或经商的需要,而是为非生产性的科举的需要,鲍莫尔(Baumol,W.,1990)认为,任何社会都不缺乏企业家资源,一个社会之所以发展较慢或停滞,关键在于社会对人力资本的使用方向的激励错误,使人力资本用于寻租性的非直接生产性用途上,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读书做官的高收益,大量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对生产发展用途不大的科举上,因此,科举越发达,社会越停滞。而工商之家在累积起家业之后,只要有可能,则或转而业儒,或转而购地成为地主,以本守之(客家地区尚务本,有不少家族将宗祠起名为务本堂),这种儒商结合导致了弃儒经商和弃商业儒的循环或两难,结果使得经济持续性发展更加困难。
三是不能有效引入外部人力资源。四堡的印书业在销售方面是外向的,而其生产要素的组织却是内向的,其在管理、用工等方面主要使用宗族内部人力,在劳动力不足时才临时性雇佣周边村落人员,这一者是由于乡土的宗族责任,保障本宗族的充分就业与维护商业利益;二者是为了保护行业秘密,他们更愿意信任本族子弟,而不愿雇用外族人员,邹马两家世代联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保护秘密的需要;再者是由于四堡在群山环抱之中,引入人才在交通与区位方面处于劣势。人力资源内部循环不利于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的引入,技术进步能力缺乏。
四是市场定位低端阻碍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力的不足,使四堡印书业的生产更多表现为印刷书籍种类与印书数量的增加,而不是书籍质量的提升和新的生产方法的改进,进而使四堡书籍的市场方向固化于底层,而无能力与南京、广州等地的书商竞争,只能定位于边缘小城镇与乡村的收入较低的人群,而这种市场定位反过来弱化了技术改进的动力。技术进步能力的不足还使四堡的书商更重视商业上的扩展,而不是重视成本较高、风险较大、时间较长的生产技术改良。因而,当近代印刷业兴起之后,四堡刻印业由于资本和技术上弱势,无力应对外部新技术的冲击,在书籍经销高度依赖于生产的情况下,生产上的劣势转化为整个产业上的劣势,家族内部的工商联合体迅速瓦解,从业人员急剧由工商转而务农,印书业也就从此一蹶不振了。
(三) 族商制度阻碍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形成
阿夫纳·格雷夫(2008)在对比马格里布商人与热那亚商人时认为,马格里布商人建立商业网络时利用其熟人或同族网络,交易成本非常低,因而扩张速度非常快,但其边际成本很高,从而影响商人群体的转型和发展;而热那亚商人通过契约建立商业网络时,交易成本高但边际成本低,速度虽慢但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与扩张性,从而最终战胜马格里布商人。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四堡书商,他们依靠宗族的信用网络实现商业网络的扩展,交易成本较低,实现“几半天下”的伟业;但由于他们的商业活动都是家族成员的亲力亲为,对外宗族人员缺乏信任,从而不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形成,其扩张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在近代商业体系逐步形成后,其与马格里布商人一样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四) 族商制度不利于产业转型和多样化
四堡的邹、马两家的经济体系是一种族商、族工的高度结合体,他们世代从事刻书业,知识、资产、人际网络均是单一的、高度专业化于书籍的生产和经销,进入新行业的学习成本、转换成本极高,风险极大,不利于职业分化,如同“资源诅咒”一般弱化了转型能力,从而使产业的选择固化,一旦印书业因时代变化难以为继,其最优选择只能退回比较利益较低的农业。随着时代发展、新学兴起、科举制度风光不再,印书内容从应试所需的儒家经典,大量转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读物,四堡书商一方面无力获得新的书籍,另一方面,新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更新速度加快,四堡书商利用传统工艺无力跟上知识更新速度;同时由于外部技术冲击,四堡的书籍在质量、供应速度与成本均无法与新式印刷工艺相匹敌,退出印书业就是一个必然结局。
(五) 族商制度不利于形成良好激励体系
四堡印书业的创设,是为了宗族在山区更好的生存、更有条件教育子孙以重现祖先的荣光、更好地扩大宗族在区域的影响力,其收益分配必须保障这些目的的实现,因而大量利润被用于非生产性用途;同时,由于宗族与商业的高度结合,宗法代替商业规则,商业从属于宗族经济,获取宗族权力优于获取商业权力,因为获得宗族权利意味着获取商业上的话语权。为此,商人们更多地被诱导从事公益或读书应试,缺乏长期从业和扩大经营规模的激励;在随时准备退商业儒和退商返本的情况下,商人们不是“无恒产者无恒心”,而是“无恒业者无恒心”,为维持企业的更好的、可持续的发展也就不在选择集之中了。若无外部冲击,其可能在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勉强维持,而当非预期性的急剧性系统性变化来临时,商人要么破釜沉舟式转型以适应,要么只能是出现断崖式溃退;而四堡僵化的族商制度显然不能提供转型的方法与能力。
六、 讨论与结论
族商作为社会信用不发达社会的一种产物,在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使地区性的具有很强自然资源依赖性的产业能扩展到地方性范围之外,发展为全国性的产业。它通过宗族内部天然的信用网络所带来低内部交易成本抵消极高的商业扩展的外部交易成本;宗族的宗法结构对工商业的勃兴起到组织作用,从而降低了组织成本。
在社会制度背景与技术环境较为稳定的社会中,宗族力量与工商业力量互相支撑、互相联结、互相强化,从而形成一种导向产业壮大的路径依赖。四堡族商利用宗族的力量组织生产要素、开辟商路、实施扩大再生产等实现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进行商业合作与协调,实现有序的竞争,保证宗族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工商业上的成功反过来增强了宗族的影响力,对宗族权力的寻租使商人投身于宗族组织建设。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宗族与工商业进一步互相渗透,密不可分。把宗族与商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占主导而商业不发达的社会中是一种企业制度创新,族商在全国各地都存在,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的缓慢转型和发展。
但商业行为规则与宗族的行为规则毕竟不同,过于紧密的捆绑在一起使族商在一个体制和技术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反技术进步的宗法思想、违背商业利益的资本使用导致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缓慢,对族群之外人员的不信任和排斥导致现代企业制度难以建立,对宗族责任的过分坚守导致对产业发展激励的弱化,对生产要素投向过度黏性导致产业分工与转向能力的弱化等,使得闽西四宝刻书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里需要指出,四堡印书业族商的衰落有外部环境因素,但主要是内部因素导致的。如果不是族商这种僵化的企业组织形式抑制了创新和变革,那么,战争和动乱等外部干扰只是一时造成族商的衰落,一旦这种干扰结束后,族商还会重新繁荣发达起来。至于印刷技术的进步看起来是外部冲击,但实际上反映了四堡印书业族商内部缺乏创新动力的事实。
四堡刻书业族商的兴衰史充分表明制度创新及其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创新的重要性,这种创新导致四堡刻书业和族商的兴盛,同样也是这种创新的衰退导致四堡刻书业和族商的衰落和灭亡。族商制度从其本性是不鼓励技术创新的,更多只是一种模仿。已有理论表明:随着一国技术与前沿国家的技术越靠近,模仿将越困难,成本也越高(Robert J·Barro et al.,1995),从而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将不再可能;再者,模仿型的技术进步难以克服临界最小差距和后发劣势问题;最后,技术进步的路径可能会被锁定,长期模仿的结果是缺乏创新的思想、理论和人才积累,从而导致创新的成本和风险高企。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实现赶超,可以选择和采用某些新兴技术,直接以技术前沿为起点,在某些方面实施突破,实现赶超型的“蛙跳”战略(Brezis et al.,1993:1211-1219)。鉴于制度创新对技术、组织、市场等方面创新的基础作用,在经济新常态下,国家不仅应当建立一整套鼓励创新的制度,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企业也应当调整其技术进步路径,不断积累创新要素,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创新。四堡印书业的兴衰史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如果企业只是守成,而不是不断地根据变化的现实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当已有的制度和技术促进企业效率提高的效应耗尽,旧的制度与技术就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企业最终就必然会走向衰亡。对于古代企业如此,对于现代企业发展来说,更是如此。
[1]阿夫纳.格雷夫(2008).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兴起.北京:中信出版社.
[2]陈微(2009).清代闽西四堡坊刻“族商”市场理念.东南学术,4.
[3]陈支平、郑振满(1998).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
[4]范阳连城四堡龙足邹氏五修族谱.
[5]侯且岸(1994).资本主义萌芽.过密化.商品化.史学理论研究,2.
[6]黄宗智(1986).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7]黄宗智(1993).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
[8]连城四堡孝思堂马氏族谱.
[9]梁小民(2010).商帮中的家庭、家族与宗族.经济观察报,2010-07-18.
[10] 刘永华(2008).包荺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评介.历史研究,4.
[11] 马卡丹(2007).千年回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2] 史晋川(2004).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浙江社会科学,2.
[13] 汤露(2005).明未清初四堡印刷业兴盛的原因探析.龙岩学院学报,4.
[14] 泰勒·考恩(2015).大停滞?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美国的难题与中国的机遇.王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5] 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1973).西方世界的兴起.历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6] 项旋(2011).明清时期福建四堡的宗族发展与雕版印刷业——关于邹氏与马氏家族坊刻的调查与研究(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七届青年学者论坛.
[17] 曾玲、马卡丹(2000).四堡雕版印刷业的兴起与衰落.中华文化明珠四堡.岩新出内书第186号.
[18] Baumol,W(1990).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unproductiveanddestructive.JournualofPoliticalEconomy,5.
[19] Bolin R,StanfordL(1998).TheNorthridgeEarthquake:VulnerabilityandDisaster.New York:Noutledge.
[20] Brezis,Elise S & Krugman,Paul R &Tsiddon,Daniel(1993).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AmericanEconomicReview,AmericanEconomicAssociation,83(5).[21] Cynthia J.Brokaw(2007).CommerceinCulture:TheSibaoBookTradeintheQingandRepublicanPeriods.Cambridge:Harvard Asian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
[22] Redding,S.Gordon(1991).Weak Organizations and Strong Linkages:Managerial Ideology and Chinese Family Businese Networks.InHamilton,G.(ed.).BusinessNetwok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EastandSoutheastAsia.Hongkong: University of Hongkong.
[23] Robert Barro & Sala-I-Martin(1995).EconomicGrowth.New York:McGrawhill.
■作者地址:戴腾荣,龙岩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龙岩 364012。Email:dtengrong@qq.com。
郭熙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xbguo@whu.edu.cn。
蔡立雄,龙岩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龙岩 364012。Email:clx213fjfj@163.com。
■责任编辑:刘金波
◆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Clan Business and Sibao Printing Industry in West Fujian
DaiTengrong
(Longyan University)GuoXibao
(Wuhan University)CaiLixiong
(Longyan University)
Sibao printing industry was conducted within the family group. As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penetrated to traditional family governance structure, it eventually formed large economic units within the family.Therefore,the clan business has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blood relationship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and the mutual binding and support of clan power a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ower.Based on the clan business institution innovation,sibao printing business carried on innovations of organization,markets,products,and distribution, and realized the expanded reproduction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in clan economy,making it an influential book business group in ancient China.But commerce and clan power tied too tightly to make clan business lack of adequate flexibility when confranting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es.Its traits against technological progress,social credit,capital input for commercial interests,and its weakness incentive structure and excessive rigidity in factor usecausedits quick collapse in printing industry and clan business under social changes.Innovations ever created the prosperity of clan business in its beginning,yet refusing innovation led its fall in the e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clan business;sibao printing industry
10.14086/j.cnki.wujss.2016.06.008
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福建省高等学校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FJ2015B087);龙岩学院国家社科基金培育计划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