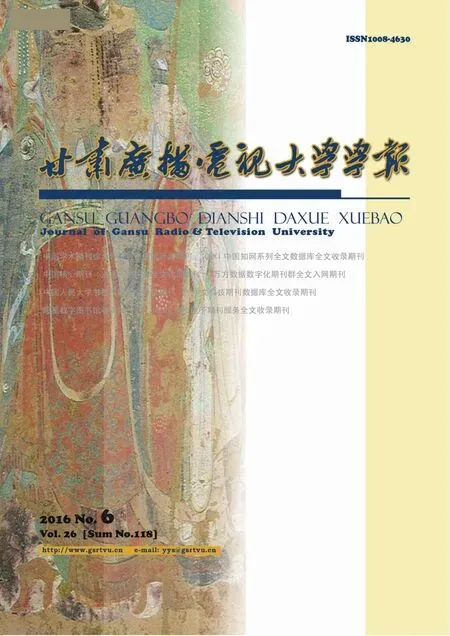网络强国背景下的网络行为文化创新研究
2016-03-09胡思琪张玉强
胡思琪,张玉强,赵 楠
(广东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网络强国背景下的网络行为文化创新研究
胡思琪,张玉强,赵 楠
(广东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建设网络强国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网络行为文化是网络文化的重要构成和现实体现,其创新发展对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价值。研究从网络行为文化的内涵及构成出发,针对网络行为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网络行为信息安全保护体系不健全、网络行为治理不到位、网络行为伦理不规范等问题,探析网络行为文化建设的创新路径。
十三五规划;网络强国;网络行为文化
21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网络大国。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同时,互联网的使用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更多方面,截至2015年12月,通过互联网实现在线教育、网络医疗、网络预约出租车的网民分别达到1.10亿、1.52亿、9664万人[1]。在2015年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指出,“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多中国人民,更好造福各国人民[2]。可见,从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国家层面的战略带动了理论界对网络强国建设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网络强国战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理论解读,明确网络强国的内涵、战略目标、实施要求等问题,有利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推动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二是重点针对网络安全开展研究,对区域性数据档案中心的建设、信息安全产业的发展、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建立和互联网安全思维的树立提供了建议。网络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包括以信息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硬件建设,也离不开以网络文化为核心的软件支持。当前,虽然部分学者强调了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但对如何创新网络文化发展,使其对网络强国建设发挥更好的支撑作用还缺乏一定的研究。以网络行为文化为对象进行研究,以这一网络文化集中体现为切入点,既可以把握网络文化的重要作用机理,又可以为网络文化创新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思路。
一、网络行为文化的内涵及构成
网络行为文化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化是“包括一切与信息技术网络有关的物质、制度、精神创造活动和成果,即以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的文化,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丁三青和王希鹏认为,网络行为文化是人们在网络空间活动本身构成的文化,分为网络行为活动规范和网络行为方式。网络行为活动规范是人们在网络活动中所遵循的规则和要求;网络行为方式是人们依赖网络进行的各种消费、娱乐等活动[3]。本研究认为,网络行为文化是在计算机网络空间环境下所创造的消费、社交、娱乐、教育等行为活动的综合体,具体包括网络消费行为、网络社交行为、网络娱乐行为、网络教育行为。网络行为文化具有能动性、自主性的特征,区别于网络物质文化与网络精神文化。同时,网络行为文化与网络物质文化和网络精神文化相互联系,网络行为文化以网络物质文化为基础和前提,又受到网络精神文化的影响,三者相辅相成。
网络消费行为指的是人们在计算机网络空间环境下消费网络文化产品和网络文化服务的行为过程。网络消费行为具体表现为人们利用网络媒体消费书籍、视频、图片、动漫、游戏等各种文化产品及利用计算机网络硬件在线上消费网络文化服务。诸如利用网上银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平台在天猫、唯品会等网站享受的网络购物服务等。由网络文化产品和网络文化服务构成的网络消费行为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体现了网络消费主体极大的自主性。
网络社交行为指的是人们在计算机网络空间环境下沟通交流的行为过程。网络社交行为具体表现为人们利用SNS、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博客等网络社交工具表达自己的观点、诉求及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美国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教授提出了六度分隔理论,即世界上任何两个人通过六个人就能建立联系。网络社交行为大大拓宽了人际交往的范围,为六度分隔理论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基础。
网络娱乐行为指的是人们在计算机网络空间环境下的娱乐行为过程。网络娱乐行为具体表现为人们可以通过酷狗、全民K歌等音乐软件聆听歌曲以及发布自己唱的歌曲;通过爱奇艺、优酷等视频平台看电影、电视等网络视频;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英雄联盟等MMORPG的网络社群游戏。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等网络娱乐行为可以缓解人们的生活压力,减少孤独感,给网络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
网络教育行为指的是在计算机网络空间环境下进行学习、教育的行为过程。网络教育行为具体表现为在MOOC、网易公开课、iTunes U等网络教育平台上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学习知识的过程。网络教育突破了传统封闭式的教学方式,突破了传统教育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促进了教育的改革。网络教育行为能够提高网民的素质,为网络生活的有序进行提供保障。
网络消费行为、网络社交行为、网络娱乐行为、网络教育行为是网络行为文化的构成部分,也是网络行为文化的表现形式。网络社交行为和网络娱乐行为具有提高网络行为文化知名度的价值,网络教育行为具有提高网络行为文化美誉度的价值。网络社交行为、网络娱乐行为和网络教育行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水平为网络消费行为发挥忠诚度的价值奠定了基础。
二、网络行为文化创新对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价值
(一)网络行为文化建设是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强国建设是一个系统、综合、长期的工程。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网络强国系统建设包括了基础设施、话语权、网络文化、制度化等内容。网络强国建设与网络行为文化建设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网络强国建设包含网络行为文化的建设。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的网络行为文化的创新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二)网络行为文化为网络强国战略提供精神内涵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行为文化所具有的共存、共生、共享的精神为具有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特征的网络强国战略提供了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共存、共生、共享的网络行为文化为网络强国战略提供了网民的思想支柱。只有提高网民的整体素质,才能从根源上防止网络欺诈,加强网络安全及网络资源的共享。另一方面,共存、共生、共享的网络行为文化提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
(三)网络行为文化产业是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经济构成
在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期,网络行为文化也在不断实现着其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形成了大量的网络行为文化产业。网络行为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创新能够促进网络消费的增加,其突破时空限制的特点,决定了它比传统行为文化产业更能带动消费的增长。其创新升级让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更好地获取网络文化产品和网络文化服务。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十二五”期间,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 3.61亿,网购在网民中的渗透率达到55.7%;网络零售交易额规模达到27898亿元,同比增长2.6倍,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4]。网络行为文化产业的创新升级能够很好地促进内需,带动网络消费的增加,使网络经济繁荣发展。
(四)网络行为文化为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动力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行为文化会带动网络消费行为、网络社交行为、网络娱乐行为、网络教育行为的活跃,从而带动网络行为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网络教育的改革创新。尤其是通过社交网络软件发表自己观点等网络社交补偿性行为文化,有利于带动人们思维的活跃。也就是说,网络社交补偿性行为文化一方面有利于反映民情,在社交网络中网民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科技等方面发表自己的观点,有利于改革创新。另一方面,有利于学习、生活类的信息流通,网络的多元化消费和娱乐行为也有利于反映人们新的需求,有需求就会有改进及创新。
三、网络行为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网络信息安全保护体系不健全
在网络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网络行为文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信息安全保护体系不健全的问题,社交网络信息安全危机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社交网络的信息安全没有保障,很容易受到攻击和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况。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站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报告(2015)》显示,2014年全体网民中有46.3%的网民遇到过网络安全问题。中国反钓鱼网站联盟在2014年共处理钓鱼网站51198个,平均每月处理4266个[5]。诸如2011年新浪微博受到XSS攻击的事件,2014年携程网信息安全门事件以及2014年考研信息泄露事件等社交网络信息安全等事件的发生,都说明社交网络信息安全保护体系还不健全。
一方面,虽然我国也出台了一些关于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但是其条文不够细化且执行不到位。2000年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法律。2012年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是对公民网络信息安全保护的条例。2016年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加强了对应用程序的规范管理,但没有明确具体处罚办法。尽管如此,但针对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社交网络个人信息泄露事件还没有专门制定出《个人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法》。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机构数量少而且发展缓慢。只有像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才有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协会等机构,很多二、三线城市并没有成立相关的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组织。网络行为的信息安全危机以及当前不健全的网络安全体系不利于网络行为文化的进一步推广。
(二)网络行为治理不到位
在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建设网络行为文化存在治理不到位的问题。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虚拟社会中社会力量显现出一种无序的强大,虚拟社会的无控制与分散性增大了网络治理的难度;另一方面,网络行为的管理方式还是主要以传统的发布命令等控制式的行政手段为主,与多元网络行为治理主体的背景不符。在网络社交文化发展中,网络信息传播、舆情引导治理是最为常见和重要的治理手段,在这方面我国尚存在着诸多不足。
第一,对虚假信息的传播治理不到位。在互联网虚拟社会中,对信息的传播具有无中心性和无边界性的特点,网民既是虚拟社会的主体也是客体,既是信息的制造者也是传播者。由于一些网民的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知识结构不健全,对一些信息不能分辨真伪,一些不法分子就会利用心态引导作用,促使网民传播虚假信息。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联合微信安全团队发布的《微信年度谣言分析报告》显示,传播最为广泛的五大热门谣言阅读量均超过2000万次,并经过多个公众号转发。网络谣言得以广泛传播是因为网络谣言传播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第二,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不到位。网络舆情是网络社交行为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不到位很容易诱发网络突发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多发性、多源性、多向性[6]的特点符合网络突发群体性事件自发性、群体性、组织性等特征的要求。网络突发群体性事件起初大多都是小事件,经过多种因素的诱发及公众情感的凝聚而产生,而在这个过程中网络舆论没有得到有效引导,就会很容易突破网络突发群体性事件的临界点,酿成网络突发群体性事件。在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的网络热点事件中,天津港特大爆炸事故尤为突出,该网络舆论事件热度较高,为95.21;舆论共识度、政府认同度、网民正能量、网络舆论生态指数都很低,分别为2.66、2.29、0.36、5.31[7]。正是因为没有及时通过新闻发布对错误的网络舆论进行引导,致使正确的网络舆论无法发挥主导作用。
(三)网络行为伦理不规范
网络行为伦理的不规范主要表现为沉迷网络、网络诚信缺失、网络犯罪等问题,其成因如下。
第一,网络行为伦理理性的缺失。伦理道德是一种规范,道德是主观的,伦理是客观的,二者具有深刻的精神同一性,也存在着深刻的精神风险[8]。所以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通过理性来协调道德和伦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使道德主体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时能遵循道德和准则[9]。一旦道德主体理性缺失便容易陷入网络行为道德危机之中。一旦网络行为伦理道德理性缺失,在互联网虚拟性、无序性环境下的行为因缺乏理性的思考,网民的自律行为就会弱化,沉迷网络、网络诚信缺失、网络犯罪等行为就会频频发生。互联网虚拟性的特征使得网络信息不对称显得尤为突出,在网上购物过程中,消费者和商家在商品信息的了解上存在差异,商家会隐瞒商品的一些瑕疵信息,消费者只能通过照片和文字对商品进行判断,因此就会出现收到的商品货不对版、质量劣质的情况。这种网络行为伦理道德理性的缺失使得网络道德诚信危机加重,阻碍了网络行为文化的建设,对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网络行为伦理道德教育的不规范,网民没有形成一种由内而外的自我约束能力。这是社会对网络行为伦理道德教育不重视的结果。一方面,学校很少开设关于网络行为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的课程,没有把计算机的应用与网络道德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没有营造网络行为道德教育的氛围,没有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在网络行为伦理道德建设上没有起到宣传导向作用,很少有关于网络行为伦理道德的学习及宣传资料,如网络行为伦理道德的评判标准等,使网民的网络行为伦理认知存在偏差,更容易使网民的网络价值观模糊,从而影响网民的网络伦理行为。
四、先进网络行为文化建设的策略
(一)健全网络行为信息安全体系
健全网络行为信息安全体系是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先进网络行为文化建设的重点。
第一,完善网络行为信息安全保护法。作为网络大国, 我国的网络安全危机不断加剧,影响了我国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进程。为了更好地实现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的转变,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但是这部草案涉及的多为国家网络安全,对于私人网络安全方面几乎没有涉及[10]。针对我国个人信息安全日益严重的问题,应该专门设立《个人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法》,细化社交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条例,保护个人在网络行为中的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在法案中应明确规定发布、泄露、出售哪些信息是违法的,以及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等。
第二,培育网络行为信息安全保护机构,这符合我国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的趋势,也为我国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中网络公民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政府应推动网络行为信息安全保护组织的发展,为其发展创造条件,降低成立标准等限制,给予更多的支持。加快网络行为信息安全保护组织平衡发展,不但在一线城市要促进这些组织的发展壮大,在二、三线城市也要推动这些组织的组建及发展,提升其专业性,为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网络行为信息安全的保护工作起推动作用。
第三,建立网络行为信息安全预警机制。通过借鉴美国基础设施信息安全检测预警机制及我国网络舆情检测预警机制的经验,建立网络行为信息安全预警机制。包括建立网络行为信息安全检测预警组织,建立网络行为信息安全预警指标,规范检测预警网络行为信息收集和分析方法,建立具有实时报警、严格执法响应等功能的网络行为信息安全检测预警处置机制[11]。
(二)改善网络行为的治理方式
改善网络行为的治理方式需要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公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通力合作来实现,以区别于以往政府对网络行为自上而下命令式的管制方式。
第一,对虚假网络信息传播的治理需要从传播源、传播主体及传播过程分别进行治理。要加强对传播源及传播主体的网络道德教育及其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加大网络教育资源的发布与分享,提高网民的素质与网络行为能力水平。由于我国的公民社会还未建成,互联网中社会力量的强大是一种无序的强大,所以需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来共治。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对网络平台的信息进行监管,成立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承担不同信息监管的职能,细化非政府组织对信息监管的类别。通过这样的方式掌握网络舆论的制高点,对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根据网络舆情的检测预警指标判断网络舆情的轻重缓急程度,对网络舆情进行分类引导[12]。对未达到网络群体性事件临界点的网络舆情,应采取公布正确信息的策略。政府要尽快发布权威性的信息来引导舆论的方向,对达到网络群体性事件临界点的网络舆情,应立即启动网络舆情检测预警系统。
第三,在源头上加强对私人网络游戏机构及个人的道德教育,在改善治理方式过程中强调政府与网络游戏行业协会的共同治理,推动网络游戏行业协会的发展,提升其对网络不良游戏的监管能力与水平。
(三)加强网络行为的伦理道德教育
加强网络行为的伦理道德教育是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网络行为文化创新建设的一部分,是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中融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网民整体素质的基础。
第一,培养网民网络行为伦理道德意识。首先,加快网络行为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包涵着深远的德育文化,加快融合速度,能使网民在网络行为中潜移默化地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其次,创新网络行为伦理道德教育宣传方式,促进网民自觉提高自身的伦理道德文化意识。
第二,加强网络教育平台建设。政府、学校及有关的第三方组织应加大对网络行为伦理道德教育资源的分享,使企业、家庭、个人能通过网络教育平台对网络行为伦理道德有正确的认知,使网民的网络价值观由模糊转向清晰。通过社会每一个成员的重视和学习,从整体上提高网民的素质,以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形式,共同规范网络行为。
[1]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6-01-22)[2016-06-20].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6/2016 01/t20160122_53283.htm.
[2]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2015-12-16)[2016-02-20].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6/c_1117481089.htm.
[3]丁三青,王希鹏.网络文化概念及内涵辨析[J].煤炭高等教育,2009(3):1-5.
[4]田超.五中全会定调网络强国,互联网引领经济新常态[N].通信信息报,2015-11-04(2).
[5]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站发展安全状况及其安全报告(2015)发布[EB/OL]. (2015-03-20)[2016-02-20].http://www.isc.org.cn/zxzx/xhdt/listinfo-31793.html.
[6]王杨,石翠.移动互联时代网络舆情的特点与引导[J].青年记者,2015(14):30-31.
[7]人民网.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2015年网络热点舆情[EB/OL].(2015-12-24)[2016-02-20].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5/1224/c401685-27972434.html.
[8]樊浩.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轨迹及其精神图像[J].哲学研究,2015(1):106-113.
[9]张玲,王舜.网络技术与伦理道德[J].科学管理研究,2003(6):52-55.
[10]刘德良.关于网络安全立法的几点看法——兼评网络安全法草案和刑法及其修正案[J]. 中国信息安全,2016(3):103-106.
[11]王玥,方婷,马民虎.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监测预警机制演进与启示[J].情报杂志,2016(1):18-23.
[12]张玉强.网络舆情危机引导策略研究[J].理论导刊,2012(1):23-26.
[责任编辑 龚 勋]
2016-09-03
胡思琪(1992-),女,广东惠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张玉强(1978-),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科技服务等研究。
F49
A
1008-4630(2016)06-00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