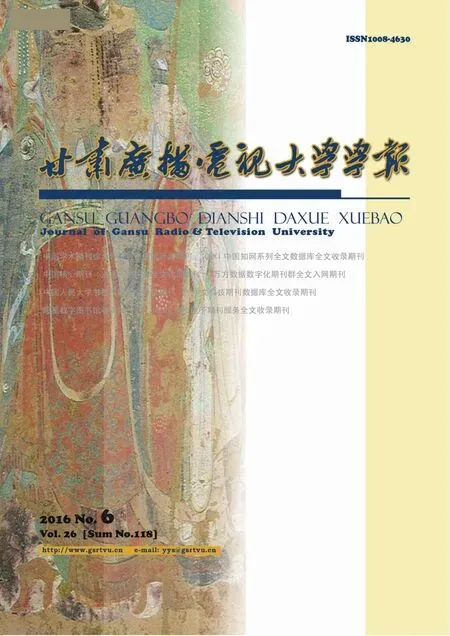论小说《末代紧皮手》的物性、人性和神性
——甘肃“小说八骏”李学辉作品解读
2016-03-09孙玉玲吕海勇
孙玉玲,吕海勇
(河西学院 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论小说《末代紧皮手》的物性、人性和神性
——甘肃“小说八骏”李学辉作品解读
孙玉玲,吕海勇
(河西学院 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小说《末代紧皮手》描述了解放前后的河西乡村和农民生活,通过对土地的物性、人物的人性、人和土地的神性,以及三者对立统一的描绘,表达了西部农民对土地的崇拜与敬畏,以及土地风俗远去时他们命运的喜悲起伏,展现了农民和他们的乡土世界被改造的过程。
《末代紧皮手》;物性;人性;神性
李学辉是甘肃“小说八骏”之一,其作品多关注河西走廊的乡村、农民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小说《末代紧皮手》是其代表作。作品以巴子营村的特殊农民——最后一位“紧皮手”余土地的一生为线索,珠连了与土地相关的“土地改革”“农会”“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各种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巴子营村农民在这些运动里围绕土地崇拜的各种行为,展现了农民和他们的乡土世界被改造的过程。小说围绕土地的物性、人物的人性、人和土地的神性,以及三者的对立统一,表现了土地风俗远去时人们命运的喜悲起伏。这也是在现代化背景之下,作者对依土而生的农民生活、生存处境的思考,更是对中国乡土社会变迁和乡村现代化的一种理性审视与反思。
一、物性——大地永恒的力量
土地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有很强的物性特点,其中最根本的便是固态性、不可移动性,而这种特有的物性对依土而生的农民从生活到思想上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费孝通说:“‘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1]土地为农民提供衣食住行,是他们的生命保障,这样的基本功能从未因社会的变迁而改变。与此同时,土地和农民之间也形成了一种“互渗关系”,这种“互渗关系”“等于是一种神秘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不能让与、窃取、强夺的”,因为土地中已包含着农民“对一个地域、一种人生环境的认同感”[2],也是他们社会身份和自己在乡村中主体地位的确证,因此,农民对土地的爱是渗透到骨血和灵魂里的。
小说《末代紧皮手》首先写了土地的这种物性。土地是用来长庄稼、养活生活在大地上的农民的,农民的人生追求就是用自己的辛劳换得饱暖。因此在巴子营,农民们对土地的依赖没有时代、等级、性别和老少之分。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土地无论私有还是公有,无论面对怎样的社会变革,巴子营人对土地的态度是不变的,他们在土地上以近乎疯狂的方式生活和劳作,无论春夏,还是秋冬,翻地、种植、除草、收获、紧皮,都围绕赖以生存的土地进行。尤其是每年冬天紧皮手的紧皮工作,原本是借助人力给土地保墒,但在多年的传承中已神圣化,其中传递出的是巴子营人对土地至高至纯的热爱与崇敬。与此同时,巴子营人已经把土地的这种物态性内化为了自己精神和心灵的保守性,呈现出对土地顽强的守护意识。无论土地曾经属于地主何三私有,还是之后属于巴子营村公有,他们都对其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何三在土改分田时,用沉塘的方式祭奠失去的土地。中国乡村长期以来以土地为基础,形成了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使得乡村除了保守性之外,也有排他性。因此,面对与土地物性相悖的外在力量时,巴子营人表现出的是对土地的顽强守护,也呈现出他们强烈的保守性与排他性。
除却物性,社会性也是土地鲜明的特点。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中,一系列的土地改革运动便承载着各种社会内容,有时,土地的物性与社会性因各种原因产生剧烈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调和者只能是人,他们的命运便会在这种矛盾与调和中发生变化。在《末代紧皮手》中,最令人深思的是建国后国家意志的执行者袁主任与巴子营村农民之间的矛盾。袁主任在巴子营村土地上以国家的名义推行各种运动时,土地偏离了其物性,成为了各种社会力量较量的载体。运动的背后,是政权执行者想用自己的思想意识和力量去打破土地原有的物性,使其社会性更加凸显,附加更多的意识形态内涵,这样的行为在表面上是打破巴子营人在土地上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建另一种符合国家意志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在深层上,其实有着对土地主宰权的争夺意味——土地究竟属于农民还是政权执行者?究竟谁是土地的主人?如此一来,以袁主任为代表的新生政治力量以破除“牛鬼蛇神”的名义,试图打倒巴子营人以紧皮手为核心的权威时,这些土地坚守者们用集体力量甚至个体生命,来捍卫土地的物性、尊严,以及自己在土地上的利益与主体地位。
作品中何菊花和余土地的死是值得深思的,表面看来,这是人与人的冲突所导致的悲剧,但其实质是土地的物性与社会性的冲突。个人的力量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可逆向而行,面对不可改变的土地的物性与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巨大冲突,能平衡这种冲突的只能是生存其上的个体的人,因此,何菊花、余土地的死就成了必然,他们成为土地物性与社会性矛盾的调和者,同时也是这两种力量冲突之下的悲剧的承受者。
二、人性——大地之子永恒的美
“土地”的颂歌与悼歌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永恒母题,与此相关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对土地的歌颂和崇拜,他们也在土地上演绎了一段段悲剧故事,而在这种悲剧中,恰恰也折射出中国农民伟大的人性。
在作品中,作为土地之神的替身,余土地是一个“人神一体”的角色,在成为“紧皮手”之前,他只是一个肉身凡胎的农民,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在成为“紧皮手”之后,非紧皮时节里,他依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种地,帮人干活,饲养牲口。他和其他农民一样,身上凝聚着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勤劳质朴、乐于助人的品质,以及对土地的热爱。比如,成为紧皮手的他冒着犯禁忌的风险,偷偷从凉州城跑回巴子营,只是为闻一闻土地的气息与五谷成熟时的味道,以求得心灵的踏实。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对土地特有的情感和一种虔诚的热爱。当社会剧变,在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冲击下,他也从来没有因成为“牛鬼蛇神”或是“成份”问题而抱以怨言,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土地上劳作,并默默坚持着紧皮手的责任。作为农民的他,人性中的其他杂念都烟消云散,发出最耀眼光芒的是对土地诚挚的爱。土地之子们为土地所唱出的赞歌,是其人性深处最美的一面。这是对土地虔诚的歌颂,更是对人性之美的歌颂。
男性是土地神的继承者,有着坚毅的性格,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也不缺少对土地的热爱。作为地主女儿的何菊花,虽在本能与责任的泥沼中拼命挣扎,但在经历过诸多苦难后,依然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土地。当面对社会变革对土地的冲击时,她用女性最宝贵的肉体和自己年轻的生命护住了象征土地崇拜的“龙鞭”,把土地之子的人性美放大到了极限。而另一位女性王秋艳则用拒绝婚姻来换得对土地的热爱。身为女子,她们用自己的生命唱响了对于这片古老土地的颂歌,她们的人性之美也在自身本能与欲望的斗争中得以体现。无论是对土地的赞美,还是人亡事变的悲剧,对土地的热爱致使巴子营人面对外来势力时,显示出人性的美。
悲剧色彩是现代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或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3]而正是在这种斗争和超越中显示出人性的伟大。小说中,无论是作为“紧皮手”的余土地,还是身为女性的何菊花,都凭着对土地的挚爱和身上的责任,在灵与肉的痛苦搏击中,展现了人性的伟大。尤其是余土地,他抛却了一切欲念,包括对何菊花的爱,只为坚守自己的信念。随着社会变化,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当“紧皮手”成了革命的对象时,尽管他命运无常,苦难无数,肉体与精神都遭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与摧残,但他依然人性地活着。余土地的命运,是社会历史变迁中各种力量冲突的结果,但正是在这种悲剧中,他和巴子营人超越了外在社会力量强加于他们肉身与精神的双重苦痛。这是一种悲剧的美,也是一种人性的光辉。
三、神性光环的黯淡
就如小说的名字一样,“紧皮手”是中心。在小说开头,作者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末代紧皮手庄严神圣的选举仪式和过程,激水、拍皮、入庙、挨鞭、改名等一个个环节都有一整套的具体仪式、禁忌和讲究,并且通过近乎宗教的仪式展现了余土地这样一个“人”到“半个废人”再到“神”的神性赋予过程。这种神性是把对土地的爱神圣化、宗教化,因此,作为土地爷化身的“紧皮手”余土地,受到了巴子营人的敬畏与崇拜,他们用行动承认和守护了他这个存在于人间的“神”的地位。这些仪式的内容指向土地这一核心,从何三选“紧皮手”到农民们争抢着让余土地紧自家的地,从新生政权下用自家粮食支持余土地的生活,到旱田时想起余土地这个土地爷,巴子营书记道出了其中的意义:“土地和人一样,得有个念想,没个土地爷,谁把土地当回事。土地供人种,养活人,人这东西很难说,心中有了神,人就有了约束。”[4]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知道,在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大西北,土地对于他们重要,他们要用“神”的精神去约束自己。土地无论是私有还是公有,它已是农民生命、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余土地的命运陷入怎样的悲剧之中,在巴子营百姓眼里,他依然是他们的“土地之神”。成立公社时余土地一加入公社,其他人便争先效仿;被迫扮演地主的余土地在巴子营百姓眼里怎么看都像土地爷;巴子营最美的两个女人都爱恋他……余土地看似是巴子营的边缘人物,但是,他的一言一行却影响着巴子营。当农民们用敬神的思想去看待余土地时,他们的希望变得单纯而朴实,他们只希望土地上能种出赖以生存的粮食,他们也就有了传宗接代的希望。土地能养育他们的生命,也就能养育他们的精神和心灵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土地爷和“紧皮手”已成为他们的精神信仰,甚至宗教。
作为土地之神的替身,余土地是一个“人神一体”的角色,作为“土地神”的代言者,余土地同时也承受着社会剧变带来的土地神性剥落的悲剧。当“紧皮如紧先人的皮”这样的话在巴子营疯传的时候,罩在“紧皮手”脸上的面纱已被挑落,把紧皮作为毕生理想去坚守的余土地也必将走向死亡。当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带来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时,新政权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便是巴子营人“精神寄托”的“紧皮手”和“紧皮”仪式。作为这项活动最有力的执行者和利益的获得者,地主何三沉塘自杀,便是这个仪式的神性走向消亡的开始。接下来土地被分,土地爷的代言者“紧皮手”成为封建落后观念的代表,需要被新的社会和新的政权去改造。即便是巴子营人暗中还进行着“紧皮”这一活动,代表新政权的袁主任还是通过自己所握的权力,一次次弱化这一仪式在人们心中的影响,从而强化他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形象,哪怕以牺牲鲜活的生命为代价。尽管巴子营人进行了抗争,但并未取得最终的胜利。何菊花的死,就是新政权下人们为保护以“龙鞭”为象征的精神寄托进行的极端抗争。在何菊花的心中,“龙鞭”就是土地神的象征,是她全部的精神信仰,失去了龙鞭则意味着失去了信仰。最后她毅然决然地舍命护鞭,甘愿为内心的信仰奉上年轻的生命,同时也带动了巴子营人全体护鞭。但这些力量还是弱小的、分散的。当新一轮的攻击开始,攻击对象直指“紧皮手”余土地时,化装闹生产、结婚、紧皮、剜毒根这一系列从精神上到肉体上的摧残和打击,都是对土地神性光环的强制剥夺。末代“紧皮手”最后终于死了,王秋艳把那条象征着神性的龙鞭连同余土地埋在了一起,这埋下去的也是巴子营人对土地神性的最后崇拜与依恋。当王秋艳默默完成一个本不该由女性完成的土地崇拜仪式时,更凸显出其神性的剥落。
对土地的神性崇拜原本是农民对土地挚爱的表现,是农民心中表现出来的对土地的最高精神信仰,遍布于中国乡村的土地庙,就是他们依土而生的对美好生活愿望的寄托和载体。随着时代的变化,原本被歌颂的精神信仰成为了封建迷信,原本对于土地挚诚的爱被当成社会发展的阻碍,因此,“人神一体”的“紧皮手”的消亡是用外在力量对土地神性的强制剥夺,更是历史发展潮流里对农民土地意识的人为改造,当土地的神圣性走向衰落之时,也是农民的土地意识由浓变淡之时。如此,表面上《末代紧皮手》表达的是一种对乡村风俗逝去的怀念,更深层表达的则是作者在新时代沉重的土地意识。“知识者对于自己的‘土地爱’或许比对土地更为迷恋”[5],李学辉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西部作家,他对于土地的描写既是对“大地母亲”诗意化的赞美,也是面对现代化、工业化取代农业化的社会大潮时,对土地消失的哀叹和对农民们生存境遇的深入思考。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2]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06.
[4]李学辉.末代紧皮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88.
[5]赵园.地之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7.
[责任编辑 龚 勋]
2016-07-28
2015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新乡土’ 视域中的甘肃当代乡土小说研究”(2015B-105)。
孙玉玲(1975-),女,甘肃民乐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西部文学研究。
I207.42
A
1008-4630(2016)06-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