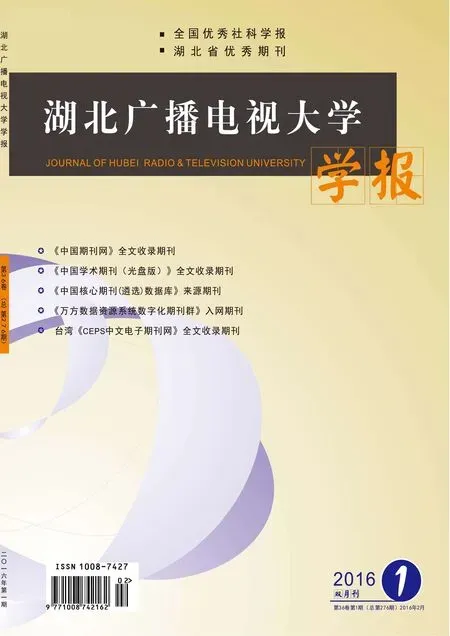从“男性”自我到“生态”自我
——《啊,拓荒者!》中亚历山德拉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
2016-03-07朱萍
朱萍
(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
从“男性”自我到“生态”自我
——《啊,拓荒者!》中亚历山德拉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
朱萍
(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0)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了《啊,拓荒者!》中女主人公亚力山德拉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刚开始女主人公是持男权观念的,对女性特质和自然的态度是排斥、征服式的,后来她逐渐认识到女性特质和自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接受认可了自身的女性特质并和自然融为一体,最终实现了从“男性”自我到“生态”自我的转变。
薇拉·凯瑟;生态女性主义;“男性”自我;“生态”自我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西方文化中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有同一思维根源即男性中心主义世界观,其核心是二元思维模式,认为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思想/身体、自我/他者等都是对立的二元存在。这些二元关系中,前者是属于高等的文化范畴,后者属于低等的自然范畴。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女性和自然扮演着同样角色,即都是作为构建“男性”自我的低等“他者”而存在,遭受排斥和压制。生态女性主义旨在打破这种思维模式,提倡构建相互关联的“生态”自我,即反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提倡两者相互依存关系,承认自然本身拥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尊重、同情自然和所有生命,提倡自然界生命通过合作、相互照料、爱来维持。
美国现代著名女作家薇拉·凯瑟(1873—1947)的代表作《啊,拓荒者!》自问世以来便获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小说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被认为是一位完美的“大地母亲”,被女权主主义批评家沙朗·奥·布莱恩称赞为“一个完美的女性,一个强大的非男性英雄,一个用爱驯服荒地的创造者”[1],体现了女性与自然天然和谐的内在一致性。本文拟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探讨女主人公对自我与自然认知的发展过程,分析她是如何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大地母亲”。
二、“男性”自我到“生态”自我的转变
小说中亚力山德拉对自我和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从“男性”自我到“生态”自我这一转变过程。青年时期,在性别意识和自然观念上,亚力山德拉表现出明显的男权倾向。她对自我和自然的认识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自我/他者之上的,这个时期她对自身的女性特质是排斥的,对自然的态度也是征服式、功利主义的。后来在艾弗和麦丽等人的影响下她开始承认和接受自身的女性特质,在大自然中逐渐认识到自我,最后经过埃米尔事件,她才真正认识和懂得土地的价值,认可了自然和女性的应有地位,女性和自然的关系变得真正和谐、融洽。
(一)对“他者”的排斥阶段
生态女性主义一个主要关注点便是女性与自然。它认为一个人对自然和女性及与女性特质的认识并不是由人的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一种心理性别的认同。在小说开头,亚力山德拉是以一个男性形象出场的:“她,很高且很强壮,走起路来步子既快又坚定有力。她穿着一件男人的长外套(看起来一点不难受,倒是很舒服的样子,好像本来就属于她的……)”[2]6。在心理学上,异性化着装是个人内心对异性审美的认同。安妮·伍德沃斯认为:“人的外表塑造人的身份意识并被这种身份意识所塑造,外表是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一大信号”[3]。女主人公的易装行为是对自我女性审美的放弃,对男性审美的追求,也是其男性化倾向的外在表现。当一个推销员夸她长得一头好头发时,亚历山德拉并没有表现出传统女性的高兴与矜持,她咬紧了下唇,以“古希腊英雄的气概狠狠瞪了他一眼”[2]7,吓得那小伙子手里的香烟都掉了。亚历山德拉对男性赞美的过激反应,说明她对自身女性特质的排斥,希望别人把她看作男性。
这一时期的亚历山德拉经常做同一个梦,在梦里她被一个强壮的人搂在怀里,“这人当然是一个男人,他比她所认识的男人都强壮,魁梧,敏捷许多……”[2]110。这个梦境表明亚历山德拉潜意识里对性的一种自然生理需求。然而,亚历山德拉每次醒来后都非常生气,她冲到浴室用冰冷凉水使劲擦洗自己身体。亚历山德拉之所以对自身作为女性的正常需求感到生气,是因为其内在的男性化思维,认为女性特质和身体是低等的存在,是弱者的象征,是其构建“男性”自我的威胁,因此必须受到压制。
早期的亚历山德拉对“女性他者”的排斥也体现在和母亲伯格森夫人的疏远关系上。作为家中的长女,亚历山德拉乐于和父亲讨论如何种植庄稼,饲养牲畜,是父亲的得力助手。然而与母亲她却很少有感情上的交流。伯格森夫人是一位优秀家庭主妇,她整日为一家人操持忙碌着,然而亚历山德拉对于母亲所做的家务活毫无兴趣,对于母亲为这个家所做的贡献毫无感激之情。男性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改造征服自然的一些活动像开垦种植、制造产品等是属于生产(production)领域,它可以给人类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像操持家务这些活动是属于再生产(reproduction)领域,生产活动高于再生产活动。亚历山德拉在生产领域的积极参与,在再生产领域的缺席,清晰反映了亚历山德拉男性化的二元对立的等级思维模式。
这一时期女主人公对待土地的态度也带有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亚历山德拉在“分界线”上辛勤耕耘种植,饲养牲畜,然而她所做的这一切并非源自她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而是为了让她爱的小弟弟埃米尔能走出这块土地。正如她对卡尔所说,“在父亲的孩子里面,总算有一个能适应外面的世界,没有栓在犁耙上,有着与土地无关的自己的个性”[2]112。当分界线上其他农民因为经营不善而纷纷卖掉自己的土地时,她让她的弟弟抵押贷款购买进大量的土地,她对土地的热情和关注都是因为经济利益。“不出五年,我们这的地一定比他们的贵一倍”[2]38。如果除人以外的任何生物都被按照其对人类的用途来划分价值,以满足人类最大利益,这种“万物皆为我用”的思想,就是男性中心主义[4]。亚历山德拉这种把自然当作利己手段而不是以实现自然内在价值为目的的行为,反映了其意识中男性自我与自然他者之间的对立,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二)对“他者”的接受与认可
恋人卡尔的的回归以及与艾弗和麦丽的交往,让亚历山德拉对女性与自然逐渐有了新的认识。
亚历山德拉少年时的好友卡尔在多年后回到亚历山德拉身边,她的两个弟弟罗和奥斯卡因为担心姐姐与卡尔结婚后她的财产会落入他人之手,完全不念及姐姐为这个家庭所做的牺牲,置姐姐的幸福不顾,一起自私粗暴地反对姐姐与卡尔交往,甚至要求将她的财产转移给他们。“一个家庭的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一家男人的,不管证书上怎么说”[2]91罗和奥斯卡对姐姐恋爱和财产问题的粗暴干涉反映出女性在男权社会所遭受的偏见和压迫。在此情形下,女主人公意识到虽然她是一家之长女,在男权社会中她也不能免受性别歧视,她不再作为男权意识的代表,也不甘忍受男权的压迫,毅然决定捍卫自己作为家庭成员和独立女性的正当权益。对父权制世界观的不满和反抗,促进了亚历山德拉思想的转变。
与热情美丽活泼的麦丽交往使亚历山德拉进一步认知接受了女性身份和女性气质。小说中的麦丽具有完美的女性气质,她喜欢家居布置,热爱自然,对野外的玫瑰、路边的野草,池塘里的野鸭都充满了感情,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和麦丽渐一起参加社交活动,向她学习如何布置家居,如何打扮自己。随着与麦丽交往的加深,亚历山德拉逐渐认识到女性特质的魅力,自身的女性气质也被焕发出,其女性自我意识在逐渐觉醒。
亚历山德拉与艾弗的深厚友谊则促进了她自然观念的转变和生态意识的产生。小说中老艾弗住在天然的山洞里,他热爱自然视一切生灵为他的姐妹,他甚至称獾为他的妻子。如果动物生病了,他会一直不停哼哼,好像病痛是在他身上似的,他了解自然就如了解自己的身体一样,可以说小说中的艾弗本身就是自然的象征。与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的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不同,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对自然真正的热爱在于发现自然本身内在的价值,而不是看它对于人类是否有用。小说中的艾弗从未想过利用自然、破坏自然,他所展现的是对自然真正的关爱和与自然的相互依赖。然而,这样一个自然之子却被文明社会所不容,被认为是“疯子”,遭受嘲笑。只有亚历山德拉相信他,会去听他讲关于他和动物之间的种种神奇故事,向他请教如何种植庄稼,照料牲畜,并在他破产时收留他、照顾他。在艾弗的引导下,亚历山德拉开始审视自己的自然观,并逐渐与自然有了亲密交流。亚历山德拉把住处装饰得像广阔无边的大花园,在这里文明与自然的隔阂开始模糊。她经常静下来聆听来自土地的声音,充满柔情地回忆起曾经在池塘边观看到的那只悠闲的野鸭。小说中野鸭是一个重要意象,象征着“女性和自然”[5]。亚历山德拉对野鸭的回忆,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对,是亚历山德拉对自然发自内心的喜爱与亲近,表明亚历山德拉逐渐开始认识自然的内在的价值,自然不再是作为一个低等的他者而存在。
(三)回归“生态”自我
埃米尔和麦丽的惨死给亚历山德拉带来巨大的精神打击。悲剧促使亚历山德拉重新思考埃米尔和麦丽之间的感情。她开始理解这对年轻人,甚至于对凶手弗兰克她也尝试着忘掉仇恨,去理解他。这个时期的女主人公正经历逻各斯(理智)与厄洛斯(情感)的冲突。她开始意识到男性中心主义思维的片面性,意识到相互理解和依赖的重要性。
在伯格森家的墓园里,悼念埃米尔的亚历山德拉遭遇到一场暴风雨。这是亚历山德拉与自然的一次身体和精神最直接的亲密接触,雨淋在她的身上,“自然之子”艾弗站在她的身旁。这一幕有着特别的意义,“雨滴在身上的甜美感觉,让人回想起当娃娃时候的感觉。它把你带回到还没出生前的混沌黑暗中”[2]146。雨水是自然和母亲体液的象征,此次淋雨于亚历山德拉而言是一场心灵的洗礼、精神的重生,表明她的“个体意识在自然/母体之内开始消融,承认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是自然的一部分”[6]。正如艾弗所言“当肉体的眼睛闭上时,心灵的眼睛睁开着”[2]152。
墓园淋雨之后,女主人公坦然接受了恋人卡尔的求婚,对之前一再出现的性梦,也不再感到恼怒,她已经坦然接受其为身体的一部分。而对于土地她也有了新的感悟,对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有了更深层的认知,正如她对卡尔所言:“我是属于土地的,现在尤其如此,人们只有热爱土地、理解土地,才能与土地共生……”[2]169。
与男性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攫取人类利益的工具不同,此时的亚历山德拉认识到自然与人类是相互依赖存在的,自我是在与所有其他生命的相互关联、尊重和关爱中体现的,至此亚历山德拉对女性及自然的认知经历了从“男性”自我到“生态”自我的转变,女性和自然的关系变得真正和谐、融洽。亚历山德拉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地母亲”。
三、结语
文本中亚历山德拉生态女性意识的发展,体现了作家本人对女性和自然关系的探索与思考。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凯瑟笔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已越来越难寻,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重新解读凯瑟作品,有助于我们反思一直以来人类对自然功利的工具主义态度,重新思考人类该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
[1]O'Brien,Sharon.Willa Cather:the Emerging Voice[M]. New York,Oxford:Oxford UP,1987:6.
[2]薇拉·凯瑟.啊,拓荒者![M].资中筠,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3]Woodhouse Annie.Fantastic Women:Sex,Gender and Transvestism[M].Hampshire:Macmillan,1989:70.
[4]Murphy,Patrick D Literature,Nature and Other Ecofeminist Critiques[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28.
[5]Hively,EvelynHelmick.SacredFire:WillaCather's Novel Cycle[M]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4:45.
[6]周铭.从男性个人主义到女性环境主义的嬗变:薇拉·凯瑟小说《啊,拓荒者》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2006 (3):57.
(责任编辑:张锐)
[Abstract]This paper is an eco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roine Alexandra's self consciousness in O,Pioneers!At first,the heroine is a disguised man,and androcentric,regarding femininity and nature as entities to be triumphed over.Then she gradually realizes the intrinsic value and the nature of femininity,accepts femininity and identifies herself with the nature and finally transcends from her former“masculine”self to an“ecological”self.
[Key words]Willa Cather;ecofeminism;masculine self;ecological self
From Masculine Self to Ecological Self——The Development of Alexandra's Self Consciousness in O,Pioneers!
ZHU Ping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Najing Xiaozhuang College,Nanjing,Jiangsu 21000)
I106.4
A
1008—7427(2016)01—0052—04
2015—11—28
南京晓庄学院2013年度青年项目“薇拉·凯瑟作品研究”(2013NXY60)。
朱萍(1978—)女,安徽马鞍山人,硕士,南京晓庄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