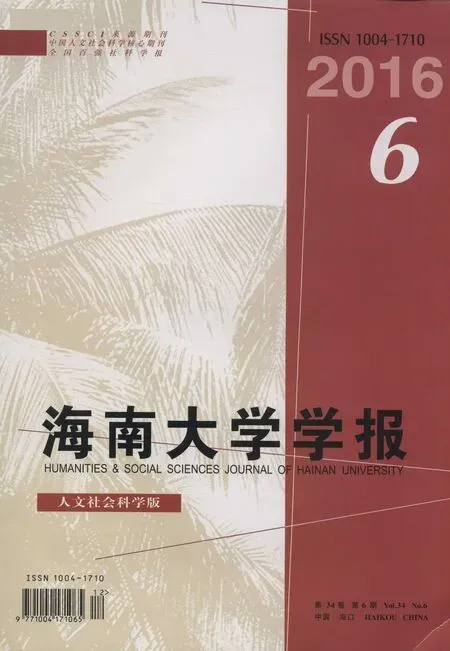民国时期词学对王国维“境界”之论的消解与辨析
2016-03-07胡建次
胡建次,杨 凤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民国时期词学对王国维“境界”之论的消解与辨析
胡建次,杨 凤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民国时期词学对王国维“境界”之论予以了不断的消解与辨析,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从本体意义上对王国维“境界”说予以反思;二是对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艺术表现之分予以论说;三是对王国维所倡“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予以辨析。它们彼此间相互依托、相互生发,从不同视域拓展、充实与完善了传统词境论的内涵,将传统词境论引入了一个新平台,标示出传统词境之论的新进境。
民国词学;王国维;“境界”之论;消解;辨析
1908—1910年间,王国维发表了《人间词话》。其中,他较为系统地对传统“境界”之论予以标举与阐说,鲜明地提出了“词以境界为最上”、“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隔”与“不隔”、“三种境界”等重要理论批评命题。之后,随着王国维在考古学、历史学、敦煌学、边疆史地学等领域学术建树的不断凸显、学术威望的不断攀升与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其早年所作《人间词话》亦受到学术界热捧,“境界”之论由此成为影响甚大的文艺美学学说之一,在文论界与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人们对王国维《人间词话》普遍持以推扬的同时,也有一些词论家针对王国维在理论总结与批评创新中所难免出现的不周延之处予以探讨、反思与补充、修正,从而使传统词境命题得到更为完善的建构,将对传统词境之论的认识不断予以了提升与深化,显示出重要的理论批评价值,对我国现当代抒情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文就此作些考察。
一、从本体意义上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反思
民国时期词学对王国维“境界”之论消解与辨析的第一个维面,是从本体意义上对王国维“境界”说予以反思。这一维面线索,主要体现在张尔田、胡适、唐圭璋、沤庵等人的论说之中。他们主要对王国维“境界”说能否成立、所论是否合理、其理论周延性如何等予以了具体的探讨。
民国中期,张尔田对王国维学术成就与为人行止甚为推崇。他论说世人在对王国维的推扬中实着力有偏,少论其思想渊源、学术体系与多方面建树成就等,而多谈《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年少时之作,他认为这是不得要领的。实际上,这几种著作,作者在后来都很少提及,并不引以为荣。其《与黄晦闻书》云:“比阅杂报,多有载静庵学行者,全失其真,令人欲呕。呜呼!亡友死不瞑目矣。……世之崇拜静庵者,不能窥见其学之大本大原,专喜推许其《人间词话》、《戏曲考》种种,而岂知皆静庵之所吐弃不屑道者乎!惟其于文事似不欲究心,然亦多独到之论。其于文也,主清真,不尚模仿,而尤恶有色泽而无本质者。又尝谓读古书当以美术眼光观之,方可一洗时人功利之弊。亦皆为名言。……呜呼!静庵之学,不特为三百年所无,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今静庵死矣,何处再得一静庵?”[1]261张尔田认为,王国维对文艺美学之道的最大贡献乃在倡导清彻空灵之意境创造与真情实意之创作态度;反对模仿,强调出新;反对虚饰,强调张本;提倡以纯粹审美的眼光观照古今中外一切文艺作品,以纯粹审美之求消解文艺欣赏与批评中的趋功近利之念。他实际上开始努力建构现代文艺理论批评体系,其对文艺之道的贡献是整体意义上的、多方面的,更多地显示出思想观念与方法把握的意义,而并不仅仅体现在少数几部青年时期所撰文艺批评与文学史著作之上。因此,对王国维的推扬应从整体上加以标树,避免只见树木而忽却森林。其《与龙榆生论词书》又云:“以为欲挽末流之失,则莫若盛唱北宋,而佐之以南宋之辞藻,庶几此道可以复兴。晚近学子,稍知词者,辄喜称道《人间词话》,赤裸裸谈意境,而吐弃辞藻,如此则说白话足矣,又何用词为?既欲为词,则不能无辞藻。此在艺术,莫不皆然。词亦艺也,又何独不然?”[1]288张尔田继续针对王国维“意境”之论予以辨说。他认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高标以“意境”为本,当世很多人受其影响,多推尚以意境表现为本位而贬抑具体用字造语之功。实际上,词作为独特的文学之体,是不可能不讲究语言艺术技巧的,语言是文学传达的工具,乃意境创造的载体,从根本上影响着意境的创造,丰盈着意境的呈现,是极见本体性的东西。语言与意境,均为文学审美表现之本,理应受到同样的重视。此论对王国维“意境”说内涵不失为一个有力的补充与修正。
胡适《致任访秋》对王国维所论“境界”之义提出质疑,认为其概括得“也不很清楚”。他归结在王国维那里,“境界只是真实的内容而已”,提出“我把意境’与‘情感’等并举,是要人明白‘意境’不是‘情感’等,而是作家对于某种情感或某种景物作怎样的观察,取怎样的态度,抓住了那一点,从那一种观点出发。”[1]390实在地说,胡适这一解说也并未将“意境”的内涵及本质特征阐说清楚,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曲解了“意境”之义,浅化了对“意境”这一理论命题的理解,但其论仍然体现出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反思消解之意,从一定方位上破解了王国维以“境界”为本的统系性,可引发人们不同方位的思考。
唐圭璋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标举“词以境界为最上”之论也予以辨说。他概括,这一论说是不准确与不全面的,词的创造是离不开创作主体情性韵致的,词境的构合与艺术生成亦须由创作主体内在的情感意绪融含于其中才能得以成就。其《评〈人间词话〉》云:“海宁王静安氏,曾著《人间词话》,议论精到,夙为人所传诵。然其评诸家得失,亦间有未尽当者,因略论之。王氏论词,首标‘境界’二字。其第一则即曰:‘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予谓境界固为词中紧要之事,然不可舍情韵而专倡此二字。境界亦自人心中体会得来,不能截然独立。五代、北宋之所以独绝者,并不专在境界上。而只是一二名句,亦不足包括境界,且不足以尽全词之美妙。上乘作品,往往情境交融,一片浑成,不能强分,即如《花间集》及二主之词,吾人岂能割裂单句,以为独绝在是耶?”[2]920唐圭璋进一步分析与辨说五代北宋词之妙,也并不完全体现在艺术境界的创造之上,而很多为人们所传诵,其实往往是因了名句效应,乃词中一两处生花妙笔激活了整个词作,赋予了词作以独特的审美意味。唐圭璋甚为重视与强调词中“情”、“境”的交融互渗,他从主客体相互结合的角度,进一步充实了“境界”说的理论内涵,将情感发生与艺术表现在意境生成中的作用凸显了出来。
民国后期,沤庵在王国维独标“境界”说及概括其本质特征乃在真实性呈现的基础上加以阐说。其《沤庵词话》云:“王静安论词,标举境界。所著《人间词话》,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而境界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余谓此人触景生情,感物造端;亦复融情入景,比物连类;故外界之物境与其内在之心境,常化合为一。当其写物境也,往往以情感之渗入,而熔铸为主观之意境,非复客观之物境。当其写心境也,往往借景色之映托,而寄寓于外界之物境,非复纯粹之心境。是故能写‘真景物’者,无不有‘真性情’流露其间;能写‘真性情’者,亦无不有‘真景物’渲染于外。心物一境,内外无间,超乎迹象,而入乎自然化境。自然化境者,词中最高之境界。”[3]286沤庵认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言纯粹之真情实性亦可创生“境界”之说,实际上是不太成立的。人们在感物触景中,其心境与外在物象往往是相互融合、不能分置的。外在之景致必然征显主体之情性,而主体之情性也必然在外在之景致中得到各样的体现,两方面是难以分开的。词的创作的最高境界,便是主体情性与外在物象的融合无垠,此乃高层次的艺术化境所在。沤庵之论,从文学创作发生及其因素构成的角度对王国维的境界生成之论予以质疑与反思,进一步对境界创造之论予以辨说,将对词境创造中情景构合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亦是富于一定启发意义的。
二、对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之分的论说
民国时期词学对王国维“境界”之论消解与辨析的第二个维面,是对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艺术表现之分的论说。这一维面线索,主要体现在胡适、浦江清、朱光潜、唐圭璋、吴征铸、沤庵等人的论说中。他们将对词境艺术表现的论题予以了切实的探讨,将对词作审美境界呈现的认识进一步引向了细致深入。
民国中期,胡适较早对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艺术表现之分予以论说。其《致任访秋》云:“静庵先生说的‘隔与不隔’,其实也说不清楚。我平常说‘意境’,只是‘深入而浅出’五个字。观察要深刻,见解要深刻,而表现要浅近明白。凡静庵先生所谓‘隔’,只是不能浅出而已。”[1]390胡适以“深入而浅出”来解说“隔”与“不隔”之境的本质内涵,他认为,“隔”其实就是不能“浅出”,反之,“不隔”即为“浅出”而已,是在“深入”基础上的“浅出”。这当然大致可谓抓住了词之审美境界呈现的特点所在,是富于启发人的。但同样地,胡适对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之分的解释,也体现出不够准确与不全面的特征。在王国维心中,“隔”与“不隔”应该还有真切与否、是否如在目前之义的。胡适对王国维词学理论批评命题的解说还显示出不太到位的特点。
浦江清将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之说与其“两种形式”之论加以联系。他论断,“隔不隔”之说乃从文艺形式诉诸于人的心智诸能力的基础上引伸而出的。其以縠永之名所发表《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云:“明先生第一形式第二形式之论,则可以言先生隔不隔之说矣。余谓先生隔不隔之说,亦出于其美学上之根据。何以言之?曰自然之景物,其优美者如碧水朱花,宏壮者如疾风暴雨,其接于吾人之审美力也,直接用第一形式,故觉其真切而不隔。一切艺术,以必须用第二形式而间接诉诸吾人审美力故,故其第二形式若与第一形式完全一致和谐,则吾人恍若不知其前者之存在,而亦觉其意境之真切而不隔。反是,二种形式不能完全和谐一致,则生障蔽。而吾人蔽于其第二形式,因不能见有第一形式,或仅能见少分之第一形式,皆是隔也。”[4]174-175浦江清认为,所谓“不隔”,即为真切之境,其意象运用与语言表现鲜明生动、具体实在,直接诉诸于人的审美感受力;而所谓“隔”,则为晦涩或浮泛之境,是文艺作品所运用意象或所用话语与人的知觉感受力存在更多的距离,更需要借助人的其他心理因素如记忆、表象、想象、理解等充分参予其中。浦江清进一步认为,“隔不隔”之说的本质关键在艺术表现之真实与否,“真”即能“不隔”,反之,“不真”即为“隔”。作者对现实生活感受体验的真实与否和创作态度的真诚与否,是作品“隔”与“不隔”显现的根本所在。其云:“且隔不隔之说,与真不真之说,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未有真而隔,亦未有不真而能不隔者。故先生隔不隔之说,是形式之论,意境之论。而真不真之说,则根本之论也。文学之真者,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如在目前,未有或隔者。凡诗词砌垒则隔,故梦窗之词最隔。强棣事则隔,故山谷之诗视东坡稍隔。古诗名篇少用典,故不隔。诗品所谓‘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者是也。凡标举兴会不屑屑词藻,则不隔。”[4]175浦江清概括造成“隔”之意境表现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味堆砌辞藻,有碍兴会直入之意;二是盲目寓事用典,炫弄与显摆所谓的一点知识学养,前者如吴文英之词,后者如黄庭坚之诗,它们都典型地体现出“隔”的审美特征,都是少见兴会直观之意的。浦江清从创作主客体因素及功能与艺术表现的联系角度,对文学意境呈现的审美特征作出了较为合理的阐说,是甚富于启发意义的。
朱光潜从文学创作所用意象与所表现情趣的关系角度,也对“隔”与“不隔”的本质内涵及特征予以解说。其《诗的隐与显》一文云:“依我看来,隔与不隔的分别就从情趣和意象的关系中见出。诗和一切其他艺术一样,须寓新颖的情趣于具体的意象。情趣与意象恰相熨贴,使人见到意象便感到情趣。便是不隔。意象含糊或空洞,情趣浅薄,不能在读者心中产生明了深刻的印象便是隔。比如‘谢家池上’是用‘池塘生春草’的典,‘江淹浦畔’用《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典。谢诗江赋原来都不隔,何以入欧词便隔呢?因为‘池塘生春草’和‘春草碧色’数句都是很具体的意象,都很新颖的情趣。欧词因春草的联想而把它们拉来硬凑成典故,‘谢家池上,江淹浦畔’,意象既不明了,情趣又不真切。”[4]175朱光潜认为,文学创造中凡所运用意象与所表现情趣相适相切的,便可归入“不隔”之列;而所运用意象与所表现情趣不能和谐一致的,则便归入“隔”之列。由此,朱光潜评说欧阳修词句“谢家池上,江淹浦畔”,认为其意象运用不够明朗,情趣表现不够真切,确乎体现出有些晦涩浮泛的艺术特征,是一般人所不易把握的。朱光潜对“隔”与“不隔”之本质内涵予以了更具理论性的阐释,其论说更体现出启发意义。
唐圭璋对王国维所言“隔”与“不隔”艺术境界之论亦予以细致的辨说。他破解王国维所崇尚与提倡的词作艺术表现以直致浅切之境为贵的主张,认为从作为艺术表现之法的“赋”、“比”、“兴”三者自古以来便同时存在而言,其相互间实际上是未有层次高低之别的,如果一味地以“赋”这一“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之法作为艺术表现的极致,则有违几千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与审美表现的传统,是与文学发展及批评历史不相符合的。其《评〈人间词话〉》云:“王氏既倡境界之说,而对于描写景物,又有隔与不隔之说,此亦非公论。推王氏之意,在专尚赋体,而以白描为主,故举‘池塘生春草,采菊东篱下’为不隔之列。夫诗原有赋、比、兴三体,赋体白描,固是一法,然不能谓除此一法外,即无他法。比、兴从来亦是一法,用来言近旨远,有含蓄,有寄托,香草美人,寄慨遥深,固不能谓之隔也。东坡之《卜算子》咏鸿、放翁之《卜算子》咏梅、碧山之《齐天乐》咏蝉,咏物即以喻人,语语双关,何能以隔讥之?若尽以浅露直率为不隔,则亦何贵有此不隔?后主天才卓越,吐属自然,纯用白描,后人难以企及;吾人若不从凝炼入手,漫思效颦,其不流为浅露直率者几希!”[2]921唐圭璋界定运用“赋”与白描之法应从凝重简练入手,如此,才不致于流为浅露直率、一览无余而导致词作缺乏应有的艺术魅力。唐圭璋对王国维在词境创造中所寓含艺术表现手法高低之分予以了破解,其论对传统词境之分与层次界划有着甚为重要的意义,将对词境呈现的论说推上了一个新的平台。
民国后期,吴征铸持同王国维以自然美妙之语为“可爱”之论,但他同时对寓事用典与人工煅炼的所谓“隔”的存在合理性也作出肯定。其《评〈人间词话〉》云:“是静安先生以目前语浑成语为不隔,凡用典用事或加以人工修琢者,皆隔也。(尚有多条皆本此立论,不具引。)夫自然美妙之语,孰不知其可爱?然而不能废用典用事者。推原其故,则有谋篇一道存焉。文章天成,妙手偶得。偶得者不能常得也。欣赏自然,忽有灵感,援笔铺笺以赴之。或有自然美妙之语出,一二语三四语无定也。然而文学一事,舍内容外,当有形式。一二断句,不能成篇。于是不得不以人事足成之。‘池塘生春草’诚可谓天籁矣。其对句‘园柳变鸣禽’,一变字不知经几许推敲而后定也。……”[4]176吴征铸论断,文学创造并不仅仅是由一些“自然美妙之语”散落其中的,它们需要连缀之功,需要将那些“目前语”或“浑成语”以巧妙适当的形式串合起来,以形成完整而富于艺术意味的篇什,因而,一定意义上的人工之巧,在文学创造中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十分必须的。自然天成与人工煅炼之语往往互为对应、互有补充之功,可产生出独特的艺术效果。吴征铸又针对称扬“不隔”而贬抑“隔”之艺术表现的观点加以论说。他论断“隔”与“不隔”之艺术境界呈现实际上是具有互补作用的。如果一个人作词全以追求“美妙”为贵,而完全摒弃一切人工的痕迹,这在事实上不仅是不可能的,亦是不真正了解创作甘苦之言,乃欺人之“大话”。其云:“古诗句数多寡不定,通篇自然浑成者,十九首以下,尚不易多见。况词之句数声调,均有一定之格律乎。故知一人一词。不隔语与隔语相杂者不得已也。今日论词而曰自然美妙之句为前人说完,故庸儒之说,若曰作词必完全求美妙,一切人工可废,则亦为不知甘苦之言,皆不足信也。自然与人工,隔与不隔,在一篇中配搭得宜,实有相得益彰之妙。”[4]176吴征铸从文学作品话语组合的角度,大力倡导自然与人工之语各有存在的合理性,各有其艺术表现的内在价值与优势所在,两者间是相得益彰的。吴征铸之论对王国维等人高张“不隔”而低视“隔”之艺术表现予以了切实的辨析,体现出对王国维所论的修正与消解意义。
沤庵将对词之意境表现的探讨与创作主客体交融的命题进一步联系起来,从情景交融的内在量度上来观照词境的生成及审美呈现。其《沤庵词话》云:“静安辩词境,又有‘隔’、‘不隔’之别。谓: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按此系《扬州慢》中之句)‘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上’,则隔矣!……白石‘酒袚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余谓凡词之融化物境、心境以写出之者,皆为‘不隔’;了无境界,仅搬弄字面以取巧者为‘隔’;‘隔’无‘不隔’之分野,惟在此耳。”‘谢家池上,江淹浦上’‘酒袚清愁,花消英气’,此数句皆仅在字面上搬弄取巧,谓之‘隔’也,宜矣!至若白石《扬州慢》下半阕,乃感怀杜牧而作。杜牧诗云:‘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笙?’今白石之过扬州也,(按白石于淳熙丙申至日过扬州)昔时之箫声,早已绝响,而美人名士,亦俱归黄土,惟桥与月尚如故耳!固有‘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之句,不可谓非‘语语都在目前’,而含思凄婉,有弦外之音,真可谓千古绝唱!静安仅以写景视之,自难领悟;其于白石之词境,殆亦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欤!静安尝推崇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谓‘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然则白石‘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融心境于物境中,其迟暮之感,沈郁之致,更是凄然欲绝;隔于何有?乃静安独赏南唐,贻讥白石!‘故知解人,正不易得!’(即用静安语)”[3]289沤庵认为,王国维仅仅是从用字造语与寓事用典的角度,来观照和把握“隔”与“不隔”之分别的,正由此,他才会将姜夔《扬州慢》中之句视为“隔”,而将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中之句视为“不隔”之列。实际上,这种区划是较为单一、片面与不准确的,“隔”与“不隔”之分,更多的应该体现在创作主体之心与外在事物的交融量度方面,如果创作者能将“心”、“物”二体有机地交融,即为“不隔”;反之,如果仅仅搬弄文字技巧以求炫目引人则为“隔”。这一区划原则才是更为内在与根本的。由此来看,姜夔《扬州慢》中语句寓情于景,“含思凄婉,有弦外之音”,实为“不隔”。沤庵的这一长段论说,可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借题发挥之意甚为明显,显示出对王国维“境界”之论构架的进一步破解与提升,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补充、完善了“境界”说的理论内涵。
三、对王国维所倡“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辨析
民国时期词学对王国维“境界”之论消解与辨析的第三个维面,是对王国维所倡“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辨析。在这一维面,朱光潜、沤庵、顾随等人展开了多样的论说。他们主要对王国维所倡“境界”称名是否切当、分类是否合理、不足之处何在等提出了各异的看法,不断丰富、拓展与深化、完善了人们对词作艺术境界呈现的认识。
民国中期,朱光潜对王国维所倡“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名予以辨说。他认为,王国维所用称名还是未能切中其所指与例证的。其《诗的隐与显》一文云:“王先生在这里所指出的分别实在是一个很精微的分别,不过从近代美学观点看,他所用的名词有些欠妥。他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就是近代美学所谓‘移情作用’。‘移情作用’的发生是由于我在凝神观照事物时,霎时间由物我两忘而至物我同一,于是以在我的情趣移注于物。换句话说,移情作用就是‘死物的生命化’,或是‘无情事物的有情化’,这种现象在注意力专注到物我两忘时才发生。从此,可知王先生所说的‘有我之境’,实在是‘无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都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其实都是‘有我之境’。我以为与其说‘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不如说‘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徘徊花上月,虚度可怜宵’,‘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都是同物之境。‘莺飞戾天,鱼跃于渊’,‘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兴阑啼鸟散,坐久落花多’,都是超物之境。”[4]20-21朱光潜认为,王国维所言“有我之境”,无非是主体“移情”于外物的结果,是创作主体将“我”之情感意绪投射于外在事物之中,通过各种内在机制的作用而创造出的独特艺术境界。其中的高层次之境恰恰体现为“无我之境”,呈现出凝神定思、物我同一的审美特征。至于王国维所言的“无我之境”,朱光潜则认为其审美本质乃在“有我”,因其“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都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其实都是‘有我之境’”。正由此,朱光潜主张以“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而替代“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名,以更利于见出其内涵,更体现出内在的学理性,亦更见合理规范。朱光潜进一步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艺术特征与审美机制予以解说与阐释。其又云:“王先生以为‘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同物之境’)比‘无我之境’(其实是‘有我之境’,即‘超物之境’)品格较低。但是没有说出理由来。如‘超物之境’所以高于‘同物之境’者,就由于‘超物之境’隐而深。‘同物之境’显而浅。在‘同物之境’中物我两忘,我设身于物而分享其生命,人情和物理相渗透而我不觉其渗透。在‘超物之境’中物我对峙,人情和物理猝然相遇,默然相契,骨子里它们虽是欣合,而表面上,却仍是两回事。在‘同物之境’中作者说出物理中所寓的人情,在‘超物之境’中,作者不言情而情自见。‘同物之境’有人巧,‘超物之境’见天机。”[4]12朱光潜认为,王国维之所以较为低视“有我之境”亦即“同物之境”,乃在于他认为其在情感表现与意致呈现上相对显得浅显直白,更体现出“人化”的痕迹;而在“无我之境”亦即“超物之境”中,其情感表现与意致呈现则相对显得幽微深致,更显示出自然天成的特征。朱光潜所倡“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之名,虽然仍然显得比较玄妙抽象,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还曲解了王国维所论之义,但其对王国维之论的阐释与补充意义还是甚为明显的,亦体现出对王国维理论概括的消解意义。
民国后期,沤庵对王国维所倡“境界”分类也予以辨说。他认为,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分类,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无我之境”在根本上是并不存在的,一切所谓的“无我之境”仍然为“有我之境”。其《沤庵词话》云:“静安于境界中,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谓:‘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余谓词人于物境心境,化合为一,而自成词境,在此境中,处处著我,断无‘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藉物境以写心境,因为‘有我之境’。至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此乃融心境于物境,初非‘以物观物’之谓。必有超脱之心境,斯得超脱之物境;此物境者,因为我心境之象征,而妙合于自然化境,安得遂谓之‘无我之境’!词人自有词心,以词人造词境,以词境写词心,固处处著我,初无‘无我之境’也。”[3]288沤庵认为,借助外在景物以抒写创作主体内心情意,这当然是“有我之境”的显著特征;但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这样的诗句,其在创作机制上并非“以物观物”的结果,创作主体之心并非变化到与外在事物处于同一层面。其实际的创作机巧乃在于主体将自己的内心情意尽数融合与化入于外在景象之中,通过外在物象的自然呈现而透露创作者之性情、心境或人生旨趣等。很显然,这其实并不是“无我”,而是创作生成过程中主客体在更高层次上的妙合无垠,因此,其艺术泛化之境也必然为“最高境界”。沤庵之论,从对词作艺术境界生成的分析探讨上,进一步破解了王国维“境界”说的构架体系,提示人们对文学意境类型作出更深入细致的观照思考。
顾随从词境划分能否成立的角度,对王国维所倡“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予以辨说。他论断这一分类也是不能成立的,并不能作为划分艺术境界之类别的标准,只是帮助人们认识诗词艺术表现具有相对的意义。其《驼庵词话》云:“静安先生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此语余不赞成。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不能成立,不能自圆其说。若认为‘假名’尚无不可,若执为实则有大错。盖王先生总以为是心即物,是物即心,即心即物,即物即心,亦即非心非物,非物非心,心与物混合为一,非单一之物与心。余以为心是自我而非外在,自为有我之境,而无我之境如何能成立。盖必心转物始成诗,心转物则有我矣。”[5]顾随提出,王国维将“心”、“物”二元混为一体,即“心”即“物”,即“物”即“心”,将“心”与“物”的内在本质差异予以了消弭,完全从“心”、“物”两者融合及其所呈现偏重的角度来加以类分,这是不太合理的。正确的概括应该是有“有我之境”而无“无我之境”,因为一切艺术境界的生成都需要创作主体将“心转物”,亦即将自我主观的情感意绪投射、注入于外物,通过外在物象的自然呈现而加以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无我”之境是不能成立的。顾随之论,从一定意义上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了人们对艺术境界划分的认识,启发人们对艺术境界构成及类型之分作出更为深入完善的思考。
[1] 杨传庆.词学书札萃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2] 张璋,职随让,张骅,等.历代词话续编[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3] 杨传庆,和希林.辑校民国词话三十种[M].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
[4] 周锡山.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
[5] 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232.
[责任编辑:林漫宙]
Deconstruction and Discrimination of Wang Guowei’s “Realm” Theory in the Field of Ci Poetic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of China
HU Jian-ci, YANG Feng
(Humanities College,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Wang Guowei’s theory of realm is constantly deconstructed and discriminated by the Ci poetics during the Republic Period of China, which mainly covers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a reflection of Wang Guowei’s realm theory from ontology, the second an adequate discussion of artistic expression proposed by Wang Guowei to distinguish “isolation” from “undividedness”, and the third a discrimination of “the context with or without oneself” advocated by Wang Guowei. These three rely on and function mutually to expand, enrich and perfect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theory of the Ci context from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hich introduce it to a new platform while marking its new progression.
Ci poetic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of China; Wang Guowei; theory of realm; deconstruction; discrimination
2015-12-31
I207.23
A
1004-1710(2016)06-009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