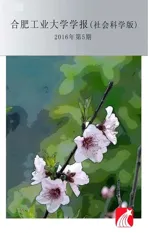论鲁迅作品的三种虚无
2016-03-07赵斌
赵 斌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275)
论鲁迅作品的三种虚无
赵 斌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275)
鲁迅作品中有三种虚无,分别聚集在麻木大众、消极启蒙者和积极启蒙者等三类人物身上,其中只有积极启蒙者才能够代替鲁迅“说话”。鲁迅作品人物的虚无思想不能等同于鲁迅本人的虚无思想,作品展现人物的虚无是作者自我审视的手段,是为了超脱虚无。
鲁迅作品的三种虚无;精神之死;超脱虚无;麻木大众;消极启蒙者;积极启蒙者
有关鲁迅虚无思想的研究比较多,且研究者往往另辟蹊径,其观察角度令人耳目一新。如汪晖[1]等学者从“历史中间物”角度来解读鲁迅的绝望和虚无;张典、彭小燕和周礼红等各自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存在主义和佛教文化等不同角度来探讨鲁迅的虚无思想。但是,笔者认为,学界对鲁迅的思想复杂性还没有充分认识,对中、西方文化及佛教文化等因素在鲁迅虚无思想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做充分的综合性的考量;对鲁迅前后思想转变的剖析还不充分,个人际遇及历史环境等因素对鲁迅虚无思想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梳理;对意识形态在鲁迅研究中的影响的认识还不足,原因在于此问题牵涉到鲁迅的再评价,以至于有些学者对鲁迅思想中的虚无有意淡化甚至掩饰。更为关键的是,学界对鲁迅文本的分析还不够精细,对作品中人物的虚无思想与鲁迅本人的虚无思想没有做精心地区分,以至于对鲁迅虚无主义的认识还不够精确。
笔者以为,鲁迅作品人物的虚无思想不能等同于鲁迅本人的虚无思想,作品展现人物的虚无是作者自我审视的手段,是为了超脱虚无。就好像一个人有意撇清“幼稚”,是为了“成熟”一样。本文立足文本阐释视角,通过剖析《野草》[2]96-113*后文涉及《野草》的内容,皆为同一出处,不再一一标出,见参考文献[2]。等作品,试图理清鲁迅复杂多变的虚无思想,梳理出鲁迅作品中的三种虚无,以区分出鲁迅的虚无思想与鲁迅作品中的虚无思想的具体差异。
一、鲁迅作品中的三种虚无
鲁迅作品中的虚无思想很复杂,也很怪异,不易于索解。长期以来,也正是这种独异性引起了接连不断的学术纷争,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鲁迅思想里有没有虚无?二是鲁迅思想里的虚无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果有消极的思想,所占比重有多大?第一个问题已经不重要,鲁迅思想中的虚无已经得到广泛的确认,论争的焦点集中在第二个问题上。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学者对鲁迅作品中的虚无刻意地掩饰或忽视。如,冯雪峰把《野草》中的黑暗、空虚、孤独等消极因素简单归结于社会客观环境方面,间接影射到鲁迅的个人主义方面,从而导致鲁迅“不能正确地把握当时的现实的发展”[3]。和冯雪峰对鲁迅虚无思想的明显掩饰不同,王瑶从鲁迅虚无思想的积极方面考察鲁迅作品,认为《野草》中的虚无是鲁迅意欲解剖、批判、并与之决绝的思想方面,预示着鲁迅在“思想发展的道路上将有一个极大的飞跃”[4]。李何林和王瑶见解相似,他比较理性地认为:“《野草》的主导思想倾向也是积极地战斗,讽刺和批判;只是……有时有一些消极的空虚失望和黑暗的重压之感,这是作者思想的另一个侧面,……是作者勇于自我革命而‘解剖’出来的思想。”[5]应该说,放在整个鲁迅研究史来考察三位学者,他们的评价基本上符合历史性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不受潜在的意识形态及鲁迅的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一种简单的逻辑、思路、话语轻轻化解了《野草》的消极面。”[6]这个总结是一针见血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实”评论?上文中分析的历史成因只是部分原因,没有对鲁迅作品中的几种虚无做思辨性探讨是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鲁迅作品中有三种虚无,分别聚集在作品中的不同类型的人物上。具体分析如下:第一,鲁迅作品中的虚无型人物大致可以归为三类——麻木大众、消极启蒙者和积极启蒙者,其中,积极启蒙者才能够代替鲁迅“说话”。第二,作品中的三种虚无紧紧纠缠在一起,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挑战,致使学界为此争论不休,纠缠不清。概而论之,麻木大众和消极启蒙者的虚无是反面的、消极的,而积极启蒙者的虚无是正面的、积极的。第三,消极的虚无是社会的病象,用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积极的虚无是生活的痛感,确证灵魂不死、精神不死。下面将具体讨论三种虚无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鲁迅思想中有消极的虚无意识是毋庸置疑的,也并不可怕。因为,一个人思想中有一些虚无意识是很正常的;但不敢正视一个人思想中的虚无意识却是不正常的。有些评论者身上似乎有“虚无主义恐惧症”,不能正确看待虚无主义问题,是不正常的。白培德曾对此做过尖锐批判,他说:“我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常与我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理想主义,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很害怕虚无主义。但这两种主义是同生同灭的。你越想追求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你就越可能造成一种非常危险的虚无感和失落感。”[7]这无疑是非常有洞见的,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当然,不能一概而论,邵荃麟对鲁迅作品的虚无思想的批评就比较公正,他认为,“在这些刹那中,鲁迅先生的心境确是绝望者的心境,确是虚无主义者的心境。”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断定写《野草》时期的鲁迅先生纯然是这种心境……”[8]他的话有两层意思,首先,人都会有刹那间的虚无感受;其次,作品与作者本人尚有距离。
鲁迅一生中有两个人生低谷期。在北京绍兴会馆这段非常孤寂煎熬的日子,鲁迅抄古碑,读佛经,心境百无聊赖、虚无静寂,但这段非常时期却使鲁迅参透了中国政治文化的隐密。鲁迅感到中国犹如一个封闭而又极难摧毁的“铁屋子”,似乎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然而,虚无心境有时候让人更加警醒,也能够催生出生存的智慧来,“鲁迅在这段时间并未成功地‘麻痹’了自己的灵魂,他实际上抓住了这段精神压抑的时间,从不断积累的文化资源中建立某种可资参考的框架,在其中寄托他生存的意义。”[9]29李欧梵的分析是真实可信的。鲁迅另一个人生低谷期是写《野草》的这段时间。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转瞬即逝,战友们流离失所、各奔东西,鲁迅有点茫然,刹那间地迷失方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感到空虚”意味着对启蒙这一行动产生了质疑,也在做深刻地反省;“空虚”则体现了在虚无状态下体验到的“实有”。鲁迅在回忆他写作《野草》的心境时写到:“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10]透过这段伤感、沉痛的文字,我们能够体会到鲁迅那时的“颓唐”和无助。也就是说,“鲁迅的虚无遭遇、虚无沉潜有他独特的悲苦、无奈,有他被逼于困境之时对自我生命价值缺失的惨痛自觉,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尼采体认虚无时的兴奋,直至自负自傲,更没有海德格尔、萨特认知世界以及生命虚无时的那份冷静、坦然。”*见彭小燕《重塑现代人类的生命信仰——“19-20”世纪的存在主义思想与鲁迅的精神之路(1-4)》,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05,第10至12期。这无疑是比较富有洞见的看法。
鲁迅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早在1907年,周作人就曾奉鲁迅之命在《天仪报》上著文探讨虚无主义,他认为:“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枝,去伪振弊,其教至溥。”[11]从这件事看,鲁迅意在探寻解剖中国历史和社会、解剖中国国民性乃至人性弱点的有效武器。正如雅斯贝尔斯所强调的,“事实上,虚无主义是一种为寻求真实存在所需要的一种解脱。”[12]鲁迅把虚无主义看成是一种认知社会的工具,有其积极作用。格尔文认为:“虚无主义的所谓经典含义是与实证论同义的。即:除了直接被感知、所观察的事物外,对一切都否定。”[13]这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是鲁迅乐于接受的,就好像《求乞》的结尾一样,“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因为,“空虚”确证了“曾经存活”,“曾经存活”能够呈现一种状态,一段历史,能够延展生命的意义。很多时候,鲁迅用“死”来确证“生”,用“死”来确证不一样的“存在”。“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而这反抗的意义却无法确证,因为鲁迅“自有我的确信”[14]。
二、虚无——精神之死
《墓碣文》是《野草》中最能够凸显鲁迅虚无思想的篇章,它延续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意志。诗用墓中的僵尸意象来表征“绝望”,来隐喻僵化的中国文化;用蛇来表征无法逃离而又与腐朽文化同逝的哀痛。《墓碣文》表达了鲁迅一种无法抹去的黑暗怨恨情绪和一丝走投无路的无奈。在《坟》的后记中,他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15]200这有“向死而生”的意思,但更多的是“彷徨”与无奈。
鲁迅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6]人似乎一直走不出这种循环的历史。鲁迅看清了中国文化缺乏诚和爱,对这种“瞒和骗”也是深恶痛绝之的,他认为,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并且,中国人“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15]254在鲁迅看来,现实中的中国文化是僵死的,有着“劣根性”的国民精神也已经死亡。从鲁迅作品人物来看,麻木大众和消极启蒙者大都掺杂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体验的鲁迅从两类人物身上发现了这个惊人的秘密,不免生出虚无的情绪来。
阿Q、奴才和无数看不清面目的看客可归于麻木大众这个人物类型。阿Q是麻木大众的典型代表,其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僵死文化的变种,尤其荒唐可笑的是,阿Q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宿命式的结局掩盖不了生命的虚无。《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奴才似乎比阿Q“刁滑”得多,他戏耍、背叛了一个夏瑜(《药》中的人物)式的人物——傻子(一个积极的启蒙者)。所以说,“奴才们”“是羊,同时是凶兽;但遇见比他们更凶的凶兽时便显羊样,遇见比他们更弱的羊时便显凶兽样。”[17]《颓败线的颤动》中的母亲遭遇与傻子相似,母亲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换取食物养育儿女,儿女长大后却不知报恩,并且用“脸面”“道义”来辱骂母亲,这正是“饮过我的血的人”反过来嘲笑、攻击我的以怨报德行为。《药》中就有这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畸形的文化现象。如,在小说中有一处写道:“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2]54
还有一些此类人物写得很隐晦,但似乎最能够表现鲁迅对虚无的敏感体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如《风筝》的结尾写道:“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风筝》已经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里。一般,这篇文章的主旨被理解为:风筝只是课文的线索,但透过“风筝事件”,“我”对小弟天性的虐杀是令人惊悚的,课文同时也控诉了封建宗族制度摧残儿童的罪恶。并且,比较一致性的见解都认为作品是突出作者的自省、自责和愧疚。如果这样理解也不是不对,但这篇散文诗就没有什么玄妙的了。本文认为,文本中“无怨的恕,说谎罢了”是理解诗篇的关键。小弟天性深受虐杀,但他还认为“我”是对的,且无任何怨恨,人物的麻木令“我”惊悚,因为“我”发现“弟弟”和阿Q、奴才等人物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我”在“弟弟”身上发现了前文中提到的“僵尸文化”,这似乎是中国文化的天大秘密。
还有一类麻木大众是无数看不清面目的看客,他们的无聊、虚无更令鲁迅怨恶。如,“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复仇》)鲁迅在这里深陷“无物之阵”而又对“无物之阵”发动一场痛快淋漓的复仇行动,但反抗的结果似乎毫无意义,一切终将走向虚无。无怪乎,鲁迅会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44另外,鲁迅对求乞者是深恶痛绝之,在鲁迅眼里,“这种虚假做戏也是导致整个人与人之间隔膜、缺乏爱和温暖的重要原因,并加强了这个世界的地狱感。”[18]
相对于麻木大众,消极启蒙者的虚无比较复杂。消极启蒙者是最先醒来的麻木大众,作为启蒙者,一开始他们是积极启蒙者。但启蒙的残酷现实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逐渐感觉前途渺茫,以至于萌生出虚无的情绪来。狂人、吕纬甫、魏连殳、娜拉、子君、涓生、《祝福》中的“我”和《过客》中的老人等可归于这类人物。《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的吕纬甫、魏连殳曾是无所畏惧的战士,但革命高潮过后就消沉、退缩了。吕纬甫变得畏畏缩缩、敷衍了事、苟且偷生;魏连殳以玩世不恭的心态,以畸形的自戕向社会作了“困兽之斗”。最终,他们都没能够走出“铁屋子”。娜拉、子君和涓生等人物结局也是一样,梦醒以后,不知道路在何方。《祝福》中的“我”也回答不了祥林嫂的“天问”,只能够搪塞,“唉唉,见面不见面呢?……”“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2]122最终,“我”的麻木不仁加速了祥林嫂的死亡。如果麻木大众带给鲁迅的是深陷“无物之阵”而不能救赎的虚无,那么消极启蒙者带给鲁迅的却是“自毁长城”而无法自救的虚无,因为鲁迅也是启蒙者中的一员,在人生困境的关键时刻,他似乎也无法预知未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吕纬甫有点类似,吕纬甫是一只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的苍蝇,狂人病愈候补去了,也回到了人生的起点。这似乎是启蒙的悖论:革命启蒙者未能够唤醒麻木大众,还成了麻木大众。而最吊诡的是,夏瑜的血成了治病馒头的材料,“傻子”打破“铁屋子”的英勇成为了“罪证”,成为“奴才们”邀功的契机……启蒙者满怀信心认为能够为大众谋幸福,大众却用沉默拒绝了启蒙。
革命竟然以启蒙者之死为结局,这令鲁迅很痛心,也无形中增添了他虚无的情绪。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我先前……在生活的道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19]这确实令人心寒。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夏瑜们死去了,魏连殳们死去了,狂人以病愈的方式更虚无地“死去”了。当然,夏瑜之死与狂人之死是不同的。夏瑜是积极启蒙者,是肉体之死,精神不死;狂人恰恰相反。套用一句诗来说,就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为什么启蒙这么难?因为,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却能唤起千万红军。“铁屋子”,也许本就是启蒙者自设的牢笼[14]。很多时候大众不愿意醒来,也甘愿做“治愈后的狂人”。《狂人日记》中有一处写道:“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2]49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就是自设的“无物之阵”,也是自造的“铁屋子”。
三、超脱虚无
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406这句话是针对小说创作来讲的,对其它文体的作品同样适用。因为,鲁迅的虚无思想大都是有感于麻木大众和消极启蒙者的消极、颓废而产生的虚无情绪。鉴于此,鲁迅揭示虚无的目的,在于体验虚无,更是为了超脱虚无。超脱虚无的方式有两个,一种是间接方式:揭示虚无,是为了逃离虚无,前文已经做比较充分的论述;另一种是直接方式:采取行动,抗争虚无。
笔者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文本现象:《野草》中的诗篇结构几乎都是转折性的,几乎都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这种巧妙的结构彰显了鲁迅对社会虚无病象的反驳,目的在于超脱虚无。《野草》文本在前面展开种种社会虚无病象,意在打破这种虚无逻辑。如解洪祥所说,鲁迅的孤独个体“既不沉醉于感官享受,也不信奉道德教条,更不皈依上帝,而是抗争,向命运抗争,向虚无抗争。”[20]为了说明这一情况,本篇把《野草》中的一些诗章的结尾统计如下:
《秋夜》: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影的告别》: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我愿意只是虚空
《希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雪》:但是,朔方的雪……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风筝》: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
《好的故事》: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
《过客》: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
《死火》: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
《狗的驳诘》:我一经逃走,尽力地走……
《墓碣文》: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她的追随
《立论》: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死后》:然而我终于也没有眼泪流下
《这样的战士》:但他举起了枪
在笔者统计的13篇诗章中有9篇直接用“但是”、“但”和“然而”等转折词进行转接的,其它四篇都有不同程度的对比。另外,在没有统计的诗章里有同样引人深思的转折结构,如《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值得注意的是,《狗的驳诘》、《墓碣文》等诗篇用“走”这一动词表达对虚无的逃离,“抒发了自己同虚无思想决绝的态度。”[21]“走”虽是无奈之举,但必定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姿态。“我一径逃走,尽力地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墓碣文》)。”“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狗的驳诘》)。”似乎,“生活就是一个走的过程,一直走下去,好完成那走向死亡的行程。因此,‘走’成为在‘无意义’威胁下的唯一有意义的行动。”[9]116也等于说“走”在这里是一种间接逃离虚无的方式,虽然还没有方向,也无法估算胜利的概率,但抗争的姿态难能可贵。
直接方式主要以积极启蒙者的行动为旨归的。过客、夏瑜、傻子、战士和《野草》中的“我”是这类人物。考虑到象征等修辞方式,《秋夜》中的“枣树”可归于此类型。在《野草》中,“走”有两个含义:一个是逃离,一个是行动;逃离是间接方式,行动是直接方式。《墓碣文》和《狗的驳诘》中的“走”是逃离,《过客》中的“走”是行动。鲁迅在给一个学生的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过客无疑是鲁迅的“代言人”。过客一边勇敢地抗拒着虚无,一边在积极想象虚无之后的革命出路。他不但走向坟(虚无),更关心坟以后的革命路径,他最可贵的精神是不知道路在何方却能够执意探寻。“《野草》的探寻……昭示的是历史性的精神企盼,或者说精神性的历史企盼。这企盼正是鲁迅精神发展的内在驱力,是鲁迅走出虚无的内在驱力。”[20]《野草》的写作处于“看清自己”、自我调整的需要……要从巨大的自我怀疑和绝望中走出来,在自我悲剧性的历史命运中作“绝望的抗争”[22]。如《淡淡的血痕中》所写:“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对鲁迅而言,这无疑是一场与虚无的生死肉搏。他希望成为一个像“枣树”一样的孤独战士,以一无所有的铁杆似的枝干,直刺着奇怪的、黑暗的、高而远的夜空,勇敢而孤独地抵抗着“虚无”。鲁迅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2]509是的,鲁迅愿意做那“孤独的雪”,因为他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也愿意“碾死在车轮底下”,只是为了“看见那车坠入冰谷中”。鲁迅对现实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坚定地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2]306
[1]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 鲁迅.野草[M]//鲁迅选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
[3] 冯雪峰.雪峰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96.
[4]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0.
[5] 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4.
[6] 彭小燕.“虚无”的意味——一份具有特定倾向的《野草》解读报告[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4-50.
[7] 李杨,白培德.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两位博士候选人的对话[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30.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学术资料汇编:第4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6.
[9]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M].尹慧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
[10]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2.
[11] 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52.
[12] 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24.
[13]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59.
[14] 韩明港.哀、怒与虚无——鲁迅的启蒙困境与生命困境[J].当代文坛,2010,(3):116-119.
[15]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 鲁迅.灯下漫笔[M]//鲁迅选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27.
[17]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3.
[18] 范美忠.民间野草[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31.
[19]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57.
[20] 解洪祥.走出虚无——鲁迅由孤独个体到文化战士的精神历程[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5-9.
[21] 孙玉石.<野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6.
[22] 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44.
(责任编辑 蒋涛涌)
Three Kinds of Nihility in Lu Xun's Works
ZHAO 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nihility in Lu Xun's works, which are embodied in three kinds of figures including the indifferent people, negative initiator and active initiator. Only the active initiator can “speak” on behalf of Lu Xu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nihilistic ideas of the characters should not be equated with Lu Xun's own nihilistic thoughts. The expression of the nihility of the characters is a means of self-reflection made by the author for the detachment of nihility.
three kinds of nihility in Lu Xun's works; death of spirit; detachment of nihility; indifferent people; negative initiator; active initiator
2016-03-27
赵 斌(1982-),男,安徽霍邱人,博士生。
I106
A
1008-3634(2016)05-008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