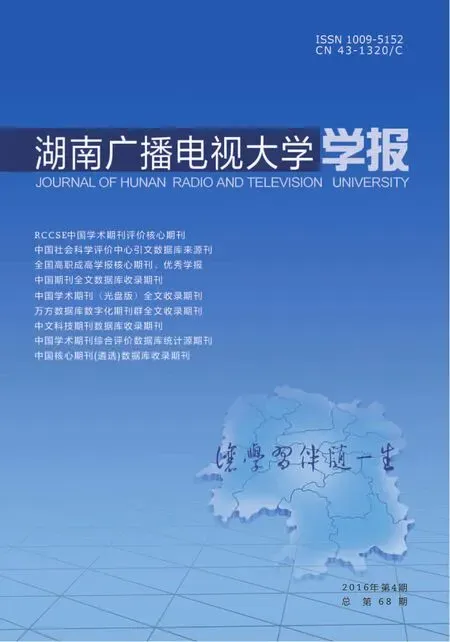先秦史传容貌品评之文化意蕴
2016-03-06徐恒
徐 恒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先秦史传容貌品评之文化意蕴
徐 恒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先秦史传中记载的容貌品评,将人物的形貌与品质、性格、命运相对应,体现了先秦时代人们对容貌的关注和由此而形成的审美观念。它所呈现的与甲骨卜辞相似的“背景—内容—结果”之结构模式,也反映出占卜知识对整个社会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春秋史官对卜辞记述手法的继承。《史记》历史人物形象的刻画、汉魏六朝的人物品鉴、后世叙事文学的类型化人物塑造,皆深受先秦史传容貌品评之影响。
先秦史传;容貌品评;审美观念;占卜文化
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物是历史著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左传》《国语》等为代表的先秦史传,置众多真实的历史人物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生活场景中,通过言行举止、心理活动、人生轨迹等诸多方面的展示,将他们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然而,通读这两部著作,便会发现,《左传》和《国语》对人物外貌的描写并不多见,且大都是从他人的品评中间接地展现出来。笔者通过对这类文字的对比,发现先秦史传中的容貌品评在内容和书写结构两方面都显示出一定的模式,并认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故不揣谫陋,聊作论述,祈请方家指正。
一、先秦史传容貌品评规律所体现的审美观念
先秦史传中的容貌品评,在内容上有一个规律,就是将品评对象的面部特征和内在质量、前途命运相对应。品评者通常认为,相貌奇伟的人会有美好的品格、光明的前途。例如,《左传·文公元年》载:“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榖也食子,难也收子。榖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周王室的内史叔服初会幼年的孟文伯(榖),便据其“丰下”(下颌丰满)的面部特点,断定他的后人必能在鲁国朝中不失其位。后来,果如叔服所料,孟文伯和他的后人孟献子、孟庄子、孟孝伯、孟僖子、孟懿子、孟武伯、孟敬子等人相继在鲁国政坛取得显赫的地位。
与之相反,长相丑陋、凶恶之人,则被认为会有不善的性格、不好的作为,甚至会遭遇恶报。《左传·文公元年》又有这样一段记载:“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大子商臣。”在子上看来,“蠭目而豺声”的商臣,必然有着残忍的天性,故不该被立为太子。果然,文公元年十月,商臣发动政变,“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
在这两个故事中,作为品评主体的叔服和子上,分别是北方周王朝的内史和南方楚国的令尹,二者之间虽山长水阔,却不约而同地以容貌的美恶来判断人物的质量、预言品评对象的命运。这说明,在春秋时代,“以貌取人”已成为一种流行于各个地域的识人手段。《国语》中对人物容貌的品评,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如《周语中》载:“简王八年,鲁成公来朝,使叔孙侨如先聘且告。见王孙说,与之语。说言于王曰:‘鲁叔孙之来也,必有异焉。其享觐之币薄而言谄,殆请之也。若请之,必欲赐也。鲁执政唯强,故不欢焉而后遣之。且其状方上而鋭下,宜触冒人。王其勿赐。若贪陵之人来而盈其愿,是不赏善也。且财不给。故圣人之施舍也议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议之。是以不主寛惠,亦不主猛毅,主徳义而已。’曰:‘诺。’使私问诸鲁,请之也。王遂不赐,礼如行人。”王孙说判断叔孙侨如的为人时,除了观察他的言行之外,也注意到他“方上而锐下”的相貌,从而推测他“宜触冒人”。这与前面所举《左传》中的两段记载如出一辙。由此可见,依据相貌的美恶来判断人物质量、预测个人命运、宗族兴衰、事件走向的品评方法,在春秋时代已经形成并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使用。
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面孔形态对个体性格特质的揭示是直观有力的,几乎每个人都能隐约感受到他人面孔所显示的某种性格模式或社会化信息。因此,面孔的这一功能很早便被察觉出来,并被运用到生活和创造实践中。”①这一“隐约感受”是否科学,姑且毋论,但《左传》《国语》中记载的以外部征象判断内在品质、人物命运、家族存亡的容貌品评思路,正说明先秦时代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并在自觉地使用面孔形态的这一功能。任何一种普遍性的自觉,都是在特定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的长期孕育下产生的,古人对外貌与个人品质、命运及事件发展方向之间对应关系的认识也不例外。在先秦史传中,凡被品评者认为美好的容貌,与之对应的质量或命运都是好的;而被品评者认为丑恶的容貌,与之对应的质量或命运都是坏的。透过这种“美对美,恶对恶”的品评方式,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古人对不同容貌的褒贬倾向。而这一褒贬倾向之发生与存在的原因,则在于整个社会对外貌的关注和由此而形成的审美观念。
首先,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了注重外貌的社会风气和好美恶丑的集体审美取向。这一点,可以从传世文献中得到有力的证明。在《诗经》的十五“国风”里,有许多吟咏人物美貌的诗句,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用鲜艳的桃花象征新娘的美貌,《卫风·硕人》用“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眉目盼兮”描写庄姜的五官和肤色之美,《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将美人的脸庞比作皎洁的明月,《郑风·有女同车》中的女主人公“颜如舜华”,“颜如舜英”……这样的篇章,在《诗经》中俯拾即是。一般认为,“国风”一类,多属各地的民间歌谣,对于了解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一时期各地的民间风俗、思想观念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描绘人物美貌的诗篇,看到这一历史时期各个地域的人对外表的重视和对美貌的喜爱。另外,庄子在《齐物论》中论及容貌美丑的绝对标准是否存在的问题:“毛嫱西施,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战国策·齐策》中“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的齐国大夫邹忌,曾多次向妻妾、门客询问“吾孰与城北徐公美”。先秦典籍中的这些文字表明,对容貌之美的关注和崇尚,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蔚然成风。既然美貌受到大多数人的喜爱,那么,丑陋的相貌自然就会遭到人们的厌弃。比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领华元在与郑、楚两国交战时被俘,被赎回后,还神气十足地监督老百姓们修缮城墙。于是,筑城者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华元大眼、腆腹、长须的滑稽相貌,成了歌者挖苦、嘲讽的对象。《左传·宣公十七年》载,晋国的跛脚大夫郄克出使齐国,“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郄子登,妇人笑于房”。《晏子春秋》中,身材矮小的齐国大夫晏婴出使楚国,“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这都说明,在先秦时代,长相不好的人常常会受到歧视。受到这种社会风气和集体审美取向的影响,先秦时代的人在面对他人容貌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主观的好恶、褒贬,从而在对容貌美丑的品评中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其次,先秦时代的人对容貌的关注,并未停留于对外表的欣赏或厌恶,而是在外貌美丑的判断中加入理性的思考,形成了外在与内在相统一的认识。前文已列举了《左传》《国语》中的一些记载,从中可以看到,容貌品评的侧重点并不在容貌本身,而在于通过对外在特征的观察来判断内在的质量或预言人物的命运。这样的判断在逻辑上之所以成立,“正是基于对人外在的物质形式与内在的精神灵魂的相通性的认识……正是因为如此,通过身体外在的有限形式,如体貌、言谈、举止便可去考虑内在的才能、德行及命运。”②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举一例。《国语·晋语五》曰:“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宁嬴氏。嬴谓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举而从之。阳子道与之语,及山而还。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从之,何其懐也!’曰:‘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若中不济而外强之,其卒将复,中外易矣。若内外类而言反之,渎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机,歴时而发之,胡可渎也!今阳子之情譿矣,以济盖也。且刚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惧未获其利而及其难,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贾季之难,阳子死之。”
宁嬴氏初次见到前来投宿的阳处父,便认为他是自己期待已久的“君子”,打算追随他去晋国,依据的正是好美恶丑的审美直觉,即“见其貌而欲之”。后来在交谈中发现此人表里不一,为避免“未获其利而及其难”,随即打消念头,“及山而还”。这一转变,恰恰是因为,宁嬴氏对阳处父的观察没有停止于对外在形貌的直觉感受,而是参照其言语作出理性的分析。“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若中不济而外强之,其卒将复,中外易矣”,也是他在理性思考之后对外表与内在之相关性的解释。
二、容貌品评的结构模式与占卜文化之关系
先秦史传中所记载的容貌品评,不仅在内容上存在外貌与性格、质量、命运相对应的特点,在形式上,也呈现出共同的模式。对照上文所举分别出自《左传·文公元年》《国语·周语中》《国语·晋语五》的四段材料,即可发现,这些关于容貌品评的记载,在结构上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品评的背景;判断性格、质量或预言命运的品评内容;容貌品评的应验结果。比如,楚国令尹子上品评商臣容貌的事件中,“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是品评的背景。“蠭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的论断,是品评的内容。后来商臣“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是容貌品评的应验结果。阳处父的故事中,“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宁嬴氏……及山而还”是品评的背景。阳处父与妻子的对话中论及容貌的部分,是品评的内容。“期年,乃有贾季之难,阳子死之”是品评之后事件发展的结果。除了已经列举的这几例之外,《左传》《国语》中其它关于容貌品评的记载,也都是按照“背景—内容—结果”的三段式结构模式书写的。容貌品评的内容,作为这种三段式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具有推断、预测的意味,与后面的应验结果相互照应。例如,《左传·宣公四年》: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
这段记载令尹子文品评越椒的文字,先交代容貌品评的背景,即越椒的出生。其次记述品评的内容,即子文根据“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的外在征象预言越椒“必灭若敖氏”。应验的结果记在同年七月: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伯棼射王,汰辀,及鼓跗,着于丁宁。又射,汰辀,以贯笠毂。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又《国语·晋语八》载:“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叔鱼的出生,是容貌品评的内容;他的母亲对其长相的描绘以及“必以贿死”的预言,是品评的内容;预言的应验情况,是《晋语九》中对叔鱼人生结局的一段记载:“士景伯如楚,叔鱼为赞理。邢侯与雍子争田,雍子纳其女于叔鱼以求直。及断狱之日,叔鱼抑邢侯,邢侯杀叔鱼与雍子于朝。”
这一“背景—内容—结果”的结构模式,和甲骨卜辞在形式上十分相似。按照前人的归纳,“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叙辞,又称前辞。即占卜的时间和贞人。命辞,又称贞辞。即此次占卜所问的内容。占辞,即商王(或子)看了卜兆后所下的判断。验辞,即征验之辞。”③如《合集》10405正曰:“癸巳卜,□,贞:旬亡祸?王占曰:‘往,乃兹亦有祟。’若偁,甲午王往逐兕,小臣载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在这条完整的卜辞中,“癸巳卜,□”是叙辞。“贞:旬亡祸”是命辞,问今后十天有没有灾祸。“王占曰:‘往,乃兹亦有祟。’”是说王看到龟甲烧灼的纹路后,预测将有不好的事发生,这是占辞。剩下的部分是占卜的应验情况,即验辞。如果将甲骨卜辞的各部分和史传中的容貌品评的“背景—内容—结果”结构相对应,则卜辞中的叙辞、命辞部分大体上相当于三段式结构中的“背景”,占辞部分相当于“内容”,验辞则相当于“结果”。可见,史传中记载的这些容貌品评,与占卜知识、巫史传统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第一,占卜在春秋时代的盛行,影响了容貌品评的思维机制。先秦史传中有大量关于占卜活动的记载,据统计,仅《左传》一书,“有关龟卜或筮占的详细记载就有19次,日常的卜问不计其数。”④这些记载表明,以卜筮来预言吉凶,作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知识,在春秋时代非常流行。“在当时,大到战争的胜负,迁都的利弊,小到人的生死,娶妻之合适与否,都要由卜筮来预测。”⑤这些占卜的活动,从整个过程来看,也可分为背景(占卜的缘起)、内容、结果(应验情况)三部分。例如,《左传·文公十一年》有一段关于战前占卜的记载:“鄋瞒侵齐,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庄叔,绵房生为右。富父终甥驷乘。冬十月甲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长狄攻打齐国,随即伐鲁,文公不知该不该命得臣率军,是此次占卜的背景事件,得到的吉兆是占卜的主要内容,鲁国在咸这个地方大获全胜并擒获长狄首领侨如,则是此次占卜的应验结果。
据《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在鄢陵之战中,晋厉公曾经用占卜来裁断作战的策略: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苖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必大败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射其元王,中厥目。’”……及战,射共王左目。
两国在鄢陵的对峙、苗贲皇的建议,是厉公占卜的背景,史官的言语属于占卜的内容,楚共王被射中左眼是应验情况。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其它占卜事件,大体上也都可以分为背景、内容、结果三部分,这和甲骨卜辞所反映的殷商时期的占卜并无二致,可见春秋时代的占卜预测知识,基本上是由殷商时期承袭而来。这类事件在史传中被大量记载,也反映了占卜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一种知识或思想,如果在某一时代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与信赖,便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生活于这个时代之人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依据外在形象判断性格、质量、命运的容貌品评,和以龟甲、蓍草、卦象预言吉凶祸福的占卜活动,在思路上十分相近;容貌品评的内容,又与占卜一样,具有推断、预测的性质。因此,占卜知识对品评者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容貌品评呈现出与甲骨卜辞相似的结构模式的重要原因。
第二,先秦史传叙述容貌品评事件的手法,是在巫史传统影响下,对甲骨卜辞记录形式的继承。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编纂《左传》《国语》所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春秋时代各国的史官记事。⑥而春秋时代史官的身份,又与甲骨卜辞的刻写者一脉相承。在殷商时代的巫史群体中,从事占卜活动的一类称为“卜人”,这些卜人在“占卜之前要把问题刻在甲骨上,占卜之后常常要把结果刻在甲骨上,所以常常既是巫又是史。”⑦他们的身份,兼具沟通天人的宗教性职能和文献载录的现实性职能,后世专门从事历史记录的史官,就是继承了后者并逐渐脱离巫的身份而形成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处在巫职和史职逐渐分化的过渡期,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虽然已经有了史官,但是当时的史官是为上层及祭祀占卜服务,其性质仍不同于后世的史职。”⑧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春秋时代的史官尽管已经开始从最初的巫史不分的状态下独立出来,但仍需从事占卜、祭祀、观象等宗教性的工作。比如,上文曾提及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会战中的那次占卜,其执行者便是晋国的史官;《国语·晋语一》中,晋献公讨伐骊戎之前,曾“命史苏占之。”有人统计,先秦典籍和《史记》《汉书》关于春秋战国史官活动的文字,“涉及史官祭祀与卜筮活动方面的记载有25项次,约占活动总项次的26.3%。”⑨由此可见,记录历史事件和从事宗教活动,都是春秋史官职掌的两个重要方面,他们和商代刻写甲骨卜辞的“卜人”一样,都有着巫、史的双重身份。而取材于春秋史官记事的容貌品评,又有着和甲骨卜辞相同的结构模式。这说明,先秦史传对容貌品评的载录,应该承袭了甲骨卜辞的记述手法。
三、先秦史传容貌品评的后世影响
先秦史传中记载的以外表特征来判断人物性格、质量、命运的容貌品评方式,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容貌的关注和审美观念。它所呈现的与甲骨卜辞相同的结构模式,反映了占卜知识对整个社会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尚未完全摆脱宗教职能的春秋史官对卜辞写作手法的继承。同时,它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借鉴了先秦史传中“以貌取人”的论人之法,运用于《史记》历史人物形象的刻画。比如,《秦始皇本纪》中,因出谋划策而受到秦王政礼遇的尉缭说:“秦王为人,蜂凖,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高祖本纪》称刘邦的长相“隆准而龙颜,美髯须”,吕公一看就知道他必将显贵,“因敬重之,引入座”,还将女儿嫁给了他。《越王勾践世家》中,范蠡寄书于文种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这种写法显然是由《左传》《国语》中继承而来。司马迁巧妙地将容貌品评运用于《史记》的叙事中,为历史人物在下文中的活动作了铺垫,使得人物的出场和结局遥相呼应,富有传奇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品评之风大兴。当时的人在品鉴人物时,十分注重容貌。魏代刘邵的《人物志》,是一部识别、评论人才的专著,集中反映了汉末至三国时期的人才识鉴理论,该书的《九征》篇云:“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刘邵认为,通过体型、气色、举止等外表特征,可以判断内在的性情、材质。另外,《世说新语·识鉴》中记载:“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卫玠年五岁,神衿可爱。祖太保曰:‘此儿有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容止》篇中也有许多对人物容貌的描写。这些都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容貌是识鉴人才、评论人物的重要依据。这种从表征推断本质的品评方法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至先秦史传中的容貌品评。
此外,先秦史传中的容貌品评,为后世文学作品中的类型化人物塑造开辟了道路。中国古代的叙事类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往往利用外貌描写来展示人物的主要性格或预示其命运、际遇。比如,《三国演义》第一回,为了突出刘备的王者气象,说他“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紧接着出场的张飞,长得“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活脱脱一副勇猛、鲁莽的武夫形象。随后亮相的关羽,则“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俨然一种忠勇、神武的大将风度。这一写人手法的滥觞,便是《左传》《国语》等史传作品中的容貌品评。
综上所述,《左传》《国语》中记录的容貌品评,有着深刻的文化意蕴,它与先秦时代的审美观念、占卜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对《史记》中历史人物的刻画、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后世文学的类型化人物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①张悦、卢兆麟:《论人类面孔审美的生物共性》,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②方英敏:《先秦美学中的身体审美和身体问题》,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61页。
③王宇信、魏建震:《甲骨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④张小龙、周来光:《简论〈左传〉占卜叙事的艺术功效》,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⑤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⑥如张居三《〈国语〉的史料来源》:“《国语》的编撰便是依据前代,尤其是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史官的记载。”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国语》文章是不同时代的各国史官早就写好了的,编者只是起到选篇、编辑的作用。”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过常宝认为:“春秋时的史官应该有两种载录方式。 其一是作为正式文献收藏在宗庙石室中,呈现给神灵和祖先的……其二是史官在自己职业内部相互传授的、更为详细的历史记录”,“《左传》则是根据《春秋》而有意继承、修改史官传闻之史而来。”载《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130页,第135页。
⑦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⑧吴晓筠:《中国的“原史”时代》,《华夏考古》,2005年第1期。
⑨林晓平:《春秋战国时期史官职责与史学传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王宇信,魏建震.甲骨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5]过常宝.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方英敏.先秦美学中的身体审美和身体问题[D].南开大学,2009.
[7]张悦,卢兆麟.论人类面孔审美的生物共性[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8]张小龙,周来光.简论《左传》占卜叙事的艺术功效[J].广西社会科学,2002,(5).
[9]张居三.《国语》的史料来源[J].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2006,(12).
[10]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J].文学遗产,2007,(4).
[11]吴晓筠.中国的“原史”时代[J].华夏考古,2005,(1).
[12]林晓平.春秋战国时期史官职责与史学传统[J].史学理论研究,2003,(1).
On the Culture Implication of the Appearance Evalu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XU Heng
The appearance evalu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combined people’s appearance, quality, character and destiny, which shows people’s focus on the appearance and aesthetic idea in that period. It presents a similar structural pattern in oracle inscriptions, that is, background-content-result, which reflects the impact of divination on people’s thinking mode and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of oracle inscription that the official historian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herited.The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s in Shiji, Han Dynasty and Wei Dynasty were all affected by the appearance evalu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 historical biography in the pre-Qin period; appearance evaluation; aesthetic idea; divination culture
2016—06—28
徐恒(1989— ),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K225
A
1009-5152(2016)04-0039-06